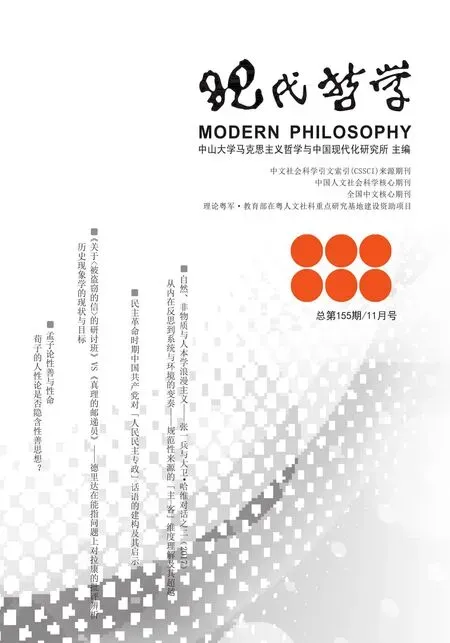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专政”话语的建构及启示
黄寿松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专政”话语的建构及启示
黄寿松
近代中国思想界民主话语纷呈,既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苏维埃)民主话语之争,又存在外来民主话语和本土民本话语之别。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借鉴传承创新,最终形成既异质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又有别于苏维埃民主的“人民民主专政”话语体系。这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合法性话语机制,又奠定了现代中国主流政治话语的基本底色。梳理该时期“人民民主专政”话语的建构历程,考察这一进程中国共产党对各种话语资源的取舍、融合和再造,应该可以为当前中国特色民主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历史资源和镜鉴。
民主;专政;人民;中国共产党
近代中国思想界民主话语纷呈,谱系复杂,既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苏维埃)民主话语之争,又存在外来民主话语和中国本土民本话语之别。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借鉴传承创新,最终建构了既异质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又有别于苏维埃民主的“人民民主专政”话语体系。话语具有型构现实的重要作用。“人民民主专政”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话语机制,而且奠定了现代中国主流政治话语的底色。梳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无产阶级民主”到“人民民主专政”话语的建构历程,考察这一进程中国共产党人对各种话语资源的取舍、融合和再造,应该有利于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历史资源和镜鉴。
一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后,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对民主话语的理解,主要囿于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基本观点。比如,李大钊指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正朝着无产阶级民主方向迈进,认为“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的时期”*《李大钊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7—108页。中国共产党颁布的第一个纲领也指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页。1949年6月,毛泽东在回溯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起源时指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帮助中国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另外,从国际方面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的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强权逻辑,引起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由向往转向怀疑,促使他们转身借鉴俄国的革命经验。如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钟情西洋文明,曾宣称近代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西洋式的新国家,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即“平等人权之新信仰”*《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48页。。但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权益的肆意践踏,揭橥西洋文明民主与人权的虚伪,促使陈独秀放弃对西洋民主文明的幻想。1919年12月1日,他在《新青年》的《本志宣言》中明确说“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同上,第427页。,并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第一次提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民主话语的分界,认为18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王权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而如今20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对资产阶级要求权利的旗帜。*同上,第449页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初,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弊病日渐暴露以及十月革命胜利的情况下,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逐渐放弃“德谟克拉西”、“平民”、“平民主义”等“五四”话语,转向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中的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范畴分析中国问题,但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襁褓之中,对中国革命的探索还处在摸索阶段,因此早期共产党人对这些范畴还不能够形成自己的理解,主要停留在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原生态层面,尚未扎根中国社会的现实。
中国共产党二大根据列宁殖民地半殖民地学说和远东大会的精神,制定了明确的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该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话语的建构,开始和反帝反封这一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主要体现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中。然而,对于这一“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及其国体形式,党内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纷争和变化的过程。1922年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认为,民主革命是要建立“民主政治”以代替“军阀政治”。所谓“民主政治”就是由民主派掌握政权,并认为在当时中国现存的各政党中,除中国共产党外,只有国民党是比较真的民主派。此时中国共产党期希冀民主革命成功后,建立国共两个民主党派联合执政的政权。然而到了同年7月发布“二大”宣言时,中共的认识似有所转变。该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中,不过获得一些自由与权利,还不是完全的解放。而且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使得资产阶级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抗资产阶级,实行与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具有强固的组织力和战斗力,这第二步目标是能在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实现的。这指出了民主革命的几种可能性,或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或是民主阶级联合掌握政权,或是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参见方敏:《“五四”后三十年民主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1页。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对无产阶级领导权认识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共和国”的认识日趋明晰,但是党内还是存在争议。陈独秀根据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分析,认为“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85页。;同时认为民主国家建设在人民权力之上,人民的权力必须集合在各种人民的组织里才可以表现出来,直接具体表现到政治上的只是政党。所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188页。。之后他再次强调,“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目前也只有这各阶级群起的国民革命是可能的。若是贪图超越可能的空想,实际上不能使革命的行动丰富起来,以应目前的需要,不但在本国的革命事业上是怠工,而且阻碍了世界革命之机运”*同上,第370页。显然,陈独秀主张在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意义上定性未来的“民主共和国”。
以瞿秋白、毛泽东等为代表,主张“民主共和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如毛泽东在1925年认为中国内外所遭受的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19 页。。192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始反省过去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分为毫不衔接的两个阶段的观点及其可能造成的贻误,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即是不断的努力,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1页。。加之自中共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一直所呼吁的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不仅使“民主共和国”具有“非资本主义前途”,而且初步具有后来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意味。
当时的共产党人对“民主共和国”的政权形式,也曾有过设计,比如主张“以人民团体亲自直接选派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军阀官僚包办选举的国会制度”,国民会议具有“接受全国政权”的意义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53、155页。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建立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就是上述构想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与“民主共和国”主张相适应,中国共产党此时还提出一系列保障民众利益的权利话语,如实行普遍选举、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男女一律平权、中央和地方重要的国家职员须民选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41页。,并且强调“民主共和国”的前途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
该时期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民主共和国”话语,既有经由“五四话语”和三民主义思想对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的汲取,又有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话语由最初的直接复制到适度的改造的转变,因而具有了新民主主义民主思想的雏形。其突出变化在于,中国共产党把民主的对象拓展至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国各革命阶级,并把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主权独立和对内反对军阀实现国内的和平,看成该时期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重要诉求。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开始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以及对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的因应来建构民主话语体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力量发展不平衡,只有首先促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团结以及国家的统一,才能实现民主革命的目标。但由于该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能够成长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独立力量,因此,在民主话语建构上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
二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革命的政党,便只剩下了共产党;革命的组织责任,便不得不落在惟一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肩上”*《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0页。。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调整民主话语策略,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新构想。
工农民主专政在当时称作“苏维埃”。经过摸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该时期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关于工农民主专政的构想:第一,中国共产党是苏维埃政权(工农民主专政政权)政治和思想上的领导者,苏维埃政权的正确组织,要以党的指导为条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08页。第二,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各级最高权力机关,全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苏维埃全部权力“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党在苏区的重要任务就是“引进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同上,第323页。;第三,苏维埃是对人民的民主与对敌人的专政的统一。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苏维埃政权需要使用强力去对付阶级敌人,但是对自己的阶级,如工农、贫民、职员、革命知识分子等大多数民众,“表现出来的只是最宽泛的民主主义”。*《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年,第259页。工农民主专政政权当时也同样强调权利保障,如宣布“在民众的苏维埃政权下面,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内的人民,凡年满16岁,对苏维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婚姻自由”“信教自由”等;对失业工人给以“劳动介绍与失业津贴”;“有受教育的权利”等;农民获得土地,不仅免除了地主的盘剥,而且基本的生存自由得到保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9页。
可见,该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农民主专政话语已经相对系统。它在政权的构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人民的主权地位及其享有的权利体系、民主和专政的相互关系等方面,都进一步明确、体现了中共民主话语建构的深入和成熟。*方敏:《“五四”后三十年民主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1—62页。同时,由于该时期国共两党已经公开决裂,因此中国共产党试图建立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新型民主政治,明确指出西方民主与苏维埃民主是两套异质的话语体系,并对这两种话语进行直接比较,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力,“而无产阶级国家的组织,则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其特点是接近民众,指挥灵敏,无互相牵制之毛病”;资产阶级所宣称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利益的私产,而“苏维埃的机关,则为真正的德莫克拉西,劳苦民众享有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解放”;资产阶级国家美其名曰的普选制,徒有其表,实际被资产阶级金钱势力包办,而“苏维埃的选举,则与之绝对相反”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页。
当然,该时期中共的民主话语建构,依然受到苏联话语较大影响。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工农民主专政思想的提出,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提出“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的目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370页。在1929-1931的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共产国际数次指示和要求中共中央成立苏维埃政权。“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792页。在共产国际的一再督促下,中共中央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内创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并指令“要有决心的使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十月革命节所召集的苏大会中产生出来,而不再延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89、370页。。因此,该时期工农民主专政话语,不仅深深打上苏维埃民主话语模式的烙印,以至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等范畴的使用,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间定于十月革命节等,都折射了当时苏联民主话语模式对工农民主专政话语的影响。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该时期还没有完全独立自主地建构民主话语体系,一定程度受到当时共产国际过于乐观地把苏联革命经验引入中国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工农民主专政思想上,也一定程度存有不切实际的倾向。比如,过分强调苏维埃政权中工人、雇农代表的人数,要求区乡苏维埃代表会议“工人雇农成分至少要占三分之一”*《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8、323页。。这显然不符合当时苏维埃政权主要建立在农村的现实,也不符合中国社会革命实际的特点。对此种盲从苏联话语的情形,毛泽东后来做出批评:“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代表大会。我们过去又叫‘苏维埃’,又叫‘大会’,就成了‘大会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4页。尽管如此,该时期工农民主专政话语毕竟为后来新民主主义民主话语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三
1930年代初,随着中日民族矛盾加剧,中国共产党因应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应地,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话语建构也与团结抗日的目标结合起来,提出新的“民主共和国”方案。
新的“民主共和国”话语的建构,同样经历一个酝酿成熟的过程。首先是将边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口号调整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大大扩展了民主实施的对象。毛泽东说,这就由过去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转变为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的政府,从而顺应团结抗日的新形势。*《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6-159页。然而,“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实施主要限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范围,随着抗日形势的紧迫,它在团结全国人民抗日方面还存有局限,也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全面参与抗战推动全国抗日局面的形成,因此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放弃“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话语,转而提出新的“民主共和国”话语,“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95页。。
新的“民主共和国”话语主要强调抵抗外来侵略,发展国民经济以减轻或免于人民生活的苦难,给予人民民主权利,有由普选权选出来的国会、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和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将国民党一党一派一阶级的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发动以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为目标的广大的民主运动。*《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6—257页。同时,为了团结国民党一致抗日,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共产党的“民主共和国”与国民党三民主义纲领的兼容性。他指出,尽管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与三民主义有区别,但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三民主义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9页。。该时期中间势力为了动员全国人民抗日,也要求国民党取消“党治”,结束“训政”。
然而,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一党专政,认为民主政治对外没有力量,国家只有对内实行专制独裁,才能对外强硬,拒绝中国共产党和中间势力的民主要求。中间势力权衡各种形势后,觉得要实现各党各派和衷共济一致抗日,还是要在民主上着力,用宪政来增加和谐和巩固团结。因此,抗战中期以后,中间势力先后发动两次宪政运动,并在运动中提出自己的宪政设想。为应付这种局面,国民党政府也改变原初反民主要求的主张,以宪政为幌子与各种民主诉求虚与委蛇。在这种形势下,既为了指导中间势力发起的宪政运动,又为了揭穿国民党政府的宪政把戏,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宪政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它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32—733页。这说明当时中国各派势力的角力对民主话语建构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之前“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表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封建专政的国家制度,资产阶级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以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均不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当时所要建立的只能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从国体看,它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5页。;从政体看,它是“民主集中制”,是“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7页。。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国情提出的比较明确的民主制度模式,从中能够管窥后来人民共和国的初步轮廓。根据“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话语,结合抗日根据地边区的实际,该时期中共还形成独特的“三三制”政权思想。
随着抗日的结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向建国转变。在经历初期国共双方和平建国复杂角力之后,内战终究未能避免。内战的爆发再次使得中国共产党重新思考中国的民主话语建构问题。194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推翻国民党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37页。。至此,中国共产党由抗战初期主张建立临时联合政府,转向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目标。之后,共产党对人民民主制度在原有民主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思考和建构,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话语。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做出明确界定,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并且要求“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不同”。*《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2)》,第13—14页。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专政话语的建构和理论论述基本完成。对人民民主专政话语的意义,毛泽东强调“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变成压迫平民的工具”,新的民权制度“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7页。,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景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至此,“人民民主专政”话语正式形成。
结 语
可见,民主革命时期“人民民主专政”这一话语的形成与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实力对包括国民党、中间势力和共产国际等在内的各方势力的因应,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各种民主话语资源融合与会通的产物。如果说孙中山是有所警惕地提出“以俄为师”,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则不断地以民主的、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话语诠释基于欧洲和俄国经验得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地位,又基于国情以及对中国社会不同势力的因应,灵活主张中国革命多阶级共存与多党派联合的民主革命性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大众联合进行社会革命的理论,逐渐演绎为多党派联合的民主话语,逐步将俄国工农大众单一阶级专政的苏维埃革命模式转换为中国众多党派和阶层广泛参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使得“人民民主专政”这一话语赢得民众、中间人士及诸多民主党派的广泛认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合法性话语机制。*参见黄寿松:《人民民主话语建设述论——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为中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2期,第199页。
到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时,“人民民主专政”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赋予中国人民诉求的新含义,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关于政治民主的概念。随着这些新含义的扩增,“人民民主专政”已转变为一个社会概念,不仅诠释了中国应建构一种怎样的民主,而且还包含了新的价值追求:它不仅是对封建专制与特权的消弭,而且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坚守,对实现社会平等与自由的期许;它既汲取了西方民主政治对个体权利保障的政治解放维度,又不同于简单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它既传承了中国传统群体和民本的意识,又不同于封建专制体制下的家国一统观念;既借鉴了苏联十月革命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积极元素,又糅合了民主革命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苏区或边区)的社会治理经验,从而创造性地重构了一种基于中国语境顺应中国政治现代化趋势的新的民主话语体系。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摆脱种种不同话语的羁绊,成功建构具有本土话语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话语体系,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实际而不是外来的理论才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话语建构的根本参照系。前面的梳理说明,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建构经历了从“无产阶级民主”、“工农民主专政”再到“新民主主义宪政”,最终发展到“人民民主专政”的话语演变历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表达及其内涵的变化,见证中国共产党民主实践探索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由初期对外来话语的简单引进和模仿,逐渐发展成熟为对外来话语的批判性借鉴与融合,并最终摆脱外来话语的规制,立足中国传统和社会实际自主地建构起契合中国历史逻辑和符合普罗大众诉求的人民民主专政话语体系。显然,中国的实际和问题是中共话语建构的重要考量。
就方法论而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体系建构的变迁,启示我们民主话语是流变的,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被不断代入的新的时代内涵所型构,我们一定要避免对民主话语进行简单的类型学归类。具体就中国民主话语体系而言,它既不能被简单回归到古老中国传统的民本话语,不能被直接等同于西方民主话语模式,也不能机械地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原初形态。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5页。显然,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简要概括,就是上述这些维度的体现。“人民民主专政”中的“民主”是“对人民实行民主”,这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域劳动群众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坚持,又有对西方民主中“民权”含义的汲取,还揉入中国传统“为民做主”的意义;“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专政”,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赋予人民道德上反抗恶人恶政的权利,又是对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革命和治理经验的总结。尽管从民主革命时期的“人民民主专政”话语过渡到新时期的“人民民主”话语,在思想逻辑上还有环节需要跨越,但民主革命时期的“人民民主专政”话语,不仅奠定当代中国主流政治话语的基本底色,成为现代中国政治话语生长的重要环节,而且也为当前中国特色民主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镜鉴。
B27
A
1000-7660(2017)06-0054-07
黄寿松,(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教育部基地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研究”(16JJD71001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特色民主话语体系建设研究”(14BKS040)
(责任编辑欣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