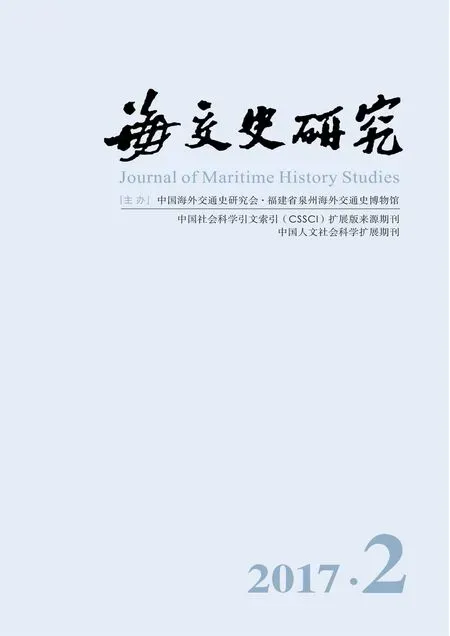叶灵凤:《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3月,144页)
陈贤波
叶灵凤:《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3月,144页)
陈贤波
早在2011年,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以“叶灵凤香港史系列”为名,汇集出版了叶灵凤先生(1904-1975)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完成的有关香港掌故、方物的开创性研究,包括《香港方物志》《香港的失落》《香海浮沉录》《香岛沧桑录》以及本文拟评介的《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著作五种。叶先生自1938年起客居香港直至终老,期间先后主编《星岛日报》及《立报》文艺副刊,因其读书涉猎广博,又兼具浓厚的乡土情怀,使得他的这些研究虽历经近五十载,仍不乏启迪后人的学术价值。江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以香港繁体字版为底本编辑出版的《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以下简称《真相》),便是其中相当引人瞩目的一种。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国内学者有关清代“华南海盗”的讨论,一般仅注意到穆黛安(Dian H. Murray)《华南海盗(1790-1810)》(198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的重要性,则《真相》内地简体字版的面世,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拓宽相关研究者的学术视野。
根据萧国建先生的导读,《真相》一书“成于一九七○年间”(第11页)。从内容上看,全书包括16篇随笔札记式的短文,形式上颇类似于今日的专题研究论文集。这些文章以中、外文档案及地方文献资料,考证张保仔的事迹、出身、盗巢、营盘、骚扰英贡船事件、与官府交战地点、投降经过和最后下落等等,内容相互贯通起来,即为乾嘉之际华南海盗活动的动态画卷。窃以为,其中最值得精读者有三:一是《外人笔下的张保仔》,二是《<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有关张保仔的资料》,三是《<新安县志>所记的海盗》。
在《外人笔下的张保仔》一文中,叶先生主要依据的关键资料有二:一是1835年广州外商出版的《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原书译为《中国报道》)第三卷第二期叙述中国海盗的文章,当中因张保仔的舰队虏获两名英国商船船员而保留了许多有关他们在海盗船上的生活和见闻;二是卡尔·纽曼(K. F. Neumann)在183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一八○七年至一八一○年为患中国海上的海盗史》(HistoryofthePiratesWhoInfestedtheChineseSeafrom1807to1810),叶先生认为此乃当时“唯一的有关这时期中国海盗的专著”。通过移译上述珍贵文献资料中有关张保仔的内容,叶先生旨在揭示海盗活动的若干重要细节。譬如,一直以来,我们对于海盗组织的武力问题仅能依据官方文献的记载,或夸大其词,或模棱两可,难以采信,因而对于海盗之所以能与官府周旋的武器装备内情难以深入勾连描述。依据被掳英国船员的报告,叶先生探讨了张保仔船队的武备问题,指出其舰队规模在五百艘至六百艘之数,最大的火炮十二门,在六磅至十六磅之间,每船另配一只小船,装有六尊至八尊小炮,可以容纳十八人至三十人。这种小船的主要用途是准备夜间可以驶近岸边,掠夺并摧毁不肯缴纳保护费的村庄(第42-43页)。又如,通过葡萄牙人的报告,叶先生注意到两广总督百龄一再与澳门总督磋商请求协助剿灭海盗的细节,较早揭示了当时双方的秘密协议:“葡萄牙供给船只六艘,并一切武装,与中国水师合作,共同剿灭澳门与广州之间的海盗,以半年为期。中国官方拨银八万两作一切费用。事平之后,中国官方应允许澳门恢复旧时所享受之特权”(第48页)。毫无疑问,这些历史细节在清朝的官府档案文献中难得一见。
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有关张保仔的资料》中,叶先生较早利用马士(Hoses Ballou Morse,1855-1934)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一书讨论张保仔受降的经过,补充了已有官书方志的不足。如我们所知,马士在1926-1929年间利用东印度公司档案完成的这部五卷本经典之作篇幅宏大,是目前研究相关课题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但迟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方有中山大学经济系区宗华先生的中译本面世,渐为学人广泛利用。职是之故,叶先生在70年代发掘该书第三卷第六十一章记载张保仔和郑一嫂率众接受两广总督百龄招降的细节,愈见其眼光和功力。譬如,文中介绍了编年史记录海盗的灾祸,揭示了不为人熟知的东印度公司对付广东沿海海盗方案以及澳门葡萄牙人与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冲突。又如在两广总督百龄招抚张保仔、郑一嫂等人之际,东印度公司在孟买的总部已经决定拨出公司的几艘护卫船只供清朝官府剿灭海盗之用,因而有驻广州代表与两广总督之间密集的磋商来往等等。
至于《<新安县志>所记的海盗》,则是《真相》一书的附录。据先生后人所言,“叶灵凤生前最重视的一套藏书是清嘉庆版的《新安县志》,香港历史依据尽在其中。叶灵凤逝世后,其家人遵其生前意愿,《新安县志》捐献内地,余愈万册藏书捐赠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第5页)。叶先生之重视《新安县志》,在于该书包含了有关早期香港历史的关键资料,因此在相关研究中屡屡征引。《<新安县志>所记的海盗》即从中抽丝剥茧地条理出早期香港海域海盗活动的种种事迹。
从《真相》全书内容来看,叶先生的研究虽集中于张保仔一时一地一人的事迹,但在资料利用上广泛地结合官方文献与私人著述、中文和西文文献,辅以实地踏勘所得的民间传说故事、石刻碑文等今日学人视为“民间文献”的做法,显然走在同时代学者的前沿,在某种程度上亦十分契合当前学术界所谓“历史人类学”的学术路径。叶先生对文献资料的孜孜追求,亦可从他在书中多次表达未能获见袁永纶《靖海氛记》原书的“遗憾”可见一斑。叶先生注意到,乾嘉之以后广东地方志书有关海盗活动的记载多次引述《靖海氛记》的内容,因此他断言“这是有关张保仔等人活动的可贵资料,可惜这书现在已不易见到了”(第138页),“这是我至今仍引以为憾的”(第144页)。值得一提的是,萧国建、卜永坚等人2007年将收藏于大英图书馆的《靖海氛记》加以整理笺注,这一重要文献方得以完整重见天日。很明显,作为学术引路人,叶先生的“提示”功不可没。
由于时代所限,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来,叶先生的研究自然不乏瑕疵和遗憾。例如,叶先生所引用的《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第三卷第二期有关两名英国商船船员的见闻,实际上仅为原始记录的只言片语,更接近于“第二手资料”。两名被虏英国商船船员的完整报告分别题为《我被拉得龙斯海盗所掳至遭遇以及有关那些海盗情况之见闻述略》,《我被拉得龙斯海盗俘虏及其以后之遭遇述略》,均有版本存世。两者构成了前引《华南海盗(1790-1810)》的重要资料,被穆黛安(Dian H. Murray)视为“两份令人激动的文献资料”(参见《华南海盗(1790-1810)》,中译本,第245页)。叶先生大概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研究征引的卡尔·纽曼(K. F. Neumann)的英文著作《一八○七年至一八一○年为患中国海上的海盗史》实际上就是袁永纶《靖海氛记》的英译本。由于未能获见《靖海氛记》的原书,《一八○七年至一八一○年为患中国海上的海盗史》中的错谬之处,叶先生当时自然亦无法甄别。此其一。
其二,叶先生有关海盗的研究,虽然尽力穷搜相关官私、中外文资料,但其时清宫档案资料尚未全面开放利用,因此难以详尽揭示官府经略海盗的全过程。在叶先生之后,如穆黛安、安乐博(Robert J. Antony)等学者极大地推进了相关研究的深度,很大程度上即得益于清宫档案文献的发掘和利用。不过,笔者也注意到,总的来说,既往的研究由于较多关注海盗活动本身,有关当局军事策略的筹划过程,尤其策略拟定和执行过程中包含来自朝廷和地方社会的多元政治互动,迄今仍很少进入研究者讨论的范围,尚存一定的开拓空间。循着叶先生所提示的学术路径,继续发掘官私、中外文献资料,仍必不可少。
按照夏衍先生的说法,“叶灵凤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有关香港历史掌故的工作。其有关著述为国家其后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从两个方面对香港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写作了大量文章,……开创了有关这方面研究写作的先河。后人有称此一领域的研究为‘香港学’,叶灵凤堪称是‘香港学’筚路蓝缕的创始人”(第5页)。若就“华南海盗”这一特殊的专题研究领域来看,叶先生的研究同样具有奠基开拓意义。后来的学者可能在资料占有上超越先生,从而在相关研究的深度上有所推进,但无法绕开《真相》一书。因此,重温这部接近半世纪之前的著述,仍深具重建学术史的价值。
作者陈贤波: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