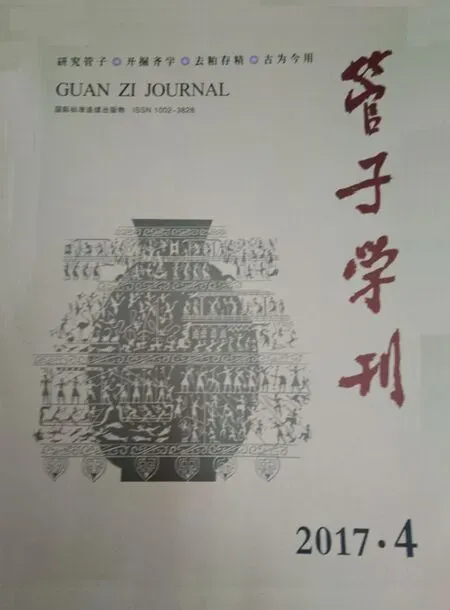汉语言时空处置模式的诗性智慧
范爱贤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汉语言时空处置模式的诗性智慧
范爱贤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汉语言时空处置模式的基本特征,一是文字层次上,以单形、单音这一特质,实现时间之音、空间之形的瞬间耦合,化解文字层次上的时空矛盾;二是话语层面上,以短音节语句结构(短句结构)、意象并置等方法,实现话语流动的时间感向空间感的转化,化解句子层次上的时空矛盾。这一处置模式的诗性智慧表现在,它遵循了人类的自然感知机制,最大限度地淡化了技术性、逻辑性的机械钳制,应合了人类自然心灵的诗性诉求。在西方语言文化面临自身无法突破的困境时,汉语言的诗性智慧提供了一个引领人们回身返顾的参照。
汉语言;时空处置模式;诗性智慧
一
文明的人类往往向往一种人与自然万物一体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既然谈不上自我意识,自然也就缺乏一种交替流逝的时间感,因而也就无所谓时间与空间的矛盾。但自语言产生,人与自然的一体状态就不可避免的破裂,因为只有这时人类才真正感到自己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物的存在。因为人是语言动物,人必须到语言中存身。而在语言中,语音的交替流动的时间感,与空间的并存性天然对立,人类不得不接受伴随语言而来的时空矛盾。
康德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特别分析了时空范畴,认为这是人类知识增长的两种最基本的直观方式:时间感是对内的直观,空间感则是对外的直观。而直观是感性的,它的发生学前提是人类感官被对象所激动的直观活动[1]54-60。康德的分析表明,时间、空间的根本特性是它们同为人类直观的主观条件,它们的本真存身状态即在人类感官“为对象所激动”的直观活动中。
二
既然时间、空间皆存在于人类“为对象所激动”的直观活动中,既然时间、空间是基于人类之自然本性的一种活动,而语言文字的诞生也并非一种远离自然的抽象活动,其根基也恰恰基于人类的自然本性,那么语言中的时空矛盾就不会无法破解,因为共同的自然本性显示了这一可能,问题只在于人类的智慧或直觉能否找到这个“阿基米德点”。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某个客体在外部世界显现自身,它引起的精神激动就为它的命名提供了场合和手段。感官印象是自我与非我遭遇时所接受的东西,其中最活泼最可爱的印象自然寻求语言的表达;它们就是说话的大众试图为事物分别命名的一块块基石。”[2]106-107结合人类文字的自然发生史,我们不妨这样说,人类的直觉所找到的“阿基米德点”,就是象形文字,虽然所谓“全知的上帝在给人类的一切启示中使用的语言由图画和象形文字所构成”[3]21不过是一种神学畅想,但世界上所有的自源文字皆是象形文字则是一个事实。维科在《新科学》中也言之凿凿地说“最初各民族都用诗性文字来思想……用象形文字来抒写。”[4]213就人类所有自源文字的发展历史来看,惟有在汉字中,在汉语言句法中,人类这一直觉智慧的结晶还保持着强旺的生命力。
汉字的独异特征,一是作为时间、听觉之表现的语音——单音,由单声母音位、单韵母音位(韵母组成无论是只有韵腹,还是包括韵头-韵腹、韵腹-韵尾、韵头-韵腹-韵尾,拼出来的发音还是一个单音)与单音调音位拼出来的仍是单音的音节。这一声音表现是瞬间的,时间表现为瞬间性。二是作为空间、视觉之表现的文字——象形,字展现为一个空间的作为整体的形,“可以在几个向度上同时并发”[5]106,其生成“是视觉瞬刻间的‘组织’或‘建构’的产物”[6]8,而汉字由象形、会意、形声等结构原则构成的从字象到字义的生成,又是隐喻式的诉诸直觉的瞬间跨越,这样一个汉字便实现了音、象、义,听觉、视觉,时间、空间,这诸多要素的瞬间一体的整合,这正是语言作为符号介入人类与自然之间时采取的最自然的方式。自然瞬间呈现之“象”,心灵、视觉、空间及心灵、声音、时间、听觉与之进行瞬间回应与一体性整合。而由此形成的以单音为特征的象形文字作为最早的文字符号,充分显示了语言产生的自然根基,也反映了人类由自然跨进文明时与自然无法割断的一体性关联。人类最初只不过以最自然的方式走进文明,走进语言,以心灵“为对象所激动”的“瞬间”直观、感悟来化解语言产生后所不得不面对的时间与空间的矛盾。印欧系语言如英语等正是在作为其物质性手段的拼音文字上,抛弃了象形这一自然根基。
印欧系语言文字音节结构比较复杂,就拿它的所谓单音节来说,也不具备汉字的单音优势。一个元音音标,或一个元音音标与一个辅音音标至数个辅音音标结合皆构成一个单音节,但单音节却未必能发出汉字那样瞬间一体的单音。如“or”与“I”都由一个元音音标构成,但“or”发一个音位的单音,而“I”则需发成两个音位的双音,但二者都是单音节;“be”和“by”都由一个元音音标和一个辅音音标构成,但“be”由单音位的辅音音标和同样是单音位的元音音标相拼发只有一个音位的单音,而“by”的元音音标由两个音位构成,在和单音位的辅音音标相拼后则需发两个音位的双音,但二者都同样是单音节;“back”由一个元音音标和两个辅音音标构成,相拼后须发两个音位的双音,“desk”由一个元音音标和三个辅音音标构成,相拼后须发三个音位的三音,但二者也都是单音节。仅就单音节分析,显然英语的单音节只有极少数和汉语的单音音值相等,具有瞬息一体的特征,而其大部分单音节的音值则相当于汉字单音的二至数倍。英语中即便是发单音位的单音节,也只有很少的几个能够直接以单音位表意,来唤起大脑的语义表象,而大部分则不能。而且在双音节以及多音节词中,一般而言单个音节词,无论由几个音位构成,也不能单独唤起大脑的语义表象,而需要二至数个音节才能唤起一个语义表象。因此在拼音文字中,音、听觉、时间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因此,与汉语言相比,英语的文字音节极大地膨胀,缺乏化解时间与空间之矛盾的基本自然物质条件。听觉、多音位在时间上的先后相继,无法像汉语言那样形成声、韵、调、象、义诸要素瞬间一体的整合,而诉诸视觉的文字也只是各表音单位书写符号前后相继的线性排列,而不是空间多向度的发散,主要服从音位的时间规律,根本无法拯救空间。即使文字在人们的日常使用中已经极为熟悉,看到字形能迅速瞬间整体的呈现意义,但字形的瞬间整体性改变不了音位的时间流动性,它和流动音位的时间感也还是不相吻合,也还是对人类自然感觉的背离,“文字的拼音化自它产生之日起就必然会掩盖其自身的历史”[3]3,这种掩盖造成两种后果,一是扭曲了人的自然感觉,二是遮蔽了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关联,其影响在今天日益突出。
三
汉字以单字、单音这一特质完善地化解文字层次上时间与空间的矛盾;在这一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单音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单音使汉语言的“无效音”降至为零,单音使语言的时间感与字象表意的空间感在文字层次上的矛盾轻松化解,并达到最大限度的统一;而单个整体字象则起到基础作用,它使语言——这个多少已是人为抽象化了的“制造品”,能够用自然感觉,以一个符号结构与外部进行最自然的沟通。但汉语言在句子层次上则不得不面临多音、听觉、时间,及多音、视觉、空间的矛盾,因为话语句的语音特征乃多音节,否则无法称之为语言;而句子——作为多个符号的线性排列——也不复能够组成诉诸视觉直感的空间画面(这种形式即是所谓原始的真正的图画语言,以一幅画表示一个句子。)。这样在象形文字层次形成的时间与空间的一体感被打破,线性、时间因素成为主要的决定因素,时间与空间在句子层面的龃龉感进一步突出。但与其他自源文字不同,当其他自源文字纷纷消亡的时候,惟汉字延续了文字的最早形态——象形——并依然保持青春活力,以象形为根基的单音、单形——这一根本特质,这就使汉语言有可能以特殊的时空处置方式自然化解话语层面的时空对立。
弗莱塞提出过一个假说,“空间性是与视直觉相应的,这种直觉作为一种‘最为精确的’的感觉形态,较之于其他感觉形态(其中包括时间性的形态)有着生物学上的优先性。”阿恩海姆进而认为空间性之生物学上的优先性的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是,“通常说来,物件是活动的载体,因此在知觉中物件优先于它们的活动,物件是处身于空间中的,时间则适于活动。”[7]103这也许与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乃存在之家”的“家”隐喻有相通之处,也许一般对于海德格尔的这句警言作了太过神秘的理解,其实所谓的“家”不过是一种归宿,是对永逝的时间之流的强行搁置与诗意逗留及回望,不过是在漂泊的语言之旅途寻找一个驻足的空间,这都是对存在之空间的呼唤与拯救。
据上所论,可以说汉语言在句子这一层次上化解时空矛盾的诗性智慧仍然遵循了自然的启示,它在符号线性排列的空间处置方式上,遵循人类发音的生理限制及大脑捕捉语义表象的直观域限,不使语音流速过快,不使句子音节过多,采用短句结构、对称结构,尽力淡化话语的时间强度。这与英语句子结构对比极为明显,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在英语中句子的平均长度是20—25个词,汉语中最佳长度是7—12个字[8]64。这是仅从字词的数量上说,而如果放在具体的话语时空感上,则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更为巨大。英语一个词的音长原则上相当于几个汉字的音长,如“湖面波光闪闪,湖边茂林修竹,西湖景色四季宜人。”这三个短句共20个字,20个音节,发音时间相当于20个音位;英译为“with glisteni-ng water on its surface and luxuriant trees and bamboo groves along it bank,the west lake has attractivelandscape all the year round。”[9]243共 26 个词,37 个音节,但却相当于71个音位,在句子结构上,双方语音量的差别十分惊人。一般的比较往往只是机械地、简单地注意了音节、字数,却忽略了十分重要的音位在实际发音时长上的巨大差异。更有价值的差别在于,在实际的发音时长上,汉语每个音位在句子的实际发音时间,与英语音位在句子中的实际发音时间并不相等,汉语每个音位的发音时间趋于延长,而英语则趋于缩短;可能最终的实际发音时间,在表达相等信息时不会是二十比七十一这么巨大,而是向单音节的数量时长靠近。这样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对比情景是:汉语每个音位都要延长,造成同一个音的重复效果,其表达效果是“循环往复,一唱三叹”,英语每个音位都必须大大缩短,形成不同音位的快速交替;由于音位的延长,增加了语音、语义表象在大脑中的回旋时间,其实也就相当于把时间变慢,而在感觉上就是时间感向空间感的转化,“重复打破了…赫拉克利特学派对时间之流的断言。人们可以再次踏入时间之流。”[7]125英语由于音位大大缩短,语音快速交替,打断了语音、语义表象的回旋空间,只是语音——这一时间之流的“义无返顾”的快速流逝,以时间征服空间。这似乎就是近现代以来西方文明持续征服之旅的一个让人类焦虑的隐喻,与人类面对大千世界所自然滋生的自在的时空感受极不吻合。
对于语言为现代人类制造的时空矛盾,阿恩海姆有一些比较深入的实证性分析,他指出,“把文章的整体分化为一些较小的部分,使我们回到了语言的最初的形态——那些一个字的陈述或词语上。”[7]124“回到……一个字的陈述或词语上”,这很符合汉字所代表的状况,及汉语音节比较简短的句子策略。汉字有一个从象形到会意、形声的发展,而到会意、形声字发展阶段,每一个字就类似一个小型的话语陈述,话语的时间流被整合在一个单一的字象、字音上,空间整合时间,体现了独特的语言智慧。另外,阿恩海姆还通过散文与诗歌的比较也表达了类似的见识。他认为散文作为一种叙述方式注重追溯因果顺序,而诗歌注重“对统整经验的察知,这是相对地自我包涵并外在于时间过程的。在这两种认识方式中,后者显然在心理学角度上是在先的。”[7]102阿恩海姆把散文与诗歌作对比,正是基于印欧系语言诗歌的句法特点:句子较短,音节隔断较多,在达意上与散文语言形成鲜明对比。而更为典型的语言试验就是欧美现代诗人庞德等人所“孜孜以求”的、以“空间隔断”为特征的诗歌句法。它把线性、横向排列、以时间为特征的长句,根据表达需求,切割成纵向排列的短句,通过这种方式弱化语言的时间感,突出语言的空间感。这反映了人类心灵对于语言的一种共同的诉求,以新的语言策略,来弥合语言制造的人与自然的分裂。而这样一种带有几分强制性的语言策略,则是汉语言最基本、最自然的语言现实。
四
汉语言还以空间意象的并置来暗示时间的变换。在这一方式中,时间并不以触目的状态出现,而是化解在空间场景的自然转换中,这符合人类心理的自然感受,“在许多情形中,时间观念并不象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见解所主张的那样是普通经验的一个要素。”[7]102汉语言没有丰富的关于时间的形态标志,动词也没有时态变化,虽有一些提示时间的符号,也往往不是要特意突出时间的位置;而且在实际的经验中时间的抽象性本身就是语言表达的一个难题。第一种时空处置所着重解决的是语言本身所引起的生理承受,说到底也就是语音本身的时空矛盾;而第二种方式,则提升为语言对人类生活经验中时空感受的表达问题。英语主要靠一些时间的语法标志词来引导,汉语更主要的是把时间融化在空间的自然转换中,汉语中所谓提示时间的符号往往也是画面的一个有机成分。如蔡确《夏日登车盖亭》“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第二、第三句的英语译文分别是“During the day I read till I am tired an d/dream a long dream.”“When I wake from the dream,I smile/alone in good humor.”[10]152-153在汉语中“午梦”“睡起”作为时间的显示符号只是空间画面的一个有机组成元素,与空间画面的结合自然而和谐,但英语特意以符号“during”“when”把时间突出出来,仿佛人在这一自然活动中,首先有一种触目的时间感,其实如果时间意识如此强烈,这种语言画面反而难以生成。再如“唱彻五更天未晓”(洪咨夔《直玉堂作》)英译“When the watch near dawn is reported I/have finished them. ”[10]154-155“寒夜客来茶当酒”(杜耒《寒夜》)英译“In a cold night,to my guests I often offe r \tea instead of wine.”[10]170-171“笛弄晚风三两声”(牧童,《答钟弱翁》)英译“In the evening breeze,a few notes from/he flute dance up and down.”等[10]182-183在这些类似的例子中,“五更”“寒夜”“晚风”作为一些带有时间标志的符号,在各自的场景中并非要突出时间,它们只是隶属整个场景的一个有机的空间性的画面成分,跟随这些词而来的首先不是时间感,而是一种相应的氛围、情调,即融嵌于情绪记忆中的自然场景。而英语的时态限制首先突出的就是时间感觉,这种突出恰恰破坏了诗意的自在与和谐。
应该说在日常的经验生活中,展现出来的符合自然心理感受常态的,是具有相对稳定感的空间场景的整体,时间往往只是融化、隐含在场景的交替中,却并不需要感觉把它突出出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在某种意义上,显然可以看作是对时间与人类生存感受的思考,而在他的思考中,能够召唤出人类极促迫的时间感受的,往往是一些特殊的生活场景,如“怕、畏、烦、死亡”,只是在这些场景中,时间才成为人类感觉的最触目的特征,“不耐烦、腻味和恐惧是召唤时间作为一种知觉构成可能的条件”,“当我的存在不再与我相一致时,时间便是对我的存在构成威胁的经验条件。”[7]102显然,时间成为“人生的经验条件”,既不是人类生活及感受的常态,也不是人类自然感觉所向往的,它倒标志着人生进入了一种对存在构成折磨的境地;真正符合人类自然感受的倒是一种地老天荒的永恒,生活在时间不触目的感受中流逝。或许可以这样说,英汉两种语言对时空的两种处置方式,在隐喻的意义上,代表了两种存在状态。相比较而言,汉语言的时空处置方式更符合人的自然感觉,更多地保留了人与自然的源始性关联,更多地透露了人类来自自然故乡的信息,因而更富有诗性智慧。
就语言对人类生存的意义来说,汉语言的时空处置方式遵循了人类自然的感知顺序,从而最大限度地淡化了技术性、逻辑性的机械钳制,应合了人类自然心灵的诗性诉求。在西方语言文化日益被技术化的浪潮裹挟而去的时候,当人类的心灵已不堪逻辑的、技术的重负时,汉语言的诗性智慧似乎提供了一个引领人们回身反顾的参照。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2]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北京:三联书店,1988.
[3]德里达.论文字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4]维柯.新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
[6]阿恩海姆.视觉思维[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7]阿恩海姆.艺术心理学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8]连叔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9]周志浩.汉英对比与翻译中的转换[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10]郭著章,等.汉英对照《千家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H1-09
A
1002-3828(2017)04-0086-04
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7.04.14
2017-03-23
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S07YF22)。
范爱贤(1964—),男,山东莒南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美学、文学理论、比较诗学研究。
王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