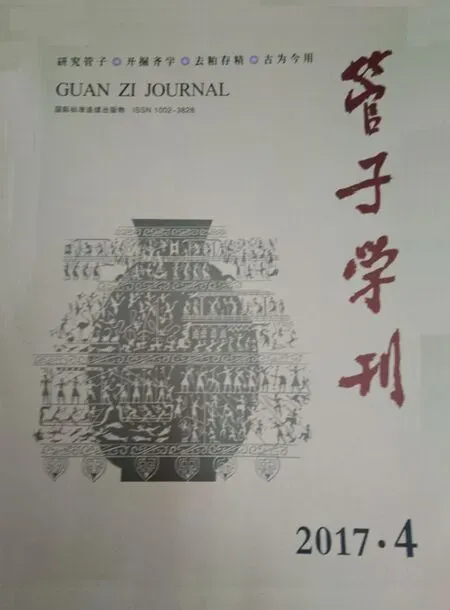齐鲁初封治国的文本解读与文化意蕴
刘雨昂,张艳丽
(1.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山东 淄博 255200;2.山东理工大学 齐文化研究院,山东 淄博 255000)
齐鲁初封治国的文本解读与文化意蕴
刘雨昂1,张艳丽2
(1.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山东 淄博 255200;2.山东理工大学 齐文化研究院,山东 淄博 255000)
齐鲁初封治国的史事在秦汉典籍中多有记载,各种思想流派从自身的学术角度对此事做出定位和评价。分析这一史事多个文本的记载,探索古代思想家重构史事情节、挖掘文化意义的过程,可以看出学者的学术主张及思想特征。这一史事带有的启迪借鉴性,及探讨齐鲁地方文化的针对性,可证明其蕴含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从而吸引学者们对此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经典解读。
齐鲁初封;尊贤;亲亲
史书《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昔武王克商,成
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1]369-370此为“封土建侯”的周初封建,被封于鲁地的是周公旦,被封于齐地的是太公望姜尚。姜太公初始分封到齐国时的治国方略,并与鲁国对比的史事,人们耳熟能详,是先秦齐鲁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学者围绕此论题对齐鲁文化进行对比分析①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有如下成果:逄振镐:《齐鲁两国建国方针之比较研究》,《东岳论丛》1987年第3期;刘敦愿:《西周时期齐鲁两国的地位及其互相转化》,《东夷古国史研究》第1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66-84页;王明:《周初齐鲁两条文化路线的发展和影响》,《哲学研究》1988年第7期;罗祖基:《论齐鲁建国方针反思中的不同意见》,《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张富祥:《周初齐鲁两条文化路线问题》,《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王志民:《齐、鲁分封的比较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等等。。而齐鲁初封治国的史事,在不同时期受到文人们的关注和探讨,他们纷纷从自己的思想立场和命题出发,把这一史事纳入理论体系,根据时代思潮的不同,对此做出引申和评价。
一、史事的早期记载
根据现存资料的整理,齐鲁初封治国的史事,较早出现在《吕氏春秋》中,原文记载如下:
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日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2]612。
此文见载于《吕氏春秋·长见》篇中,“长见”即远见。《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著作,写作目的即为综合各家学说之长,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吕氏春秋》在此篇章引用齐鲁初封治国的事例,意在指出贤明的国君会具有远见,能预测出后世必会出现的结局。姜太公尊敬贤人,崇尚功绩,周公旦预言齐国会被篡权;周公旦亲近亲人,崇尚恩爱,姜太公推断说鲁国从此会日益削弱。二人的推测后来都被应验,说明他们非常具有远见,这恰与“长见”篇目相应合。
汉代时期,韩婴《韩诗外传》中提及到这一史事,原文曰: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见。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赏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矣。”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观之,圣人能知微矣。《诗》曰:“惟此圣人,瞻言百里。”[3]883
《韩诗外传》是春秋故事、伦理规范、诸子杂说、道德说教等内容的集合,借助《诗经》发挥著者的政治思想。摘录齐鲁初封治国这一史事后,《韩诗外传》得出结论说:圣人能够知微见著,这恰巧印证了《诗经》提到的“惟此圣人,瞻言百里”。这句话出自《诗经·大雅·桑柔》,“瞻言”指有远见的言论。在此处,著者叙述了这一史事,引用《诗经》中相应的诗句,来点明、论证自己的观点。
《淮南子》继承了先秦道家的思想,是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哲学著作,并杂糅了儒、墨、法、阴阳等家思想。书中讲述齐鲁初封治国如下: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4]170!
此文选自《齐俗训》篇,作者指出,不同时代、国家、民族有各自的习俗,这些习俗是一定物质基础、社会环境、道德观念的反映,作为君主对不同的习俗应给以尊重,不能区别对待[5]。以道家观点而论,各种东西都存在其对立面,各种东西都会在条件变化的时候随之发生变化。圣人能够知道这中间变化的道理,能从开头细微的迹象,预见到事物发展的结果。在齐鲁初封治国的史事讲述中,姜太公和周公旦都是知晓变化的圣人。
史学家司马迁编著《史记》,把齐鲁初封治国看为正史,当作鲁国、齐国历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载入史册。这段历史详细记载于《史记·鲁周公世家》中,其文曰: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6]1524
与《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子》比较而言,《史记》记载的内容相似,但细节有所区别。前者的对话发生在姜太公和周公旦之间,而《史记》指明这应是姜太公和鲁公伯禽之间的治国方略比较。周公旦对两位国君的治国方略进行评价,结论是鲁国必定不如齐国发展实力雄厚,所依据的原理是政简民亲、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
西汉末期,学者刘向根据皇室所藏典籍与民间流传的图书,按照类别编辑了先秦至西汉时期许多传说及历史故事,编成《说苑》一书。《说苑》中一般以第—则,或前数则故事为一卷的大纲,引述前人的言论来论证本卷的主旨,然后用大量的历史事例加以证明。刘向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通过对历代治乱之道的研究,期望刘汉皇帝尊贤、贵德、重道、听谏等,以解决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巩固刘氏皇权,重振刘氏雄风,阻遏外戚、宦官篡权的阴谋。
《说苑·理政》篇中,刘向征引了齐鲁初封治国这一事例:
齐之所以不如鲁者,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疾也?”对曰:“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泽及五世。”五年,伯禽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难?”对曰:“亲亲,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鲁之泽及十世。”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之所以不如鲁也,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也[7]200。
刘向承继了司马迁的写法,由周公来点评齐、鲁治国发展方向,批评性地指出,齐国治理方略不如鲁国,原因在于贤能方面姜太公比不上鲁公伯禽。姜太公的治国方略重在“尊贤”,属于凭借武力征服别人的“霸道”;鲁公伯禽的治国方略重在“亲亲”,属于先王之正道的“王道”。在《说苑》成书的西汉末期,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依照儒家“仁厚”的原则进行评判,齐国的治理方略比不上鲁国。刘向希望借助这一史事,告诫西汉统治者,推行王道是获得长治久安的根本治国政策。
要之,西汉之前,齐鲁初封治国主要记载在《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说苑》等典籍中,所载内容在细节方面有所不同,各有偏颇和侧重。《吕氏春秋》强调圣明统治者应具有远见的能力,《韩诗外传》证明圣人能够知微见著,《淮南子》重在申明道家所称事物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史记》作为正史,把此看作齐鲁两国历史发展的组成部分,而《说苑》站在儒家的立场对齐国霸术进行批判。作为一种文化资源,齐鲁初封治国史事被学者们征引,显现出极大的文化魅力。
二、史事真实性的探讨
齐鲁初封治国在古代典籍中有多种记载,流传至后世,许多文人并未怀疑其真实性,而把其当作历史故事来引用分析。如东汉无神论者王充,针对神学唯心主义先验论者所宣扬的圣人“生而知之”的论调,以齐鲁初封治国为例证,驳斥了神学家“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先验论。王充指出:“放象事类以见祸,推原往验以处来事,贤者亦能,非独圣也。周公治鲁,太公知其后世当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齐,周公睹其后世当有劫弑之祸。见法术之极,睹祸乱之前矣。”所谓“圣人”能预见一些事情,其实不过是根据同类事物相推其原委、始终,“揆端推类,原始见终”[8]398,周公与姜太公关于齐、鲁两国的发展推测,即为例证。王充肯定一切知识都是学问而来的,有了学与问才能认识事物。
北宋学者唐仲友较则质疑这一史事的真实性,认为其带有战国时期的诈谋性,不是周公所言。在《周论》中,唐仲友认为周代是历史上享国最长久的朝代,究其原因,在于周文王、周公旦以德治理国家的方式。周文王、周公旦待民宽厚,出于自然:“二圣人信之笃,守之固,至诚恻怛之心,宽厚和平之政,浃于斯民,固结而不可解。此岂矫拂而伪为?亦出于自然而已。”但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时候,对于这一点并未有清楚的认识,并流毒无穷于后世。唐仲友指责说:“彼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又曰:‘周公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此特战国变诈之谋,后世苟简之说,殆非文、周之言也。迁不能辨其是非,又从而笔之于书,使后人怀欲得之心,务速成之功者,藉此以为口实,其害岂小哉?”[9]755唐仲友较早否定了齐鲁初封发生的真实性。
南宋学者曾丰也认为人们对周公旦的评价不公平,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此即以齐、鲁初建国家为例。曾丰指出,“尊尊亲亲”可能不是周公的原话,应该是后世史学家故意编造的。姜太公五月报政,与伯禽三年报政,一个太快,一个太迟,这两种做法周公都不欣赏:“太公之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疾也?’伯禽之鲁,三年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夫迟疾,周公两不取,盖有以也。治道不欲太疾,太疾则人将无以措手,而或巧为规避以塞上之责。亦不欲太迟,太迟则人将无以献状,而或毛举弥文以鬻己之长。”曾丰认为,后世之所以编造这样的故事,是好事之人根据齐、鲁两国发展后期的弊端,往前推测到始封者姜太公、周公身上而已:“周公既为太公忧,又为伯禽忧,则假令就国,岂肯自犯其所忧者哉?世之好事者,徒见齐、鲁之末流其弊如彼,而推其始封则周公、太公也。”[10]
对于齐鲁初封这段历史,明末清初学者黄淳耀断言说:“此非周公之言。”并直言这种说法十分荒谬。究其原因,从国家制度而言,伯禽受命于周公治理鲁国,伯禽报政时周公不会疑问于其时间的迟缓、立政的繁简,更不会感慨于其子的智慧不如姜太公;其次,从地方治理来看,“三年报政”是符合规定的:“夫三年者,报政之常期,虞廷三载考绩,孔子为政,亦曰三年有成。”黄淳耀继而推测说,初封治国五月与三年的说法,战国时期已经十分谬误,司马迁采录了这种说法,后来的学者也坚持这种说法,都是根源于“轻信”的缘故:“与为此说者,战国谬悠之谈,而太史公采之,《淮南子》采之,《韩诗外传》采之,则皆义理不精,好奇轻信之故也。”[11]95
清朝辨伪学者崔述专门撰文《辨伯禽、太公报政迟速之说》,就齐鲁初封治国的真实性进行分析。崔述先引用《史记》和《说苑》的记载,然后指出,姜太公和鲁公伯禽都是圣贤之人,治理国家的策略不会差异太大;再则,从历史记载来看,齐国、鲁国受封的时间不同:“齐封于武王世,鲁封于成王世,其相隔远矣,安得同时而报政!”对于报政的时限,各种典籍记载并不相同:“且报政之日,《史记》以齐为五月,《说苑》以为三年,《史记》以鲁为三年,《说苑》以为五年,传闻之异显然。”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这一史事无疑属于传闻,真实性值得推敲。
崔述也提到古代地方治理的规章制度,报政时间应以三年为期。齐鲁初封治国的史事之所以得以流传,是后人根据齐、鲁国势的发展杜撰而来,论据并不充分:“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冉有之言志也,皆云:三年可使有勇、足民。子产之治郑,亦三年而后与人诵之。三年政成,常也;伯禽之三年何得为迟,太公之三年亦何得为疾,而周公乃异之乎!此乃后人据其后日国势而撰为此说者,不足据。《吕氏春秋》亦载此事,而其文尤支离。故今皆不录。”[12]408崔述从春秋时期的报政惯例来分析,指出先秦的一些文献记载根本不可相信,更不足为凭据。
可见,宋代唐仲友怀疑一些话语不是周公旦的原话而质疑司马迁的记载,明代黄淳耀从国家制度的推行而言认为史事的谬误自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清代崔述明确指出这一史事是后人根据齐鲁两国日后发展的情势杜撰而来。对于这一史事的真实性与细节描述,学者们探讨得比较详细。
三、史事在科举考试中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
科举考试自隋唐兴起以来,齐鲁初封治国因涉及到国君治理国家的不同方式,成为科举应试的重要内容。历朝科考士子们对这一史事进行分析、关注和评价。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准备科举考试期间,关心时事,“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后来分为四卷,命名曰《策林》。其中第十二则讨论的主题是“政化速成,由不变礼,不易俗”。白居易认为,国君若要政事快速成功,必须做到简明清晰。他以齐建国初期姜太公治国方略为例,分析如下:“夫欲使政化速成,则在乎去烦扰,弘简易而已。臣请以齐、鲁之事明之。臣闻:伯禽之理鲁也,变其礼,革其俗,三年而政成。太公之理齐也,简其礼,从其俗,五月而政成。故周公叹曰:夫平易近人,人必归之。鲁后代其北面事齐矣。此则烦简迟速之效明矣。”[13]1298在策论中,白居易指出,从治国理政的角度出发,春秋时期齐国姜太公简而速的方略收效明显。
北宋初年徐铉撰《骑省集》,内有《策秀才文四首》,记载有官府策问秀才的题目,其中第三首提到齐鲁发展不同的史实,原文如下:“昔太公理齐因其俗,故报政速而后世强。伯禽为鲁易其俗,故报政迟而后世弱。然则商辛淫虐之风,不可不去也;周家仁厚之化,不可不被也。修旧者未见其迁善之途,革故者岂伤于惟新之义。迟速之效,强弱之由,愿闻嘉言,以释斯惑。”[14]11059这是一道官府出的策问试题,出题者也注意到齐、鲁建国初期治国方式之不同,从而导致迟速与强弱之发展区别,要求秀才学子们对此种历史现实做出解释。因受资料收集的限制,士子们的答卷无从见到,但至少反映出时人对齐鲁治国方略的关注。
文学家苏轼熟读史书,应试科举,对齐鲁初封治国有所评论。苏轼应试时,策问题目为:“问:《传》曰:‘秦失之强,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至其后世,有浸微之忧。太公治齐,举贤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争夺之祸。夫亲亲而尊尊,举贤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齐鲁行之,皆不免于衰乱,其故何哉?”[15]529苏轼的回答是,虽则创始国君制定出优秀的治国政策,但若后世子孙不能很好地遵循奉行,都会流于形式而产生弊端。苏轼曰:“臣所撰《策问》,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齐、鲁,后世皆不免衰乱者,以明子孙不能奉行,则虽大圣大贤之法,不免于有弊也。”[16]780
与苏轼生活于同一时期的北宋学者毕仲游,也参加了这次策问考试。面对同样的问题,毕仲游答曰:“周公治鲁,尊尊而亲亲,岂不知举贤而上功?太公治齐,举贤而上功,岂无尊亲之道?使鲁不举贤而上功,齐无尊亲之道,则齐、鲁岂可以为国?盖尊尊而亲亲,近乎周之弱而道无弱也;举贤而上功,近乎秦之强而道无强也。鲁久而偏于弱,齐久而偏于强,后世从其偏而失之。如齐、鲁之后,知其偏之所在,以齐之所偏者治鲁,以鲁之所偏者治齐,各举其偏者救之,则鲁不至于衰,齐不至于夺。非谓尊尊亲亲,举贤上功,为召衰、夺之端也。”[17]70
毕仲游认为,历代人们对齐、鲁初建所采取的措施有所误解,齐国并非不“尊亲”,鲁国并非不“尚贤”,只是相比较而言这方面的做法不突出而已。如果齐国、鲁国在所短缺的方面调节、补充的话,鲁国发展不至于衰落,齐国姜氏政权不至于篡夺。依照这种理解,齐国施行“举贤上功”、鲁国施行“尊尊亲亲”并不是导致齐国篡权、鲁国衰落的直接原因。
北宋时期,朝廷积贫积弱,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对峙中处于弱势地位。统治者重文轻武,希望借助知识分子的力量,来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贤能英明国君的治国策略受到重视,故而宋代时期把齐鲁初封治国史事纳入科举考试体系中,让文人各抒己见,期望找寻治国强盛的有效途径。
四、史事在分析齐鲁地方文化时的佐证
齐鲁初封治国的史事包含有齐、鲁治国特色的元素,后世学者在分析齐鲁地方文化时,常常对其点评。如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分析各地风土民俗时认为,齐地风俗的利弊与姜太公有密切关系:“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齐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恰当印证了这一结论:“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杀之臣。’其后二十九世为强臣田和所灭,而和自立为齐侯。初,和之先陈公子完有罪来奔齐,齐桓公以为大夫,更称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齐,至孙威王称王,五世为秦所灭。”[18]1661田氏代齐的齐国历史发展轨迹,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周公推测的正确性。
与齐地情况相同,鲁地的风土民情,与周公伯禽的治国方略有关,并直接影响到鲁国后来的发展路径:“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太公曰:‘后世浸弱矣。’故鲁自文公以后,禄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为楚所灭。”[18]1662鲁国后来发展为三桓专政,国君势力日渐衰弱,最终为强楚所灭亡。
历经千年以后,人们在谈到鲁齐文化时,仍不免会提及周公、姜太公的治国方略。北宋学者黄裳依据于此推演齐鲁文化的演变,与建国之初统治者施行礼教,或俗教的治国策略有直接的关系:“有以礼俗驭其民者,其以此欤?任俗则其入人也浅,其为效速,故齐五月而报政;任礼则近道,则入人也深,其为效迟,故鲁三年而后报政。因俗而与之同,制俗而与之异,然后可以语道焉。齐变其所任而从礼,然后至于鲁;鲁变其所任而从周,然后至于道。”[19]141于此,黄裳释读了孔子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含义。
进而黄裳指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姜太公的这种“任俗”做法,影响了后世的管仲,辅佐国君成就霸业,但缺少“大道”的风范,令人遗憾:“惜夫仲之才为志所屈,仲之志为才所屈,苟求近功以副其欲。其为德也,利仁而已,不知安仁;其为政也,因俗而已,不知制俗。虽有太公之遗风,而不知有先王之大道,卒为霸者之佐,固无所恨焉。”[19]141黄裳的这种德性评价结论,与其所处的儒者理学思想境地保持了一致性。
北宋文人苏辙对此也有评论。在探讨商代和周代的历史时,苏辙认为,商代的政策与姜太公相似:“圣人之虑天下亦有所就而已,盖不能使之无敝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强,能以自奋而不能以及远,此二者存乎其后世之贤与不贤也。故太公封于齐,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簒夺之臣。’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太公曰:‘后世浸衰矣。’夫尊贤尚功,则近于强;亲亲尊尊,则近于弱。终于齐有田氏之祸,而鲁人困于盟主之令。盖商之政近于齐,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鲁也。故齐强而鲁弱,鲁未亡而齐亡也。”[20]233苏辙指出,圣明的国君治理天下,未免后世不会出现弊端,关键在于后世继承者的贤能与否,春秋时期齐、鲁两国的发展结果即为明证。
南宋理学家朱熹在解读四书时,提到《论语·雍也》中孔子关于齐鲁文化的看法,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朱熹认为,齐国、鲁国在一些方面体现出不同之处,比如:“以地言之,则齐险而鲁平;以财言之,则齐厚而鲁薄;以势言之,则齐强而鲁弱;以俗言之,则齐尚夸诈而鲁习礼义。”姜太公治理齐国,伯禽治理鲁国,在治国方略上有所不同,后世依循这种治国策略,分别走向“霸道”和“王道”之途。朱熹详细分析如下:“而太公治齐,尊贤尚功;伯禽治鲁,尊尊亲亲,其治化又不同矣。齐自桓公、管仲不无变乱太公之法,而益趋于薄;鲁则虽日衰弱废坠,而其规模气象,犹有周公之遗意,则其旧俗之变,又不同也。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则虽太公之盛时,已必一变而后可以至于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则齐俗益坏之后,又必一变而后可以及鲁之衰也。”[21]227-228
谈到与齐国有关的历史,文人们大都会想到姜太公尊贤上功的历史,如“营丘”这一地名,曾是齐国的都城,让人不禁联想到齐国的历史。元代学者杨维桢曾应邀为一书房名曰“营丘山房”写记,杨维桢写到:“营丘在虚危分埜,为今济南地,太公吕尚父之食邑也。太公治齐,举贤而尚功,至十四世为小白,主霸,以管仲富国匡天下,而太公之泽益远且大。孔子曰:微仲,吾其左袵矣。多其功也。太史公曰:太公尊贤,智尚功能,而其敝则夸奢虚诈而不情。伤其俗也。善欲振其绪于营丘,而又直明天子之登贤以图治,其以仲之富国匡天下者为勉,而以俗之失不情者为戒,则可谓善嗣营丘者矣。”[22]385看到“营丘”的字眼,文人们会想到齐国的历史文化,姜太公的尊贤尚功不得不提,杨维桢即为此中之例证。
到了民国年间,国学大师刘咸炘对历代史书当中记载的齐鲁初封治国这一史事进行总体点评,意在分析齐鲁二地的风俗,特撰文《齐鲁二风论》来阐述自己的史学理念:“凡观史迹,必纵察其时而横察其地。顾或谓土风虽重,不关政事风俗之大纲,不知此特郡县统一以后为然耳。古者封建分治,各君其国,因其俗以为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但节偏而一之中和耳,不以一切治也。”刘咸炘指出,齐鲁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非常重要:“故论春秋之世,尤必以横观为主,惜书缺有间,多不可详其轶。见他说得推知者,独有齐、鲁。吾尝通观而详察之,则知横之二国,与纵之四代质文,实汉以上史迹之大纲。而周、汉之异,亦即齐、鲁之殊。鲁为周之末,而齐为秦、汉之先,不可不细论也。”[23]321单就齐地而言,刘咸炘认为:“齐风之特异,在于尊贤。”“齐风之大变古者,重商也,而亦云始于太公。”[23]326-327齐地的这些地方文化特点,都与姜太公初封治国政策有密切的关系。
余论
学者陈少明指出,先秦时期流传着一些后世比较熟知的故事,这称之为“经典”[24]。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些经典的寓言或史事会不断出现演绎和解构。不同时代的知识精英站在不同社会需求和阶级立场上面,对这些“经典”故事不时添加一些细节和情景描述,提出不同的评价体系,以期承载新的情感和思想内容。
直接记述或点评齐鲁初封治国史事的典籍,主要为《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说苑》等,其记载内容各有侧重点,对后世影响也有不同。针对于此,刘咸炘总结说:“功利云云,本于《汉书·地理志》;从简之说,乃本《史记》世家;尊贤尚功,则本《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及《说苑》皆谓太公,程氏谓为桓公者误也。《语类》之说,儒者多不从,大抵谓太公、周公皆贤圣,必无异道,不得以桓公以后之弊俗归咎焉,此论是也。”[23]321-322可见秦汉时期,齐鲁初封治国的文本记载,各有其要凸显的文化特征。
对于这一史事的真实性,后世有些学者进行反思,尤以宋代学者为主。而持代表性看法的当推刘咸炘,他分析说:“战国所传古事,诬妄甚多。其时记载疏阔,惟恃传说,而诸子参以己意,引为重言。”也就是说,虽然齐鲁初封治国的记载有不可信性,但学者依托其讲述道理而不依托其他故事,是有缘由、有一定道理的:“故报政之事不可信,而简礼因俗尊贤尚功之语有可取也。且核之以齐、鲁后世之风,则简礼因俗又非,而尊贤尚功则是也。削弱篡弑王霸之言,绝非太公、周公之本语,而亲疏仁义先后之论,则虽衍说而实有理也。”[23]325
由上可知,多位古代学者转引并参与评析齐鲁初封治国,可见其流传的广泛性。至于齐鲁初封治国在历史上到底史实如何,周公旦究竟如何点评,也就是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或已不再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这一史事蕴含的历史借鉴性,及探讨齐鲁地方文化的针对性,更容易引起文人的注意。这恰巧可以说明,无论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还是在大一统的王朝时期,齐鲁初封治国的史事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吸引着各派思想家们从多维角度出发,把其作为阐述自己观点的材料和依据,进行深度阐述,彰显地方文化底蕴。
[1]左丘明.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8.
[2]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M].成都:巴蜀书社,1996.
[4]高诱.淮南子注[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5]刘贯成.《淮南子·齐俗训》的主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科技与生活,2010,(6).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刘向.说苑疏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8]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9]唐仲友.周论[C]//庄仲方编.中华传世文选·南宋文范.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10]曾丰.缘督集·齐鲁[Z]//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本.
[11]黄淳耀.陶庵全集·鲁周公世家[Z]//丛书集成续编:第121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12]崔述.七百种考信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3]白居易.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徐铉.策秀才文四首[Z]//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 4部第4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15]苏轼.试馆职策问三首[C]//张春林编.苏轼全集: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16]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之二[C]//张春林编.苏轼全集: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17]毕仲游.西台集·召试馆职策问[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18]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19]黄裳.知予为取政之宝[C]//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03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20]苏辙.苏辙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21]朱熹.四书或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2]杨维桢.营丘山房记[C]//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41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23]刘咸炘.推十书(甲辑第一册)[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24]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K255
A
1002-3828(2017)04-0068-06
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7.04.11
2017-07-19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管子治国理政思想的传承与发展研究”(批准号:17CLSJ03)。作者简介:刘雨昂,男,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张艳丽,女,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张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