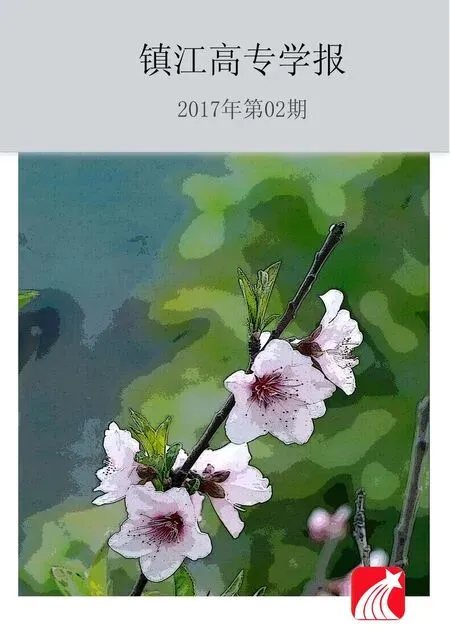逃离与奔向
——格非小说“逃离”主题论
贾晓梅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逃离与奔向
——格非小说“逃离”主题论
贾晓梅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作为由人类生存困境引发的创作主题,人物“逃离”在格非小说中得到了突出呈现。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艺思潮的涌进和90年代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构成了格非小说“逃离”主题的重要创作背景。而对人物“逃离”模式和“奔向”之所的设置和探索,则反映了格非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入思考和对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
格非小说;生存困境;“逃离”主题
人物“逃离”作为格非小说的重要现象,已然成为其作品创作的主题之一。就目前学术界对格非小说创作的研究看,其成果大多集中在隐世书写、死亡叙事、神秘叙事以及知识分子叙事方面。现有研究成果虽对其“生存困境”主题已有所涉及,但人物“逃离”主题鲜被视为探究主体而缺乏系统性、详细性的阐释。事实上,“逃离”同“死亡”“性”及“知识分子书写”等主题一样,同为格非小说的重要内容。对格非小说“逃离”主题进行探讨有利于我们进一步阐释与把握格非小说的人文审美内涵。
1 永恒的生存困境和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携代表作《迷舟》进入当代文学史的格非,深受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但正如“对‘先锋派’(先锋性)最大的误解莫过于认为‘先锋派’只是在玩弄形式技巧,制造阅读障碍”[1],现代西方文艺思潮对格非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形式实验和叙事技巧层面。虽然在《褐色的鸟群》等早期作品中,格非曾一度热衷于“迷宫叙事”“空缺”“拼贴”等小说技巧的探索,但随着对西方作家的进一步学习,他逐步认识到内容和思想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在八十年代,我们大家都说关键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后来在好多场合我都提到写什么同样重要”[2]。格非认为,借鉴外国小说的叙事技巧、进行形式实验固然重要,但作品的思想内核也不可忽视。因此,“对存在本身的深刻的怀疑和追问”[3]成为格非经常思考的问题。如果说《褐色的鸟群》《青黄》《陷阱》《没有人看见草生长》等早期小说传达了格非对存在可疑性、偶然性以及荒诞性的抽象化哲学思考,那么在《迷舟》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的《敌人》《边缘》等长篇小说中,格非则更加注重对生存困境的具体展现。他认为:“许多作家一生的写作都是围绕一个基本的命题,一个意念的核心而展开的,除了卡夫卡之外,陀斯妥耶夫斯基、加缪等都是典型的例子”,[4]这个“基本的命题”和“意念的核心”便是对存在的追问和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关注。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入考察,引发了格非小说创作中的“逃离”主题。
格非对社会现实中人们生存困境的关注,与20世纪90年代先锋文学的境遇以及中国的社会转型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初,先锋文学陷入了发展上的困境。作为一种精英文学,先锋文学曾彻底打破、颠覆了传统阅读方式和审美趣味,“造成了读者和作家的疏离”[5]。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场域表明,学院批评力量的捍卫是先锋文学在文坛引发轰动效应的重要因素。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文学期刊的“改刊”,学院派批评家极大削减了对先锋文学的支持力量。面对困境,马原逐渐淡出小说界,余华、苏童开始寻求创作转型。作为先锋派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格非,在忍受社会转型的阵痛中也尝试做出一些改变。社会的急剧转型不仅给经济文化带来深刻影响,也形成了新的生存困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成为调节社会结构的重要杠杆,金钱物质利益成为大众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在世俗利益的诱惑面前,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被最大程度地呈现。“无限度地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欲望被看成是人的内在本性”[6],“导致对于精神、灵魂、意义或超越问题的冷漠,对一切人文价值的冷漠”[7]。不论是知识分子精英群体还是普通大众,都处于精神危机之中。面对社会的急剧转型以及自身创作困境,将现实生活纳入小说创作成为格非实现“变化”的探索性方案。正如格非自己在《眺望·自序》中所言,他“试着抛开了那些所迷恋的树石、镜子,以及一切镜中之物”[8]1,开始探讨“文化和存在的境遇”[8]2。
2 从“出走”到“隐身”
出走和逃亡,是格非小说常见的逃离模式,涉及的作品主要有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的《敌人》《欲望的旗帜》以及新世纪的《山河入梦》。 几十年前发生的一场大火使赵氏家族逐渐走向衰败,虽经赵伯衡、赵景轩两辈人的苦苦找寻,纵火者却一直都未找出。因此,“敌人”作为一个空缺的神秘概念,一开篇便成为赵氏子孙挥之不去的梦魇。到赵少忠这一辈,其子孙赵虎、柳柳及猴子的离奇死亡,让大女儿梅梅对家族“敌人”的恐惧与日俱增。最终,集市上传开的关于赵家命运的谶言,迫使她出走他乡。此外,“出走”的逃离模式还表现在《欲望的旗帜》中,张末最后的出走不仅是她的一次无奈选择,更是她逃离以往矛盾感情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知识分子,张末在爱情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浪漫主义者,但现实的爱情却远非她所想象,小说结尾,流着眼泪的张末走向了候车大厅。一次离家出走的远行,是否能使张末结束理想与现实的自我分裂,我们不得而知。但对张末来说,“出走”是她经过内心挣扎后的一种自我解脱方式。相比之下,《山河入梦》中格非对姚佩佩的“逃亡”叙述则更加注重情节和过程。由于犯了杀人罪,姚佩佩不得不踏上逃亡之旅,而在逃亡途中,因与谭功达通信而暴露了行踪,在一种神秘力量的牵引下,她几经辗转,最终沿着圆圈式的路线回到了自己的逃亡起点。
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对时代的逃离,自杀显得更加决绝和彻底。《欲望的旗帜》中的高校教授贾兰坡、《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奇人”胡惟丏最终都以自杀结局收场。除了空间上的出走、逃亡以及自杀,“自我封闭”亦是格非小说人物的一种逃离模式。“自我封闭”主要存在两种形式,即禁语与“自我囚禁”。涉及的人物主要有短篇小说《沉默》中的高校学者柴峻以及《欲望的旗帜》中的小女孩姗姗。随着创作时间的向前推进,格非小说对主人公逃离方式的设定,呈现出温和化与人性化倾向。发表于21世纪的《春尽江南》和《隐身衣》,其主人公既不自杀也不自闭,而是以一种隐身方式与社会现实保持着距离。《春尽江南》中,无论社会如何剧变,身处市场经济时代的诗人谭端午仍选择待在地方志办公室,拿着微薄的工资,干着可有可无的工作。而《隐身衣》中的主人公崔师傅,与谭端午同为时代的“边缘人”,作为一位专门制作胆机的音乐发烧友,崔师傅对于外界,既不评论,也不附和,而是一心沉醉于自己的古典音乐世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生活。
不难看出,从“出走”到“隐身”,格非小说中的逃离模式在空间和程度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就空间而言,“出走”“逃亡”等模式主要侧重的是物理空间上的远距离逃离,而“自杀”“自我封闭”及“隐身”则侧重的是心理空间的远离。就程度而言,“出走”“自杀”“禁语”等决绝且彻底,而“隐身”则显得温和且暧昧。事实上,不同的逃离模式反映了格非在不同文化环境和思想状态下对人类存在处境的不同处理态度。作为新历史主义文本,《敌人》《山河入梦》在一定程度上承续了格非八十年代对“存在”问题的探讨,“出走”“逃亡”无疑成为最为符合情节发展和故事背景的“逃离”模式。而《欲望的旗帜》《沉默》以及《蒙娜丽莎的微笑》,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格非探讨社会文化转型的现实性文本。正如张末的“出走”不能解决其心中的困惑一样,空间意义上的逃离已不再能满足现代人寻求自我解脱的需要。因此心理上的“自我封闭”、彻底解脱——“自杀”或“隐身”,成为现代社会人们进行逃离的有效方式。而新世纪对“隐身”这一温和模式的设定,与格非对其行为主体——当代知识分子出路的选择倾向密切相关。在新的时代里,格非认为,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同现实社会的那种紧张对立状态应当有所改变,新世纪知识分子在保留20世纪80年代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应努力找到自身定位,虽然,“隐身”并非最好之选择,但亦是一种出路。
3 由缺席到探索的 “奔向”之所
悲剧作为文艺理论中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美学范畴之一,在格非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呈现,其表现之一便是逃离者“奔向”之所的缺席。在《欲望的旗帜》中,格非曾借主人公曾山之口阐述了自己对“逃离”的理解:“逃离……三十年后,这个词语更换了一个面目在他心中扎根,占据了他的全部意识,那就是‘奔向’。一个是另一个的原因或结果,但它们从本质上说也许是一回事。”[9]在格非看来,“逃离”在本质上意味着一种“奔向”。
而在20世纪90年代及之前的小说中,“奔向”却总是呈现出一种缺席状态。作为一位存在主义者,格非认为人类的生存困境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他不可避免地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形而上的怀疑与悲哀,一度将“逃离”下的“奔向”之所置于悬空和虚妄状态,从而使小说呈现出具有宿命意味的悲剧美学色彩。《敌人》中赵家大女儿是除赵少忠之外唯一存活下来的赵氏子孙,但作者运用“空缺”的叙事技巧,悬置了人物逃离之后的命运。赵家大女究竟会漂泊到何方,我们无从知晓,但孤身一人背井离乡无疑是该人物的又一悲剧命运。此外,《欲望的旗帜》中,张末虽然走向了车站,但她心中的迷茫并未有所消减,未来人生也无法预知;《沉默》中柴峻虽以禁语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逃离了时代的同化,最后也因理想成为笑谈而陷入无人理解的精神苦闷。而贾兰坡、胡惟丏等人虽然完成了永久的逃离,但个体生命的终结使未来和希望也一并葬送;小女孩姗姗的“自我囚禁”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实现了对外界的隔离,但这无疑给她的成长带来了新的局限和伤害。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皆无法看到“奔向”之所指向或允诺的美好未来。
到了新世纪,不得不说《春尽江南》与《隐身衣》打破了之前“逃离”主题的悲观消极色彩,反映了格非对“奔向”之所的探索和对人类精神“乌托邦”的追寻。虽然“江南三部曲”在一些评论者看来是格非对“乌托邦”幻灭后的凭吊和反思,但正如格非自己所言,“三部曲”的创作目的之一还在于唤起人们对梦想和乌托邦的记忆和向往。《春尽江南》与《隐身衣》是格非在革命乌托邦和社会乌托邦探索失败后的又一尝试。在格非看来,文学和音乐的世界始终是人类的两大精神家园,“文学的职能之一就是白日梦,在现实生活重压之下给我们提供一丝喘息”[10],而“一个人喜欢音乐,音乐给她带来了一个屏障,使得你听音乐的时候忘掉痛苦”[11]。在《春尽江南》与《隐身衣》中,格非为处于生活和精神困境的谭端午与崔师傅搭建了文学与音乐的精神“乌托邦”。在这里,谭端午找到了安顿灵魂的精神之所,而崔师傅则在古典音乐的纯净之地中,远离了那以邻为壑的社会竞争。
之所以出现此种转变,这与格非个人的文学观念和内在思想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80年代,由于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影响和对人类存在的存疑,初涉文坛的格非在小说创作上带有浓厚的悲观情绪。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见证了人们在转型时代的悲观境遇,并遭遇到作家知识分子身份带来的尴尬,无论对他人命运还是自身处境,格非一直抱有“迷惘”和“伤感”心理[12]。而到了新世纪,经过十年的沉寂与思考,正如格非所言,自己“终于想清楚了一些问题”[13]。他选择逐渐从以往厚重的消极情绪中走出,并再次相信文学对社会的“矫正与反省的力量”[14]。
4 结束语
人物“逃离”是格非小说创作研究的重要方向。格非小说的“逃离”主题源于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的涌入以及90年代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不仅令格非对存在主义哲学以及人类的生存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同时也使其小说的“逃离”主题愈加深刻和贴近现实。在小说中,格非设置了出走、逃亡、自杀等多样化的逃离模式。
通过以上逃离模式的设置,格非不仅塑造了包括当代知识分子在内的众多逃离者形象,而且表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精神心理物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余华、苏童、北村等先锋作家在转型过程中书写到逃离主题,且王小波、张炜、阎连科、徐小斌、陈染、虹影等其他当代作家也有所涉及。但就具体思想主题和塑造手法来讲,格非笔下的人物“逃离”更多地蕴含了他对独特私人经验和社会文化认知的个性化传达。人物逃离行为的主题化书写,一方面,表达了格非对人类存在的困境的深入思考; 另一方面,表现了其对转型社会下当代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注。因此,作为格非小说中的重要文本现象,人物“逃离”主题应该成为其小说批评的重要研究内容。
[1] 陈晓明.先锋派:当代性与开放性[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3(12):69-73.
[2] 张学昕,格非.文学叙事是对生命和存在的超越[J].当代作家评论,2009(5):58-73.
[3] 格非.欧美作家对我创作的启迪[J].外国文学评论,1991(1):115-116.
[4] 格非.塞壬的歌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34.
[5] 格非.何谓先锋小说[J].青年文学,2006(22):1.
[6] 大卫·雷·格里芬. 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9.
[7] 陶东风.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276.
[8] 格非.眺望[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9] 格非.欲望的旗帜[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26.
[10] 赵振杰.拒绝规训的白日梦写作[EB/OL].(2012-05-28)[2016-11-23].http://blog.sina.com.cn/s/blog-9f06697f0101575n.html.
[11] 孙若茜.格非的《隐身衣》,用“眼睛”聆听的音乐[EB/OL].(2012-07-20)[2016-11-23].http://www.lifeweek.com.cn/2012/0720/37956.shtml.
[12] 胡野秋.六零派文学对话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51.
[13] 格非,冯唐.关于文学:和格非问答.[EB/OL].(2012-10-16)[2016-11-23].http://culture.inewsweek.cn/20121016/detail-22675-1.html.
[14] 格非.文学对社会具有矫正与反省的力量[G]//王世龙,钟湘麟.名家名师名校名社团校园文学论萃.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40-44.
〔责任编辑: 刘 蓓〕
Escape and running toward — On “Escape” theme of Gefei’s novels
JIA Xiaome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 China)
As the creative theme caused by human survival dilemma, the characters “Escape” in Gefei’s novels has been highlighted.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literary current in the 1980s and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e 1990s form an important creative background of “Escape” theme of Gefei’s novels. And the setting of characters “escape” model and the exploration to place of rushing toward reflects Gefei’s deep thinking on human survival dilemma and human concern for the real society.
Gefei’s novels; survival dilemma; “Escape” theme
2016-11-14
贾晓梅(1993—),女,四川西充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7.42
A
1008-8148(2017)02-002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