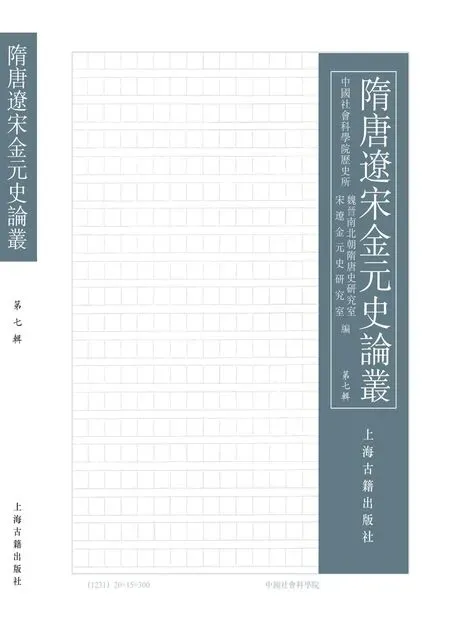時間法與唐代日常生活
——《天聖令·假寧令》劄記
牛來穎
對王朝統治中的時間秩序和規定,歷來是傳統社會日常行爲與政治倫理的準則。對相關問題的關注,成爲禮儀、思想、文化乃至經濟、制度史研究的對象。如楊聯陞《帝制中國的作息時間表》*《國史探微》,中信出版社,2015年,45—66頁。的貫通闡述,[日] 久保田和男對開封時空的細節注意所撰寫的《宋代開封研究》*王水照主編《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到[美] 司徒琳(LynnA.Struve)《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 從明到清時間的重塑》*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等等。時辰、時節到《時令》,反映出時間的多重層面的内容及秩序的漸進強化,直至宋代《時令》以令典的篇目形式出現在律令體系當中。本文擬從幾個例證來説明這一漸進過程在唐宋律令制度中的具體體現,從而展現這一時段時間法形成中漸次完善的歷史過程。
一
寧波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整理出版後,令條文字的解讀和制度史的把握關係至密,唐宋時期制度的變遷是對唐宋令異同理解的基礎和令文復原的依據,而對制度的長時段考察就顯得愈加重要。《天聖令·假寧令》宋19條記載:
諸私忌日給假一日,忌前之夕聽還。*《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中華書局,2006年,413頁。
日本《養老令》中没有這一條,仁井田陞《唐令拾遺》、池田温《唐令拾遺補》作了增補。此次復原,其依據是《天聖令》之前有的《大唐開元禮》卷三和《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員外郎條注文*中華書局,1992年,35頁。。今日所見的《天聖令》宋19條與二者文字相同,可以篤定此條保留了唐令令文的原貌而未作改動。
所謂私忌日,按照《資治通鑑》卷二三五“賈耽私忌”胡三省注曰:“父母及祖父母、曾祖父母死日爲私忌。”*《資治通鑑》卷二三五,德宗貞元十二年(796)九月條,中華書局,1956年,7575頁。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二敍述其源流:“舊法: 祖父母私忌不爲假。元豐編勑脩《假寧令》,於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意謂生時祖父母尚存爾。然不當言逮事,蓋誤用禮之文也。原爲此法者,謂生而祖父母死,則爲不假,存則爲假,所以别於父母也。”*《全宋筆記》第二編,十,大象出版社,2006年,24頁。則唐宋在私忌的理解和所包含的對象上是有所區别的。《假寧令》是對官員放假的規定,分作公假(節日、旬假、國忌等)與私假(婚喪、病假、探親等),私忌與國忌相對應,屬於私假。
按照規定,私忌日前一晚即“忌前之夕”官員得以還家,第二天放假一天。令文中“忌前之夕”的規定,顯然是唐代視事制度所規範的。《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記載:
凡内外百僚日出而視事,既午而退,有事則直官省之;其務繁,不在此例。*《唐六典》卷一,12頁。《唐會要》卷八二《當直》同。
賴瑞和《論唐代官員的辦公時間》*《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4期。相關内容收入《唐代基層文官》,中華書局,2008年,300—307頁。,後林曉潔《唐代西州官吏日常生活的時與空》*《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61—83頁。再論,唐代官員是有早衙和晚衙之分的,按照韓愈《上張僕射書》中對工作的不適應和要求改以一般的上班時間是:
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寛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 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80—182頁。
韓愈提出的“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以爲常事。按照上午寅至辰而退,是3—5時上班,9時回家;下午申至酉,是3—5時上班,至遲7時返家。這樣,唐令規定的“忌前之夕”就是在晚衙結束之後,也就是説,上完一天班再許可回家*十二地支計時法,每個時辰相當於如今的兩小時。即子時23—24時;丑時1—2時;寅時3—4時;卯時5—6時;辰時7—8時;巳時9—10時;午時11—12時;未時13—14時;申時15—16時;酉時17—18時;戌時19—20時;亥時21—22時。。
但是,令文没有規定何等人不在其中。《唐會要》卷八二《當直》有一條記載如下:
開元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是中書舍人梁升卿私忌。二十日晩,欲還,即令傳制報給事中元彦沖,令宿衛。會彦沖已出,升卿至宅,令狀報。彦沖以旬假與親朋聚宴,醉中詬曰:“汝何不直?”升卿又作書報云:“明辰是先忌。”比往復,日已暮矣。其夜,有中使賫黄勅,見直官不見,回奏。上大怒,出彦沖爲邠州刺史,因新昌公主進狀申理,公主即彦沖甥張垍之妻,云:“元不承報,此是中書省之失。”由是出升卿爲莫州刺史。*《唐會要》卷八二《當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796 頁。
上引史料中的當事人梁升卿,就是那件有名的由崔湜撰寫、完成於開元十一年(723)的《御史臺精舍碑》的八分書法的書寫者。中書舍人梁升卿在私忌日的前一晚想返家,但是他需要狀報請求别人幫忙,是因爲那天晚上他當值,而被他托付的人没有替他當班,以致中使送敕書時找不到直官,升卿因此被貶官。按照令文規定,既然允許在私忌日前一晚返家,爲何還要遭貶?原因恰恰是梁升卿正在值班,即當直。按照唐朝對直官的制度要求,當直者若不在崗是要受罰的。《唐律疏議》卷九《職制律》“在官應直不直”條有規定:
諸在官應直不直,應宿不宿,各笞二十;通晝夜者,笞三十。
疏議曰: 依令:“内外官應分番宿直。”若應直不直,應宿不宿,書夜不相須,各笞二十。通晝夜不直者,笞三十。
若點不到者,一點笞十。(一日之點,限取二點爲坐)。
疏議曰: 内外官司應點檢者,或數度頻點,點即不到者,一點笞十。注云“一日之點,限取二點爲坐”,謂一日之内,點檢雖多,止據二點得罪,限笞二十。若全不來,上計日以無故不上科之。*(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卷九,中華書局,1983年,185頁。
唐律中当直細節的約束是點檢,一天中不論幾次點檢,只計兩次,不到即受笞罰。這樣,梁升卿的受罰説明官員遇到私忌日給假一天,前一天的晚上得以回家的令文内容,是有特定例外或附加條件的約束,起碼直官不行。再比如《舊唐書》卷一三六《竇參傳》的記載,同樣是因爲宿值者缺位:
(竇)參習法令,通政術,性矜嚴,強直而果斷。少以門蔭,累官至萬年尉。時同僚有直官曹者,將夕,聞親疾,請參代之。會獄囚亡走,京兆尹按直簿,將奏,參遽請曰:“彼以不及狀謁,參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之。*中華書局,1975年,3745頁。
這條材料也是對於當直官離崗的處罰。重視行政辦事效率的大唐對於當直的紀律約束是嚴格的,從相關規定入律來看,對違反者是不留情面的,即使是私忌日前夕,也不能豁免。
進而再考察宋以後該制度的沿用,可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二的記載:
初,開寳中,文武官郎中、刺史、將軍以上,私忌日給假,其後,編敇者失不載,有司第相縁遵用。乙亥,始詔群臣自今私忌日並給假一日,忌前之夕,聽還私第。*《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二,真宗景德三年(1006)二月條,中華書局,2004年,1386頁。
《宋史》卷一二三《禮二六》也記載:
群臣私忌。開寳敕文:“應常參官及内殿起居職官等,自今刺史、郎中、將軍以下遇私忌,請准式假一日。忌前之夕,聼還私第。”*中華書局,1977年,2893頁。
可見宋初還是延續唐代令文,未作修改。這種情況延續了多久並不得知,但是現在從保留下來的南宋《慶元條法事類》來看,令文在南宋以前已經做了更改,增加了内容,具體爲:
諸應給私忌假者,忌前之夕直宿聽免。*楊一凡、田濤主編,戴建國點校《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第一册,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211頁。
説明至遲在《慶元條法事類》的時代已見到針對直宿者的立法,明確規定在私忌日前夕他們即使當直也獲准還家。不僅體現出令典的人性化,也是行政實踐中針對制度缺陷長期積累下來的問題最終解決的結果。此後不會再發生梁升卿之輩的爲難,更不會遭致貶官。
至此,唐令還僅僅是籠統規定了私忌日前官員聽還家,未針對當值者等特殊情況加以限定(或者像南宋令中的豁免)的内容,所以纔會一再出現像梁升卿所遇到的實際問題。由此聯繫到另一條令文的復原文字,似乎也可以提出再討論。這就是私忌日條的前一條令文,即宋18條:
諸遭喪被起者,服内忌給假三日,大、小祥各七日,禫五日,每月朔、望各一日。祥、禫假給程。若在節假内,朝集、宿直皆聽不預。*《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413頁。
在這條宋令當中,也有明確的對於朝集和宿直者的規定性内容,即使是地方朝集中央的使者,抑或當班的值官,這一類特殊身份者也獲准與普通官一樣放假。從立法精神上與宋19條應該是一致的。在針對宋19條作唐令復原時,池田温《唐令拾遺補》没有復原“若在節假内,朝集、宿直皆聽不預”十三個字。《天聖令·假寧令》的唐令復原文字则幾乎完全與宋令相同,僅“服内忌”後補“日”字,從《開元禮》;並認爲上述十三字的内容在《儀制令》中有所體現,所以認定爲唐令文字。這就是《唐令拾遺》所復原的《儀制令》第十八第六條:
諸文武官九品以上,應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以後二月二十日以前,並服袴褶。五品以上者,著珂繖。周喪未練、大功未葬,非供及諸宿衛官,皆聽不赴。*[日] 仁井田陞《唐令拾遺》,477頁。
第二五條:
諸齊衰心喪已上,雖有奪情,並終喪。不吊、不賀、不預宴。周喪未練、大功未葬,並不得朝賀,仍終喪,不得宴會。*[日] 仁井田陞《唐令拾遺》,505頁。
從仁井田陞復原的兩條來看,並没有關於當直官的内容,所以,依此來推斷上述文字應爲唐令原有文字,似乎證據不足。況且將宋18條與宋19條聯繫起來看,唐代似乎還没有對當直官的特别規定的可能性更大。故贊從池田温先生的審慎复原,“若在節假内,朝集、宿直皆聽不預”或非唐令。
此外,唐代除了前面所述十二時辰計時法以外,另一種計時方法也見於《天聖令》,如《關市令》宋9條:
諸關門並日出開、日入閉。管錀,關司官長者執之。*《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404頁。
唐8條:
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其市當以午時擊鼓三百下而衆大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下散。其州縣領户少之處,欲不設鉦鼓者,聽之。*《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406頁。
以“日出”、“日入”等根據太陽的出入爲參照的計時,從日出到日落爲一天,即莊子所説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莊子《讓王第二十八》。這種計時法結合漏刻,而分晝夜爲十八時。按馬融云:
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説。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孔安國《尚書注疏》附釋音尚書注疏卷二。
日出爲晝,日入爲夜,進而細分爲十八時,包括夜半,夜大半,雞鳴,晨時,平旦,日出,蚤食,食時,東中,日中,昳中,晡時,下晡,日入,昏時,夜食,人定,夜少半等十八時。而這種計時方法,更多的是與農業社會的生産實踐相聯的。
二
筆者曾經參加北大中國史研究中心榮新江主持的“長安讀書班”,就唐宋時期的假日進行過討論。按照《文昌雜録》的記載宋代的假期有76天,見該書卷一記載:
祠部休假,歳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慶節、上元節同天聖節、夏至、先天節、中元節、下元節、降聖節、臘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節、春分、社、清明、上巳、天祺節、立夏、端午、天貺節、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社、秋分、授衣、重陽、立冬各一日,上中下旬各一日。大忌十五,小忌四。而天慶、夏至、先天、中元、下元、降聖、臘,皆前後一日後殿視事,其日不坐。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大忌,前一日亦後殿坐,餘假皆不坐,百司休務焉。*《全宋筆記》第二編,四,大象出版社,2006年,117頁。
這是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祠部所訂立的新令,此時正式將鴻廬寺分管的官員放假等事宜全部收歸祠部。而《天聖令·假寧令》是宋仁宗天聖七年(1029)所頒定,兹移録所涉令文如下:
宋1 元日、冬至、寒食,各給假七日(前後各三日)。
宋2 天慶、先天、降聖、乾元、長寧、上元、夏至、中元、下元、臘等節,各給假三日(前後各一日。長寧節惟京師給假)。
宋3 天祺、天貺、人日、中和節、春秋社、三月上巳、重五、三伏、七夕、九月朔授衣、重陽、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立冬,諸大忌日及每旬,並給休假一日(若公務急速,不在此限)。*《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412頁。
表面看,《天聖假寧令》大忌日給休假一日,似乎與《元豐假寧令》“大忌十五”不一致,所謂十五者,是總計十五位皇帝的忌日,而遇每一位的忌日假依舊是一日。兩個《假寧令》的區别,首先是清明節的出現。在唐代清明節與寒食節爲同一節連假,即敦煌文獻P.2504《天寶令式表》所記載:“元日、冬至,並給七日。節前三日,節後三日。寒食通清明,給假四日。”而寒食清明放假時間的變化也恰恰發生在唐代。敦煌文獻S.6537v-14鄭餘慶《大唐新定吉凶書儀》記載:“寒食通清明休假七日(寒食禁火,爲介子推投綿上山,怨晉文公,公及焚山,子推抱樹而燒死。文公乃於太原禁火七日,天下禁火一日)。”時間上延長了。在史籍中也有所反映。如《册府元龜》卷六〇《帝王部·立制度一》:
(大曆)十三年,詔自今已後,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
(貞元)六年三月丙午,加寒食假寧七日。*中華書局,1960年,673頁,674頁。
直到元豐五年爲清明節立節,給假,而《天聖假寧令》還没有清明節單獨假日,是延續唐令體系的緣故。
其次是休務與放假間的關係。“休務”的記載不見唐代,這一辭彙雖然早見於前朝*如《北齊書》卷一三,“休務一日”。《北史》卷五一等。。唐代與之對應的是“廢務”,如《唐律疏議》卷二六《雜律》“忌日作樂”條:
諸國忌廢務日作樂者,杖一百;私忌,減二等。
尔議曰:“國忌”,謂在令廢務日。若輙有作樂者,杖一百。私家忌日作樂者,減二等,合杖八十。*(唐) 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卷二六,480頁。
《容齋隨筆》卷三《國忌休務》記載:
《刑統》載唐大和七年敕:“准令,國忌日唯禁飲酒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笞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蓋唐世國忌休務,正與私忌義等,故雖刑獄亦不決斷,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今在京百官,唯雙忌作假,以其拜跪多,又晝漏已數刻,若單忌,獨三省歸休耳,百司坐曹決獄,與常日亡異,視古誼爲不同。元微之詩云:“縛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又可證也。*(宋) 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卷三,唐宋史料筆記,中華書局,2005年,36—37頁。
同是國忌日,唐因以廢務,宋則稱休務,是爲放假。同樣,一個不甚明確的問題是哪些假日官員真正享受假期,而哪些假日官員並非休假,在唐令中並没有明確標注,故而宋人存疑。
又《容齋五筆》卷一《天慶諸節》:
大中祥符之世,諛佞之臣,造爲司命天尊下降及天書等事,於是降聖、天慶、天祺、天貺諸節並興。始時,京師宫觀每節齋醮七日,旋減爲三日、一日,後不復講。百官朝謁之禮亦罷。今中都未嘗舉行,亦無休假,獨外郡必詣天慶觀朝拜,遂休務,至有前後各一日。此爲敬事司命過於上帝矣,其當寢明甚,惜無人能建白者。*同上,831頁。
至《慶元條法事類》卷一一《給假》引《假寧令》規定:
諸假皆休務(軍期若頒謄赦降、給受官物、禁推罪人、領送囚徒之类,不用此令)。人日、中和、七夕、授衣、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立冬、單忌日並不休務。天慶、開基、先天、降聖、三元、夏至,臘前後日准此。*楊一凡、田濤主編,戴建國點校《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第一册, 211頁。
在休務與不休務上規定得非常明確,不會再有疑問。諸如“皇帝前後殿不視朝,百司作休務假”等類似的記載在《宋會要輯稿》中頻頻出現。休務的假日意味似乎更濃,更明確。
——德里達與胡塞爾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