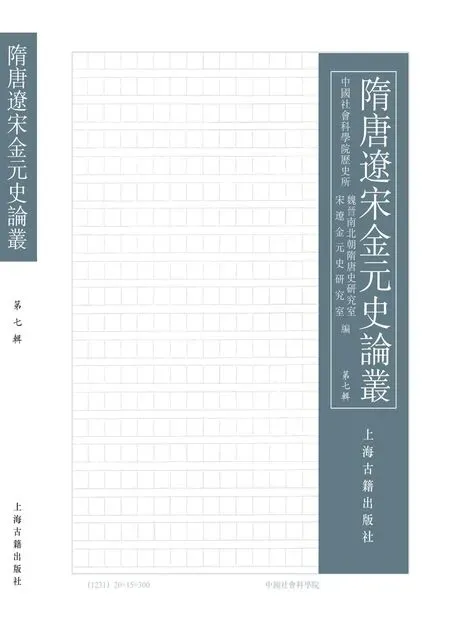13世紀蒙元帝國軍隊的戰利品獲取和分配方式詳説
周思成
一、 引言
《蒙古秘史》第195節講述,當成吉思汗率領蒙古軍與塔陽罕率領的乃蠻大軍在鄂爾渾河之東的納忽昆山相遇時,身處敵方陣營的札木合如是形容成吉思汗麾下兀魯兀惕和忙兀惕兩部軍隊的出陣:“聽説他們追趕有長槍的好漢,剥取染血的財物;追著,打翻,殺死有環刀的男子,奪取其財物……如今他們不是歡欣鼓舞地尥著蹶子殺來了嗎?”*阿爾達札布譯注《新譯集注〈蒙古秘史〉》,内蒙古大學出版社,2005年,361頁。札木合意圖通過描述蒙古壯士在戰鬥中攫取戰利品的凶狠勁頭,給塔陽罕留下深刻印象,不妨看作是張儀以“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恐嚇韓王之故伎。在熟悉内亞歷史的當代學人看來,“染血的財物”(戰利品)對於遊牧民族的吸引力和重要性幾乎是不言而喻的: 戰利品不僅直接補充了軍事行動的消耗,據説還是遊牧社會同定居社會進行物資交换的一種替代方式,遊牧社會的軍事領袖甚至通過戰利品及其他從“草原之外”榨取的物資加強集權化和支撐遊牧帝國*對内亞遊牧民族與劫掠戰利品之關係的一般研究,可參見蕭啓慶《北亞遊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收入氏著《元代史新探》,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303—322頁;〔美〕 巴菲爾德《危險的邊疆: 遊牧帝國與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11頁。史懷梅(Naomi Standen)對此也有準確的概括,見Naomi Standen, What nomads want: raids, invasions, and the Liao conquest of 947, in Mongols, Turks and others: Eurasian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ed. Michal Biran and Reuven Amitai (Brill), pp.129-174,以及Naomi Standen, Raiding and frontier society in the Five Dynasties’, in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ed. Nicola di Cosmo and Don Wyatt (Curzon Routledge),pp.160-191.。
蒙元帝國亦被認爲素來“以殺戮俘擄爲耕作”*梁啓超《中國文化史》,收入氏著《飲冰室合集》第10册,《專集》卷八六,中華書局,1989年,45頁。,戰利品對於蒙古征服者自然也具備上述多方面重要意義,迄今學界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卻遠不夠深入。弗拉基米爾佐夫(Б.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在《蒙古社會制度史》中曾引《蒙韃備録》説明蒙古軍的戰利品分配是“以分數均之,自上及下”,“同時常把一定份額獻與没有親自參加出征的蒙古汗、諸王和高級那顔”*〔俄〕 符拉基米爾佐夫著,劉榮焌譯《蒙古社會制度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180頁。。德福(G. Doerfer)在《新波斯語中的突厥語和蒙古語成分》一書中探討了在蒙元時代歷史記載中頻繁出現、專指“戰利品”之蒙文詞olja在蒙文和波斯文史料中的使用情況*G.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Band I,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63, pp.143-145.。拉契内夫斯基(Paul Ratchnevsky)在《成吉思汗: 生平與事業》中考證了成吉思汗在攻打塔塔兒部之前嚴令殲敵前不得哄搶戰利品的記載(《秘史》第153節),認爲此舉係對傳統遊牧習俗的破壞*Paul Ratchnevsky, Cinggis-Khan: sein Leben und. Wirken, Wiesbaden: Steiner, 1983, pp.61-62.。羅伊果(Igor de Rachewiltz)譯注《蒙古秘史》該節時強調:“早期蒙古人關於戰利品(war booty and spoils)獲取和分配的規定值得徹底研究一番,目前我們只好參考拉契内夫斯基在《成吉思汗》中的評論。”*Igor de Rachewiltz,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Brill: Leiden, Boston, 2004, Vol.1, p.568.以研究蒙元軍事史著稱的美國學者馬丁(H. Desmond Martin)和蒂莫西·梅(Timothy May)在討論蒙古軍紀時也提到過《秘史》第153節關於禁止哄搶戰利品的記載*H.Desmond Martin,The Mongol Army,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No.1 (Apr, 1943),p.77;Timothy May,The Mongol Art of War, Yardley,PA: Westholme Publishing,2007.pp.47-48.。徐美莉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則指出,蒙古族的戰利品分配與匈奴、鮮卑以及契丹、女真相似,經歷了從個人逐利向統一控制分配演進的過程*徐美莉《中國古代北方草原部族的戰利品分配方式及其演進》,《内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5年第4期。。以上幾種研究徵引的史料大體不出《蒙古秘史》、《蒙韃備録》和《黑韃事略》數種,結論也稍欠完整和準確。筆者擬在蒐集若干新史料的基礎上,盡可能全面和仔細地探討蒙古軍獲取和分配戰利品的規定和實踐*“戰利品”有廣、狹二義: 狹義的戰利品指“戰場上繳獲的敵人之物”,因直接軍事行動的勝利(如攻城之類)獲致的敵方物品則屬於較廣義的戰利品,至於因軍事優勢間接獲致的物質,則應屬“貢賦”等等。内亞遊牧民族的戰利品主要由財物(主要是牲畜)和俘虜構成。本文所指的戰利品係兼廣、狹二義而言,但不包括“貢賦”。,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二、 戰利品與遊牧社會的政治威權: 問題框架
如上所言,戰利品的獲取和分配在遊牧社會具有軍事、社會經濟和政治等多重意義,此處顯然無法一一加以申説。在這些維度中,政治(或言威權)這一維度不可不謂具有關鍵意義: 戰利品在遊牧社會各階層中的流動,即意味著財富和支配權力的流動,戰利品獲取、分配、維持和轉移,乃與政治權力之獲取、分配、維持和轉移交互影響,並時而否定、時而加強遊牧社會中政治軍事領袖的威權。唐武德五年(622)唐朝使者鄭元璹爲勸誘突厥接受和親,向頡利可汗指出:“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司馬光撰,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第13册,中華書局,1956年,5955頁。馬長壽先生將“虜掠所得,皆入國人”解釋爲“自古以來草原社會所具有的一種傳統制度”。見馬長壽《突厥人和突厥汗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88頁。此處戰利品(“虜掠所得”)就因其分配方式而被解釋爲一種削弱甚至否定可汗權威的資源。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在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看來,戰爭領袖也可以通過控制戰利品和榮譽的分配,對追隨者實施“威權主義”的控制*〔德〕 馬克斯·韋伯著,錢永祥譯《韋伯作品集: 學術與政治》,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202頁;〔德〕 馬克斯·韋伯著,康樂等譯《韋伯作品集·支配社會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277頁。。本文之宗旨,正是要探討蒙古大汗如何通過參與改變和塑造遊牧民在戰利品獲取和分配上的行爲規範,從而確立自身威權。具體而言又可分爲兩個方面:
(1) 對於不以攻城掠地爲目標的内亞軍事集團而言,在戰場上搶奪戰利品具有難以抵禦的誘惑力。明萬曆十七年(1589),努爾哈赤率軍圍攻趙家城:
圍四日,其城將陷,我兵少懈,四出擄掠牲畜財物,喧嘩爭奪。太祖見之,解甲與大將奈虎曰: 我兵爭此微物,恐自相殘害,爾往諭禁之。奈虎至,不禁人之擄掠,亦隨衆掠之。太祖將己綿甲復與把兒代,令往取奈虎鐵甲來,以備城内衝突。把兒代復隨衆擄掠。忽城内十人突出,有族弟王善,被敵壓倒於地,云云。*《清太祖武皇帝實録》卷一,見潘晶等編《清入關前史料選輯》(第一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313頁。
若無適當紀律加以規訓,遊牧民作戰中途放棄進攻敵軍而哄搶戰利品的行爲,必然阻礙乃至徹底破壞既定軍事目標的達成。新興的蒙古大汗威權如何超越遊牧社會的軍事習慣,調控戰利品的獲取方式?這一問題我們姑且名之爲“努爾哈赤難題”。
(2) 大汗威權並非遊牧社會的唯一權威,它並不能滲透到草原生活的各個角落,從而徹底排除私人、家長、部族權力或社會傳統習慣的制約,在戰利品的分配和占有上也是如此。圖爾的格列高里在《法蘭克人史》中講述了著名的“蘇瓦松封臣事變”: 在軍隊洗劫教堂後,法蘭克國王克洛維希望將一件被士兵奪走的聖器(一隻瓶子)還給教堂主教,遂至公開抽簽決定戰利品分配的廣場,在全軍面前請求額外多有所得(extra partem)。不料行伍中一位莽夫高吼:“除了你自己抽中的那份東西以外,這隻瓶子你一點也拿不到手!”並舉起戰斧砸碎了瓶子,克洛維銜恨默然。一年之後,克洛維在大檢閲時借口武器養護不佳,用斧子劈死了那名戰士,從而樹立起了威信*〔法蘭克〕 葛列格里著,壽紀瑜,戚國淦譯《法蘭克人史》,商務印書館,1981年,81—82頁。對“蘇瓦松封臣事變”的描述,還可參見〔德〕 馬克斯·韋伯著,閻克文譯《經濟與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430頁。。蒙古大汗的威權如何超越遊牧社會的占有習慣,調控戰利品的分配方式,甚至在占有成爲既定事實後仍然能(像克洛維那樣)直接插手干預分配?這一問題我們姑且名之爲“克洛維難題”。
要言之,本文所欲探討的僅限於蒙古大汗在不斷確立政治威權和締造帝國過程中,如何在戰利品獲取和分配上解決前述兩大“難題”。
三、 “努爾哈赤難題”的解決
《史集》記載成吉思汗父輩與金朝的戰事時,提到蒙古軍“殲滅了大量乞台人,並進行了劫掠。奪得無數戰利品(ūlj)在軍隊之間進行分配後,他們便回來了”*〔波斯〕 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務印書館,1983年,54頁。。從這條記載看,早在成吉思汗崛起之前,集結在部族軍事領袖周圍的遊牧集團中就存在某種戰利品獲取和分配的約定,可惜史料闕如,已經難以稽考。新興的蒙古汗權首次嘗試越過遊牧社會的傳統界限,規訓戰利品的獲取方式,應是《蒙古秘史》第153節所載成吉思汗出征塔塔兒前頒佈之“札撒”(1202)。《秘史》言:
交戰前,成吉思·合罕與衆議定了[軍]法,説:“戰勝敵人,不得逗留於[擄獲]財物上。一戰勝,那些財物[自然]歸於我們,大家可以分份。”*明代總譯作:“未戰之先,號令諸軍,若戰勝時,不許貪財,既定之後均分。”見阿爾達札布譯注《新譯集注〈蒙古秘史〉》,281—282頁。
《元史·太祖紀》也提到了這一事件:
歲壬戌,帝發兵於兀魯回失連真河,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二部。先誓師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慎無獲,俟軍事畢散之。”既而果勝,族人按彈、火察兒、答力台三人背約,帝怒,盡奪其所獲,分之軍中。*宋濂等撰《元史》卷一《太祖紀》,中華書局,1976年,8頁。
此外,《聖武親征録》和拉施特的《史集》也多次提到同一事件: 成吉思汗頒佈“戰時不許搶奪戰利品”的札撒,阿勒壇、忽察兒和叔父塔里台·斡惕斤“犯軍令搶物”,遭到没收戰利品的處罰*《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163—164頁,又41、60頁。。拉契内夫斯基在《成吉思汗: 生平與事業》一書中,充分肯定了“不許搶奪戰利品”軍令造成的權力格局變化:“這一法令與遊牧民之古老習俗相抵觸(gegen einen alten Brauch der Nomaden)。各部首領自有其擄獲之物,並分其一部與汗。如今鐵木真則要求全部擄獲歸自己所有,並按己意分配之。鐵木真雖然意識到,這一法令必將引起各部首領的不滿,但他更清楚,没有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他就無法戰勝優勢之敵。”*Paul Ratchnevsky, Cinggis-Khan: sein Leben und. Wirken, pp.61-62.這一禁止作戰中途擄掠戰利品的軍法,其後是否一直得到嚴厲執行呢?研究者並没有繼續探究。其實,中世紀歐洲曾親歷蒙古之地或目睹蒙古征服的基督教僧侣就留下了有趣的綫索。柏朗嘉賓(Plano Carpini)曾出使蒙古汗廷,他的《蒙古史》(IstoriaMongalorum)提道:“無論何人,凡在敵人的軍隊尚未被完全打敗時,就離開戰鬥,轉而擄取戰利品者,應嚴加懲罰,在韃靼人中間,對這樣的人要處以死刑,決不寬恕。”(Et sic similiter quicumque fuerit conversus ad predam tollendam, antequem omnino sit exercitus adversarioirum devictus, maxima pena debet mulctari; talis enim apud Tartaros sine ulla miseratione occiditur)*〔英〕 道森編,吕浦譯,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45頁。拉丁文見: Anastasius van den Wyngaert: Sinica Franciscana, Vol 1, Itinera et relationes Fratrum Minorum saeculi XIII et XIV, Ad Claras Aquas: Collegium S. Bonaventurae, 1929, p.97. 蒂莫西·梅已注意到這條史料與《秘史》第153節之關聯,參見Timothy May,The Mongol Art of War, p.48.1241年4月11日蒙古軍在奧賽河畔擊潰貝拉四世國王率領的匈牙利軍,匈牙利地方的副主教湯瑪斯(Thomas von Spalato)在描繪匈牙利人戰敗之慘狀時特意提道:“韃靼人因極度的殘暴,置戰利品於不顧,對珍貴細軟視而不見,一味地屠戮人衆。”(Die Tartaren kümmerten sich aber in ihrer unerhörten Grausamkeit nicht um die Beute, sie achteten die Erbeutung der Kostbarkeiten gering, sondern widmeten sich allein der Abschlachtung von Menschen)*Hansgerd Göckenjan und James R.Sweeney, Der Mongolensturm, Berichte von Augenzeugen und Zeitgenossen 1235-1250, Wien-Köln: Verlag Styria Graz, 1985, p.224.亞美尼亞史家乞剌可思(Kirakos)也提到,蒙古軍在擊潰谷兒只軍之後,纔“收集谷兒只人遺棄之戰利品,收兵回營。”(Les Tartares, ayant rassemblé le butin laissé par le Géorgiens, l’emportèrent dans leur camp)*Ed. Dulaurier, Les Mongols, d’après les historiens arméniens: fragments traduits d’après les textes originaux, 2eme fasc., extrait de Vartan / trad. par M. Ed. Dulaurier,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61, p.200.由這些目擊報告不難推測,蒙古軍在戰鬥中確實極少不顧追殲敵軍轉而搶奪戰利品,成吉思汗訂立的“戰時不許搶奪戰利品”的軍法,在蒙古帝國軍隊中一直得到較爲嚴格執行。不僅如此,其處罰措施甚至可能隨著大汗威權的擴張而愈加嚴酷(從最初的没收到處以死刑),這一點從後來伊利汗合贊的軍事改革中似乎也可得到佐證——據《史集》記載,合贊汗曾頒佈如下整頓軍紀之命令:“軍隊所發生的種種不幸,最常出在搶奪擄獲物(波斯文: ūlji giriftan)上。當戰鬥結束時,戰俘和擄獲物(波斯文: ūlji va ghanīmat)什麽地方也没有了。應當讓他們[指揮官們]爲了札撒,不顧情面、不惜殺死[違犯軍紀者]。”*《史集》第三卷, 378頁。波斯文見: Rashīd al-Dīn, Jmi’al-Tawrīkh, ed. by Muhammad Rawshan, Tehrn: Nashr-i Alburz,1953, p.1364.
四、 蒙古軍分配戰利品之主要原則:“等級”與“份額”
1202年頒佈的成吉思汗札撒不僅禁止了戰時哄搶戰利品的行爲,也爲戰鬥結束後統一集中分配戰利品創造了前提。如果説蒙古大汗威權在解決“努爾哈赤難題”時遇到的阻力甚小,那麽解決“克洛維難題”則要複雜和曲折得多。現有史料中缺乏對蒙古軍按照何種程式瓜分擄獲物的集中描述,故精確還原這一過程十分困難;不過,依據零散的史料,我們能勾勒出蒙古軍分配戰利品的四種原則,即1) “等級原則”,2) “份額原則”,3) “先占原則”,4) “均分原則”。變化雖多,大體不出這四種之外。這四種原則並不具有同等之效力,其中前兩種原則係主要之原則,後兩種係輔助之原則。兹請先論兩種主要原則。
對蒙古軍戰利品分配法最準確的描述,來自出使蒙古的南宋使節。宋寧宗嘉定十四年(1221)出使的趙珙在《蒙韃備録》中提道:
凡破城守有所得,則以分數均之,自上及下,雖多寡每留一份,爲成吉思皇帝獻,餘物敷表有差,宰相等在於朔漠不臨戎者,亦有其數焉。*王國維《蒙韃備録箋證》,《王國維遺書》第13册,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12頁。
“自上及下”是爲“等級原則”,“以分數均之”是爲“份額原則”。宋理宗紹定四年(1232)和端平二年(1235)兩度出使蒙古的彭大雅在《黑韃事略》中也記載蒙古軍“擄掠之前後,視其功之等差;前者插箭於門,則後者不敢入”*王國維《蒙韃備録箋證》,《王國維遺書》第13册,15頁。。所謂“功之等差”,亦屬一種“等級原則”。
1) “等級原則”所依據的主要是蒙古帝國内部的身份和權力等級。《蒙古秘史》第123節記載,阿勒坦等推舉鐵木真爲汗時立誓説:“你若做皇帝呵,多敵行俺做前哨,但擄的美女婦人,並好馬都將來與你;野獸打圍呵,俺首先出去圍將野獸來與你。”*阿爾達札布譯注《新譯集注〈蒙古秘史〉》,219頁。在遊牧社會中,圍獵與戰爭密切相關,兩者的制度安排也多具同構形態。由此不難斷定,“打圍”獲取獵物的等級或次序,也大致是戰時分配戰利品的優先次序。志費尼對前者作了十分準確的描述: 最先進入獵圈的是大汗,他捕獵完畢後便“觀看諸王同樣進入獵圈,繼他們之後,按順序進入的是那顔、將官和士兵”*〔伊朗〕 志費尼著,J.A.波伊勒英譯,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商務印書館,2004年10月,31頁。。因此,“大汗—諸王—那顔—將領—普通士兵”就是蒙古人分配戰利品等級秩序。再具體言之,首先,蒙古大汗對戰利品擁有最高和絶對之優先權*這種最高優先權亦可參考可薩突厥人戰利品的分配方式:“繳獲了戰利品後,士兵們會把所有的戰利品收集在一起,拿到國王的帳篷,由國王挑選出他中意的,其餘的分發給士兵們。”見桂寶麗著《可薩突厥》,蘭州大學出版社,2013年,29頁。。《蒙古秘史》第252節記載: 蒙古軍攻陷金中都後,成吉思汗遣失吉忽禿忽、汪古兒和阿兒孩合撒兒三人前往檢視中都府藏,金將合答“將金帛等物來獻”,二人受其獻,唯獨失吉忽禿忽嚴辭拒之:“昔者中都金帛皆屬金主,如今中都金帛已屬成吉思,如何敢擅取!”事畢報命,成吉思汗詢問三人曾受獻否,厚賜忽禿忽,而責讓汪古兒和阿兒孩合撒兒*阿爾達札布譯注《新譯集注〈蒙古秘史〉》,465頁。。其次,在上述等級秩序中,尚有一些特殊身份群體,如“出征處得的財物,圍獵時得的野獸,都自要”*參見韓儒林《蒙古答剌罕考》,收入氏著《穹廬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8—39頁。的答剌罕勳貴,以及少數功臣如鎮海和札八兒火者等,在攻陷金中都後,成吉思汗特許此二人登上高閣,向四方各射一箭,“凡箭所至園池邸舍之處,悉以賜之”*宋濂《元史》卷一二○《鎮海傳》,2964頁。。這類群體受大汗之私恩,可以看作“等級原則”中大汗最高優先權的派生物。
2) “份額原則”即按照固定之份額分配戰利品,相關史料遠爲稀少。除《蒙韃備録》中記載的“以分數均之”外,《秘史》第260節還記載: 蒙古軍攻陷花剌子模都城玉龍傑赤後,成吉思汗三子朮赤、察合台和窩闊台“將百姓分了,不曾留下太祖處的分子。及回,太祖三日不許三子入見”*阿爾達札布譯注《新譯集注〈蒙古秘史〉》,第482頁。。在全部戰利品中自蒙古大汗以下各貴族和官兵的份額(qubi)究竟有多少,尚不清楚,伊利汗國的制度(雖然帶有濃厚的伊斯蘭色彩)或可資參照,即“五分之一給伊利汗及其親族,剩餘的戰利品,騎兵是步兵的兩倍”*С.Л. Тихвинский, Отв.ред, Татаро-Монголы в Азии и Европе,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M.: Наука Страниц, 1977, p.233.。“份額原則”的起源其實較“等級原則”更早,其中份額之多寡,應該經歷了一個由遊牧社會等級陡峻化之前相對平均的“均分原則”(詳見後)到不平均的“份額原則”的演變。换言之,蒙古帝國時代的“份額原則”其實是同樣在“等級原則”背後運作的權力也扭曲了“均分原則”的結果,並通常與“等級原則”共同發揮作用。
最後還值得一提的是,貫徹於“等級原則”和“份額原則”中的大汗最高優先權,在元朝初年集中體現在所謂“外用進奉軍前克敵之物”上。《元典章》的《聖政》卷收有庚申年(中統元年,1260)四月的忽必烈詔書之一部分,禁止各級官吏以“撒花”爲名向百姓科斂財物,並允諾親自做出表率:“始自朕躬,斷絶斯弊。除外用進奉軍前克敵之物、並斡脱等拜見撒花等物,並行禁絶。”*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第1册,中華書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70頁。“外用進奉軍前克敵之物”的説法,似不見於他書,其實就是蒙元政權各處征討的軍隊自戰利品中選出並獻給元朝君主的精華。《元史》記載,至元十二年(1275)正月,南征大軍統帥“丞相伯顔遣使來獻宋寶,有玉香爐”*宋濂等撰《元史》卷二○三《方技傳》,4536頁。云云。南征軍前綫將領高興奉召入朝,“侍燕大明殿,悉獻江南所得珍寶,世祖曰:‘卿何不少留以自奉。’對曰:‘臣素貧賤,今幸富貴,皆陛下所賜,何敢隱俘獲之物!’帝悦,曰:‘直臣也’”*宋濂等撰《元史》卷一六二《高興傳》,3804頁。。蒙古大汗對臣僕敢於染指自己在擄獲物上的最高優先權往往採取零容忍的態度,如《漢藏史集》記載: 平宋後,伯顔見“蠻子國王有一珍珠寶衣,伯顔丞相説:‘此爲我戰勝之表證,’自取之,將其餘財寶等遣人呈送給皇帝”,後被告發入獄*達倉宗巴·班覺桑布著,陳慶英譯《漢藏史集: 賢者喜樂贍部洲明鑒》,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174頁。。阿合馬誣告伯顔擅取宋宫的“玉桃盞”,恐怕也是狡猾地利用了這一規則。
五、 蒙古軍分配戰利品之輔助原則:“先占”與“均分”
依據占有事實發生之先後確認戰利品歸屬的“先占原則”,以及均分戰利品的“均分原則”,是主要原則之外的輔助原則。將這兩種原則稱爲“輔助原則”,一是因爲“份額原則”和“等級原則”纔是在實踐中首先適用的、占據上位的原則,它們是明顯偏向於蒙古貴族統治階級的分配原則,只有在權位或身份不相上下的情形下,纔適用“先占”與“均分”作爲輔助原則解決戰利品分配上的爭執;二是“先占”與“均分”也是受到大汗權威影響較小的傳統分配原則,這兩種原則内在的平等和平均精神,甚至與主要原則内在的不平等(按等級分配)和不平均(按比例分配)傾向暗中對立(説詳後)。
3) “先占原則”。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較爲仔細地考證過“先占原則”在蒙古軍戰利品分配和明清蒙古法中的地位: 在古代法中,敵人的財物通常會被看作無主財産,並因此而能爲第一個占有人合法取得,而在早期的蒙古草原社會存在一種以“箭”爲標誌,宣示“先占”權利的傳統習慣。在戰利品分配過程中,經由這種使用箭矢的特殊程式,産生了一種對物的、具有排他性和優先性的支配權利*參見拙文《〈元史·鎮海傳〉中的“四射封賜”新論——蒙元法制史研究劄記》,《北方文物》2014年第4期。。此處僅據個别新發現的史料作一點補充分析。
蒙古軍在戰利品分配中適用“先占原則”的第一個證據來自前引《蒙韃備録》,其中提到蒙古軍攻下城池後,“擄掠之前後,視其功之等差;前者插箭於門,則後者不敢入”。不過,本條記載實質上説的仍然是按“功之等差”即“等級原則”來分配戰利品,只是在形式上採用“插箭於門”來表示先占意思。《元史·趙迪傳》記載,在蒙古攻破真定後,蒙古軍將領試圖擄獲瓜分城中人口,軍官趙迪保護下了千餘鄉親,他主張的便是自己對戰利品的先占事實和因之而産生的所有權:
先是,真定既破,迪亟入索藁城人在城中者,得男女千餘人。諸將欲分取之,迪曰:“是皆我所掠,當以歸我。”諸將許諾。迪乃召其人謂曰:“吾懼若屬爲他將所得,則分奴之矣,故索以歸之我。今縱汝往,宜各遂生産,爲良民。”衆感泣而去。*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五一《趙迪傳》,3596頁。
4) “均分原則”。前面已經提到,“份額原則”實是“均分原則”的一種變體——“均分原則”隨著蒙古大汗威權的建立和帝國構建,不斷向更不平均的“份額”分配制度過渡。可見在等級化不夠陡峻和固化的“前蒙古帝國時代”,草原遊牧社會對共同獲得的戰利品的分配方法,應主要是將擄獲物品劃分爲等分,並在個體間平均(抽簽)分配。蒙古入侵歐洲的重要目擊者之一,聖寬庭(Simon de Saint-Quentin)在《韃靼史》中記録了一則殘酷然極具代表性的逸事,他提到在蒙古人第一次入侵谷兒只地區時,三個蒙古士兵合夥伏擊並俘虜了一家谷兒只貴族連同他們的大量財物:
這三個韃靼人議定這樣分配人口和財物: 一人獲得大貴族,一人獲得貴族之子,一人得黄金,婦女則賣掉三人均分,那個得到貴族之子的人反對説:“爲什麽分給我這個像小狗一樣的小孩兒?我還得養活他。這絶對不行!”最終他們議定了另一個解決辦法: 父與子都殺掉,三個人均分金子,然後把婦女賣掉。*J. Richard: Au-delà de la Perse et del’Arménie. L’Orient latin et la découverte de l’Asie intérieure. Quelques textes inégalement connus aux origines de l’alliance entre Francs et Mongols (1146-1262), Turnhout: Brepols, 2005, p.107.
由此可見,蒙古帝國時代給“均分原則”留下的空間,僅剩下在身份、權位和功勞完全相同情況下,特别是在成千上萬的普通士兵之間的分配。當然,儘管“均分原則”不屬於占優勢的主要原則,並不意味著它的實際應用不廣泛,恰恰相反,它恐怕是那個戰亂年代中最廣泛出現的事件之一。
須附帶論及的是,主要由“先占”和“均分”(當然也包括“等級”、“份額”)等原則造成的戰利品分配,在現實中進一步産生了兩個次生的權利或制度安排: 其一,私人得享有擄獲到的戰利品之所有權,且由國家承認並保障之。這一點後來體現於至元十五年(1278)忽必烈頒佈的“省諭軍人條畫(二十三款)”,條畫之一旨在保障軍人“出軍時得到些小討虜”應得的權益,明確規定:“出軍時,軍人討虜到人口、頭疋一切諸物,各自爲主。本管頭目人等並不得指名抽分拘收,亦不得羅摭罪名,騙嚇取要。”*《元典章》卷三四《兵部》卷之一《省諭軍人條畫》,陳高華等點校,第1册,1169頁。其二,私人得享有擄獲到的戰利品之處分和交易權。由這一交易權則衍生出蒙古軍營中頗具特色的擄獲物交易市場。《經世大典·敍録》記載: 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軍隊在南甸附近擊潰緬軍,“捕虜甚衆,軍中以一帽或一兩靴、一氈衣易一生口”*蘇天爵《國朝文類》卷四一,《四部叢刊初編》影元至正西湖書院刊本。。《史集》也記載: 伊利汗阿魯渾擊潰捏兀魯思叛軍之後,發現從札木到也里漫山遍野都是叛軍遺棄的牲畜,“蒙古人捉住[被拋棄的]牲畜牽走,在村裏按每頭羊一答捏克出售。在不得擅取戰利品(ūlj)的命令發出後,他們纔不敢更多地捕捉”*〔波斯〕 拉施特主編,余大鈞譯《史集》第三卷,248頁。波斯文見: Rashīd al-Dīn, Jmi’al-Tawrīkh, ed. by Muhammad Rawshan, p.1223.。
六、 總論
1) 戰利品獲取和分配上的“努爾哈赤難題”和“克洛維難題”,並非遊牧民族獨有的問題,毋寧説,一切軍事性質的威權的崛起必然或多或少要面對這些問題,唯獨對於草原遊牧帝國而言,形勢或許更加急切和嚴峻。蒙古大汗在確立和擴張權力的過程中,頒佈了“戰時不許搶奪戰利品”的札撒,較順利地克服了“努爾哈赤難題”,規制了戰利品的獲取方式;而爲了解決“克洛維難題”,蒙古軍逐漸發展出一套解決戰利品分配爭執的制度安排,大體可用“等級”、“份額”、“先占”和“均分”四種原則來概括之。
這四種原則並不在同一層面發揮作用,“份額原則”和“等級原則”之所以成爲主要原則,是大汗威權進一步滲透、改變和塑造遊牧社會傳統行爲方式的結果,二者一縱一橫,構成了蒙古帝國軍隊分配戰利品的主要制度框架;相反,“先占原則”和“均分原則”之所以成爲(更準確地説是淪爲)輔助原則,是因爲二者原是遊牧社會的傳統分配規則,隨著蒙古帝國的建立和擴張,這兩種原則被占支配地位的權力不斷排斥並邊緣化,最終下降爲較次要的原則,僅僅在主要原則得到滿足後,纔適用於在那些權位或身份相牟的個體之間解決戰利品歸屬爭議的情形。主要原則與輔助原則是既對立又互補的關係。
2) 若進一步考察蒙古軍以札撒和四種原則爲框架的戰利品分配制度,還可以發現如下兩個特徵: 一方面,在新興蒙古汗權支配下形成的這一套體系,建立在盡可能尊重草原傳統的基礎上,舊傳統和舊習俗並未被家産制國家的立法徹底取代或破壞,公共權力也未自上而下地侵占一切社會空間。在戰利品分配上,它就小心翼翼地爲習俗留下了活動餘地,默許私人對戰利品的先占和各自所有權,放任均分原則調節底層爭端等等;但另一方面,從總體趨勢看,集權化國家逐漸排斥帶有平均與平等主義殘餘的草原傳統,這一趨勢也十分明顯: 加強並維護蒙古上層貴族利益的不平等和不平均的戰利品分配原則,壓制草原社會原初的主流規範,成爲上位原則。
特别是在元朝建立前後,第二特徵或趨勢呈現出加速發展的勢頭,首先表現在國家對擄獲戰利品(尤其是預計將成爲國家財政收入基礎的民户人口)採取了進一步的管控。例如,元朝軍隊於“俘馘”有“申報”之制(“軍官凡有所獲俘馘,申報不實……委監察並行糾劾”)*《元典章》卷五《台綱》卷之一《設立憲台格例》,陳高華等點校,第1册,145頁。,又有“分揀”之制(“捕叛賊軍官、軍人虜到人口,本管出征軍官與所在官府隨即一同從實分揀……委系賊屬,從本管萬户、千户出給印信執照,中間卻有夾帶良民,罪及軍官”)*《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卷之一九《禁乞養過房販賣良民》,陳高華等點校,第3册,1881頁。,在征服南宋和平定内亂的戰爭中,元廷甚至三令五申力圖制止軍隊劫掠地方。這類禁令在元初記載中比比皆是,無待臚列。在這種情形下,遊牧民對於戰利品的傳統權利,顯然又不得不讓位於王朝建立合法性的迫切需要。甚至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元軍統帥有權剥奪任何一件依“各自爲主”原則已經歸擄獲者所有的戰利品。在決定南宋王朝最終命運的崖山一戰中,陸秀夫“以金璽繫主腰”,抱幼主自沉:
二帥(按: 謂張弘范、李恒)止謂世傑必奉幼主南奔,恒率海舟追逐,宏範留部分降,時訊降人,始知祥興君相俱赴水,遂大搜金帛,拘括將士,所掠皆歸宏範。尋於軍中得金璽,訊之,卒云: 於小兒浮屍上得之,不識爲璽也,懼爲人所知,棄其屍矣。*佚名《昭忠録》,守山閣叢書本,216頁。
在作爲元帝國統治階級代表的張弘範身上,哪還有半點克洛維面對傳統時嚅囁畏縮的影子呢?總之,元代國家要求在戰利品獲取和分配上擁有更多的支配性權力,再度壓縮了草原傳統習俗的活動空間。蒙古人解決戰利品獲取和分配中“努爾哈赤難題”和“克洛維難題”的嘗試,同時凸顯出家産制國家形成過程中,公權和草原傳統的私權之間的種種張力和矛盾,真實地反映出在蒙古人建立帝國的過程中,集權化和官僚化的邏輯如何最終取得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