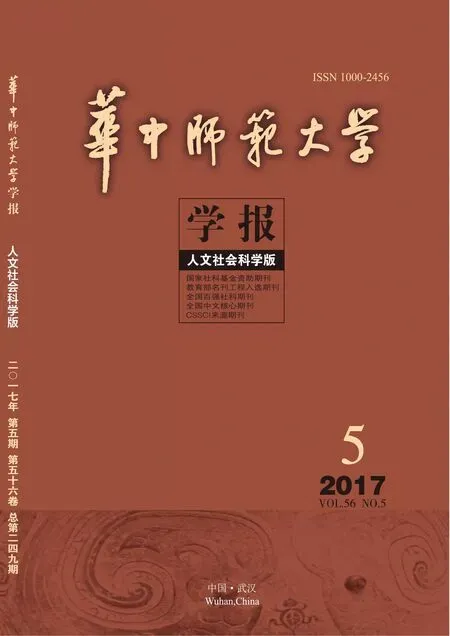十六国北朝政区演变的背景、特征及趋势略论
——以特殊政区为中心
牟发松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062)
十六国北朝政区演变的背景、特征及趋势略论
——以特殊政区为中心
牟发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062)
魏晋以来,直至十六国、北朝前期,伴随着北境诸少数族或主动或被动内徙,秦汉以来的郡县制政区从北方边境渐次后撤,而代之部落组织式的或军事统制式的特殊政区,即领民酋长、地方护军、军镇,以及地方行台等。北朝后期(大致始于北魏孝文帝朝),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化,统一进程的加速,反映在政区上则是特殊政区的普遍退出,郡县制政区的全面回归,这正是十六国北朝政区演变的大势所趋。
十六国北朝; 政区演变; 特殊政区
一、十六国北朝政区演变的总体趋势
自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巴賨李雄在四川、匈奴刘渊在山西相继建立政权,至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魏灭北凉统一中国北部,曾先后出现各族割据政权近二十个,史称“为战国者一百三十六载”①。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就是记载这些“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即刘渊(汉、前赵,匈奴)、李雄(成汉,巴氐),张轨(前凉,汉)、石勒(后赵、羯)、慕容儁(前燕,鲜卑)、苻健(前秦,氐)、姚苌(后秦,羌)等“十有六家”的历史②,后世遂以“十六国”指称这一时代。
作为历史朝代名的“北朝”“南朝”则得名于正史,即唐人李延寿所撰《北史》《南史》。延寿在《上南北史表》中,称二史分别记载“自魏以还”的“北朝”和“从宋以降”的“南朝”的历史③,可知《南史》《北史》之“南”“北”,实为“南朝”“北朝”之省称。事实上南北朝当时人,即以南朝、北朝自称、称人④。公元581年杨坚受周禅称帝,建立隋朝,北朝遂告结束,但就南北对峙而言,周隋嬗代不过是从陈周对立转变为陈隋对立而已。严格地说,直至589年隋灭陈,作为西魏北周后续政权的隋朝仍为北朝的延伸。唯其如此,故李延寿《北史》仍将隋朝包括在北朝之内,叙事“尽隋义宁二年(618)”亦即李渊代隋称帝之年⑤。
结束十六国的北魏,纵跨十六国和北朝两个时代,在北朝历史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高欢控制的东魏和宇文泰控制的西魏,元氏皇帝虽为傀儡,但两魏仍以北魏的正统继承者自居,北齐、北周不过是东魏、西魏的后续政权而已。因此之故,李延寿《北史》即始于“自魏以还”,上溯至北魏道武帝复建代国的登国元年(386),而非北凉亡国之年(439)。但就行政区划史而言,北魏真正意义上或者说符合充分、必要条件的政区⑥,尚待道武帝皇始元年(396)攻占后燕并州,“仍置”即承后燕而置的并州及其所属郡县⑦,而其政区体系的正式形成,还要等到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攻占后燕河北地区之后。故我们讨论北朝行政区划,实自北魏初入中原的皇始元年(396)始,至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禅隋退位止。
我们将十六国和北朝的政区合并讨论,既在于二者时间上前后相续,甚至可以说是无缝对接:北魏的兴起、灭国与复国,与所谓“五胡”诸族在内地建立政权特别是前秦的兴亡密切相关,十六国最后一个政权北凉即为北魏所灭,空间上两个时代均以北中国为主要活动舞台;更在于二者包括政区变化在内的社会、政治进程,原为一具有内在联系的历史过程。如果要对这一过程及趋向略加概括,那就是在民族关系上由胡(诸内迁少数族)汉对立而趋于胡汉融和,政权形式上从多边分裂走向统一。与之相应,地方行政区划也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或曰两种方向,来把握此变化的态势及趋向。
一方面,伴随着北境诸少数族或主动或被动内徙,秦皇朝创立的以郡县制为标志的传统政区(下文简称“郡县制政区”)被迫从北方边境地区后撤,代之以部落组织式的或者军事统制式的非郡县制特殊政区⑧。这种特殊政区并不始于十六国北朝,可以说在郡县制全面确立的秦汉时代就有出现,魏晋时期日益增多,而在所谓“五胡十六国”时代,这种特殊政区不限于边境,还一度交错杂存于长期以来实行郡县制的内地。
特殊政区的大量存在,是十六国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
与此同时,传统的郡县制政区,在政区层级、数量乃至地方统治方式上也发生了若干重大变化,如地方行政机构的军事化,又如出于对地方大姓豪强、少数族酋豪既有势力的承认和收编,增设郡县以署抚豪酋、酬赏劳勋,导致政区滥置——郡县制政区的密集化、细分化,甚至还出现了郡县制政区和特殊政区同治一地、其长官一身二任,以及“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县置三令长”,“刺史令长各之州县”而太守“虽置而未临民”等非常可怪之现象⑨。上述变化主要发生在十六国和北朝前期。
另一方面,伴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化,统一进程的加速,反映在政区上则是特殊政区的逐步退出或曰向传统郡县制政区的回归。北朝后期(大致始于北魏孝文帝朝)在政区层级数量上以省并精简为核心、在地方与中央关系上以削弱地方权力为旨归的努力⑩,都促使郡县制政区的本质属性——作为秦始皇创立的中央集权体制的代表性制度,或曰君主专制集权得以实现的保障性制度,逐步恢复和强化。隋朝初年将行政区划从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或郡县)二级,同时“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对政区大加省并,并将过去由州郡自行辟署当地大姓豪强为僚佐的权力尽收于中央,“皆吏部除授,每岁考殿最”,这可视为北朝后期行政区划演变趋势的总结。
二、特殊政区的大量存在——十六国及北朝前期政区建置的一个重要特征
十六国北朝的特殊政区,是指此期带有地方行政区划性质的领民酋长、地方护军、军镇,以及作为高层政区的地方行台。谓之特殊政区,除了在治理对象、方式上有异于一般郡县制政区外,还在于其中有的不见于前此时代,如领民酋长、军镇;有的虽名称见于前代,但实际内容却发生了变化,从而具有了政区性质,如护军、行台。
这类特殊政区虽不始于十六国北朝,但十六国北朝特殊政区名目数量之多,分布地区之广,设置时间之长,则为前此时代所未见。五胡诸国及北魏前期在政治体制上残留着大量的游牧部族传统,即部落制残余,以及基于部落制的社会组织军事组织合一、军政民政合一的治理体系。为了统治包括汉族在内的在人口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非本族民众,“五胡”诸国(包括北魏前期)大多建立了基于民族对立和民族统治的特殊政区,有的学者称之为“异民族统御官”。胡汉分治(乃至胡胡分治)和军事化,正是其特殊性所在。
虽然民族对立、胡汉分治是十六国北朝特殊政区产生、演变的基本动因,部族制残余和军事化统制是这些特殊政区的特殊性或曰共性所在,但各种特殊政区仍各有其特点。
正式出现于北魏的领民酋长制,以部落组织的存在为前提,并与北魏的部落解散政策相须而行。近些年来日本学者特别强调十六国北朝的所谓“胡族体制”,即以胡汉分治、注重部族制传统为特征,领民酋长制堪称其典型。领民酋长制及相应的部落解散政策虽正式出现于北魏前期,实则取法于十六国。
如果说领民酋长制基本上保持了原少数族部落固有秩序,国家通过部落首领对部民实行间接统治,领民酋长自领其部落、自治其部众,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民族自治色彩,有类于秦汉“因其故俗”的属国和道,那么,护军和军镇则具有强烈的军事统制和民族压迫性质,是一种管理、统治少数族或曰异民族部落组织的军管机构。护军通常设置在统治民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这些少数族的部落组织往往被保留,因而护军又称为“诸部护军”。护军原本为统军的武职(护军将军),作为以军统民、政军合一的军管机构的地方护军,照例由军将出任,“军府”为其职能机构,属僚亦多同于“护军将军”府属官,其军事统治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顾名思义,军镇的军事性更不待说,它原本脱胎于军队的驻防镇守之所。五胡诸国包括太武帝统一北方之前的北魏,主要是通过设置于交通要冲的军事据点对其统治地区实行点的控制,平时以武力威慑,乱时则出兵镇压。这些军事据点就是军镇的前身。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实已军镇化,只是到了北魏,“镇”和“镇将”才正式成为以军统民的一级政区及其政军长官的名称。就以军统民、政军合一而言,护军与军镇名异而实同。而且北魏军镇亦多设置于少数族聚居地,最初主要针对柔然、敕勒等北边游牧族而设置在北部边境(六镇)。对鲜卑拓跋族而言,汉族同样是异民族,只是由于汉族人口众多,分布广泛,因而只能在一些战略重地择要设镇,以配合内地长期实行的传统的郡县制政区。护军与军镇在产生原因、分布区域、统治对象、政区级别以及终止时代等等方面,也有显著的差异。魏末北齐因应世乱兵兴局势而出现的地方行台,作为高层政区,其产生机制仍与两汉以来的州刺史、都督诸州军事相类,即根源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由中央派出的监察机构和军区转化而来。只是北朝的最高统治核心为北族勋贵集团,其军队构成亦以鲜卑族及其附从部落以及鲜卑化汉人为主,而且行台的设置也主要在于防范和镇压其他少数族及汉族人民的反抗,因而在军事性之外,行台又带有一定的民族统治色彩。
三、特殊政区大量存在的民族背景及制度渊源
以特殊政区大量存在为特征的十六国北朝政区的变化,原因诚然是多方面的,有些变化如政区设置的密集化、细分化、军事化,在东晋南朝也有发生,但民族因素——边境少数族的内迁及建立政权,无疑是十六国北朝政区演变最重要的背景和原因,而变化的渊源可以上溯到东汉初年匈奴之分裂为南北两部,甚至更早。
“五胡十六国”联称而成为一固定词组,至迟已见于元代文献。“十六国”一词出现于北魏已如上述,而“五胡”一词在十六国当时即已出现,苻坚面叱姚苌“五胡次序,无汝羌名”,为治史者所熟知。“五胡”即匈奴(胡)、羯、鲜卑、氐、羌。十六国中五胡所建者凡十二国,但五胡所建政权并非全部纳入十六国,如鲜卑人所建西燕、代国就不在其中。十六国亦非全为五胡所建,如前凉、北燕、西凉即为汉人所建,成汉为賨人(巴氐)所建。不过创建北燕的冯跋虽出自长乐信都,但其父“东徙昌黎”之后“遂同夷俗”,实为鲜卑化汉人。北魏为鲜卑拓跋部所建。魏分东西以后执政西魏并最终代魏建周的宇文氏,为鲜卑族。执政东魏、其子最终代魏建齐的渤海高欢,史称其为渤海蓨人,然自高欢祖父“坐法徙居怀朔镇”,“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实即鲜卑化汉人。总之,十六国北朝的创建者大多为北边少数族,当时被概称为“胡”。诸胡族所建政权,直至今日学界,仍被习称为“胡族国家”、“北族国家”。相对于此前的秦汉、三国西晋,以及同时代南方的东晋南朝,这批胡族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独具特色。长期以来,研究者以“胡汉分治”、“胡汉二元(重)体制”(乃至“一国两制”之类表述)来概括其特色,在学界基本上已形成共识。
以往研究亦表明,尽管诸胡族的社会发展程度并不一致,内迁及建立政权的时间早晚有别,所建政权在制度设施及统治结构上也各不相同,但就其中多数国家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体制的主要特征而言,用“胡汉二元体制”来概括是大体合适的。进而言之,胡族国家的特征,实际上是由二元体制中的胡族因素或曰胡族体制这一元所决定的。胡族因素也深深影响到十六国北朝的地方统治体制和行政区划设置。
所谓“胡族因素”、“体制”,就其原始面貌、典型特征而言,要之有二:其一是主要经济形态为游牧,与之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上的流动不居(“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其二是基本的社会政治组织为血缘结合的部落制(部族制),与之相应的兵民合一(“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的部落兵制、军事民事合一的治理体系,其部落联盟国家即为高度军事化的“日常战斗共同体”(“以马上战斗为国”)。其中部落制、军事化对胡族国家政区设置的影响最大,在特殊政区的设置上体现得最为显著。
差不多与秦帝国同时兴起的匈奴游牧帝国,也不过是部落制在更高联合层面上的复制和整合。单于之下的地方官体系二十四部首长(万骑)及其所属千长、百长、什长,即是不同层次的部落联合体首领,下至作为基层游牧生产生活单位的牧团的酋长。如果说有政区,那就是这些部落联合体范围大致稳定但时有变动的驻牧区,政区首长则是这些不同层面的部落集团首领。在“分枝性结构”的游牧社会政治体制中,具有“平等自主化”倾向的部落组织从来未曾消失过,无论是北部蒙古草原建立了大型游牧汗国的匈奴,还是东北部西辽河流域森林草原地带建立了“部落联盟”的东胡(乌桓、鲜卑),更不用说西北部河湟高原河谷地带长期处于部落分立、纷争状态之中的西羌及氐等游牧人群。如果说汉武帝伐匈奴“取河南地”置朔方郡,降匈奴浑邪、休屠二王于其故地置河西四郡,开西南夷置武都郡等,是汉式郡县制政区向胡族游牧区的扩张,那么,两汉之际下至魏晋,北边游牧部族或主动侵入、或被允许迁入,或被强制移徙至帝国边郡乃至内地,则是胡族部落式、军事化的地方统治方式对郡县制政区的取代。如东汉初因匈奴南侵被迫放弃雁门、代、上谷三郡,吏民六万余口内迁,北地、朔方、五原、云中、代诸郡亦迹近废弃,故至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南匈奴八部降汉,即被安置在这实际上已不为汉朝控制的八郡中,南单于庭亦由五原西部塞而云中而西河美稷而离石,节级南迁,匈奴部族亦随之蜂拥南下,至魏晋时已深入至并州汾水流域。随着匈奴部族的内徙,原由匈奴控制的东胡乌桓,逐步内迁至辽东、辽西、太原、朔方等沿边十郡,同属东胡的鲜卑亦步乌桓后尘而渐次南徙、西迁。原居于大鲜卑山的鲜卑拓跋部,东汉时南迁至匈奴故地即阴山一带,及至西晋末拓跋猗卢受封代公,取得句注陉北地区五县地,乃率部落南徙居之。西北的氐、羌各族,东汉一代多次被成批迁入关中,如建安二十四年(219),曹魏一次即徙氐人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二郡界内,其后又多次移徙户以万计的武都氐族于关中。东汉一代,曾多次移徙西羌到关中三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诸郡也有羌族分布,号称“东羌”,常与胡连称为“羌胡”,他们可能是东汉前随从匈奴从塞北、河西一同迁来。东汉时羌人多次举兵,一度建立滇零政权,汉廷不得不诏令陇西、安定、北地、上郡四郡郡民内徙,被镇压的降羌遍布关陇。及至魏晋,众所周知,“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戎狄居半”,与之相应的则是郡县制政区的大幅度后撤。
“胡俗以部落为种类”。东汉以来内迁诸胡长期与汉族错居杂处,但直到西晋末,他们基本上都保持着各自的部落组织,部落首领以往的名号、地位也得以保留下来,他们迁徙到哪里,就把部落组织带到哪里,郡县制政区实际上也就从哪里退出。汉武帝时对于率部降汉后被安置在西北五郡故塞的匈奴浑邪、休屠二王,“因其故俗”置五“属国”。所谓“故俗”,即是保存原来的国号、官称和部落组织,乃至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属国虽臣属于汉,汉设有都尉进行管理,实际上为一自治性的特别行政区。汉光武帝时对于叩关入塞附汉称臣的南匈奴呼韩邪部,汉朝设有“将兵卫护”即加以保护、监督的“使匈奴中郎将”(又称“护匈奴中郎将”),但对于南单于所统八部,仍由各部“大人”统领,分驻于北地、朔方等八郡中,中郎将官署和驻军并不直接干涉南匈奴部族的内部管理,实为一个有特定监护对象、戍守地域的军管、防戍区。建安中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立各部“贵者”为部帅(后改都尉),尽管配置“汉人司马以监督之”,使部帅对部落的统治权受到削弱,但五部仍然是以部落组织为基础,由部落酋长担任部帅(后来都尉司马亦有胡人充任),从而成为具有高度自治性质的特别行政区。
汉魏朝廷对于“保塞降附”或经汉朝同意附塞、内迁的乌桓、鲜卑、羌、氐诸族,处置方法一如匈奴:或置属国,如“以处降羌”的金城属国,管理归附的乌桓、鲜卑的辽东属国;或置“使匈奴中郎将”之类的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等。“因其故俗”的间接统治方式则一如既往。
总之,汉魏朝廷对于主动归附或者被迫内徙的胡族部落,往往在安置地设置管理机构,驻军监护,同时给部落首领授予汉式官爵,但这些内迁的胡族部民,朝廷所设官署或驻军机构并不直接统治他们,他们仍旧生活在部落组织中,受原部落首领的直接领导,朝廷所设政军机构不过是通过部落首领对他们进行间接管理而已。于是内迁胡族部落的安置、聚居区,就原部落组织而言,是一个自治行政区;由于兵民合一,部落组织即是军事组织,因而同时也是一个部落军队驻镇防戍区;就朝廷所设管理机构而言,则是一个实施民族统制或曰民族压迫的特别行政区;因朝廷往往还派兵驻镇监护,因而又是一个兼具镇防、保护功能的军事防戍区。从这些胡族部落聚居区的特殊治理方式及复杂性质,可以窥见十六国北朝特殊政区的渊源所自。
当五胡在内地建立政权后,本部族及附从部族均以部落为单位聚族而居,实行部落制的地方统治,军事与民事、部落组织与武装组织合一,颇类后来北魏的“领民酋长”制。汉赵的“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都尉及以下首领,“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这些“豪杰”实即不同层次的部落酋长,同时也是汉赵单于所统部落军队的各级将领。汉赵刘粲曾冤杀“氐羌酋长”十余人,刘曜杀巴氐酋长数十人,前者致“氐羌叛者十余万落”,后者致“四山羌、氐、巴、羯”反者三十余万人。后赵石虎曾徙秦、雍民及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以氐帅苻(蒲)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使居枋头;又以羌帅姚弋仲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使帅其众数万徙居清河滠头。苻洪集团和姚弋仲集团各自作为一个完整的部族组织分别在枋头和滠头滞留达十八年之久,打下了以后前秦、后秦建国的政治、军事班底。他们自成一区,非郡非县,也与当地的郡县制政区无隶属关系,与后来北魏领民酋长尔朱氏率契胡部落世代割据于秀容川方三百里之地,实异代而同调。这种基于部落制的自治性政区、部落兵驻屯区,在十六国时期大量存在,如泾河东北卢水胡、屠各、西羌等皆“分堡而居”(彭沛谷堡、胡空堡、姚奴堡等),当时这类坞堡、垒壁林立于黄河流域,几乎部分取代了原有地方行政系统,其中由胡族酋豪所建者,固然为兼具部落制、军事性的领民酋长式政区,那些同样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汉族大姓豪强所据坞堡,实具有同样性质。拓跋部建国前后曾实行统率本部族和附从部族的“分部制”,“部”原本为“游牧社会的体制”,带有浓重的部族制传统,是兼具部族制性质和行政区划性质的特别行政区,诸部大人虽不能等同于原来的部族酋长,实际上也不过是更高层面的部落联合体的“领民酋长”而已,而诸部大人所统,均是由领民酋长率领的大小部落。十六国及北魏前期主要设置于少数族聚居地区,以及部分郡县制政区内的军事枢纽或战略要冲之地的军镇、护军,实即取法于汉朝处置降附少数族的属国、领护中郎将、校尉等特别行政区、军事防戍区制度,护军更是直接继承曹魏为统治内迁氐族而设置的安夷、抚夷二部护军之制。就其内部治理方式而言,军镇、护军也是具有一定民族自治性质的特殊政区。先后进入中原的诸胡长期生息于特殊政区内,因而在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内出现多种特殊政区是容易理解的,其中入主中原最迟的鲜卑拓跋政权,统一了北方,年祚最长,特殊政区的设置也最为普遍,存在时间也最为长久。
四、北朝后期特殊政区的退出和郡县制政区的全面回归
十六国北朝的特殊政区既根源于胡族因素,属于胡族体制,那么,随着这些胡族国家的民族政权色彩逐步淡化,其统治阶层逐步汉化,特殊政区的逐步消失乃是合乎逻辑的必然进程。正是在大力推进汉化改革的孝文帝时代,军镇、护军、领民酋长等特殊政区急速退出,渐为郡县制政区所取代。被孝文帝汉化潮流所抛弃、世代生活在非郡县制政区,或本为北族或已鲜卑化的北镇豪强所建立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政权,一度似乎有胡族体制回潮的迹象,在军队及统治核心的构成上,在姓氏(改胡姓)、语言(特别是军语)、风俗等方面,都有明显表现,但在地方行政体制特别是政区设置方面却并无反映,郡县制政区之维护中央集权制的性质,反而有强化的倾向,北朝后期开始大量出现的特殊高层政区——地方行台制,其发展演变及最终消亡也与中央集权逐步加强的倾向合拍。
我们之所以将十六国北朝存在的带有部落制特征或曰民族统治色彩的政区称之为特殊政区,是相对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更具普遍性的郡县制政区而言的。如果说“行政区划的基本前提首先是存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那么,秦始皇所确立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便是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由以产生的基本前提。我们知道秦始皇中央集权体制是由皇帝制、官僚制、郡县制组成的,但其中最能体现中央集权体制特征的,实为郡县制。尽管汉唐间在统县政区和中央政府之间出现过各种名目的高层政区,但这都不过是以郡为代表的统县政区在层级及职能上的进一步分合而已。总之,秦始皇广行“海内”的郡县制(以县级政区和统县政区为基本构成的“郡县制政区”体系),既是帝制时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基础性制度,也是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主流形式或曰代表性制度。所谓“百代都行”的“秦政法”,以郡县制概之可也。这在十六国北朝也不例外。
当时诸胡族政权,都是在秦汉以来长期实行郡县制的内地建立的。中原诸政权不论,诸燕发迹的东北,诸凉建政的河西,虽地处边陲,历来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又是附汉诸少数族安置之所,但这些地区同样自秦汉以来即置郡县。永嘉之乱后中原世家大族率宗族乡里避难四徙,辽水流域的幽州和河西凉州,是仅次于江南的难民集中抵达地。本为汉人所建的前凉,慕容氏所建前燕,都曾大量吸收侨旧世家大族加入政权,前燕还专门为中原流人侨置郡县。前凉张氏和前燕慕容皩称王以前,均奉东晋为正朔,分别以凉州刺史(牧)和平州刺史(牧)为最高行政头衔,所统区域内自然也以郡县制为主。中原地区的汉赵、后赵二国,胡汉二元体制中的胡族体制占有较大比重,但胡汉分治主要体现在军事上,行政区划上仍沿袭汉晋以来的州郡县地方行政制度。地方行政体系几乎完全军镇化的赫连夏政权,其军镇长官仍带有州刺史的虚名,大夏之兴勃亡忽,与其郡县制政区缺失导致政权基础薄弱不无关系。诸胡中社会发展相对落后、进入中原时间最迟的鲜卑拓跋族,在入主中原之初即在中央建立台省,地方设置州郡县,其后又顺应时势锐意汉化改革,逐步废止特殊政区,北魏能够成为十六国时代的终结者,新的时代的开启者,包括政区在内的统治体制上的主动脱胡入汉,实为重要原因。已有的研究表明,十六国北朝时期各政权总体上都沿袭了魏晋以来的州郡县制,郡县制政区始终是占主流地位的政区形式,而特殊政区之普遍退出(尽管作为郡县制政区系统必要补充的特殊政区以后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郡县制政区之全面回归,正是北朝后期地方行政区划演变的大势所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十六国北朝的所有政权中,统治阶层中不可或缺的世家大族,被统治者,或者说国家赖以存在的赋役承担者的绝大多数,都是世世代代生活在郡县制政区中的汉族人民,诸胡族政权如果要维持在内地的统治,实行郡县制实为最明智、最上策之选。
注释
①《资治通鉴》卷85“晋惠帝永兴元年十月”条,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第2702页。《晋书》卷121《李雄载记》,卷101《刘元海载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3036、2644、2649页。《魏书》卷96《賨李雄传》,卷95《匈奴刘聪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111、2044页。
②《魏书》卷67《崔光附崔鸿传》,第1502-1503页。
③《北史》卷100《序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3344-3345页。
④《魏书》卷43《刘休宾传》,卷79《鹿悆传》,第965、1764页。《南齐书》卷57《魏虏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第992页。《梁书》卷56《侯景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第839页。
⑤《北史》卷100《序传》,第3345页。
⑥说详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13页。
⑦《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第2466页。
⑧所谓“特殊政区”,是相对于“郡县制政区”而言,实即周振鹤先生“特殊行政区划”、“特殊地方行政制度”的简称。周说详见氏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33-394页。并参周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第100-151页。北朝特殊政区,严耕望先生称之为“诸特制”,并对之作了开创性的系统研究,详见严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卷下《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年,第413-418、691-851、907-908页。
⑨《魏书》卷113《官氏志》,第2974页。
⑩详见何德章:《北魏太和中州郡制改革考释》,《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侯旭东:《地方豪右与魏齐政治——从魏末启立州郡到北齐天保七年并省州郡县》,《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
责任编辑梅莉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Background, Feature and Trend of the Evolu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s during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and Northern Dynasties ——Focusing on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Mou Fas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ern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From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o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and early Northern Dynasties, with the northern minorities’ active or passive migration,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under the prefecture and county system gradually retreated from the northern border and was replaced by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under the tribal and military controlled system, which were the regime of Lingminqiuzhang, local Hujun, garrison towns and the local Xingtai. During the late Northern Dynasties (since Emperor Xiaowen of Northern Wei), with the deepening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nification,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withdrew generally and the prefecture and county system regressed universally. It was the trend of the evolu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s during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evolu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s;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feature and trend
2016-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