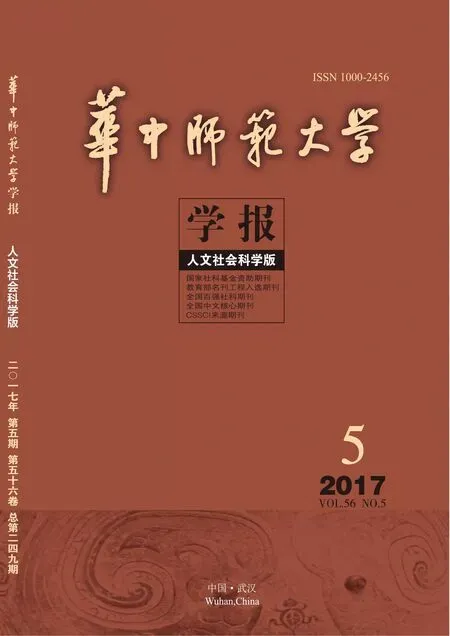从道德审判走向法治化:对大学校园学术性骚扰的审思
王 俊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从道德审判走向法治化:对大学校园学术性骚扰的审思
王 俊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大学校园学术性骚扰事件频发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但普通公众及学术界对此却存在较大认知差异,各类话语大都从道德审判角度来探讨问题,从加强师德建设的思路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认为,要想有效防治校园学术性骚扰的发生,绝不只是关乎道德伦理,它更需要法律的介入和制度的约束。在高校推进法治化的进程中,规范师生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走出“自由论”的思维困境,将学术性骚扰关注焦点由个人意愿、道德审判转向对高校相关体制、规章制度的建构与改善,并纳入女性权益和性别平等的概念框架,从而建立起针对学术性骚扰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机制。
学术性骚扰; 师生关系; 道德审判; 法治建设
前言
近些年来,大学校园性骚扰事件频发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据国际上相关研究报告显示:若根据加害者与受害者关系分类,校园内师生间的性骚扰普遍率为10%~60%,同学间的为30%~86%①。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AAUW)2006年曾公布过一项全美的在线调查,显示在校大学生遭受性骚扰是家常便饭,62%的被调查者称她(他)们曾受到别人“不恰当”的评论或身体接触②。日本一位反校园性骚扰的专家指出,在日本校园里,性骚扰现象也非常普遍③。台湾一部涉及校园性骚扰的影片《不能说的夏天》也曾一度被媒体热议,影片改编自发生在台湾某大学的一起真实的校园师源性侵案。女主角在被自己的教授性侵后心理崩溃。尽管影片最后,案件胜诉,施暴教授受到惩罚,导演也给女主角安排了一个得到新生的结局。但影片之外,现实版的校园性骚扰事件还在不断上演,校园性骚扰的新闻依然一次次登上报刊网络的头条。从国内厦门大学某教授性骚扰女学生到四川美院某教师的“强吻门”事件,以及2016年的一篇题为《沉默的铁狮——2016年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引起的广泛热议,乃至被媒体频频曝光的美国诸多常春藤大学各类“性侵门”事件等等,总是能吸引公众的眼球。
在多种形式的校园性骚扰案件中,其中教师基于自己身份、权威及地位对学生的性骚扰更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也最受社会关注,这就使得一个长期存在于高等教育界的敏感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事实上,长期以来,大学校园的这种师源性骚扰都处于“无以名之”的状态,一般公众和媒体都习惯称之为“潜规则”,正如美国女权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侬(Catharine A.Mackinnon)所说,“1976年之前,都没有适当名词能够言说性骚扰这一行为,以至社会无以形成普遍的、有共识的定义,但没有命名不等于不存在,沉默往往意味着带来的痛苦和屈辱更甚”④。概念是一种命名,也是一种识别,1990年代中期,“性骚扰”才作为一个新概念传入中国,使一些早已存在的习以为常的现象,开始变得“不正常”,“从‘正常’变得‘不正常’本身就是一个观念转变的漫长过程”⑤。至于来源于教师,发生在师生间的性骚扰直至学者Frank J .Till 1980 年正式提出了“学术性骚扰”( Academic Sexual Harassment) 这一概念才被命名,Frank J .Till 将其定义为: “利用权威强调学生的性特征或性认同,这种行为阻碍或损害了学生对于全部教育福祉、教育氛围或教育机会的享有”⑥。至此,学术性骚扰的问题也才开始真正进入研究者视阈和社会关注范围。学术性骚扰除了具备一般性骚扰的普遍特征,即“不受欢迎的性行为或其他以性为目的的行为”⑦外,还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特指发生于高校教师与成年学生之间的、教师施与学生的性骚扰;其二,学术权力的滥用是这种性骚扰得以发生的主要原因;其三,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或学术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基于学术性骚扰给高校社会声誉、大学教师形象、教学生态及学术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社会各界要求高校建立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机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⑧。推动建立大学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已成为高校管理工作中不容回避的议题。
在中国大陆高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就是一项具体的举措与工作实践。2014年10月9日国家教育部特别下发了《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即所谓的“红七条”,直指师德构建。其中规定“严禁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并在《意见》中呼吁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努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高校教师队伍⑨。在此基础上,许多高校在涉及教师职务(职称)评审、晋升、岗位聘用等核心利益的考核中也明确将师德师风列为必要条件,实行一票否决制。
但在此需要追问的是,具体到大学校园的学术性骚扰事情,道德约束和师德建设的作用与限度又在哪里?如果仅求助于道德审判和对师德的严格要求,是否能有效遏制校园学术性骚扰的频繁发生?虽然《意见》中提出师德建设的机制要与“法律约束相衔接”,可是中国大学关于校园性骚扰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并未完善,甚至几乎是空白,“衔接”又如何可能?要想有效遏制校园学术性骚扰的发生,目前仅仅靠道德上的倡议、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文件及原则上的禁止都是有局限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特别是来自师源性的学术性骚扰更多的是“基于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其持续既是因为操作性规则的缺位,也是因为缺乏性别平等的文化氛围的支持”⑩,因此,解决该问题更需要一个全面的方案来系统考察校园学术性骚扰的现实情境,规划更具有操作性的程序性议程,建立师生互动的指导性规范,特别是提供法律和制度的关照与约束。
2014年教师节前夕,由256位来自国内外高校教师、学者和学生参与联署的公开信曾寄给教育部部长,建议教育部制定出台《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公开信上明确提出,“目前在保护学生免受校园性侵害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教育部应该推动各地教育部门、教育机构构建一个从事前预防、紧急救助到事后治疗辅导的完整的预防性侵工作机制,创建安全的校园环境。”“事实上,学校必须承担保护师生不被骚扰的责任,建立一个安全、良好、平等的工作和学习环境”。
一、高校学术性骚扰的普遍性及认知差异
(一)各国大学校园性骚扰的普遍性
近年来,美国一些知名大学所发生的性骚扰事件被媒体频频报道,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最后白宫也被牵动,不得不出来郑重表态,2014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发表讲话:“在美国大学校园里,5名女生中,大约有1名遭受过性侵害……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如刑事司法制度.....我会推动政府采取措施”;美国副总统拜登也随后发言,“学院和大学不应该再对校园暴力置若罔闻,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学院和大学要行动起来”。2014年5月1日,奥巴马政府正式公布了防治高校性骚扰的新举措:即今后全美大学排名将与高校防治性骚扰的政绩挂钩。美国《华盛顿邮报》和凯泽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2015年6月曾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美国,过去四年里曾经上过大学的人当中,20%的女性和5%的男性称在校期间曾受到性侵犯和性骚扰。为了这份报告,研究人员在2015年1月至3月随机电话采访了1053名在过去四年中曾经上过大学、并住在学校及附近、年龄在17至26岁的年轻男女。调查范围覆盖全美500多所大学和学院,遍布美国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华盛顿邮报》称,实际的受性侵人数可能还要大于调查结果。“全国反对强奸、虐待和乱伦网络”是美国最大的反对性暴力组织,该组织的理事特雷西·谢夫尔说,虽然如何定义性侵和性骚扰会使数据产生变化,地区之间数据可能会出现重复,学校间数据有差异,但只要这个数据不是零,大家就应该多加关注。调查结果显示,相对于报告所说的女生1/5受性侵的比例,虽然男性比例较低,为1/20,但这样的问题仍不容忽视。在性侵发生后,受害人向社会服务机构求助时,工作人员表现出的不信任、对受害人的指责或不友好,都会对受害人造成精神上的二次创伤。特雷西·谢夫尔说,受害者不论男女,在性侵事件中受到的伤害是相等的。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美国两位学者经过历时两年的调查,访谈了四百余名大学教职工后,合著出版了《好色的教授:校园性骚扰》一书,就指出大学校园早已不是一片净土,其中学术性骚扰已成为大学校园不可小觑的现象。
《中国妇女报》一则报道曾援引过这样一组数据: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57%;另一项调查也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有学者对1200名女大学生调查发现,其中有531名女性(占总数44.3%)表示曾遭遇性骚扰,而且不少受害者遭受过两次甚至三次以上的性骚扰。该调查还发现:23%的女大学生认为当前性骚扰的“情况很严重”,60.4%的女大学生认为“情况严重”。“其中老师对学生的学术性骚扰或者是性侵案,具有很明显的特点”。
在台湾地区,大学校园学术性骚扰也一直是广受社会关注的议题。1994年发生的师大案,一名女学生在师大外墙上喷漆,控诉教授强暴,并爆发师大“七匹狼”的丑闻,为此,女学会还特别组织控诉人在“立法会”召开公听会。1999年台湾地区出台了相关性侵害的法律,2005年通过了性别平等教育法和性骚扰防治法,尽管如此,有关校园学术性骚扰的问题依然频频出现于报端,乃至被搬上荧幕,可见大学校园性骚扰的普遍性和受关注程度。
在香港,第一个有关大学环境里同侪或教职员间性骚扰的普遍性调查于1992年进行,接下来进行的是一个访问全港全日制大学生的大型调查。两个调查中有关性骚扰普遍性的结果大致相似。大约13%的女学生表示她们曾经被教职员学术性骚扰。其中,11%表示她们受到非自愿的亲密接触,9%表示受到性骚扰,2.5%表示被强迫进行性行为。
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律师张伟伟曾接手过多起大学校园性骚扰案件。她说,大学校园中,发生在师生之间的师源性学术性骚扰最受关注,教师通常是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和权力,对学生进行性骚扰、甚至性侵。但由于女性为性骚扰感到羞耻,亦担心影响与性骚扰者的关系,受害的通报率偏低。在没有为性骚扰问题立法的地区,根本就没有相关记录。即使进行了调查,由于各地区,特别是男性和女性间对如何构成性骚扰的定义各异,我们亦很难就不同地方的性骚扰普遍性做出准确的比较。
由此可见,大学校园性骚扰现象并非单一的经验和偶发性事件,其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
(二)大学校园性骚扰的认知差异
在大学校园学术性骚扰案件中,对性骚扰的认知差异是困扰和处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目前学术界对性骚扰内涵的理解颇具争议,更谈不上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法律上的定义与学术界定义也不尽相同。西方学者Fitzgerald在1990年曾提出了最具功能性的实证定义,这一定义被学术界许多性骚扰研究所采用。该定义以性骚扰的具体形态和连续性的观念来判断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性骚扰行为,依据情节轻重区分为性别骚扰、性挑逗、性贿赂、性要挟、性攻击(性侵害)五个等级。但在实际生活和具体案件的调查与判决中,非专业人士(包括各类传媒,甚至法官)很难去做这样的专业区分和判断。以2014年四川美院某教师的“强吻门”事件为例,当时舆论分化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强吻”自己熟悉的女学生,究竟算不算性骚扰?这到底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梳理网络上各种不同的声音大都与道德审判相关。一边是不绝于耳的谴责和谩骂,“叫兽”“道德败坏”“流氓教授”的骂声铺天盖地;另一边则是为教师的辩护,认为舆论夸大了事实。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一篇名为《人心不散:另一面的王小箭》的文章出现在网络上,文章试图说明某教师的举动并非性骚扰,尽管在生活上“有些放纵”,但实际是一个“内心简单的人”、“一个随和的老头”。前者以道德批判之,后者以道德维护之,却似乎都无法证明某教师“强吻”行为本身的属性。前者主观上已经认定了“强吻”的性骚扰性质,由性骚扰的判断推断出道德败坏的判断,却并没有有效证明该教师的行为是否属于性骚扰。至于后者,那些替该教师努力辩护的人,则试图塑造一个“好人王小箭”的形象。以道德维护,无非要证明该教师并没有性骚扰两名女生的主观愿望,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强吻”的行为没有在客观上对两名女生进行了性骚扰。因此,两方面的观点都无法说明问题的核心:“强吻”是不是性骚扰?
在评判教师行为时,除了道德眼光更需要法律的意识,法律能够促成性别关系的社会变迁,涉及人们对于性别平等的社会实践,也能规范道德行为,提升师德水准。但在目前中国法律体系中尚无针对性骚扰的专门立法,只在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中加入了一条:“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但是对性骚扰的定义和形式并未做出具体的规定,在已成文的《教师法》中对来源于师生间的性骚扰行为基本上也处于空白,校园学术性骚扰更是缺乏明确的界定,一旦发生相应问题,无法可依,很难进行法律判断和操作。
美国学者最早提出了性骚扰的概念并进行了大量研究,世界上凡有性骚扰立法的国家,一般都接受美国关于性骚扰的理论。凯瑟琳•麦金侬是最早定义性骚扰的学者,她将性骚扰定义为:“处于权利不平等条件下强加于人的讨厌的性要求”,是利用控制手段扩张男性权力和统治的过程。如果我们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四川美院某教师“强吻”女学生的行为,其实不难发现问题的核心——该教师的行为是否属于性骚扰,不在于教师的道德水准,而关键要看两个参考标准:第一,该教师与女学生之间是否存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第二,对两名当事女生而言,该教师的行为是否“不受欢迎”。事实上,也正因为在一些学术性骚扰案例中,被害人并没有拒绝行为人的性骚扰行为,因此人们会认为,既然被害人当时是自愿的,似乎也就不存在什么性骚扰了。然而性骚扰案件却并不以受害人当时是否自愿来进行判断。
198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Meritor Savings Bank,FSB v.Vinson一案中首次审理了性骚扰案件。法院引用平等就业委员会的《性骚扰指南》(EEOC Policy Guidance on Sexual Harassment)指出:性骚扰案件的诉讼要旨,在于认定被指控的行为是否是不受欢迎的。法院应当审查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不受欢迎,而不是受害者实际参与的性交行为是否是自愿。这是因为,对于交换型性骚扰而言,特别是大学校园中的学术性骚扰,骚扰者常常会以学业成绩、论文发表、课题申报、学位授予、保研、就业推荐等方面的好处加以引诱,而受害人为自身利益或者迫于压力,也可能对性骚扰行为表示容忍和同意,持默许态度。这些情形中,受害人表面上都未抗拒,但内心却对性骚扰行为并不欢迎,因而同样给她(他)造成不利影响。
学者们关于性骚扰的研究能为我们展示哪种程度的行为是性骚扰。一般情况下,性行为或身体接触被认为是性骚扰行为。其实,性骚扰有很多种形式。据香港《性别歧视条例》的法律界定,“性骚扰是当任何人对另一人提出不受欢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欢迎的获取性方面的好处的要求;就另一人做出其他不受欢迎并涉及性的行径;而在有关情况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顾及所有情况后,应该会预期到另一人会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吓”。另外,当“任何人如自行或联同其他人做出涉及性的行径,而该行径对另一人造成有敌意或具威吓性的环境”,这亦应被视作性骚扰。当然,“具性威吓性的环境”对很多人,尤其是那些认为性骚扰只等于非自愿的身体或性接触的人来说,是一种崭新的概念。很多人会以为性骚扰等于性侵犯,但当不涉及身体接触,她/他们就通常会低估事件的严重性,并以为这只是社会常态。可是,事实已证明不论任何形式的性骚扰,都会导致受害人恐惧、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引致她/他们逃避、并最终退出学业或工作。因此,对于校园内比较普遍的学术性骚扰绝对不只是一个师德提升就能解决的问题,它更需要法律的介入和制度的规范,完善校园性骚扰行为的认定、预防、申诉和处置的程序与机制。
二、高校学术性骚扰法律操作的困境
在北京“95世妇会”通过的《北京行动纲领》中,性骚扰已被明确归类为一种对妇女的暴力及歧视。可是,在推出《北京行动纲领》的20余年间,性骚扰并没有在任何重要领域上得到特别关注,也没有在立法上向前推进,但是,由于信息网络资讯的发达及普遍化,近年来,大学校园内学术性骚扰问题作为社会性事件却在各类媒体被频频热议,倒逼着法律和高校自身不得不正面应对。
(一)师生“恋”的迷思与师生间的权力困局
长期以来,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学术性骚扰事情,大都会牵涉到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的探讨,因此关于性骚扰的各类讨论也以“师生恋”的角度加以分析的居多。如论及“师生恋”的负面作用时,研究者会关注伦理层面的“有悖伦常、有伤风化”等;或有学者持“自由论”的思维,在肯定师生皆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前提下,主张应重新厘清教师专业伦理的界限;也有学者对此持成人之间“情欲自主”或“性自主”的另外一条希望对抗传统道德伦理的思考路线,那就是“情欲自主”的思维。这里“情欲自主”的思维与之前“自由论”思维的不同在于:在看待校园内发生的性骚扰/性侵害事件时,认为我们传统观念中以为正确的伦理关系,实际上是不平等、不正确、充满压迫的,只是此种不平等权利关系被伦理的外衣所美化。台湾学者何春蕤等人因此提出了“解放师生恋”的主张,认为只要“师生恋”正常化,将可同时解放校园内师生关系,将潜在的其他形式的不平等(性别、性偏好、族群、阶层等认同)同时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只要师生间性行为出于当事人自愿,没有欺骗、毁谤、胁迫、剥削等情况,就应该受到尊重。简单说来,“情欲自主”的思维强调解放与尊重师生恋,因此也被视为一种“自由论”的思维。这里无论是“师生恋”从违反伦理到自由恋爱而强调专业伦理、或者是“师生恋”正常化的解放情欲,表面看似互相辩论的观点,实际上都是在伦理层面讨论问题,显然忽略了师生之间性关系所涉及的“利用权势发生亲密关系”的可能性,即使出现了强调权利关系的思维,许多讨论也仍是在“专业伦理”的框架内叙述。
2014年7月前后,网民“汀洋”、“青春大篷车”举报厦门大学某教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举报人称其利用发表论文、保研等机会,诱奸及性骚扰女学生。这一事件曾引发全国瞩目。但从各路媒体报道到网络口水仗以及校方不得要领的说明也都大致在“教师伦理道德”这个框架内谈论问题。此种思维所隐含的其实是回避性、欲望与权力三者间的纠结,只关注了最表面、最直观的互动关系,因此也排除熟人之间因不同社会处境所导致的自我认知与亲密关系的差异与不对等。如果只在“自由论”思维框架下讨论该问题,实质上是更强调“自由论”建构的是一种特殊亲密关系类型,也就是说,“自由论”的思维所建构的利用权势发生性关系的规范意义,对于达成保障性自主的社会目标来说,反而社会将性与性欲放置在一种近乎真空的状态,造成强化一种特殊亲密关系类型的结果。事实上,厦大事件就已向我们揭示了校园学术性骚扰高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师生之间存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中国有师道的传统,如今尽管教师的权威已经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但这种权威依然存在,它往往有可能变成性骚扰的工具。而在大学校园中,一些教师确实在学术写作、论文发表、课题申报、保研读博、就业指导等方面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和资源,这也给性骚扰提供了便利。
电影《不能说的夏天》的另一片名叫作《寒蝉》,它所暗示的正是这种不对等的权力结构所制造的一种“寒蝉效应”:受害者迫于种种压力,选择隐忍顺从。除了权力结构所制造的“寒蝉效应”,还有受害者是因为性骚扰、性侵之后造成的创伤和心理疾病。电影《不能说的夏天》中,学生在遭受性侵后,竟陷入“我是不是爱上了李教授了”这样自我“催眠”式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中。她只有逃避性侵的事实,寻求某种合理性的解释,才能释放让她倍感羞愧的侵扰行为带来的心理压力。
需要思考的是:遭受性骚扰的女学生绝对不止一人,可是如举报人一般站出来揭露的却屈指可数。这种集体沉默使得校园性骚扰极少出现在公共话题之中,媒体没有报道,社会没有讨论,就在这种沉默和失声之中,性骚扰不断地以各种形式被复制、重演和再现。要从根本上遏止校园里的性骚扰,就必须深刻反思社会性别结构的运作方式与深层意义,反思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性别乃是权力的一根轴线,其运作并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多维度的,因此,性别交织于其他的权力轴线之中,如何重构男性与女性的性行为理解模式,以及性骚扰规范模式,就需要新的概念、新的意识形态框架。这既需要受害个体勇敢地站出来,也需要各种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和介入,更需要高校自身的作为,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建立对受侵害者的制度保障和申诉机制。只有这样,校园学术性骚扰问题才能透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例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得到有效解决。
(二)自由论:大学校园学术性骚扰法制化的思维困境
目前关于性骚扰的诸多表述中常常会出现“强制”与“抗拒”等字眼,“强制”的意义经常被转译为以拒绝表示强制,而以“抗拒”表示拒绝,其背后的原因则蕴涵着将性行为放置在你情我愿的自由状态,台湾学者王晓丹将其称为“自由论”的思维,认为此种思维忽略了性行为双方所处的权力或支配关系的脉络。这在利用权势性骚扰/性侵害的行为上更为明显。由于目前各国刑法体系设计的关系,这种利用权势或机会性侵害概念,往往会使得受害人意愿成为法庭审判的焦点,这反而会让受害者陷入困境。根据相关法律的解释,“强制”与“主观意愿”二者差别在于违反意愿的手段和强度不同,前者的性自主决定权全面被压抑,而后者的性自主权并非全然无法行使,只是在精神压力下不得不顺从。事实上,利用权势或机会行使性骚扰/性侵害罪如果成立,就意味着受害者有衡量利害的空间,或者贪恋权势地位而屈意顺从,或者唯恐失去某种权益或遭受某种伤害。而受害者在此种权势关系的不对等交换中,其个人的欲望、期待和努力等往往必须完全被揭露,如在教师权势的威压和诱惑下,受害人是否也考量通过性交换可以带来适当的世俗利益(如奖学金、课题申请、文章发表、工作推荐等)乃至性满足?如果受害人这种意愿被揭示,必然因此遭到贬抑,这种女性不能有任何欲望的逻辑,在传统文化又往往是通过社会性别体制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女性“妇道”“妇德”话语及评价系统,这也是促使女性自责的重要机制。在这些机制还没有被挑战的状况下,将使得受害者在法律实践中陷入新的困境。如果无法走出这种以“自由论”为基础的认知与思维困境,结果也不容乐观,大致会出现两种情形:第一,大量的性骚扰案件不是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最终不了了之,主要还是因为受害人恐惧在法庭上对自身主观意愿进行深度发掘,害怕某些“难以启齿”的私欲被赤裸裸的揭露;第二,由于诸多法律体系设计中,基本没有考虑性骚扰/性侵害的权力关系,性骚扰问题即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也往往面临性骚扰行为难以明确界定,特别是当法律调查的重点放在受害人主观意愿上,更可能出现判罚无所依据的问题。如四川美院、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术性骚扰这样的案例,若不是高校自身面对局内人或媒体曝光的压力,事情也很难得到处理。如何将学术性骚扰的关注焦点由道德审判、个人意愿转向对大学相关体制规章制度的建构与改善,使之进入到制度化与法治化的阶段,纳入犯罪处罚、行政事件处理的范畴,应该成为中国高校推进法治化进程中受关注的议题。
(三)大学校园学术性骚扰调查和取证面临的困境
由于高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组织和利益群体,校园性骚扰案的调查和取证都面临重重困难。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受害一方站出来维权,往往还会遭受一些流言的中伤。如常会有人说其实是学生别有用心勾引老师,或者是勾引未遂在栽赃。受害者很容易被当成替罪羊,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因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认为,防止校园学术性骚扰的发生,还是应该依靠校方加强管理和教育,校方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律师张伟伟谈到她办案经历中印象深刻的典型案例,是一个发生在研究机构的学术性侵案。施暴者是位博士生导师,在业内还很有名气,他会趁着带学生出差的机会进行性骚扰,甚至性侵。“如果学生反抗的话,他就会通过限制论文、科研项目等进行报复。”张伟伟说,也因为这样,很多人都敢怒不敢言。直到有个女孩开始出现抑郁、自杀等不正常现象,才被该机构的领导注意到,但最终还是因为缺乏直接证据而没有起诉。后来,该研究机构在内部开展了整顿行动,开除了涉事导师的党籍和所有任职,并在师生中开展了批评教育。但张伟伟也指出,她在处理相关校园学术性骚扰案件中,遇到过“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校方。“学校竟然给性侵的老师开假证明,说他人品端正,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这种学术共同体的“地方保护主义”成为很多高校管理中的潜规则,特别是当骚扰者为拥有各类称号的知名学者、学科带头人时,其个人声誉的崩塌必然会殃及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共同体成员组织起来为骚扰者辩护的现象很容易发生。在张伟伟提到的上例案件中,那份由学术共同体开具的证明后来被法官采纳,老师被判无罪,而被害女孩的精神却失常了。因此,有学者指出,大学“组织环境中学术权力过度集中、师生关系缺乏制度制约、学术机构中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文化氛围,是性骚扰被忽略、被容忍、被合理化而免于实质性惩处的根本原因”。
此外,目前中国大学校园学术性骚扰在罪名的认定上也存在空白。《妇女权益保障法》虽然首次规定禁止性骚扰,但对性骚扰缺少进一步的法律解释,在实际运用中更缺乏可操作性。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尽管对高校性骚扰的处罚做出了规定,但由于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尤其对高校性骚扰的定义、预防和处置措施还缺乏明确规定,所以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和完善空间。
三、走向制度化和法治化:美国高校应对校园学术性骚扰的经验及启示
在诸多高校性骚扰案例中,学术性骚扰的典型特点就是很容易激发人们关于“师生恋”的想象。中外历史上,师生恋曾被赋予一种罗曼蒂克的想象,但是在美国高等院校中,随着男女平等的进一步深入,自1980年代以来,已明确规定禁止有共同学术兴趣的师生之间产生亲密关系。虽然这个规则不是严格的法律,但是作为学校的规章制度已经被绝大部分大学采纳。2015年2月,哈佛大学面对校园学术性骚扰的困扰和各方压力不得不公开发布声明:禁止该校教师与在校学生发生性关系以及恋爱关系,并附上了一张同样拥护该措施的高校名单。
这个规则直接产生于美国女权主义理论以及性骚扰教育在校园的普及。女权主义理论强调关注任何不平等关系中权力的作用,校园内一种常见的不平等的关系就是师生之间的恋情关系。女权主义理论指出,在这种不平等的恋情关系里,有权力的一方(大多是老师)可能会滥用权力,对没有权势的一方进行性威胁或性压迫。教师可以通过自己的资历、地位来许诺或惩罚教师有兴趣的学生。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里,弱势者不得不屈从。为了保护弱势者的利益,美国大学从1980年代起就纷纷制定规则,禁止师生恋,杜绝任何滥用权力的可能。
但事实上,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美国大学禁止师生恋的规定从开始就有反对的声音。虽然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但并没有能阻挡各个大学越来越严格的规定,原因在于禁止师生恋对教师和学生都有好处,而且这种好处被大家认同,特别是被教师和学校管理者认同。教师们当然意识到这个规则与人权和自由的关系,但是绝大部分教师都支持这个规则,这才是规则能被绝大部分美国大学接受的根本基础。法制高于一切,一旦出现教师追逐学生的问题,一旦学生受到伤害,学生和家长很可能会诉诸法律,起诉学校和教师。美国各大学管理者之所以也非常积极推动禁止师生恋,也是因为很多这种法律诉讼会使校方左右为难,对大学的名誉和资金来源都会产生较大影响。即使发生了这种事情,许多高校都有相应的部门及一套较为完善、规范的程序和机制进行处理。以美国密歇根大学为例,该校就专门出台了性骚扰防范的规章制度与处理指南,设置学生纠纷调解办公室专门受理此类事件,同时,对提出这类申诉的人员以及参与调查的人员予以保护,以保证其不会因为相关行为受到打击报复。当然,美国高校禁止师生恋的初衷“绝不是禁止爱情,而是禁止滥用权力,监督权力,不给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的可乘之机”。
美国高校在防治学术性骚扰方面走向制度化和法治化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高校作为神圣庄严的教育场所和学术殿堂,必须责无旁贷地努力为每一个个体营造尊重、安全、零恐惧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高校的学校文化和制度建设都应该在其中担负起责任并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实施学术性骚扰的只是少数大学教师,但对大学声誉和大学教师形象的破坏却是毁灭性的且影响深远——哪怕只有一例出现。目前国际上的共识是“一例都多”,即哪怕只有一例发生,也不应该被忽视和容忍。解决大学校园学术性骚扰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应该从高校内部制度和机制建设着手,因为高校是一个相对自成体系的组织,防止性骚扰的组织也应该设置在高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制度化和法治化。
中国台湾地区高校和香港高校近些年也都出台了相应的校园反性骚扰的法律法规和较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使校园性骚扰事件能进入制度化的程序,不少大学都向师生提供了完善的受理投诉和处理机制,从而避免责任院校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及对受害者的再次伤害。但反观2014年厦门大学案件出来后,在媒体介入之前,其中某几位当事人早已通过组织途径向大学进行投诉,但并没有得到重视与处理,其原因就是大陆高校目前并未建立相关的制度和管理机制,导致接到举报的相关负责人对于此类事件大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如果没有高校对自身进行监督,对学术共同体的制度和法律约束,即使诉讼至法庭,相关取证也很不容易。再者,大陆高校一般对突发事件的处理和管控,大致都采取报喜不报忧的姿态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原则,何况是这类视为“家丑”的,严重影响学校声誉与形象的学术性骚扰案件呢?
把校园学术性骚扰纳入妇女权益和性别平等的概念框架,并进入立法体系,在大学校园治理中成立性别平等委员会,建立具体的实施细则及申诉、处罚机制,协调行政程序和资源,让女性可在安全和受尊重的环境下工作、学习和生活。近几年两会期间,都有多位代表委员关注校园性骚扰案件,指出应从加强立法监督、细化学校责任、普及性教育等方面出发,建立事前预防、紧急救助到事后治疗辅导的全套工作机制。有学者还非常具体地提出,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等,明确禁止校园性骚扰并规定性骚扰的处罚措施;建议教育部出台专门预防和制止校园性骚扰的相关规定;建议推动中国妇女研究会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所在高校率先成立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建立预防和制止校园性骚扰机制,以便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为全国高校做出表率。可以预见,对于校园学术性骚扰这样一个目前在社会上和学术界都还颇有争议的议题,在走向法治化的过程中,肯定会遭遇到诸多思想观念的冲突,各高校在认知上达成共识也需要时间,相关规章制度的酝酿、起草、落实、执行与评估更需要专业人士的介入与专业化的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高校反校园学术性骚扰的制度化和法治化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但目前,这个议题已浮出地表,基本完成了从“个体经验”“个别现象”到“问题建构”的启蒙阶段,相信并期待未来会有更持续深入的关注和更具体可行的措施。
注释
②春风:《最新调查显示美国男女大学生遭受性骚扰是家常便饭》,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6/2006-01-26/8/683691.shtml.2006-01-26.
③《日本校园性骚扰现象严重 受害者大都保持沉默》,http://news.sohu.com/38/35/news210583538.shtml.2003-06-03.
⑤宋少鹏:《何为性骚扰:观念分歧与范式之争——2014年教师节前后“性学派”对“女权派”的质疑》,《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6期。
⑥Till, Frank J.SexualHarassment:AReportontheSexualHarassmentofStudents.Washington D. C.: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1980,7.
⑦“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研究”课题组:《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多重权利和身份关系的不平等——对20个案例的调查与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6期。
⑧周韵曦:《尽快建立高校性骚扰防范机制》,《中国妇女报》2014年9月13日。
⑨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002/201410/xxgk_175746.html.2014-10-17.
责任编辑曾新
From Moral Judgment to Legalization: Reflection of Academic Sexual Harassment in Universities
Wang Jun
(School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cademic sexual harassment in universities cause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but the public and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have different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n it. As to the discussion of academic sexual harassment on campus,all kinds of discourses are mo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judgment. This study argues that, legal interven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re needed in order to mak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sexual harassment /sexual assault on campus. It is urgent and important to regulate the righ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going out of the thinking dilemma of “freedom theory”, turning the concerning focus of sexual harassment from personal willingness and moral judgme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systems in universities in China.
academic sexual harass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moral judgment;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2017-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