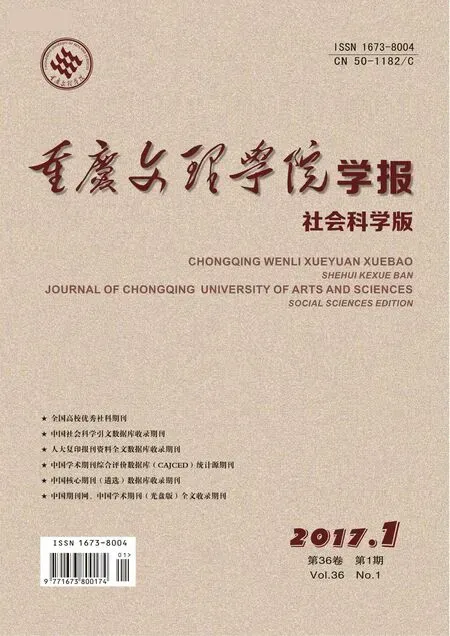另一份遗产:民俗与“非遗”的历史交情
彭兆荣
(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沙坪坝 400053)
另一份遗产:民俗与“非遗”的历史交情
彭兆荣
(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沙坪坝 400053)
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与民俗“内存”发生逻辑关系;而在世界遗产事业的历史中,这一关系也真切地表现出来。在UNESCO遗产事业的进程特别是推进过程中,民俗一直扮演着特别的角色。我国的民俗一如“民俗”的本义,有自己的表述逻辑和知识谱系。在我国的遗产运动中,不仅要在“名录”上表现民俗学的成色,更要在脉理上体现民俗与遗产的学理逻辑,知识产权不失为历史的切入口。文章为此提供了一些相关档案材料。
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
一、引言
在西方,“民俗”(Folklore)系由两个词合成,即Folk和 Lore,原义为“民众的知识”或“民间的智慧”(the Lore of the Folk),并逐渐形成专门的学问和学科。虽然欧洲各国以及不同学派在对其意义和理解上存在差异,边界也不完全一样,但并未抵触“民众”“民间”“传统”等基本语义[1]1-3。 邓迪斯提醒人们,“民俗”不独具地方性,连“概念”都是地方的。因此Folklore既指研究的材料,也指研究本身。他以美国的“民俗”概念为例,阐明Folk和Lore在美国特殊的意思、意味和意义[2]25-26。
在我国,“民俗”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和特别的意义。“民俗”与“风俗”的表述和含义交叉,有时可以互用[1]3。现在,人们经常将风俗视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生活,也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我国古代的“风”与“俗”不是同类词,而是对照词。《汉书·地理志》中说:“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风”是从上至下的教化所产生;“俗”则是下层人民自我教化的结果。《汉书·地理志》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风”是自然条件促成的,“俗”是社会条件决定的。孔子说过:“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风俗成了社会伦理建立的基本范畴。
白川静认为,“俗”字中的“谷”是“容”“浴”和“欲”的“谷”。 它表示在祭祀祖先的祖庙(“宀”)中,供起“”(置有向神祷告和祝咒之器)进行祈祷。“”上隐约有神的姿影。希望目睹神的姿影的心情谓“欲”,“欲”意味着希望通过向神祷告而有幸目睹神的现身。这样的一般性信仰、常见的礼仪内容谓“俗”[3]285-286。“民俗”是民众生活的样态,这个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早就出现。“俗”字是形声字,由意符的“人”和声符的“谷”两部分组成,表示人不断学习、重复进行的意思,即习惯。从古代文献记述的基本意思看,古今承袭了“民俗”的基本意义[4]。
民俗包含着吉尔兹所说的“地方知识”与“民间智慧”[5]。“地方知识”与地理、地缘有关。在我国,“地方”首先是宇宙观,相对于“天圆”论者。其次,“地方”具有传统政治地理学的范畴和意义。“风俗”一个重要的视角,即区域和空间的叙事差异,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再次,“地”与“土”构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地形”,它是“中国”之所依。《淮南子·地形训》:“凡地形,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山为积德,川为积刑,高者为生,下者为死。丘陵为牡,溪谷为牝……土地各在类生。”
民俗与“非遗”不独具有学理上的天然关联,甚至可以在宽泛的意义上,将“非遗”视为民俗现象和事物。实际上,二者在当代世界遗产事业中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历史关系。
二、民俗与知识产权保护
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遗产)之间有着不解之缘,这一“缘分”又与保护民俗的“知识产权”有关。事实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事业的发端也与民俗性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关,并导致了一系列活动,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法律、法规性质的文件、文书。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部门提出了《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案》。这是多年来为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法律保护体系而努力的结果①。这一历史性成果经历了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和活动,如表1所示。

表1 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建立过程

续表
这一历史过程包括不同机构和组织的配合,如:195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缔结了《世界版权公约》,启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民俗保护的工作。具体工作由以下两个部门负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权部、文化部):直到1982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民俗保护专家委员会会议”④之前,都坚持国际层面对民俗的保护要集中于对民俗智力产权、财产的法律保护。因此,相关工作主要由版权部负责。这次会议之后工作开始逐渐由文化部负责。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1976年首次出现在萨曼塔·谢尔金(Samantha Sherkin)梳理的历史中。WIPO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组织草拟《发展中国家版权突尼斯标准法》。直到1987年,因感到“很多成员国缺乏恰当、可靠的资源鉴别出需要予以法律保护的民俗表达形式”,难以继续对民俗的智力产权、财产进行法律保护的研讨工作,于是在当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权部召集的“保护民俗的技术和法律专家特别委员会会议”后,退出整个1989年建议案的筹备工作。
这项工作的起因之一与玻利维亚有关。玻利维亚并非是以法律保护民俗理念的首创者。在国家层面,早在1956年,墨西哥出台的版权法里就规定,源自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⑤的作品包括民俗,均要由版权理事会(Copyright Directorate)进行注册。1968年,玻利维亚最高法院第08396号判决(Supreme Decree No.08396)将一些作品的所有权划归国家所有。
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开始保护民俗的研究,并完成了 《用国际文书保护民俗可行性报告》。这次研讨没有具体决议,但提醒国际社会,民俗现状继续恶化,保护民俗的工作在未来将变得越来越紧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民俗的关注当然也有自己的目的。鉴于1972年公约不适应于(也没有扩展至)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为了促进对各文化身份(包括不同传统、生活方式、语言、文化价值和文化意愿)的欣赏和尊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需要将自己的工作扩展到民俗这一重要的文化领域。
三、保护的整体与维度
民俗保护具有本质的文化特质。保护工作主要包括:
对民俗进行的整体保护:包括民俗的定义、鉴别、保护和保存,并提出具体保护原则和方法。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成员国进行调研,评估各缔约国非物质(Non-physical)文化遗产现状,寻求确保民俗真实性(Authenticity),免于失真变形(Distortion)的措施。具体工作包括:1979年8月向成员国发放问卷,1981年9月回收92份有效问卷,就民俗的定义、鉴别、保护、保存、利用以及如何避免不利开发等问题进行访问,根据调查结果形成了《保存民俗和传统的大众文化之措施》的报告。该报告于1982年2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的“民俗保护专家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并成为1989年建议案的重要参考文献。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次大会通过了《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案》。民俗保护进入新阶段。
保护民俗的智力产权、财产:只针对民俗中涉及智力产权/财产的部分,要求草拟具体法律条款。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WIPO共同负责。这两个组织在1981年2月召开了民俗智力产权、财产保护工作组会议,在1982年6月至7月召集有关民俗智力产权保护问题的政府专家委员会会议。根据其他类似的智力产权法的原则,草拟并通过了《保护民俗表达免于非法开发和其他侵权行为的国家法律之标准条款》(Draft Trea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Expressions of Folklore against Illicit Exploitation and other Prejudi cial Actions),强调民俗的利用须获得授权,为获授权要缴纳固定数额的费用。该费用由相关社区或依法拥有版权的作者或有政府指派的权威机构管理,用于促进和保护国家文化和民俗,对民俗材料的扭曲或不当商业性开发都要受到法律限制或禁止,但无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采用这一条款。
第2条规定“民间表达形式”指由传统艺术遗产的特有因素构成的、由某国某团体(或该民营团体某个体)所发展和保持的产品,主要包括4种基本形式:⑴口头表达形式;⑵音乐表达形式;⑶行动表达形式;⑷有形表达形式。
WIPO自觉在民俗保护工作中被边缘化了。WIPO与版权部交流,强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工合作的理由是:保护民俗的整体行动中需要理性、合理的分工与合作,避免重复劳动。同时对民俗的智力产权进行保护又是一个专门性的问题,需要专业部门负责。1986年8月至9月,WIPO两次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权部写信,表达暂时退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原因。一场耗时16年,耗费百万美元⑥,涉及大大小小10多次会议的民俗保护战役终于告一段落。两种保护理念和方式此起彼伏。版权保护的理念虽然是起点,而且在开始的几年都占上风,但后来峰回路转,全面保护民俗的理念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也就是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公约之外,其他有关文化财产的国际文书中也有一股保护民俗的力量,这股力量为在版权之外保护民俗提供了可行的方式。尤其值得强调的是,1982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化政策的墨西哥城宣言》(Mexico City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Policies)达成了有关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的新定义:
人类的文化遗产包括艺术家、建筑师、音乐家、作家和科学家的作品,也包括无名艺术家的作品,人们精神的表达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价值核心(the Body of Values)。文化遗产包括物质的和无形的作品(Tangible and Intangible Works)。通过这些作品,人类的创造得以表达:语言、仪式、信仰、历史遗址和纪念物、文化、艺术品、档案馆和图书馆。每一个人因此拥有守护和保存其文化遗产的权利和义务。因为社会通过价值认识自己,在这些价值里他们发现了创造灵感之源⑦。
这一概念真正弥补了1972年公约中“文化遗产”概念中缺失的部分——无形文化遗产(虽然不是在严肃的定义层面上,但却在理念方面做到了这一点),进一步巩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面保护民俗理念”在1982年2月会议上取得的胜利。
另一方面,全面保护民俗的理念与欧洲民俗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时,由芬兰民俗学家航柯(Lauri Honko)领导的北欧民俗研究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9年“建议案”的筹备过程,以及其后的实施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卡尔·克隆(Leopold Kaarle Krohn)堪称民俗学学科的奠基人,芬兰也是民俗学学科的摇篮。“芬兰方法”(历史地理学)至今依然是理解不同人群间观念关联的有效方法。尽管芬兰航柯以及当代国际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界的核心人物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都认为这种方法被冠以“芬兰方法”是“过度民族主义热诚”[2]174所致。
1989年建议案通过后,以航柯为代表的民俗学家积极加入到民俗全球调研和保护系统的建构工作中。1990年1月,航柯等人着手建立国际民俗学者组织(Folklore Fellows International)。在航柯看来,“芬兰方法”基于大量民俗材料重构原形的研究范式难以再延续下去。民俗学家的田野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区域和族群需要合作研究,以便通过民俗和传统文化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随着1989年建议案的通过,民俗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被推到了前台⑧。1991年6月至8月,航柯等人组织了首期国际民俗学者组织夏季学校(Folklore Fellows’Summer School),来自24个国家的30位学员和1名观察者参加了这期培训,其中9位来自北欧和西欧,9位来自东欧,7位来自亚洲,3位来自非洲,2位来自北美,还有1位来自南美。14名老师分别来自丹麦、芬兰、德国、印度、挪威、瑞典和美国。通过这样的培训,航柯希望将各国各有所长的民俗学家聚集到一个圆桌前,形成对民俗不同焦点、维度的研究和交流系统⑨。
航柯从学术角度评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9年建议案时,认为不论人们怎样看这个建议案,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它拓宽了民俗学家过去以国家或区域为取向的研究视野,它呼吁在尽可能宽泛的领域内,为了当下和未来世代的利益进行合作⑨。可以说,1989年建议案全面民俗保护的理念和途径,暂时胜过了对民俗进行版权保护的理念和途径。这也是民俗学家的一次胜利,不论建构一个全球民俗分类框架是否现实,但民俗学科却因为这一“建议案”在各成员国得到极大的重视和推动。这一理想在2003年《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里得到另一方式的实现,即通过评估世界无形文化遗产的方式建构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分类和评价体系。
四、保护:两个不同的面向
以一个几百年前由某个族群祖先画在牛皮纸上的图画为例。对这一民俗的智力产权层面的保护旨在避免一些跟这个东西不相干的人把这幅图画复制在一些商品上,如杯子、衣服上去赚钱。博物馆式的保护应该把这个东西保存起来,研究它在这个族群中曾代表的意义,同时通过展览让人们增进对这个族群及其文化的了解和尊重,尤其是让这个族群的后代能观摩、解读自己的历史,增进他们的认同感。根据1989年建议案⑩,对民俗的全面保护应按以下几个步骤展开:
民俗的鉴别(Identification of Folklore):鉴别是建立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研究。具体措施包括:
编制国家与民俗有关机构的名册,以便将其纳入地区和全球民俗机构一览表。
创立鉴定和记录系统(收集、编索、抄载)或以手册、收集指南、编索模板等形式梳理现有的鉴定和记录系统,以协调各民俗机构的分类系统。
鼓励创建民俗的标准分类法(Standard Typology),包括一份供全球使用的民俗总纲(A General Outline)、一份民俗综合一览表(Comprehensive Register of Folklore)和地区民俗分类。该分类应该基于田野考察⑪。
民俗的保存(Conservation of Folklore):保存范围包括民间传统及其相关物件(Folk Traditions and its Object)的记录。倘若这些传统未被利用(Non-utilization)或演化(Evolution),那么研究者和传统的传承人(Tradition-Bearers)将能找到我们理解这些传统变化过程的材料。鉴于活态民俗不断变化,难以对其进行直接保护,因此,那些固化为一个有形形式(Fixed in a Tangible Form)的民俗就应得到有效保护。保护措施包括:
建立国家档案馆,使收集到的民俗资料得到恰当保存并能供人们使用;
建立国家档案中心机构以提供编制总索引,传递民俗资料的各种情报,传达各相关工作的规则、标准(Standards of Folklore Work);
建立博物馆或在现有博物馆中增设民俗板块,展出传统和流行的民俗⑫;
优先考虑表现传统和流行民俗的种种形式,因为它们突出这些民俗文化的现在或过去(展示其环境、生活和工作方式、生产技能/技术)⑬;
协调收集和存档的各种方式;
对收集人员、档案人员、记录人员⑭以及其他专门人员进行培训,包括物质保存和分析等;
制作民俗资料的档案和工作副本以及供各地区机构使用的副本,确保相关文化社区能够接触到所收集的资料。
民俗的保护(Preservation of Folklore):保护范围包括民间传统及其传承人。鉴于每个人都拥有对自己文化的权力,以及人们与其文化的附着关系常因大众传媒传播和工业文化而遭到腐蚀,必须采取措施,在生产民间传统的社区内外确保给民间传统以社会地位和经济上的支持。具体措施包括:
以适当方式进行民俗教学与研究,并将其纳入学校内外的教学计划,应特别强调对广义民俗的重视,不仅应考虑到乡村文化或其他农村文化,也应注意城市里那些由各种社团、行业、机构等创造的、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文化多样性和不同世界观的文化,尤其是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的⑮;
支持各文化社区自己的记录、存档、研究,以及传统实践等活动,确保社区享有自己民俗的权利;
在跨学科基础上建立由各有关团体组成的国家民俗理事会或类似的合作机构;
向研究、宣传、教育(Cultivating)或保存(Holding)民俗材料的个人和机构提供道义和经济上的支持;
促进有关民俗保护的科研。
民俗的传播(Dissemination of Folklore):应当使人们注意到民俗作为文化身份认同基本要素的重要性。为了使人们意识到民俗的价值以及保护民俗的必要性,应广泛传播民俗。但为了保护传统的完整性,在传播过程中必须避免任何歪曲。为此各成员国应该:
鼓励组织民俗方面的全国性、地区性或国际性活动,如巡回展、节日、电影、展览、研究班、专题讨论会、讲习班、培训班、会议等,并支持传播和出版这些活动的材料、文件和其他成果;
鼓励国家和区域媒体(新闻、出版、电视、广播等)加大对民俗的报道力度,在其机构内为民俗学家设置职位,确保大众传媒采集的民俗材料恰当地存档和传播⑯;
鼓励各地区、各市政当局和民俗团体设立专职的民俗学者职位以促进地区内的民俗活动以及合作;
资助现有团体或新建团体制作民俗教育材料,如新近田野调查的影碟,鼓励在学校、民俗博物馆,以及国家和国际民俗展览和节日上使用这些材料;
通过资料中心、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机构以及民俗方面的简报和期刊,提供充足的民俗类资料;
根据双边文化协定,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为与民俗个体、团体和机构间的会晤与交流提供方便;
鼓励国际科研界采纳恰当的伦理态度,在接触其他文化时尊重各传统文化。
民俗的维护(Protection of Folklore):民俗是个人或集体精神创造力的明证。保护民俗是这一精神创造力在国内外得到促进、维持和传播,同时其任何相关合法利益又不至于受损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除维护民俗表达的智力产权外,在民俗记录中心和档案机构里,有很多种权利已经得到维护并应继续受到维护⑰。为此,各会员国应:
民俗的智力产权:吁请有关当局注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智力产权方面开展的重要工作,但同时也承认,这些工作只触及维护民俗的一个方面,故采取措施全方位保护民俗乃当务之急;
民俗的其他权益:
保护传统传承人(消息提供者)的秘密和个人隐私;
保护收集者的利益,确保其所收集的材料以良好状态和恰当方法得以存档;
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收集材料被有意或无意地滥用;
承认档案机构有责任监控收集材料的使用。
以上是“建议书”对民俗保护具体措施的建议。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明确的保护路径:

这一路径与博物馆的保护理念和方法如出一辙,但其保护路径的不同之处也显而易见。博物馆保护的是物件,在民俗保护中,虽然强调难以直接保护“活态民俗”故而主要保护“固化为一个有形形式”的民俗及其物件,但我们仍然不能把一些活的因素丢掉,比如保护范围包括了民俗传承人,维护内容包括了报道人和传承者。这一点虽然没有在“建议案”中得到专门强调,但民俗保护本身不同于物件保护的特点,难度也显而易见。可以说,1989年建议案将现成的、成熟的保护框架——博物馆保护框架——移植到民俗保护中来,在国际层面缺乏民俗保护研究和实践的情况下,这不失为权宜之计,在民俗保护十分紧迫的情况下为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打下了第一个基础。
如果民俗可以简化为“民众生活”,那么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所形成的威胁也因此在民俗中获得了空前的历史价值,即保护地方民众的生活有了与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质性的意义。做这样的链接不是主观认知,而是历史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另一个称法为“活态遗产”,即“活在”民间的遗产,也正是这一原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的交情非其他可比。在遗产研究的历史中,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又历史性地叠加在一起。当人们回到生活中又真切地发现,二者难分泾渭。
致谢:感谢李春霞教授提供的资料。
注释:
①Samantha Sherkin.A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1989 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资料来源:http://www.folklife.si.edu/resources/Unesco/sherkin.htm.
②Intellectual Property,我国习惯翻译成知识产权,但Intellectual一词强调“智力”而不是“知识”,Property指拥有之物,也不是特指拥有财产的权利。在法律中,Intellectual Property具体包括了版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概括起来大概是指智力劳动所创造的智力产品或智力成果的权利,所以译为智力财产/产权皆可。
③资料来源:http://www.folklife.si.edu/resources/Unesco/sherkin.htm.
④这次会议在巴黎召开,共有123人参加,除了80名与会者,还包括联合国及其相关部门的代表5名,35名国际非政府组织观察员以及3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代表。
⑤指人类的一部分作品与一部分知识的总汇,可以包括文章、艺术品、音乐、科学、发明等。对于领域内的智力财产,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具有所有权益(所有权益通常由版权或专利体现)。这些知识发明属于公有文化遗产。
⑥Noriko Aikawa.1998年2月24日—3月2日东京亚太文化区域研讨会 (Regional Seminar for Cultural Personnel in Asia and the Pacific)上的主题发言。资料来源:http://www.folklife.si.edu/resources/Unesco/hornedo.htm-26k.
⑦UNESCO.Mexico City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Policies,World Conference on Cultural Policies Mexico City,26 Jul.-6 Aug.1982.资料来源:http://www.unesco.org/culture/laws/mexico/html_eng/page1.shtml#CULTURAL%20HERITAGE。
⑧Lauri Honko.Introduction.Folklore Fellows Network(FFN).1.April 1991:1-2.资料来源:http://www.folklorefellows.fi/ netw/ffn1/introduction.html.
⑨Lauri Honko.The Unesco Perspective on Folklore.Folklore Fellows Network(FFN).3.January 1992:1-5.资料来源:http: //www.folklorefellows.fi/netw/ffn3/unesco.html.
⑩UNESCO.Resolution adopted at the thirty–second plenary meeting on 15 November 1989.1989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次大会(巴黎)通过。资料来源:http://www.culturelink.or.kr/archive/UNESCO/Dec_Rec/UNESCO_D_3.pdf.
⑪英文版和中文版均来自同一文件。笔者根据情况做了归纳,并对中文版中翻译不当之处作了修改。UNESCO.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1989.http://www.unesco.org/culture/laws/paris/ html_eng/page1.shtml-25k.
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版1989年建议案的翻译为:建立博物馆或在现有博物馆中增设民间创作部分以展出传统的民间文化。英文版为:create museums or folklore sections at existing museums where traditional and popular culture can be exhibited.
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版1989年建议案的翻译跟本文略有不同。此处英文原文为:give precedence to ways of presenting traditional and popular cultures that emphasize the living or past aspects of those cultures(showing their surroundings, ways of life and the works,skills and techniques they have produced)。中文版翻译为:优先考虑种种表现传统民间文化的形式,因为它们突出这些文化现在或过去的见证(遗址、生活方式、物质或非物质知识)。
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版1989年建议案的翻译为资料人员。
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版1989年建议案的翻译为:以适当方式进行民间创作教学与研究,并将其纳入校内外教学计划,应特别强调对广义的民间创作的重视,不仅应考虑到乡村文化或其他农村文化,也应注意由各种社团、职业、机构等创造的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世界各种文化和看法的文化,尤其是不属于主要文化的那些文化。英文版为:design and introduce into both formal and out-of-school curricula the teaching and study of folklore in an appropriate manner, laying particular emphasis on respect for folklore in the widest sense of the term,taking into account not only village and other rural cultures but also those created in urban areas by diverse social groups,professions,institutions,etc.,and thus promot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different world views,especially those not reflected in dominant cultures.
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版1989年建议案的翻译为:例如通过提供补助金,在新闻、出版、电视、广播和其他国家及地区传播机构设立民间传说研究者的职位,通过确保对传播机构收集的民间创作方面的材料进行适当归档和传播,通过在这些机构内部设立民间创作节目单位等方式,鼓励这些单位在其节目中使民间创作资料占更大的比重。英文版为:encourage a broader coverage of folklore material in national and regional press,publishing,television,radio and other media, for instance through grants,by creating jobs for folklorists in these units,by ensuring the proper archiv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se folklore materials collected by the mass media,an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departments of folklore within those organizations.
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版1989年建议案的翻译为:民间创作作为个人或集体的精神创作活动应当得到维护。这种维护应和精神产品的维护类似。这一保护十分必要,通过这种手段可以在本国和外国发展、保持和进一步传播这种遗产而同时不损害有关合法利益。除民间创作维护中的“知识产权”方面外,在有关民间创作的资料中心和档案机构里,有几类权利已经得到维护并应继续受到维护。英文版为:In so far as folklore constitutes manifestations of intellectual creativity whether it be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it deserves to be protected in a manner inspired by the protection provided for intellectual productions.Such protection of folklore has become indispensable as a means of promoting further development,mainten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those expressions,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country,without prejudice to related legitimate interests.Leaving asid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pects’of the protection of expressions of folklore,there are various categories of rights which are already protected and should continue to enjoy protection in the future in folklore documentation centers and archives.
[1]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
[2]阿兰·邓迪斯.民俗解析[M].户晓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白川静.常用字解[M].苏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4]韩敏.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衣食”民俗[G]//周星.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穆 刚
Another Legacy:Folklore and Non-legacy
PENG Zhaorong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Shapingba Chongqing 400053,China)
The cultural heritage,especially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has a logic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memory”of folklore.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heritage,this relationship is also manifested,accompanied by the progress of the UNESCO heritage.In the process,folklore has been playing a special role.China’s folklore,a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folklore”,has its own logic of expression and genealogy.In the heritage movement in China,not only in the“directory”performance of folklore,but also in the pulse on the folklore and heritage of intellectual logic,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entry point of history.This article provides some relevant archival materials for this purpose.
folklore;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G119
A
1673-8004(2017)01-0001-08
10.19493/j.cnki.issn1673-8004.2017.01.001
2016-11-09
彭兆荣(1956— ),男,江西泰和人,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国家重大课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首席专家,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和文化遗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