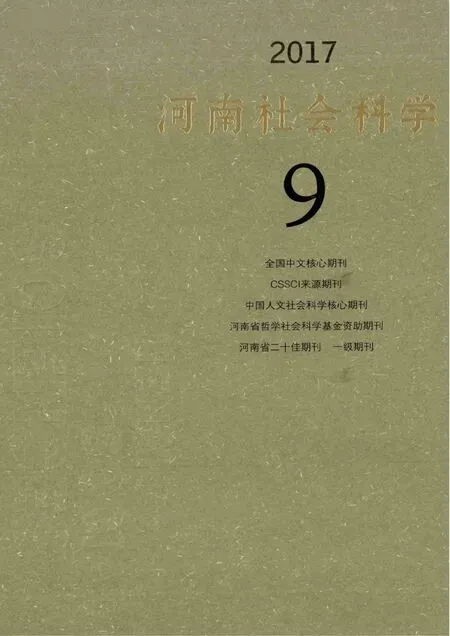传统重压之下的被扭曲
——《灶神之妻》中雯丽母亲形象的文化解读
周聪贤
(河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传统重压之下的被扭曲
——《灶神之妻》中雯丽母亲形象的文化解读
周聪贤
(河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灶神之妻》是美国当代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二部畅销小说。国内外学界对书中雯丽母亲的文化形象鲜有关注,这个人物形象主要呈现以下文化特点:“有意识”自由与“无意识”束缚、自我与现实的冲突、人格的独立与依附。通过对这个女性形象的剖析,后世读者对民国女性在传统重压下被扭曲的生存境遇,以及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艰难历程有更为真切和全面的认知。
《灶神之妻》;雯丽母亲;文化解读
《灶神之妻》是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二部畅销小说,该书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更在于作家对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种种描写。生活在一个外源性现代文化同本土传统文化激烈冲突的过渡时代,雯丽母亲身上非常明显地凸显出在传统重压下被扭曲的精神特质。
一、“有意识”自由与“无意识”束缚
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现代性体验迅速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源于欧美的各种现代社会思潮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传统礼教的纲常伦理观念所主宰的“陈腐固陋的思想界,受了这种新的激荡和灌溉,也奔上新生的道路”[1]55。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现代价值观念逐步进入中国社会的视野。受其影响,中国传统礼教的婚姻伦理观念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全新审视。《申报》《晨报》《大公报》《新青年》等报刊前赴后继,提倡自由恋爱,批判传统婚姻制度,与当时“女学校立矣,女学会开矣,女报馆设矣,女子游学之风行矣”[2]的社会生活新现象相互激荡,使得一些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敢于抨击禁锢女性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全力摆脱女性在其中“不得任一肩,赞一辞,惟默默焉立于旁观之地位”[3]的“尚情而无我”[4]157式的传统包办婚姻,追求爱情自由与两性权利的平等,更追求恋爱婚姻从“无我”向“自主”的态势转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灶神之妻》中的雯丽母亲和一位自命“新潮”的男性陷入自由恋爱,并且答应了他缔结婚姻的请求。然而这一段在后世读者眼中平淡无奇的情感经历,却因为没有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其寡母极为恐怖:“你怎么能干这种事!你怎么能答应那个男人!只有国家没了皇帝才会发生这种无法无天的事!”[5]97接下来,雯丽母亲追求情感自主的一切努力都只是使得其寡母更为惶恐。为了维护自己作为母亲的权威,也为了维护她心目中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这位母亲竟然用一纸协议把自己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儿变成了另一个男人(江少言)的第二个二姨太。得知契约之事,这位“新潮”的男性除了那些“一定要坚持到底,只有这样才能结束这桩封建包办婚姻……这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的爱情,更是为了你的国家”[5]98空洞的言辞外,并无任何实际行动来支持雯丽母亲可能的反抗行动。因此,雯丽母亲在经过两天的纠结之后,屈从于传统礼教的淫威,成为江少言的第二个二姨太。
雯丽母亲的这段情感经历是当时中国女性憧憬“有意识”自由与深受“无意识”束缚的生动体现。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方面憧憬着新的、现代的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又无法彻底摆脱传统礼教的不散阴魂。章太炎1913年刊登了一份征婚广告,提出三项征婚条件:“一、须文理通顺,能做短篇;二、须大家闺秀;三、须有服从性质,不染习气。”[3]这些征婚条件与现代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的时代主题显然相悖,反映出他灵魂深处的无意识层面与传统礼教之间无法割舍的情愫。由此可知,现代的婚姻观念虽已被中国社会有所认知,但对大众的影响力还非常有限,缺乏充分的社会接受度,根深蒂固的传统礼教仍然支配着部分民众对婚姻生活的认知。这是因为,“除了遗传的天赋和品质以外,是传统使我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但我们极少意识到,同传统的强有力的影响相比,我们的自觉的思想对于我们行为和信念的影响是那么微弱”[6]。
二、自我与现实的冲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使得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男权中心话语开始遭到质疑与动摇。正是因为五四运动注重个人自由和妇女解放,女性纷纷效仿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毅然走出束缚自己的家门,这是中国女性第一次开始发现自我。当时接受新思想启蒙的女性纷纷放足,追求优雅得体的现代衣饰。她们开始积极地接受现代的生活方式,甚至能够用英语作为交际工具,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意味的社交场上应对自如。雯丽母亲就是这样一位摩登新女性。她出身于有教养的富裕家庭,八岁就放了足,有幸进入教会学校就读,她“有好多好东西,都是从不同的国家买来的。她喜欢英国的饼干……喜欢英式的家具、意大利的汽车、法国的手套和鞋子、白俄的浓汤和忧伤的情歌、美国的爵士乐和汉弥尔顿的手表。水果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另外所有的东西必须是中国的”[5]82。她会玩西洋跳棋,在外国客户面前也落落大方。在时代大潮的熏陶下,“女性的发现”日益成为她更愿意认同接受的伦理价值取向,从而对“夫为妻纲”的传统礼教的家庭安排越发排斥。当她因接受现代教育而不再只是软弱和缺乏智慧时,也就越来越不能安于传统家庭安排给女性对丈夫言听计从、忍辱负重的角色。由此,她开始试图用新的人生观、价值观衡量自我,审视自己的现实地位和文化处境,反思自己的生命意义和生存方式,追求做“人”的资格,在生活的调教下,她逐渐成为有主见有思想、敢于蔑视传统礼教的新女性。面对妻妾成群的丈夫,雯丽母亲不像其他姨太太,一味压抑自己的个性,从不敢把任何对男人的不满流露出来,更遑论和丈夫争吵,“假惺惺的,装得比别人都高兴,好像在争夺一个奖品似的”[5]83。
曾经,在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里,中国女性的自我被泯灭于“三从”“四德”的十字架上。穷其一生,中国女人的人生轨迹无非是做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妻子和一个好母亲,外面精彩纷呈的世界和她们无关。她们接受的是非常传统的教育:“女人的眼睛决不是用来读书的,而是用来做针线的;姑娘家的耳朵决不是用来听各种意见的,而是用来听命令的;姑娘家的嘴唇应该很小,不轻易启齿,只在表示喜欢或请求同意时才开一下口。”[5]94对女性而言,忍辱负重是美德,相夫教子是天职。所以,当雯丽母亲觉醒的自我,邂逅了江少言其他几位没文化的姨太太时,女人间的勃谿相向一次又一次发生,雯丽母亲每次都占不了上风。“她想要一碗稍稍特别一点的面条要看白眼,她喜欢法国皮鞋要受到嘲笑,她看报纸也要受到另眼看待。”[5]99而且还经常受到这样的嘲笑:“哼,二姨太,老实说,你不过是第二个二姨太,只有她一半权利。”[5]99第二个二姨太像咒语似的压得她透不过气来,每到晚上她都要跟镜子里的自己说话,特别是当别人用第二个二姨太这几个字来骂她时,她会“在镜子前坐好几个钟头,骂那个盯住她看的第二个二姨太”[5]84。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雯丽母亲想要得到自由平等,想要得到社会的认可,甚至是丈夫的认可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她受的教育让她明白:“不管她怎么改变她的生活,她也无法改变她周围的世界。”[5]94黑云压城般的沉闷与压抑,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绝望地缠绕着雯丽母亲。终于在一次激烈的冲突后,江少言的一句“这事已经定了,你变不了了”[5]84让她下定决心:“你以为我变不了吗?”[5]84为了自由,为了爱情,胆识过人的她冒天下之大不韪,决绝地割裂亲情血缘,抛下年仅六岁的爱女,义无反顾地逃出了家门,奔向了心爱的人。
雯丽母亲身上呈现的这种自我与现实的冲突在五四时期曾经困惑过一代青年学者。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婚姻自由、个性解放,打破父权、夫权。追求恋爱、婚姻自由平等的“娜拉”成为中国青年女性的样板。然而,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多么丰满,当时的社会生活现状就有怎样的骨感。许多接受了新思想、具有新观念的女性,为了爱的那丝光阴,努力抗争,萧红、庐隐、石评梅、谢冰莹等,莫不如是,她们在追求浪漫爱情和个人幸福时,曾经怎样的义无反顾,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悲惨遭遇,足以令后世读者悚然心惊。因此,一部分萌生了自我意识的新青年在她们的遭遇面前,选择了对现实屈从。鲁迅向许广平非常坦诚地承认:“我自己还是世人,离不掉环境,教我何从说起。但倘到必要时,我算是一个陌生人,假使从旁发一通批评,那我就要说,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有时也想另谋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这生活还要遭人打击,所以更无办法,‘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苦苦过活’,就是你防御打击的手段……但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7]224在争取婚姻自由的道路上,被公认为精神斗士的鲁迅尚且要在某种程度上向社会表示屈从,更遑论一般的青年了。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士,鲁迅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他犀利的批判锋芒和热情的鼓动宣传曾经激励大批年轻人义无反顾地向传统婚姻发出决绝的反抗,但自己的婚姻却依旧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其根源便是传统礼教的重压。
三、人格的独立与依附
辛亥以降,中国社会的先进女性知识群体,在现代社会思潮的启蒙下,透过女性作为性别意义上的“女人”的迷雾,开始意识到女性作为社会“人”的价值,从而积极投身于争取民族解放而后达到自身解放的时代洪流中,身体力行阐释这样的认识:女性不是物化的男性附属品,更不是男权中心话语的附庸,而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新兴力量。五四新文化运动更使得中国女性正式浮出历史地表,伴随着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离家出走的那“砰”的关门声,中国女性中的先进分子从沉睡中被猛然惊醒,她们以决绝的姿态挣脱传统礼教的严酷羁勒,纷纷走出家庭的牢笼,勇敢面对前辈们不曾遭遇的难题,在寻求社会空间和心灵解放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文艺复兴”。在此背景下,雯丽母亲从追求自由恋爱到反抗传统的家长意志、从争取婚姻内男女平等到毅然从夫家出走,无不表现出她在精神上和行动上与时代先进思潮的合拍。
然而,民国时期的先进思潮并没有使得中国女性立即摆脱传统的重压。在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中,支配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礼教的伦理观念倡扬“尚群”而“无我”,即以牺牲自我个性来维持社会群体内部关系的稳定,最大限度地保证统治者对社会成员的掌控。这种“无我”特性使个体丧失自我,淹没于群体当中。而人格的丧失,必然会产生社会依附性。这种依附性在中国女性身上有着极深的烙印。当人类社会初入文明状态时,自然的两性差异形成“男强女弱”的社会分殊。男性因体力优势成为家庭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提供者,女性因只在家中从事次要的、辅助性的劳动,成为被供养者。经济上的优势赋予男性在家庭事务中更多的发言权,使其能够主宰整个家庭乃至家庭成员的命运。由此,女性被排除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男性权力结构和主流话语之外,被迫遵守“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伦理要求,成了完全丧失自主意识的被物化的奴隶。漫长的专制社会把“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积淀内化为一定的文化—心理结构,渗透于人们的深层意识,以广泛、持久的隐在观念传递形式实现特殊社会遗传,被动、柔弱的依附型女性人格模式不仅被男性肯定,连女性自身也在维护这个道德藩篱。雯丽母亲身上就呈现出这种人格依附现象。依靠着父亲学者官员的身份,雯丽母亲有幸接受现代教育的洗礼;当懵懂的婚恋自由遭遇家长的反对时,“在家从父”的依附性人格占了上风;做第二个二姨太的日子没有平等,没有尊严,但优越舒适的物质生活却使她离不开江少言;当最后以爱情为由离开夫家时,她又把自己的人生幸福寄托到恋人身上,成为另一个男性的附属物。
女性人格的这种独立与依附的矛盾在民国时期相当普遍,就连一些名满天下的女性也未能免俗。看似“世事洞明”的才女张爱玲因幼时得不到父亲保护,长大后总不自觉地选择年长的男性做伴侣;才女林徽因对父爱不满形成了自恋、暴躁、情绪化的小女孩性格;更有一部分出身底层的女性因经济匮乏,人格的依附现象更为严重。在逃离闭塞旧家庭的日子里,才女作家萧红挨饿、受冻,拖欠房租。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家信请求火速援助,但远离家庭的她等到的只是更为寒冷的冬雪和更加刺骨的北风。一生追求自由独立的她为生计所迫,被一个男人抛弃之后必须找到另一个男人做依靠,未能自由自在地生活过一天,就因为不能安身立命,年纪轻轻就凄婉谢世。作家庐隐先后爱上几位男性,但他们都不能承担家庭责任,这位名噪一时的才女始终没找到一位合适的男性来安放她的情感、思想与自由,最终被生活的柴米油盐拖累致死。离开了家庭的护翼,仅经济的困顿就会使她们轰轰烈烈的反抗结局变得黯淡、凄惶。
这些状况的出现,充分反映了作为后发型的中国社会演进的独特复杂性:社会政治经济状态的成熟、进步总是滞后于社会精神层面、观念层面的成熟、进步程度。因此,女性在自我觉醒后,总会遭遇因社会相应的变革尚未开展而导致无法寻觅到足够的、合适的生活空间的历史尴尬。那些追求自由的女性在这样严酷的社会环境面前,出现异化也就在所难免。
同时,在男权中心话语的长期浸润下,已经进入许多女性层面的男权至上传统伦理仍是羁绊女性的沉重枷锁,成为中国社会在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过程中难以根除的病灶癌变,即使在女性反抗男权中心话语的侵害过程中,女性自身还带着这种传统的锁链。因此,民国时期传统桎梏虽已开始松动,但女性尚未在情感层面、清醒的生命体验层面建立起“我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的自我意识。这种情况下,像雯丽母亲这样的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大时代中的浮萍,她们从一种附属品转变成另一种附属品,而所谓的男性的救赎只能为她们的自由独立蒙上阴影,她们受伤的灵魂和坎坷的命运几乎是注定的。模仿娜拉出走的精神和勇气固然可嘉,但她们的出路却只有两条:堕落或者回来。
四、结语
民国时期,一些先进女性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生在变动的时代,所以我有两副面孔,一副听从旧言论,一副聆听新言论。我的内在有一部分停留在东方,另一部分眺望着西方”[8]。在这样一个时代,她们一方面欣喜地感应着现代社会思潮的强劲启蒙,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传统礼教的重压。雯丽母亲就是一个典型。谭恩美通过对雯丽母亲形象的塑造,向后世读者昭示:这个女性身上所展现出的“有意识”自由与“无意识”束缚、自我与现实的冲突、人格的独立与依附,首先是民族传统的产物。中国女性要实现真正的独立解放,除了要依靠自身能力、信念和理想外,实现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健全的现代转型是更为关键的。非如此,中国女性便不可能真正彻底、全方位地摆脱传统礼教的阴影,不可能实现与极端偏废的女性价值观念的真正决裂;非如此,中国女性便只能像雯丽母亲那样,无法摆脱在个体无力抗拒的传统重压之下被扭曲的生存境遇。
[1]邓颖超.错误的恋爱[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
[2]朱彦茹.毛彦文的婚恋经历与时代变迁[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
[3]梁景和,寥熹晨.女性与男性的双重解放[J].史学月刊,2012,(4):83—91.
[4]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5]谭恩美.灶神之妻[M].张德明,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6]王栋梁.民国时期婚姻文化悖论现象解析[J].人民论坛,2014,(11):180—182.
[7]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何晓鹏,张幼仪.旧道德与新女性[J].看历史,2011,(6):42—51.
Distortion under the Great Pressure of Tradition——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Image of Mother Wen1001b3 s Mother
Zhou Congxian
The Kitchen God’s Wife is the second best-selling novel of contemporary female Chinese-American Amy Tan.The cultural image of Winnie’s mother in the book has gone unnotic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This character shows such features as conscious freedom and unconscious constraint,conflict between reality and ego,dependence and independence of personality.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image can help readers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s hardship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culture as well as the females’distorted life under the great pressure of tradi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Kitchen God’s Wife;Winnie’s Mother;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06
A
1007-905X(2017)09-0091-04
2017-05-25
周聪贤,女,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编辑 贾 敏 陈 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