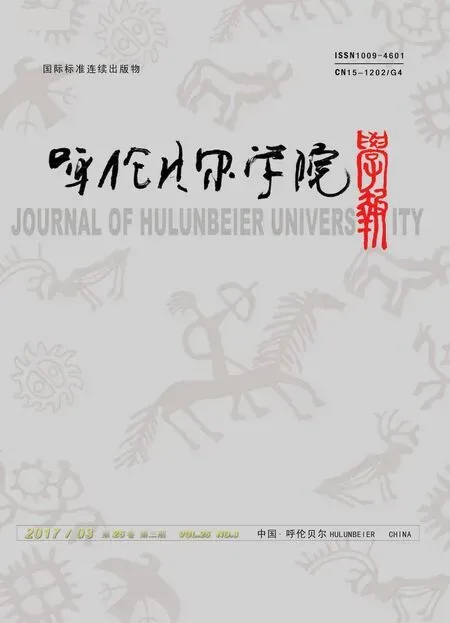村落边界的开放与封闭
——基于“理想类型”的反思
潘 琼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4)
1990年至 2010 年期间,我国行政村的数量从 100 多万个锐减到 64万多个,平均每天减少50个左右[1]。而在2002年至2014年,我国自然村从363万个减至252万个,10年锐减110万个自然村,每天约有300个村庄消失[2]。学术界也对这一社会热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李培林教授以发达地区的城中村为研究对象,提出了“村落终结论”,在其众多的村落终结的研究成果中,于2004年出版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一书对作者思想的展现更全面、更深入,也颇具亮点。然而,村落的终结具有很强的地域局限性,村落个体化、原子化的现象更具普遍性,尤其是在中部的农村地区更显著。
一、调查资料的加工:塑造“理想类型”
作者以广州市地处市区、无农用地的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介入观察、个案研究、深入访谈、问卷调查等实证调研方法,但没有像《江村经济》等那样局限于一个村落的剖析,也没有像王汉生、王晓毅、李国庆等那样通过一些变量构建一个象限图。作者为了避免个案解释力的局限性,也为了避免所构建的象限类型难以对现实中的村落进行全面的分类,另辟蹊径,试图塑造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想类型,通过构建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概念以便提高本书的学术对话能力,弥补个案研究的不足。作者没有将其在珠江三角洲中调研的城中村一个个单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是将这些村落“揉碎”在一起,根据它们真实现象背后的共有本质,按照相应的主题将它们进行重新组装。作者还给这些地处市区、无农用地的城中村起了个学名——“羊城村”,它代表着这样一类村庄——“羊城村不仅仅是一个村落,它也是一个特殊的企业,是一种村落和企业合一的特殊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网络和企业组织之间的一种形态。[3]作者试图用一个“连续谱”①的分析框架来解读这一类处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村庄,具体而言,这是一类拥有集体经济的村落,但归村民集体所有的集团公司不同于市场中的一般的公司,其经营管理不仅受到正式的法律制度的约束,还深受村规民约、乡土道德、人情关系等乡土文化及村落行政权力的约束。
但本书没有完整地、全面地呈现出一个村落的真实风貌,而是将多个村落的实态杂糅在一起,它们之间有相同的“共性”,但也有不兼容的“个性”,这必然会引起冲突、不协调,甚至使得书中一些描述羊城村现象的内容相互矛盾。其次,这样只能为我们呈现出当地所有城中村的所有焦点问题,让我们知道这些村庄面临的一切迫切需要解决的困境。但每个村落不会遭遇以上所有的困境、问题,本书不能将一个真实的城中村还原在读者面前,让我们真正地了解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架的城中村。
二、村落边界的开放与封闭
(一)羊城村:五大边界的完全开放
村落的存亡成为了现实焦点,也引来了学术界的探讨,关于农村的最终命运,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存续论”。Essexetal认为:“只要存在着粮食和农产品生产需要,存在着地理、文化、治理体系方面的支持,农业和农民、村庄似乎就会继续存在。”[4]龚春明、朱启臻认为多数处于“中间形态村落”若能将自己的价值与国家的政策有效连接,村落可以得到持续发展。[5]第二,“转型论”。毛丹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 30年变迁的考察,发现“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4]。贺东航、张现洪认为在国家力量下沉、市场环境的刺激、城镇化等的作用下,农村有能力整合社会经济资源,实现乡村社会的转型。[6]刘玉照以传统农村社区为研究对象,提出了“村落转型论”,他认为村庄拥有集体经济后,会从道义型共同体转向利益型共同体。[7]而李培林却提出了更大胆的观点——“村落终结论”,甚至将“农民工、失地农民、农业村落终结问题”称为“新三农问题”[8]。他以广州城中村为研究对象,总结其村落终结的过程,也是其村落边界开放的过程——经济边界、自然边界、行政边界、文化边界、社会边界依次开放。具体而言:首先,在城市化的客观浪潮下,羊城村由“乡下农村”摇身一变成为“城市中心”,经济边界开放。其次,经济边界的开放为羊城村提供了大量商机,许多房地产公司纷纷前来开发土地,村民拥有开发权的土地面积减少,村民自由活动的地理范围缩小,自然边界发生了变化。再次,集团公司的规模已经冲破了行政村的界限,并且行政村随着集团经济规模的变化或合并或分解,行政边界也开放了。另外,现在的羊城村中不仅有大学生、白领、小老板、打工者,还有经营走私、贩毒等非法交易的人员,原本简单的羊城村充斥着多种社会阶层、职业背景的外来人员,影响着当地村民的价值观念。受到多元文化影响的村民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了原有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精神风貌等。原来的共有的文化价值、乡土理念、传统规约被摧毁,传统的价值体系解体,文化边界被冲破。最后,随着经济边界、自然边界、行政边界、文化边界的开放,社会边界也遭遇冲击。其中最深刻的是迁居与迁坟使得社会关系网络完全解体。“如果说迁坟是历史沉淀的村落社会关系网络的解体,那么迁居则意味着现实社会关系网络的解体。”[3]142祖坟是血脉相连的表征,也是村民寻根溯源的根据,迁坟使得祖先传承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生了变化。而“迁居”对现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冲击更直接、更深入,村民以前是聚居在一起,过着“鸡犬相闻”、“相互串门”的乡村生活,但村民现在搬入不同的小区,与陌生的外地人居住在一起,这为村民的日常交往增加了很多障碍,熟悉的生活共同体就这样被搬迁打破。随着村落最后一道边界的破碎,村落就此终结。
(二)中部原子化村庄:情感边界的封闭
然而“现有的城中村以及即将步其后尘进入城市化进程的这一类村落,在全国所有的村落中毕竟是少数。”[9]所以,对于多数村民而言,村落的消失离他们还很遥远,他们的苦恼不是产权的界定、公共资源的分配,他们也不关心社会关系网络的破裂;他们的苦恼是个人的经济条件得不到改善,他们关心的是个体利益的得失。而对于多数村落而言,其面临的治理危机不是集体经济的经营不善、村落利益受损,而是“公共事务治理从‘集体化’转向‘个体化’”[10]。就中部的农村地区而言,贺雪峰曾指出“中部农村的农民是分散的、原子化的”,每个人都是独自地践行个人利益的理性人[11]。如果说羊城村经历了上述边界的开放,那么中部原子化农村正在面临情感边界的封闭,村民依据个体利益单独行动,传统时期浓厚的乡土归属感正在淡化,同村同根观念淡薄,村民集体行动困难,村落公共事务衰败。
在河南省鄢陵县有庆祝元宵佳节的传统,当地村民认为正月十五日晚上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这天是庆祝今年丰收、感谢诸神保佑,祈求明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祥瑞之日。各家各户在春节期间祭拜祖先、缅怀先人;而元宵节则是祭拜天地全神、祈求祥瑞,全村村民有一个共同祭拜的对象,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其重要性可想而知。所以,传统时期的村民为了向神灵彰显诚意,会集中全村的人力、物力、财力隆重举办最高水准的庆祝、祭拜活动,由此产生了组织、协调该项活动事宜的社会组织——同庆会。以段庄村同庆会为例,其活动主要有祭拜天地全神、在本村的庙宇祈福、搭建“熬山”(即闹元宵必备的花灯架,总高度将近4米)、表演节目等。同庆会的会员默认为全村村民,各村同庆会的入会条件也只有一个——拥有本村村籍。传统时期的每个村民都会拿出自己的优势、特长积极参与,家庭富裕的村民会主动多拿“灯油钱”(举办同庆会的资金来源);年轻力强的青年男子负责危险的、耗体力的工作,如搭“熬山”、点“三眼铳”(又称“火枪”)、表演杂技等;中老年男子负责活泥巴、搬运东西、护场儿(维持秩序)等;女性则负责制作萝卜灯、剪纸、整理道具等;小孩子则到本村或附近村庄扯柏树枝、递送萝卜灯等。尤其是一些乡村精英更是积极奉献,为了给本村的同庆会争名誉、攒人气,曾有村民不顾病情冒险演出。段庄村的普通村民郑留印表演的“小毛驴”在当地很有名气,是段庄村同庆会与其他村落的同庆会一较高低的金牌节目。有一年他刚做完手术,不听医生嘱咐、村民劝阻,依旧在扯犟驴表演中卖力表演“跳天桥”(村民将2个将近2米高的木制车立起来,中间搭一个木板,做成“天桥”,他踩着1米多高的“高跷”、套着小毛驴道具往下蹦。)最后导致病情恶化。当时的村民心系村庄,村民的情感边界在村落内部是开放的,村民的集体行动有序、高效。
但在市场经济盛行的客观浪潮的影响下和农民个体理性的主观选择下,本村的经济边界、文化边界开放了,情感边界却随之封闭了,他们只关注自家利益的得失,不再关心村庄的公共事务,集体行动意识淡薄。孙立平将这种个体间社会联系薄弱、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形式追逐自己的利益作为原子化的特点[12]。当地的村民也已呈原子化状态,作为内生的社会组织的同庆会也正在面临着生存危机,村民不再积极参与这项传统的公共活动。段庄村位于县城东边,与城区仅一条环城公路之隔,所以本村村民多是在当地县城打工、做小生意,做着离土不离乡的工作。但年轻的劳动力每天早上 8:00以前就外出务工,直至天黑②才回家,而且在元宵节这天,村民依旧辛勤工作,只是下午下班稍早一些。多数村民晚上回家后,都要休整一天的疲惫,迎接明天繁重的体力劳动,无暇顾及花灯、烟花,更没有村民参与表演;孩子们都在家玩手机、打游戏,沉浸在丰富有趣的网络世界中,对身边的老传统漠不关心;就连留守在家的老年人也不再“迷信”了,他们不再相信神灵的作用,也无力操持公共活动。村民们早已不把这项传统的公共活动放在心上,多数村民都无心参与其中。最后,在会长与村干部的组织下,一些村民象征性地参与庆祝、祭拜,几个暂时无工活儿的年轻人在焊制的铁花灯架子上简单地挂一些彩灯;几个中老年妇女带着儿童去拜神。曾经由全村村民积极参与的一项集体活动,却在高薪的诱惑、无神论的影响、现代娱乐的冲击下,成为一项参与者寥寥无几的“鸡肋”。而纳入城区的村庄及县城近郊的村庄(苏岗、轩岗、王岗、新庄等)自90年代以来陆续解散同庆会,同庆会的传统、惯例也早已被村民遗忘。在集体行动中存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说的“搭便车”的理性个体,但当地的村民对此事的漠视已经达到不屑于搭便车的程度了。而且我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危机很普遍,“在很多村庄无人组织、少人参与,呈现普遍衰败的景象”[10]。
从个体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羊城村的农民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所以出现了“一线天”、“贴面楼”等建筑怪物以达到空间利用最大化;而段庄村的农民则是充分利用务工机会以达到机会成本损失最小化。在当地,多数村民从事建筑、装修行业,这些行业的工期安排受天气、气温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所以冬季会有停工现象。由于成年男性劳动力的日工资较高,可达到 150元——350元,所以村民会觉得几天不上班就损失了一笔可观的收入,短暂休整的农民都希望早日上班。而每年临近元宵节时,气温回升,工地开工,村民不愿失去赚钱机会而放弃参与同庆会。所以在村民看来,同庆会的活动已不再充满着祥瑞与欢乐而是充斥着高额的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参与同庆会就意味着损失了本可以获得的经济收益。村民的情感具有内向性、封闭性,没有向村落开放,难以为了整体的村落利益而不顾金钱、利益的得失,村落的公共事务陷入了自利经济学陷阱之中。
道格拉斯·诺斯曾指出文化因其特殊的渗透方式而具有连续性[13]51,“具有极大的生存能力”[13]61。但同庆会作为民间文化产物的社会组织已经面临着解体的危机,那么原子化村落的现代公共事务更是无人参与。村民大会只在换届时召开,而且参与者都是走过场;2015年以前政府没有设立垃圾箱、垃圾场,村民早已习惯性地将垃圾丢入公共河道、坑塘等等。村民在传统公共事务与现代公共事务中的低参与度都表明村民个体的情感边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乡土归属感低,集体行动能力不足,公共事务治理面临着“个体化”的困境。虽然这些村落的边界不像羊城村那样遭到完全解体,但村民封闭的情感边界造成村落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极低。如果说羊城村是珠江三角洲的城中村村落边界开放的代表,那么段庄村则是河南原子化村庄情感边界封闭的代表。
三、不同类型村庄的相同行为逻辑
羊城村的公共事务受到村民的密切关注,段庄村的公共事务却无人问津,看似相悖的行为,却有着共同的行为逻辑——农民的经济理性。羊城村拥有村集体经济,村集体经济的分红是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虽然羊城村的集团公司推行现代企业管理革新,但重大经济决策仍由股民“一人一票决定”;集体经济实际上由村委会管控;羊城村股份的分配、管理深受当地村规民约、人情关系的影响。所以村庄规章制度的制定、村干部的选举、村民的意见等都与每位村民的分红收益、长期利益密切相关,所以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很高。而段庄村因为没有集体经济的维系,村民没有共同的利益目标,公共事务对村民利益的影响很小,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就很低。
进一步讲,他们的经济行为都是嵌入到当地的行为规则之中的。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现象是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本书深受新经济社会学的影响,旨在寻求经济生活中的社会规则,其主要假设就是“经济行动是一种社会行动,经济行动是嵌入社会境况的,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构成。[3]15”就村集体经济的运行规则而言,企业制度和村落行政组织、社会关系网络是混合在一起的,看似充斥着弹性的土地产权却有着乡土社会特有的运作规则。过去违反计划生育规定或违法犯罪等的村民却在股份分红中的正当利益遭到侵犯,这虽然不合法,但却保证村民能够遵循村规民约和乡土道德,维持乡村秩序的稳定。此外,民间金融组织的规则、民间借贷的利息等都是羊城村的传统惯例。羊城村的交易关系契约除法律契约外,还存在着民规契约、关系契约,看似理性的经济行为实则深受社会规则的制约。而段庄村虽然没有完善的契约体系,但村民具有行为性相互依赖的特点,农民个体采取行动时会考虑其他农民的行动,大家把多数人的行为规则作为必须遵循的社会规则。当大家发现身边的工友都没有参与同庆会的活动而是继续工作时,每个人都觉得“工作”的行动是同大家保持一致的,是遵循村民们默认的规则的。久而久之,集体行动的传统惯例被打破,单独行动的现代惯例得以形成,村落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极低。
注释:① “
连 续谱” 是一种 打破传 统二元 分析框 架的分 析方法,它试 图划分 或解释 更符合 现实的 类型或 现象。②
当地 的下班 时间不 固定, 根据天 色早晚 确定。
[1]李培林.从“农民的终结”到“村落的终结”[J].传承,2012(15):84-85.
[2]凤凰财经.保护村落,更要守护村魂[EB/OL].(2016-05-30).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531/14442893_0.shtml
[3]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毛丹.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四个观察维度[J].社会学研究,2010(01):1-33.
[5]龚春明、朱启臻.村落的终结还是纠结——文献述评与现实审视[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06):138-142.
[6]贺东航、张现洪.集体林权改革后的农村社区共同体的转型与重建[J].东南学术,2013(06):40-45.
[7]刘玉照.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J].社会学研究,2002(05):193-205.
[8]李培林.全球化与中国“新三农问题”[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02):5-8.
[9]王振威.另一类“村落的终结”[J].社会观察,2008(02):71-72.
[10]王亚华,高瑞,孟庆国.中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危机与响应[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23-29.
[11]贺雪峰.论熟人社会的人情[J].南京师大学报,2011(04):20-27.
[12]吴思红.乡村秩序的基本逻辑[J].中国农村观察,2005(04):65-73.
[13]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