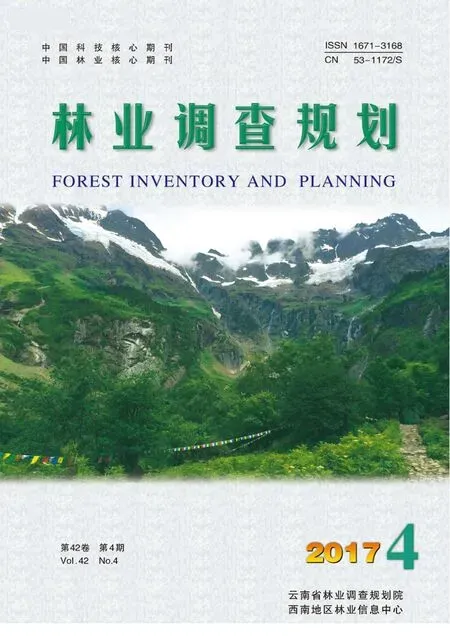生态文明背景下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发展关系探讨
杨 科,吴 霞
(1.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云南 昭通 657000;2.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云南 昆明 650051)
生态文明背景下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发展关系探讨
杨 科1,吴 霞2
(1.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云南 昭通 657000;2.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云南 昆明 650051)
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的关系一直是影响保护管理成效,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程度,反映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重要方面。文章以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对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从绿色发展的视角,提出保护区社区实施绿色发展的对策措施,如扭转自然资源低及利用方式,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促进社区产业结构升级,加大科研支持力度等,以扭转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生态良好”与“经济贫困”的不和谐状况,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社区发展;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
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健康、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主要保护地类型,是人类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在我国,许多自然保护区在划建之初,往往先划后建,以抢救性保护为主。由于社区人口压力大,基础设施落后,信息闭塞,经济发展水平低[1],造成自然保护区与社区争夺资源的现象普遍[2-3],在西部地区尤为突出。据统计,经济发展水平较不发达的西部地区有10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93.4%,其中80%以上的保护区内部及周边存在成型社区[4],平均每个保护区内定居约 1.5万人,周边人口达5万之多[5],与周边社区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地处云南省昭通市的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近年来,学者们对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发展方面分别从社区共管[6-8]、协调发展[9-11]、参与机制[12]、生态补偿[13]、人为干扰[14]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为解决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的矛盾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以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案例,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试图从绿色发展视角,探讨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发展的关系。
1 研究区概况
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是2013年12月25日经国务院以国办发〔2013〕111号文件批准建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保护区成立之前,这些区域基本上都属国有林场,因区位特殊和重要,自然资源丰富,自1984年以来,初步划定为市级、省级自然保护区后,再经整合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1 基本情况
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昭通市境内,地理位置为E103°51′47″~104°45′04″,N27°47′35″~28°17′42″,海拔905~2 450 m,由朝天马(彝良、盐津、大关三县结合部)、三江口(大关、永善、盐津三县结合部)、海子坪(彝良和威信两县结合部)3个片区组成。保护区总面积 26 186.65 hm2,其中:朝天马片区面积 15 004.06 hm2,三江口片区面积 8 386.98 hm2,海子坪片区面积 2 795.61 hm2。
保护区是整个乌蒙山系目前保存面积较大而完整,类型结构自然而原始,并具有云贵高原代表性的亚热带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和高山沼泽化草甸湿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区内由珍稀孑遗树种为优势组成的珙桐林、水青树林、十齿花林、扇叶槭林、峨眉栲林、桦木荷林等珍贵的原始森林群落保存完好;云豹、林麝、黑熊、藏酋猴、小熊猫、中华鬣羚、大鲵、贵州疣螈、四川山鹧鸪、红腹锦鸡、白腹锦鸡、白鹇、白冠长尾雉、凤头蜂鹰、黑耳鸢、珙桐、桫椤、南方红豆杉、福建柏、连香树、水青树、天麻、筇竹等为代表的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资源广泛分布。在保护区近期组织完成的科考中,记录到野生维管束植物179科756属 2 174 种(包括28亚种,153变种),其中:中国特有种 1 063 种、与云南共有种125种、保护区特有种28种,哺乳动物9目27科71属92种,鸟类18目54科363种,两栖爬行动物4目24科61属94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天然种质基因资源库。保护区还是我国野生毛竹的天然分布地,是世界筇竹的最集中分布中心,是天麻的原生地和模式标本产地,是长江水系的重要水源地,是区内的高山水塔,更是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自然保护区所涉社区基本情况
保护区地跨大关、彝良、盐津、永善、威信5个县。涉及彝良县小草坝镇、两河镇、钟鸣镇、龙海镇、牛街镇、洛旺乡,大关县木杆镇、天星镇,永善县团结乡、细沙乡、桧溪镇,盐津县柿子镇、庙坝镇、中和镇、豆沙镇,威信县长安镇等5个县的16个乡(镇)31个行政村756个村民小组 26 881 户 110 751 人。同保护区接壤的有162个村民小组,部分在保护区内生产生活的有24个村民小组723户3 404人。
朝天马片区位于彝良、盐津、大关三县结合部,涉及彝良县、盐津县和大关县3个县9个乡(镇)17个行政村462个村民小组 16 586 户 66 705 人。同朝天马片区接壤的有85个村民小组,部分生活在朝天马片区内的有6个村民小组272户 1 040 人。
三江口片区位于永善县东北面,东连盐津县对河坪,南与大关县北端的癞子坪接壤,西邻永善县二坪子,北至永善县马颈子。涉及大关县、永善县和盐津县3个县5个乡(镇)11个行政村222个村民小组 7 743 户 31 420 人。同三江口片区接壤的有59个村民小组,部分生活在三江口片区内的有1 个村民小组13户51人。
海子坪片区位于彝良、威信县境内,北与四川省筠连县接壤,东临大雪山,南抵灯草湾,西毗角子山。涉及彝良县、威信县2个县2个乡(镇)3个行政村72个村民小组 2 598 户 12 626 人。同海子坪片区接壤的有22个村民小组,部分生活在海子坪片区内的有13个村民小组438户 2 313 人。
2 自然保护区与社区的主要矛盾分析
2.1 自然保护区挤占了社区土地资源
直接把社区土地权属为集体的部分土地纳入了自然保护区范围。1984年建立海子坪省级自然保护区时,由于当时整个昭通地区的生态植被破坏极为严重,因抢救性保护的需要,为保持保护区生态系统的相对完整性,把洛旺乡中厂村的小河、厘金、豆地、塘房、海子、湖坝等村民小组的集体林地一并纳入海子坪省级自然保护区。2012整合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时,由于考虑到彝良朝天马和大关罗汉坝之间动物通行的方便,为了不使保护区片区形成孤岛,在整合申报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过程中,根据保护区建立的相关规程需要,建立了一个生物廊带,又把大关县天星镇沿河村的龙塘、三合等村民小组的部分集体林地纳入保护区范围。目前,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范围内还有15%的土地面积权属为集体,有24个村民小组的723户 3 404 人在保护区保护范围内生产生活。
2.2 野生动物肇事危害加大
野生动物对社区居民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影响。随着保护区自然环境改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增长较快,保护区3个片区中均存在野生动物肇事的情况。肇事的主要是黑熊和野猪等,不仅大面积破坏庄稼,造成粮食的大量减产减收,对村民的牲畜形成伤害,更为严重的是对村民的正常生产、生活构成了严重人身伤害威胁。同时,肇事补偿没有完全跟上,野生动物肇事补偿交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程序复杂,理赔较难,加剧了社区与保护区管理部门的矛盾。
2.3 土地权属争议尚未得到及时解决
保护区同社区部分土地权属争议没有得到及时解决。由于历史的原因,在20世纪50~60年代划建国有林场时同社区间的界线不是十分明确,群众也不太计较。现在部分国有林场整合申报成自然保护区,农村土地经营权已随之下放,涉及到对森林资源的直接利用,群众对林地权属问题逐步看重,开始出现村民同保护区之间的一些土地权属争议。因为历史久远,或确实存在边界不清,或是双方都有权证等情况,解决处理难度很大,争议难以得到及时处理,导致争议地块逐年增多。
2.4 生产经营行为受到约束
建立自然保护区后社区群众的部分生产生活行为受到限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自然保护区内禁止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笋、采药、开垦、采石、采沙等活动。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大于3 300 hm2天然方竹林和大于1万 hm2的天然筇竹林一直是保护区周边社区群众的采笋对象,每年每户居民的采笋收入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全面禁止后,对周边社区群众的影响不小,收入减少不小,产生的矛盾也不小。
2.5 发展机会遭受限制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可能会导致周边社区失去较多发展机会。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后,在保护区周边矿业资源的开采必然受到严格控制,水利资源利用、农特产品加工、竹木制品加工、家畜集中养殖都将受到一定的限制,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社区的发展。
3 以绿色发展理念促协调发展
在传统发展理念下,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长期难以调和。昭通市由于开发较早,人口密度达260人/hm2,人地矛盾突出,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社区关系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的关系实质上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是反映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重要表征。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绿色发展理念为协调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保护与社区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具体对策建议如下:
1)转变自然生态资源利用方式,促进绿色发展
云南乌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资源丰富多样,具有多样性和脆弱性特点,决不能按照传统资源利用方式,走拼资源、拼环境,最终牺牲生态的老路。保护区是为了抢救性保护而划建,使当地极为稀缺的自然生态资源得以存续。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面广量大,而且气候宜人,发展生态旅游、生态休闲、森林康养等基于生态优势的生态休闲服务业条件十分优越。只要创造必要条件,转变资源利用方式,变“砍树”为“看树”,变“卖木材”为“赏景观”,大力培育发展森林旅游、生态休闲、森林康养等产业,抓住国家正在实施的供给侧改革机遇,推进生态服务型绿色产业发展,把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转化成为发展的基础条件,促进保护区内外社区产业结构从“一产”向“三产”跨越,就能够把青山绿水转化为金山银山,从而使保护区的保护成果和提供的生态服务惠及社区群众,构建起自然保护与绿色发展融合互惠的自然保护区新模式,扭转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生态良好”与“经济贫困”的不和谐状况。
2)改善社区基础设施,为保护区社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造条件
积极争取国家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倾斜政策,对农村及贫困地区的各项扶持政策,以及2017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支持农村“旅游+”政策,充分利用这些政策红利,加以科学合理整合,使保护区社区的交通、通讯、电力、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条件得到全面改善,为保护区森林旅游、生态休闲、森林康养等生态服务型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3)落实中央生态保护扶贫政策,把保护区周边社区作为扶贫项目支持的重点区域。
不能把保护区仅视为保护区管护局的保护区,它是全区域乃直全人类的保护区。因此,政府应高度重视并做出明确的安排,林业、扶贫、水利、农业、交通、教育、卫生、通讯、电力等相关部门必须把保护区周边社区作为退耕还林、产业扶持、生态移民、生态护林员、太阳能建设、饮水工程、农村电网改造、通讯建设、技术培训、教育卫生等项目覆盖的重点区域给予安排。
4)加大对科研监测工作的支持力度
保护区管护局应极积争取财政和上级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多方位开展科研监测工作。对保护区的生物资源种类及数量应定期做好科考、监测及专项调查,掌握清楚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和通报;对天麻、筇竹、方竹等当前已在开发利用的特殊物种,应做好生态学习性、生物学特性以及采摘强度与影响程度的比较研究等各方面的研究工作,为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野生种质基因资源的支持和应用技术的支撑。
5)坚持“保护优先”
不可否认,还有很大数量的群体对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资源的认识不够,无论是管理者、实施者或是参与者都存在。对稳定的生态系统、良好的生态环境、安全的生态屏障提供的宜居舒适环境和优美景观人人向往,但是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缺乏保护意识,对所造成的破坏视而不见。有的旅游规划坚持把道路修进保护区的核心区,这不仅有审美的问题,也存在认识上的问题。所谓“酒饮微醉、花赏半开”,应把握好距离和美的关系,更应树立尊重自然,保护优先的观念。生态旅游开发必须高起点谋划,通过开发建设,能够真正为保护区增色升值,而不是破坏。只有保持保护区的吸引力,开发才有价值,投资才有回报。对保护区其它资源的利用必须做到可持续,保护区周边社区群众才有稳定的收入和永续利用的资源。
[1] 刘静, 苗鸿, 欧阳志云, 等. 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典型模式[J]. 生态学杂志, 2008, 27(9): 1612-1619.
[2] 苗鸿, 欧阳志云, 王效科. 中国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参与机制研究[J]. 林业工作研究, 2007 (7): 57-68.
[3] 欧阳志云, 王效科, 苗鸿, 等. 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探讨[J]. 科技导报, 2002,1(1): 49-56.
[4] 傅晓莉. 中国西部自然保护区社区经济发展研究[J]. 未来与发展, 2005 (5): 51-53.
[5] 苏杨. 改善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的对策[J]. 绿色中国·理论版, 2004 (9): 25-28.
[6] 刘锐. 共同管理: 中国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和谐发展模式探讨[J]. 资源科学, 2008, 30(6): 870-875.
[7] 张金良, 李焕芳, 黄方国. 社区共管——一种全新的保护区管理模式[J]. 生物多样性, 2000, 8(3): 347-350.
[8] 谢屹, 李伟, 温亚利, 等. 构建我国自然保护区区域共管体系的思考[J]. 林业科学, 2007,43(6):111-116.
[9] 苏杨. 中国西部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协调发展的研究[J]. 农村生态环境, 2004, 20(1): 6-10.
[10] 贺慧, 李景文, 胡涌, 等. 试论保护区及其周边社区的可持续发展[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02, 24(1): 41-46.
[11] 杨科, 李文虎, 姚昌礼. 药山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和谐发展研究[J]. 林业调查规划, 2005, 30(4): 115-118.
[12] 诸葛仁, 陈挺舫, 特里, 等.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资源管理中社区参与机制的探讨[J]. 农村生态环境, 2000, 16(1): 47-52.
[13] 甄霖, 闵庆文, 李文华, 等. 海南省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初探[J]. 资源科学, 2006, 28(6): 10-19.
[14] 温庆忠. 人为干扰对珠江源自然保护区森林植被的影响[J]. 林业调查规划, 2002, 27(1): 43-48.
Development of Wumeng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and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YANG Ke1,WU Xia2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Wumeng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Zhaotong,Yunnan 657000, China;2.Yunnan Institute of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 Kunming 650051,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reserve and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case study of Wumeng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reserve and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development to transform the ways of resources utilization, improve the infrastructure, upgrad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crease the support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by whic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undeveloped economy of nature reserve and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would been minimized, and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ould been promoted.
Wumeng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communities development; green develop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10.3969/j.issn.1671-3168.2017.04.022
S759.9;C912.8;F316.23
A
1671-3168(2017)04-0099-04
2017-02-22.
杨 科(1968-),男,云南威信人,高级工程师.从事保护区管理、科研、监测等工作.Email: ztyk68@126.com
吴 霞(1964-),女,江苏沛县人,高级工程师.从事林业调查规划、监测等工作.Email: kmwuxi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