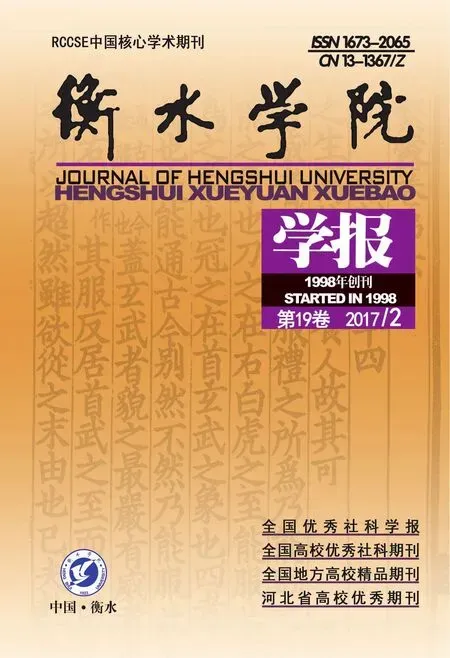董仲舒限田思想再探
秦进才
董仲舒限田思想再探
秦进才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土地兼并与限田抑制土地兼并,是西汉以来重要的社会现象。文章追根溯源,考察董仲舒限田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认为董仲舒限田思想是土地兼并社会存在的反映。董仲舒创造性地揭示了土地私有、土地买卖、土地兼并三者紧密相连的奥秘。其主张限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开启了中国古代限田思想的先河。
董仲舒;限田思想;土地
兼并,亦作并兼,意为并吞、合并等。起源于战国时代,政治、军事方面,指兼并别国土地的行为;经济上,指商人高利贷资本兼并百姓的财产。兼并别国土地,往往与秦兼天下、兼有天下、并兼天下、并兼六国等相联系,与汉并天下、汉兼天下、大并天下等相组合。西汉中期以后,兼并主要用来表述豪强地主等对农民土地的兼并等行为。李奇曰:兼并,“谓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兼役贫民”[1]180。经常出现在史籍中的词语有:兼并之家、亲戚兼并、并兼役使、权门并兼、并兼任侠、豪杰兼并之家、天下豪桀并兼之家等。兼并一词,由战国时代君主雄心勃勃追求的目标、尊崇鼓励的行动,变成了政治家、学者们不断讨论的土地兼并问题,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不可医治的基因之病。董仲舒的限田思想,就是针对土地兼并的社会锢疾,最先揭示其奥秘,最早开出的药方,开启了两千余年限田思想变迁史的先河。前些年笔者曾撰写《董仲舒限田塞并兼思想探微》一文略述窥蠡测之见[2],现在运用新发现的资料,汲取学术界研究新成果[①]关于中国古代田制的研究,从战国至今一直不断,董仲舒限田思想影响深远,阐释、实践者甚多。近三十余年以来,随着简牍新资料的出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新成果。刘泽华先生在《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发表《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提出战国授田制度,袁林、李瑞兰、张玉勤、乌廷玉、余敏声、晁福林、吴荣增等赞同并进行了完善。林甘泉、施伟青、杨生民、白寿彝、高敏等认为国家授田制与私有制并存。沿袭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说法者仍然存在。详请参考郝建平《战国授田制研究综述》(《阴山学刊》2003年第1期)。随着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的发现,张金光、臧知非、杨振红、武建国、朱红林等学者对于汉代的授田制、名田制进行了探讨,深化了其研究成果。胡寄窗、赵靖、徐伟等对董仲舒的限田思想进行研究。笔者受这些研究成果的启迪,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探讨董仲舒的限田思想。,再次探讨董仲舒限田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分析其主要内容等,以求教于大家。
一、董仲舒限田思想的历史背景
土地兼并,从两汉到民国一直存在,构成了中国土地制度的特色,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诸多方面,追根溯源,土地兼并与土地私有密切相联,与土地买卖形影相随。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是形成土地兼并的客观条件,土地兼并是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的必然结果。然而,从土地国有制到土地私有制、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并存和土地买卖的产生、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
(一)西周、春秋时代的土地多级所有制
遥远的原始社会、夏商两朝,年代久远,史料散佚,土地制度暂且不说。
西周时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315,本是周人讽刺政府役使不均的诗句,转化为后世帝王将相追求的目标,现代人又认为是土地国有制的反映,见仁见智说法纷纭。实际上,周天子是天下共主,而不是后世的专制皇帝;是名义上土地最高所有者,而不是能随心所欲地处置天下土地的君主。周天子所直接统治的区域不过方千里[②]《诗经今注·商颂·玄鸟》载:“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第528页)(清)焦循撰《孟子正义》卷六《公孙丑上》言:“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5页)(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卷一一《强国》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1页)《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6页)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肆《称》亦言:“天子之地方千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78页)《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称:“初,雒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至襄王以河内赐晋文公,又为诸侯所侵,故其分墬小。”韦昭注曰:“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颜师古注曰:“宗周,镐京也,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为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为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故《诗》云‘邦畿千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50-1651页)从上述引文看,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区域不过方千里,溥天率土为天子所有,是周人的诗句,而非周王能够实际上控制天下的所有土地。,主要通过天子建国,分封诸侯。“锡之山川,土田附庸”[3]518,授土、授民,把土地分封给诸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4]1284从王土变成了君土,诸侯成为封国土地的所有者。诸侯建家,把土地再分给卿大夫。形成了国王、诸侯、卿大夫等土地多级所有制。固然,周天子可以对受封者有权因功加封土地,也可以因罪夺回田地,但随着周朝的东迁,这些权力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在土地制度上,表现为“田里不粥”。郑氏注曰:“皆受于公,民不得私也。粥,卖也。”[5]357但债台高筑的贵族,为保持其身份、得到必要的钱财,把受封的土地、田里折合成货币,转让给商人、新贵等。周共王三年(约前919年),裘卫以瑾璋、鹿皮披肩等物交换矩伯十三田,执政大臣等主持田地移交手续等事[6]。标志着土地转让行为的出现。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周天子丢掉了号令天下的实力,被人作为尊王攘夷的旗帜。与此同时,争田[③]《春秋左传注》文公十八年载:“齐懿公之为公子也,与邴歜之父争田,弗胜。”(第629页)成公十一年,“晋郤至与周争鄇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讼诸晋。”“晋侯使郤至勿敢争。”(第854页)成公十七年,“郤犨与长鱼矫争田,执而梏之,与其父母妻子同一辕。”(第900页)徐元诰撰《国语集解》卷一四《晋语八》载:“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久而无成。”(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23页)卷一五《晋语九》载:“邢侯与雍子争田,雍子纳其女于叔鱼以求直。及断狱之日,叔鱼抑邢侯,邢侯杀叔鱼与雍子于朝。”(第443页)董仲舒概括为:“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1页)由上述可见争田之激烈。、夺田[④]《春秋左传注》闵公二年载:“公傅夺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贼公于武闱。”(第262页)夺田成为导致鲁闵公杀身之祸的因素之一。成公十七年,“郤锜夺夷阳五田,五亦嬖于厉公。”(第900页)《国语集解》一二《晋语六》载:晋厉公六年,范文子曰:“今我战又胜荆与郑,吾君将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敛,大其私昵而益妇人田,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第393页)可见鲁国、晋国等都有夺田发生。、赏田[⑤]《春秋左传注》成公七年载:“楚围宋之役,师还,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第833-834页)《战国策》卷二三《魏策一》载:“魏公叔痤为魏将,而与韩、赵战浍北,禽乐祚。魏王说,迎郊,以赏田百万禄之。”公叔痤说明后,魏王又“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巴宁、爨襄田各十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84页)。由此可见贵族求赏田的欲望大,君主赐予赏田规模亦大。、赐田、丧田[⑥]《春秋左传注》襄公十年载:“初,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第980页)可见丧田人之多。等事件,不断见于记载,这些土地的争夺与主人的变更是政治行为,是凭借着政治权势的抢夺,是君主对于亲属、功臣、宠爱者等人的赏赐,而不是经济买卖活动;井田、爰田、辕田等田制,屡见于典籍文献,昭示着土地国有制逐渐发生变化。齐国推行的相地而衰征、鲁国的初税亩等,标志着随着土地制度的变革,赋税征收的方式也发生了变革。
(二)战国时代的授田
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思想解放,此伏彼起的各国变法运动,军功爵制、举贤任能等富国强兵政策的实行,铁工具、牛耕等先进技术的普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土地制度的变化,秦、魏、齐等国推行授田制[⑦]战国时代,实行授田制,出土文献有记载。四川青川县出土的秦武王二年的《更修为田律》木牍。《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乙种竹简集释》八三《贞在黄钟》作:“曰:贞在中吕,是谓中泽,有水不腞,有言不恶,利以贾市,可受田宅,擅受其利,人莫敢若。”(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页。《秦简牍合集》肆《放马滩秦墓简牍》二《日书乙种·贞在黄钟》,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3页,除与此标点符号稍有不同外,其他一致)《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附《魏户律》曰:“自今以来,叚(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曰:“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或(域)。”(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46页)诸如此类的资料,都可以证明秦、魏、齐等国的确实行过授田制。。授田制——国家按户授予土地,受田人向国家缴纳租税,服兵役、劳役,受田人年老及身故要还田于国。从国家来看,是授予官僚、黎民百姓田地,从农民来看,是接受国家分给的土地,授与受字义相通,因此文献中既有授田的说法[⑧]有关战国实行授田制的传世文献很多,如(清)孙诒让撰《周礼正义》卷二九《地官·遂人》载:“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注曰:“谓四时小案比,以任民授田也。”(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21-1122页)石光瑛校释《新序校释》卷七《节士》载:“晋文公反国,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将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万。”(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57页)可见授田是政府的行为。,也有受田的记载《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载:“农民户人己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第1119-1120页)《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刘宠》注引《风俗通》载:“人年三十,受田百亩,以食五口。五口为一户,父母妻子也。”(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78页)可见受田是从百姓接受国家授予的田地而言。,授田行为又称为行田[⑩]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卷一六《乐成》载:“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990页)《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载:“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第54、56页)《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的《二年律令·田律》载:“田不可田者,勿行;当受田者欲受,许之。”注释曰:“行,指授田,《礼记·月令》注:‘犹赐也。’”(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二年律令·户律》载:“不幸死者,令其后先择田,乃行其余。”(第52页)又载“有籍县官田宅,上其廷,令辄以次行之。”(第52页)上述的行田,或与授田有关的“行”字,都是指给予、赐予田地。由此可知,《龙岗秦简》载:“廿二年正月甲寅以来,吏行田赢律(?)诈”(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9页)的“行田”,指授予田地。“行田赢律”,即授田数额超过了法律规定。,国家分配土地给耕者耕种称为分田[11]《孟子正义》卷一〇《滕文公上》载:“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第349页)《荀子集解》卷七《王霸》载:“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第214页)由上述可见战国分田制的存在。或分地[12]从田制来看,分地,既有分地予人,又有份地之意。如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卷四《大聚》载:“称贤使能官有材而归之,关市平商贾归之,分地薄敛农民归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07页)《吕氏春秋校释》卷一七《审分》载:“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第1029页)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卷三《园池》载:“故古者分地而处之,制田亩而事之。”(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2页)其他分地含义,不予列举。。国家授田给耕作者耕种并出租赋,称之为赋田[13]《银雀山汉墓简》壹《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载:“巧(考)参(三)以为岁均计,二岁而均计定,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口均之数也。”(第146页)《史记》卷一二八《龟策列传》载:“夫妻男女,赋之田宅,列其室屋。”(第3232页)《汉书》卷二九《沟洫志》颜师古注:“赋田之法,一夫百亩也。”(第1678页)这是从国家的角度看,是赋予百姓之田,故称赋田。从耕作者的角度看,这是国家授予的交纳田赋之田,故也称为赋田。。此外,还有国家出租的土地称为假田[14]《龙岗秦简·释文注释校证》载:“黔首钱假其田已(?)□□□。”(第125页)“诸以钱财它物假田□□□□□□”(第129页)这些简牍可以证明,秦代有假田,后来被汉朝所继承发展。等。诸如上述的称谓,都可以证明战国国家授田制度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方式。
(三)秦始皇的“使黔首自实田”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三十一年(前216年),“使黔首自实田”[7]251。黔首,即平民、百姓。这是中国第一次全国范围内黔首土地的大登记。自实、自占,即自己如实申报,由政府审验确定,是秦汉时代的习惯性用语,经常性行为[15]自实,如《后汉书》卷五六《王龚列传》载:王“龚深疾宦官专权,志在匡正,乃上书极言其状,请加放斥。诸黄门恐惧,各使宾客诬奏龚罪,顺帝命亟自实。”(第1820页)自占,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载:“十六年七月丁巳,公终。自占年。”(第7页)《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的《奏谳书》载:“令曰:诸无名数者,皆令自占书名数。”(第97页)《居延汉简释文合校》载:“初元三年十月壬子朔辛巳,甲渠士吏强敢言之,谨移所自占书功劳墨将名籍一编敢言之。”(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72页)可见,秦汉时代的年龄、土地、财产、功劳等登记,往往由本人或户主申报,然后再由官府审验。“自实”与“自占”等,是秦汉时代具有特色的习惯性语言、经常性行为。。自实田的含义,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考一》说:“是年,始令黔首自实田以定赋。”增加了“以定赋”三字。从清朝以来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解释,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王之枢等编纂的《历代纪事年表》卷二十《秦世系表》曰:“自实,令民自具顷亩实数也。”添加了呈报的意思,这个解释似为今日众说之始祖。一是认为占有土地的地主与农民,只要向政府申报土地数额,交纳税赋,承担徭役,其土地所有权就可以得到政府的承认与保护。二是认为使黔首自由占有土地。三是命令黔首自己去充实(充满、具有)土地,即命令黔首按照国家制度规定的数额,自己设法占有足额的土地,国家不再保证按规定授田[8]。除上述诸说外,还有防止黔首隐匿土地逃避赋税和官员隐匿不报黔首土地贪污的意义等。“使黔首自实田”的措施,承认了黔首拥有土地的现实,无疑给土地私人所有制开了绿灯,但并未公开宣布土地私人所有为合法,也未放弃国家对土地的管理、控制。
(四)西汉初年的授田制
西汉初年,继续推行授田制,张家山汉墓竹简中的《二年律令·户律》所载的从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到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公卒、士伍、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的法令,可以证明的确存在国家规定的授田制,授田制中有着授予土地数量的限制。并规定:“其已前为户而毋田宅,田宅不盈,得以盈。”[9]52不足的可以补足。宅与之适应,“关内侯九十五宅,……司寇、隐官半宅”[9]52。授田制使一些开国功臣获得了土地田宅,在落实的过程中也有困难。因此,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五月,皇帝下诏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1]54-55反映汉初推行授田制的现实以及所遇到的问题,土地已经成为稀有的资源。
(五)土地私有、共有与授田、买卖并存
在汉初实行授田制时,已经存在着合乎法律规定的私有土地和土地买卖。
譬如张家山汉墓竹简记载:“诸不为户、有田宅者,附令人名,及为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边二岁,没入田宅县官。”[9]53就是说没有登记于国家户籍建立户名,而实际上占有田宅者,或依附于他人户籍名称占有田宅者,以及用自己户籍替他人占有田宅者,都属于违法行为,要受到惩罚,这三者实质都是自己占有田宅者。如果用自己的户名,登记于政府的册籍,就合乎法律规定了。
又如规定“欲益买宅,不比其宅者,勿许。为吏及宦皇帝,得买舍室”[9]53。百姓、官吏买卖舍室要符合法律规定,才允许购买。
再如规定“受田宅,予人若卖宅,不得更受”[9]53。国家授予的田宅可以赠予或出卖,但国家不再重新授予。
还有规定“代户、贸卖田宅,乡部、田啬夫、吏留弗为定籍,盈一日,罚金各二两”[9]53。基层的政府官员要为购买田宅者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不得故意为难,故意拖延者要受惩罚,说明土地买卖不仅合法,而且得到了国家的支持。
受田者身死之后,土地不再还给国家,可以由亲属继承。“诸(?)后欲分父母、子、同产、主母、叚(假)母,及主母、叚(假)母欲分孽子、叚(假)子田以为户者,皆许之”[9]53。继承方式多种多样,“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勿听。所分田宅,不为户,得有之,至八月书户。留难先令,弗为券书,罚金一两”[9]53。这是遗嘱继承方式,基层政府官员要亲自参与其事,办理相应手续,即使不能马上办理手续,也可以先拥有,届时再办理,故意刁难遗嘱,不给办理相关手续者,要予以惩罚。
并且还规定“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稾”[9]53。卿以上的三公等官僚、贵族,不仅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田户田”——家庭私有土地,而且享受不缴田租、不出刍槀的优惠政策。
上述史料证明,在汉初推行授田制的同时,已经存在着土地私有、土地买卖。具体到在一个家庭中,有时既有国家授予的土地,也有自己买来的土地,公有、私有共存于一个家庭之中。期望占有更多的土地,是无数人生前的追求、死后的愿望,有墓葬中“溥土”“薄土”简可为证[16]《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载汉文、景帝时代墓葬出土遣册简牍上的文字,八号墓有“溥土一”,在竹笥中有一堆泥土(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7页);九号墓有“薄土一”(第65页);一六八号墓有“薄土二”(第199页);一六九号墓有“溥土一”(第221页);一六七号墓有“薄土一枚”,并有用方绢包裹的土块。六个出土简牍的汉墓中,五个遣册简牍中有“溥土”或“薄土”,可知其并非偶然。对于“薄土”为何物,有学者认为:溥通薄,“薄土,指入册的土地”“薄土,应是地主私人占有土地的直接象征”(《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第173页)。李家浩认为:“名词的‘溥土’实际上也就是《淮南子·坠形训》所说的‘禹乃以息土填洪水’的‘息土’。”(《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龟盾”漆画试探》,《文物》1974年第6期,第64-65页)是神奇之土。裘锡圭认为,“薄土”是《急就篇》中的“薄杜”,指车中荐(《古文字论集·说“薄土”》,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64-565页),与土地没有关系。王晖认为:“薄土”“应就是汉代取自薄姑氏故国五色土中的赤土,是用来封建诸侯王的专用土。但这不是实际上的受封之物,而是通过虚拟的方式希望死者在地下能够受封‘薄土’‘溥土’,享有封土而为侯王”(《汉简“薄土”考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09页)。是否是取自薄姑氏故国的五色土,需要化验后才能够确定。笔者认为,“薄土”与汉代诸侯封国时朝廷授予的“茅土”“主土”一样,有表示土地的含义,有等级高低的差别,反映了汉代人生前与死后对于土地追求的理念、愿望。。授田制下存在的土地私有、土地买卖活动,迅速地膨胀扩展。随着国家掌握的土地资源的萎缩,定期还授调整的授田制很难继续推行下去。汉文帝时,开始“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颜师古注曰:“不为作限制。”[1]1142随之打开了土地买卖的大门,导致土地买卖日益活跃,逐渐形成了国有、私有与集体共有[17]父老僤约束石券曰:“建初二年正月十五日,侍廷里父老僤祭尊于季主疏,左巨等廿五人,共为约束石券里治中,乃以永平十五年六月中造起僤,敛钱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买田八十二亩。僤中其有訾次当给为里父老者,共以客田借与,得收田上毛物谷实自给。即訾下不中,还田转与当为父老者,传后子孙以为常。其有物故,得传后代户者一人,即僤中皆訾下不中父老,季、巨等共假赁田,它如约束。”(宁可《关于〈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文物》1982年第12期)此为汉代土地集体共有的例证。等并存的土地制度,形成了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形态,导致了土地兼并,从而成为自两汉以后无药可以医治的社会基因之病。
(六)中国古代对于土地重要性的认识
中国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农业是根本所在。土地不仅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对于其重要性的说法很多,如“地者,政之本也”[10];“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11];“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曰贵土。土,食之本也”[12];“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13]114;“土田,衣食之源”[14];“土地,本也;耕获,末也。无地而责之耕,犹徒手而使战也”[15]。诸如此类的言论,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土地的重要意义。
土地私有,既使土地成为自耕农赖以生存生活的基本保障,也使土地成为地主剥削佃农的物质基础,成为可以买卖而能生息、增殖、带来剩余产品的特殊商品,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标志。“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16]。楚汉战争时,“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7]2041,“传土地于子孙”[1]2578-2579,是许多人奋斗的动力。清朝人张英指出:“天下货财所积,则时时有水火盗贼之忧。至珍异之物,尤易招尤速祸。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积则不能高枕而卧。独有田产,不忧水火,不忧盗贼。虽有强暴之人,不能竟夺尺寸;虽有万钧之力,亦不能负之以趋。千顷万顷可以值万金之产,不劳一人守护。即有兵燹离乱,背井去乡,事定归来,室庐畜聚,一无可问,独此一块土,张姓者仍属张,李姓者仍属李,芟夷垦辟,仍为殷实之家。呜呼!举天下之物不足较其坚固,其可不思所之保之哉!”[17]同时,土地私有使土地成为社会地位和实际权力的基础,占有大量土地的人,不仅可以享受豪华奢侈、高贵舒适的物质生活,而且可以以一介布衣,其权势“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7]3282,成为横行一方的土皇帝,作威作福。这种现实,使人们对土地趋之若鹜,因此,汉字中的“福”“富”等字,都是以田字为底,正是反映了田为富贵、幸福之本的观念。土地私有、土地买卖,形成了“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18]的格局,因此,生活困苦贫贱者迫于生计压力不得不卖,而拥有权势和财富者,都会不遗余力地去购买占有,豪强兼并土地日益兴盛。
(七)两汉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土地私有、土地买卖,提供了土地兼并的可能性,土地的特殊属性,又会促使人们去千方百计地兼并土地,但兼并土地者必须拥有一定的财富、权势和被兼并的对象。这种条件,随着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日趋成熟。从汉高祖刘邦到景帝刘启时,政治上,汉承秦制,与民休息,迁徙六国后裔,强干弱枝,使社会逐渐稳定下来。经济上,复故爵田宅,赐予随军征战者土地,招抚流亡,开垦荒地,轻徭薄赋,发展生产。思想上,奉行黄老之学,清静无为。师丹概括为:“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1]1142师丹说法是可信的,亦有不准确之处。有土地私有,有土地买卖,就会有兼并之害,当时晁错提出了“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1]1132的问题,只是与师丹所处的汉哀帝时相比轻多了,后人美化为“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19]。历经七十余年的发展,扭转了西汉初年“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残破局面,而发展成为“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7]1417,1420。繁荣的经济,社会的进步,建立在农民辛勤耕作的基础之上,但主要受益者却是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大商人,他们积聚起雄厚的经济实力,以无限膨胀的贪婪欲望,猛烈地兼并农民的土地,掀起了两汉第一次土地兼并的高潮。
官僚贵族,身份高贵,社会地位高,手中掌有权势,经济实力雄厚,是土地兼并的先行者。如淮南王刘安的后妃、子女,“擅国权,侵夺民田宅”[7]3083。衡山王刘赐,“又数侵夺人田”还“坏人冢以为田”[7]3095。汉初诸侯王,是“以千里为宅居,以万民为臣妾”者[1]2138,汉武帝时代,还是“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7]2961,具体到“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7]3098,但他们还要掠夺、兼并平民百姓的田宅,说明他们也是名义上王国土地的拥有者,实际上只能“独得食租税”[18]《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第2140页)。《汉书》卷三八《高五王传》赞曰:“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第2002页)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卷六《谴非》载:“王但得虚尊,坐食租税。”(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9页)三书记述大同小异,同在都是“食租税”,异在表述的程度而已。而已,土地所有权是私有制或国有制,他们并不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土地,因此他们加入兼并土地的行列,掠夺百姓田宅。朝廷大臣上书请求制裁他们,汉武帝不允许。比诸侯王的政治地位略微低些的官僚、列侯,也兼并土地。如相国、酇侯萧何,为免除皇帝的怀疑,“多买田地,贱贳貣以自污”,因此,平民百姓上书“言相国强贱买民田宅数千万”,萧“何买田宅必居穷辟处”[7]2018-2019。萧何贱价购买田地固然是一种政治避祸的方式,但能够买田宅是没有问题的。丞相、南窌侯公孙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1]2879。乐平侯卫侈,“建元六年,坐买田宅不法,有请赇吏,死”[1]622。外戚在兼并土地方面也不落后,汉景帝王皇后同母异父弟、丞相田蚡,本来就“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7]2844,但还不满足,不仅兼并平民百姓的土地,而且要以权势夺取曾为丞相、魏其侯窦婴的城南田,窦婴不允,而种下矛盾的祸根,以致家破人亡。其实,官僚贵族,扩大其田产规模,除了以权势兼并、侵夺外,还可以由受赏赐,合法地把国有土地变为己有,汉武帝寻找到居住在长陵的同母异父姊金俗,“奉酒前为寿,奉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以赐姊”[7]1982。因为是王太后的女儿、汉武帝的姐姐,长陵女子金俗变成了贵族修成君,公田百顷转化为修成君的家产。但贵族官僚趁赐予土地之机营私舞弊超出限度则要受到惩罚。“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又盗取神道外壖地一亩葬其中,当下狱,自杀”[1]2449。盗取公有土地,引来了杀身之祸。有些人依靠其俸禄、赏赐等,购买土地。河东霍中孺之子名将霍去病,曾“大为中孺买田宅奴婢”[1]2931,使其父为富人。当然,官僚贵族兼并土地,并不是要自己亲自耕种,而是作为产业遗留给子孙,成为剥削佃农地租的基础。
豪强地主,西汉中期发展起来,武断乡里,作威作福,“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1]1137,反映的是作为乡里主宰者豪强地主的情况。他们有的是在职或致仕的官僚,有的是土生土长的财主,他们与官府交通勾结,成为兼并农民土地的重要成员。曾为太仆、燕相的灌夫,“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侵夺百姓,以致人们用儿歌诅咒他“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7]2847。内史宁成因罪受刑,诈刻符传出关,回归南阳郡穰县,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后来随“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后,会大赦,形成产业数千金,挟官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7]3135。汉代,“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7]3274。“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20]1648。至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豪强地主兼并土地者,无疑当会更多。
商人、高利贷者,是兼并农民土地的老手。西汉初年,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发财致富。不仅从事盐铁业的临邛卓氏、程郑、南阳孔氏、曹邴氏等富至巨万,田池射乐,拟比人君;而且从事平常行业的,如博戏、行贾、贩脂、卖浆等行业的人,也发展到了千金、鼎食、连骑的地步。他们“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1]1132。但他们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除了供其豪华奢侈的消费、维持简单再生产外,没有合适的部门可供投资牟利,因此将商业资本投向土地,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7]3281穷困潦倒的司马相如、卓文君凭借着盐铁商人卓王孙分予的“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7]3001。宣曲任氏经营粮食发财后,“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7]3280。商人兼并土地,无农夫之苦,而有阡陌之得,粟米之积。
土地兼并者为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商人,而被兼并的土地,除少量官僚贵族、地主、商人的土地和国有土地外,主要是自耕农的土地。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也给自耕农带来了好处,也会使部分自耕农通过兼并土地而成为地主。但是,大部分自耕农由于小农经济的局限性,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生产规模狭小、生产水平低下、经济力量薄弱,再加上天灾人祸、赋税徭役和高利贷商人的盘剥,就是在文景之治的盛世,自耕农的日子也不好过。当时晁错曾具体描述过自耕农生活的困境:“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征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1]1132到了汉武帝时代,“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1]1101。自耕农的生活处境更为恶化,其土地不就更容易被兼并吗?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土地兼并,是土地私有、土地买卖的必然产物,是经济积累的必然趋势。从根本上讲,弊病不在于是否有土地兼并,而在于:一是兼并的土地,能不能转化为商品生产的资本,由兼并而产生新的生产方式。二是土地是一种特殊商品,地理位置不可移动,买卖之后并不能立即消耗掉,又再重新生产出来,但会使贫穷者欲耕作而无土地,富者有田地而缺乏人耕种。失去土地的自耕农,除部分人转化为“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1]1137的佃农外,有的落魄成为奴婢,有的失业成为流民,有的因困苦无告揭竿而起,日积月累就会集聚为推翻皇朝统治的农民起义风暴。这样的土地兼并活动,不仅影响到编户齐民减少、经济衰退,使国家赋税资源枯竭、财政收入减少,而且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直接威胁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土地兼并者以个人财富积聚的目的、形式,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相矛盾,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从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来看,必须使自耕农拥有一块土地,在维护土地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前提下,适当地限制土地兼并,以保证国家对自耕农的控制,以保证社会的安定和财政收入的稳定。
在西汉初年,授田制萎缩,土地买卖兴盛,土地私有制逐渐形成以后,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商贾富豪等利用发展起来的权势、金钱,疯狂地兼并国家和农民土地,形成了官僚贵族、豪强地主等“田宅逾制”[19]《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42页)。对于“田宅逾制”,有些学者认为是观念性词语,而非实指或特指,也有人认为是实指,有具体内容。袁延胜《三杨庄聚落遗址与汉代户籍问题》指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一宅’的面积是‘大方卅步’,约相当于今天1 700 多平方米。三杨庄聚落遗址中庭院面积近 2 000 平方米,基本符合《二年律令·户律》中普通民户‘一宅’的面积。这表明汉代关于住宅大小的规定,可能是一项长期实行的比较稳定的制度。”(《中原文物》2012年第3期)可见“田宅逾制”有着具体的内容规定。“占田逾侈”[20](汉)荀悦撰《汉纪》卷八孝文皇帝纪下(《两汉纪》,上册第114页)。占田,亦是当时的习用语,如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肩水金关汉简(肆)》载:“神爵二年十二月壬申朔,辛卯,东乡啬夫生敢言之:昌乐里韩忠自言以令占田居延,与子女婢温、小男。”(73EJT37:871,中西书局2015年版,下册第75页)。占田居延,即是在居延占有耕种土地。的格局,农民生活环境日益恶化。汉武帝在前辈积累的丰富物质基础上,外事四夷,开疆拓土,增设郡县;内兴更化,制礼作乐,大事土木,激化了社会矛盾,土地兼并更为严重,形成了两汉第一次土地兼并的高潮,社会蕴藏着动荡不安的因素,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在这种大背景下,董仲舒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主动地分析思考,向汉武帝上书指出了土地兼并的根源、危害和抑制兼并的办法——“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的思想,以维护汉家统治的长治久安。
二、董仲舒限田思想的初步分析
董仲舒的限田思想,是以董仲舒上书汉武帝请限民名田建议的形式问世的,立足于现实,贯古通今,内容丰富,论述深刻,笔者稍作辨证分析。
(一)董仲舒请限民田上书的时间
《汉书·食货志上》说:“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董仲舒说上曰。” “是后”叙述了大背景,没有明确记载上书的年月时间,留下了后人见仁见智的空间。东汉荀悦的《汉纪》系于元狩四年(前119年)春,言:“是时,董仲舒说上曰。”[13]219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为“初,董仲舒说武帝”[21]系于绥和二年(前7年)师丹建言限田限奴议之前。宋代王益之的《西汉年纪》也将董仲舒上书的时间,排列在元狩四年[22]。宋朝吕祖谦的《大事记》将董仲舒请限民田,系于元狩五年三月[21](宋)吕祖谦撰《大事记》卷一二元狩五年载:三月“董仲舒请限民田,不从”(《吕祖谦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册第166页)。这是系年中较为具体细密的一个。吕祖谦撰《大事记解题》卷一二元狩五年除记载“董仲舒请限民田,不从”外,还说明了系于元狩五年的理由(《吕祖谦全集》,第8册第818-819页)。。明代王锡爵辑《历代名臣奏疏》标为“汉武帝建元元年”[23]。清朝张英、王士祯等撰《渊鉴类函》则曰:“孝武即位,董仲舒说上曰。”[24]“汉武帝建元元年”虽然具体,但与董仲舒建议所言“盐铁皆归于民”不符,因为当时尚未实行盐铁官营,提出如此建议,有些无的放矢。“孝武即位”比较笼统,也有些为时尚早的瑕疵。
《汉书》的《武帝纪》载:元狩三年,“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食货志上》载:董仲舒言:“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两者相同之处在于“种宿麦”,《武帝纪》记载的是皇帝派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食货志上》记述的是董仲舒建议皇帝下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地点不同、执行机构不同。究竟是汉武帝听取了董仲舒建议,还是董仲舒受皇帝派遣谒者督促种宿麦的启发,不好判断,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两者时间相距不会太远。
元狩三年(前120年)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时间坐标,董仲舒请限民名田的建议当在其后。元狩三年,“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7]1428。元狩四年,大农上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书,言盐铁官营之策,朝廷“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7]1429。推行盐铁官营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董仲舒言“盐铁皆归于民”才有了针对性。仔细推敲《汉纪》《大事记》《西汉年纪》把董仲舒请限民名田的建议置于元狩四年或元狩五年,都是根据《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的记载,都是以盐铁官营作为确定年代的依据,差别在于是元狩三年还是元狩四年,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其实这只是说具备了董仲舒上书所言内容的客观条件,究竟董仲舒何时上书史无明文记载,我们只能说元狩四年、五年及以后可能性比较大,不一定就是在元狩四年或元狩五年。
(二)董仲舒请限民田上书的内容
董仲舒限田思想的内容包含在上汉武帝疏中,董仲舒曰:“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22]《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37页)。董仲舒的上书,后人收录到多种著述中,拟定了不同的篇名。如:(宋)真德秀编《文章正宗》卷九作《董仲舒论限民名田》,(宋)陈仁子辑《文选补遗》卷五作《论限民名田》,(明)吴国伦校《秦汉书疏·西汉书疏》卷二作《论限民田》,(明)梅鼎祚编《西汉文纪》卷八作《又言限民田》,(明)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卷三作《乞种麦限田章》,(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二四命名为《又言限民名田》,(民国)吴增祺编《涵芬楼古今文钞简编》卷一一作《限民名田奏》。各书所拟定的篇名,并不完全相同,但都明确标出了限田的关键词语。董仲舒立足于现实,反思历史,指出了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描绘了社会严重危机的状况,提出了盐铁皆归于民、薄赋敛、省繇役等一系列的建议,尤其是提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的办法——“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是具有创造性的思想。
(三)董仲舒的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卖买”说法不准确
董仲舒论述了土地兼并的根源,“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废除井田制,民得买卖土地,是土地兼并的根源所在。董仲舒看得透彻,抓得准确,论述得简明清楚,思想具有创造性。但从时间角度来看,董仲舒说法似乎不准确。
首先,董仲舒所言“除井田,民得卖买”,并不反映秦国土地制度的实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看不到土地买卖的法律与记载,有“入顷刍稁,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稁二石”[25]21的记载,说的是“受田之数”,受田又作“授田”,是说国家把土地分授给农民耕种,农民给国家拿赋税、服劳役。战国秦魏齐等国实行授田制情况,前面有所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其次,有些秦国晚期或秦始皇时代的秦简记载了秦人的家庭情况。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乡某封守爰书记载了奉县丞文书查封某里士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服、畜产的情况,连“牡犬一”[25]149也未遗漏。湖南里耶古城护城壕发现的秦代户籍简牍记载了户主的籍贯、爵位、姓名,以及户主的兄弟、妻妾、儿子、女儿与奴婢的情况[2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发掘报告》第二章《里耶古城遗址》记录了二十余户的户籍,其中完整者有:“南阳户人荆不更蛮强 妻曰嗛 子小尚早□ 子小女驼 臣曰聚 伍长。”“南阳户人荆不更黄□ 子不更昌 妻曰不实 子小上造悍子小上造 子小女规 子小女移。”等(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203-210页)。可见秦国户籍著录的项目,可以由此了解家庭成员的情况。。也就是说目前所发现的记载秦人家庭情况的秦简中没有关于土地方面的记载。居延汉简中记载的隧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家有宅、妻、子、男同产、女同产、用牛,“田五十亩直五千”[26]34;候长觻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家有宅、小奴、大婢、用马、服牛、牛车、轺车,“田五顷五万”[26]61。汉简中专门记载了土地的情况。上述秦汉简牍资料相互比较,家庭成员、奴婢、畜产等项目是相同的,也有明显区别,睡虎地秦墓竹简和里耶秦简的文书中都曾未涉及到土地,而居延汉简准确地标明了土地的数量与价值,这说明秦国土地尚归国家所有,尚未计算在家产范围之内。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日书》中有买卖臣妾、人民(奴隶)、畜生(马牛)、货财(财物)的记载[24]《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买卖臣妾、畜生、财货不吉利的忌日和吉利的良日等记载。如《日书甲种》载:“毋以午出入臣妾、马【牛】,是胃(谓)并亡。”“毋以申出入臣妾、马牛、货材(财),是胃(谓)□□□”(第197页)。这里说的是忌日。出为卖,入为买。出入,指卖出与买进,也就是买卖,这里所买卖者有臣妾、马牛、财货。《日书乙种》载:“作阴之日,利以入(纳)室,必入资货。”(第231页)又载:“窞日,可以入马牛、臣【妾】。敫日,可以入臣妾,驾驹。”(第233页)这里说的是吉日。入,即可以买进;又有敫日,“出入人民、畜生”、阴日,“入货、人民、畜生;……出入人民、畜生”(第234页)。人民,指奴婢。这里也是说在吉日可以买卖奴隶、畜生等。壬寅等日,“不可以入臣妾及寄者,有咎主”(第241页),不可以买入奴婢。上述史料证明奴隶、畜生、货财是可以买卖的。,说明当时存在着奴隶、财物等买卖,但没有买卖土地的记录,这也证明秦国晚期或秦始皇时代土地尚未随便买卖,那么在此一百年之前的商鞅时代,就会“除井田,民得卖买”吗?
其三,战国两汉人说到商鞅变法,多不言“除井田,民得卖买”,而言决裂或开阡陌。如后为秦国丞相的蔡泽曰:“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27]216蔡泽说的是“决裂阡陌”。《史记》的《秦本纪》载:秦孝公十二年,“为田开阡陌”。《索隐》引《风俗通》曰:“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河东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2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考。”(第290页)(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卷五《秦始皇本纪》曰:“此乃孝公十二年事,而以为昭襄四年,误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6页)梁玉绳所言为是。《六国年表》载:秦孝公十二年,“为田开阡陌”。《商君列传》载:“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正义》曰:“封,聚土也;疆,界也:谓界上封记也。”《史记》记述的这几条史料都说到了“为田开阡陌”的事情。《汉书》的《食货志上》载:“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仟伯,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颜师古注曰:“仟伯,田间之道也。南北曰仟,东西曰伯。”《地理志下》载:“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伯,东雄诸侯。”《汉书》说的是开仟伯(即阡陌),即破除原来的阡陌封疆,重新规划农田道路、地界等,建立新的阡陌封疆。上述所引用的《战国策》《史记》《汉书》等都说到了商鞅变法决裂或开阡陌(仟伯),而不涉及到“除井田,民得卖买”,这不是偶然的。
除了秦简中不记载土地买卖外,近些年来出土的简牍提供了一些秦国整理规划农田道路的新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可以深化对于秦国阡陌封疆制度的了解。
如青川木牍记载,“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日,王命丞相戊(茂)、内史匽,□□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捋(埒),正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28]这是秦武王二年(前309年)颁布的农田阡陌、疆畔规制的法律,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畛、阡道、陌道、疆畔的规格、形制等情况,了解每年整修阡陌封疆的时间。所谓“修封捋(埒)”的“封”,“封,起土界也”[29]692,“封者,聚土之名也”[4]281。封,也就是指用土筑造的田间地界。秦国的农田阡陌、疆畔制度后来变为秦朝制度,并被汉朝所继承沿用[26]《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二年律令·田律》载:“田广一步,袤二百卌步,为畛,亩二畛,一佰(陌)道;百亩为顷,十顷一千(阡)道,道广二丈。恒以秋七月除千(阡)佰(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陂)堤,利浸梁。虽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第42页)此简与秦青川木牍相互比较,两者有同有异,相同者是汉承秦制的具体例证,但已经有些变化,标志着秦汉阡陌制度的不同。。
又如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盗徙封,赎耐。’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佰。顷半(畔)‘封’殹(也),且非是?而盗徒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25]108封,是田间阡陌,即是地界。盗徙封,指私自移动地界,是要受到赎耐惩罚的。
上述三种简牍资料都有与秦国阡陌封疆制度相关的法令,证明了秦国存在着阡陌封疆的现实和有些人破坏阡陌封疆的行为,说明了政府对于维护阡陌封疆制度的重视,法令明确规定对于破坏阡陌封疆者要予以惩罚。
封疆,又称为疆畔[27]徐元诰撰《国语集解》卷一《周语上·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载:“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镈,不解于时,财用不乏,民用和同。”韦昭注曰:“疆,境也。畔,界也。”(第21页)疆畔,此处指田界。、疆埸[28]《诗经今注·小雅·信南山》载:“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注:“疆埸,田界也。”(第325、326页)《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载:“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颜师古注曰:“《诗·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庐,疆埸有瓜’,即谓此也。”(第1120-1121页)《文选》卷三张平子《东京赋》曰:“兆民劝于疆埸,感懋力以耘耔。”薛综注曰:“兆民,谓百姓也。疆,田畔也。”(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0页)疆埸,此处指田界、田边。、顷畔、田畔[29]《汉书》卷八九《循吏传·召信臣》:“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第3642页)《说文解字注》十三篇下《田部》载:“畔,田界也。”段玉裁注:“田界者,田之竟处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96页)田畔,指田界。、地约[30]《周礼正义》卷六八《秋官·司约》载:“治地之约次之。”郑玄注曰:“地约,谓经界所至,田莱之比也。”孙诒让引惠士奇云:“地约者,封人所封之四疆,量人所量之涂数,形方所正之华离,遂人所造之形体,匠人所画之沟洫,皆是也。”(第2845、2847页)地约,指土地的疆域界线。、封洫[31]《春秋左传注》襄公三十年载:“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注曰:“封,田界。洫,水沟。”(第1181页)《吕氏春秋校释》卷一六《乐成》载:“子产始治郑,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高诱注曰:“封,界;洫,沟也。”(第989、994页)封洫,指田界。等,后人又称为地界、田界、田陌、疆畛[32]《新唐书》卷一四五《元载传》载:“膏腴别墅,疆畛相望,且数十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13页)疆畛,指地界、界限。、疆陇[33](唐)杜牧著《樊川文集》卷一三《上池州李使君书》载:“然与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齐立,亦抵足下疆陇畦畔间耳。”(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1页)(宋)曾巩撰《曾巩集》卷三九《太平州祈晴文》:“水之既去,民于完堤防、修疆陇,以从事于田,其艰且劳亦甚矣。”(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7页)疆陇,指田界。、地边等。这些丰富多彩的关于封疆、田界的词语,有些是先秦人创造的,有些是后人沿袭使用的,也有些是后人命名的。这些关于田界的词语与新发现的秦、汉初有关阡陌封疆的法令,说明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重视阡陌封疆,以便于授田制的实行与管理。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才能够按照国家的法令规定来实施修理阡陌封疆。到后世土地国有、私有、集体共有等多种所有制并存,土地经营单位日益分散,土地无限细碎化,不可能再修建整齐划一的阡陌封疆,而出现了绘制土地分布状若鱼鳞的鱼鳞图册,国家还会做这些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吗?后来土地国有、私有、集体共有等并存,也不会再有如此整齐统一的田界。这正说明当时土地“民得卖买”不存在。不独秦国如此,齐国亦有类似的措施[34]黎翔凤撰《管子校注》卷一《乘马》载:“三岁修封,五岁修界,十岁更制,经正也。”(第90页)卷一四《四时》载:“四政曰:端险阻,修封疆,正千(阡)伯(陌)。”(第843页)定时修理封疆,齐国规定与秦国有些类似,这当是战国时代的特色。。同时,地邻相互之间对于田界的纠纷争夺历代都有,《周礼》载:“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汉代郑玄注:“地讼,争疆界者。”唐朝贾公彦疏:“谓民于疆界之上横相侵削者也。”[31]这是汉唐人对于地讼以当时的语言进行了解释。直至当代因为地界发生的纠纷、诉讼等还是习以为常。还有,古代国家授田有阡陌封疆,私有土地也会有田界,占田、均田等都有地边,历代耕种的土地都会有田界、地边,只是重视程度相异,规模大小不一,名词说法不同而已。开阡陌封疆,并不直接涉及土地的“民得卖买”问题,与土地兼并没有直接的联系[35]有些人认为开阡陌封疆导致了土地兼并,如(宋)廖行之撰《省斋集》卷四《田制论》认为:“自秦开阡陌,坏井田,于是兼并纵横而贫富相绝,上无制民产之法,而趋末者益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7册第327页)。(宋)孙梦观撰《雪窗集》卷二《董仲舒乞限民名田》言:“三代之民,所以无甚富甚贫者,以井田之法在也。自秦变为阡陌,而兼并之祸起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97页)(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田赋一》引吴氏语曰:“井田受之于公,毋得粥卖,故《王制》曰:田里不粥。秦开阡陌,遂得买卖。又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亩为畔,无复限制矣。”(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页)卷二《田赋考·田赋二》说:“盖自秦开阡陌之后,田即为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贵者可得之。富者有赀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属役于富贵者也。”(第43页)诸如此类的说法很多,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说法,在于把开阡陌封疆与土地民得买卖联在一起了。其实,这是有联系而不完全相同的两回事。。因此,董仲舒说“除井田,民得卖买”,而不说“开阡陌封疆,民得卖买”。土地“民得卖买”是说土地所有权转移的方式,由国家授田转为土地买卖,与开阡陌封疆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而与土地私有、土地兼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其四,有关于战国土地买卖的资料,经常说到的有赵中牟令“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32]。这里放弃的是田耘,出卖的是宅圃,从侧面说明土地不能随便买卖[36]对于此问题,传世文献能够提供例证,从现代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农民承包土地,不愿意耕种时出现的抛荒地、撂荒地事实中也可以获得启发。如果土地能够买卖,又不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扔下土地不管而变为抛荒地呢?是因为不能够随便卖卖,自己不耕种,又不愿出租或委托他人代耕,只好抛荒。。战国百姓生活困苦时,解燃眉之急的办法多说是“鬻子”[37]《管子校注》卷五《八观》载:“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鬻子矣。”(第261页)卷二三《揆度》言:“轻重不调,无之民不可责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国之数也。”(第1388页)卷二三《轻重甲》曰:“今君铸钱立币,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数,然而民有卖子者何也?财有所并也。”(第1432页)《韩非子新校注》卷一八《六反》言:“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第1011页)。上述史料可见战国时代卖子的情况,而不言卖田地。,不说出卖田地。如果有子女与土地可卖,一般应当是先卖土地,后卖子女,从侧面说明土地还不能买卖。汉文帝时,晁错曰:“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1]1132已经是卖田宅优先于鬻子孙,标志着土地可以买卖了。战国时代说到卖地的还有:韩国上党太守冯亭曰:“是吾处三不义也:为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与人,不义一也;主内之秦,不顺主命,不义二也;卖主之地而食之,不义三也。”[27]619-620此处“卖主之地”,既反映当时有了卖地的观念,又说明冯亭所谓“卖主之地”,是指出卖国君之地,并不是民间的土地买卖。赵国将军赵括以“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7]2447。这是汉朝人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赵国土地买卖的资料,是否可靠尚需考索,即使可靠,这也是两个不同国度和时间的问题,是赵国土地买卖的资料,而不是秦国的土地买卖的资料;还有商鞅变法的年代与赵国赵括生活的岁月,前后相差一百余年,也不能够证明“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的问题。
由上述可见,董仲舒所说的“除井田,民得卖买”并不符合商鞅变法的实际,而后人以讹传讹,认为土地买卖从商鞅开始是一个不确切的看法。之所以如此,因为董仲舒是思想家,不是历史学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是董仲舒为论证“限民名田”的合理性而制造的一个证据,既与西汉过秦的思潮吻合,也与西汉人对于秦国土地制度的认识吻合[38]《汉书》卷六七《梅福传》载:“秦为亡道,削仲尼之迹,灭周公之轨,坏井田,除五等,礼废乐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第2918页)其中的“坏井田”与董仲舒的“除井田”,看法相吻合,也是汉代人立足于现实,追溯历史的言论。,还给限民名田主张提供了历史的证据,也规避了政治风险,这是战国西汉诸子说明自己主张的惯用手法。王充指出:“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33]167“盖言语之次,空生虚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常之加。”[33]190王充所言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如韩非言:“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周勋初指出:“武王让以天下:周武王把天子位置让给伯夷、叔齐。史实不详。”[34]太田方曰:“周武王让天下事,传记所未见,盖战国辩士之言耳。”[35]这是韩非为论证自己的说法而编造了一个周武王让天下的故事。再如《庄子·杂篇·说剑》所说的赵文王喜爱剑的故事,文章本非庄周所撰写,赵文王、太子悝似乎为虚构人物,赵文王喜爱剑当为寓言故事,怎能够用来证明赵国历史问题?董仲舒也曾经说:“昔者鲁君问柳下惠曰:‘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之也,谋伐国者,不问于仁人也,此何为至于我?’”[36]267这件事似乎也不存在[37]。董仲舒所言“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沿袭战国诸子所习用的方法,也具有汉代人思维的特色,因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闇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38]。为了减少阻力,达到说服别人的目的,因此有托古的必要。再则,理论论证需要有证据,尤其是历史上的证据,更有说服力,没有只好编造。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中,把自己对未来的憧憬、想象投射在他们所描述的古代事实中,有些所谓古代的事实,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政治主张与理想,是他们思想主张的注脚,是为了论述的需要编造出来的故事,并非都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董仲舒所言的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卖买”亦可如此看。
(四)董仲舒限田思想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39]37。虽然董仲舒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是不确切的,其实这是董仲舒的一贯做法,如天人三策曾言:“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1]2510-2511从开头语到句式,以及其思路、精神都很一致,这是在汉代君主专制条件下,批评时政的一般做法,从过秦开始,经针砭现实,到提出自己的主张结束,过秦是引用亡秦的历史借鉴,而重点在于评论现实、完善制度。因此,说董仲舒对于秦国土地制度说得不准确情有可原,但如果说是董仲舒所处时代土地兼并情况的描述倒是十分准确的,对于土地兼并的原因归为“除井田,民得卖买”,即土地国有制转化为多种所有制并存,获得土地的途径由授田制、土地买卖等转变为以土地买卖为主,找到了转折点。有土地私有制度,就会有土地买卖,就会有土地兼并,比起晁错所说商人兼并农人,更深刻地揭示出了土地买卖背后的奥秘。“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39]44。土地私有、土地买卖、土地兼并,三者形影相随,董仲舒揭示出的这一点,是西汉社会土地兼并存在的现实反映,的确是了不起的形而上的抽象升华,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话题,是一个卓越的历史贡献。因为从西汉直至民国,土地国有、私有与集体共有等多种所有制并存,土地买卖与土地兼并始终相伴随,贫富两极分化总是存在,从而成为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所以,两千余年来,众多学者、政客们成百上千次地评价、探讨董仲舒所提出的限田话题,提出了无数的解决方案——理论的论证、学术的探讨、现实的对策、法律的规定等,进行了多次的尝试,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而这一切的起点就在于董仲舒的限田思想。
虽然说董仲舒论述土地买卖的时间起点不准确,但对于现实问题的论述,说得很确切。“汉兴,循而未改”,说明他是借着批判亡秦暴政的题目,而作批判汉代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可见董仲舒批评的重点所在。作为思想家,他尖锐地指出了土地兼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现实,生动地描绘了豪强地主的势力——“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诉说了贫民生活的艰难——“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具体地指出政府横征暴敛的残酷程度——“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当然这不仅仅是政府的专横,也是生产方式变化,耕作技术进步的结果。尤其是“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39]《吕氏春秋校释》卷一九《为欲》载:“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夫无欲者,其视为天子也与为舆隶同,其视有天下也与无立锥之地同。”“无立锥之地至贫也。”(第1293页)古人用“无立锥之地”形容其困难艰苦。如《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载郦生言:“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第2040页)《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载:淮南王言:“陈胜、吴广无立锥之地,千人之聚,起于大泽,奋臂大呼而天下响应,西至于戏而兵百二十万”(第3090页)。《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优孟》载:楚国令尹公孙敖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第3201页)。无立锥之地,也是具有特色的秦汉语言,董仲舒运用得恰到好处,又影响了后世。的名言,虽然具有夸张的色彩,但形象生动地道出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状况,说明了土地兼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董仲舒是思想家,是儒学大师,并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统计学家,他在这里没有细致地统计当时全国土地的总数量,没有详细说明富者、贫者各自占有多少土地,也没有准确计算自耕农与地主占有土地的数量比例,而是高度概括地描述了土地兼并所造成的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因土地兼并始终存在于两汉以来的古代社会中,所以后人往往借用这句名言说明贫富分化的情况,有些人还套用董仲舒这句名言的格式,创造了诸如:汉代郑玄“富者贵美且多,贫者贱薄且少”[29]964;刘宋“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40];北魏“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41];北齐“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42];唐代“富者得以专其利,贫者不能专其业”[43],“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44];宋朝“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富者益以多畜,贫者无能自存”[45],“富者跨州县而莫之止,贫者流离饿殍而莫之恤”[46];明朝“大户田连阡陌,小民无立锥之地”[47];清代“今富民至有田数万,而贫民无寸土可耕”[48]等,从诸如此类的言论中,可见董仲舒对土地两极分化的分析、描述,为后人所认同、所发挥,由此可知历代都存在着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现象。
董仲舒以其为人廉直的性格,对于现实问题关心的态度,论证了由于豪强兼并自耕农的土地,以“见税十五”的比例剥削佃农,再加上国家垄断山林川泽之利,杜绝了人民谋生之路,还有国家沉重的赋税徭役,致使处于极端贫穷境地的贫民,被迫“亡逃山林,转为盗贼”,以求生存,以反抗剥削掠夺。这样就形成为严重的社会向题,不仅直接影响赋税征收、财政收入和徭役调发,而且严重地威胁汉皇朝的统治。如何解决这种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董仲舒想到了历史上的井田制度,可以作为遏止土地兼并、化解贫富分化的理想措施。他又清醒地看到在土地私有、土地买卖的社会条件下,造成的“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7]1420的状况,绝非一旦就可以改变“法无限,则庶人田侯田,处侯宅,食侯食,服侯服,人亦多不足矣”[49]的现实,地主、自耕农世代拥有自己的田宅,是其安身立命基础所在,与其生命息息相关,土地私有观念根深蒂固,人多势众,难以轻易夺取,恢复古井田不是马上就能办到的,因而应当有所变通[40]对于井田制当以《孟子》论述得最为详细,但那是为滕国提供的设想,被后人作为解决土地兼并的法宝来用,古代是否实行过井田制,争论了多年。如着眼于国家土地所有制,在占田制、均田制中曾经多少得到过落实。董仲舒主张“宜少近古”,是指合乎井田制精神但不必恢复井田制,借用井田制的名声,来宣传自己的限田主张。。所以,他认为“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建议“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董仲舒的“限民名田”的“限”字,说的是限制、限量等,也就是政府应当规定每户占有土地的限额。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的关内侯九十五顷到公卒、士伍、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也就是晁错所说的“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7]1132。即《二年律令·户律》规定的公卒、士伍、庶人授田额度,这是平民百姓占有土地的基本额度,其他等级的家庭也有着不同的数量规定,超过其相应的数量规定就是“田宅逾制”。实际上,并非所有平民百姓每一户都能够达到百亩规定的额度,按照《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土地、户数计算,平均每户占有土地六十七点六亩强,根本达不到平均每户百亩的规定[41]《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载:“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第1640页)据此计算,平均每户占有土地六十七点六亩强,平均每人占有土地十三点八亩强。。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郑里廪籍》记载了二十五户农民,能种田者六十九人,人口一百零五人上下,田地六百一十七亩,平均每户占有土地二十四亩七分弱,每个能种田者合九亩弱,每个人合六亩弱[50]141。大大小于根据《汉书·地理志》计算出来的全国平均数字,当是这些户属于贫民所致。最少的一户,“户人圣,能田一人,口一人,田八亩”[50]106。最多的一户,“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田五十四亩”[50]108-109。而贵族官僚、商贾豪强大大超过限额也是司空见惯的,汉宣帝时,阴子方“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20]1133。汉成帝时,丞相张禹,“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1]3349。汉哀帝一次赏赐给宠臣董贤二千顷土地。贫富两者占有土地数量相比,悬殊可见。是“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因而导致“百姓失职,重困不足”[1]336。西汉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土地额度规定,汉哀帝时代规定的“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那是最高限额。王莽改制规定的“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也属于最高限额。从政府法律规定来看,西汉应当是一个限制土地占有数量的时代。从实际情况来看,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土地兼并高潮的时代。正是法律规定与现实存在的巨大反差,成为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建议的社会基础。
(五)限民名田即限民占田
董仲舒的“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荀悦记述为“限民占田,塞兼并之路”[13]220,又说:“孝武时,董仲舒尝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时,乃限民占田不得过三十顷。”[13]114荀悦把“名田”写为“占田”;颜师古注亦曰:“名田,占田也。各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则贫弱之家可足也。”[1]1138可见在荀悦和颜师古看来“名田”与“占田”是相通的。那么,汉代名田与占田有何区别联系呢?
首先说说名田。汉武帝时代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索隐》曰:“谓贾人有市籍,不许以名占田也。”[7]1430-1431《汉书》作:“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颜师古注曰:“一人有市籍,则身及家内皆不得有田也。”[1]1167两者所说同一件事,表述不同,但都有“名田”二字,解释有区别,司马贞解释为“不许以名占田”,这个“名”应当是户籍名。颜师古注释为“不得有田”。可知占田与有田相同,名田即是占有田地。绥和二年六月,限田限奴议中规定:“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如淳注曰:“名田国中者,自其所食国中也,既收其租税,又自得有私田三十顷。名田县道者,令甲,诸侯在国,名田他县,罚金二两。今列侯有不之国者,虽遥食其国租税,复自得田于他县道,公主亦如之,不得过三十顷。”又规定:“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1]336-337如淳对于“名田”的注释是“自得有私田”。综合上述两例,可知名田是自得占有的田地。
其次说说占田。荀悦认为:汉代“豪强富人,占田逾侈”,“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13]114。汉哀帝时,规定“王侯已下至庶人占田不得过三十顷,贾人不得占田,过科没入县官”[13]487。这里的“占田”,《汉书》作“名田”。从上述例证看,名田,即占田,也就是私人占有土地。
由此可知,董仲舒所说的限民名田,与商鞅变法的“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7]2230和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的“及为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边二岁,没入田宅县官,能先告,除其罪,有(又)畀之所名田宅”,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无论是商鞅变法的“各以差次名田宅”,还是《二年律令》的“名田宅”,都是国家把田宅授予黎民百姓,而董仲舒所说的“限民名田”则是在私人占有土地的基础上,限制其占有的数量,要保持一个适当的限度,从而使农民拥有自己的一块土地,以遏制土地兼并的趋势,使“强奄弱,众暴寡,富使贫,并兼无已”[36]107的情况有所缓和,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
当然,作为儒学大师的董仲舒,在论述限田时难免有不严密之处。如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土地私有和买卖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而来,但董仲舒归结为“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时间不准确,有失片面,并误导了后人对于土地买卖的认识,至今仍然在以讹传讹。同时,董仲舒没有具体说明井田制难以实行的原因,对限田,只是原则主张,而没有具体的限田数量标准、措施,失之于笼统。这些既是不足,也是由董仲舒的社会角色所决定的,作为思想家、儒学大师他所能做的就是观察社会现象,剖析问题结症,升华其认识,提出建议。不可能由他来做出决策,不会由他来制定法律条文,更不会由他来推动实施,因而原则性的话说得多,可操作性比较差。再则,限田作为抑制土地兼并的创造性思想,首先系统论述抑制土地兼并问题,创始者难以做得尽善尽美,我们不能苛求董仲舒一提出问题就论述得完美无缺,解决思路就设想得天衣无缝,那是不现实的。
(六)限田与调均思想关系
董仲舒限田思想的基础,在于孔子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51]的思想,这里的“均”,并非平均如一而是说差别不要太大,避免贫富两极分化,以保持社会安定。董仲舒继承、发挥了孔子思想,提出了“调均”的概念。“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36]230,把官僚贵族不得与民争利业,提高到天理的高度。“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36]227。因此,要采取措施,以限制贫富两极分化。主张“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36]228。也就是对富者限制其兼并,生活得不要太骄奢;对贫者搜刮不要太重,日子过得不要太窘迫,把贫富差别限定在适当的范围之内,使利益均布,天下太平。这个限度的界限,董仲舒并没有具体画定。但这个限度的确是历代圣明的统治者都注意的问题——如何使贫苦百姓既不会因生活贫困窘迫而揭竿造反,又不会使贵族官僚、豪强地主因生活富裕而生奢侈邪恶,让社会简单再生产能够平安顺利地继续下去,使“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5]12,让社会各阶层的人认同礼制,各有其位,各安其位,以维护社会的和谐——一般情况下,就是要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让贫富两极和中间一般保持在两头小、中间大的正态曲线分布之中。
正是基于调均的思想基础,董仲舒提出了限田思想,反对“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的人,“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他们“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而没有限度,就会使“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所以造成“奸邪不可胜者也”[1]2520-2521,也就是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揭竿而起反抗残暴的统治。
董仲舒为神圣其调均思想,汲取前贤的“利不兼,赏不倍”[52]的思想,把调均与天理、天意联系起来。他指出:“天不重与,有角不得有上齿。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夫己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况人乎?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36]229-230固然,其中充满阴阳五行思想的色彩,难免带有牵强附会之意,但从西汉时阴阳五行、天命灾异学说流行的社会现实出发,就不难体会董仲舒为调均思想披上天数、天理等神圣光环的良苦用心。
调均思想是董仲舒对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思想的发挥,是限田的理论基础,限田是调均思想的具体体现,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得益彰。这种思想为后人所继续阐释。郑玄曰:“玄之闻也,《周礼》制税法,轻近而重远者,为民城道沟渠之役,近者劳远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养者多,与之美田;所养者少,则与之薄田。其调均之而足,故可以为常法。”[29]964用调均思想来解释《周礼》制度。
董仲舒对土地买卖、土地兼并现象的描述,对其本质的概括,从西汉到民国二千余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两汉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时,董仲舒提出限田的建议,以求土地与劳动力有较为合适地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土地兼并是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的必然结果,与二千余年的古代中国长期相伴,不是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适当地予以调整限制,总比任其放任自流、不抑制兼并,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更有利于统治的巩固,更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正因为如此,董仲舒的限田思想对历代抑制土地兼并的理论研究和国家授田政策的制定等,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董仲舒与儒学论丛[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292-311.
[3] 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284.
[5] 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357.
[6] 庞怀清.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窑穴发掘简报[J].文物,1976(5):26-44.
[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8] 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战国类型国家授田制的崩溃——“使黔首自实田”新解[M].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41-344.
[9]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10] 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84.
[11] 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1001.
[12] 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177.
[13] 荀悦.前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 2002.
[14] 曾巩.隆平集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2:231.
[15] 李觏.李觏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191.
[16]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1986:88.
[17] 张英.文端集[G]//永瑢,纪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08.
[18] 袁采.袁氏世范[M].贺恒祯,杨柳,注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162.
[19] 刘珍.东观汉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529.
[20]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5.
[21]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1059.
[22] 王益之.西汉年纪[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267-268.
[23] 王锡爵.历代名臣奏疏[G]//《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46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39.
[24] 张英,王士祯.渊鉴类函[G]//纪昀,于敏中.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290册.台北:世界书局,1988:40.
[25]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26]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27] 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8] 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报告[M].文物, 1982(1):11.
[29] 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3:692.
[30] 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岗秦简·释文注释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 2001:111.
[31] 郑玄.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713.
[32] 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698.
[33] 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4] 周勋初.韩非子校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112.
[35] 张觉.韩非子校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73.
[36]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7] 秦进才.“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探析[G]//葛荃.反思中的思想世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331.
[38]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653.
[39] 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0]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37.
[41]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6.
[42]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27.
[43] 章如愚.群书考索[G]//永瑢,纪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93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865.
[44] 陆贽.陆贽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6:768.
[4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621.
[46] 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453.
[47] 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9:216.
[48] 郭起元.介石堂古文[G]//《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2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119.
[49] 汪荣宝.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308.
[5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西汉简[M].北京:中华书局, 2012.
[51] 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649.
[52] 裘锡圭.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2014:180.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An Exploration of Dong Zhongshu’s Idea of Limiting the Amount of Private Land
QIN Jinca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Land annexation and limitation of the amount of private land to control the land annexation have been the important social phenomenon since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Dong Zhongshu’s idea of limiting the amount of private land, holding that his idea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society in which land annexation exists, that he creatively reveals the secret of the close relationship among land privatization, land sales and land annexation, and that his idea of limiting the amount of private land to give the extra land to those whose land is insufficient so as to control land annexation has set a precedent for ancient Chinese ideas of limiting the amount of private land.
Dong Zhongshu; idea of limiting the amount of private land; land
10.3969/j.issn.1673-2065.2017.02.002
秦进才(1953-),男,河北衡水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衡水学院特聘教授。
B234.5
A
1673-2065(2017)02-0017-18
2015-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