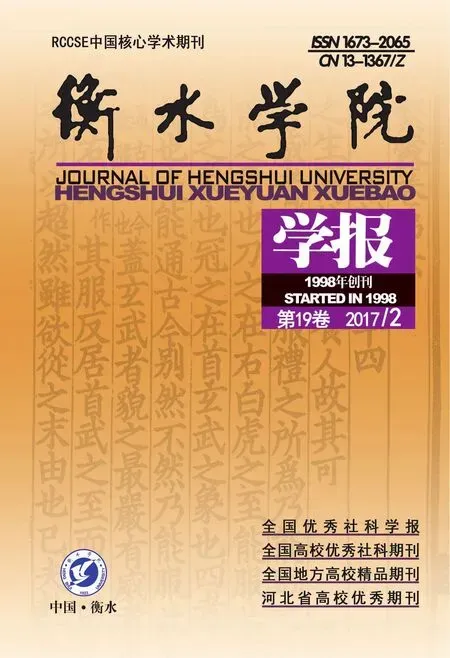“德主刑辅”说之驳正:董仲舒德刑关系思想新诠
李德嘉
“德主刑辅”说之驳正:董仲舒德刑关系思想新诠
李德嘉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872)
“德主刑辅”是现代学界对古代儒家德刑关系思想的概括与总结,这一思想往往被认为是源自于东汉大儒董仲舒。然而,“德主刑辅”说并不能准确概括董仲舒的德刑关系思想。董仲舒针对汉初因袭秦朝“刑治”所带来的弊政,提出了“任德不任刑”的政治法律主张。董仲舒提出“任德不任刑”的主张是在社会管理模式的层面要求施行儒家的“德治”,德与刑的关系是本与用,而非主与辅。自汉武帝复古更化之后,儒家“德礼为本、政刑为用”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并且深刻影响了大一统时期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
董仲舒;德刑关系;德主刑辅;德治
学界普遍认为,“德主刑辅”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特征,其理论缔造者是东汉大儒董仲舒。然而,“德主刑辅”一词却并非古人的原话,董仲舒对此最为接近的表述是“刑者,德之辅也”。可见,“德主刑辅”的概念其实是现代学者对古代儒家德刑关系思想作出的总结。其实,董仲舒所主张的德刑关系并不是在刑事政策的层面讨论德教与刑罚在社会统治上的作用孰轻孰重,或以“任德不任刑”加以概括更为确切。所谓“任德不任刑”思想则是针对当时政治中的“刑治”思想,彻底清算暴秦所遗留下来的弊政,要求汉武帝恢复儒家“德治”之传统。在董仲舒看来,任德的首要内容是正君,对统治者树立政治正当性的观念和准则,只有先树立君德、官德,然后才能使百姓有德。而最终才是以德教治理天下,对百姓施教。同时,董仲舒还指出对百姓施教的前提是将百姓视作有理性、有仁心的具有人格的主体来对待,施教不能急于求成、扭曲人性,应该成全人性。
一、以“德主刑辅”说概括董仲舒德刑关系思想的不足
学术界首先在教科书中将儒家德刑关系思想总结为“德主刑辅”说的学者,是法律思想史学科体系的奠基者杨鸿烈。杨鸿烈在《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第四章“儒家独霸时代”中专门列了一节来讨论中国古代的“德主刑辅”思想。杨鸿烈对“德主刑辅”说的解读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从治理方式来看,“德主刑辅”是儒家德治思想的重要组成,主要是以“德化”或是“德教”的方式管理社会,而不是以法律的规范来统治社会;而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德主刑辅”意味着道德和法律的混同,法律的目的在于实现道德,而道德则是更重要的法律。杨鸿烈所提出的“德主刑辅”说现在已经成为学界“定论”。所谓“德主刑辅”实际就是推行依靠统治者自律的德政,对百姓以道德教化为主的统治策略。这样的“德主刑辅”说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治国”论,要么寄托于统治者道德的自律,要么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这样的“德主刑辅”说实际上很难解释为什么奉行“德主刑辅”思想的古代中国会有如此发达的律令体系。有学者在质疑法律史研究中的某些“定论”时指出:“当‘中国法律思想史’教科书将‘德主刑辅’作为中华法系主导思想时,‘中国法制史’的教科书却把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主线定位在‘以刑为主’‘重刑轻民’上。”[1]目前学界主流的“德主刑辅”说实际上误读了古代儒家的“德”观念和德刑关系思想。古代儒家的“德”并非今人所谓的道德,这一点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然而,一些学者关于“德主刑辅”说的解读却依然停留在道德与法律的相互作用关系上。
欲对近现代学者所提出的“德主刑辅”说进行去伪存真的驳正,必须首先对董仲舒的德刑关系思想进行一番正本清源的解读。首先,应该明确“德主刑辅”的概念并非董仲舒原话。董仲舒与之接近的表述是“刑者,德之辅也”,这种表述仅是对德与刑的相对关系进行概括总结,并不能意味着治国理政总是应该以德为主而刑辅之。其次,董仲舒对德刑关系最为核心的概括是:任德不任刑。理解董仲舒德刑关系思想的关键就在于对其“任德不任刑”的思想进行解读。本文试图通过解读“任德不任刑”的思想,重新诠释董仲舒德刑关系思想的真正内涵,从而对深刻影响法制史学界的“德主刑辅”说进行检讨。
二、“任德不任刑”——董仲舒德刑关系思想的核心
(一)“任德不任刑”思想的提出背景
秦汉之际的制度与思想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秦以法家之“刑治”统一天下,废封建为郡县,在政治上以“刑治”为核心构建国家制度,严刑峻法统治百姓,最终酿成民怨,二世而亡。汉初黄老思想偏重于经济改革,提出与民休息的自由经济政策,但是对于政法体系,黄老思想则倾向于承袭秦朝法家“刑治”之余绪,以在立国之初迅速恢复秩序、建立法制。因此,汉初政治之弊就在于其传承了秦朝法家“刑治”刻薄寡恩的政法传统,未能给经济与文化的复苏提供一个宽容、自由的政治环境。汉初官场崇尚酷吏,官员以学习刑名之学,治狱严苛为荣,一时之间出了诸如张汤等著名酷吏。司马迁认为酷吏以刑名之学统治乡里,摧毁了社会的优良治理秩序。虽然酷吏的铁腕可以收一时之效,使地方社会出现短暂的“道不拾遗”局面,然而,社会的自生活力及礼俗秩序被严重破坏,政治高压一过,社会立即溃崩。酷吏的政治高压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史记·酷吏列传》)。而班固则对汉初的法制状况作了一个概括性的描述:“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治者也。”(《汉书·刑法志》)
针对汉承秦制之蔽,董仲舒提出了“更化”的主张,所谓“更化”就是要改革秦政以“刑”治天下的政治体制和统治精神,起到拨乱反正的历史意义。在董仲舒看来,汉初之政治已经犹如“朽木粪墙”,必须经历彻底的改革才能恢复治理。他说:“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所提倡的“彻底改革”“更化”并不是革新,而是要恢复西周以来的儒家德治传统。董仲舒批评汉初的统治者没有深刻反思秦政“刑治”之恶劣,反而继承了秦政狱吏治天下的弊政,他说:“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的全面更化不仅仅只有以“德教”取代刑罚这么简单,而是要以儒家之“德治”全方面地代替原来秦政中的“刑治”,这就是董仲舒所提出的“任德不任刑”。
(二)“任德不任刑”的思想内涵
董仲舒的更化方案主要集中于其上书武帝的《天人三策》一文中,其最为重要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任德不任刑”,下面仅就其中最为有意义的三个方面加以评述[①]下文所引原文,如无特别注明,皆引自董仲舒所著之《天人三策》,载于《汉书·董仲舒传》。:
其一,董仲舒“任德不任刑”的思想主张建立在其天人合一的王道政治基础之上。董仲舒的天命政治观的目的是实施王道政治。董仲舒所谓王道政治,第一步则是“深察名号”,即确立君主权力运作的合法性标准。“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标准最终落实于“天”。“是故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按天道的要求施行统治,具体说来就是“任德不任刑”,因为天有阴阳,而德为阳,刑为阴,“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既然天道是以阳为生育养长之事,那么统治者要施行统治,养育万民,就必须“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徐复观在论及董仲舒政治思想时,认为董仲舒的真正精神被其“迂拙神怪的天的哲学所遮掩了”。其实,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重点并非应验神怪,而是为了给现实政治寻找一个超验的正当性标准。从古至今,政治的正当性无非诉诸人或超验的神,诉诸人的正当性标准或为民主政治或为圣人政治,而诉诸超验的神的政治在西哲则谓之自然法,在董仲舒则谓之“天”。
其二,董仲舒讲“任德教而不任刑”并没有将“德教”简单为对百姓实施道德教化,而是将矛头指向了统治者。董仲舒认为,德政治下之民也有德,而乱政专门产生暴民。既然百姓之道德修养取决于统治者是否有德,那么,德教的关键就不在于教民,而在于正君。“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因此,董仲舒一方面强调君主统治必须有德,认为施行王道的开端就是要正君、正朝廷,然后正百官、正万民。另一方面,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的“仁学”思想,以仁为核心解释人的精神实质,认为人之所以“超然异于群生”,是因为人有伦理、知仁义。论证人具有仁心、有伦理是为了说明人“超然异于群生”,人是具有尊严和个性的,董仲舒称之为“性”。“性”与“天命”都是统治者所必须认真对待的,“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因此,君主应该成全人之秉性,以德化的方式治理天下。君主以刑赏驾驭民众、役使民众的做法都是违背人之秉性的做法。董仲舒将教化与人之“性”相联系,并不是认为民众天性愚顽需要教化,而是认为民众天生具有理性和仁心因此可以教化,因此,教化也必须“以渐而至”,不可急于施教,教化必须符合人之本性,任何违背人之本性的教化都是残害人性的做法。
其三,董仲舒提出的“任德不任刑”是在社会管理模式的层面主张应该施行儒家的“德治”,而非法家的“刑治”,并没有否认刑罚或是法律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和价值。就社会调整的手段而言,董仲舒将“庆赏刑罚”比喻为一年之四时,认为在社会管理当中,刑罚与德教犹如一年四季,不可或缺。他说:“庆赏刑罚之不可不具也,犹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但是就德与刑的关系而言,其中却有着明确的本用之别。德在董仲舒的政治哲学体系中居于“本”的地位,董仲舒的“复古更化”之核心就在于恢复西周以来的德治传统,可以说“德”规定了政治性质和根本。而刑在社会治理的体系中则居于“用”的层面,是说在社会管理中刑政的手段不可或缺。若以后世《唐律疏议》中的话来概括则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三、“正己”与“治人”之别——董仲舒德治思想的自由价值
董仲舒“任德不任刑”的核心是恢复儒家“德治”传统,清除汉初因承袭秦制而保留的法家“刑治”之弊端。现代学界对儒家“德治”思想有一种批评,认为“德治”就是统治者借政治之权威向百姓推动某种道德标准的建立,而全面伦理化的法律不仅调整人的行为而且干涉人的内心,从而导致自由空间的丧失[2]。实际上,这种批评是对儒家“德治”思想的误读。儒家的“德治”思想有两个面向:一是规范君主的行为,要求君主实施德政;另一方面则是德教,培育百姓自治之德。儒家之德教并非君主对某种价值观念的强制推行,而是启发人的德性之心,使其能够耻于为非作恶而向善。儒家德治思想的两个面向在汉代就体现在“正己”与“治人”的区别,在方法上不仅主张“先自正而后正人”(《公羊传》襄公九年春,何休注),同时强调“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公羊传》隐公二年春注)。
董仲舒在孟子“仁心义路”的基础上对汉代“先自正而后正人”的朴素政治伦理进行了发展,形成了“仁义法”的核心思想。《春秋繁露·仁义法》提出:“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董仲舒提出“仁治人”“义治我”的思想使先秦儒家关于“仁”与“义”的关系更加明确。董仲舒认为“人莫欲乱,而大抵常乱”的主要原因在于“暗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人们通常对自己宽仁,而对他人则责之以义。所以,“《春秋》为仁义法”,规定“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仁与义必须分别用来治人与正己,不可颠倒,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作用方向正好相反。“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春秋繁露·仁义法》)。
董仲舒继承孟子“君正而物正”的思想,提出了“我虽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的主张。就“正己”与“治人”的关系而言,关键在于理解“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的内治之道与“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的外治之道的深刻内涵。
“反理以正身”与“据礼以劝福”均为统治者以“义”正己的内治之道。其中,“反理以正身”的“理”与“义”相近,指“义”中所包含的道理。贾谊《新书·道德说》中说:“德生理,理立则有宜,适之谓义。”说明“义”不过是“理”在实际运用中所体现的外在原则。董仲舒的“义理”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事明义”,即君主以自身的德行感化万民,其中事明义的要义在于君主之德行应该足以德泽万民,如日月照耀阴暗。“圣人事明义,以照耀其所暗,故民不陷。《诗》云:‘示我显德行。’此之谓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二是“义之养生人大于利”。《春秋繁露》中解释:“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其中“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这些义利之辨的目的均只是君子正身之任务,而从来不是对小民所施加的道德要求。君主辨义利的目的在于“据礼以劝福”,即要求统治者不要穷奢极欲,要合理分配财富,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故“诸有大俸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先王之礼正是对君主之利的限制。在董仲舒看来周末以来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统治者不遵先王之礼,而“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汉书·董仲舒传》)。大一统时代,帝国之势力日益庞大,国家对财富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必然引起国家与小民争利业的现象产生。董仲舒提出“据礼以劝福”实是对国家权力干涉民间经济以聚敛财富的限制。
“推恩以广施”和“宽制以容众”是君主“以仁治人”的外治之道。周桂钿对这两句话的解释是:“推恩广施,可以使多数人得到好处。宽制容众,就是放宽制度,容纳各种各样的人。”[[3]此说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推恩广施”与“宽制容众”的意义,但是除此之外,董仲舒“以仁治人”还有更为深刻的内涵。
“推恩广施”是与“据礼劝福”相对应的治人之道。前文已述,“据礼劝福”是对君主提出的正己之道,要求君主明辨义利之别,对君主、国家提出不与民争利的要求。而“推恩广施”则是要求大兴民利,要求君主在享受天下之大利的同时,同情民间疾苦,为百姓寻求谋利的道路与途径。董仲舒以孔子“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之语说明治理社会以富民为先,富民是教化的必备前提与基础,故此,董仲舒提出“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春秋繁露·仁义法》)。“宽制以容众”强调的是儒家德治的非强制性与启发性。董仲舒承认民性虽有向善的本质,但是却常常“趋利而不趋义”,因此而产生祸患。要想使民自觉地趋义而不趋利,必须使百姓对义做到“自得”与“自好”,主动认识和遵守“义”的要求。实现这一目的不能以礼法将义强加于民,只能通过统治者与接受儒家教化的士君子的躬亲示范而使百姓“自省悟以反道”(《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董仲舒对“治人”与“正己”之别的讨论类似于富勒所谓“愿望性道德”与“义务性道德”。富勒所言“义务性道德”是指“从最低点出发,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使有序社会得以达到其特定目标的基本原则”[4]8,也就是人们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与“义务性道德”相对应,富勒对“愿望性道德”的定义是“它是善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4]7。“义务性道德”与“愿望性道德”的意义在于为法律推进道德实现划定了一个界限与范围,法律以“义务性道德”为基础内容,因此法律成为人们的最低道德标准,以维护人类社会中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的存在。而“愿望性道德”则为法律推进道德进步划定了一个范围,“愿望性道德”属于伦理与道德的领域,政府不得以推进道德为名立法干预个人的私德空间。一直有人认为,儒家“风行草偃”的教化是树立以君子为典型的道德楷模,然后要求全社会效法君子之行的道德教化。因此,有人将儒家的“风行草偃”之教与现在的道德教育相比较,认为这样的做法不仅造成教化者假话、空话、大话连篇,而且在社会上酿成了伪善成风的局面。树立君子为榜样,要求一般百姓人人向君子学习,要求人人致圣,会导致强制推进道德,消灭公权力与私人生活的界限,使得个人自由的空间消失殆尽。这种对儒家的指责实际上并不能成立,将“忠恕之道”一以贯之的儒家怎么可能认可这种强人从己的思想呢?“子曰: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礼记·表记》)。董仲舒明确了“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的儒家德教原则,实际上为儒家的德教确立了两个方面的基本范围:一是就正己而言,君主应该以“义”正己,对自己提出更高的伦理要求;二是治人,则应该“宽制以容众”,不能以儒家“君子”之教教化小民,不能以君主的政治手段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
四、《春秋》决狱——司法领域的“任德不任刑”
儒学真正对国家的政治制度起到影响,开始制度化的发展是在元、成以后,史称:“自元、成后,学者藩滋,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此处所说的元、成以降,改郊兆、定三公可以说是儒家制度化的关键转折。而在此之前,《春秋》决狱就已经开始了以儒家经义影响、改变司法审判的努力。因此,有学者指出,《春秋》决狱所引领的“法律儒家化”趋势,其实是政体“儒家化”的其中一个环节。其引用春秋经义以论断刑狱者,则以儒家之道德人伦主义及仁恕思想,注入实证法制之中[5]。法律体系不纯是一些技术性规范的整合与杂糅,而是以一整套伦理基础和价值信念为其基本的内核,不仅与政治体制相关,而且与一个时代或民族的道德规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全盘改变的。所有的成文法典的规范、原则往往是从反复出现的个案中抽象、凝练出来的。《春秋》决狱恰恰就体现了这样一个由个案逐渐形成一般性原则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程。
董仲舒以《春秋》决刑狱的核心原则是“原心论罪”。“原心论罪”之本义是为了矫正秦政之弊,董仲舒在一份对汉武帝的奏章中指出秦朝法律之弊病在于:“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在董仲舒看来,秦朝政治法律之问题在于法律的僵化规定与情理的现实状况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规范的外在性与人的意志、情感之间的矛盾。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孔子看来,人如果没有真性情,即便行为符合礼乐的外在规范也不过是使人更加虚伪。因此,儒家传统历来要求外在的规范与内在的情理要相互统一。而秦汉之际的政法体系源自于法家“循名责实”的思想,其发展流弊就是过分强调行为与规范的外在一致,而忽视了行为的主观态度和实际情感。现实中的事实问题复杂多变,行为背后的心理基础也千差万别,如果仅以简单、僵化之法条调整规范复杂之人情现象则会有“削足适履”之嫌。同时,由于古时所谓“法”实则只是“刑”,只强调人的行为外在与规范的符合,未免会导致刑法的过分严苛,董仲舒认为良好的司法应该探究人的内心状况和事实的真切,因此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繁露·精华》)同是一种行为,如何处断,关键要看行为人的内心意志究竟如何。所谓“《春秋》之定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盐铁论·刑德》),这种司法方式之目的就在于消除法律僵化之流弊,以追求人情与法理的相互协调。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6]
本案并无直接引用《春秋》或其他儒家经典中的成例,但董仲舒却凭着儒家经义,将儒家的义理抽象为一项司法裁判中的原则,矫正了僵化适用法律所造成的不公正。儒家自孔子起对内容和实质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形式和外在规范,因此,儒家往往更注重人在具体案件中的情感,而不是表面的合乎规范。任何规范,不仅是法,甚至于礼、乐都不过是内在的人的情感和人性的表现和辅助。礼乐法制之规范制度都是为了顺应、调节人情和人性而产生的,所以说:“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儒家对于案件的审理就要求必须合乎人情、义理的要求。
儒家对于“孝”的伦理规范也更重视其情感的实质,子对父母应心存有“孝亲”之情,而父母对子则须有“慈爱”之意,若为父者已失亲亲之义,为子者不再负为人子的责任。所以《春秋》所载,献公不以申生为子,而申生自杀,实乃愚孝;又不以重耳为子,而重耳逃亡,《春秋》不以为不孝。可见父子之孝慈的义务不仅出于血缘的表面关系,而是需要有内在的情感和恩义为基础。因此,在此案中父甲对于乙一无供养之事实,二无哺育之恩情,董仲舒援引儒家重视情感实质的伦理原则认定乙杖父不是子杖父,不能加重处罚。
在法制发展的历史经验中,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法律形式上的严格适用和法律目的的实现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为了防止司法者滥权并且取得心里强制的效果,因此需要在司法中严格适用法律条文的文本规定,不因司法者主观的好恶和案件的具体情况排除或改变法律的适用;而另一方面,律文的规定过于僵硬、刻板,则不免使法律的目的和个案的正义难以实现。在中国古代,法律往往以刑事制裁为强制力的表现形式,因此,如果像法家一样片面强调法律在形式上的严格遵守,难免会有刑罚过于严苛的危险。从功利的视角来分析,严格执行成文法虽然可以在专制社会维护法律的普遍适用,有效地减少官吏滥权的可能,但是僵化执行法律所造成的不正义的后果却十分严重,而且无法恢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儒家强调司法首先应该原其情理,并且以儒家思想中的伦理原则来解释法律,实际上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减轻传统法制运作中的严酷性,并且使得传统法的实践趋于人性化。
汉代的《春秋》决狱开始了以儒家经义解释法律甚至以儒家经义作为司法审判依据的实践,在这场司法实践的运动中,儒家经义中“仁政”“恤刑”的思想对汉初的政治法律起到了深刻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酷吏们“重刑思想”对司法的影响。《春秋》决狱的推行,由于儒家宽仁思想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使得汉代的司法逐渐趋于“宽厚”,有效地缓和了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如《后汉书·何敝传》中的记载:“以宽和为政,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无怨声。”
[1] 马小红.中华法系中“礼”“律”关系之辨正——质疑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某些定论[J].法学研究,2014(1): 171-189.
[2] 孙莉.德治与法治正当性分析——兼及中国与东亚法文化传统之检省[J].中国社会科学,2002(6):95-105.
[3] 周桂钿.秦汉思想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135.
[4] 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 黄静嘉.中国法制史论述丛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66.
[6]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1911.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Counter-Argument of the Idea of “Morality Given Priority over Penalty: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Dong Zhongshu’s Idea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Penalty”
LI Dejia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872, China)
The idea of “morality given priority over penalty” is the modern academic scholars’ summary of the ancient Confucian idea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penalty. This idea tends to be considered originating from Dong Zhongshu’s idea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penalty. According to the maladministration caused by the rule of penalty that was inherited from Qin Dynast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Han Dynasty, Dong Zhongshu put forward the political legal idea of morality-ruling over penalty-ruling, which required rulers to carry out Confucian “rule of morality” in social management, and the idea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penalty as foundation and application rather than primary and supplementary. Since Emperor Han Wu restored ancient ways, the idea of “taking rule of morality and didactic rule as foundation and government order and penalty as applic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trend and greatly influenced the mode of social manage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unific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penalty; rule of morality with its priority over penalty; rule of morality
10.3969/j.issn.1673-2065.2017.02.007
李德嘉(1987-),男,河南洛阳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法学博士。
B234.5
A
1673-2065(2017)02-0055-06
2016-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