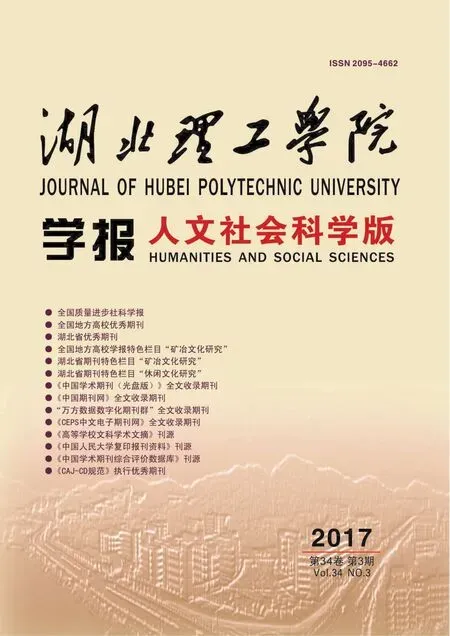工作与休闲的关系辨析
——一种价值论解释的尝试
方 芳
(浙江大学 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8)
工作与休闲的关系辨析
——一种价值论解释的尝试
方 芳
(浙江大学 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8)
文章在揭示工作与休闲融合的内在逻辑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概念的基本分类,对工作与休闲进行同一价值范畴下的关系辨析。在经济范畴中的不可融合性与哲学范畴中的可融合性的综合考量中,提出与“工作-休闲”融合论相左的观点,即休闲与工作不是位于同一范畴的融合与非融合关系,而是工作具有天然的休闲属性、休闲终将超越工作的动态发展关系。
工作;休闲;融合;价值论
从历史的角度看,工作与休闲一直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竞争状态中。刘惠梅和张彦从伦理学历史的视角,对工作与休闲的关系进行了梳理:第一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崇尚休闲贬低工作的时期;第二时期,中世纪,从宗教意义上凸显工作价值的时期;第三时期,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彻底漠视休闲、将休闲视为工作补偿的时期;第四时期,现代社会,通过对消费主义进行不断反思而重视休闲的时期[1]。现代社会正处于对休闲重视的觉醒状态,然而,工作与休闲的竞争状态似乎已经趋于终结了,越来越多的人著书认定,随着我们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休闲与工作的融合势在必行[2]。但是,当学者探讨这样融合的基本特征的时候,已经将工作与休闲放在了同一范畴之内,因为只有同一范畴的事物才有融合的可能,而对这个先行的认知却是缺乏充分论证的。如果休闲与工作并不属于同一范畴,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随着社会转型又将出现怎样的变化?本文从价值论的视角,分两步探讨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关系。第一,同一范畴假设中的工作与休闲关系辨析:分别从劳动作为经济学概念的交换价值和作为哲学概念的使用价值入手,分析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关系;第二,工作与休闲的关系再探究,该部分致力于回答一个假设:如果休闲与工作本身并不处于同一价值属性,而是拥有属种关系的概念,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拥有怎样的特性?
一、“工作—休闲”融合论
从一种高度概括的角度来说,休闲是生活世界中的自由时间、心理状态中的自由感知、存在状态中的价值感受。“工作—休闲”融合论的思想是从“工作休闲化”的趋势出发,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述的:1)后工业社会时代对劳动方式需求的改变,带来了工作方式和类型的变革。在物质经济走向知识经济的时代变革的进程中,工作的休闲化是工业社会中以体力劳动为代表的被固定、僵化、刻板、枯燥的纯工作方式的改变。学者们认为,知识经济下的工作方式“使工作有人性化,更符合人的需要,以此来改变以往工作沉重丑陋的面目”,并且,信息化时代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将有可能彻底改变以往工作与休闲割裂的格局”[3]。这样的劳动需求类型、工作方式的改变,一方面由于智力因素的更多参与,人们不再把工作“看作是痛苦渊薮,因为智力劳动与智力成果会使人更多地体验成就感”;另一方面改变了这样的一种现状——“以往由于对效率的过度追求与利润最大化的指标导致了工作对人的异化,专业化分工带来了工厂的效率,却剥夺了手工艺者工作的魅力与乐趣,机械的使用降低了劳动的强度,但也破坏了自然劳动的节律”——从而使“智力型工作”成为人们休闲和工作融合统一的现实途径[4]。2)“人本主义”的思想,带来个体对人生境界的重视和关注,期望通过劳动者内在的努力,使工作成为一种人生境界,一种审美体验。该观点将“休闲看成一切活动的理想状态——人心投入、欢喜进行的自由愉悦状态”,认为“如果工作和责任是非休闲的苦役,那么,安插在工作之间或之外的补偿性、恢复性的暂时休闲,对成就生活幸福的作用是很有限的”[5],因此,为了提升个人的境界和生活的价值,必须强调和重视“工作带给主体的精神畅快性和心灵愉悦性”,使得每个劳动者都要“像庖丁一样使休闲成为生活的普遍品格,淡化工作的强制性,使之更为接近主体的固有兴趣、能力和天赋,用休闲审美的心胸将之视为人生意义和欢乐的无尽源泉”[6]。
综上所述,“工作休闲化”的观点基于这样两个内外趋势的基础上:知识经济时代的“智力型”劳动的崛起,带来了各行业工作条件的改善、体力劳动强度的降低、工作被迫性的解除;“人本主义”的思想重视人在工作中的主体性,强调工作带给主体的精神畅快性和心灵愉悦性,个体能够使工作艺术化和工作的人生境界化。从这样的内外两个趋势出发,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工作—休闲”融合论进行了阐述,这些理论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之下:1)休闲之所以是人们喜欢做之事,缘于休闲是人们“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是人们按照自己所选方式活动的相对自主状态,是人们自我完善并使自己愉悦的自为状态。因此,自由、自主和自为可以被视作休闲的本质特征。2)工作是我们必须做之事,缘于人们生命的维持和再生产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东西,而只有工作才能为社会、为自己提供这些生活资料。因此,“由必须的外在目的规定”为社会创造必要财富,可以被视为工作的本质特征。3)如果有某种活动既是人们喜欢做之事,又是人们必须做之事;人们既实现自我,又为社会创造财富,那么这种活动应被视为休闲和工作的融合。这就是“工作—休闲”融合论的基本内涵。这样的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但它是建立在一种简单的糅合性的思考中,混淆了“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区别,即将A的优点与B的优点结合起来就是未来应当拥有的一种状态。这样的理论缺乏科学性、深刻性和洞见性。因此,不从一个融合的愿望出发,而从科学的角度去仔细辨析休闲与工作的关系,是回答休闲与工作是否可以融合的必要基础。笔者选择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基本分类,对两者进行同一价值范畴下的关系辨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劳动”概念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作为一种经济概念的劳动,劳动是一种商品,拥有交换价值;二是作为一种哲学概念的劳动,是基于使用价值之上的一个体现价值旨趣的哲学范畴[7]。
二、作为经济概念的“工作”
(一)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最为核心的概念。经济学里关于价值概念是商品经济概念,商品经济的表现是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商品价值,不应该同其他价值,如价值取向、价值观、学术价值、人生价值等混同起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了杜林的所谓“绝对价值”观,指出:马克思研究“知识商品的价值”,“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8]。创造价值的劳动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关系,所以,在经济学意义上,劳动本身的价值不在于劳动对劳动者的“价值”,而在于它的交换价值。这是经济学划定的关于劳动价值的概念范围。尽管工作与劳动在概念定义上会有差异,但是,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说,商品经济时代的工作就等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的概念。工作是商品的理论,是经济学关于工作价值的基本定义。从基本定义中可以得到工作是具有交换价值的,是人换取货币的基本方式。那么,除了交换价值,工作还具有其他价值吗?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指出,工作是一个社会的本质先决条件,而渴望工作是人的天性,人类的工作本性来源于人的活动本性和游戏本性。Erikson和Maslow的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证明,工作是一个人从青少年向成年转变的关键条件,对一个人建立健康的自信和自尊也很重要[9-10]。Jahoda和Warr认为,一个伐木工人从倒下的树中可能不会直接感受到满意感,而是从自身工作的无形产品中体会到了主观幸福感[11-12]。更有研究证明,工作是潜在的使人更加满足的因素,参加工作是满意生活的基本要素,即便是在非常差的条件或者非常恶劣的环境中,工作所含有的非物质实质也具有巨大的心理支撑意义。因此,工作的价值不仅包含以工资为代表的物质产品,还包括了非物质的、与金钱无关的方面。工作的非物质价值部分具有独特内涵(包括看不见和主观的产品),它有一个严格的限定,它并不像金钱方面的收入可以存下来或者购买其他物质产品,因此它具有不可存储性,它的生产和消费具有同时性。而这部分非物质价值与休闲的价值表达形式相似,学者们也越来越重视这一部分价值的体现,它是智力型劳动需求和人本主义思想的融合论考量的基石,是学者们认为工作可以与休闲进行融合的主要原因。虽然这部分非物质工作价值与休闲价值形式类似,都是无形的,且能让人体会到生活的价值,甚至因为喜爱工作的内容而达到忘我的、“畅”的体验,但是,这就意味着工作与休闲的融合吗?就真的可以将这部分的价值简单的等同于休闲价值了吗?处于后工业社会时期的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工作是公益性的,这一部分工作并没有物质价值。那么,彻底抛开物质价值的工作可以完全等同于休闲吗?如果将这部分价值完全等同起来,将会得到以下判断:如果在工作中的非物质价值大于或者等于休闲所获得的效用,那么从理论上说,人不会在工作和休闲之间主动选择休闲以获得其他价值。这样的判断似乎就是“休闲无用论”的一种推论。这种推论,显然是违背了人类普遍追求休闲体验的现状的。笔者认为,仅仅用体验效用来度量工作与休闲的内涵,将工作的非物质部分的体验效用与休闲的体验效用等同起来,必然会造成在概念上、在现实认知中的谬误。因此,要仔细辨析工作的非物质效用的价值与休闲作为经济价值形式的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
(二)工作与休闲的经济价值差异
作为一门系统性知识的建立,休闲学一直是作为工作的对立面而发展起来的。无论学者从何种角度、持何种观点,休闲与工作的差异都主要落在了自由体验之上。从价值论的角度解释工作中非自由感知的来源和休闲中的交换价值的实质,是理解工作与休闲关系的立足点。
首先,与休闲相比,为什么工作中会有非自由的感知。作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工作,它是有价格和有目的性的,是为了无障碍地换取一切商品的货币,因此,只要有与货币交换的需求,就无法摆脱束缚。生产者生产产品需要得到购买者的主观价值的认可,他人主观价值的认可成为了生产者的束缚。戈比指出两种工作与休闲纠缠在一起的现象:一种是原始社会狩猎——采集部落和农耕社会中,工作和休闲是浑然一体的;一种是对于艺术家或者手工艺人来说,同一个行为既能满足内心冲动,又能解除外在压力,所以工作与休闲的区分是无意义的[2]。这两种状况,一种处于非商品经济时期,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决定了劳动不需要具有交换价值的内涵,没有交换价值也就没有非自由感知和外在压迫感。另一种艺术家的状况在于,其艺术创作可达到满足内心冲动和解除外在压力的双重结果。需要追问的是,如果这件艺术作品是事先有买家预定,或者艺术家希望能够换取金钱,而不仅仅作为自身消遣所用,那么他真能摆脱外在压力吗?他真能毫不顾及买家的喜好和市场的状况而进行心无旁骛的创作吗?这里的追问,也是汉娜·阿伦特所认为的工作在普遍处于“劳动社会”的境况中瓦解为劳动的内涵[13]。工作中的非自由感知来源于工作本身的内涵——交换价值。交换需要契约精神,需要双方都同意交换,才创造了市场中的财富,因此,需要交换而被识别和肯定的价值,一定是具有非自由属性的。
由此可以推论,虽然工作中会产生非物质的价值,但是它只是围绕着交换价值所产生的附加价值,没有交换价值就没有工作中的非物质价值,交换价值是工作非物质价值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工作的价值以向外和向内两种方式体现,而外向价值是内向价值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外向价值具有决定性。在公益类的工作中,交换价值的另一方并不是物质的、金钱的,而是对他人的效用,是以自身的工作换取对他人的效用,换取自身价值在他人、在世界中的体现,这样的价值是交换价值本身的一个变形,并没有脱离交换价值的内涵,因此也将缺少一部分的自由感知。
其次,如何理解作为经济学交换价值形式的休闲价值?休闲中表现为交换价值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是像传统的商品经济一样,由希望得到休闲的人用货币向拥有某种休闲商品的人购买?一个人只要花钱购买了梵高的画作,就能获得非凡的审美价值了吗?一位希望得到美景的人,只要报名参加旅行团就可以看到美景,那么这样的美景对他就有价值吗?答案都是否定的。理解休闲的经济价值,并不能从传统的交换者双方割裂的商品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那么,休闲经济中的交换价值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价值呢?笔者认为,休闲经济中交换价值其实质是一种自产价值,是一种由自己作为生产者、消费者和接受者的一种交换,在这样的交换过程中有其他经济活动作为参与者参与到休闲价值的创造。这些作为参与者的经济活动是价值创造的参与者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产者,它们参与到休闲自产价值的创造过程中去,但是只有作为休闲活动主体的个人,才是自产价值产生的源泉。
工作里的交换价值与休闲中的自产价值的根本区别在于:价值判断的主体。交换价值是由经济当事人,即购买者对财富所具有的主观上的意义判断,因为在商品经济中一项事物的价值最终可能并不在于生产它时的时间或实物耗费,而在于人们对它的主观估价。一个人在工作中创造出的价值由付给工资的企业决定,这个工资就是企业所认定的工作者工作价值的价格。而在休闲的自产价值中,决定价值的一方就是价值创造者自身。这就是与工作相比,为什么休闲能让人感知到自由的根本原因。
(三)不可融合的工作与休闲
越来越多的人期待出现像帕克所描绘的未来的生活场景。“在这种融合中,工作将失去它目前所具有的强制性,获得现在主要同休闲联系在一起的创造性。同样,休闲将不再是工作的对立面,而得到一种现在主要同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创造财富的地位,值得人们认真计划,获得人类所得到的最大限度的满足感。”[14]然而,“工作—休闲”融合论只是对未来一种生活状态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和美好希望,这样的想象,来源于人们渴望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够长期或者一直保持非常自由和快乐的状态,却又无法肯定或者言明在未来的生活里可以不需要工作的一种矛盾的状态,而“工作—休闲”融合论似乎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样描绘未来场景的难题。可这样的理论和预测,并没有建立在工作和休闲本质的内涵上,没有在“人为什么要工作”和“人为什么要休闲”两种不同方向的追问中,洞见两者的关系,以至于对一些显而易见的现象缺乏解释效力,或者陷入诡辩论的陷阱里。“交换价值”所创造的财富本身是会带来快乐和成就感,人类也曾经在拒斥休闲而努力工作的几个世纪里,为社会的大发展而欢欣鼓舞并对未来充满期待,这样充满愉悦的体验更多基于社会性大生产和经济大发展的成就感。如果硬要说是因为工作和休闲的融合使个人在工作中达到“畅”的体验,是与当时的社会的实际现状和价值观所不相符的,也是对工作价值本身的大大低估。我们不能因为现代社会对休闲的重视而去否定近代工作所赋予人类的对自身充分肯定的价值。
工作与休闲融合论,误解了工作的非物质价值,混淆了它与休闲价值的本质区别。工作的非物质价值既不能与休闲价值相等同,也不会被休闲价值所替代,更不能完全摆脱交换价值的非自由性的内涵。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的异化”的境况并没有因为资本市场对工作方式要求的改变而改变。工作仍然保持着交换价值的本质,对工作者(劳动者)进行外在的控制。在同一经济价值范畴之下,劳动依旧是资本的附属物,“劳动不仅不是休闲的基础,而且休闲完全被排除在人生追求、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亦即人类本质的视域之中”[15]85。
三、作为哲学概念的“工作”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非经济范畴概念出现的劳动概念,是一种基于使用价值体现价值旨趣的哲学范畴。劳动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与经济学范畴所强调的交换价值不同,哲学范畴的劳动内涵落在了使用价值之上,马克思也正是运用使用价值来批判现实生活中的交换价值。“如果人们保留使用价值,那么物品的诸属性(这将是属性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就会总是极具人情味的,并会恰恰因为这一点而令人放心。它们就会总是关联着当属于人、属于人的属性的东西:或者与人的需要相适应,而这恰恰是它们的使用价值;再不就是人类活动的产品,而人类活动的目的似乎就是想让它们满足他们的需要。”[16]208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价值的意蕴并不只是局限于以手工业为代表的物质劳动之中。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一种“对象化过程”,并且是一种赋形活动。这一观点起源于黑格尔,黑格尔在他的著作中清楚的指出:“在经验条件下,既定的形式可能会呈现出最多样化的具体形态。因此,我所讨论的领域是既定的形式。至于无机界,我并不总是直接为它赋形。”[17]使用价值的内涵并不局限于物质产品的创造,也可以是对象的保存、动物或人的属性的改变、社会关系的转型等等[18]33。因此,劳动的使用价值包含在一切物质劳动(手工业)和非物质劳动(符号性或智力劳动,以及处理感觉和态度的情感劳动)之中。在此基础上,黑格尔认为,通过劳动,人们把自己对象化在我们的产品中,然后逐渐意识到人类的力量,并且在世界中具体化,把自己发展成有反思能力和自我意识的存在者[18]41。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说,人在创造“使用价值”的同时,不断发现自身的本质,即作为具有能动性的人的新的价值,这是对使用价值的一种超越。
马克思沿袭了这个观点,他将劳动理解为一种在人类赋予物质以形式的活动并且通过这一活动在世界中实现自身。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的“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认为人正是在劳动中确证自己的本质,“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劳动创造了人,并且本身就是人的生命的表现。马克思所认定的本真的劳动,与经济范畴中创造了物质财富的劳动不同,它是一种彻底抛出外在强制性的非功利性的活动而变成了自由的人类行为本身。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的劳动定义为本真的劳动的样式,这样的劳动才是人的真正的类本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在此层面上的本真意义的休闲,也就是劳动成为克服外在障碍的活动,成为人的自我实现活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15]89。在此哲学范畴的意义上,本真性的劳动与休闲的内涵互相润泽而相得益彰,劳动和休闲成为了统一的人的本真实体状态。
四、“工作—休闲”关系再探究
经济范畴中的不可融合性与哲学范畴中的可融合性都不可回避,如何处理劳动的经济范畴和哲学范畴(价值旨趣)的关系,是“工作—休闲”关系辨析的关键。
经济范畴中的工作因为存在着交换价值而摆脱不了被“外在力量”(看不见的手)控制的基本境况,成为异化了的劳动。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异化是马克思所刻画的人类在其历史进程中走向歧途的一种境况,那么时至今日,劳动的异化已经成为工作的一个本质特征,工作已经无法脱离经济社会环境而存在。受困于资本市场的运作,工作的概念已经被牢牢地固定在了经济与价值之间的灰色地带。当人们指出一件艺术品或艺术工作者的工作具有价值的时候,它的指称包含了对其经济价值的肯定。无法摆脱“异化劳动”内核的工作,与休闲无论是从经济范畴还是哲学范畴,都已经完全不是处于同一价值范畴的概念了。这也是阿伦特所指出“劳动社会”的本质,即在一个整个异化了的世界,“劳动社会”的出现与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相吻合[19]。简而言之,工作与休闲的表征差异在于,工作无法脱离经济范畴的意义而独立存在,但可以没有价值旨趣,也就是说,工作不能没有交换价值,却可以将人完全受控于外在力量从而丧失主体性;休闲则因其在经济范畴中的自产价值的本质,因此可以完全不受控于外在力量,即交换双方的合二为一使其保持自由性,但却不能丧失人对自身主观能动性体验的价值旨趣。综合考量经济范畴和哲学范畴,休闲与工作在统一范畴之中的不可融合的论点,在此殊途同归了。需要进一步推进我们的思考的是,如果工作与休闲完全不是处于同一范畴的概念呢?如果它们存在某种“种”与“属”的关系呢?
由上文可知,本真性的劳动是对“异化了的”劳动的克服,休闲与本真性的劳动是相互贯通的,马克思劳动解放的意蕴就是休闲的实在内涵。那么,笔者提出一个大胆的论断:休闲与工作不是融合的关系,而是工作具有天然的休闲属性,它们之间应当存在起始于“种”与“属”关系而终将成为休闲超越工作的动态发展关系。这种论点基于以下几个推论:
1)无论是后工业社会时期对工作方式需求的变化,还是人本主义对主体性的强调,都无法改变现有的经济关系和资本市场,因而无法改变工作的交换价值的本质属性,但是,劳动社会的工作虽然无法与休闲相融合,却具有天然的休闲属性,这种休闲属性隐藏在马克思所论述的本真劳动论之中。异化的劳动不会彻底掩盖本真的劳动特性,交换价值也并不会吞噬使用价值,更不会掩盖人在创造使用价值的时候,对人的本质、能动性发挥的价值创造过程的认识和反思。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工作具有非物质价值部分,工作对自尊自信的树立、满意度幸福感的产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现代性的休闲产生于劳动社会的工作,是对工作的超越,是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的价值发现,是一种处于自由境界状态中的人的自我实现。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把劳动作为了人的存在的起源,希望能够用本真性劳动的思想,将已经误入歧途的人引回正道。然而,马克思用使用价值去批判交换价值的劳动价值思想,在近代受到了鲍德里亚、德里达等人的批判,他们认为,从来就不存在游离于交换价值之外的使用价值。“和资本一样,幻影就开始于交换价值和商品形式。”“一种被彻底纯化走向交换价值和商品形式的使用价值的确定性究竟来自何处?如果无法确证这种纯粹性,那么,人们就不得不说,那幻影在所说的交换价值之前,在一般价值之价值的起始处就已经出现了,或者说商品形式在商品形式之前,在它自身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16]219-220而正是休闲与本真性劳动的融会贯通,对生活世界中的工作的超越,确证了这样的纯粹性。以手工业为例,木工这种传统手工业的劳动或工作方式,已经走上了休闲化的进程;作为休闲的木工所产生的产品,完全保持了它纯粹的使用价值形态,而不具有任何商品的性质。
3)休闲的自由体验为工作的非经济价值之外的价值提供一种引领,它不断地激发个体在生活世界各个层次中对马克思所描述的本真性劳动价值的体验和发现。这个价值的发现过程,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从而成为人的自我实现活动。在已经异化了的世界中,人们生活世界的境况被海德格尔描绘为“此在之沉沦”的“日常世界”,即人首先通常寓于他所操劳的“世界”,人首先从本真的能自己存在脱落而沉沦于“世界”[20]。人们需要一种本真性的“存在”的体验来激发个体重新掌握自身、脱离外在的束缚。休闲的概念以及围绕它所涉及的体验、活动、状态等等,提供了这样一种价值发现过程的引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过程需要公共事业领域的价值观的塑造和推动。
休闲的概念从劳动的概念中产生和发展,超越了母体概念范畴,成为一个独立的、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的概念。在以交换价值为主导的现代经济社会之中和劳动的语境下,工作本身已经无法像马克思所期盼的那样实现其自身的“最大价值”。“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已经成为人生活世界的基本形态,而正是在这样的危机之中,休闲扛起了“成为人”的伟大旗帜。在实现人类逐步脱离了物质条件束缚的进程中,休闲在异化劳动中成功突围,立足于异化劳动的批判视角,成为本真性劳动属性的引领,它使人们重新回归“成为人”的历史进程中去。休闲超越了工作。与本真性的劳动融合为一体的休闲,将“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21],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建立起“自由个性”[22]。
[1] 刘慧梅,张彦.西方休闲伦理的历史演变[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22(4):91-95.
[2] 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M].康筝,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145.
[3] 王小波.工作与休闲——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变迁[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8(8):59-62.
[4] 楼慧心.从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走向互相融合——知识经济时代的休闲和工作[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20(5):90-93.
[5] 方红梅.梁启超“趣味主义”的审美化休闲境界[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12):98.
[6] 赵春艳.工作休闲化的实现与审美人生境界的建构——“庖丁解牛”的休闲美学阐释[J].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0(3):13-16.
[7] 颜军.马克思劳动幸福思想的哲学意蕴[J].理论学刊,2014(5):63-68.
[8]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6-323.
[9] Erikson,EH.J.Psychological Issues,Vol.1,No.1: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M].NY: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1959:50-100.
[10] Maslow,A.H..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J].Psychological Review,1943(50):370-396.
[11] Jahoda,M..Work,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values,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social research[J].American Psychologist,1981,36(2):184-191.
[12] Warr,P..Well-being and the workplace.In:Kahneman,Diener,Schwarz(Eds.),Well-Being:The Foundation of Hedonic Psychology[M].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9:392-412.
[13]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4] Parker,Stanley Robert.Future of work and leisure[M].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1.
[15] 吴育林.论马克思的劳动休闲观[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22(7):85-89.
[16]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7] Hegle,G.W.F.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86.
[18] 肖恩塞·耶斯.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围绕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考察[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44(1):33-41.
[19] 唐正东.马克思与“劳动崇拜”——兼评当代西方学界关于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两种代表性观点[J].南京社会科学,2005(4).
[20]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04.
[21]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4.
[22]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0.
(责任编辑 陈咏梅)
Work and Leisure: An Axiology Perspective
FANGFang
(Asia Pacific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Leisure,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Based on logical analysis of the argument "work is leisure",this paper pro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isure and work in the same axiological category by using Labor Theory of Karl Max.From th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s of economy and philosophy,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viewpoint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fusion of work and leisure and holds that work and leisure is not in the same category,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isure and work is dynamic in that work has a natural attribute of leisure and leisure will eventually transcend work.
work;leisure;fusion;axiology
2017-02-23
方芳,博士;研究方向:休闲哲学、旅游人类学。
10.3969/j.ISSN.2095-4662.2017.03.005
G122
A
2095-4662(2017)03-002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