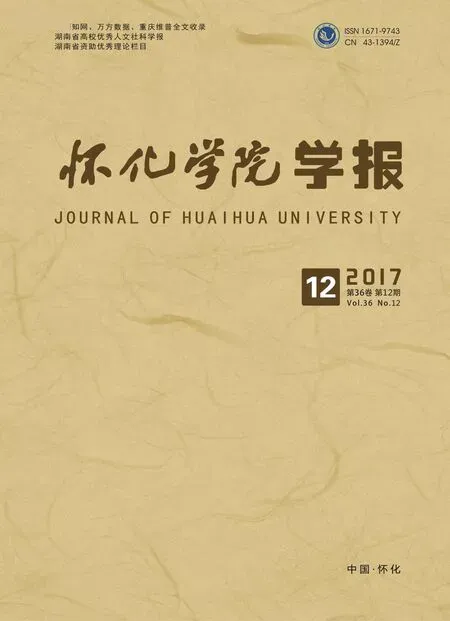创造的批评
——朱光潜意象批评论
袁 龙
(1.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2.邵阳学院中文系,湖南邵阳422000)
当下文艺批评存在重吹捧表扬轻棒喝批评、套用西方理论剪裁国人审美、用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红包评论等不良现象,引起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注意。他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作家艺术家“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1]。
习近平的讲话对文艺批评和标准的理解切中时弊;对文艺批评的要求具有古为今用,西为中用的特点。朱光潜于1935年提出的“创造的批评”是古为今用,西为中用的鲜活个案。因此,以朱光潜的“创造的批评”为参照,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下的文艺批评,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习近平的文艺批评思想。
一意象,无论在中国古典诗学还是西方意象派诗学中都是重要的概念。苏珊·朗格指出:“意象及其原型的关系却一直是艺术哲学上的中心问题。”[2]63朱光潜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他的美学理论被叶朗称为“美在意象”理论[3]。因此,我们要了解他的“创造的批评”,得先了解朱光潜围绕“意象”展开的生动有趣的讨论。
首先,意象牵涉到知识论。“知识所产生的不是意象,就是概念。”[4]6知识又基于直觉,因为“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基础。”[4]6所以朱光潜论意象从克罗齐的直觉说谈起。“事物刺激感官,所起作用名‘感受’,感受所得为印象。”[4]22感受与印象都是主体对客观事物的被动反应,“心灵观照印象,于是印象才有形式(即形象)”[4]22这一活动过程即是直觉(Intuition)。“印象由直觉而得形式,即得表现。”[4]22印象表现为形象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它的意义,寻求它与其它事物的关系和分别,在它上面做推理的活动,所得的就是概念(Concept)或逻辑知识(Logical Knowledge)。”[4]6这一过程,叫知觉(Percption),即“见一事物形象而知觉其为某某,明白它的意义”[4]9。
综上,我们可以总结出基于经验感受的知识论谱系:感受(主要是视觉感受,见)客观事物(无形式的物质、印象或表象,后来称为物甲)→直觉(形象或意象,后来称为直觉物、物乙)→知觉(判断推理)→概念(逻辑知识)。这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其中暗含克罗齐“形象直觉”的美感经验:“直觉是突然心里见到一个形象或意象,其实就是创造,形象便是创造成的艺术。”[5]19这与意象派创始人物庞德关于意象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6]305的概念略有不同,因为朱光潜对意象和概念有严格区分:“感官所得的是具体意象,理智所运用的是抽象概念”(《具体与抽象》)[7]262。如感官所见到的白马、白玉、白雪等个别事物的“白”;某一棵特别的树的形象是具体意象。脱离具体事物而统摄其共象的“白”、泛指的一般叫做“树”的植物都有理智参与逻辑推理,因而是抽象概念。通过对意象与概念的这种区分,朱光潜将意象定义为:“意象是个别事物在心中所印下的图影”(《诗的意象与情趣》)[8]369。
其次,意象与心理距离有关。形象的直觉或意象引起美感,这种美感超脱于现实实用目的,从而使物的实用功能被孤立。中国古人所谓“超然物表”与“凝滞于物”皆是心理距离的远与近的情感体验。意象作为艺术表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源于实际生活,一方面却要脱离生活经验而升华。艺术这种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矛盾,就是布洛所谓的“距离的矛盾”(the antinomy of distance)。朱光潜说:“创作和欣赏的成功与否,就看能否把‘距离的矛盾’安排妥当,‘距离’太远了,结果是不可理解;‘距离’太近了,结果又不免让实用的动机压倒美感,‘不即不离’是艺术的一个最好的理想。”[5]25所以,艺术家和欣赏者必须要有很高的艺术修养才能从切身的现实利害中超脱出来,不仅能感受到这种距离,而且能表现和领会这种距离。在意象的选取与表现上,熟悉亲切又能带来陌生化效果的意象无疑是上选。
再次,意象是移情的结果,是情感外射的产物。刘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9]132的言论表明古人已窥移情之妙:人的情感外射于物,无情的物便有情化,便有了生命。“菊残犹有傲霜枝”中残菊的“傲”,“云破月来花弄影”中花的“弄”,皆是移情作用的妙处。朱光潜也注意到西方对移情现象的理论概括,如黑格尔“艺术对于人的目的在于让他在外物界寻回自我”与洛慈“凡是眼睛所见到的形体,无论它是如何微琐,都可以让想象把我们移到它里面去分享它的生命……我们也可以外射情感给它们,使它们别具一种生趣”[5]40的言论,法国心理学家德拉库瓦的“宇宙的生命化”(animation del’univers)、英国学者罗斯金的“情感的误置”(pathetic fallacy) 等皆突出移情的物我同一。而立普斯在对审美快感特征界定的基础上提出的移情说,即“自我”的对象化更是“给‘自我’以自由伸张的机会,‘自我’寻常都囚在自己的躯壳里面,在移情作用中它能打破这种限制,进到‘非自我’里活动。”[5]50从有限到无限,从固定到自由,移情可以拓展意象的表现空间和审美张力,并由此形成境界:“诗是心感于物的结果。有见于物为意象,有感于心为情趣。非此意象不能生此情趣,有此意象就必生此情趣。诗的境界是一个情景交融的境界。”(《诗的意象与情趣》)[8]369
简而言之,朱光潜的意象论在吸收克罗齐“艺术即直觉”、布洛“心理距离”、立普斯“移情说”等西方美学和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注重生命感受与体验的“诗性生命本体”[10]的意象和境界理论加以融合,构建了西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中国现代意象理论。
二在意象理论的基础上,朱光潜形成了自己的文艺美学观念。“美觉即是直觉,美感的经验即是形象的直觉,无论一件什么东西觉得美的时候,都能引起一种意象(image),并且用全副精神去欣赏。”(《文学批评与美学》)[11]369-370“艺术就是情感表现于意象。”[5]155“美术是抒情的直觉,是意象的表现,是灵感的活动。”(《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学者》)[11]244以上诸观念在其著作中多次出现。谈文艺时,他说“文艺说来很简单,它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作者寓情于景,读者因景生情”(《看戏与演戏》)[8]256;“文艺和游戏在起源上本很接近,它们都是富裕的生命流露于自由的活动,都是要在现实世界之上另造一个意象的世界来应情感的需要。”[8]25谈文学时,他认为“像其它艺术一样,文学必须寓亲切情趣于具体意象”(《流行文学三弊》)[8]21;“诗人用有音乐性的语言来传达他的情趣于意象”(《诗的难与易》)[8]244……总之,朱光潜的文艺美学观念的核心是意象和情趣,同时也涉及到文艺对现实的再现与表现、文学语言的音乐性等审美因素。
朱光潜的文艺美学以意象和情趣为核心,其文艺批评也以意象或境界为标准。他批评新文化运动中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诗歌时指出:“五四时代作家和他们的门徒勇于改革和尝试的精神固然值得敬佩……他们的致命伤是没有在情趣上开辟新境,没有学到一种崭新的观察人生世相的方法,只在搬弄一些平凡的情感,空洞的议论,虽是白话而仍很陈腐的词藻。”[12]271-272他读李义山的《锦瑟》强调“诗的佳妙往往在意象所引起的联想”[11]408;分析王国维自评《浣溪沙·天末同云黯四垂》“意境两忘,物我一体”容易被人误解的原因是“前后两段所描写的是两面相反的图画,两种相反的情感”[11]405;推介施蛰存的小说《黄心大师》时指出“小说还有一条被人忽视的路可走,并且可以引到一种新境,就是中国说部的路”[11]548;推介程鹤西的散文《落叶》“写出一种意味深永的境界”[11]549;推介废名的小说《桥》“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11]553;欣赏鲍蒂切利的名画《春天》所见到的是趣味和情感;中国文人画是“在现实世界之上创造一些易与现实世界成明暗对比的意象的世界,不是更能印证人类精神价值的崇高么?”[8]213……他将这种以意象或境界为标准的批评称之为“创造的批评”——“在整个的艺术活动中,创造和欣赏与批评是一气贯穿的。创造和欣赏根本是一回事,都是突然间心中直觉到一种形象或意象,批评则是创造和欣赏的回光返照,见到意象之后反省这种意象是否完美。……创造欣赏有批评做终结,才底于完成。”[5]79“创造的批评”的基本信条是“一切美感经验都是形相的直觉。无论是在创造或是欣赏,我们心目中都要见出一种形象或意境,而这种意境都必须有一种情趣饱和在里面。”[11]377
朱光潜在意象理论基础上提出“创造的批评”有三个层面值得注意。
首先,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中国处于近代向现代转型时期,西学东渐和新文化运动等文化思潮风起云涌,在国故与新学盘根错节的学术脉络中,“意象”成为沟通古今中西文艺美学的交汇点。当时,胡适提倡的“八不主义”拉开了现代文学革新的序幕,这不仅与英美意象派庞德的《诗的几条禁例》在追求诗歌形式自由、使用日常语言、不模仿古人等方面精神相通,而且胡适提倡的“须言之有物”与庞德提倡的“表现一个意象”更凸显出“意象”是中西文学的共同体。值得一提的是,庞德有关意象的认识源于古希腊的抒情诗人伊比库斯和中国的汉武帝刘彻[6]15。同时,在人文学科科学主义转向的背景下,心理学的兴起为意象研究和意象批评提供了理论和实验依据。意象无疑成为中西融合和学科交叉的一个典范,既有纵向的延续,又有横向的交织,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其次,从个人经历来看,朱光潜生长于古文大家辈出的桐城,从小打下扎实深厚的古文功底。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后,他陆续辗转求学香港和英法,既专注于文学,又旁涉哲学、心理学、艺术史等,还做过不少自然科学实验,可谓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朱光潜在深入研究克罗齐学说后发现,克罗齐否认传达与表现一样也是艺术活动。克罗齐“忽略去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艺术家在心理酝酿意象时常不能离开他所习用的特殊媒介或符号”[11]380。克罗齐也忽视艺术的社会性。艺术情感背后牵涉到全人格(personality),即个性,艺术是个性的表现,个性又受时代精神影响,故艺术所包含的意象与时代历史有着密切关系。“艺术的风格改变往往起于社会的背景。”[11]381刘禹锡“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爱莲说》) 之语可为参证。忽略艺术的传达和社会性抹杀了艺术的价值,从接受者和批评者的角度而言,艺术无法传达出来,价值的接受与批评便无法继续,艺术可以“群”的功能便无法实现。所以朱光潜突破克罗齐的表现说,提出意象通过语言文字、线条色彩、音乐旋律等物质媒介传达意象,使之连接意象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同时突出了社会与艺术的相互影响。这种受西方影响却又不失个人灼见的眼界和魄力,与朱光潜个人的求学经历和深厚的传统文学修养密不可分。
第三,创造的批评是对当时已有批评方法的总结与提升。西方现代文艺批评家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抱有某种美术理念而无法创作,并以此为批评标准去引导批评他人创作的指导者(pedagogue);二是对创作者的得失优劣进行评判的裁判者(judge);三是解剖作者性格和作品意义的诠释者(interpretator)。但是朱光潜认为“指导,裁判,诠释三种工作仅可算是批评的准备而非批评自身”[11]244。在对圣伯夫、阿德诺、克罗齐等欧洲近代批评学者的批评方法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在创造的批评活动中,“批评家应该设身处地,领会到诗人作诗时的直觉意象以及灵感。一般人以为批评无须天才,其实批评是创造的复演,所需天才不亚于创作”[11]224。创造的批评注重创造与批评的综合,从接受者的角度还原创作者的意象或意境入手,把握创作者的经历与心理;从历史传承的角度看发展,避免历史错误(historic fallacy) 与私见错误(personal fallacy)。朱光潜意味深长地指出:“文学是全民族的生命的表现,而生命是逐渐生长的,必有历史的连续性。所谓历史的连续性是生命不息,后浪推前浪,前因产后果,后一代尽管反抗前一代,却仍是前一代的子孙。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先例,让我们可以说某一国文学在某一个时代和它的整个的过去完全脱节,只承受一个外国的传统,他就能着土生根”(《现代中国文学》)[11]330。创造的批评既注重宏观视野与微观分析,也注重历史传承与个体发展相结合,超越指导式批评、裁判式批评和诠释式批评的局限,通过意象这一关键因素将文艺活动中文艺创作者、世界、文艺作品和文艺接受者四个要素有机联系起来,创造、欣赏和批评也随之连贯一气,不再以其中某一要素为中心,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欣赏、评价文艺之美。这与恩格斯评价文艺作品的最高标准——“美学的”与“历史的”标准具有一致性。
三在当下文艺批评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回顾朱光潜以意象论为核心的“创造的批评”,有助于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反思当下的文艺批评并理解习近平文艺批评思想:
第一,文艺批评也是一种文艺创造。“为他人做嫁衣”、“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吹鼓手”等观念折射出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似乎是一种主次关系,而不是对等关系。真正的文艺批评不仅仅指导、裁判、诠释文艺创作和文艺作品,也应该是一种文艺创造。这种创造可赋予作品以二次生命。优秀的文艺批评能有力引导、推动文艺创作的发展,并在文学作品经典化以及文学创作经验理论化的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别林斯基对果戈里、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成就了当时俄国文学众星璀璨的佳话,也留下了“艺术是形象的思维”和“熟悉的陌生人”等经典理论话语。巴赫金对拉伯雷的批评研究不仅提出了“狂欢化”的理论,也影响到苏俄符号主义学派的研究方向,并开西方新历史主义批评之先声。萧统对六朝时期不为人所重视的陶渊明诗歌的再批评使之被尊为田园诗派之宗。脂砚斋评点《红楼梦》、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皆与原著互补增色,并成为构建中国叙事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即使在朱光潜提出“创造的批评”的时代,国内各种文学团体之间因为不同的文学主张而产生的争鸣与批评活跃了当时的文坛,中国现代文学也在短短三十年间产生了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习近平提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是因为文艺批评也是一种创造,“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1]
第二,文艺批评要有标准。无规矩不以成方圆。没有标准,或以其他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文艺批评就无法评判文艺作品的水平高低。习近平提出“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四个标准,体现了“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艺术追求与美学追求的高度统一”[13]。朱光潜认为“艺术就是情感表现于意象”,以意象论为基础的“创造的批评”的基本信条是“创造和欣赏根本是一事”[12]415。意象的创构与欣赏本身就涉及到社会风气、时代精神、美感经验、艺术修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因素反映出创作与批评的历史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上文提及朱光潜在文学批评中重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兴观群怨”说中“群”的标准,是因为文艺批评必须在文艺价值得以传达的基础上实现,而“群”不仅实现了文艺创作与文艺欣赏、文艺批评活动的交互循环,文艺活动社会群体性的特征也得以显现。孔子强调“诗可以群”是基于周礼宗法制度而言的,以期通过学诗来实现团结宗族成员,培养集体意识和道德伦理,建立和谐社会的政治理想。如果我们将这种社会群体性的特征转换为马列主义文论话语,契合“人民的”标准。
综上所述,朱光潜建立在意象论上的“创造的批评”是在历史发展的中西文化比较视野观照下形成的一种审美批评。创造的批评体现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古今中西并蓄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不仅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下的文艺批评现状,也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文艺批评思想。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A].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2][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傅志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叶朗.从朱光潜“接着讲”[J].北京大学学报,1997(5):69-78.
[4]克罗齐.美学原理[M].朱光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6][英]彼德·琼斯.意象派诗选[M].裘小龙,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7]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8]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九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9]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陈伯海.释“意象”[J].社会科学,2005(10):111-116.
[1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八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12]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三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13]丁国旗.当代我国文艺批评的新标准[J].前线,2016(3):4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