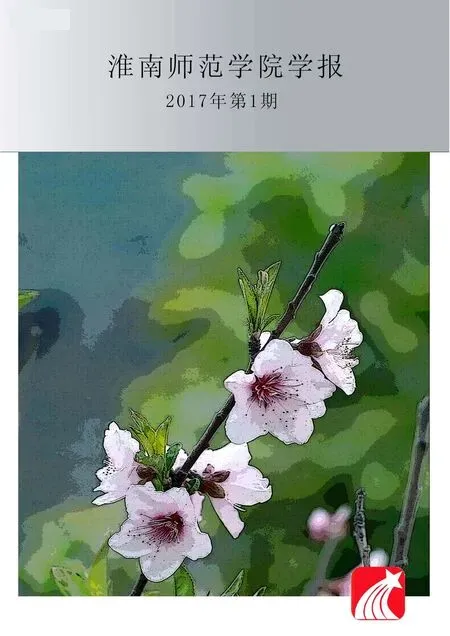18世纪英属西印度群岛院外游说团体研究
熊孜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1)
18世纪英属西印度群岛院外游说团体研究
熊孜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1)
18世纪的英属西印度群岛院外游说团体是当代政治游说团体的前身,它通过其组织良好的游说力量运作影响了帝国中心的立法并打破了原有航海法体系下英帝国殖民体系的平衡,最终与七年战争之后的帝国税制改革一起,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一大诱因。而了解这一往往为人忽略的诱因的最佳路径,是对西印度政治游说团体的组织发展、机能运作以及影响动员手段进行制度以及细节层面的考察,并进一步以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探究政治游说团体得以发展的条件。
英属西印度群岛;政治制度史;院外游说团体;英帝国史;航海法体系;18世纪英国史
在世界上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如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以及台湾等,利益团体游说组织都在其政治进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按照英国政治学家塞缪尔·芬纳对游说团体所下的经典定义,它们“以自己选择的方向去努力影响政治实体的政策,但它们并不像党派那样,能够对该国的政府产生直接的影响”①S.E.Finer,Anonymous Empire:A Study of the Lobby in Great Britain,Pall Mall Press,1966,p.3.。关于当代游说团体通过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政治决策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而本文则试图对游说团体这一政治现象进行溯源。一般认为当代游说团体源于19世纪初的美国,但事实上,它是大英第一帝国的遗产。早在18世纪,在英国庇护政治盛行的背景之下,各殖民地为了在帝国的殖民体系之下谋求更好的利益,通过组成各种利益团体的方式争取着帝国中心对其政策的倾斜。而这些殖民地利益团体中最为成功的,莫过于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利益集团。本文试图通过还原这段历史,来分析利益集团,或者说压力集团产生与活动的条件、方式以及影响,兼对航海法体系失序后的美国革命作出另一视角的解读。
一、西印度院外游说团体之起源背景
(一)18世纪英国的庇护制政治背景与航海法体系
追溯18世纪院外游说利益团体的形成历史,想要离开大英第一帝国的殖民体系这一语境是不可能的,但本文在此所需要的并不是铺陈罗列或者大而化之的叙述。切合这一问题发生的关键因素毋宁说是英帝国中心,也就是伦敦威斯敏斯特的政治运作状况与帝国的殖民体系特征这两点。首先来看英国本土:在1788年革命之后,英国人将原先集中在都铎王朝手中的权力进行分割,将其分给几个互相独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自治的机构。正如芬纳所说:“在1603年权力还集中在国王一个人身上,到了1714年,这种集中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灵活而复杂的制衡机制。从一个近似专制的君主制国家,英国成为一个贵族君主制共和国。”②[英]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三:早期现代政府和西方的突破),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9页。通过两院的制衡,国王通过议会统治(KinginParliament)在形式上已被建立。然而,国王的控制与影响力在18世纪长期统治英国的汉诺威王朝那里,仍然在事实上存在着。长期的战争导致政府权力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建立了巨大的管理新财政制度的机器,这直接地带来了大量新的庇护关系。1688年革命后的政府迫切需要在下院中赢得多数票,因此为了控制议会,更需要在议会利用这种庇护制。膨胀的官僚机构给了国王以更多资以利用的政治资源,即相对不受议会控制的行政人员薪酬,故通过金钱与职位对议会选票进行贿买的情况时有发生,它也事实上在国王和下院之间久已存在的鸿沟上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从而开始了一个行政权与立法权相互协调的新时期。①[英]肯尼思·O·摩根:《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90-391页。值得注意的是,下院的这种庇护的通道一旦被打开,就不可能仅为国王所用。在汉诺威王朝统治时期,无论是威斯敏斯特或是郡选区,庇护与腐败都是常态,②John A.Phillips,"The Structure of Electoral Politics in Unreformed England",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19,No.1(Autumn,1979),pp.76-82.并且随着英国的海外殖民活动扩张到各殖民地区。
在此还需对当时以重商主义政策为背景的航海法体系做一叙述。在之前漫长的17世纪里,大英第一帝国的蓝图已于现实中由伊丽莎白女王的重商主义政策及克伦威尔的宗教殖民热情基本确立。而查尔斯·达文南特、哈林顿等思想家则从马基雅维利的“世界君主国”的概念入手,结合英国独特的地缘环境,将以罗马为范本的陆地帝国概念转换成海洋帝国,从而在智识上为帝国的发展开辟了一片坦途。③[英]尼古拉斯菲利普斯,昆廷斯金纳主编:《近代英国政治话语》,潘兴明,周保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4-325页。而航海法就是帝国用以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最佳工具。它并不是指一部制定法,而是指由当时的多部法律构成的制度体系,其内容在地域上包括欧陆旧世界,也包括殖民地新世界,并随着殖民领土的扩张进一步拓展,在内容上则主要包括对船只,尤其是英国船只的垄断航运及贸易权利、英国及殖民地贸易、欧陆商品进口规定与税收,尤其是关税的规定组成。④Lawrence A.Harper,The English Navigation Law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9,pp.387-414.这一法律体系构建的最终目的在于限制英国的内外对手;对内则是帝国内部相对英格兰本土来说处于边缘地区的殖民地,限制各殖民地自主的工业发展以满足英格兰本土贸易利益是该体系的核心目的;对外则是针对欧陆以法国为代表的竞争对手,通过关税及航运垄断等手段保护本国市场是第一要务。在本文聚焦的内部殖民体系中,以爱尔兰、北美殖民地为代表,殖民地利益虽说并非无条件地被本土所榨取,但毫无疑问它们是为帝国中心服务的。⑤出于帝国中心利益对殖民地贸易、航运以及税收等多方面利益进行损害的例子汗牛充栋,在爱尔兰,破坏当地经济以适应帝国贸易所需的法案实施详情可见T.W.Moody and W.E.Vaughan ed,A New History of Ireland,Vol.4,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192-217.在北美,以汤申德为代表的印花税法体系是重商主义政策的最佳表现,可参见H.T.Dickinson ed,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London:Longman,1998,pp.26-27.尽管在18世纪晚期,已经有了亚当·斯密这样对重商主义政策提出抨击的思想家,但很显然,在现实中,18世纪正是帝国重商主义政策发展到顶峰的时候,这一顶峰直到美国革命之后才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反思。在19世纪中期之前,北美以外的殖民地想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就只能通过影响帝国中心的决策而为之。它们既无可能冲破航海法体系的束缚,又在议会中谋不到席位,在此条件下,利益团体及游说者方能产生并发展壮大。
(二)以蔗糖种植业为主的西印度殖民经济与社会
读过英国作家萨克雷的著作《名利场》的人,都会对小说中家财万贯的西印度女继承人斯沃尔茨小姐印象深刻:尽管这名“黑小姐”其貌不扬,言行粗鄙,但仍受到众多伦敦公子哥们的热烈追求。⑥[英]萨克雷:《名利场》,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二十至第二十一章。事实上,用这个例子来形容18世纪的西印度经济在殖民帝国中的地位非常恰当,由于蔗糖贸易的巨额利润,西印度殖民地确实在整个殖民体系中享受着众星捧月的地位。巴巴多斯、牙买加以及其他加勒比岛屿以其种植的蔗糖给大英帝国带来了其他殖民地无法望其项背的利润。以1787年10月至1788年的各商品带来的关税总值增长为例,该年度关税净增长为3789274英镑,但蔗糖贸易一项,增长值就达1195116英镑,将近总增长的三分之一。其他对关税增长贡献较大的商品如烟草(428768英镑)、葡萄酒(473485英镑)、丝绸(125738英镑)等都无法媲美蔗糖贸易。⑦Sir John Sinclair:The History of the Public Revenue of the British Empire,Part III,London:Nabu Press,2010, pp.122-124.乔治三西印度贸易的商人一起组成了在英国本土活动的政治力量。但它在创立初期并非以政治目的而成立的组织,非连续性的、大众的、群体性的政治诉求在其成立初期尚闻所未闻,最初的西印度驻英组织更多是为了扩大西印度人个人的商业机会所存在的社交团体,其时间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世纪。最早在英国设立殖民地代理机构的地区是巴巴多斯,其伦敦代理机构成立于1670年。其他西印度岛屿也纷纷步其后尘,比如牙买加伦敦代理机构成立于1676年、背风群岛代理机构则成立于1677年。⑤Lillian M.Penson,"The London West India Inter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36,No.1,pp.374-375.而这些早期的殖民机构,政治活动仅限于出于自身利益向殖民地政府、委员会以及城镇大会投书以陈明自己的观点而已,并未更多有组织的政治活动记录存在。这种情况直到1707年牙买加咖啡馆设立后开始慢慢有所改观,西印度殖民地代理机构开始利用自己的组织向贸易与种植王室专员施加影响,首次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潜能。⑥[特]埃里克.威廉斯:《加勒比地区史》,辽宁大学经济系翻译组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76页。Lillian M.Penson,"The London West India Inter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36,No.143,1921,p.376.
空有组织的雏形并不能预示这些殖民地组织未来的政治行动,要想组织起群体性的政治诉求活动,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公开的要求、申诉、批评或支持活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为公共生活舍弃一定程度上的私人生活,需要强有力的共同政治诉求。而西印度群岛团体以其独有的共同利益,高度组织起了自己的游说团体组织。究其共同利益,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驱逐外糖的急切需求,二是防止北美与爱尔兰与非英属殖民地进行交易,三是与组成压价同盟的英国加工商与零售商们作斗争。⑦Richard B.Sheridan,"The Molasses Act and the Market Strategy of the British Sugar Planter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17,No.1,1957,p.67.这三点综合起来,成为西印度团体的核心利益,究其动因则需考察18世纪的蔗糖贸易状况。在18世纪早期,英国本土的蔗糖消费要远胜其殖民地产出,而外国糖又因为航海法体系被排除在本土市场之外,故英国的糖价要高于欧陆,且由于欧陆他国生产蔗糖这一热带产品的能力之低下,使得高价的英国转运糖得以通行欧洲,故当时西印度蔗糖种植世曾因为看见西印度商人奢华的马车向皮特追问税收之事,这并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街头笑谈。①Wylie Sypher,"The West-Indian as a'Character'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Studies in Philology,Vol. 36,No.3,1939,p.504.在当时的英国人眼里,加拿大广袤的领土甚至不抵西印度一个小小的岛屿,它无愧于“英女王皇冠上的宝珠”之称号。
同时,由于西印度群岛独特的地缘环境与种植园经济特性等原因,其社会结构与其他英属殖民地相比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首先,西印度群岛主要依赖蔗糖种植园经济,而蔗糖种植业最为依赖的是大量的劳动力,故西印度群岛地区是英属殖民地中蓄奴最为严重的地区。岛上白人比例极低。1720年曾有法令控制黑白人种比例,设罚金以鼓励雇佣白人劳动力,但种植园主宁可交罚金也不愿意雇佣白人,故该法案竟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岁入法案,因为几乎所有的种植园主都需缴纳此罚款;②[特]埃里克.威廉斯:《加勒比地区史》,辽宁大学经济系翻译组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57页。其次,是西印度白人种植园主多不在本土经营的现象非常普遍。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几重原因:一是由于航海法体系的限制,西印度群岛本身所存有的产业非常单一,除蔗糖以外的制造业发展几乎停滞不前,更不用说其他文化教育产业的发展了;二是由于种植园经济的投机性以及高度的商业化特征,根本没人愿意在此安家。富有的西印度种植园主更愿意将财富带回本土购置产业或是挥霍,西印度本土并没有吸引他们的投资或者消费环境。西印度的人口结构及其较低的人口教育水平,使得他们很难像北美一样产生根植于本土的精英阶层,西印度社会的精英被吸纳到英帝国的中心,③同②,第178页。直至1770年有四分之三的西印度白人后代在母国接受教育。④同①。而这也是西印度人更加积极地参与本土政治事务的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
(三)西印度利益团体的产生
正如上文所说,加勒比海的蔗糖种植业是依赖大量黑奴劳动力而形成的产业。这些种植园主多半不在本地,他们将产业留给代理人打理,与英国做者得以大发其财。但自从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之后,法属西印度的糖产量大大增加了。在这样的因素影响下,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英国糖价经历了短暂的下滑,并使得盈利颇丰的英国殖民地糖转运欧洲贸易的比例从40%下滑到5%。西班牙王室继位战争之后,欧洲便宜的糖价对英格兰贸易的原有格局的冲击影响很大。①See ibid,pp.62-63.
上述情形给殖民帝国的贸易经济带来了些许变化:首先,外国糖与朗姆酒的引入使得英国中间人倾向于将原有的西印度产品去交换英国工业品制造品与便宜的法属殖民地产品,再将这些产品运往北美殖民地,并将法属殖民地产品按英属殖民地产品的价格卖(由于航海法体系的垄断性所致),蔗糖贸易从乌得勒支条约之后,并不掌握在英国人自己的手中,故当时有人认为,这种与法属殖民地的交易会带来短期利润,但会毁了种植业的未来;其次,原本北美与爱尔兰殖民地被航海法牢牢地限制在了体系内,被迫与英属西印度群岛进行于己无利的贸易,但这之后,北美与爱尔兰由于有了欧陆便宜蔗糖的输入,压缩了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间接地还提高了西印度群岛进口北美货物的价格,这让西印度人的利益受到极大侵犯;②See ibid,pp.64-66.最后是伦敦的蔗糖买家,尤其是加工者与零售商,组成了压价联盟。他们之后成为西印度种植园主攻击的目标。③Andrew J.O'Shaughnessy,"The Formation of a Commercial Lobby:The West India Interest,British Colonial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40,No.1,1997,pp.83-84.由此,可以看出西印度群岛利益由于帝国命运的变化,特别是乌得勒支条约的变化,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此情况下,原有的非政治性组织开始借助共同的经济利益形成共同的政治话语,并开始尝试对帝国中心产生影响。
二、西印度利益团体的组织要素与动员手段
西印度利益团体在18世纪有过两次伟大的政治胜利,一次是18世纪30年代,以1733年糖蜜法(MolassesAct)为代表的蔗糖产品税调整;之后便是“七年战争”后的1764年糖法(SugarAct)的颁布实施,这一举措确立了西印度群岛在英帝国内部市场中不可撼动的地位,并成为美国革命爆发的诱因之一。而这些政治与立法成就是与其政治组织的发展以及影响动员手段密不可分的,这里将先对其组织要素进行分析,进而以其影响帝国内部贸易平衡的两次重要的斗争胜利为例加以叙述之。
(一)西印度群岛利益团体的组织发展
当代利益团体理论中经常提及“搭便车”与“资源问题”,这都是因为一个利益团体中不可能所有的成员都同仇敌忾,在一个利益多元的组织结构里,总有一部分成员为组织负担较大的运作成本,而另一部分人在以较小的成本坐享其成,甚至会因利益分歧而加大组织运作的成本与施加影响的效率。④关于利益团体理论的综述,可参见Kay L.Schlozman,Who Sings in the Heavenly Chorus?The Shape of the Organized Interest System,in L.Sandy Maisel&Jeffrey M.Berry 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Interest Group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428-430.毫无疑问,西印度利益团体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的分歧主要在种植者与商人之间、新旧殖民地之间、本土种植者与在外种植者之间以及英国本土港口利益相关者与外港之间等,但最主要的分歧还是种植者与商人之间的冲突。⑤同③,第74页。举例而言,背风群岛就常与其他英属西印度岛屿产生利益分歧,因其更加依赖对北美大陆的贸易,故在多次政治行动中会表现出更加亲北美殖民地的一面。⑥Andrew J.O'Shaughnessy,"The Stamp Act Crisis in the British Caribbean",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Vol.51,No.2,1994,p.204.商人与种植者利益在某些方面是分开的,比如说对奴隶贸易征税,其实价格负担转嫁的对象是种植者而非商人,故关于此事务的会议,商人并没有发言。⑦同⑥。但是,西印度群体并没有像其他群体那样,往往受党争内斗而困扰,其原因有二:一是西印度利益团体并非单独存在,西印度群岛利益团体也同样隶属于一个大的殖民地利益团体,而殖民地团体又被更大的英国议院外利益团体所囊括,⑧Lillian M.Penson,"The London West India Inter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36,No.143,1921,p.378.故种植园主与商人常有共同的敌人,这让他们可以在某些重要的斗争情境下忽视这种内部的利益分歧;二是其组织机构所致。西印度人比其他殖民地的游说者更早拥有完整的组织,有选任的组织与职能人员,并且薪酬独立,这让该组织很大程度上能够摆脱由一方利益把持的局面,而保持相对的独立性。①See Ibid,pp.383-384.高度的组织性特征是西印度群岛在18世纪的一系列斗争中获胜的重要因素。
具体而言,一个成熟的政治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职业的代理人,而非利益相关者本人,因为后者很可能由于缺乏政治技巧或者狭隘的利益偏见而不能成事。西印度利益集团从非正式团体慢慢转向有组织的团体,并开创当代经济利益团体之先河,在当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有薪酬的说客之雇佣。当时的西印度驻伦敦代理机构,已经出现了对这种专业说客的雇佣行为。将这种人群纳入团体任职,重点考量的不是他们与西印度群岛的血缘联系,而是他们的政治资源与技巧,这在某些方面称得上是当代游说团体的前身。②Andrew J.O'Shaughnessy,"The Formation of a Commercial Lobby:The West India Interest,British Colonial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40,No.1,1997,p.72.当然,这种政治团体的职业化并非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随着18世纪英国官僚机构的快速膨胀、纯粹私人关系的影响会遭到官僚机构的层层阻力所致。故若无职业说客,便仍稍嫌无力。职业说客与私人影响的施加能够双管齐下地发挥作用,这在1769年由威尔克斯运动带来的反政府游说运动高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③See ibid,pp.76-77.追究这一组织发展的原因,与西印度群岛对英国政治力量倾斜的极端依赖有关系。蓄奴、航海法与关税、法国人可能的侵袭甚至飓风问题,都会很严重地影响当地经济,但解决这些问题的良方并不在本土,而在于帝国中心。故事实上,西印度群岛利益团体要比其他利益团体具备更大的政治动力,加之他们的财富能带来的政治资源,这种组织上更胜一筹的发展也就不奇怪了。事实上,此时段的西印度团体经历了从私人利益性质的咖啡馆组织性质到政治抗议群体再至职业化政治游说机构的三段式飞跃。待到七年战争之时,西印度商人协会已然成长为有会长、秘书与出纳,能积极地为商业利益而奔忙,并处理包括关税、运费、贸易与安保等事务的专业组织了。④See ibid,p.79.相比之下,其他地区的游说机构甚至还停留在政治抗议群体的阶段,故在组织上就相对落后,而这也是西印度利益团体能够达成下文所述诸多手段的一个重要的组织保证。
(二)西印度群岛利益团体的影响动员手段
当代学者对游说团体的策略进行过类型化的分类:大体上,利益团体的策略可分为较直接的影响大臣或是议会议员与较间接的影响舆论与公众意见两种。⑤J.D.Stewart,British Pressure Group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28.在我们所关注的这段时间内,西印度群岛利益团体也有综合利用上述策略的表现:请愿、有组织的院外压力和全国性的教育运动都可以影响政府和议会。首先来看前者,18世纪时各个院外集团通向议员个人的门始终是敞开的,议员或是代表他们提出请愿,或是支持私人提案。组织十分良好的压力集团,无论是经济性质的还是宗教性质的,都可以影响政府的政策和议会的决策。⑥H.T.Dickinson,The Politics of the People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 1994,pp.208-210.影响议会议员或是大臣,可以通过私人关系来施加影响,这一点对院外团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私人晚宴不止是团结本岛商人的方法,也是在庇护制政治背景下对议会施加影响的重要渠道。另外,有组织的游说活动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西印度商人集团会会在威斯敏斯特对可能接受他们影响的下院议员进行游说,其方式包括写请愿书与直接的游说活动。需要提及的是,这种直接影响的方式需要大量的金钱方能保障实施,但这恰恰是西印度人的优势。
对于后一种相对间接的影响手段,西印度利益团体也利用颇多。利用舆论在言论自由得以保障的18世纪是一种普遍的政治影响手段。《公报》(Gazetteer)、《每日广告报》(DailyAdvertiser)等大众媒体是西印度人常用的武器。⑦Lillian M.Penson,"The London West India Inter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36,No.143,1921,p.388.除此之外,付印小册子的手段也被广泛应用在1740年代糖税调整以及1770年代争取殖民地贸易运输税率斗争上。⑧See ibid,pp.380-386.舆论作为一种斗争策略并不能对当权者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可以被西印度集团用来确保他们的声音被当权者听到。在公众影响上,西印度群岛团体在18世纪60年代之前都未曾听说有过有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公众抗议事件、骚乱、冲突或集体行动,而这些活动是其他政治团体所善用的。西印度群岛在这之前更加擅长的是非正式的私人关系渗透。但在18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帝国税收体系的收紧以及海外战争的潜在威胁等不利因素的加强,西印度群岛群体开始认识到仅仅对政府和议会产生非正式影响是有不足够的。在1769年的威尔克斯运动的影响下,西印度群体也开始寻求自己斗争策略的转变,更掀起了一股反政府游说运动的高潮,在此之后,各地利益团体都在转型,而西印度由于其碰到挑战的急迫性,则变化得更快。①Andrew J.O'Shaughnessy,"The Formation of a Commercial Lobby:The West India Interest,British Colonial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40,No.1,1997,pp.76-77.
三、西印度群岛利益团体的两次重要胜利
(一)18世纪30年以糖蜜法为代表的政治斗争
为了捍卫大英帝国这一对西印度人来说不容侵犯的市场,西印度人并非仅仅选择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吵大闹,早在1715年,他们就有过本地立法的尝试:时年巴巴多斯立法对外部货物进行限制。1756年牙买加甚至试图通过一条法案,其中规定运贩外国商品的都是重罪,应当在处以死刑并剥夺牧师予以祈祷的权利。这一刑罚显然过重,以至于枢密院死活没有通过这条法案。②Richard B.Sheridan,"The Molasses Act and the Market Strategy of the British Sugar Planter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17,No.1,1957,p.68.但西印度人显然明白:仅有本土立法,在这样一个帝国殖民体系内会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只有帝国中心的立法风向变化才能带来实际的好处。为此他们在18世纪30年代为糖蜜税的调整了贡献了非常多的力量,而这首先是与其组织的发展完善脱不开干系。
1733年的糖蜜法是一次西印度人谋求垄断北美殖民地糖类产品市场的尝试。为此,已具备日常运营政治组织的西印度人向议会情愿,并游说议会和提供必要的证据,使下院议员确信非常有必要向不列颠北美殖民地进口的外国糖、蜜及朗姆酒征收高额关税。在1739年,他们成功地游说议会通过糖法,这一法案允许西印度公司不用首先在英国港口停泊就将产品运往南欧。尽管其他的英国商人对此激烈反对,他们担心这会减少西印度对英国制成品的需求并提高英国国内食糖的价格,但这一法案仍最终获准。在四十年代时,当政府提议提高进口食糖的关税时,西印度的商人们便发起一项运动进行抵制。他们反对增税的理由被印成小册子,并把副本寄送给每一位下院议员。这些副本也被散发到遍及英国的所有港口,而且将与此有关的主要论点都登载在《伦敦晚邮报》上。西印度商人集团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之间不断走动,以游说那些特别有影响力或者对他们事业呈友好态度的下院议员。③H.T.Dickinson,The Politics of the People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 1994,pp.65-67.最后,这一系列组织良好的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33年蔗糖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立法强化了西印度的国内市场垄断,使得帝国内部原有的贸易平衡向西印度倾斜了不少,是西印度游说团体发挥作用的经典时刻。④Lillian M.Penson,"The London West India Inter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36,No.143,1921,p.374.
1733年是西印度群岛利益团体的第一次议会胜利,他们由此得到直接(不用经由英格兰转运)向爱尔兰运贩商品的立法,尽管这一立法是在北美殖民者的强烈反对下完成的,而这也为之后的殖民地之间的斗争埋下伏笔。之后,西印度群体甚至谋求直接向欧陆市场出口的权利。当1739年法案被最终提交到议会时,各大工业城市代表都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会导致北欧工业产品对殖民地的倾销,不利于英国本土工业制造品的销售。为此,伦敦蔗糖加工商还组织了请愿以反对该法案,但它最终还是得以通过。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西印度群岛组织已经成为卡特尔那样的垄断组织,他们无力控制价格,但通过这些改革能够有效地通过威胁要将糖运往国外以使国内的加工商与零售商付更高的价格。事实上,海关记录证明,即使在这些法案被通过之后,运往国外的货物也很少,但在国内市场取得的胜利确实是毋庸置疑的。除在国内市场,殖民地市场方面西印度群体成功地把握了爱尔兰市场,使后者在1733年之后变为西印度人最重要的市场。而爱尔兰在遭遇这种由航海法正名的损己暴行之后,开始与北美殖民地一样,出现了大量的走私。在1707联合法案之后,苏格兰也加入了航海法体系所保护着的市场。在1732年之后,格拉斯哥成为与西印度贸易的重要港口。北美也同样是被强迫的西印度市场。北美对印度糖的消费量日益增大,同时非法贸易也在大量增加。⑤同②,第72-78页。
(二)七年战争带来的英帝国殖民地结构变革与1764年糖法
“七年战争”是一次影响英帝国殖民秩序并导致其重新洗牌的标志性事件,之所以它能产生如此影响,其原因是与之前的殖民地经济秩序分不开的。30年代以糖蜜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立法已经确立了英国对西印度群岛的政治倾斜。上一节已经提到,由于北美与爱尔兰等在帝国中心看来更为不重要的地区被航海法体系所束缚,以至于大量走私犯罪涌现并试图冲破这一体系,于是在七年战争时期就出现了在英国人看来不可弥补的问题:以北美作为主战场的英军,发现大量的北美殖民者在从事与法属西印度群岛从事蔗糖走私贸易。这种走私行为的危害不止是侵犯国家财政岁入,在英国人眼里看来更是一种通敌的叛国行为。①H.T.Dickinson ed,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London:Longman,1998,p.40.北美殖民者们这种通过法外方法以求生计的方法在战时被无限放大,加之英国战后的财政危机,成为糖法以及之后的印花税法案等税制改革的重要诱因,而这一诱因是与西印度团体之前在糖蜜法生效时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糖法是为这种失序而进行的弥补措施,其出发点在于英法的贸易竞争,事实上是英国两块殖民地利此薄彼的调整。北美与法属西印度群岛是攻击的目标,英属西印度蔗糖种植园主与北美的利益总是相对的。试图对北美进行更严厉限制的糖法遭到北美殖民者的强烈反对,如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长期居住在英国的富裕美洲人曾为此进行游说,但很显然,北美殖民者在英国的政治游说要比西印度群岛的糟糕很多。尽管北美的游说组织不是完全没有成就,但他们并不能对威斯敏斯特发挥像西印度群岛组织那样重要的作用。②H.T.Dickinson,The Politics of the People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 1994,pp.76-77.相比之下,西印度群岛驻伦敦代理机构在七年战争之后数量激增,这些机构在税法危机、美国独立战争以及之后的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入侵威胁等事件中都发挥了作用,如西印度商人协会这样有影响的组织在英国殖民政策的形成上贡献卓著。③Andrew J.O'Shaughnessy,"The Formation of a Commercial Lobby:The West India Interest,British Colonial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40,No.1,1997,pp.78-79.由此,他们再一次在英国航海法体系这一背景下取得了胜利,西印度人垄断了整个帝国的蔗糖与蜜糖贸易,并加重了对北美走私者的限制。按照当时波士顿商人的说法,1764年糖法是:“……因西印度种植园主们的利益而铸成的,除了填满他们的钱包以外没有别的作用,而这是通过迫使北方殖民地的人以他们的给养来填补他们的胃口来实现的。他们还想为这种行为找一个借口,说他们是以自己的货物来供给大英帝国及其殖民地,真是荒唐至极。”④Sir Lewis Namier,England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63,p. 239.虽然言辞激烈,其对情境的描述确是无误。
四、余论
有学者质疑过西印度游说团体对当时英国政治产生的作用,认为有被夸大之嫌。因为其实西印度人想要做的事,正是英国政府早已有此意去完成的事,故看起来西印度游说团体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⑤同③,第93页。此观点的合理性根植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帝国的哪个部分执行以航海法为代表的重商主义原则执行的最好,那就是西印度群岛。之所以西印度利益集团能够在18世纪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其与英国帝国中心利益的内在契合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哪怕是有50个议会相关者,在500多议员的下院中其实也不能做到呼风唤雨。西印度群岛团体在美国革命之后,组织发展更为完善,却未获得之前那样的成功,它在1783年试图与新兴的美国恢复贸易的努力就没能实现。⑥See ibid,pp.93-94.其背后的原因恰恰是因为西印度群岛所占的地位,它是帝国力量与财富的重要来源所致,而非其组织的优越带来的直接结果。
上述观点其实揭示了利益游说团体的另一个面向,一个较容易为人所忽视的面向。利益团体从来不能单独地自下而上发挥作用,按照艾森斯塔得的解释,统治者会将自己所需水平的普遍化权力纳入通道、使之定型并加以维持其深切关注。⑦[美]S.N.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闫步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6页。英国于1688之后确定下来的议会政治形式是利益群体于1688 之后确定下来的议会政治形式是利益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天然土壤,但如果没有统治集团急需的政治、经济、文化或是军事资源,其组织在政治斗争的竞争环境下缺乏支持,也必然会相对较弱,这一点在上文所阐述的历史中可以得见,西印度与北美在航海法体系下的争执是最好的明证。利益团体组织的政治活动与角色之分化与发达程度、与中央政治的联系以及精确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程度与其成败皆有联系,需依具体情境判断,不可一以概之。
在政治游说团体在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的今天,追溯西印度群岛利益团体这一前身的历史并非没有意义。它是一种潜在的政治权力,在议会政治的土壤中被纳入了正规通道,这种政治诉求的形式尚在确立之中,但这种政治的创新形式的不断积累最终将使这一看似混乱的政治剧目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最终导致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①关于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的概念,见[美]查尔斯.蒂利:《政权与斗争剧目》,胡位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53页。以往的斗争历史仍在影响着当下的斗争实践,并持续不断地对其制度化然扮演重要角色的今天,追溯西印度群岛利益团体过程,也就是相关立法过程产生着影响。
Research on the lobbying groups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an island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XIONG Zi
The lobbying groups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an island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re the predecessor of modern lobbying groups.Its well-organized operation of lobbying power affected the legislation of the center of the empire and broke the balance of the whole colonial system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English navigation laws.Together with the taxation reform after the Seven Years’War,it became a trigger of the American Independent War.Observation on its development,function,and means of mobilization may be the best way to study on this issue.The inquiry with social economy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conditions of it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s also necessary.
British West Indian islands;history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lobbying group;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 navigation laws;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909
A
1009-9530(2017)01-0011-08
2016-11-27
熊孜(1987-),男,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法律史、西方法律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