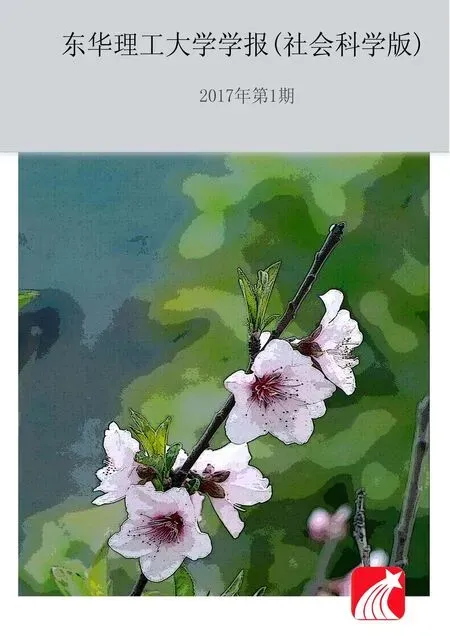抚州采茶戏在新时期的发展思考
李 坛, 廖夏林
(东华理工大学 艺术学院,江西 抚州 344000)
抚州采茶戏在新时期的发展思考
李 坛, 廖夏林
(东华理工大学 艺术学院,江西 抚州 344000)
通过对抚州采茶戏这一地方剧种的发展剖析,努力探究放下历史包袱,与时代相接轨对于传统戏曲改革的现实意义;进而折射出观念更新的艰难与必要性。换位的思考、审美的与时俱进,这些既是改革进程中应有之艺术举措,更是在当代社会流行文化潮流中的有益尝试。
抚州采茶戏;发展;表演;审美
李坛,廖夏林.抚州采茶戏在新时期的发展思考[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6(1):4-8.
Li Tan,Liao Xia-lin.The development of Fuzhou Tea-Picking Opera in the new period[J].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7,36(1):4-8.
近日阅读叶秀山先生《古中国的歌》一书时,看到京剧声腔与字音的章节,不由得按捺不住对于当代抚州采茶戏表演及创作领域一些现象的担忧,于是就有了以下诸多文字。若有不当之处,请各位专家与同志予以指正。
1 抚州采茶戏的发展简述
作为临川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地方戏剧种,抚州采茶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近三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从早期的民间戏班形式“三脚班”、“半班”,到建国后的专业戏剧表演团体,它的历史,恰如一个农家少女向城市家庭妇女的转变,可以用三个成语来代表它的前后三个发展阶段,即是:饱经风霜——绚丽多彩——垂垂老矣。
饱经风霜,这个词对于抚州采茶戏的成长阶段来说,似乎有些过重了。但很符合抚州采茶戏萌芽之时的社会写照。抚州采茶戏是在清初诞生的,它肇起于抚州民间小调与灯彩等民间歌舞形式的迅速结合。关于这点,由于笔者手头的史料不多,暂将已有观点罗列如下:(1)东华理工大学的黄建荣与高赟两先生所作的《抚州采茶戏发展史》一书第6-7页:“到清康熙、乾隆年间,湖北的大批灾民进入赣北、赣中、赣东,带来了黄梅采茶戏的‘三脚班’……这便是最早的抚州采茶戏。”(2)武汉音乐学院的刘正维教授所著《20世纪戏曲音乐发展的多视角研究》第87页提到:打锣腔是一个涉及近四十万平方公里内,一亿多人口、八个省区几十个剧种的戏曲声腔系统,其所涵盖的剧种中即有抚州采茶戏。这其中,南昌采茶戏与抚州采茶戏和高安丝弦戏与瑞和锣鼓戏的主要腔调称作“湖广本调”,亦称为“本调”。
以上两点如果对照来看,则后一则材料中的“湖广本调”(本调,后文皆采用该简称),可推断为是由前一则中的“湖北的大批灾民”传播至抚州地域的。从前后因果关系来看,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只是,笔者仍然有些疑虑:既然以“本调”为主要腔调,为何在京剧中大行其道的“湖广腔”在现在的抚州采茶戏之音腔使用中渺无痕迹呢?
诚然,地方戏的最大特点之一便是使用其当地的方言作为唱词与宾白的语言系统,然后只取外来的音乐系统,声腔系统则弃之,这个现象确实值得我等思虑。
进入民国以后,抚州采茶戏逐渐进入了一个较为蓬勃的发展时期,知名的如1934年由崇仁籍采茶戏艺人张佑民创办的抚州采茶戏第一个职业班社“佑民堂”,还有之后1938年临川本籍的周仙斋与张佑民等共同创办的“筱仙台”,其他的“抚采”班社也如雨后春笋般陆续组建。必须指出的是,班社的组建并不意味着新阶段的开始,真正标志着新阶段开始的,则是由于连台本戏——即完整剧本的上演与剧种演唱腔调的正式成型。在20世纪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抚州采茶戏一直是和傀儡戏、抚州大戏等其他本土剧种同时存在发展的,在这种你中有我、百花齐放的环境与封建时代末期的时代大背景下,抚州采茶戏可以拔中头筹的资本,正是在于借鉴与吸收其他剧种中的腔调与表演技巧,以其适合于抚州采茶戏的腔调演唱以及表演的有利部分融合进本剧种,从而“后来居上”,在观众群体的争夺上拔得头筹,并最终成为抚州地域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戏剧种。前人也好,后人也罢,符合时代欣赏风格的剧种总是受人喜欢,这与京剧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其实如出一辙。同时也再次证明了:只有不断地对现时文艺流行思潮进行总结和以之为准绳,才能使得传统民间文艺焕发出绚丽的新彩。
对于民国时期的抚州采茶戏发展,现在只单单限定于几个人名与一般的班社历史上,而没有去做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这点是抚州采茶戏历史研究上的一个短板。笔者未来将花时间重点在此领域做一定的搜集整理,以期能够为抚州采茶戏的剧种系统学术体系之建立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新中国建立以后,文艺领域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一道开始了其迅速而又缓慢的进程。1952年,全国戏曲改革以当年十月份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拉开了序幕,虽然整个过程很快结束,但实际牵涉到各个剧种本身的转变,那又千差万别。整个改革的方针是“先内容后形式”,也就是说,首先从剧目上就要消除以前存在的封建糟粕等与社会主义主旋律不符之相关内容,然后再从剧种的各个细节如旋律等方面加以改进。不过总体来看,基本上是以京剧为原型学习对象,包括唱腔扮相以及剧目移植等诸方面都是从前者身上进行嫁接等。所以,新中国以后的抚州采茶戏,其必然与解放前那种非系统、非条理化的局面有很大的不同。
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文艺是政治的风向标,自然也就有所反映。抚州采茶戏在1958—1982年之间较知名的剧目有《红松林》以及八个样板戏改编而来的《沙家浜》《秧》《平原作战》等。其中《红松林》一剧在全省颇为出名,亦为抚州采茶戏之名剧。
改革开放以后,抚州采茶戏的创作方向也发生了转变,除了与时代相接轨,也保持了对传统农村题材以及历史的关注与回望。在1982年之后的创作剧目中,既有反映农村新时期发展变化的《翠竹青青》,又有以1949年国共决战为创作背景的《残霞》。客观地说,由于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文化消费习惯与种类也随之多元化。因此,抚州采茶戏整体来说是走向了一个比较低靡的发展区段,但是在农村地区的受欢迎程度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水准。世纪之交的时候,当时的抚州市采茶剧团为参加第十一届全国群星奖而编排的现代农村题材剧目《县官下乡》,应该说是回归了抚州采茶戏的灯彩小调的原本特色的,它以获得当届群星奖金奖的事实告诉我们:对于地方剧种,只有抓住反映其地域文化与艺术美学特点的本来精髓特质,才能获得群众的真心喜爱与热切响应。之后由著名抚州采茶戏表演艺术家潘凤仙女士担纲的独角剧目《王妈妈爱鸡》又一举斩获第十三届群星奖之小戏金奖,从当时比赛现场的录像实况可以看到,即使是对临川文化不太熟悉的浙乡民众都被表演的生动与活灵活现逗得乐不捧腹,可以再次印证笔者这一观点。
在这里,笔者在欣慰之余,对于抚州采茶戏在新时期的现状不甚担忧。首先,专业的地方戏曲团体由于改制等原因而出现解散等现象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作为政府职能主管部门的各地文化局在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多是在一些诸如手工艺或者更确切地说,“迎合GDP”方面,以满足政绩好看为主要宗旨,而不是切实地从对地方民间文艺的扶持中去感受其对于传承本民族文化精髓之重要性。因此,必须尽快扭转这种“为政绩而艺术”的文艺发展指导思想,才能避免那种“唱戏就是跳舞”的错误观念继续流传或者在文艺指导政策制定中的“阴魂不散”。
2 与大剧种比较下的换位思考
现在抚州采茶戏的舞台表演情况,与上世纪相比,为了适应时代而有了诸多变化。对于这些变化,笔者也有些个人感想,愿与诸君共勉。
现在的中国传统戏曲为了吸引青年观众,在舞台上大搞“声光电”,更加强调氛围营造,这种做法本无可厚非。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强调一些所谓的“形象” 、“场景”,却于表演之本身这一真正体现剧种之精华所在的部分没有去认真地琢磨与下工夫,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1]。就拿我们抚州采茶戏来讲,近年又重新开始编排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据笔者所知,主要还是围绕其中的《牡丹亭》来做。综合媒体报道与一些专家学者的评价,似乎“华服美景”成为老戏新排的亮点乃至重点。相比较的是,演员的表演功底尤其是演唱水平等与剧种发展密切相关的实质性因素却在诸如“排练刻苦”之类的大话、套话中一带而过地被忽视,这或许只是笔者的“杞人忧天”。
我们知道,京剧的成长与发展史上,汉剧、秦腔与昆曲都有它们的贡献。这里不是说其他剧种没有出什么力,而是指这三个剧种在京剧的形成关键期所给予的客观结构骨架搭建是至关重要的。其一,即是指老三鼎甲(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在“徽汉合流”时的首要之功;更主要的还是后世包括“汪、谭、孙”以及梅兰芳、余叔岩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们在各自表演中对其行当从唱腔、扮相等诸方面的探索与充实。而这种探索与充实,恰恰就是在他们不断借鉴包括声腔(中州韵与字音)、表演程式(其他剧种相同行当之身段手眼的优势模仿)等有利于京剧发展的宗旨上进行的。再拿黄梅戏和越剧两剧种来说,这两个剧种的成型都是在上世纪初,较抚州采茶戏的成型年代还晚;它们在各自的发展中,一是演员们注意到了从其他剧种中借鉴声腔“为我所用”。其次是在剧目和演员的性别上,注意到了当时观众的欣赏习惯:黄梅戏的剧目多是一些宫廷与民间神话戏,同时又考虑到了徽州地域的方言音韵,因此黄梅戏的唱腔就逐渐向甜美与京音化的方向转变,乃至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黄梅戏电影《天仙配》问世后,带动了一股“黄梅调”风潮流行于港澳与东南亚华人区[2];而越剧从浙江绍兴嵊州发源,本是男班,在流传到上海后,除了在板腔体音乐的引进和音乐伴奏的职业化上进行了创新,更重要的则是确立了以女性演员为主要从业人员的传统。这是与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市民欣赏习惯分不开的。
这两个剧种直到今天的发展态势,都要比抚州采茶戏好,其原因在哪里?前文已经谈到了包括借鉴融合、欣赏习惯等几个因素,这里再谈谈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这些所谓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在笔者看来,颇存担忧。
当前对于音乐伴奏,许多地方戏都开始大量地采用电子音乐这一新方式。一来可以节省伴奏人员的舟车劳顿与费用支出;二来可以创造出比较完美的伴奏音乐,不会因为伴奏人员的参差不齐等客观原因进而导致演出或者编排的进度放慢。这两个优点从时间和效率上来看的确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从传统戏曲的艺术美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短视的做法。殊不知,传统戏曲之韵味恰恰在于其“味”,电子音乐是好,音色纯正,节奏精确,但是恰恰把那种人工的“呼吸感”以及演员之表演中的可操控感取消了,反过来成了“伴奏的演员”,而不是“演员的伴奏”。而这点上则是那些鼓吹传统戏曲新发展的人们所容易忽视而撇开的,最终结果,人们在观赏表演的时候,会被这些次要因素所分散注意力,而演员的演唱这一根本要素反而不太为观众们去认真赏韵。同时,由于电子音乐是固定的,而不似人工伴奏那样随演员的演唱而“进出有序”,整个表演俨然成了以电子音乐为纲的一台演出,演员无法施展他(她)的临场发挥,他(她)只是这个调校好的演出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按部就班。我想,没有哪个真心热爱抚州采茶戏的观众希望看到的是这样的表演。
那么是不是就不要电子音乐了?当然不是。前面已经说过,任何传统剧种的发展,都是要符合时代的欣赏习惯的。同样,艺术美学的宗旨也不能丢。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既能够与当代文艺潮流不脱节,同时又保持抚州采茶戏的原汁原味。
3 新时期剧种发展的几点建议
从中国戏曲的一般美学观点来看,抚州采茶戏的感性美相对于理性美即内容美更为重要。因此,形式上的强调是必然的。这种形式美不是说“美女如云,绚丽夺目”,它的关键在于一种从演员演唱以及舞台表演程式中散发出的韵味之品。大凡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在忆及当年孩童时期看戏的点点滴滴的同时,感叹演唱之旋律是如何如何的沁人心肺,打动感情。这种回忆的根基恰在于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幼年的真切记忆往往是伴随一生的。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角度来看,随着年轻一代,尤其是80、90后逐渐成为观众阵容的主体,如何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的确是现阶段比较普遍的难题。其实,人的好奇心是可以转变的,至于促成转变的方法,笔者略述己见以为之观。
正如昆剧青春版《牡丹亭》在全国的风靡一般,我们同样也可以打造出抚州采茶戏的“青春”。时下普遍的观点是青年人不喜欢这种慢悠悠的文艺品种,而昆剧的思维开拓所获得的成功则在于其在立足于传统形式美的同时,又以年轻观众之好奇心为有利契机,将好奇转变为“惊奇”,再通过演员与观众之间台上与生活中的双向交流,打造出一个昆曲艺术推广的好环境。回归我们抚州采茶戏,其前身就是湖广调与民间小调的融合形成,因此,重新凸显其民间活泼以及抚州乡土特色这两个特质才是首要的根本所在。当然,这种活泼的乡土特色最好与现代音乐元素去有机结合[3]。例如笔者在为抚州采茶戏进行的数次音乐配器工作中,感觉到一点:电子音乐伴奏最大的缺点即是没有现场伴奏所独具的那种呼吸感,这种呼吸感从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决定了戏曲之艺术感情对观众之影响的最大魅力所在。因此,在配器过程中,笔者在制作音乐的同时都会加入一些体现抚州采茶戏特色的人工乐器伴奏,如高胡等弦乐器之音色。这样,在保持戏剧伴奏音色丰满优美的基础上,又不失抚州采茶戏之为“抚州”采茶戏的地域乡土特色,从而使“传统与发展并重”的观点得以保持与维护。高胡作为南方尤其是赣粤两省的多个戏曲种类所常用的乐器,其地域特色是十分鲜明的。在抚州采茶戏中,它往往又是作为旋律乐器被使用。通过这种“新+旧”的组合尝试,抚州采茶戏的音乐形态也从一种单纯的民族小乐队伴奏向全方位的中西混合“乐队”制式转变。
前面提到时下普遍青年人不喜欢的观点,这要从两方面来看。其一,从音乐风格上来说,从小就在流行等现代音乐风格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们,他们的欣赏思维定势的转变的确是不容易。所以,在剧目创制与旋律写作上,笔者建议,不妨也来个中西嫁接:第一步,现在的抚州采茶戏剧目,虽然不全是“才子佳人,生离死别”,但真正能够反映当代现实尤其是青年题材的寥寥无几。因此,文学工作者们应该从作品编创上写出反映当代青年真实生活内容的作品出来;第二步,虽然地方戏曲的旋律由于程式化与声腔板式的传统限制,在改进上的确不易,但是,我们不妨从西方综合艺术门类的角度——如音乐剧电影,在其中歌剧、音乐剧等多种声乐种类是可以“和谐共存”的,这样延伸性思维下去——采茶戏里面难道就不能有流行歌曲,或者音乐剧里面就不能有采茶戏唱段么?诚然,思易行难,但笔者坚信,只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不被那些传统思维过度束缚,让青年观众耳目一新、为之一振的好作品是完全可以创作出来的。
其二,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也给予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不是说青年们不喜欢依依呀呀吗?为什么还如此深受青年学子们的热捧?这一现象的背后,恰恰可以反映出传统文化那持久而又深藏于其内部的精神魅力。当然,这一魅力的重见天日,一来,源于白先勇先生的不懈努力;而更重要的,则是前文笔者所强调的“艺术推广的好环境”。笔者在本文动笔之初,无意中接触了日本冲绳新民谣这一民族艺术品种。而它目下兴盛的发展状况,则正好可以给我们发展自己的地方文艺品种以有益的启示。这其中,环境的外部因素支持,是冲绳新民谣这一在古老冲绳传统音乐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变种能够得到可持续性发展的最大使然之因。而笔者也将在未来对该一题目做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期能够用之于己,使得抚州采茶戏的发展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光有以上两方面的措施,显然还不够。俗化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中国戏曲在舞台上的华丽表演背后,往往是演员们十年乃至数十年的辛苦训练所造就而成的。演员队伍的培养和后续接班人的训育是当前制约抚州采茶戏发展的最大问题。由于事业单位改制的大背景,全国大多数的地方专业戏剧院团都进入或者已经完成了改制过程,或变为企业,或转为“非遗中心”。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大多数的改制成果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也不乏例外。抚州采茶戏的唯一专业团体——原临川区抚州采茶戏剧团的改制情况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败笔。在老一辈演员们相继离开舞台后,由于种种原因,新的血液没有得到补充,表演人才的挖掘工作没有坚持下去,而这恰恰是抚州采茶戏赖以维持的重要条件。在分成“非遗中心”和演出公司两个实体①由于文章初创时间所限,上述单位已被新的“临川区抚州采茶戏传习所”所取代,特此说明。后,整体状况对于抚州采茶戏的未来并没有起到一丝能够看到希望的有利作用。反倒是以歌舞为主业的抚州采茶歌舞剧院“反客为主”,成为现在唯一能够勉强担负抚州采茶戏正常演出的专业表演队伍。反观前文笔者所谈到的有关剧种发展实质性因素的担忧,却也不失为一种希望抚州采茶戏有可能重现那昔日辉煌的善意讽刺。
从现在的实际可操作情况来看,笔者建议,可以依托职业类教育机构,从职业教育方向起步,培养抚州采茶戏的后备力量。在抚州现有的职业教育机构来看,抚州职业技术学院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学戏当从娃娃抓起,因此,少儿时期的早期启蒙是极为重要的。限于篇幅关系,笔者未来将另起专章以探讨人才培养问题。
昆曲大师汪世瑜先生2013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青年观众的培养,提出了一些对策,笔者认为很好。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提升昆曲的普及:首先是进校园开讲座,二是公益性演出的举办,最后是跨界收徒[4]。这三个点子其实对于抚州采茶戏的发展来说,都可以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现在的大学生虽然都比较强调自我,但是并不能低估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能力与喜爱程度。虽然抚州采茶戏没有昆曲那么雅,但是作为乡土文化、尤其是临川文化的一面活镜子,它同样有对历史的承载与传统道德的体现。而这正是对当前社会道德缺失和青年学生们的历史缺失感的最好的双重教育手段之一。公益性演出与跨界收徒这两条,其实可以结合起来做。先在青年学生中培养出一批爱好者,通过舞台演出实践,既让他(她)们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感同身受,又起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示范性作用,在可以想见的将来带动这个爱好者的群体逐渐扩大并形成规模效应。
4 结语
文章写到这里,心理有些矛盾。一来,觉得有些想法还没有一吐而尽,对于抚州采茶戏总还是有那么点恨铁不成钢的心理作祟。二来,本文首稿第二部分包含了有关于“四梦”早期演出唱腔[5]的相关研究内容,但是由于篇幅关系,忍痛删去,是为笔者一大憾事,只能另文刊出。
以上只是笔者有感而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整个华夏大地都迅速进入了一个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新时期。我想,抚州采茶戏同样也将乘着这股东风,迎难直上,开创新的好局面。
[1] 刘祯.中国戏曲理论的“戏剧化”与本体回归[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118-127.
[2] 邵雯艳.华语电影与中国戏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3] 李雪萍,黄振林.南方地方腔调的活跃与传奇“原生”的民间版本考证[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4(1):27-32.
[4] 杨馥戎.昆曲大师汪世瑜:昆曲不能过分小众化 要改革[N]. 苏州日报,2013-12-30.
[5] 苏子裕.越调吴歈可并论 汤词端合唱宜黄——清初南昌李明睿沧浪亭观剧活动一瞥[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3):261-267.
The Development of Fuzhou Tea-Picking Opera in the New Period
LI Tan, LIAO Xia-lin
(SchoolofArt,East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Fuzhou344000,China)
With the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Fuzhou tea-picking opera——a local opera,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laying down the burden of history and being in line with the times on the reform of traditional operas; furthermore, it is reflected that it is difficult and necessary to update the concept. Transposition thinking and aesthetic of the times are not only the art action in the reform process , but also beneficial attempts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Fuzhou tea picking opera; develop; performance; aesthetics
2016-10-09
李 坛(1982—),男,江西进贤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作曲与传统戏曲研究。
J825
A
1674-3512(2017)01-0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