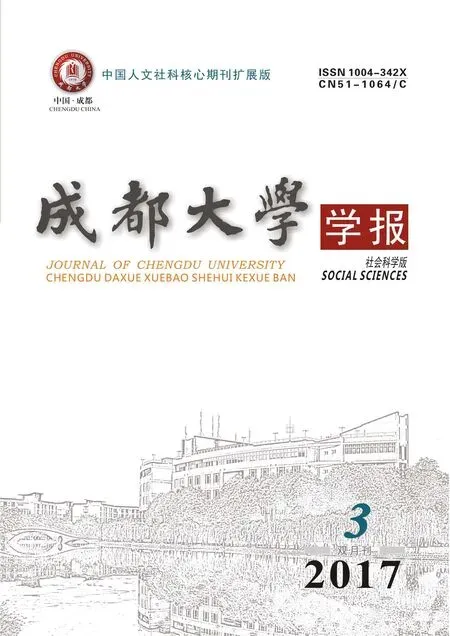互文视角下的“闺阁女性”书写*
——论《绣枕》与《桃红》
吴军英
(淮海工学院 文学院, 江苏 连云港 222005)
·文艺论丛·
互文视角下的“闺阁女性”书写*
——论《绣枕》与《桃红》
吴军英
(淮海工学院 文学院, 江苏 连云港 222005)
凌叔华和师陀同为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绣枕》和《桃红》分别是其短篇名作,比照之下可以看出,两篇小说在主题追求、人物形象塑造及诗学策略诸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互文性。通过互文性的角度进行解读,为作品的重新理解和阐释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凌叔华;师陀;互文性;《绣枕》;《桃红》
“互文性”(Intertexuality),又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它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化了别的文本。”①意即任何一个文本都与来自本文化的或者他文化的其他文本进行着对话。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概念,它彻底打破了对文学文本孤立、封闭的解释,将其置于浩瀚的互文本海洋,从文本的互相关联、彼此参照、相互指涉中获得了更为自由的阐释空间。正是在此意义上,反观凌叔华的《绣枕》和师陀的《桃红》,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为此概念做了一极好的注解。
凌叔华和师陀同为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绣枕》最初发表于1925年3月21日的《现代评论》,《桃红》作于1939年10月10日,初载于香港《大公报》。两篇小说先后出现,皆为短篇体式,在诸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互文性。
一、主题追求的一致性
恩格斯在其名著《反杜林论》中曾转述19世纪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1772-1866)的一句名言,“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②以此观照中国社会,妇女解放的程度才是衡量中国社会解放的标尺。两篇小说同以闺阁女性生活为题材,反映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闺阁女性仍然窒息于男权强大的话语力量之下,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主宰自己的婚姻,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作家在对其不幸命运表现同情的同时,也对其自身弱点予以了批判。
凌叔华在学习写作之初,曾致信周作人言明自己的创作观,“我立定主意作一个将来的女作家”,“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先生意下如何,亦愿意援手女同胞这类事业吗?”③表达了鲜明的女性写作立场。《绣枕》中,大小姐谨遵父命,冒着酷暑赶制绣枕,以便如期送往白总长家,以精湛的绣艺博得众人称赞,促成她与二公子的婚事,结果却以失败告终,两年后仍然待字闺中。虽身处五四后,大小姐却丝毫不受影响,她的命运完全掌控在父亲手中,缺乏自己独立的愿望和价值判断,陷于失语状态。对于白二公子的品行、才华如何小说中全无交代,似乎也不必交代,因为大小姐的父亲更关心的是通过强势联姻带来的仕途升迁和门楣光彩,女儿自身的幸福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大小姐势必成为父亲仕途发达、官运亨通的献品,出众的才艺更是让父亲待价而沽。
师陀在回顾创作历程时说自己“同情一切弱者,一切被社会欺凌压迫的人,憎恶一切欺凌压迫别人的人”④。身为男性作家,他对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压迫最深重的女性给予了无限同情和关注,他书写她们被践踏、被压抑的人生,也对她们懦弱不争、缺乏主体性的性格予以揭露、批判,是一个有着进步两性意识的作家。《桃红》中素姑的父亲早已去世,操纵她命运的是她的母亲。孟林太太因为婚姻生活不如意,没有生下男丁曾备受丈夫欺凌,不愿让女儿重蹈覆辙,左右挑拣女婿,使其二十九岁仍然空守闺中。尽管从表面看孟林太太有所谓正当理由是为女儿谋幸福,可是不难发现私心里她只想把女儿留在身边,陪她度过孤独的晚年,对于女儿的心事她漠然置之,对于女儿的将来毫无打算,从小说中简单的一笔描写“她正幸福的一无所欲的在床上领略午睡后的懒倦”⑤我们就知道自私的、异化的母亲也成了压榨、迫害同类的父权家长。而以长者为本位的传统礼教观则让素姑在自己的婚姻大事面前毫无发言权、自主权,她在母亲面前恪尽孝道,牺牲的却是一生的幸福。
由此可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闺阁女性仍旧遵循“以情爱之事为丑”的封建伦德理道德,父辈家长依然牢牢主宰着她们的命运,而她们也从不怀疑、任其摆布,可见闺阁女性所受到的男权思想毒害之深和中国女性解放步履的迟缓、滞重。稍有不同的是:在揭示女性悲剧性命运时,凌叔华侧重凸显女性作为第二性被赏玩、遭践踏的客体、他物的命运,师陀则着重揭示女性情爱追求的被忽视、被人们熟视无睹的婚恋悲剧。
二、人物形象的互涉性
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缺乏鲜明时代气息、更具历史感的闺阁女性形象。她们虽身处五四之后,却丝毫不染西风,她们有共同的特质:身材姣好、容颜秀美,绣艺精湛、性情温婉动人,为人处事“不逾矩"、“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⑥、“怨而不怒”⑦,极其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闺阁女性的完美想象。
《绣枕》中大小姐身材窈窕、容颜俊美、绣艺精湛,让佣人张妈忍不住称赞,“我从前听人家讲故事,说那头面长得俊的小姐,一定也是聪明灵巧的,我总想这是说书人信嘴编的,那知道就真有。这样一个水葱儿似的小姐,还会这一手活计!这鸟绣的真爱死人!”大小姐听了,则是“嘴边轻轻的显露一弧笑涡,但刹那便止”。张妈继续说,“听说白总长的二少爷二十多岁还没找着合适亲事……上回算命的告诉太太今年你有红鸾星照命主……”大小姐则打住说,“张妈,少胡扯吧。”“她的脸上微微红晕起来”⑧,这一系列的描写体现出大小姐尽管内心对于婚姻生活充满向往,但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⑨,表现出十足的闺秀风范。为了早出闺门,她不顾酷暑,精心而耐心地绣制着靠垫,靠垫上那荷塘边的翠鸟、石山上的凤凰精美绝伦、巧夺天工,可就是这样一件倾尽大小姐心血的艺术品在送到白家的当晚,“便被吃醉了的客人吐脏了一大片;另一个给打牌的人,挤掉在地上,便有人拿来当作脚踏垫子用,好好的缎地子,满是泥脚印。”⑩可是当两年后大小姐得知真相,尽管大失所望,心理落差极大,“直着眼,只管看那枕片儿”,连小妞儿的提议“明儿也照样绣一对儿不好吗?”也没听见,“只能摇一摇头算答复了”,令人几乎察觉不到她情感上经历的巨大变化,其喜怒哀乐完全吻合中国传统礼教对于情感表达的规定。
《桃红》中素姑身量苗条、气质端庄大方、举手投足间极具古典美,且绣艺出众。小说开篇后写道,“素姑小姐——孟林太太的女儿,一个像春天一样温柔,长长的像一根杨枝,看见人和说话时总是婉然笑着的,走路是像空气在流似的无声,而端凝又像她的母亲的老女,很早很早她就动手,我是说她低着头开始在绣花了。”在小说的几近结尾处作家推出了一个特写镜头,“在镜里,一个长长的鹅蛋形脸蛋儿;一缕散乱的头发从额上掉下来;一双浅浅的眉在上面画了两条弧线;眼的周围有一道淡黄的灰晕;她的嘴唇仍旧是好看的有韵致的,却是褪了色的——一个中国的在空闺里憔悴了的少女。”由于父亲早亡,母亲倾向于过一种幽僻的生活,素姑勤快而早慧,她“十二岁就学会了各种女红”,每天“当阳光从屋背上照进这个寂静的老宅”,素姑就开始绣花了,为自己、为母亲、也为同城待嫁的女伴。她为自己绣满了两大箱嫁衣,可是还没有出嫁,尽管她对婚姻生活充满憧憬。她绣好的嫁衣“逐年都有个不同的式样,它们是宽的、瘦的、长袖的、短袖的、挑花的、镶绲的”,就可见她年年都做好了出嫁的准备。闺房桌上摊开的一本李清照的《漱玉词》:“……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更暗示了她备受折磨的心事,可是她却对母亲只字不提,只是对镜暗泣,“一颗泪珠从她脸上堕下来,接着又是一颗。”尽管素姑恨嫁之心强烈,对年华老去、婚事无望充满焦虑,可是外表始终保持端庄、娴静的闺秀风度,感情内敛而不外露,十分符合中国传统观念对于情感表达的规约。
此时新思想早已吹进中国大地,许多新女性已然离家出走,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伸张生命的意志和活力,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的青春呼喊,可是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有压抑和凄凉,她们是数千年来沉默的闺阁女性的代表。凌叔华在小说中以不具名姓的“大小姐”来称呼、命名主人公即旨在此,师陀也以排斥个性、更具共性的素姑形象予以了呼应。
只不过凌叔华善写“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大小姐是京城一正在拼命往上爬的中上层官员家的女儿,可谓名门闺秀,而素姑是外地小城“果园城”里一去世多年的普通小官员的女儿,实乃小家碧玉;大小姐正值花样年华,而素姑韶华已逝,可是我们不难设想:倘若被父亲长久谈婚论嫁不成,囿于礼教的大小姐也会是素姑这般落寞的境地!
三、诗学策略的趋同性
两篇小说皆以女子绣花待嫁和嫁人未果结构全篇,淡化故事情节,突破了传统小说以情节作为结构中心的模式,重视场景描写;并且注重象征意象的采用和心理描写的妙用。
《绣枕》中通过两幅场景的呈现使读者明了事件的始末,并领悟到大小姐的悲剧性命运。第一幅:大小姐满怀期待、冒着酷暑赶制靠垫;第二幅:小妞陪着大小姐夏夜绣活,大小姐无意间获知靠垫的命运,心境黯然。两个场景的时间跨度是两年,小说的故事性不强,几乎没有什么情节,而大小姐的命运已清晰敞开。
《桃红》描写了素姑在一天里的行为表现,主要由绣花、挑布料、哭泣三幕场景组成。第一幕:素姑在庭院里绣花,隐含了她对青春流逝的隐忧和母亲对此的漠然和自私;第二幕:素姑在天井里挑选布料,突然意识到自己已做了足够的嫁衣而仓促离开;第三幕:素姑自知嫁人无望于深闺暗泣。小说的线索单一,几乎是平铺直叙地描写了人物一天的经历,呈现出情节淡化的倾向,而人物悲剧性的一生已清楚凸显。
两篇小说皆以绣花作为第一和主要场景出现在读者视线里(绣花是闺阁女性的典型姿态,也寄托了她们对于婚姻生活的无限憧憬):《绣枕》中两幅场景都是主人公在绣花;《桃红》虽只是场景之一,但毋庸置疑它是最重要的场景,占据了约五分之三的篇幅。小说的结尾也都营造了“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审美效果,她们的命运最终将如何?小说中并没有交代,留给读者一个无言的、让人惆怅和具有开放意味的结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读者的参与,达成了互动。稍有不同的是:《绣枕》中注重戏剧性场景的呈现,而《桃红》则侧重日常生活场景的展现。
象征意象的采用则升华了小说主题,提升了意境。如《绣枕》的中心意象“绣枕”即是一个象征物,它被蔑视、遭践踏的境遇正是大小姐不幸命运的象征,也是无数旧时代婉顺少女悲剧命运的象征及隐喻。《桃红》中的秋日、黄昏意象也蕴含有象征义,它们是素姑青春已逝、寥落人生的象征和隐喻,在此自然之景与人生之景相映合,这恰是作家用景的虚实相生处、精妙之所在。
心理描写在小说中得到了突出、巧妙的运用。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寡言少行的闺阁女性,再大的波澜起伏也只是在心理,外表则娴然不动,保持着端庄的仪态,故而作家着重使用了心理透视法。他们或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描写暗示人物心理,或通过气候描写烘托人物心理,或通过心理闪回直接剖析人物心理。凌叔华被称为“中国曼殊菲尔”,而师陀在《桃红》中刻画人物心理的细腻准确程度也丝毫不压于女作家。
如《绣枕》中“大小姐没有听见小妞儿问的是什么,只能摇了摇头算答复了”。通过动作的描写暗示出沉浸于往事忧伤回忆和现实失落心境中的大小姐根本无暇理会外界的事,只能敷衍应对,内心与外表的巨大反差有力地刻画出大小姐这一大家闺秀形象。《桃红》中挑水的老王沉重的脚步声打断了素姑的思绪,她突兀地喊道“老王,老王!”并随即脸红的神情泄露了她心底的秘密:对于男性的渴望。在听到大门外的巷子里传来的一阵一阵叫卖声时,“素姑于是又一遍的抬起头来问:“还不该烧饭吗,刘嫂?”这一举动则凸显了素姑觉得时间的漫长难捱感和生活的单调、乏味感。《绣枕》中对盛夏炎热气候的反复描写烘托出大小姐火热的心境、热情的期盼,《桃红》中风声鹤唳的秋景描写也烘托出了素姑寂寥、凄凉无着的心境。心理闪回是一种直接的心理剖示法,它“是瞬间的感觉,也就是说,它是空间"。《绣枕》中有两次精彩的心理闪回,第一次是大小姐听见小妞儿夸赞一对做工精致的靠垫时,第二次是大小姐猝然面对已裁成枕片儿的靠垫时,她突然回想起了绣它时的辛苦点滴,“大小姐只管对着这两块绣花片子出神,小妞儿末了说的话,一句都听不清了。她只回忆起她做鸟冠子曾拆了又绣,足足三次,……所以她永远不愿再想起它来撩乱心思。今天却不由得一一想起来。”这是很长的一段心理描写,其中还有对梦境的回忆,深刻地发掘出人物的潜意识,大小姐对于父亲观念的认同已深入骨髓。《桃红》中素姑向母亲询问时间,在听了“瞧瞧看!”的照例回答后(屋里的老座钟不知几时早就停止了),也有一长段心理闪回,“素姑手中捏了针线,惆怅地望着永远是说不尽的高的蓝的而且清澈的果园城的天空;天空下面,移动着云。……是茅舍、猪、狗,大路,素姑上坟祭扫的时候看见过的;是远远的帆影,是流霞,是平静的嫣红发光的黄昏时候的河,她小时候跟女仆洗衣的时候看见过的。她想的似乎很远很远……”这最末的一句意味深长,引发读者猜想,她想到了什么呢?一对平凡的夫妻?正常的家庭伦理关系?……
两位作家综合运用了多种心理描写手法,将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描写得细致入微、精妙传神。略有不同的是:《绣枕》中大量的心理描写侧重于往事的回忆,而《桃红》中注重现实心境的刻画,时间向度上有所差异。
四、结语
正是互文性在文本中的运动促成了文本多元化、开放性的阐释,凌叔华和师陀在对闺阁题材的共同关注中融入了五四现代文化、现代观念的诉求,也表现了京派作家在小说文体方面作出的自觉和努力,他们的创作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经验,为其多元化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注释:
①蒂费纳·萨莫瓦约,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页。
②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7页。
③转引自张彦林:《凌叔华·周作人·〈女儿身世太凄凉〉》,《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1期,第127-8页。
④师陀:《我如何从事写作》,引自《师陀全集》(第五卷)(书信、日记、论文、附编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1页。
⑤师陀:《师陀全集》(第一卷)(下).(短篇小说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84页、第483页、第486-487页、第483页、第484页、第487页、第485页、第484页。
⑥⑨孔子,杨伯峻,杨逢彬译:《论语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31页、第136页。
⑦黄永堂译注:《国语全译》(修订版),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⑧⑩凌叔华:《凌叔华经典作品》,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138页、第140页、第141页、第141页、第141页。
⑨鲁迅:《鲁迅小说全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49页。
⑩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引自《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50页。
(责任编辑:刘晓红)
“Boudoir Women”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OnEmbroideredPillowandPink
WU Jun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anyungang, Jiangsu, 222005)
Ling Shuhua and Shi Tuo both ar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of Beijing School novel,EmbroideredPillowandPinkare short masterpieces.By contrast,we can see that the two novels have some intertextuality in subject pursuit,characterization and poetic strategies.Through intertextuality,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re-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o works.
Ling Shuhua;Shi Tuo;intertexuality;EmbroideredPillow;Pink
2016-11-04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对峙与互渗——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13SJD750001)。
吴军英(1971-),女,淮海工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
I207.427
A
1004-342(2017)03-3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