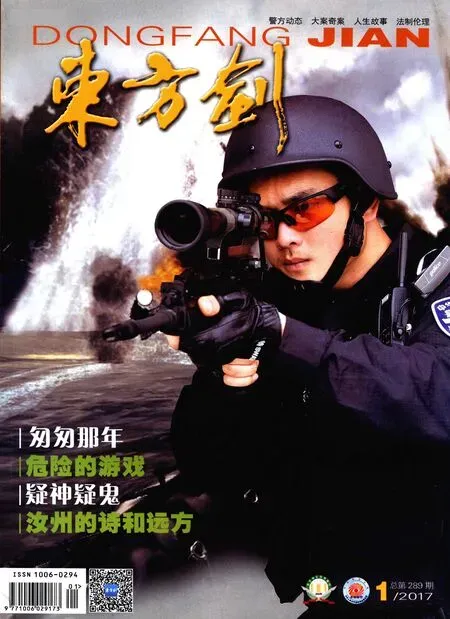斗纱(下)
◆ 孙建伟
斗纱(下)
◆ 孙建伟


十一
就在前一天,比尔又和严彤江在他的厂房里见了面,相谈甚欢。比尔把合并后的一些想法告诉严彤江,严彤江连连点头,然后神秘地告诉比尔,几年前,他女儿从南通纺织学校毕业后就去了英国学习印染技术,而他现在正在跟一个英国纱厂老板谈判,这是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比尔欣喜地说:“这是不是你我的缘分?”严彤江说:“是,就是缘分。我早已通过女儿了解了英国最新的印染技术,否则,你我的谈判哪有这么容易。”比尔说:“原来严先生还有商业情报啊。”两人开怀大笑,哈出的气很快在窗上凝成一层薄霜。严彤江伸出手指在上面画出一个圈,又一个圈,然后说:“比尔先生,今天我带你吃浦东老八样去。”
空中洋洋洒洒飘起了雪花,比尔跟着严彤江兴致高昂地到了一家挂着灯笼的饭馆。严彤江感慨,淞沪会战之后,好久不见他们的灯笼了。再过半个来月,又是新年了。辰光过得真快呀。也不知道比尔能听懂多少严彤江夹杂着浦东方言的洋泾浜英语,反正他能对这个比他大了二十几岁的男人的意思理解得八九不离十就可以了。
菜端上来的时候,比尔感到他的视线太忙碌了,啊,太丰富了。严彤江一个个介绍着,但他犯难了,菜名怎么说,洋泾浜英语也没有啊。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了,反正好不好舌头说了算,扣三丝、肉皮砂锅……他搛起一块肉皮,说:“来,比尔先生,你尝尝。这个砂锅现在吃正好,外头落雪,里厢砂锅。”
比尔试探着用汤匙舀了一块肉皮,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一嚼,吱吱的响声,片刻之后,他向严彤江伸出了大拇指。严彤江看他吃得开心,又叫店家温一壶黄酒,放上姜丝。严彤江唆了一小口,说这是中国威士忌,示意比尔依样画葫芦。比尔端起了酒杯,用舌尖沾了一点,皱了皱眉。严彤江替他把小酒杯端起来,又把自己的酒杯和他的碰了一下,一饮而尽,说:“喝下去你就知道它的好处了。”比尔皱着眉头喝了一口,觉得喉咙里慢慢发热,然后,整个胸腔都热了。后来就吃得放开了,也不管绅士风度了。再后来他打着酒嗝说严先生,这是我吃得最开心的上海饭。不,是浦东饭。我们的新厂建立后,我就可以随时到这里来吃饭了。
一个月后,协隆纺织有限公司隆重挂牌。比尔憧憬着未来几个月内,簇新的厂房初具规模。老乔治在曼彻斯特的公司将为他们提供机器。更重要的是,停泊在外滩的英国海军舰艇使比尔的安全感大增。那里距离白莲泾并不太远。
严少卉回来了。本来随她一起到达的还有协隆在曼彻斯特订购的纺织机械,但英国和日本已成敌国,日本控制下的上海口岸拒绝放行这些铁家伙。
多次听严彤江说起过的严少卉一出现,比尔就一眼认出了她。两年前在曼彻斯特中国城面馆的邂逅之后,这个女孩给他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标准的伦敦音和后脑勺上两根油亮的辫子。
严少卉瞬间发呆的时候,比尔说话了:“还认识吗?”严少卉也想起来这一幕了,她微笑着:“您就是比尔先生,爹爹说的大老板原来是您呀!”
比尔也不谦虚:“我当时就告诉过你的,我不像吗?”
“不是您不像,而是我不敢想象。”
“严小姐真会说话。”
一旁的严彤江一头雾水,凭他那点洋泾浜英语,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只是觉得他们很熟,就问女儿:“少卉,你认识比尔先生?”
“爹爹,我在曼彻斯特读大学时打工,比尔先生来中国城面馆吃面,我们就认识了。”
比尔对严彤江说:“不过当时,我们只说了两句话,小气的面馆老板就把她叫走了。”
严少卉立即反驳:“不,也许他怕你把中国小姑娘拐跑了。”
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严彤江拍着比尔的肩说:“比尔先生,我说过的,我们有缘分。这下,你相信了吧。”
“我太相信了。严先生,我更相信我们的合作。”
严彤江对严少卉说:“阿卉,接着就要检验你的学成,为协隆尽力了。”
比尔说:“不过,我们的机械被日本人扣着进不来,这一定会影响产品的产量和更新啊。”
严少卉立刻接住了话头:“但他们扣押不了我脑袋里的东西啊。”
比尔的眼睛里闪出一丝光亮:“是啊,我忘了严小姐脑袋里装着最先进的印染技术呢。”
“阿卉,可不作兴夸海口啊。”
“爹爹你不相信我啊,我从小到大说过大话吗?”
“唔,你这小囡倒是从来不吹牛的。”
比尔说:“坦率地说,也许只有印染技术才是我们占有市场份额的一条生路了。严小姐,你有把握吗?”
“比尔先生,我爹爹说过,我从来不说大话,但我会尽全力。”
“那好,明天你就开始。”
那天晚上,布莱德利来了,表示把自己的老公茂纱厂作为股份抵押给协隆:“日本人惹了美国,那就等着报复吧。而且我打赌,这报复会很残酷。比尔,反正我的市场份额也不大,所以抱在一起还可以增加点实力。渡过了这段困难,局面一定会改观的。”
比尔很激动:“布莱德利先生,有您的支撑,我就有底气了。”
当晚的洗尘宴还是老八样,这也是严少卉从小吃到大的。上一次是严彤江和比尔两个人,这次是四个人了。凯特琳瞪大眼睛看着一盘盘菜端上来,着实有点惊讶。她没见识过这排场。紧实而丰满的菜肴把一个个硕大的瓷碗撑得满满当当,相比起来,无论是英国还是印度大餐,盘踞在一个大盘中间的那点东西,像是大海中孤独的小岛。
比尔说因为喜欢“老八样”,就当自己是半个上海人了,他周围的上海人听得懂他说的上海话,严少卉也说听得懂。他为此很得意。严彤江告诉凯特琳,因为日本人的控制,像这样的大餐我们也是几个月才吃一次啊。饭桌上的空气凝重起来。比尔说我来上海这些年,在这里经历了很多事。我觉得,日本人快撑不住了,到时候不知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上海。但不管如何,我是喜欢上这个地方了。
严少卉在比尔的陪同下在新建的厂房里转,她看得非常仔细,谈起问题来全是印染专家的专业口吻,比尔惊讶之余,不禁叫好。但严少卉的另一个问题让他踌躇了很久:“比尔先生,你能告诉我收购我父亲纱厂的动机吗?”
比尔字斟句酌地说:“严小姐,我和你父亲是经过谈判的。我们总共谈了三次,双方都认为可以从合并中获得各自的利益。而且,你父亲还是新的协隆纺织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他用了“合并”这个词。
严少卉顺着他的思路再问:“你认为合并后的新公司能保证股东们的利益吗?”
“这一切要看公司的管理和运作,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那我跟你交个底吧。父亲送我去曼彻斯特,也就是你的家乡学习印染技术,就是要我把裕昌振兴起来,所以我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曾经是反对的。但我毕竟不能左右我的父亲。”
“我非常能理解严小姐的想法,我也说实话,我到上海来办纱厂是为了实现我父亲的遗愿。但我来上海之后,发现远不是我想的那样。日本纱厂太强大了,我们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但我既然来了,就绝不撤退。我看到大批华商纱厂被日本无条件地收购了。不,这不是收购,这是可耻的吞并。严先生在如此险境中没有屈服于日资,令我十分钦佩。所以我和严先生谈判的前提是尊重他的意愿,而且全盘考虑双方的利益。当我听说严小姐在曼彻斯特学印染,又增加了我的信心。”
“对不起,比尔先生,我的问题勾起了你痛苦的回忆。”
“哦,我不会介意的,我感谢你的坦率。我想,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的。如果我们的产品打开了国际市场,前景将是不可估量的。”
严少卉听着,觉得自己的心跳加速。她想,这个男人的确有煽动性,父亲一定是被他的说辞打动了,不过看得出来他是真诚的。那就相信他,至少他没有强取豪夺吧。
几个月后,严少卉主持研发的“龙和”牌印染织品投放市场。
那天,比尔邀请严少卉去外滩走了走,路过上海总会的时候,门外有日军士兵把守着。现在,剧院影院跑马厅俱乐部,包括上海总会,都是禁止盟国公民进入的。比尔叹了口气说:“其实上海的奢侈场所对我来说,除了上海总会,我几乎没去过其他地方。”
后来严少卉就随比尔去了他的家。令她稍感惊讶的是,除了壁炉和画框,这个家与一般上海家庭无多少区别。比尔指着一把藤椅对严少卉说:“这是我一年前买的,休息的时候,我就坐在这里看书,非常舒服。请坐。”他做了个请严少卉就座的手势。然后他从柜子里取出一瓶酒来,说:“这是我最喜欢的马提尼酒,不知道你是否喜欢?”
“我没喝过,但我很愿意尝尝。”
“太好了。”他拿出两个杯子,各自斟了少许,拿起自己的一杯抿了一口,非常惬意。
严少卉谨慎地唆了一口,皱了皱眉。比尔注意到了:“什么感觉?”
“唔,自然,纯粹,优雅,也有点尖锐,深不可测。你应该喝这酒。”
比尔又咽下一口酒,然后专注地看着对面精致的五官。严少卉忍不住笑了:“你这是干什么?”
“你还在英国进修了读心术?”
“什么意思?”严少卉也瞪大了眼睛,睫毛也被撑开了。
“你的意思是说马提尼很像我,对不对?”
“也许是吧。”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我一定要敬你一杯。我干了。”比尔仰起脖子一干而尽。
“这又是……”
比尔显得很激动:“你知道吗,这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想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今天才突然明白了。不,是被你破解的。”
倒是严少卉有点局促了:“我不过随便说说,你用不着当真的。”
“不,你随便说说,这就叫歪打……”
“歪打正着。啊呀,不是这意思……”
比尔仍沉浸其中:“或者是醉翁之意……”
“不在酒。嗨,也不对。”
比尔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我怎么总是只记住半句,中国成语太难了。不过,有你就没问题了。你知道马提尼酒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吗?因为酿酒师在它的制作后期加了烈性白酒和蜜糖。”
严少卉端起酒杯,这次是学着比尔的样子抿了一口,细细品味着:“唔,我感觉到了。辣中带甜,香气清爽。看来,我也会喜欢上它的。”
“那就让我们干杯。”
几杯酒下肚,都有了点酒酣耳热的感觉。这感觉非常好。
比尔的目光停留在这个纤细娇小眉眼精致的女人身上,那种自在和自信或许和这个躯体并不相称,她对协隆的未来意味什么,对我又意味着什么?两人四目相对,感觉着对方此刻的心思。
十二
连浦东那些低矮的建筑物上也飘起了太阳旗。英国海军舰艇早已形同虚设。中村发现,日军士兵中还有带着长崎口音的。但这些士兵实在太稚嫩了,他们的声音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浑厚和粗犷,你看,就连喉结也没有形成一个应有的弧度。虽然他们都显得亢奋、抖擞,但感觉像虚张声势。他们的军用靴子踩在浦东的泥地上,也没有发出触碰柏油马路时咔咔的声响。
白莲泾,当年的机器轧花厂早已物是人非,眼帘往前抬,百余米之外那个新矗起的厂房就是协隆纺织有限公司。想想比尔和凯特琳失魂落魄的样子吧。中村似乎又回到了几年前的那个夜晚,仰望星空,体味清新的夜露。不远处,稚嫩的长崎口音在空气中游荡。
但他分明看到了协隆的烟囱里依然吐着浓黑的烟。
一连好几天,中村持续奔波于被太平洋战争终结的“孤岛”,高鼻子们,尤其是灰溜溜的英国佬,哪里还有绅士的矜持。他再次庆幸自己当初留在上海的选择,这里是日本纺织业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也是他中村健太建立功勋的地方。
这天他回到家已是半夜。
打开门,他惊骇了。
理惠子不见了。
这一夜,中村在厂区的家属区里到处找,完全没有理惠子的踪影。
她来了一年还不到,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执拗地占据着中村的思维系统,每一次寻找未果后就像一道绳索把他的大脑又勒紧了一点,生疼。他无数次向自己发问,直到他确认这已成为一道无解之题。
无解之后,中村的脚步不知不觉又到了竹内餐馆。他忽然想,多久没来这里了,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了。幸枝还在吗?正想着,身后响起熟悉的声音:“是中村君吗?”中村猛一回头,激动立刻变成一连串问号:“幸枝,真的是你吗?你一直在这儿吗?你还记得我?”幸枝也显得特别激动:“中村君,我一直记得你啊!您好久没光顾了,您请坐。”中村坐下来,那种惬意的感觉立刻就回来了:“照以前的样子来一份吧。”“是,中村君。”她的木屐发出急促的嗒嗒声。几分钟后,幸枝端着一个托盘过来了:“中村君,您请用。”中村微微点头致谢,然后问:“幸枝,你陪我一起吃吧。”幸枝退到一边,连连摆手。中村再次向幸枝点了点头,说:“不必拘礼,幸枝,请接受我的邀请吧。”幸枝扭捏着在中村的对面坐下来。
中村喝了一口清酒,问道:“幸枝,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上海?”
“我到上海已经十多年了。”
“啊,那你想过要回去吗?”
“我没想过,我在上海过得很好,为什么要回去?”
“是啊,很多人都这么想,我在上海开纱厂,事业兴旺。这里不愧是远东第一啊。”
“中村君说得太对了。”
“不过,昭和十二年(1937年)第二次上海事变,你也没被领事遣送回国吗?”
“我被遣送了。但是,年底我又回来了。我家在宫崎县,离上海很近。搭上船,很快就到了。”
“你是宫崎县的?我是长崎的。原来我们都是九州人啊。”
“真的,中村君,真是太巧了。”幸枝激动得都不知怎么表达了。
“幸枝,这么说我们真是很有缘啊。来,干一杯。”
这一晚,幸枝对中村百般缱绻,中村情绪高昂,但后来他又把幸枝当成理惠子了,幸枝一点都不恼,反而全力迎合。问题是,此时的中村怀着的不仅是思念,还有怨愤。所以借着酒劲的中村就把自己变成了一头暴戾和凶狠的狼,幸枝带着虐痛的呻吟助长了他的暴戾,也使他病态的亢奋不断攀升到新的高度。
这样的狂放并没有结束,中村欣喜地发现,和幸枝在一起的感觉超过了理惠子,难道这才是他的真爱吗?
冬天来临的时候,大纯纱厂也与严寒越来越近。
中村早就知道这一天总会来的。这是纱厂高压政策的必然结局。日夜轮班,工资菲薄,连去厕所也要领牌子,五百个人用两个牌子。工人们三四家甚至七八家挤在一起。中村曾想作些调整,但遭拒绝。纺织株式会社高层坚持,规定沿袭了很久,不能擅自更改。对工人的管理历来如此,何况是猪一样的支那工人。中村并不认为支那工人是猪,但也无能为力。所以当他看到夜幕中的工人们高喊着“摇班”(罢工)、“日本纱厂搬回日本去”蜂拥而出的情形并不惊讶。他拿起电话吩咐关闭厂门,然后透过窗帘的一角目睹工人们扛起巨木把门撞开,或者爬墙而出。有人把纱厂的工作帽脱下,高声大喊,我们不戴东洋帽了!然后丢在地上猛踩,然后有更多的工人紧随其后……这一幕是中村最不愿意看到的,大纯的工作帽源于他的亲手设计,这顶帽子是上海棉纺市场的一块招牌,是他在上海事业的象征。放下窗帘的时候,中村觉得自己的手居然有点颤抖。他不敢再看了。
他连灯都不想开,就让屋里暗着吧。连心情都和这空间一样一团漆黑。他倒在沙发上沉沉睡去。
这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上午。连续好几个阴霾笼罩的天气了,是个难得的艳阳高照,却与他当下的心绪十分别扭。读报是中村早餐的一部分。当他把第二个寿司塞进嘴里的时候,眼睛就被这一版报屁股上的一个黑色小方块粘住了。那是一个讣告,上面写的是斯泰格的追悼讯息,发布人是比尔。寿司噎在喉咙口不上不下,紧接着感到一股气直冲上来,把寿司顶了出来。他站起来,打开窗户,大口呼吸着,还是觉得气息急促。
葬礼上,中村和凯特琳的眼光遇上时,他避开了。
凯特琳觉得自己被罩在一张莫名的网中,周身冷彻。他为什么要避开?难道斯泰格的死真和他有关?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他们俩究竟是什么关系?真相究竟是什么?
比尔拿着那些照片去了巡捕房,探长来回翻着照片表示可以立案,但因缺乏关键证据,结局也许并不乐观。如探长所说,半年过去,案件毫无进展。
中村沮丧之余,决定不向凯特琳作任何解释。他既想压过怡信一头,又想保持跟凯特琳的关系,看来是痴心妄想了。就算他真的爱上了这位进入盛年的优雅的英国女人,又能有什么结果呢?就让这一段似是而非的男女之情无疾而终吧。葬礼后她约他去了咖啡馆,质问他和斯泰格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对斯泰格做了什么。他知道她在等他解释,或者辩驳,但他打定主意不解释不回应。然后,她一把夺过他的咖啡杯,狠狠地扣在桌上,杯子的碎片使深褚的汁液渗着鲜血的暗红,像一朵诡异的花突然绽放在她的手心里,刺一般射向他的眼睛,他用眼角的余光胆怯地瞟了她一眼,她的脸色煞白,潜着隐隐的青紫……
十三
店铺里和街上的同胞都在议论山本五十六大将在所罗门群岛布干维尔岛上空殉国的事。据说他的座机在三十秒之内被打成了筛子,奉命寻找的日本士兵发现他的尸体一直保持着端坐握着指挥刀的姿势。这位海军大将出生时父亲年已五十六岁,这个年龄就成了他的名字。山本五十六的殉国使日本举国上下像一个巨大的气球那样瞬时破裂,包括中村在内的日本国民只知道太阳旗下的勇士们所向披靡高歌猛进,但现在谁都看得出来,日本已经处于守势了。想起那天他看到的士兵,这么年轻就到国外为天皇陛下效忠,哎,谁知道还能撑多久呢?如果战败了,大纯的前途又将如何呢?他不愿去想这些问题,但挥之不去,上海这么大规模的纺织业,这么多的人员、管理、技术和机械设备,将会面临什么结局呢?
结局在他还没想明白的时候就出现了。中村认为还不会这么快,但天皇陛下的“玉音”已向全世界“放送”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了。在经过了几天的沉默后,中村和所有居住在虹口的日本居留民一样接到了通知,进入日侨集中营。去溧阳路上的日本侨民管理处登记的时候,中村路过那个几乎可以摸黑走到他的专座的咖啡馆,心中不免隐隐作痛。好时光结束了。彻底结束了。
他的生活场景被颠覆了,晚上8时之前就必须“回营”了。作为战败国国民,这是必须承受的。那天他作为日本居留民代表接受上海方面总司令汤恩伯将军的召见,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国民政府的战争赔偿条件竟如此宽大,中村也深感震惊。震惊之余,他拒绝被遣送回日本。上海是他的福地,留下来是最好的选择。他想,既然纱厂被作为敌产没收,那么他继续在这里工作,也算为中国工作,总是可以的吧。他向遣送机构提出了要求,然后静静等待。
不久后宣布成立的国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就是在上海的日本纱厂的班底,也包括了中村的大纯公司,但在留用的一百二十多个日籍技术人员名单中,没有中村健太的名字。他失望之极,比将近半年前听到天皇陛下宣告投降还要失望。这也意味着他被遣送回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那天他再次来到杨树浦,在心里对他的大纯进行最后一次祭奠。许多日本居留民称上海为“宝山”,中村喟叹,的确是一座宝山啊,现在都要离开了,没有选择地离开了。目光游移之间,他心里忽然一颤,近在咫尺的还有当年的对手怡信。时势决定命运啊,庞大的日本纺织业变成了战胜国的财产,苦撑坚持的怡信却变成了更大的协隆。虽然他已失去了想这事的资格,但有一个人就在这时潜入了他的内心,凯特琳,凯特琳。很久没想起她了。忽然很想见她一面,跟她说点什么。他立刻又嘲笑自己,这个愿望太离谱了,太不着边际了。
这天晚上,他铺开信纸,写下自己到上海后的种种遭际,一个风头健硕的青年变成了即将进入中年头发开始稀疏的男人。从白莲泾的创业到杨树浦的发达,大纯和怡信的恩怨,对斯泰格的内心忏悔,和凯特琳的纠缠,写到了他欲留上海而不能的惆怅,还写到了对协隆的祝愿……最后极其庄重地在信封上写下了收信人,凯特琳女士。
他想,也算是对自己十几年上海生涯的一个交代吧。中国人说,尘埃落定。
早在1921年,长崎的诹访神社就按它的原样迁到了上海神社。中村对神社的记忆很清晰,儿时父母常带着他去祭祀。想起神社,就自然想起天照大神、神武天皇和明治天皇。比起长崎老家,上海神社距离他住的文监师路(今塘沽路)更近,就在那个被工部局命名为“新靶子场公园”(今鲁迅公园)的地方。不同的是,神社的偏殿还造了一个招魂社,祭祀在二次上海事变中战死的日本军人,不远处就是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上海本部。这里完全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来来往往很难看到一个中国人。中村总是非常得意地对第一次来虹口的同胞说,这里是小东京,比东京还要繁华的小东京。
离开上海之前,必须再去一次神社。理由很简单,战胜国绝不会允许战败国的所谓神祇留下任何印迹的。过不了多久,那里的神龛和祭祀物都会被清除。所以他必须在此之前去完成最后一次仪式。在中村看来,这是一种使命。
中村是带着幸枝一起去的。但幸枝说的一句话让他很生气,她说她是第一次来这里,为此他凶狠地训斥了她一通。幸枝惊慌失措地站在一边,不停地说着“是,是,中村君,是我错了”。
三三两两的同胞在神社进出着,他们表情平静,这里的一切似乎已与他们完全融合,似乎战败国国民的身份并没有带来多少忧虑。幸枝学着中村的样子,先洗净双手和嘴,然后虔诚地走近神龛前,朝盒子内投入硬币。然后鞠躬,拍手,再次鞠躬祈祷,这个祈福仪式就完成了。
中村想,他的家乡长崎继广岛之后遭到了第二颗原子弹的轰炸,至今都没有家人的消息。回到日本以后,我们这些上海居留民将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他没想到的是,幸枝也不愿意离开上海,而且态度坚决,她说即使躲也要躲在上海。中村狠狠扇了她两个耳光,凶神般大吼:“混蛋,不要忘了自己的战败国国民身份,你能躲得下去吗?你知道支那人有多恨我们吗?告诉你,我们不是居留民了,日本人的虹口结束了,再也没有什么小东京了。”他知道,这么大喊大叫其实是发泄自己心里的怨怼,竭力说服自己。
1946年1月,上海进入严冬的一天,间或日出,间或阴霾。一早,嘤嘤抹着泪水的幸枝被中村拽着登上了停泊在十六铺码头的“江鸟丸”。这条货船被大刀阔斧地改装成了遣送船。货舱上面搭起的一个大棚里竟然挤着四千多人,全部通铺。密密匝匝,光线昏暗。所有人都静默着,鱼贯进入自己的位置。
中村走上甲板,视线始终在黄浦江两岸的建筑上徘徊。十六铺向东的白莲泾,是他到上海的第一站。近在咫尺的西岸,日清洋行、横滨正金银行阴着哭丧的脸向他告别。他忽然想起沿外滩的四川路上还有他最熟门熟路的三井洋行上海分行。嗨,结束了。此生再也无缘相见了。直到漆黑将天幕完全覆盖,他才万般无奈地向大通铺走去。
清晨醒来,船已驶入舟山海面,突然猛地一震,又是一震,紧接着是一连串剧烈的爆炸声。黑烟越来越浓,像一个志得意满的蒙面大盗迅速扩张着地盘。船长一面发出求救信号,一面在广播室里接连呼叫:本船触碰水雷,即将沉没,请全员立即登上甲板。
没有惊叫,所有人只是把恐慌藏在心里。中村在人群中忽然瞥到一个身影,啊,是她吗?他不禁激灵了一下,再定睛看,的确是她,理惠子。他刚想喊,看着周围的静谧,又把喊声吞了回去。但又不能挤。他寻找机会慢慢向她靠近,看来也是徒劳,因为他和她相隔了至少有十几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弄出点动静来,让她的目光注意到他。所以他咳了一声,又响亮地咳了一声。果然他的余光就感觉到周围的目光正向自己聚拢。有她的吗?他抬起头来的时候,她向来抑郁的眼神正盛满抑郁地与他相遇,而后闪出惊异,然后她捂住了嘴。中村知道,这是她下意识的一个动作,表示极度的惊讶。她当然惊讶。他也惊讶。他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好像要把她盯到自己的眼睛里去。两人就这么看着。幸枝诧异地在中村身后问中村君,中村君,你怎么啦?中村背对着她说没什么。但中村的后背给幸枝的感觉显然是有事的。幸枝其实看到了前面那个捂着嘴的女人,她与中村君对视着,她捂着的嘴里一定藏着什么。
船长开始向人们发放木板,是从大棚上卸下来的,每个家庭一块。船长告诉大家,如果无法获得救援,就只能跳海逃生了。人们依然沉默地领取木板。幸枝对中村说:“我也领一块吧。我和你一起。”中村仍没回过头来,轻轻地说:“还有她。”
大约三海里远处一艘挂着美国国旗的“百利华”号正向“江鸟丸”驶来,救援和被救援的都知道,第二次爆炸的危险还在,救援的成功概率很难把握,“江鸟丸”上不见嘈杂,反而一片寂静。
两条船靠近时,“江鸟丸”才响起克制的欢呼声。美国船员指挥人们一个接着一个踏上“百利华”的甲板,忽然有人发出惊呼。一个少妇把婴儿交到美国船员手中时,却不慎失足掉入海里,恰被“百利华”的推进器卷入,渗着鲜血的海水打着漩,又被更大的漩涡吞没。已经和中村会合的理惠子又一次捂上了嘴巴。船上的人默默向少妇致哀。中村忽然对理惠子和幸枝说:“你们先走,我留到最后。”两人盯着他问:“为什么?”中村说:“现在很危险,还有二百多人在‘江鸟丸’上,越早离开越好。”幸枝问道:“那你为什么不走?”中村说:“我只是想让别人先走。”幸枝再问为什么,中村低沉地说:“没有为什么。”理惠子忽然说:“那我要跟你在一起。”中村瞪着她:“不,你先走。”理惠子很坚决,声音也高了起来:“你想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吗?”中村默然。理惠子说:“因为我看到你的时间太短了,甚至几天都看不到你。我需要一直看到你。”中村一把抱住理惠子,眼睛里盈满泪水。幸枝也嘤嘤着抱住了中村。中村突然觉得有人狠劲地拉他,要把他和这两个女人分开,所以他死死地抱住她们,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啊,斯泰格,你怎么来了,是找我复仇吗?对,是我找的浪人干掉了你,这是你的劫数。现在,我的劫数也要到了,你别扯着她们,我要跟你对决。来呀。你这个混蛋。恶棍。骗子。“
理惠子和幸枝被中村的样子惊呆了,他眼睛通红,凶狠中含着惊惧,鼻翼急促收缩,嘴里含糊不清,他真的疯了吗?他死死盯着她们,嗓音一下子变得沙哑:“你们快走,走啊!斯泰格,你来了,终于来了。我不怕你,我……不怕你!我要和你决斗,决斗!”理惠子和幸枝倒退着走上了“百利华”的甲板。中村看着她们上了甲板,然后双手掩脸,号啕起来。幸枝和理惠子再想往回走,被船员拦住了。
“江鸟丸”继续下沉着,还有几十个人没有登上“百利华”。更可怕的是,被“江鸟丸”拴着的“百利华”也在缓缓下沉,船长决绝地割断了连接“百利华”的绳索。中村忽然紧紧抱住船长,大喊众人一起跳船。中村和船长合抱着一块木板在湍急的海水中挣扎,船长喘着气告诉他,刚才我想对所有人说一句话,但我一直没说出来,现在再不说就没机会了……我告诉你,根据我的经验,这是一个固定的水雷,这一定是帝国军人干的。中村惊讶得张大了嘴,恰好一个浪头打过来,把他完全淹没了。船长想去拉他,又一个巨浪接踵而至……
十四
比尔和严少卉从曼彻斯特带了新的一批机械回到白莲泾,已是1948年的冬日。出了机场,严寒就给了他们当头一击。比尔把严少卉搂进怀里,感到她的身体微微颤抖。
积雪把协隆厂区变成了白色世界。
一年前,在老乔治的安排下,严少卉再去曼彻斯特学习最新的印染技术。这一年里,她和比尔用情书精心构筑了他们的爱情城墙,也成了一个真正的印染专家。
严彤江病了,病得很重,为了不影响严少卉的学业,他一再要求比尔不要告诉她。
第二天上午,比尔就带着严少卉来到仁济医院病房里。严少卉好像认不出父亲了,一下子变得这么老迈。她挨着父亲蹲下来,泪水滴滴答答掉落在他枯槁的手上。严彤江抚摸着女儿的头发,说:“阿卉,你回来了就好啊,看到你,我今天精神好多了。”
“爹爹,怎么会这样啊?”
“生老病死,谁都逃不过。你晓得的,爹爹四十二岁才有了你这个宝贝女儿,你这么有出息,给爹爹争光,也给我们严家宗祠争了光啊。”
“这全是爹爹的心血。现在协隆经营得越来越好了,多需要爹爹啊。”
“爹爹晓得阿卉孝顺。协隆主要还是靠比尔先生,你回来了,就可以做他的助手了。”
“爹爹放心,我晓得。”
严彤江向比尔招了招手:“比尔,你过来。”比尔俯下身看着严彤江:“严先生,您有什么事,尽管说。”严彤江的声音忽然轻了起来,气息也急了:“比尔,看来我没有福气看到你们的婚礼了……现在……我就把女儿交给你了。你一定要照顾好她。”
“严先生,您放心。我一定记住您的话,照顾好少卉的。”
严少卉挂着泪水,硬挤着笑:“爹爹安心养病,您一定会好起来的。”
比尔忽然想,此时此刻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一幕和父亲当年在印度的经历惊人地相似。不同的是,母亲是父亲老板的女儿,而他自己是老板,未婚妻是一位中国股东的女儿,还是临终嘱托。他陡然感到沉重起来。
一个星期后,严彤江不治身亡。在他身边守候了两天的严少卉红肿着双眼对匆匆赶来的比尔说:“爹爹走得很安详,临终前他一直叫着亲人的名字,其中也有你。”比尔紧搂严少卉,轻抚着她的肩说:“我知道,我知道岳父的心意。少卉,我从心里感谢我的岳父,他给了我一个好妻子。我想,有我岳父的保佑,协隆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好运的。”这时,久藏他心里的那个钟摆再次响了起来。
冬去春来,比尔带着严少卉又去了上海总会。比尔慢慢看着,像一个好学的小学生那样重温着他曾经阅读过的每一个细节,后来他对严少卉感慨:“四年前我们只能和这里擦肩而过。幸运的是,它的一切都没变。你看这个一百一十英尺的长吧台,是日本设计师的大手笔。我在上海的对手也是日本人,我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充满智慧和力量的。我想,这段经历对我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
严少卉沿着长吧台默默走着,忽然问:“比尔,想喝马提尼吗?”
“马提尼,太好了。我们是该庆贺一下了。你看到长吧台尽头转弯的那一段了吗?那里与黄浦江是并行的。据说是那些大银行和洋行老板的包座,除非他们邀请,别人不能坐在那里喝酒。”
“那我们今天就坐在那里喝酒,看我对岸的家。”
“少卉,说得好。”
这一次,他们喝得很尽兴。
夏季来临之前,协隆公司宣布迁往曼彻斯特。临行之前,凯特琳再次打开中村的那封信,重读了一遍,悄悄烧了。然后,她又去了国际礼拜堂。
几年后,“龙和”系列产品相继问世,行销国际市场。比尔想,我终于可以告慰父亲了。
1980年,比尔和严少卉携凯特琳重回上海。
将近九十岁的凯特琳一直念着徐家汇的国际礼拜堂,还会常常想起那里的石柱、红色砖墙和鲜艳明媚的彩色玻璃。其实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它都无法和英国的任何一个教堂相比,但凯特琳对它的思念仍是挥之不去。站在这个地方,她又一次真切地体味到那种美丽的宁静。她想象着当年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博士在此讲道的情形,好像自己身处其中虔诚聆听。她慢慢在教堂里走着,看着熟悉的管风琴、洗礼池和铜十字架,她不可能知道不久前它们曾遭受过一场空前的洗劫。
不过,比尔就没母亲那么幸运了。上海总会叫东风饭店了。比尔和严少卉走进去,身穿蓝色工作服的服务员略显诧异地瞟了他们一眼,然后继续呼噜呼噜吃面条,忽然他们发出了非常响亮的笑声,是哄笑。比尔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但他还是固执地寻找着长吧台。没有了,只有一段一段的桌面,但那分明是他熟悉的长吧台的黑白大理石啊,连它们的纹理都熟。哦,我的天哪,难道它真是被割成一段段了吗?比尔感到自己眼前金星乱窜,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又是10年过去。
1990年秋,比尔和严少卉受邀参加浦东开发开放外商投资考察团。宽大舒适的大巴沿着外滩缓缓驶过,万国建筑依旧,人们的穿着比10年前繁复起来。那幢熟悉的大楼渐渐接近了,还叫东风饭店,但在顶端显眼位置出现了一个硕大的美国老头头像,他围着一条围裙,笑容可掬。哦,那是肯德基家乡鸡。
下午,他们将去考察的地方就是白莲泾,当年的协隆旧址。两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十指相扣,默默念着,那里,现在都什么样子了?
(全文完)
特邀编辑/浦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