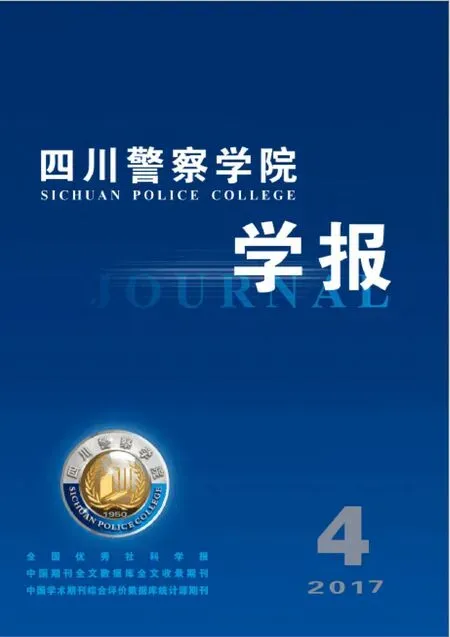现实与重构:“中国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
王 统
(山东大学 山东济南 250100)
现实与重构:“中国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
王 统
(山东大学 山东济南 250100)
世界范围内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和犯罪低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危害社会安全的突出问题。当前我国社会处在转型期,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渐突出,需要发挥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要引入区别于成年人的刑事和解制度,并构建“中国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以和为贵”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精髓,这种“和”理念更应贯穿于“中国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整个过程。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构建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刑事和解制度,它是一种与传统刑事诉讼模式相抗衡的非诉处置犯罪的机制。近些年,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案件频现,未成年人犯罪也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公认的社会问题,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各国共同的讨论热点。而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非诉的制度,旨在实现未成年犯罪人和被害人双方利益的最大化[1],所以在未成年人犯罪处置机制中引入刑事和解这一制度是世界各国的通识。本文通过梳理法条时发现,在我国司法理论中,很少有关于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专门化、规范化的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虽然认识到了这一重大社会问题,我国在2013年颁布的新《刑事诉讼法》中新设特别程序一章,用24个条规规定了4个特别程序,其中第一个就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但新《刑事诉讼法》由于刚刚颁布,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相关立法难免还不完善。其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专章并没有特别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和解程序,仅用第276条简单规定直接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程序”相关条款。一般来说,相较于成年人,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各方面尚未发育成熟,加之未成年犯罪人大多是偶犯和初犯且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程度较小,所以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司法制度上应更多是推崇区别于成年人犯罪的人性化、轻刑化的处罚制度,而不应该如法条规定那般直接、简单。
由于立法不完善,使得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操作起来并非法条规定的如此简单,在各地司法实践中也是做法不一,争议不少。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中的争议问题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适用的案件范围有限。未成年人由于自身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很容易一时冲动而走上犯罪道路,未成年人犯罪所触及的案件范围也是五花八门。其次,适用的阶段不明确。在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中,并未赋予公安机关主持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的权利。该规定仅仅指明了公安机关可以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但却没有给公安机关到底能否主动促成刑事和解的这一疑问一个明确答案。这其实也是涉及到了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和解制度,特别是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运行中的角色定位问题。再次,监督的力度不足。一个制度的良性运行必然需要强大监督机制支持。刑事和解要求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以非诉的方式解决刑事案件。虽然未成年人一直以来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但我们不能忽略未成年加害人的行为仍是犯罪行为,所以司法机关必须对这一制度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最后,和解的其他争议点的归纳。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刑事和解的主持人,在不同阶段由公检法三大司法机关做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主持人是否真的合适?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是否更加理想呢?达成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过程中,是否也应该赋予律师在场的权利呢?倘若加害方的未成年人家庭着实没有赔偿能力并因此导致被害方家庭生活十分困难,这种情况下,国家司法救助制度是否是给当事人双方打开了另一扇窗?
二、“中国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这一概念是20世纪中叶从英美等发达国的司法实践中衍生而来的,是恢复性司法的重要内容。刑事和解也可以称为被害人犯罪人的和解、被害人犯罪人的会议或恢复性司法对话等。它的基本内涵是:犯罪发生后,加害真心悔过并积极认罪,经调停人的帮助,与被害人直接沟通、共同协商,解决纠纷。西方少年法庭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方面原因,西方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研究领先于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本身又具有妥善、积极解决矛盾与纠纷的社会功能,使得未成年人刑事和解这一制度在西方广泛发展。随后,世界各国也纷纷着手于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探究。虽然各国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各有不同,但总体来看是两个模式:一个是国家主导模式,它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为典型;另一个是社会主导模式,则是以芬兰、加拿大等国家为典型代表。
国家主导模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主要是国家的立法机关经正式立法程序,制定具有国家强制色彩的相关法律法规,将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正式纳入国家刑事司法体系并明确规定此制度运行适用的条件、适用的范围、适用的程序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等[2]。社会主导模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就是指对适用于未成年人的刑事和解并没有正式的规范性依据,而是灵活地依靠社区自治、地区自治来指导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实践。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突出特点是未成年犯罪人与被害人可以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并且协商结果对案件处理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民间“私了”,而是国家处理犯罪的一种特殊的方式[3]。基于此,构建“中国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仍然是以“国家主导模式”为主。
综上,立法和司法上,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中适用刑事和解这一举措仍处于摸索阶段。吸收借鉴国外未成年人刑事和解运作模式的优点,坚持“国家主导模式”为主,从未成年人和解制度适用的案件范围、适用的阶段以及监督机制上进行本土化的设计,构建“中国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已迫在眉睫。
三、大势所趋:“中国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构建
(一)案件范围的构想:不再单纯以“刑法分章节的方式”限定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解决纠纷、分流案件的方式,案件范围要有限制。我国刑事犯罪主要可分为三大类,刑事和解的进行必须得到被害人同意,所以在案件没有明确的被害人,刑事和解根本无法达成。所以一般认为刑事和解着重适用第一类犯罪。过去未成年人犯罪主要是盗窃等侵财型犯罪为主,但是目前未成年犯罪类型已经向多元化趋势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类型明显增多,如计算机、金融、涉毒、卖淫等犯罪日渐增多,这就造成了各地司法在实践中处理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范围往往比《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更广些的局面。
笔者愚见,“中国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仍需以有明确直接被害人的犯罪类型为主,但可以考虑不完全以“刑法分章节的方式”[4]来规定。本文更赞同,把未成年人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规定在有明确被害人案件的同时,还应根据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其悔罪表现来确定是否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甚至对一些严重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也可以有限度的适用刑事和解。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易冲动,犯罪的主观恶性、客观行为的恶劣程度以及带来的社会危害性往往小于成年人,所以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态度应该更宽容。
(二)适用阶段的设计: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
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三阶段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笔者认为,既然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和解制度旨在最大限度地教育、挽救涉罪的未成年人,帮助他们回归校园,重返社会,那么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和解贯穿于刑事诉讼整个过程更为合适。换言之,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可适用于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五大阶段。在刑事诉讼任一阶段,只要未成年人犯罪符合刑事和解的条件且未成年加害人和被害人有自愿和解的意向,就可以相应的启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
第一,作为刑事诉讼的首要阶段,立案和侦查阶段是相对其他后续阶段,对不履行和解协议这一行为救济更为广泛,所以笔者认为在立案、侦查阶段只要犯罪案件符合刑事和解启动的条件,双方就可以在侦查人员的组织下提起和解,达成和解协议。侦查机关可以就此终结诉讼活动,撤销案件并且也没有必要再移送到检察机关。同时可以引入检察机关对和解案件的监督,从而更加确保和解结果公平公正。第二,审查起诉阶段是刑事诉讼的关键阶段,在我国各地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这一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例也是最多的。因为经过侦查机关的细心侦查,搜集整理证据,未成年人的犯罪事实已基本清楚、证据也已经固定下来,同时未成年犯罪人经过自己的反思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家人的耐心劝导逐渐稳定心神,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此阶段更有利于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开展。具体操作上,检察机关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后,经过审查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可以由当事人双方或检察机关启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检察机关可以在启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的同时设置一定的考察期,在未成年犯罪人成功度过考察期后正式作出不起诉的决定。第三,未成年人犯罪在审判阶段是否适用刑事和解,一直以来备受争议。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公诉案件的和解可适用于审判阶段,鉴于此,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和解也完全可以适用于审判阶段。案件进入了审判阶段也就意味未成年犯罪人马上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也是未成年犯罪人真诚悔罪求得被害人原谅以从轻处罚的最后机会。由于这一阶段已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未成年人已经明确构成犯罪了,所以此阶段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主要作为适用缓刑或从轻减轻的量刑条件更为合理。第四,随着审判终结合议庭作出最终裁判,刑事和解也应画上一个句号。但由于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的家庭、教育以及社会文化等种种原因,当事人双方在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没能达成刑事和解的,在执行阶段也应当给予未成年犯罪人刑事和解最后的机会。未成年犯罪人如果能够真诚悔悟,认真服刑,改过自新,在积极赔偿的同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那么这时的刑事和解协议完全可以作为对未成年犯罪人给予减刑、假释的依据。
“中国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应当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目的不仅仅在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挽救未成年犯罪人,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健康成长,早日回归校园,走向社会。
(三)监督机制的建立:实现从制度启动到后续的全方位监督
我国各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蓬勃发展,但目前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还没有专门关于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条文,所以部分地方司法机关零星地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做出了规定。这些地方“立法”虽然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和解适用条款,但由于自身法律位阶较低、约束力小,公检法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司法难以操作。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监督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运行这一重担,自然也应由检察机关主要来承担。“中国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构建,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非常重要,具体而言:
一是对制度的启动进行监督。启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的前提是案件符合刑事和解的条件。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适用的监督要从和解启动就开始。无论和解在哪一阶段启动,检察机关都应严格监督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能否启动或者和解的启动是否合法,是否有金钱、人情等社会因素介入以促成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启动。二是对和解过程的进行监督。如前文述,“中国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那么不同适用阶段也应配有相应的监督措施。为了确保监督的效果,最理想的状态是检察机关深入参与每一个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例如:首先,立案及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可以派员监督侦查机关处理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全过程。其次,审查起诉阶段。这一阶段的监督只依靠检察机关自身监督管理部门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在完善内部监督机制的同时,利用外部力量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进行监督。再次,审判阶段。此阶段检察机关主要监督法院因刑事和解而做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相关依据是否正当、合法。检察机关认为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和解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以提出检察建议或直接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最后,执行阶段。“中国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之所以可在执行阶段适用,主要考虑未成年犯罪人的家庭状况、受教育程度、社会文化等因素对犯罪人的影响以及未成年犯罪人的悔罪表现,从而给原本已经终结的诉讼程序开一扇小窗监,因此阶段督应主要侧重于审查未成年犯罪人及家属提供的信息是否属实,被害人在此阶段愿意参与和解的具体原因,以及对未成年犯罪人悔悟程度。三是对和解后续的进行监督。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后续的监督,一方面对刑事和解协议的履行情况监督,实时监督当事人双方有无反悔情况;另一方面,把未成年犯罪人置于社会中对其进行改造和矫正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重要的意义所在。
(四)制度的完善:几个细节的再思考
除上述愚见外,在此,最后本文还想对其他几个问题求教于各位同仁:
其一,在全国各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实践中,大部分是由不同阶段的办案机关主持和解,而设立专门的调解机关则是西方国家的一贯做法。笔者认为,为保证和解程序更加公正、合理,“中国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也应当学习借鉴以德国等国家主导模式的做法,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而不应再有司法机关本身主持和解。其二,“中国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完全可以赋予律师在场权利。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被害人之间往往缺少沟通平台,并且他们在司法机关面前也常常表现得很敬畏,不敢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律师作为其委托的人,能够充当他们之间的沟通使者[5]。辩护律师在场,可以帮助双方在和解过程中提出更合理更理性的和解意见,同时也能够有效避免被害人漫天要价等现象。其三,把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灵活运用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中是刑事和解本土化的另一有力举措。我国在2014年颁布的《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中明确把刑事案件被害人因加害人死亡或无赔偿能力而造成生活困难的作为国家司法救助的对象。笔者认为,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下对被害人的救济措施。当加害人确实无能力赔偿时,由加害人申请国家司法救助,由国家向被害人先行垫付赔偿金,加害人通过劳动等在一定时期内偿还国家。
四、结语
在世界范围内,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经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和多元化趋势也越发明显。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需要当代社会的特殊保护,尤其需要区别于成年人的社会制度和司法制度的特殊保护。古以来,儒家都主张,“礼之用,和为贵”。“以和为贵”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精髓,这也与刑事和解所体现的“恢复性司法”共通。在我国,这种“和”理念更应贯穿于“中国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整个过程。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引入区别于成年人的刑事和解制度,构建“中国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不仅使得被害人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得以恢复,有利于加害的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同时更是有利于对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最大限度地节约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1]肖晚祥,张 果.刑事和解的困境与出路[J].法律适用,2010,(4).
[2]黎 莎.两种模式下的西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特征解读[J].公民与法:法学版,2010,(5):34.
[3]孙 勤.刑事和解价值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111.
[4]田文昌.新刑事诉讼法热点问题及辩护应对策略[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277.
[5]岳礼玲.刑事审判与人权保障[M].法律出版社,2010:121.
Reality and Reconstruction:Chinese-style System of 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for the Juvenile
WANG Tong
All around the world,the rising juvenile crime rate and the decreasing age of criminal offenders have become the problems which endanger society safety.The juvenile crim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nction the Chinese-style system of Victim-offender Mediation(VOM)for the juvenile,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VOM for the adult and blends with the idea that harmony is a virtue,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morality,in the meditation process.
juvenile;VOM;system construction
DF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12(2017)04-0049-05
(责任编辑:吴良培)
2017-04-26
王 统,(1993- ),女,山东青州人,山东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博连读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