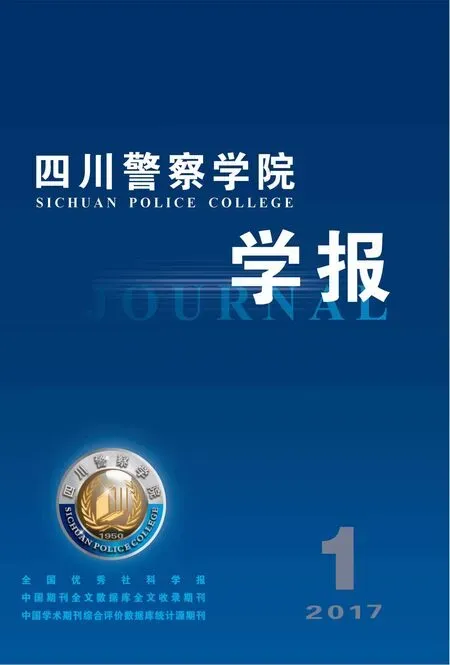违法信息行政公告在我国的历史演变
禹竹蕊
(四川省委党校 四川成都 610072)
违法信息行政公告在我国的历史演变
禹竹蕊
(四川省委党校 四川成都 610072)
随着政府信息公开的推进和完善,违法信息行政公告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目前的研究普遍缺乏历史研究的视角。认真研究中国古代、近现代的相应制度,从源头把握违法信息行政公告的起源和演变,有利于我们对违法信息行政公告形成全面认识。
违法信息行政公告;历史;演变
违法信息行政公告,是指行政管理部门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将其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和制作的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规定的相关信息,通过报刊、网络、电视等媒体,主动向社会公众予以公布的行为[1]。依据行政过程论的观点,行政实施的过程是动态的、复杂的,其间包含了各种行政行为的综合运用,方能确保行政的实效。违法信息行政公告显然是一种确保行政实效的有力举措。
通过建设,中国自上世纪末开始,逐步迈入信息时代。各级各类行政管理部门在行政执法中,普遍将违法信息行政公告作为一种规制手段,在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环境保护、广告管理、土地管理、税收征收、金融监管、商标管理等领域广泛加以运用。实践中违法信息行政公告风生水起,在社会管理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学界对于违法信息行政公告的研究还比较滞后,更为遗憾的是,极少有人对违法信息行政公告的历史源流进行考察,对我国古代运用这一行政管理手段的情况缺乏相应而必要的介绍。由于普遍欠缺历史研究的视角,现有研究缺乏对违法信息行政公告的全面认识,认知难免有失偏颇。有学者将其视作信息社会“新型的政府规制手段、管理方式”、“新型实效性确保手段”[2],更有甚者认为这是我国借鉴日本和韩国制度的产物[3]。但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中国古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将违法信息行政公告作为一种规制工具,并在历朝历代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加以运用和逐步发展。智慧的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利用声誉机制对违法行为、违法事件等违法信息加以公告和宣传,不但可以惩戒违法、教化公众,还可以让公众接收到信息之后了解官府的政令决策,作为行为上的依据和规范[4],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一、我国古代的违法信息行政公告
中国古代,由于信息传播技术不够发达,榜文、告示便成为了官府向民众公布政令、法令和上情下达的重要载体①。据《周礼》、《礼记》、《尔雅》等书记载,先秦时期,我国便已有“玄法象魏”制度,即将法令、公文悬挂于宫门的门阙两侧,用以宣扬、告知百姓。到了周代,“玄法象魏”已是普遍寻常的现象。以后历代各朝皆沿袭此制度来传递政令讯息,在宫门门阙两侧悬挂文书的方式也逐步发展为使用张贴、刊布的告示榜文[5]。告示榜文主要刊布在官方行政机构、地方乡村邻里、商业贸易地区和水陆交通要道。随着社会发展,其内容日渐丰富,由最初的宣扬法令发展到圣旨诏谕、人事升黜和惩处禁令。告示榜文不但成为了官方传播政令的工具,也是一种社会管理的工具,对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6]。到了汉代,布告成为中央向民众发布和传播朝政消息的重要媒介。汉代的布告本质上属于告示而非古代邸报,其内容“既有告老、赦免、登基、改元等一些国家大事,也有大赦天下或通缉要犯的重要律令,还有褒赞吏民、召集贤俊的内容,甚至还包括一些有关盛世祥瑞的社会新闻。”②查阅两汉、唐宋诏令及会典类文献就可看到,“格文榜示”、“版榜写录此条”之类的用语频频出现,一些诏令后也有“布告中外,令使知悉”的要求[7]。唐玄宗就曾为更好地让各方了解案情、消除疑虑,因张琇兄弟手刃杨汪为父报仇一案,令河南府发布告示,广为宣传并解释朝廷对于孝子复仇之义、杀人偿命之律,两者间的取决与审判死刑的结果[8]。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布告和露布是政府主要的传播媒介。这一时期的布告作为政府文告,包含皇帝诏书和行政法令,通常悬挂或张贴在固定地点[9]。宋元时期,地方官府和长官运用榜文、告示公布政令、法令的做法已很盛行,公告违法信息也成为当时的官府惩戒违法、教化百姓、治理社会的一种惯用手段。在宋代,涉及违法信息的官府榜文主要在市曹加以公布,教化风俗、以示劝诫。朱熹任南康军时,所辖区域内两兄弟争夺财产,朱熹在此案判決文书(“晓喻兄弟争财产事”——朱熹集卷九十九)的最后批示,“出榜市曹并星子县门、都昌、建昌县市张挂,晓示人戶知委。”[10]随着告示榜文制度的臻至完备,粉壁告示③也在宋代首度出现。元代则通过明文条例将粉壁制度化,普遍用于遏止盗贼的措施上[11];为惩治特定人户还专门设立红泥粉壁,即在违法犯罪人家门前立粉壁,以红泥装饰而成,以示醒目④。
至明代,基于朝政的需要,以皇帝名义或部院衙门及地方奉旨发布的榜文告示,逐渐融立法、司法和宣扬法律为一体。《明实录》、《明会典》、《皇明条法事类纂》、《条例备考》、《军政备例》等书中记载了大量的榜文告示[12]。这些告示榜文主要用于推行地方政务、端正社会风气、维护社会秩序、传递战讯军情以及特殊政治宣传[13]。朱元璋更是倡导创建了“申明亭”,运用“申明亭”书记十恶、奸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及犯赃至徒者,“昭示乡里以劝善惩恶”⑤。根据调整内容的不同,各类榜文分别悬挂于各部衙门或州县乡里之申明亭。可见,公告违法信息以端正社会风气、维护社会秩序,在明朝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而且,明代对于告示榜文内容的适当性、公平性比较看重。如果内容不当,有违公正,则牵涉到告示的合法性与否。不当的告示榜文,一旦受到台谏、舆论非议之后,就会以撤榜的方式取消[14],且撤榜也需要发布告示予以说明。
实际上,明清时期,不仅君主和朝廷六部发布榜文,各级地方长官和巡按各地的朝廷命官也把发布告示做为治理地方的重要措施[15]。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秋瑾案发生后,面对各界人士的质问和谴责,浙江巡抚张曾敭就发布了安民告示,将秋瑾所谓的“罪状”告知天下,试图缓解民怨压力⑥。在1911年(宣统三年)的“保路运动”中,嘉州知府李立元在成都血案发生后随即签发布告,一方面承认“集会结社固属法律之行为,保路争约亦原爱国之公理”,另一方面提出“罢市罢课抗粮抗捐迹近要挟……倘敢意存破坏……惟有执法相绳”[16]。
二、我国近现代的违法信息行政公告
近代以降,辛亥革命时期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通告”开始出现在政府公文中。如革命党人于1911年11月6日,通过《沪军都督府条例》,成立沪军都督府[17]。王某、徐某等以军政府筹饷为名设定“拼死团”名目,勒捐巨款,并以炸弹、手枪多方恐吓,影响极坏。1911年12月10日,沪军都督府在《民主报》发布《禁止勒捐通告》,指出王某、徐某等人“此种不法行为,实为同胞之蠹。嗣后凡有无赖者借筹饷为名,故意需索,仰即扭送来府,从严惩治。本都督府为顾全大局起见,决不稍予宽贷也。”[18]国民党统治时期,“公文程式条例”规定之外的的“杂体文”中“通告”常与“公告”通用,二者程式和用语基本相同[19],内容也包括了违法信息的行政公告。如1936年(民国25年)10月,陕西省政府就曾发布钱币反假防伪的宣传布告,公告无业游民林福田在京伪造辅币的违法犯罪事实,提醒民众注意辨别、避免蒙受损失,以杜奸欺[20]。
土地革命时期,我党虽然还没有组建起属于自己的政府,但基层革命组织也非常重视违法信息行政公告的运用。1927年1月,湖南省成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曾判决没收一批大土豪劣绅的财产,由省农民协会委员胡某负责清查管理。胡某在清点财物时,私自隐藏了一些贵重财物,企图占为己有。事情败露后,湖南省农民协会立即在报上公布了这一事件和对胡某的处分决定,得到民众的支持和肯定[21]。抗日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3年10月23日,联合发布禁种禁吸烟毒的布告,对陕甘宁边区极少数不法分子,不顾政府禁令,偷运、贩卖毒品的违法行为进行警示,加强陕甘宁边区的禁毒斗争,杜绝死灰复燃的吸毒现象[22]。新中国成立之初,鸦片烟毒依然十分猖獗。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烟禁毒活动,各级、各地政府大量采用布告的形式,利用公告宣传查禁工作,呼吁民众检举揭发,共同抵制烟毒。例如,1952年3月20日颁布的“甘肃省人民政府禁烟禁毒布告”(秘字第五号)就指出“……近查本省少数地区,仍有不法之徒,种植鸦片,贩制烟毒,为害人民,影响生产。特颁布禁令如下:……倘再违犯,或竟敢以武装贩运者,除将其武器烟毒没收外,并从严治罪……各地人民对种植、制造、贩运、吸食烟毒等一切非法行为,均有检举密告之责,各地人民政府对依实检举者,予以奖励。……”[23]
三、我国当代的违法信息行政公告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在突飞猛进的同时也发生了深度变革,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民主法治的进步促使公众的表达积极性和参与热情与日剧增,多元的价值观屡屡发生碰撞。在改革的浪潮中,多种元素的利益纷争频频出现,社会矛盾凸现。面对社会矛盾高发的态势,要想化解各种冲突、凝聚民心,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稳定经济发展的势头,行政方式的变革无疑正是破冰之举。政府唯有转变职能,变管理为服务,关注民生、以民为本,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公众的支持和理解,才能真正带领国民走向繁荣、富强。与此同时,随着上世纪80年代“民主风暴”席卷全球,西方国家主导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以及“合作政府”的变革,逐渐演变为一种国际性浪潮和趋势,各国的福利性质大幅增强,政府职能逐步转化,规制行政(秩序行政)逐步向服务行政(给付行政)迈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建设服务型政府正式成为了中国政府的改革目标,各级政府开始积极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改进和创新执法方式,各种柔性行政方式被广泛运用到行政执法中。
这类以行政指导、行政资助、行政调解为代表的柔性行政方式,与传统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刚性行政方式相比,因缺乏强制约束力,行为方式更为柔和,有效化解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可以大幅提升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同时,这类柔性行政方式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秩序,在确保行政效率的同时兼顾了权利保障,符合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也有利于在和谐的氛围中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因此,成本低廉、对抗性低、可塑性强的柔性行政方式不但受到执法者青睐,也逐渐得到公众的认同。
早在1994年,我国大陆地区就在《审计法》中就规定,审计结果可以向社会公布⑦。这里的审计结果,当然也包括被审计对象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1998年1月1日,大陆地区正式实施了税务违法案件公告制度。2001年7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就上半年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药品广告予以第一期公告,标志着我国违法药品广告公告制度的建立[24]。2002年8月23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卫生部联合发布 《关于建立违法食品广告联合公告制度的通知》(工商广字〔2002〕221号),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卫生部每两个月将通过新闻媒体对违法食品广告进行联合公告,“违法食品广告的生产企业名称、食品名称、主要违法事实(广告内容)”等为联合公告的主要内容。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罚法”⑧、“消费者保护法”⑨、“食品卫生管理法”⑩中也都有关于违法信息行政公告的明确规定。随着信息公开的深入发展,各地在探索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更加普遍地运用这一柔性规制手段,在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广告管理、环境保护、金融监管、土地管理、商标管理等行政执法领域都能见到违法信息行政公告的适用。
四、结语
丰富的史料证明,违法信息行政公告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行为并不是发肇于信息社会的新生事物,更不是借鉴域外制度的产物。虽然中国古代行政法极不发达,但历代统治者都很青睐这种借助社会力量来优化执法效果的管理模式。不过,我国古代官方所作出的违法信息公告内容庞杂,既涉及违法和犯罪行为,也涉及违反伦理道德的信息;从性质上看,某些领域,由于官府行政职能与立法职能、司法职能的界限较为模糊,导致古代的违法信息公告也是兼有政治、行政或司法公告的性质。当然,古代的行为方式与当下相比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当时的违法信息行政公告更多地带有一种警示和劝诫的意味,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类似于行政指导的作用。近代以来的各个时期,我国的行政管理领域中,违法信息行政公告也相对“活跃”。时至今日,违法信息行政公告更是随着互联网、自媒体的发展,随柔性行政方式的推广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今天,研习中国古代制度,全面了解和认知违法信息行政公告的在我国历史演变,并结合域外经验,方能为今后的立法和制度完善提出更好的建议。
[注释]:
①我国历史上告示的称谓有多种,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也有变化。如秦、汉、魏、晋时期称“佈告”者居多,唐、宋、元各代和明代前期,“榜文”、“告示”、“布告”等各称混相使用,此外还有“告喻”、“文告”、“公告”等称呼。明代中叶以后,大概是出于 “上下有别”,并区分其适用地域的范围,君主和朝廷六部的布告称榜文,地方各级政府和长官的布告则称为告示。榜文、告示都是官府针对时弊或某种具体事项向百姓公开发布的文书,二者虽叫法相异,实际是同一性质的官方佈告。与其他官文书、法律、法规比较,榜文、告示具有以下特色:其一,文字比较简洁、通俗,易於为基层民众所理解。其二,内容针对性强。其三,规范性较差,适用效力较短。在古代地方官府官吏有限、信息传播不便的条件下,榜文、告示不仅是公布法律法令和进行法制教育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加强官民沟通、提高办事效率的有效方式。参见杨一凡,王旭.古代榜文告示汇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序言1-7。
②东汉桓帝时期,侍中寇荣因遭权贵的忌恨和诬陷而获罪被布告通缉。他在逃亡途中曾上书桓帝痛陈自己被布告通缉所遭遇的苦楚。参见黄春平.汉代朝政消息的发布——布告[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3):54-56。
③“粉壁”类似一种耻辱刑,官府在违法犯罪人家门前立粉壁,上具姓名,违法犯罪情由,使犯过错之人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感到耻辱,以达到惩戒的目的。《宋大诏令集》记载:“凶狡之徒,希望恩宥,民之多僻,无甚于兹。其八月一日以后,持杖强盗,遇南郊赦恩,不在原免之限,令所在牓壁告示。”连启元.明代的告示榜文——讯息传播与社会互动(上)[M].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 36。
④《元史·刑法志》之“志第五十三 刑法四”中“杂犯”记载,“诸恶少无赖,结聚朋党,陵轹善良,故行斗争,相与罗织者,与木偶连锁,巡行街衢,得后犯人代之,然后决遣。诸恶少白昼持刀剑于都市中,欲杀本部官长者,杖九十七。诸无赖军人,辄受财殴人,因夺取钱物者,杖八十七,红泥粉壁识过其门,免徒。诸先作过犯,曾经红泥粉壁,后犯未应迁徙者,于元置红泥粉壁添录过名。”载中国经济网http://cathay.ce.cn/lzk/yuanshi/zhi/200805/12/t20080512_15429966.shtml。
⑤洪武五年二月,朱元璋鉴于“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宪”,命令“有司于内外府州县及乡之社里皆立申明亭,凡境内之民有犯者,书其过名,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惩戒。”《大诰》可以说是把重刑威吓和说教有机结合的法律文件,颁行后,朱元璋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并将《大诰》列为全国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之后,朱元璋又多次谕天下诸司,要运用申明亭书记十恶、奸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及犯赃至徒者,“昭示乡里以劝善惩恶”。参见怀效峰.明清法制初探[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72。
⑥这一告示宣称秋瑾在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学堂,与武义、嵊县匪党勾结,密谋起事,已派兵破获,查获秋瑾亲笔悖逆字据及枪弹马匹多件,业将秋瑾正法。参见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08-217.
⑦《审计法》第36条第1款规定,“审计机关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⑧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 2条第 3款规定,“影响名誉之处分:公布姓名或名称、公布照片或其它相类似之处分。”
⑨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37条规定,“直辖市或县(市)政府于企业经营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务,对消费者已发生重大损害或有发生重大损害之虞,而情况危急时,除为前条之处置外,应即在大众传播媒体公告企业经营者之名称、地址、商品、服务、或为其它必要之处置”。
⑩台湾地区“食品卫生管理法”第29条第2款规定,“制造、加工、调配、包装、运送、贩卖、输入、输出第一项第一款或第二款物品之食品业者,由当地主管机关正式公布其商号、地址、负责人姓名、商品名称及违法情节”。
[1]禹竹蕊.违法信息行政公告的界定[J].社会科学家,2015,(1):111.
[2]章志远,鲍燕娇.公布违法事实的法律属性分析[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6):47;章志远,鲍燕娇,朱湘宁.作为公共警告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2(2):63页;施立栋.行政上的公布违法事实活动研究[D].浙江大学2012:3、11;鲍燕娇.公布行政违法事实的法律属性分析[D].苏州大学2013:2;汪厚冬.论公布违法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为例[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2):93;梁亮.行政机关公布违法事实行为的法律问题分析[J].河北法学,2013,(4):173.
[3]章志远.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违法事实公布[J].法学家,2012,(1):53-54.
[4]连启元.明代的告示榜文——讯息传播与社会互动(下)[M].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294.
[5]连启元.明代的告示榜文——讯息传播与社会互动(上)[M].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21-26.
[6]连启元.明代的告示榜文——讯息传播与社会互动(上)[M].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36-177.
[7]杨一凡,王 旭.古代榜文告示汇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序言2.
[8]连启元.明代的告示榜文——讯息传播与社会互动(上)[M].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30.
[9]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5.
[10]郭 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八)[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5059-5060.
[11]连启元.明代的告示榜文——讯息传播与社会互动(上)[M].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30-36.
[12]柏 桦.榜谕与榜示——明代榜文的法律效力[J].学术评论,2012,(2):41.
[13]连启元.明代的告示榜文——讯息传播与社会互动(下)[M].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179-246.
[14]连启元.明代的告示榜文——讯息传播与社会互动(上)[M].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32.
[15]杨一凡,王 旭.古代榜文告示汇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序言2.
[16]高国芬.辛亥嘉州布告及知府李立元[J].四川文物,1991,(4):68-69.
[17]邱元猷,张希坡.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辛亥革命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20-121.
[18]邱元猷,张希坡.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辛亥革命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41-142.
[19]任雪浩,李伟华,刘新钰,卢湘.行政公文文种历史源流浅探[J].兰台世界,2001,(8):28.
[20]党顺民.西安发现民国时期钱币反假布告[J].中国钱币,2008,(1):36;43.
[21]张希坡.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与“史源学“举隅[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51-252.
[22]陈子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禁种禁吸烟毒的布告[J].陕西档案,2010,(3):14.
[23]邓宝珊,王世泰,张德生,马鸿宾.甘肃省人民政府禁烟禁毒布告[J].甘肃政报,1950,(3):64.
[24]周大平.公告制度“封杀”违法药品广告[J].瞭望新闻周刊,2001,(30):52.
(责任编辑:李宗侯)
DF3
:A
:1674-5612(2017)01-0021-0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20068);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15SA0082)
2017-01-12
禹竹蕊,(1975- ),女,四川泸州人,法学博士,四川省委党校教授,研究方向:行政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