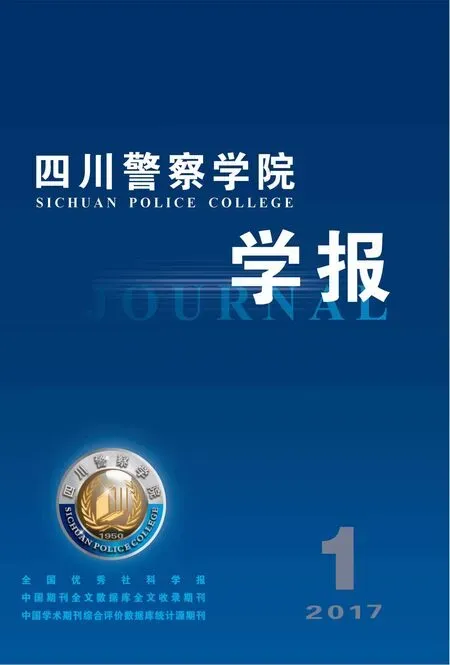毒品再犯问题再审视
张洪成,李 蔚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蚌埠 233030)
毒品再犯问题再审视
张洪成,李 蔚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蚌埠 233030)
我国《刑法》第356条是关于毒品再犯的规定,毒品再犯的成立条件为:前罪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之一,后罪包括所有的毒品犯罪;国外的判决也属于《刑法》第356条“被判过刑”的范畴;前后犯罪行为不需要时间上的限制;单位可以成为毒品再犯的犯罪主体。在毒品再犯和《刑法》第65条规定的累犯发生竞合时,应优先适用累犯条款;在毒品再犯与《刑法》第71条规定的发现新罪的数罪并罚发生竞合时,应当先对毒品再犯进行从重处罚,然后根据“先减后并”的并罚原则进行量刑,这种处理方式并不违反“禁止双重评价”的规则。
毒品再犯;毒品犯罪;累犯;常习犯;数罪并罚
毒品再犯是一个重要的量刑情节,也是国家从严打击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表现形式之一。该量刑情节在我国《刑法》第356条具体表述为:“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刑法》本条款,最早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11条第2款的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决定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1997年《刑法》直接予以吸收,从而形成第356条毒品再犯的相关内容。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界,对于毒品再犯的称谓、成立条件、毒品再犯与累犯、发现新罪的数罪并罚的法律适用等方面都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即立足于毒品犯罪“严打”的刑事政策,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以求教于学界。
一、正名:毒品再犯概念之确立
如何称谓《刑法》第356条,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有常习犯说、毒品特别累犯说、法定从重处罚情节说、毒品再犯说之论争。以下分述之。
(一)常习犯论及评析。
常习犯论者认为,“《刑法》第356条是毒品犯罪的常习犯的规定,而不是所谓毒品再犯的规定,毒品再犯概念应予放弃。”[1]该理论以大陆法系的广义累犯说为基础[2],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按照日本《刑法》,广义的累犯分为普通累犯和常习累犯,“所谓常习累犯,是指累犯者带有其犯罪的常习性,也简称为常习犯。……常习累犯是以行为人反复犯罪的危险性为核心的观念,在《刑法》学上被作为特别的考察对象”[3]。而用毒品再犯来概括毒品犯罪的常习犯,本身并不恰当,因为“一方面,再犯不是一个《刑法》理论的专业指导术语,至少在目前可见的官方认可的教科书中,几乎看不到有关再犯概念的分析内容,其内容不明,成立条件也无从知晓;另一方面,从字面上看,再犯既可以包括‘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的再犯’的累犯情况,也可以包括以毒品犯罪为习惯的常习犯,在未对再犯概念作出说明之前,将常习犯现象包括在‘再犯’概念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常习犯’与‘再犯’是具有重合关系还是具有从属关系难以区分”[1]。
作为一类贪利性的犯罪,毒品再犯的规定本身就是考虑了行为人反复实施毒品犯罪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将其作为常习犯也有一定的道理。故从刑罚处罚的角度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毒品犯罪受过刑罚处罚,又进行毒品犯罪,本身已经显示出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这本身应当属于从重处罚的事由之一。但是该观点的局限性就在于:首先,我国《刑法》采用的是狭义的累犯概念,累犯和常习犯在内涵、外延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区别的情况下,将累犯作为常习犯的上位概念,无疑是不合理的;其次,该论者所提出的毒品再犯并非专有术语的说法,也是对理论与司法实践的误读;再次,按照我国《刑法》理论,常习犯是基于犯罪的常习性即反复实施犯罪的癖性的犯罪。由于《刑法》在构成要件上将常习犯类型化,因而预想行为人实施数次行为以构成常习犯罪,故行为人基于反复实施犯罪的癖性数次实施某种犯罪行为时,就被包含在一个构成要件中,只成立一罪[4]。常见的常习犯类型为赌博罪,而从社会相当性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毒品犯罪本身并未达到如此反复实施的程度。虽然在实践中的确有多次贩卖毒品或者以贩养吸的情形,“常习犯现象不只在赌博、盗窃等场合出现,在毒品犯罪场合也会出现。如‘以贩养吸’的行为人,刑罚完毕后毒瘾复发,或难以支付吸毒所欠债务,在经济支持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又重操‘以贩养吸’旧业,这种现象在实践部门查获的案件中普遍存在”[1]。但《刑法》第356条所涉及的并非仅仅为贩卖毒品,除了前罪限定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非法持有毒品罪以外,后罪则可以是任何一种毒品犯罪。故单纯界定在常习犯属性上,有失片面。
(二)毒品特别累犯说及其评析。
有论者认为,《刑法》本条是专门规定了一个毒品特别累犯,用意显然是为了对毒品犯罪施以更严厉的惩罚。“事实上,《刑法》本条的适用对象,之所以被称为特别累犯,正是因为它与普通累犯,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普通累犯的构成条件之一,是前后两罪有一定的间隔时间的限制,因此‘前罪刑罚已执行完毕或被赦免’的条件,主要是为计算间隔时间的长短而设定的。而本条规定的毒品特别累犯,并无前后两罪间隔时间的限制,再考虑前罪从何时起算,岂非多余?”[5]在该论者看来,毒品特别累犯与总则中的一般累犯、特别累犯处于并列的地位,其立法目的、成立条件和特别累犯具有相似性。而《刑法》之所以将该特别累犯规定在分则中,主要是因为其与特别累犯除了在“犯过罪、判过刑,又犯罪”等成立条件方面存在重大差别外,还因为本条款专门针对毒品犯罪,其针对性较强。
应当说,将本条界定为特别累犯,与总则的规定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我国的累犯,包括一般累犯和特别累犯,都是总则明确规定的量刑情节,其适用会导致禁止缓刑和禁止假释的配套后果;而毒品犯罪的这一特殊条款,目前还不能上升到影响总则的程度,故如果将其与总则中的特别累犯规定等同,势必要涉及对总则条款的解释或者变更,而这在目前看来并不现实,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对第356条的定性应立足于《刑法》的现有规定,特别要重视该条文在《刑法》中所处的体系地位。既然立法明确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累犯,而没有规定毒品累犯,且在表述上对二者加以区别,就应当认为第356条规定的是毒品再犯而不是毒品累犯”[6]。事实上,从实定法的角度看,毒品再犯与毒品累犯也是存在根本性区别的。故本观点的局限性还是比较明显的。
(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说。
有的论者认为,“我国《刑法》第356条规定了对再犯毒品犯罪的行为人从重处罚,此条规定不是已存的累犯制度,也不是将存的再犯制度,而是众多法定从重情节之一”[7]。将本条直接认定为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即使上述几类观点,也都可以归类于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说,但关键在于,《刑法》规定本条的初衷仅仅是为了做一个特殊性的规定吗?理解为一个单纯情节,是否显得过于简单?故整体而言,在上述几类观点都无法有效表达的前提下,可以考虑该观点的成立,但是又有过于笼统之嫌。
(四)毒品再犯说及评价。
毒品再犯说是目前的主流观点,张明楷教授在其《刑法学》教科书中对累犯、再犯、常习犯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剖析,认为:“在当今《刑法》理论中,累犯与再犯已不是等同概念。凡是第二次犯罪的,均可谓再犯,但累犯的成立条件比再犯更为严格。累犯与常习犯也存在严格区别。常习犯是反复实施某种犯罪而形成了犯罪习癖的情况。累犯仅具有形式的基准,即基于纯粹偶然的原因而再次犯罪的,也可能成立累犯;而常习犯的成立具有实质的标准,即必须是作为习癖的发现而反复实施某种犯罪。累犯是因为无视刑罚的体验再次犯罪而被认为再犯罪可能性大;常习犯是因为具有反复实施犯罪的危险性格而被认为反复犯罪的可能性大。但常习犯中可能包含了累犯的情况,累犯也可能发展为常习犯。”[8]在此基础上,张明楷教授承认《刑法》第356条的规定属于毒品再犯,并对其处理方法做出了论述。
事实上,毒品再犯本身属于再犯之一种,这样的认定,除了顾及行为人本身的危险性之外,更多的是考虑《刑法》总则虽然有累犯从重处罚的规定,但对于一些更加严重的行为,需要在总则确定的处罚条件之外再考虑相关的情节,以充分贯彻国家禁绝毒品的坚定立场。
通过以上的介绍及评述,笔者倾向于将《刑法》第356条的规定认定为毒品再犯,其成立的理由除了上述再犯说论者的见解外,还包括:第一,以毒品再犯概括本条款,是属于非常恰当的说法,这可以避免特别累犯说、常习犯说等所存在的与总论的不协调问题,而事实也表明,要完成这一协调,并非朝夕之间可以实现的;第二,当前,毒品再犯的概念已经被理论和司法实践广泛接受,相关的司法解释亦直接以毒品再犯概括本条,该概念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用来特指《刑法》第356条的内容;第三,毒品再犯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其法律后果则仅仅局限于本条款,并不会对整个《刑法》体系或者相关《刑法》理论产生冲击。故笔者认为,将《刑法》第356条概括为毒品再犯,是比较恰当的。
二、解读:毒品再犯之成立条件
正确理解《刑法》第356条,必须对以下几个基础问题进行正确把握:第一,毒品再犯成立之前后罪要求;第二,前后两罪的时间限制;第三,毒品再犯的主体可否为单位。下文将详细阐述之。
(一)毒品再犯成立之前后罪要求。
1.毒品犯罪成立之前罪要求。毒品再犯的前罪必须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或者非法持有毒品罪,这是比较确定的。但是前罪的附加要求“被判过刑”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概念。
由于“被判过刑”的外延较为宽泛,而且《刑法》亦未对其进行刑种上的限制,因此从理论上说,应当包括一切种类的刑罚,既包括主刑,也包括单独判处附加刑的情况,缓刑亦能涵括在“被判过刑”的范围之内。而定罪免刑和不起诉,则无法有效涵括在本条件之内,原因在于:“免刑是免于处罚的意思,而《刑法》本条设定的条件是‘被判过刑’,显然不相符合。但如果《刑法》的措辞是‘受过刑事处分’的话,免刑就符合条件了,因为免刑是以有罪为前提的,判处免刑,也应当视为一种刑事处分;至于不起诉,表明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已经了结了,尚未进入审判阶段,‘被判过刑’自然也就无从谈起”[5]。
“被判过刑”理解上存在争议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被外国法院判处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是否属于毒品再犯的前罪范畴?对此,笔者认为累犯成立条件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本条之理解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于行为人受到外国刑事审判,能否成立累犯,目前存在很大争议。否定说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第10条关于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再依我国《刑法》处理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凡是受刑人在国外实施犯罪行为,经外国法院审判并执行刑罚,其罪依照我国《刑法》应负刑事责任,进入我国境内又犯罪的,应该不承认外国法院审判效力,国外之前罪与国内之后罪并合审理”[9]。按照此观点,“被判过刑”不应当包括外国法院的刑事判决。
而肯定说则认为,行为人受外国司法机关审判并执行刑罚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依照我国《刑法》也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承认其已受过刑罚执行,也可依我国《刑法》再次进行处理。该犯罪人如果在法定时间里在国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时,可以定其为累犯[10]。张明楷教授也认为:“如果对国外的刑事判决采取积极承认的做法,则无疑应宣告为累犯。我国采取的是消极承认,尽管如此,仍然应认定为累犯。因为消极承认的前提是考虑到行为人在外国受到刑罚处罚的事实,而免除或者减轻处罚;同样,在行为人于我国犯新罪时,我国法院也应该考虑行为人在外国受到刑罚处罚的事实,如果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累犯条件,就应以累犯论处。这与消极承认并不矛盾”[8]。“显然肯定说符合《刑法》对于我国公民在外国犯罪的刑事管辖原则,既有利于维护我国对外的刑事管辖权,又有利于对累犯的打击和控制”[11]。按照该观点,对外国法院的刑事判决可以认定为“被判过刑”。
笔者认为,毒品犯罪作为国际罪行,各国《刑法》一般均规定对其具有普遍管辖权,我国也不例外。我国《刑法》典第9条明确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而我国加入的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第2条第1项就规定了各国应当采取可行措施,打击毒品犯罪:“缔约国在履行其按本《公约》所承担的义务时,应根据其国内立法制度的基本规定,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立法和行政措施。”毒品犯罪应当属于各缔约国均需施予以严厉打击的行为。其《公约》第4条第2款第2项规定:“当被指控的罪犯在其领土内,并且不把他引渡到另一缔约国时,也可采取可能必要的措施,对其按第3条第一款确定的犯罪,确立本国的管辖权。”这就表明,毒品犯罪属于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所明确规定的,可以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案件。对于此类案件,我国除了行使管辖权,也存在对国外相关判决、裁决的承认问题。
从毒品犯罪管辖权的国际公约规定看,毒品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的差别在于,普通刑事案件因各国或者地区的特殊情况,可能导致犯罪圈划定、刑罚权行使及其限度等存在较大差别;而毒品犯罪属于普遍管辖权范围的刑事案件,各国在条约规定的范围内,应当尽量保持其犯罪圈、处罚限度等层面的一致性,与之紧密相关的就是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等应当在处罚范围内尽量地保持一致,由此就决定了对于外国相关刑事判决的承认,易言之,这一承认并不是消极的承认,而应当是强制性承认,是对相关公约的贯彻与执行。所以,在毒品犯罪中,对国外法院所做出的毒品犯罪的判决,尤其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判决必须成为我国《刑法》第356条所规定的前罪的范围。只要行为人因为上述犯罪,被相关的缔约国进行过刑罚处罚,均可认为达到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的成立毒品再犯的前提条件。
2.毒品犯罪成立之后罪要求。按照《刑法》本条之用语,毒品再犯成立后罪之要求的“毒品犯罪”,是指违反禁毒法规,破坏毒品管制活动,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12]而从我国的刑事立法看,主要就是指的《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12个具体毒品罪名,既包括前罪之外的10个罪名,也包括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本身。
有论者认为存在特殊情况,比如《刑法》第352条规定的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由于该法条不像《刑法》第347条那样包含一个走私毒品行为,也不像《刑法》第350条那样包含一个走私制毒物品行为,所以对走私毒品原植物种子或幼苗的行为,就只能定普通的走私罪,而不能定毒品罪。从而也就不能构成毒品罪的特别累犯[5]。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正确理解该条款,就涉及对毒品犯罪的理解,笔者认为,毒品犯罪应当是一种统称,凡是涉及《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所有犯罪,均可谓毒品犯罪,这也是现行法理论和实践的一致看法。
(二)前后两罪的时间限制。
《刑法》第356条的表述并未体现时间上的限制,由此就带来了争议,有论者就认为,成立毒品再犯,必须具备“前罪刑罚已执行完毕或被赦免”的条件[13],这一理解建立在对累犯认知的基础上,应当说具有一定的机械性,因为《刑法》第65条所规定的累犯,其条文明确表述了时间上的要求。而这也正是《刑法》单独对毒品再犯作出此规定,并主张从重处罚的根据之一;否则,直接套用第65条的累犯规定即可解决问题,无须对毒品再犯单独规定。
如有论者就明确指出,虽然《刑法》第65条关于累犯的规定中,确实有“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一语,但是不能想当然地就将其适用于毒品再犯。对一个因毒品罪而正在服刑,且又犯了新的毒品罪的行为人来说,完全可以并且应当既适用数罪并罚,又按毒品罪特别累犯从重处罚。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情况也是完全可能发生的,比如在假释期间,又犯了走私毒品罪,或者在劳改农场改造期间,又犯了非法持有毒品罪,等等”[5]。这一论断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为《刑法》本条只规定了“被判过刑”,而未明确要求刑罚执行完毕,从其字面理解,只要是被人民法院定罪并判处了相应的刑罚,即可谓“被判过刑”。而且本条的立法初衷正是为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在行为人已经被法院确定有罪的情况下,仍然实施毒品犯罪,反映了其严重的人身危险性,出于对社会公众健康等权利的维护和对社会秩序的维持,对其从重处罚亦完全有必要。故笔者认为,前后两罪不需要时间上的限制,而且后罪亦并不以前罪执行完毕或被赦免为已足。而且从法律效果看,其也不会产生《刑法》第65条累犯的法律效果,如假释、缓刑等的限制等,即本条只是出于严峻的毒品犯罪形势而采取的一种严厉打击的态度,对其他条款并无普遍的法律效力。
(三)毒品再犯主体之确定。
关于累犯是否适用于单位,一直存在较大争议,马克昌教授认为:“单位犯罪的特点决定了不符合累犯制度的立法意图”[11],故应当否定单位累犯。而很多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如有论者指出:“单位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类型同样具有人身危险性,这是单位累犯成立的实质根据和解决单位累犯实践问题的基点。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不能改变单位的整体性人格实体,只要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无根本性消减,单位累犯的成立就有正当根据”[14]。笔者认为,单位构成累犯应当不存在任何障碍,因为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单位和自然人一样可以成为犯罪主体,这就意味着其已经被赋予一定的人格,虽然这种人格要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实现,但是并不能否定其犯罪性。而且将其排除出累犯的范围,亦无充分的根据,对此不再赘述。本文主要探讨毒品再犯的主体问题,既然单位本身可以构成累犯,那么对于成立规格相对更为简单的毒品再犯来讲,更应当不成问题。
在《刑法》第347条到第357条所规定的12个罪名中,有4个是涉及单位犯罪的,而且毒品再犯的前罪中,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就属于单位犯罪。笔者认为,如果前罪属于单位所犯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后罪又是单位实施的可以由单位构成的犯罪,则完全应当按照《刑法》第356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三、司法实务:毒品再犯之处罚原则及评析
毒品再犯之处罚,主要应当考虑其与《刑法》第65条累犯、第71条发现新罪的数罪并罚之关系问题,因为这涉及是否重复评价以及如何实现罪刑均衡问题。
(一)毒品再犯与累犯竞合之法律适用。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00年纪要》)第4条规定:“对依法同时构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今后一律适用《刑法》第356条规定的再犯条款从重处罚,不再援引《刑法》关于累犯的条款。”自该文件出台,学界对其质疑的声音就未曾中断过。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08年纪要》)对这一条款进行了重新解读,其中的第8条规定对毒品犯罪的再犯采取以下处理方法:(1)只要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不论是在刑罚执行完毕后,还是在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犯罪的,都是毒品再犯,应当从重处罚;(2)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犯罪的,应当在对其所犯新的毒品犯罪适用《刑法》第356条从重处罚的规定确定刑罚后,再依法数罪并罚;(3)对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从重处罚。
以上两个规范性文件在毒品再犯和累犯不发生交叉的情况下,其处理方法是一致的,即均按照第356条的规定进行从重处罚;而在二者发生竞合的情况下,采取的立场则存在着差别,《2000年纪要》认为应当排斥累犯规定的适用,而《2008年纪要》则采取双重的从重处罚的立场。如果按照《2000年纪要》的精神,排斥累犯的适用,就意味着符合累犯条件的毒品再犯可能产生相较于累犯为轻的法律后果,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张明楷教授就认为:“这一做法存在疑问。本来,《刑法》第356条是鉴于毒品犯罪的严重性才做出再犯规定的,如果对符合累犯条件的也仅适用该再犯规定,则意味着对符合累犯条件的毒品犯罪人可以适用缓刑、假释,而其他犯罪的累犯则不得适用缓刑与假释,这显然有失公允”[8]。在理论界,《2008年纪要》存在的问题就是对于同一个量刑情节,是否有双重评价的嫌疑,有论者就认为:“这一规定也并非没有疑问。亦即,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是否具有两个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如果持肯定回答,显然是对一个事实进行了不利于被告人的重复评价。如果持否定回答,就意味着完全没有必要同时引用《刑法》总则关于累犯和分则关于毒品再犯的条款,只需要引用总则关于累犯的规定即可”[8]。故《2008年纪要》本身也存在过于武断的嫌疑。
针对累犯和毒品再犯出现竞合时的处理方法,有观点认为:“当犯罪人的行为满足累犯条件时,不可适用《刑法》第356条而放纵犯罪人,而应适用第65条的累犯条款;当犯罪人的行为满足数罪并罚的条件时,不可适用《刑法》第356条,而应适用第71条的数罪并罚”[7]。即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五年以内,又犯《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毒品犯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都应当适用《刑法》总则关于毒品累犯的规定,承担累犯的法律后果,从而避免法律适用之间的极大不平衡,只有在其不符合累犯规定的情况下,才适用《刑法》第356条的规定。有论者做出了更为详尽的论述“应当以《刑法》系统解释和目的解释方法来正确解释《刑法》第356条的适用,对于符合累犯条件的毒品再犯,直接适用《刑法》总则关于累犯的条款从重处罚,不适用缓刑和不得假释,不再适用分则第356条再犯的规定。换句话说,《刑法》分则第356条的规定仅仅适用于不符合累犯条件的毒品再犯。唯有这样,才符合立法原意,才真正体现《刑法》对毒品犯罪严厉打击的立法目的”[15]。也只有这样处罚,才能真正实现毒品再犯和累犯在法律后果上的协调,并充分体现国家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态度。
应当说,以上对两个纪要的评价都是比较客观的,而且也有论者对毒品再犯与累犯竞合时的法律适用方法进行了分析,为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笔者认为,正确适用毒品再犯与累犯,归根结底要从累犯、毒品再犯设置之初衷、设置毒品再犯之价值考量这两个角度来寻找答案。以累犯为例,《刑法》规定累犯主要着眼于行为人之敌视法规范的态度,而这种敌视的态度必须进行严格的限制,因为“首先,不能简单地从重新犯罪的事实中推论行为人的顽固的反规范性,重新犯罪可能是因为单纯的意志薄弱,也可能是受第三者的影响。其次,对累犯加重处罚,与德国《刑法》第46条规定的量刑原则相冲突”[4]。因此,为了避免过分扩张累犯可能形成的重复评价或者将本不属于犯罪性的因素纳入刑法评价范畴,形成罚不当罪的情况,德国现行《刑法》用“前科”取代累犯概念,并将其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即“只有行为人在自己以前实施同种犯罪或类似犯罪而被判刑后对社会规范的效力很清楚的情况下,自然反抗社会规范,因此刑罚被提高的,才属于这种情况”[16]。事实上,无论是累犯还是前科概念,本身均考虑了行为人反规范的人格态度,而这种态度应当限定在与犯罪的密切联系上。由这些立法例可以发现,累犯、前科、再犯等之所以加重处罚,其更多的还是立足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
虽然我国《刑法》总则规定的累犯制度考虑了时间上的限制,但是对于前后罪之种类的关系则考虑较少,于毒品再犯而言,则恰好是考虑了前后罪之种类,这契合了德国《刑法》中所设立的作为从重处罚情节之一的前科制度,从这个角度看,毒品再犯所反映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或者行为人对法规范蔑视的态度远远超过一般的累犯,故我国《刑法》第356条规定的毒品再犯从重处罚,应当认为其重点关注的是行为人敢于同国家禁毒规范直接敌视的法态度。
从适用的法律效果看,毒品再犯的规定,是在《刑法》总则规定的累犯无法有效覆盖至相关行为时的一种补充性规定,因此,从处罚的周延性上讲,毒品累犯属于毒品再犯的下位概念,所有的毒品累犯均属于毒品再犯的范畴。因此,毒品犯罪的再犯成立条件并不必然受到累犯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刑法》修正案所修正的累犯概念及其成立范围,并不必然影响本条款的成立范围。笔者认为,从成立主体上讲,只要具备相应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成立毒品再犯,单纯的刑事未成年人并不能成为排斥毒品再犯的成立条件,即使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对之也可适用毒品再犯的规定;从主观方面看,其罪过形式也应当理解为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这和累犯的成立存在着重大差别,但是限于毒品犯罪的罪过形式均为故意,故此区别的意义不明显,但从理论上可以作此界定。
毒品再犯的条文设置,亦是从严打击的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毒品犯罪一直采用的是“严打”的刑事政策,这从三次“严打”的行动中可窥见一斑。三次“严打”行动中,毒品犯罪均属于重点整治的犯罪类型之一,而且在规模性的“严打”活动结束后,我国又接连发动了几轮禁毒人民战争,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在毒品犯罪治理上的坚定立场——坚决从严、从重打击毒品犯罪。虽然现在刑事犯罪治理的策略转变为宽严相济,但没人否定,在毒品犯罪的治理中仍然是严厉打击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故从这个基本的刑事政策出发,可以断言,我国《刑法》规定毒品再犯的最终立足点仍然是“严打”,故对于行为人同时符合总则关于累犯的规定、分则关于毒品再犯的情况下,优先采用可能对犯罪人处罚较重的条款。这与当前世界性两极化刑事政策的立场亦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在行为同时符合累犯和毒品再犯条件的,应当优先适用累犯条款;在行为不符合累犯条款时,则适用毒品再犯的条款,从而实现从重处罚的目的:既包括量刑上的罪刑均衡(包括不允许缓刑),也考虑行刑中的假释等。采用择一的从重的处罚原则,不会违背立法本意与现行的毒品犯罪刑事政策。
(二)毒品再犯与《刑法》第71条竞合之法律适用。
行为人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被判处相应的刑罚,在刑罚执行期间,又犯毒品犯罪的,按照《刑法》第71条的规定应当进行“先减后并”的数罪并罚,即“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应当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相较于第70条对漏罪“先并后减”的并罚原则,“先减后并”在起点刑期与总和刑期上都可能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刑法》分则第356所涉及的毒品再犯的处理方法,也是从重处罚,如果两个条款之间发生竞合,还能否同时适用两个条款,分别进行处罚呢?分别处罚会否违反行为中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有论者就对此展开过详细的论证,认为即使同时采用这两个条款,也并不必然导致评价上的重复,如,有论者就指出:“即使这种双重评价客观上不能完全忽略,考虑到《刑法》对毒品再犯的特别规定应当优先于禁止双重评价原则得到遵守和适用,故不妨把此情形下对毒品再犯的双重评价和双重从重处罚理解为对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一种例外,其目的在于加大对毒品再犯的惩罚力度,以遏制毒品再犯。”[6]通过特殊的立法政策来淡化可能出现的重复评价,也是一种思路,毕竟毒品再犯和第71条的立法目的、价值取向等存在重大差别。
而有的论者则直接认为,对毒品再犯同时适用《刑法》第356条和第71条进行并罚,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的基本原则,因为“如果将这种特别规定视为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不予适用,那么对毒品再犯的处罚与其他再犯(不包括累犯)的处罚均仅适用《刑法》第71条之规定实行‘先减后并’的并罚方法进行处罚,则《刑法》第356条对毒品再犯从重处罚的‘特殊’规定就形同虚设,无法彰显,试图通过特别立法来加大对毒品再犯惩罚力度的目的也就无法实现”[15]。
事实上,我国《刑法》第71条规定的对犯新罪采用“先减后并”的并罚原则,就表明在毒品再犯和第71条竞合时,应当首先根据第356条对新犯的毒品犯罪根据从重的要求进行量刑,然后根据第71条进行并罚,但在并罚时,可以通过适度的限制加重方法来弥补量刑上的畸重情形。而在理论上如果必须探究《刑法》第71条是否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也应当将之放在整个《刑法》理论中探讨,因为在“先减后并”的适用过程中,只要涉及后罪从重处罚的——无论是法定的还是酌定的,均应当分析是否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而从现行的司法过程看,这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刑法》第71条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而并不涉及从重或者重复评价的问题,这种“先减后并”司法技术的操作完全可以通过相应的自由裁量权来适当限制,从而避免所谓的双重评价的问题,毒品再犯和《刑法》第71条的关系亦是如此。
四、结语
毒品再犯是一个成熟且恰当的称呼,用其指代《刑法》第356条不存在任何障碍。而从毒品再犯的成立条件及其与累犯的相互关系来看,应当认为,毒品再犯的成立范围远大于毒品累犯,而且在一定范围内二者存在竞合的可能。当一个毒品犯罪行为无法充足毒品累犯的规定时,直接援引第356条关于毒品再犯的规定,从重处罚即可;而在行为同时符合毒品再犯和累犯的条件时,直接适用累犯的规定即可达到从重处罚、罪刑均衡的法律效果。当行为人在刑罚执行期间又犯毒品犯罪的,可以同时适用《刑法》第356条和第71条,并通过适当的刑罚裁量权,来实现罚当其罪的目的。
[注释]:
①以下文章中均明确使用了毒品再犯这一术语:朱建华:《毒品犯罪再犯与累犯竞合时的法律适用》,《人民检察》2006年第9期;李炜、肖华:《论毒品再犯与一般累犯之适用关系》,《法学》2011年第9期;李海滢:《毒品再犯之我见》,《当代法学》2002年第2期;张洪成、黄瑛琦:《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曾粤兴,蒋涤非.毒品犯罪若干刑罚问题新议—以大陆刑法理论为研究视角[J].北方法学,2007,(3).
[2]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900.
[3][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M].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61.
[4]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346;408.
[5]高铭暄,马克昌.中国刑法解释(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502;2503.
[6]高贵君,方文军.数罪并罚情形中毒品再犯的认定问题[N].人民法院报,2007-09-26.
[7]常秀娇,吴旸.再犯毒品犯罪情节的定性与司法适用[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2,(1).
[8]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513;515;1013.
[9]喻 伟.刑法学专题研究[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359.
[10]赵廷光.中国刑法原理[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590.
[11]马克昌.刑罚通论[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23-424;412.
[12]张洪成.毒品犯罪争议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0.
[13]刘家琛.新刑法条文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1560.
[14]陈 伟.单位累犯的内在结构与理论剖析[J].当代法学,2012,(1).
[15]佚 名.关于审理毒品犯罪再犯案件的几个问题[EB/OL].http://www.110.com/ziliao/article-214727.html,2011-04-25. [16][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M].冯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064.
Reflections on Drug Recommitment
ZHANG Hong-cheng LI Wei
The 356th article in Criminal Law is the provision about the drug recommitment.The establishment conditions of drug recommitment are the following:the former crime is smuggling,trafficking,transporting,manufacturing or illegally holding drugs crime,and the latter crime includes all drug-related crimes;Foreign judgments also belong to the sentenced to punishment category of the 356th article in Criminal Law;There is no time limit for the former and latter criminal behavior;Units can become the subject of drug recommitment crime.When competing relations of the provision about the drug recommitment and the recidivist in the 65th article in Criminal Law occurred,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application of recidivism provisions;When competing relations of the drug recommitment and the provision about combined punishment for plural crimes of the discovery of new crimes in the 71st article in Criminal Law occurred,drug recommitment should be punished severely first,and penalty should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sentence after reduction of concurrent punishment measures,which is not against the rule of the prohibi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double.
drug recommitment;drug crimes;recidivism;habitual offender;combined punishment for plural crimes
DF6
:A
:1674-5612(2017)01-0026-09
(责任编辑:吴良培)
2017-01-07
张洪成,(1978-),男,江苏新沂人,法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刑法学;李 蔚,(1992-),女,安徽合肥人,安徽财经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