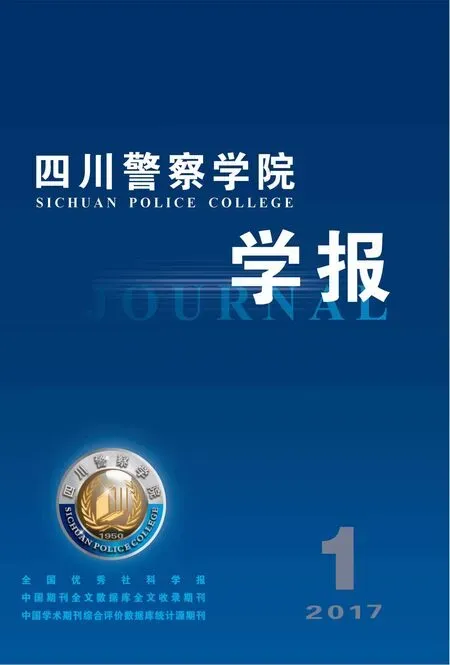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告人的自愿性及其考察方式
虞惠静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2249)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被告人的自愿性及其考察方式
虞惠静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2249)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是司法改革的重点。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利于在制度上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理念,缓解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司法效率。然而,司法资源的节约就不得不考虑其对个案实体正义的影响。现有的制度构建中对实体正义的保障中强调了坚守证明标准,不得转嫁证明责任,侦查阶段不得进行协商等程序性问题,而忽略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的考察。旨在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法层面和程序法层面分别讨论认定被告人自愿性的评价标准,厘清不同评价标准背后的依据,探讨认定被告人自愿性时应当纳入考察的因素以及采取的认定方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效率;实体公正
伴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不断增长,如何提高司法效率成为21世纪司法工作主题之一。如何解决有限的司法资源与持续增长的法律需求之间的矛盾成为摆在法律人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课题。我国创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是缓解当前我国紧张的司法资源和大量案件之间的矛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在保障公正的前提下,通过控辩双方之间的协商程序,简化审判程序,以此达到提高司法效率,鼓励被告人主动认罪认罚的目的。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前提是不能损害司法公正,即简化程序不能影响到司法机关对正义的保障,效率的提高不能以公正的牺牲为代价[1]。认定被告人是否是真诚自愿地认罪认罚,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地认罪认罚对于刑事案件量刑的从宽幅度有重要意义。认定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保障正义与公正的重要部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兼具实体法和程序法两种性质[2]。若想厘清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认定问题,就有必要去探查自愿性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上的不同含义,如此才能更好地界定自愿性认定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定位。在司法实践中,正是由于对两个层面上的自愿性的含义有所混淆(当然也不排除现存法官责任制度和法官考评机制对法官判断的引导,此处不论),在认定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问题上就容易走向极端。
对于自愿性的判断本身就是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行为是可以通过证据进行推定的,而对动机的判断则存在技术上的困难。我国的审判强调证据的重要性,这容易导向的一个错误认识就是法官判案需要的是绝对理性。但是,人的行为难免带有或多或少的主观性,必须要承认主观判断也存在部分的合理性,尤其是对于判断那些本身就难以用客观证据来证明的认罪动机来说,法官在主观上的判断也要得到重视,不能一棍子打死。正是对主观判断的忽视,导致实践中对被告人的自愿性的认定停滞不前,法官对于难以用证据表明的心理活动往往避之不谈或者不去深究,在实践中甚至存在仅凭借被告人的口头认罪就认定其属于自愿认罪认罚而予以从轻处罚的情况。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案件需要评价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什么因素应当被纳入自愿性的评价系统之中?自愿性的评价结果应当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对量刑的结果又有何影响?这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程序法和实体法层面上“自愿性”解读的分歧与对立
探求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含义,要使自愿性的含义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价值追求相符合。那么首先就要厘清在不同层面上,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能够从宽处理的原因和其背后的价值追求。
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的背景来看,不得不说其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的产生有着相类似的社会原因。美国的辩诉交易始于19世纪初,当时,美国的犯罪率节节攀升,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使社会动荡不安,在巨量案件的压力之下,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弊端逐渐显露,有限的司法成本与繁琐的普通审判程序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提高司法效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此时,辩诉交易这一诉讼制度的出现,加速了诉讼程序,大大提升了案件的审理效率,也缓解了司法资源紧张的矛盾。在《布莱克法律辞典》中,辩诉交易的定义是:“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者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质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3]。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辩诉交易是指在开庭审理程序之前,控诉方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被告人的有罪答辩作为筹码,换取检察官以较短刑期、较轻的罪名或者较少的罪数控诉。当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之间的协议达成,法官通常仅用判决确认协议的内容与效力,以此作为形式上的审查而不再进行实质上的审判。由此,辩诉交易节省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使得交易双方实现了利益平衡,更重要的是保证了大量案件堆积情况下司法机器的正常运转[4]。
在相似的背景下,随着我国进入社会的转型变革时期,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限的办案力量和频发的轻微刑事案件之间的矛盾,也将案多人少的问题推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同时《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将公正和诉讼程序正当性的司法价值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公正和程序正当的保障无疑需要司法资源的支持,这也就给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带来的新的挑战,即坚守公正司法和刑事诉讼程序正当性的底线,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需求的推动下,寻找适用于我国现有国情的改革突破点。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运而生[5]。
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产生背景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从程序法的层面上去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产生,其背后最主要的改革动力就是司法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说,国家在法律上承认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行为可以取得法律上对其犯罪行为的从宽处理,其背后的逻辑是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行为减轻了司法人员的负担,节约了司法资源,使得司法资源可以更多地投入到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中去[6]。那么如果在程序法的层面上去讨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行为,这个行为就可以定义为“承认自己犯下了被指控的行为以及对该行为可能带来的否定的法律评价后果予以接受”,据此,法官就可以缩减庭审流程直至做出有罪判决。那么,无论是被告人做出认罪认罚表示的动机是什么,在其他条件也符合的情况下,都应当适用认罪认罚从宽而取得较轻的刑罚。因此,在程序的层面上去认定“自愿性”,就相当于默认了只要被告人不是在被胁迫、逼供等不法情况下做出了认罪认罚的行为,那么就认为他的行为已经符合了程序法上“自愿”的要求。
但是在实体法上的层面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得到重视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该制度本身就充满人文关怀的因素,其与我国宽严相济的政策理念不谋而合[7]。被告人之所以能够被从宽处理,原因在于其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构成了犯罪,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错误的一面并自愿接受法律的制裁,换言之,被告人被从宽处理是因为其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和再次犯罪的可能性的降低。刑罚的目的之一就是特殊预防,在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情况下,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就有所降低,这体现在判决中就是较轻的刑罚[8]。
在这个层面上,如果被告人仅仅是做出了认罪认罚的表示,以此达到减轻刑罚的目的,并不能当然地认为其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降低,对其当然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也就是不合理的。只有被告人做出了认罪认罚的意思表示,并且这种意思表示是出于其自愿,才能认定其特殊预防的必要性降低,对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才是正当的。
二、自愿性认定的理论和实践困境之因
正是由于自愿性在实体法层面上和程序法层面上的概念界定存在区别,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究竟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还是兼具两者的因素,在学界上尚在热烈讨论之中,无论是最高法还是最高检都尚未明确地指出其性质。这就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带来了困扰,实践中不乏被告人出于对减轻处罚的渴求而主动表示认罪认罚,然而其在之后的行为中则可以强烈感受到其认罪认罚并非真心,甚至于对于受到惩罚的结果是十分抗拒的,只是出于对国家司法机关的畏惧,认定即使不认罪认罚案情也早晚水落石出,而自己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想法而选择了认罪认罚,甚至于在之后的执行之中,口出恶言,对司法人员及其不尊重,对司法程序及其不配合,对司法执行充满厌恶甚至存在肢体上的反抗行为。如果我们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定义为一项纯粹的程序法,因为被害人存在认罪的表示,就可以认定其自愿,在其他条件也符合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对其从宽处理。如果我们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定义为一项纯粹的实体法,那么明显在这个案例中被告人不存在任何反悔自省的心理因素,那么也就不能对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如果仅从这个案例来看,仿佛我们从实体法的层面去定义“自愿性”会更加合理,也更加符合法律的公平正义的价值。但是,这样的推理也是不合理的。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绝不妥协的”[9]。专家学者们一直在强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效率的提升不得以损害公正为代价,在此理念之下又强调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有罪证明标准是不可动摇的一根红线,是必须把握的一条底线,要时刻谨记基本犯罪事实必须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同时对被告人的“认罪”和“认罚”行为进行鉴别[10]。其中,坚持证明标准和审查犯罪事实都是法律技术上的问题,是建立在证据和法律事实上的操作性的问题,而如何鉴定被告人是否是真诚地“认罪”和“认罚”,是犯罪心理上的问题。在足够的技术手段面前,行为是可以鉴别和复原的,但是心理依旧是难以捉摸的。如果在分析被告人的真实内心想法上花费过多的精力,那么显然是有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的初衷的,更无益于效率的提高,但是如果完全忽视被告人做出“认罪”“认罚”行为的心理行为,无异于放任被告人不思悔改,带着钻法律空子降低刑罚的想法要做出“认罪”“认罚”的表示。
由于对动机的判定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对其进行考量必然要降低效率,而完全不对其进行考量又损害了法律的正义价值。我们就可得知,单纯从实体法的层面或者是程序法的层面去定义“自愿性”都会得出荒谬的结果。我们必须承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兼具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因素,如此才能得到一个合理的结论。在对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判断这一环节,要平衡实体层面和程序层面上的价值追求。
我们将自愿的程度分为几个层次。首先,自愿的高级状态就是出于悔过的心理,承认实施了控方所指控的行为,并且愿意承担该行为可能带来的刑罚,积极主动地挽回被害人的损失,主动地进行赔偿,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等。在这种情况下,实体法层次和程序法层次上的价值得到了统一,此时对被告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是毫无争议的。自愿的中层状态就是被告人出于减轻刑罚的心理,权衡利弊后做出了认罪认罚的表示,同时对所要面临的概括的刑罚后果也予以承认。这种情况下,被告人的认罪认罚行为确实带来了司法效率提升的后果,其认罪认罚的出发点虽不是完全出于悔过心理,其配合调查,主动认罪认罚的行为的动机虽不受法律的鼓励,但也是法律所允许的。最低状态的自愿是被告人在未受到欺诈、胁迫的情况做出了认罪认罚的表示。
对自愿的程度进行分类界定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判断是否对被告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上,其次则是影响量刑从宽的幅度。
笔者认为,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其他条件都已符合的情况下,对于轻微刑事案件,只要被告人达到了自愿的最低程度,就应当对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在程序上从简,量刑上从宽。对于重大刑事案件,只要被告人的“自愿”达到了中层状态以上的程度,就应当对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而如果被告人的自愿仅达到了自愿的最低状态,原则上也应当对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但是,若被告人对案件的主要事实避重就轻,敷衍搪塞或者妄图推卸责任减轻自己的罪责的,或者与司法机关的配合上存在明显的心理甚至肢体上的抗拒的,或者对司法机关以及执法人员及其不尊重的,或者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恐吓威胁等,诸如此类能明显证明其毫无悔意,再犯危险性高的行为,就不应对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并由司法人员在文书中做以简要说明。
另外,不同层级的自愿应当纳入量刑从宽程度的考察范围之中,被告人的自愿性越高,对其进行从宽处罚的理由也就越充分,体现在量刑上就是从宽的幅度更大。自愿性的分级,要在量刑上有所区分。
三、自愿性评定的考察因素和方法
对自愿性的评价本身就是一个对主观因素进行衡量的行为,尽管主观因素必然外化为一定的客观行为,但是由外在的客观行为去推演主观动机是一个逆向的思考方式,是由外在推测内在,由现在推测过去,其中需要证据等辅助,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有可能造成法官对自愿性的错误判断,因此,将更多的合理因素纳入对自愿性的评价系统之中,才能更加准确地对被告人的自愿性程度进行定位,进而更加准确地进行量刑,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双重价值在最大程度上达到统一。现下通说所强调的法官对于案件材料的审核、庭审上的询问和依照职权进行调查,此处不再赘述[11]。
(一)明确主动认罪和被动认罪的区分。
主动认罪,是行为人完全自发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是触犯法律的,出于真诚的悔悟,真心实意地承认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自愿接受法律对自己的行为的纠正,这是一种完全的、彻底的认罪。而被动认罪是行为人出于外界的强力因素的作用,被迫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性,其对自己的过错的承认是不得已的,其对自己的行为所要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是抗拒的,只是出于对法律的畏惧而接受了这种结果。我国刑法尚未对主动认罪和被动认罪进行严格的区分和定义,但是在自首制度的规定中对两者的区分已经有所体现,主动认罪在自首制度中的体现就是主动自首,而被动认罪在自首制度中的体现就是被动自首。同样的,用以判定主动认罪和被动认罪的学理上的通说也可以用来判定自愿性的程度,主动认罪对应的是自愿的最高状态,被动认罪对应的是自愿的中层情况和最低情况。
(二)将赔偿程度作为自愿性判断的因素。
如今学界主流的刑罚根据论和盛行的恢复性司法理念都主张,被告人主动赔偿的行为,能够体现其意欲减轻自己的危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补偿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损失的积极态度,这说明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的降低,对于这种态度,法律应当做出积极的评价。而赔偿是否能够影响到量刑,就要去考量赔偿的程度是否已经足够弥补被害人的损失、赔偿的行为是否在实际上减轻了损害的后果,赔偿的程度是否足够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因此,最经典的赔偿是赔偿影响量刑的模式就是“悔罪→赔偿→被害人谅解→量刑从宽”。
赔偿程度可以影响量刑背后的原因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体层面上被告人认罪认罚可以从宽的理由是一致的,因此,将赔偿程度作为考量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考量依据之一也是合理的。赔偿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动机,可以辅助判断被告人自愿性的层次,此时,赔偿程度对量刑的影响模式大致为:“悔罪→赔偿→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高→量刑从宽”。
这两种从宽模式背后的法理依据是相似的,在被告人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并同时取得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的情况下,无论是采取哪一种模式,其取得的结果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量刑的从宽。而在某些情况下,被告人对赔偿数额漫天要价,提出完全不合理或者显然超出被告人承担能力的赔偿要求,或者出于对被告人的仇视心理,即使接受了对方的足够的赔偿,也拒不原谅被告人,此时如果按照第一种模式,被告人就无法获得从宽处理,其积极赔偿的行为无法得到法律上的正面评价,有打击被告人悔罪赔偿积极性的倾向。而如果被告人选择认罪认罚并且主动做出了足够的赔偿,那么即使被害人并没有明确表示谅解,也可将被告人主动赔偿的行为作为判断其自愿性层次的一个因素,通过第二个模式给予其赔偿行为的正面评价。
赔偿的程度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判断因素,对于赔偿程度对自愿性的判断,一般来说,赔偿数额越多表明犯罪人悔罪的决心越大,其人身危险性降低程度越高,同时赔偿数额越大,对受害人损害的修复效果越好,因此,法律上对赔偿行为的评价也就更加积极[12]。但是同时还要考虑被告人赔偿的能力。在赔偿程度对量刑的影响上的讨论,学界已有激烈的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三)慎用社会调查报告。
如果出于绝对的正义的追求,那么为了追求对自愿性层次的准确定位,法官有必要了解被告人潜在的社会危害性和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可以通过社会调查报告体现出来,因此,有人主张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引入社会调查报告,以此来判定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动机,或者用以辅助参考是否对被告人采取认罪认罚从宽。笔者对此持坚决的反对态度,现阶段下,将社会调查报告引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任何一个环节之中都不够成熟,即使在判定被告人认罪认罚的主观动机这一环节中,对社会调查报告也应当持最谨慎的态度。理由如下:
首先,社会调查报告中主要包括对被告人的性格特点、道德品行、家庭情况、成长环境、智力水平等情况,这些内容首先不能成为证据,因为它与案情事实无关,它既与被告人行为时的主观状态无关,更加不涉及行为时的客观表现[15]。仔细考察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大多数信息都应该被归入品格证据的范畴,而在定罪和量刑程序相分离的国家,鉴于“那些包含被告人前科和不良品行的社会调查报告很可能会导致法官的预断和偏见,最终可能使无罪的人被错误定罪”[13],品格证据一般要被排除在定罪程序之外,以此避免品格证据对法官的误导。但是在我国,定罪量刑程序是一体化的,此时引入社会调查报告,必然存在程序上的一系列冲突。
其次,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可能存在调查者的主观和片面之词,通过走访、调查等方式获取的信息难以保证真实性和准确性。
其三,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耗时耗力,这在根本上就违背了认罪认罚制度构建的初衷。
(四)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是否应当纳入自愿性的考量因素。
在公诉案件中,根据罪行相当理论和刑罚个别化理论,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不能作为刑罚裁量的情节,也不具备成为酌定情节的理由[14]。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是考虑到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前提是犯罪人真心实意地悔过,因此取得被害人谅解应当能够反映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的降低。这个推论看似合理,背后却存在逻辑上的漏洞。这里的推理逻辑是被告人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可以推出其是诚心悔过的,再可以推出其人身危险性的降低,最终推出可对其从宽处理的结果,也就是“取得被害人谅解→诚心悔过→人身危险性降低→从宽处理”。那么,取得被害人谅解就必然可以推出被告人是诚心悔过的吗?显然不是的,被害人作为案件的受害者,受到伤害后一段时间内身体或内心的创伤都尚未修复,此时对犯罪嫌弃人带有憎恨仇视的主观情绪,即使被告人出于诚心地悔过,积极地补偿受害人,挽回受害人的损失,被害人也有极大可能依旧强烈要求从严处罚,若因此就不对被告人从宽处理,是否有重回报应论的风险?甚至于,在审判结束之后,随着时间的逝去,被害人对被告人的仇视情绪淡化,逐渐开始理性地对待犯罪人,此时才表示对犯罪人的表示谅解,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行为在常理上是应当可以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的,但是由于被害人限于一时的愤恨心理,拒不表示谅解被害人,在判决之后哪怕被害人的态度有所转变,也于事无补。还有的情况下,被害人已经表示谅解,但是受到身边人的鼓动,媒体的推动等,仇恨心理又起,这时又当怎么处理呢?更何况“取得谅解”本身就是一个难以量化的标准,过于强调被害人是否谅解,那么被害人主观情感的变化就会导致认罪认罚协商过程的随意变更,不仅将严重影响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常运行,也与其提高司法效率的初衷背道而驰。
因此,笔者主张,将被害人是否原谅排除出认定自愿性层级的系统之外,而替代以“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并且在实际上对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有所助益”。至于是否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对案件处理情况的意见,应当被听取,但不应当影响到依法作出的决定[16]。
四、结语
在对被告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时候,要加强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动机即自愿性层次的判断,要细致地考察被告人悔改表现的真实性及其程度,不能不分真假轻重、漫无目的地对被告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要真切地把握对被告人自愿性的考察因素,要在最大程度上使被告人所承担的刑罚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争取认罪认罚从宽的双重价值追求得到同时实现。尤其要重视自愿性程度分级对量刑从宽幅度的影响。
[1]陈卫东.公正和效率——我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两个目标[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5):95-97.
[2]陈 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探究[J].犯罪研究,2016,(4):23.
[3]布莱克法律词典[M].北京:北京市进出口有限公司出版社,1990:248.
[4][5]廖 明.辩诉交易:美国经验与中国借鉴[J].法治论坛,2009,(4):194.
[6]王瑞君.“认罪从宽”实体法视角的解读及司法适用研究[J].政治与法律,2016,(5):113.
[7][10]陈光中、马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重要问题探讨[J].法学,2016,(8):3.
[8]毛煜焕.修复性刑事责任的价值与实现[D]:华东政治大学,2015.
[9][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97.
[11]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J].中国法学,2016,(2):61.
[12]高铭暄,张海梅.论赔偿损失对刑事责任的影响[J].现代法学,2014,(4):112-114.
[13][14]王贻飞.论社会调查报告对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借鉴[J].当代法学,2010,(1):52-54.
[15]王瑞君.刑事被害人谅解不应成为酌定量刑情节[J].法学,2012,(7):132-135.
[16]陈光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问题研究[J].法律适用,2016,(11):10.
Voluntary of Defendant and Method for its Investigation under Leniency System
YU Hui-j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eniency system is a major point in judicial reform,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lementing policy of combining punishment with leniency,alleviating conflict that many cases but few labor in judiciary authorities, optimizing judi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moting judicial efficiency.However,effect of saving judicial resource on substantive justice of individual case has to be considered.The safeguard of substantive justice in existing system construction ha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procedural problems,such as holding testification standard,forbidding to transfer testification responsibility,forbidding to negotiate on the stage of detection,etc.,but ignored investigation to defendants’voluntary in leniency system.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evaluation standard of affirming voluntary of defendant respectively from substantial law and procedure law in leniency system,clarify basis of different evaluation standard,discuss factors included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t method for affirming voluntary of defendant.
Leniency System;Voluntary;Efficiency;Substantive Justice
DF6
:A
:1674-5612(2017)01-0127-07
(责任编辑:吴良培)
2016-12-15
虞惠静,(1993-),女,浙江温州人,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刑事法学。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