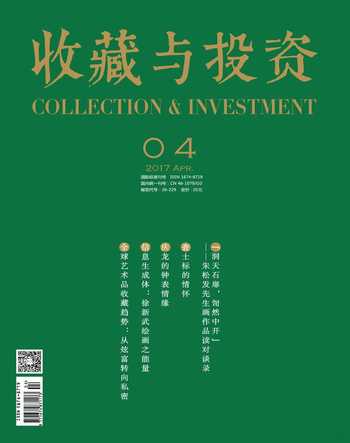韦力:洪亮吉更生斋:藏家五等之分,性情耿介之果
韦力



“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板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从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
这段引文虽然有点儿长,但对爱书之人来说,几乎都能把这段话烂熟于心,应当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给藏书家排座次,虽然在这段引文之前,也有人谈到藏书以及藏书的水准等等,但是明确地把藏书家进行归类,以上的这种说法却从未见出现过。
从内容上看,这段话把藏书家分为了五个等级,虽然作者没有说明这五个等级孰优孰劣,但是业界将此视之为等而下之的排列方式,也就是说,排在最前面的考订家,作者认为是最高级的藏书家,而排在最后面的掠贩家,则是藏书家体系中的最末一等。
自这段话诞生之后,直到今天,还有着不同的声音,且不管这种排序方式对还是错,至少藏书家或者文献研究家,都会本着这段话,来展开评说,即此可见,这一段话对业界影响有多大,而这段话的作者就是洪亮吉。
洪亮吉为什么要给藏书家排列出个等级来?他没有仔细说明,甚至我怀疑他这段话也是随口一说,因为这不是一部著作,甚至不是一篇文章,仅是他在其它著作中的一段话,这部著作就是洪亮吉所撰的《北江诗话》。
诗话这个题材,凡是搞文史者,当然都很熟悉,其所谈主要就是跟诗人有关的掌故轶闻以及诗作背后的事情本末。这部《北江诗话》当然也是如此,里面所谈,都是作者洪亮吉摘引或者评论历代诗人的诗作以及故事等等。这种写作方式有点儿类似于今日的微博,因为每一则诗话长短不一,短的仅二三十字,最长的也就三百字左右,但是在这些诗话之中,却夹杂了这么一段对藏书家的评价,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
洪亮吉对藏书家的这段评价,不知道是不是只是随口一说,因为在《北江诗话》里,这段话的前面和后面,甚至整部著作之中,都再没有扯上跟藏书家有关的话题。这段话出自该书卷三的第一句话,而此后的一段,就是评论南宋的诗文了,已经跟藏书家没有了丝毫关系。
洪亮吉的这个随口一说,却引起了藏书家们的高度重视。按其所排,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说出是五个等级,但是他的这段话却被后世的藏书家总结为“藏书家五等”。
从这五个等级看,排在最前面的,是考订家和校雠家,如此看来,洪亮吉更看重以藏书做基础而能写出重要著作的学者。排在第三等的则是收藏家,应该说收藏家才是藏书的正途,或者说是主体,而洪亮吉把他列在了第三等。即使就是第三等吧,至少这是五等中的中间位置,但是,他把大藏书家黄丕烈和鲍廷博列在了赏鉴家的位置。这个排列顺序多少让后世爱书人有些心里不平。然而,洪亮吉却把书店经营者列为掠贩家,这应该说是一大进步,也就是说,經营之人也算是藏书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总之,从这五等的排列方式可以看出,洪亮吉更看重的是著作而非收藏本身,应该说,他是用学者或者作家的眼光来看待收藏本身,这种看法直到今天,也应该说是社会对藏书家的主体印象。
洪亮吉的这个分法,当然令藏书家不是很满意,比如晚清民国的大藏书家叶德辉在《书林清话》里,针对洪亮吉的这个分法进行了辩驳。因为叶德辉的这个看法,代表了藏书家的大多数,所以,我把他的这段话也录在这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将此文跟洪亮吉的那个分法对照着看:“洪亮吉《北江诗话》云:……吾谓考订校雠,是一是二,而可统名之著述家。若专以刻书为事,则当云校雠家。如顺康朝钱谦益绛云楼、王文简土祯池北书库、朱彝尊曝书亭,皆著述家也。毛晋汲古阁,校勘家亦藏书家也。钱曾述古堂、也是园,季沧苇振宜,赏鉴家也。毛氏刻书风行天下,而校勘不精,故不能于校雠分居一席。犹之何焯义门读书记,平生校书最多,亦止可云赏鉴,而于考订校雠皆无取也。与洪同时者,尚有毕制军沅经训堂,孙观察星衍平津馆、岱南阁、五松园,马徵君子日璐丛书楼、玲珑山馆,考订、校雠、收藏赏鉴皆兼之。若卢转运见曾雅雨堂、秦太史恩复石研斋,以及张太史敦仁、顾茂才广圻,则纯乎校勘家也。若康熙朝纳兰侍卫成德之通志堂,乾隆朝吴太史省兰之艺海珠尘,刻书虽多,精华甚少,然古书赖于传刻,固亦有功艺林。但求如黄丕烈《士礼居丛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既精赏鉴,又善校勘,则亦绝无仅有者矣。”
虽然叶德辉并不完全同意洪亮吉的分法,但还是本着这个体系,做了一定的补充和新的分类而已,即此可见,洪亮吉的这藏书家五等观,对业界影响有多大,而他本人也喜欢藏书,并且还有一定的藏书量,我倒是很好奇,他把自己归到了这五等中的哪一等?可惜,他没有进一步地说明。
洪亮吉的祖上也本是官宦之家,比如他的八世从祖洪远,就是南京的工部尚书,而曾祖洪璟,也是位重要人物。当年洪璟跟赵熊诏结为了儿女亲家,因为赵在朝廷中势力较大,故其女婿洪案在朝中被提升得很快,而这洪寀就是洪亮吉的祖父。但是,赵熊诏的父亲赵申乔,曾经兴起过戴名世《南山集》案,致使戴名世族人大多被杀,这件事使赵家结下了很多的仇怨,为此也影响到了洪家,后来赵家被查出时,把洪家也牵连了进去,这使得洪家迅速衰败了下来。到了乾隆十六年,洪亮吉的父亲也死在了他乡,而那时,洪亮吉只有五岁,母亲带着五个孩子只好回到了娘家。
洪亮吉的母亲因为是知县的女儿,所以有一定的文化,她每天督促儿子用心苦读,常彻夜达旦。有一天洪亮吉读到《仪礼》中“夫者,妻之天”这一句时,母亲忽然痛哭良久,说:“吾何戴矣!”洪亮吉从此以后,为怕母亲伤心,每遇此句则跳过不读。因自幼见母亲辛苦,故其一生事母至孝。其外祖父家有南楼藏书,洪亮吉曾撰《南楼赠书图记》:“先是外王父嵋峨君,喜贮书,有田十双,岁以半所入购积轴。历数十年,而仓粟未满,书签已盈。又赴洛之后,增蓄异书,校阁之佘,兼存别本。每年朱明入序,赫日县庭,陈万卷于轩楹,散群函于室牖。”
洪亮吉天性嗜书,因此特别得外祖母钟爱,其程度迥异于其他诸孙。洪亮吉十岁时,有天陪外祖母曝书,外祖母随手抽出数卷教其读书,并感叹:“吾家代衰矣,能读是者,其惟甥乎?”童年经历,给洪亮吉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成年后多次请人绘下忆母图、读书图,并请诸多好友题跋。
未曾出仕前,洪亮吉曾入朱筠幕府,为其校书,《洪北江先生年谱》载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先生以馆谷不足养亲,买舟至安徽太平府,谒朱学使筠。”进入朱筠幕后,洪亮吉结识了邵晋涵、王念孙、章学诚等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馆开,江浙搜采遗书,安徽省设局太平,洪亮吉又应太守沈业富之聘,总司搜采遗书之事。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孙星衍来信邀请洪亮吉入陕西巡抚毕沅幕,并在信中力陈毕沅钦慕之情,洪亮吉于是前往陕西,在毕沅幕中校勘古籍,参与编纂地方志数种,并写出了《公羊古义》、《汉魏音》等。在贵州任学政时,因贵州地处偏远,书籍无多,洪亮吉于是购买了大量经、史书籍,又广设书院,将书籍放置在各府书院中,以便士子读取,同时刻了不少时文诗集。
洪亮吉考取举人之后,乾隆四十九年他参加会试。在那个时候,洪亮吉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这一科的主考官是蔡新和纪晓岚,他们两人都希望洪亮吉被录取。但是洪亮吉的房考官不知什么原因,阅卷的速度最慢,这使得监察御使郑澂“以得卷迟,疑之欲移置四十名外”。这样的结果当然让纪晓岚不愿意,于是纪就跟郑争执了起来,争执的结果比预想的还要坏,最终,洪亮吉没有被录取。
五年之后,开考恩科,洪亮吉也去参加考试。本场的主考官是朱珪,朱也听到过洪的名气,朱也跟纪晓岚一样,希望洪亮吉能够被录取,并且考得第一名。关于这段事,《洪北江先生年谱》中有记载:“欲暗中摸索得先生作第一人。及得李君赓芸卷,有驳策问数条,以为先生,拟第一。复得朱君文翰卷,用古文奇字,又以为先生,遂置李君卷第六,而以朱君冠多土。及拆号,而先生名在第二十六。及相与叹息,以为名次亦有定数云。”
其实科举考试远不如戏剧里说得那么随意,在古代有着一套极其严格的制度。因为是匿名阅卷,阅卷官也只能从文意上来猜测某个试卷是哪位考生所书。朱珪猜测了一番,最后,他所关注的试卷在拆封之后,发现不是洪亮吉所答,这让爱才如命的朱珪也只能望卷兴叹。但是,洪亮吉有其先悲后喜的福分,到殿试的时候,乾隆皇帝把他钦点为第二名榜眼。然而,这位洪亮吉的耿介性格,并不因为被皇帝的慧眼识珠而增加多少感激之情。
到了嘉庆初年,皇帝想整顿朝纲,让大臣们提出改革的建议。那时洪亮吉正在任翰林院编修,按照规定,翰林没有给朝廷提意见的职责,但是,他还是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奏章,通过成亲王转给了嘉庆皇帝。洪亮吉这份奏章里的用语很是尖刻,其中有这样的词句:“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数十年来,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所遭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定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土大夫渐不顾廉耻,……”
他的这些话直把矛头指向了嘉庆帝,这等于说,皇帝所领导者,都是一群庸才。他的这个指责当然让皇帝大为震怒,于是把他交给刑部,让军机大臣们审判,结果以大不敬的罪,把他判处为斩立决。据说洪亮吉听到这个结果后,面无惧色,并且还写了首诗,诗中有这样一句:“丈夫自信头颅好,须为朝廷吃一刀。”但是,在众人的求情下,皇帝还是放了他一马,只是判了他个流放罪,把他押送到新疆的伊犁,并且下旨告诉洪亮吉,“不许作诗,不许饮酒”,可能这是对一位诗人的最痛苦的惩罚方式吧。
其实,洪亮吉这个人不止对皇帝这样,甚至他对自己的座师也照样顶撞。昭梿的《啸亭杂录》有这样一段记载:“戊午年(嘉庆三年,1798年),大考翰林。公(洪亮吉)上《平邪教疏》,深中当时窾要,人争诵之。朱文正公招之入都,欲荐于朝。先生乃于朱座首斥其崇信释道,为邪教首领之语。朱正色曰:‘吾为君之师辈,乃敢搪突若尔?先生曰:‘此正所以报师尊也。又讥王韩城相公为刚愎自用,刘文清公为当场鲍老,一时入座,无不被其讥者。”
我们上面讲到,朱珪是洪亮吉的座师,并且洪亮吉还曾经在朱筠之幕,而朱珪还是朱筠之弟,洪亮吉完全不管這一套,他认为指责老师,正是爱师。其实,他不止是对他的座师如此,当年翁方纲是诗界的名流,而洪亮吉照样在《北江诗话》中贬斥翁方纲作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即此可知,洪亮吉就是这样一个耿直的性格,所以,他通过成亲王给皇帝上谏议书,也就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但是,他的运气如我所说,并不坏,比如他被流放到了伊犁,仅过了百天,就遇到“皇恩大赦”。这么短的时间又回来了,而且这仅仅的百十天,他也并没有遵守皇帝给他的禁令,他写了不少歌咏伊犁的诗句。
其实,洪亮吉并不甘心只是做一个藏书家或者是诗人,他也有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政治抱负。他曾写过一篇《治平篇》,里面谈到了社会人口激增的问题。到乾隆末年,中国的人口已经近3亿,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洪亮吉经过一系列的分析,认为人口的增长速度远比社会资源的供给陕得多,他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必然成为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洪亮吉的主张跟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极其相像。但是,按照中国人的固有思维方式,一定要排比出任何事情都比西方发现的早。比如洪亮吉的这个人口论述,就被专家考证出比马尔萨斯的那篇论著早了5年。甭管早了几年吧,总之,洪亮吉也有着很浓重的忧国忧民之心。
无论在朝在野,洪亮吉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著述与校勘上,其藏书处有卷施阁、红豆山房、墨云轩、晓读书斋、更生斋及收帆港等,这些斋名的变更与他的心境有着极大的关系,尤其是更生斋及收帆港。《更生斋文集·西圃记》记载:“楼之后架平台,以眺东北隅巽宫楼、玉梅桥及杨园、陆园诸胜,名台日曙华,名楼日卷施阁,名楼以下日红豆山房。楼前皆叠石为小山,石径曲折,莳古梅及红豆、金粟、春桐、紫薇共十数株,春秋二时可慰岑寂。迤西南得平屋二层,因其旧而新之,名其北日更生斋。斋有后楹,列架藏所著地理书木刻于内,名日墨云轩。墨云轩之右复道以通于南,亦二楹,名收帆港,盖于惊涛骇浪中得归藏息于此,是以名也。”
癸巳年秋来到江苏常州访古,洪亮吉故居是必访之地,其址位于常州市戚墅堰延陵东路西狮子巷口20号。出租车司机是本地人,说起常州的名人,他使劲推荐我去看张太雷故居,途经天宁寺时,他又极虔诚地让我看天宁寺宝塔,说这是中国最高的宝塔。我看了看,原来是一座现代化的十三层大楼,只是外形做成了宝塔状,这让我哭笑不得。在我概念中,宝塔就应该是木制、石制或者砖制,这样装着电梯的宝塔,不知让唐僧来扫此塔,他会有怎样的感受。
洪亮吉故居极好找,门口悬挂着两块牌子,左边是“洪深纪念室”,右边是“洪亮吉纪念馆”。洪深是近代电影戏剧理论家,为洪亮吉的六世孙,看来,洪家人都在文艺方面有着特殊的才能。从外观看,旧式的门楼应该是近年仿建的,但台阶上铺的青石却是新旧杂陈。大门敞开着,两位看门的老者在闲话家常,近日常州大雨,因此没有什么游客,他们也落得了清静。
正厅的门口悬着一副对联:“家参越水吴山界,诗在三唐两宋间”,正厅中悬有匾额“风雪授经堂”,匾下为洪亮吉画像,与常见的肩上斜背一枝戟的画像不同,这张画像里的洪亮吉站在一棵松树下,手挂画卷,身旁是一卷书帙及一函古籍。
来此之前,我并不知道洪亮吉还有风雪授经堂这个斋号,回来后搜集洪亮吉的资料,《清史列传》中的《洪亮吉传》中有“六岁而孤,母蒋贤明,督课严,风雪夜授经至鸡鸣”之句,洪亮吉事母至孝,估计这“风雪授经堂”即出自这个典故。
整座故居现存三进,第一进为门厅,风雪授经堂为第二进,第三进为洪深纪念室。事实上,洪亮吉故居是作为常州名人纪念馆在使用,虽然主体上仍然是洪亮吉。两侧的厢房里,悬挂着常州的一些名人介绍,其中一间又专门辟作周璇纪念堂,墙上挂着有关周璇的资料,窗沿下陈设着一张小方桌。我對周璇没有什么兴趣,如果墙上挂着的是吴彩鸾介绍,那我倒会仔细阅读一番。
室内临窗的地方设着一张小方桌,桌上胡乱地摆放着开水瓶、梳子和肥皂盒等杂物,还有半滩水渍,生活气息极浓,这些东西与周璇显得格格不入,刚才在后面看到楼上搭着临时床铺和棉被等物,知道门口见到的两位老者平时就宿在这里,因此知道这些杂物应该是他们放的。
可是正准备离开时,我突然注意到桌面是石制的,上面还刻着许多字迹,这让我停下了脚步,想看个究竟,但是因为下雨的缘故,屋内光线极暗,我拉开了灯,但灯光极暗,于事无补。
我只能勉强看清石桌下半部分的字迹,赫然见到有“洪君墓志铭”字样,又有“阳湖孙星衍篆”字样,心里陡然一跳,这竟然是洪亮吉墓志铭的原物,而这原物居然变成了放置杂物的桌子,这种处置方式让我在情感上难以接受。
然而这意外继续发展,我看见对面展室的相同位置也放着一个方桌,桌页也是石头,上面放着一双雨鞋及穿过的袜子。我移开鞋袜,由于光线原因,同样只能辨出一半的字迹,上面刻着“皇清诰授”、“翰林院编”及“君墓志”等字。
洪亮吉的墓志铭及其墓志铭盖儿,竟然回到了他的故居,并且在故居内受到了如此的待遇,这让我大感不平,于是我走到大门处问那两位老者:“你们知道屋里那两块石桌是什么吗?”其中一位老者说:“哦,那可是好东西,真东西。那是从洪亮吉墓上挖出来的,他们不要,就搬到这里来了。”老者说话时态度极和蔼,看着我的表情有如邻家后生,这反而让我意识到自己语气上的无礼。
虽然这里游人稀少,但是他们并未因游客稀少而怠慢,故居内外收拾得极干净,唯一不相称的就是我刚才看见的杂物。我想起那一滩水渍,可能是放置雨伞时所致,这样大的雨他们仍然来维持故居的正常运作,我又不忍去责难了。
闻老者所言,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两块碑石的价值,但这个说法却给我以提醒,因为我一直查不到洪亮吉的墓具体在哪里,于是马上向两位老人请教,但可惜的是,他们也不知道,只是跟我说:“早就没有了,都盖房子了。这些东西因为不吉利,所以没人要,就扔到了这里。”
这个答案当然非我所愿,心中又升起了一丝的无奈,看来,只有在读书人或者藏书人心目中,洪亮吉才是洪亮吉,对于普通的常州老百姓来说,他不过是一个死去的古人,其具体意义在哪里?跟他们无关,他们也没有兴趣,常州名人太多了,与张太雷相比,洪亮吉又算得什么呢?
洪亮吉在历史上的名声,更多的被目之为著名的诗人,他的诗作按照张维屏在《听松庐诗话》中的评价:“洪北江诗有真气,亦有奇气。”但是,洪亮吉自己并不看重他在这方面的才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读书只欲究世务,放笔安肯为词章。”再加上他那口无遮拦的憨直性格,因此,李慈铭在《越缦堂诗话》中认为洪亮吉作的一些诗“尤叫嚣”,而张维屏也同样指出“未免失之太快”。
但袁枚却不这么看,袁认为洪的诗有着“天风海涛之奇,云蒸霞蔚之彩,已照耀耳目。古之人欤?古之人也。”袁枚的这个评价可谓极高,但洪亮吉的诗是否真达到了他所说的这个高度?我不好评价,但是,洪亮吉在诗学方面的贡献,被后世称道者,则更多的是他跟黄仲则之间的友谊。
黄仲则就是黄景仁,他本是北宋大文豪黄庭坚的后人,在他四岁时,父亲就病逝了,他七岁那年,认识了洪亮吉,自此两人成为了莫逆之交。因为黄仲则早卒,洪亮吉帮他处理了后事,两人的惺惺相惜有着太多的故事,我在此也就不再展开细谈。
但后来,洪亮吉又跟孙星衍成为了生死之交,洪亮吉曾经说:“平生性命视知己,得一死友殊堪夸”,可能正是受孙星衍的影响,洪亮吉对经学也有研究,为此也引起了袁枚的不满,这之间也有太多的趣事,有兴趣了解细节的朋友,可以去查看相关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