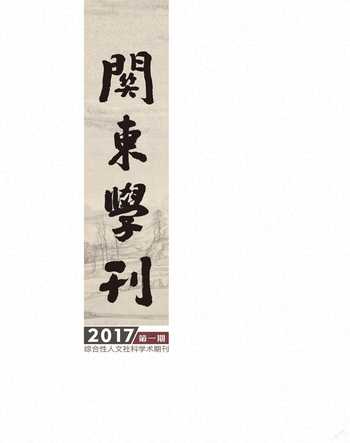现代戏剧史上的胡适与鲁迅
[摘 要]在世界戏剧史上,挪威戏剧家易卜生被公认为“现代戏剧之父”,他创作于1879年的著名戏剧《娜拉》,还被后人推崇为女权运动的“独立宣言”。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鲁迅是较早介绍易卜生的一个人;而完整准确地介绍易卜生的戏剧作品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倡“易卜生主义”,进而尝试性地创作出充满现代文明意识的白话戏剧《终身大事》的胡适,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戏剧第一人。以塑造以人为本、自我健全的戏剧人物为首要目标的现代戏剧,是从胡适主编的《新青年》“易卜生号”正式起步的。
[关键词]现代戏剧;胡适;鲁迅;易卜生主义
[作者简介]张耀杰(1964-),男,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29)。
一、胡适主编“易卜生号”
1918年1月,《新青年》杂志从4卷1号起改版为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轮流主编的白话文刊物。由胡适主编的4卷6号首开先例,集中介绍易卜生的戏剧作品和艺术追求,号称“易卜生号”。
在“易卜生号”的首要位置刊登有胡适的长篇论文《易卜生主义》,文章分六部分,胡适在第一部分首先介绍“易卜生主义”的创作方法:“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1882年,他有一封信给一个朋友,信中说道:‘我做书的目的,要使读者人人心中都觉得他所读的全是实事。(尺牍一五九号)”
中国现代戏剧史以及现代文学史上的“写实主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就是由胡适通过《易卜生主义》较为完整系统地介绍进来的。可惜的是,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戏剧史,都刻意回避了这一历史事实。
在第二部分里,胡适主要介绍了易卜生戏剧所展现的家庭生活的阴暗现实,也就是他所说的四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做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胡适认为,《娜拉》一剧的男主人公托伐·海尔茂,就是这四大恶德的代表人物。
《娜拉》的英文原名是ADollsHouse,意思是一个玩偶的家庭,剧中的女主人公娜拉就是易卜生所说的玩偶。胡适和罗家伦合作翻译的ADollsHouse的第一部中文译本改名为《娜拉》。罗家伦的北京大学同学潘家洵,后来把这部戏剧更加准确地直译为《玩偶之家》。
娜拉是一位富商的女儿,郝尔茂当律师的时候,曾经利用他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帮助娜拉的父亲度过商业危机,娜拉的父亲就把女儿嫁给了郝尔茂。八年前,在娜拉将要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郝尔茂由于过度劳累得了重病。医生告诉娜拉说,郝尔茂必须出国到暖和的南方疗养一年,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娜拉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便假冒已经病危的富商父亲的签名,通过丈夫的同学尼尔·柯洛克斯泰律师从银行借到一大笔钱。在随后的八年中,她通过节衣缩食和帮人做零工悄悄地归还着贷款。这件事不仅是她的私人秘密,而且是她引以为自豪的快乐源泉。
八年后,郝尔茂当上一家合资股份银行的经理,他的老同学柯洛克斯泰恰好是这家银行准备辞退的职员。就在娜拉为丈夫能够“拿大薪水,分红利”而興高采烈的时候,柯洛克斯泰找上门来,威胁娜拉说要揭发她八年前伪造签名的事情。刚刚还在甜言蜜语地呵护妻子的郝尔茂,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变脸,他气急败坏地怒斥娜拉说:“这八年工夫——我最得意、最喜欢的女人——没想到是个伪君子,是个撒谎的人——比这还坏——是个犯罪的人。真是可恶极了!……”
柯洛克斯泰在初恋情人林丹太太的善意劝说下,主动退还了娜拉八年前留下的字据,一场危机由此化解。郝尔茂不再担心妻子的违法丑闻会连累自己的美好前程,就很快恢复了对于妻子的呵护态度,并且装腔作势地表示说:一个男人赦免了妻子的过错,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
郝尔茂在这一突发事件中的态度转换,让娜拉看清了更深层次的事实真相:自己在丈夫的心目中只是一个玩偶,郝尔茂平常叫自己是“小宝贝”“小鸟儿”“小松鼠儿”“我的最亲爱的”,并且给自己一点钱去买糖吃、买化妆品用、买好衣服穿,只是为了让自己讨男人欢心,而不是让自己拥有个人的思想、个人的选择和个人的尊严。于是,娜拉当面对郝尔茂表示说:
“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托伐,我知道大多数人赞成你的话,并且书本里也是这么说。可是从今以后我不能一味相信大多数人说的话,也不能一味相信书本里说的话。什么事情我都要用自己脑子想一想,把事情的道理弄明白。”
正是为了“学做一个人”,娜拉第一次做出自我健全的自主选择,留在她背后的是“砰”的一声关门声,全剧就在关门声中拉上了大幕。
在《易卜生主义》的第三部分,胡适介绍了易卜生戏剧中的三大社会势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在第四部分里,他通过对于《国民公敌》的介绍,指出了易卜生笔下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残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想要维新、想要革命。”
《国民公敌》中的男主角斯铎曼医生最早发现当地温泉可以用来建造疗养浴池。当地人觉得有利可图,便筹集资金建造了几处浴池,吸引各地游客避暑养病,还聘请斯铎曼担任负责卫生监督的官员。
随着游客增多,当地经济开始走向繁荣,洗浴的人当中却出现了一种流行病。斯铎曼从浴池里取出水样,寄给一所大学的化学试验室,化验结果表明,由于他的岳父经营的皮革厂污染了水源,又由于浴池里的水管安得太低,导致浴池里产生了有害病菌。
斯铎曼向市长和浴场主提交报告,建议对浴池进行重新改造。考虑到改造浴池要花费很多资金,并且要歇业一两年,市长和浴场主拒绝了此项建议。斯铎曼据理力争,当地的报馆却不肯刊登他的报告,印刷厂也不肯替他印宣传材料。斯铎曼要召集会议发表演说,全城的人都不肯给他提供演讲场所。他费尽心机找到一个会场,当地居民不但不听从他的建议,还把他赶下台去,然后通过表决宣布他是国民公敌。第二天,斯铎曼的市长哥哥还亲自免除了他的医官职务,他的岳父也来告诉他留给女儿和外孙的遗产此前已经全部换成浴场的股票,他的房东也来赶他搬家,他的两个儿子在学校里面先被同学们围攻而后又被校长停课。在这种情况下,斯铎曼依然不肯屈服于多数人唯利是图的蛮横顽固,并且说出了最著名的一句台词:“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在第五部分里,胡适主要谈了易卜生的政治观念。易卜生起初是一个极端反对国家观念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在亲眼目睹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他开始放弃无政府社会主义思想,进而转向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建设与改造。
在《易卜生主义》的第六部分,胡适正面总结了他所理解的易卜生主义:“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
在胡适眼里,发展个人的个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娜拉的离家出走,就是承担责任的第一步。而易卜生的一生,就是要呼吁全社会极力容忍和鼓励包括娜拉、斯铎曼医生那样的有个性和建设性的精锐人物,从而使现实社会不断涌现出敢于说老实话的“国民公敌”。
需要说明的是,“易卜生主义”是英国著名社会主义戏剧家萧伯纳于1891年率先提出的一个概念,而真正把“易卜生主义”确立为以创造以人为本、自我健全的戏剧人物为第一目标的现代戏剧本体论的,却是胡适。
到了1930年11月27日,胡适在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选》写作的序言《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对于“易卜生主义”另有更加经典的概括总结:
易卜生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这便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宝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斯铎曼医生为了说老实话,为了揭穿本地社会的黑幕,遂被全社会的人喊作“国民公敌”。但他不肯避“国民公敌”的恶名,他还要说老实话。他大胆的宣言:“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这也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
胡适:《胡适文选》,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
与这段话相印证,胡适在1914年7月18日的《留学日记》中写道:“自伊卜生(Ibsen)以来,欧洲戏剧巨子多重社会剧,又名‘问题剧(ProblemPlay),以其每剧意在讨论今日社会重要之问题也。业此最著者,在昔有伊卜生(挪威人),今死矣,今日名手在德为赫氏,在英为萧伯纳氏(BernardShaw),在法为白里而氏。”
赫氏即霍夫特曼,白里而氏即布莱希特,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0页。
在同年8月9日的日记中,胡适另有阅读易卜生晚年名剧《海妲传》的感想。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确实通读过易卜生大部分的戏剧作品和生平传记。
二、鲁迅笔下的易卜生
鲁迅笔下最早出现易卜生的名字,是连载于1908年2、3月出版的《河南》月刊第2、3号的《摩罗诗力说》:
盖人既独尊,自无退让,自无调和,意力所如,非达不已,乃以是渐与社会冲突,乃以是渐有所厌倦于人间。若裴伦者,即其一矣。其言曰,……凡有事物,无不定以习俗至谬之衡,所谓舆论,实具大力,而舆论则以昏黑蔽全球也。此其所言,与近世诺威文人伊孛生(H.Ibsen)所見合,伊氏生于近世,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假《社会之敌》以立言,使医生斯托克曼为全主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自既见放于地主,其子复受斥于学校,而终奋斗,不为之摇。末乃曰,吾又见真理矣。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其处世之道如是。
裴伦即英国诗人拜伦,《社会之敌》即《国民公敌》,见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9页。
1908年8月,鲁迅继《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之后,在《河南》月刊第7号发表长篇论文《文化偏至论》,正式提出了一对矛盾概念:“文化偏至”和“神思新宗”。
被鲁迅定性为“文化偏至”的,主要是“近世之人”从欧美国家学习来的“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而构成新式宗教“神思新宗”的“先觉善斗之士”,首先是“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的“斯契纳尔”,也就是德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家斯蒂纳。其次是“勖宾霍尔”即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再其次是“契开迦尔”,也就是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其后还有“显理伊勃生”,就是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这些“先觉善斗之士”的最高代表,是公然以超人自居的尼采。鲁迅认为,尼采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
鲁迅是把易卜生当作“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的尼采式“超人”来加以歌颂的,他认为易卜生戏剧“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而偏至者,无不加之抵排”。
然而,无论是易卜生本人还是出现在他笔下的“国民公敌”斯铎曼医生,敢于说老实话和敢于与社会恶势力作战,都是为了造福于全社会,进而带动整个社会与自己共同进步;而不是想要充当尼采式的“往往反社会民主”的“极端之个人主义”的“超人”。
关于这一点,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专门引用易卜生的一段原话予以说明:
十年之后,社会的多数人大概也会到了斯铎曼医生开公民大会时的见地了。但是这十年之中,斯铎曼自己也刻刻向前进。所以到了十年之后,他的见地仍旧比社会的多数人还高十年。即以我个人而论,我觉得时时刻刻总有进境。我从前每作一本戏时的主张,如今都已渐渐变成了很多数人的主张。但是等到他们赶到那里时,我久已不在那里了。我又到别处去了。我希望我总是向前去了。
继《文化偏至论》之后,鲁迅在《河南》月刊第8号发表《破恶声论》,再次对被他判定为“伪士”的洋务维新人士,实施全盘否定的神圣清算。
在鲁迅眼里,提倡洋务维新的“伪士”们所学习到的欧美现代科学和现代民主制度,只不过是低层次的“恶声”,只有他自己从尼采等人那里学习到的“神思新宗”才是既超人又超科学的新式宗教。
随着《河南》月刊第9号被日本当局予以查禁,正在构建新式宗教“神思新宗”的鲁迅,连《破恶声论》都没有写作完成。他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二集,虽然在绍兴同乡蒋抑巵的资助下得以出版,每集也只卖出21本,想通过收回投资再翻译出版第三集、第四集的计划因此落空。
1909年8月,经许寿裳介绍,鲁迅回国到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化学和生理学教员,从此中止了形而上的构建新式宗教“神思新宗”的超人事业,开始操持起挣钱养家、抄书自虐的形而下的灰暗生活。
1910年11月15日,鲁迅在写给许寿裳的书信中,表现出的完全是落魄失败的黑暗情绪:“中国今日冀以学术干世,难也。……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
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7页。
鲁迅当时已经离开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植物教员兼学监。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和饭碗,他明明同情闹学潮的学生们,却不惜充当开除学生的“屠伯”即刽子手。由于鲁迅既找不到“以学术干世”的人生出路,也不喜欢自己的妻子朱安女士,只好把别人用在“醇酒妇人”上面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收集整理古书和碑帖方面。
在1911年3月7日致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另有更加彻底的丧气话:“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闵叹也。”
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4页。
起孟就是在日本留学并且与日本女人结婚的周作人。两年前的鲁迅,不仅在《文化偏至论》中以“唯超人出,世乃太平”的尼采式超人自居,而且在《破恶声论》中斥骂主张洋务维新的中国人是“为饮啖计,不得不假此面具以钓名声于天下”的“伪士”。由于回国后找不到“干世”之路,鲁迅不仅要依靠自己并没有认真学习的化学、生理学和植物学来换取米肉,还要以学习法语不能换取米肉为理由,逼迫周作人中止学业返回国内。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鲁迅所构建的超人救世加超人专制的“神思新宗”,实际上已经归于破灭败坏。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几十年如一日,所表现出的都是反抗绝望的失败超人的精神面貌。
1928年8月11日,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三)》中提出一个自问自答的设问:“但何以大家偏要选出Ibsen来呢?如青木教授在后文所说,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Ibsen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罢,现在细看墓碣,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第163页。
事实上,在《新青年》同人团队当中,真正把自己置于“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的劣势地位的,只是魯迅、周作人等少数人的生命体验。直到1932年4月30日,加入左联并且成为盟主的鲁迅,还在《二心集·序言》中颇为真诚地清算自己以失败超人自居的“坏脾气”:
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是的确的。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第191页。
同样是公费留学,在日本期间并没有学习到足够的谋生本领和现代知识的鲁迅,与从美国留学八年后学成归来的胡适等人,是完全不能够相提并论的。与鲁迅的失败超人的精神面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胡适富于朝气、富于阳光、富于进取心的优胜心态。
1917年3月8日,已经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并且正在努力撰写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18章125行的英文诗句:“Youshallknowthedifferencenowthatwearebackagain.”然后用中文介绍说:
英国前世纪之“牛津运动”(TheOxfordMovement)(宗教改良之运动)未起时,其未来之领袖牛曼(Newman)、傅鲁得(Froude)、客白儿(Keble)诸人久以改良宗教相期许。三人写其所作宗教的诗歌成一集。牛曼取荷马诗中语题其上,即上所记语也。其意若曰: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语见Ollard:OxfordMovement)
其气象可想。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第555页。
1919年7月,胡适在少年中国学会发表演讲,把鲁迅的恩师章太炎的意见认定为“消极的忠告”,然后从积极的方面提出自己的“少年中国的精神”。在结束语中,胡适再一次谈到英国的“牛津运动”,并且把《伊利亚特》中的诗文,重新翻译为“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欧阳哲生编:《再读胡适》,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1931年,胡适在为清华大学20周年校庆题词时,更加准确地翻译了这句诗文:“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
三、《终身大事》与《过客》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富于以人为本、自我健全的现代文明意识的第一部戏剧作品,是胡适创作的《终身大事》。
1919年3月,《终身大事》刊登在由高一涵主编的《新青年》6卷3号中,胡适专门为剧本加写了一个副标题:“游戏的喜剧。”而在实际上,《终身大事》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剧中的女主角田亚梅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娜拉式的女性人物,她与易卜生笔下的娜拉的主要差别,表现在她所反抗的并不是夫妻生活中的男权丈夫,而是宗法制家庭中的严父慈母。这其实是在整体上处于前文明的农耕等级社会的中国特色所在。
田亚梅与陈先生是在东洋留学时相识的一对情人,两个人回国后征求父母的意见正式结婚。田亚梅的母亲田太太是“不敢相信自己”的一个人,她疼爱自己的独生女儿,希望女儿不要“糊里糊涂”地嫁给一个合不来的人,就背着家人去观音菩萨面前求签,然后又请来一位瞎眼的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自己是“据命直言”的,按照命书上的说法,陈先生和田亚梅从属相上说是属蛇和属虎相克,从时间上说是猪和猴相克,这两个人要是成了夫妇,就犯了夫克妻的命,一定不能够团圆到老。
在这种情况下,田亚梅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禁止家人拜菩萨、请算命先生的父亲身上。她的父亲田先生回家后,先把田太太教训一通,接下来却说出了反对这桩婚事的另一项理由:“两千五百年前,姓陈的和姓田的只是一家。后来年代久了,那寫做田的便认定姓田,写做陈的便认定姓陈,外面看起来,好像是两姓,其实是一家。所以两姓的祠堂里都不准通婚。”
田先生因为害怕被革出宗族祠堂并且被老先生们笑骂,竟然搬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学把戏:“要是你这位姓陈的朋友是没有钱的,倒也罢了;不幸他又是很有钱的人家。我要把你嫁了他,那班老先生们必定说我贪图他有钱,所以连祖宗都不顾,就把女儿卖给他了。”
田亚梅在绝望中看到女仆李妈替陈先生送来的情书,上面写着:“此事只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决断!”她因此当机立断,在桌子上留下一张字条就离开了家庭。她在字条上写道:“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暂时告辞了。”
《终身大事》是很短的一部独幕戏,戏中的观音菩萨是中国传统佛教的化身,算命瞎子是中国传统道教的缩影,田太太所充当的其实就是佛教、道教两教的代言人的角色。而自以为文明新派的田先生,却是一直以正统自居的孔教儒学的代言人。田亚梅的离家出走,一方面是她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以现代人道反抗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中国传统神道文化的第一步。
《终身大事》在当年曾经引起很大反响。1919年6月1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给学生运动筹集经费,邀请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北京农业专科学校的新剧团,在珠市口第一舞台举行联合公演。第一天晚上由北大学生演出《新村正》和《终身大事》;第二天晚上由高师学生演出《波兰亡国惨》和《劫余泪》;第三天晚上由农专学生演出《美人剑》和《笑死你》。
周作人于6月17日从刘半农手中购票两张,6月19日晚上与鲁迅一起观看了演出。鲁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与二弟同至第一舞台观学生演剧,计《终身大事》一幕,胡适之作,《新村正》四幕,南开学校本也,夜半归。”
鲁迅:《鲁迅全集》第14卷,第359页。
被胡适称赞为“颇有新剧的意味”
胡适:《与TEC关于《论译戏剧》的通信》,《新青年》第6卷第3期。的《新村正》,是他的留美同学张彭春为南开新剧团编写和导演的,1918年10月17日首演于天津南开学校。如果说胡适的《终身大事》是直接脱胎于《新青年》“易卜生号”所翻译介绍的《挪拉》一剧的话,张彭春的《新村正》可以说是直接脱胎于《新青年》“易卜生号”所翻译介绍的《国民公敌》。
与胡适、罗家伦、张彭春等人一上手就介绍引进世界一流的戏剧作品相比,鲁迅、周作人兄弟对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四幕反战戏剧《一个青年的梦》情有独钟。
1919年8月2日,鲁迅在周作人影响之下应《国民公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的约稿,开始翻译《一个青年的梦》,并且在当天写作的《〈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中,正面介绍了自己理想中的人类、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第193页。
接下来,鲁迅解剖了自己担心《一个青年的梦》“未必有人高兴看”的“自己的根性”:“武者小路氏《新村杂感》说,‘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在大风雨中,擎出了火把,我却想用黑幔去遮盖他,在睡着的人们的面前讨好吗?”
换言之,鲁迅翻译这部反战戏剧就是要像武者小路那样“擎出了火把”而不是掩盖光明。纵观鲁迅一生中所留下的所有文字,这篇序言是他最为光明的一篇。然而,一年之后,鲁迅在小说《头发的故事》中,却借着“恨人”N先生之口,否定了包括娜拉式的争取女子剪发、婚姻自由的女权运动和武者小路式的新村运动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理想追求: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465页。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标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他在演讲中給出的答案是:“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162页。
1925年3月,鲁迅创作戏剧小品《过客》。这位“过客”依然是一位鲁迅式的以劣势者自居却又不甘心失败的失败“超人”。他“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赤足破鞋”,决绝于“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的现实世界;怀抱着孤注一掷自蹈死地的殉道信念,从记事起就迎着前面的声音,去寻找“走完了那坟地之后”的所在。鲁迅通过他笔下的“过客”展现出的,恰恰是他此前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虚无黑暗的精神境界和绝望的心理状态。
1925年8月14日,鲁迅因为支持许广平等人闹学潮而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职。于是,他一边与许广平秘密恋爱,一边在小说《伤逝》中再一次提到易卜生和他的戏剧。
《伤逝》中的涓生,和鲁迅一样是曾经寄居在会馆里的小京官。他在孤独中认识了子君,然后背诵着《娜拉》的台词背叛家庭过起了同居生活。涓生被免职后无力供养子君,便在一整套大道理的伪装之下,向子君提出分手要求。子君跟着从外地赶来的父亲返回家中,不久便在父亲和旁人的冷眼中默默死去。连自己和自己的爱人都养活不了的涓生,却依然在自欺欺人地表白说:“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由反抗绝望的“过客”到背叛爱情的涓生,1925年的鲁迅在为中国娜拉划定“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人生道路的同时,并没有找到自己的“新的生路”。
心态阳光、富于朝气的胡适,对于周作人所提倡的武者小路式的“新村运动”和城市大学生所谓的“工读主义”,给出的是另一种以人为本、自我健全、脚踏实地、逐步改良的建设性批评和建议:
我希望用组织来帮助那极平常的工读主义,并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新生活和新组织也许都是很该提倡的东西,但是我很诚恳的希望我的朋友们不要借“工读主义”来提倡新生活新组织。工读主义只不过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美国至少有几万人做这事——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新生活。
胡适:《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原载1920年4月《新青年》7卷5号,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9-563页。
1922年6月,胡适在为《努力周刊》写作的《这一周》中,针对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所推崇的俄国革命式的“根本解决”进一步写道:
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相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然后可以冷静地估量那现实的政治上的变迁。
胡适:《这一周》,原载1922年6月18日《努力》第7号,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第401页。
在此后的岁月中,中国社会既没有完全按照胡适所选择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脚踏实地、逐步改良的现代化的文明路径走下去,也没有完全按照鲁迅以反抗绝望的虚无心态从事思想革命及政治革命的道路走下去。尽管如此,胡适通过对于易卜生戏剧的直接引进和完整介绍,还是为中国现代戏剧树立了一个直到今天也没有能够充分实现的以塑造以人为本、自我健全的戏剧人物为首要目标的文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