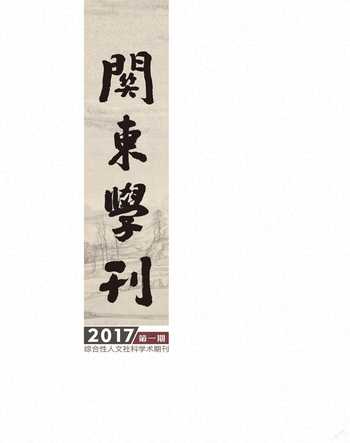吴伯箫《波罗的海》译话
一
吴伯箫的著译中,译诗集《波罗的海》也许是最被忽视的一种。就算偶尔有人提到,也往往语焉不详甚或认知有误。
有梳理海涅诗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历程者提及此书,有如许表述:“1957年,吴伯萧(萧字误,子张按)根据英译本译出海涅诗集《波罗的海》,书中收录《波罗的海》、《哈尔茨山旅行记》以及《西里西亚织工》、《路易皇帝的赞歌》、《两个掷弹兵》等短诗。他总结了海涅作品的特点,即‘丰富的想象、‘尖锐的讽刺和‘崇高的理想。并提到:‘海涅,若不是更以诗著名,他在法律、宗教和哲学方面的研究也许会很显著。”
梳理者将《波罗的海》出版时间写作“1957年”,不能说不对,可的确又不准确。因为这只是修订版或再版本,而并非最早的初版本,修订版或再版较初版本整整迟了七年,作为严格的历时性学术梳理,这表述可就过于离谱了。
不妨引用艾思奇1949年3月26日复吴伯箫信中的一句话看看:“谢谢你寄来的译诗集,庆祝解放的中国出版了海涅的第一部译诗!我读了几首,我很喜欢它译得自然!”
“解放的中国出版了海涅的第一部译诗……”这才是对吴译《波罗的海》出版时间的准确表述。查《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吴伯箫”之“译文部分”,《波罗的海》出版信息为两条:1、上海文化工作社1950年2月初版188页30开(上海文化社译文丛书9);2、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4月初版133页32开。再对照手头《波罗的海》两个版本的版权页,确定无误。
不妨回顾一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对海涅诗文的译介。
据说,最早在文章中引述海涅诗的中国人是辜鸿铭,其后胡适、鲁迅、郭沫若、李之常、成仿吾、邓均吾、冯至都分别译介过其诗其文,这其中已经有《波罗的海》中的诗章,冯至还在1928年翻译了含有散文和诗两部分的《哈尔茨山游记》。另外,段可情、剑波、杜衡的译品都出版过单行本。进入三十年代,朋其、李金发、艾思奇、林焕平、林林也都是海涅诗的译者,李金发还译有《北海之诗》,可见在吴伯箫之前,《波罗的海》已有了译本。可惜一时查不到李金发原书,不知他翻译的是否完整本?
吴伯箫对海涅诗的翻译其实缘于延安时期与哲学家艾思奇的交往。“我很喜欢他从德文海涅原著翻译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流丽,押韵,保持了海涅诗歌的隽永幽默、情感炽热的特点。我学习翻译的《波罗的海》就是从老艾同志收藏的一种海涅诗歌英译本翻译的。在延安抗日战争年代里他主动借给我那本书又鼓励我翻译它,那是治学中无私的帮助,令人至今深切地怀念。”(吴伯箫《我所知道的老艾同志》)
据拙编《吴伯箫年谱》所记,吴伯箫从艾思奇收藏英文版海涅诗集转译的海涅诗比较集中地发表在1941-1944年延安、重庆的报刊上。如下列数条:
1941年12月9日,译文《宣言——〈波罗的海〉一部之六》刊载于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署名“吴伯箫”。
1942年2月20日,翻译海涅诗作《近卫兵》刊载于延安《诗创作》第8期。
1942年3月15日,译文德国海涅诗作《哈兹山旅行记》刊载于延安《谷雨》第1卷第4期,署名吴伯箫。
1944年2月,译诗《海涅诗抄》(三首)刊载于重庆《文阵新辑》之二(总62号):“哈罗尔德的旅行及其他”,署名“孙纬、吴伯箫译”,1944年2月出版。
除了延安《解放日報》和重庆《文阵新辑》,吴伯箫还在《波罗的海》1950年初版的《追记》中说“译诗的有些篇章曾在艾青同志主编的《诗刊》和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过;”那么,创刊于1941年的延安《诗刊》也该算在内。
顺便说一句,《追记》写于1949年12月15日,初版本1950年问世,照这个时间,可不正是“解放的中国出版了海涅的第一部译诗……”
二
作为译者,吴伯箫为1950年初版本《波罗的海》写的“追记”仅只数百字,可也有不少内容。罗列一下,大致有这些意思:一、译海涅诗篇的时间(1942年左右);二、不是译自德文原版,乃从英文转译(依据艾思奇提供英译本);三、诗难译甚至不可译(完全保留作者的精神、风格、韵致不容易);四、有些篇章曾在延安《诗刊》《解放日报》发表过;五、集结后的稿本由艾青保存三年,第一次文代会时交还译者;六、最后由上海周而复介绍出版。
也许还应该包括第七个意思,即“追记”最后一句所表达的谢意:“这里向鼓励和帮助我的同志们致谢。”那么,给译者以“鼓励和帮助”的,首先应该是前面提到过的艾思奇、艾青和周而复吧?
艾思奇,就是那位以《大众哲学》为三四十年代左翼青年所熟知的哲学家,吴伯箫在老年时期写的《我所知道的老艾同志》中有介绍:“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作通俗的阐述,这本书是大胆的尝试。纸贵洛阳,影响很大。抗日战争初期印行到第十版。那时进步的知识青年谁不知道《大众哲学》呢?而且提到《大众哲学》就想到艾思奇。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几乎成为同义语。”吴伯箫1938年初夏在延安抗大学习时,以学员的身份结识了小他四五岁的教员艾思奇,后来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同事过三年,此后也一直保持较为密切的来往。至于翻译海涅诗,自然也与这种交往有关。艾思奇本人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开始研究、翻译海涅的诗作,1934年上海《春光》杂志第1卷第2号就刊出过他翻译的海涅政治讽刺诗《德国,冬天的童话》的章节,四十年代且在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吴伯箫喜欢艾思奇的译文,艾思奇又主动将他手头的英译本出借,鼓励吴伯箫由英译本转译,这才使英文系出身的吴伯箫多出了文学翻译者的身份。这样的鼓励和帮助,自然是值得铭谢的。
吴伯箫提到的第二个人是诗人艾青。与吴伯箫译诗有关的是两件事:一是译稿曾在艾青主编的延安《诗刊》上发表过,二是译稿集结后由艾青保存了三年最后又交还译者。初版《追记》中还有一段话专讲这段“佳话”:“译诗的有些篇章曾在艾青同志主编的《诗刊》和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过;集结之后,艾青同志又曾在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的日子里带着它出入战争环境三整年,直到在北京一块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他才又交给我转周而复同志介绍印行。”这里,吴伯箫提供了一个与其《羽书》集相似的“托孤”故事,当年《羽书》托王统照保存,是出于抗战爆发自己不便带着稿本流亡,现在又把《波罗的海》译稿交艾青保管又是因为什么?
查吴伯箫年谱,知1945年日本投降后吴调入延安大学,又很快接受随学校干部队到东北创建东北大学的任务,并于当年11月动身,翌年8月到达佳木斯东北大学。而“曾在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的日子里带着它出入战争环境三整年”云云,就提供了两种可能性:一是离开延安前将稿本托付给艾青,二是1946年从张家口或佳木斯将稿本寄给艾青。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最后的结果都是艾青“完璧归赵”,将稿本重新交还给了译者,这在那样的战争环境下,无论如何是令人感激和振奋的。
至于吴伯箫与周而复,实在也早就有过文字因缘。吴伯箫的通讯报告集《潞安风物》就是被纳入周而复主编的“北方文丛”第二辑由香港海洋书屋出版的,当时周而复正在香港担任中共华南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副书记,而此前在延安“文协”二人就是同事,1944年还与另两位作家合写过报告文学《海上的遭遇》,当时吴与周同为中央党校学员。再考虑到《波罗的海》初版本1950年在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周而复当时已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多项职务,“转周而复同志介绍印行”实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文学史就是这般充满种种偶然的巧合、机缘与细节,到处都晃动着人的影子,哪里像教科书那样空洞与刻板呢!
事情到这里,也还没有结束。到了1957年,《波罗的海》经过一番修改和调整,又在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重版了。译文改动之外,书的封面、插页也都变了,还有,书后的《追记》删去了关于艾青、周而复的信息,增加了1957年1月写的两句话:“这本译诗于1956年纪念海涅逝世100周年的时候,曾作了比较多的修改,现在加一篇附录《谈海涅》重印出来。错误的地方一定还有,仍请读者指正。”
至于为什么要删去那段艾青保留稿本三年的佳话,恐怕就不能不考虑再版本问世的时间背景了。印在书上的出版时间是1957年4月,但实际印出一般总要迟一段时间,如果是拖到艾青被卷入反右风暴的下半年,译者或出版社作出这样的文字处理就不奇怪了。
三
1980年春,已经74岁的吴伯箫远游海南岛归来,为表达“洋溢在内心里的真实的颂歌”,将“自己喜爱的德意志诗人亨利希·海涅”的诗句引入正在写作的散文《天涯》里:
我用有力的手臂从挪威的树林里
拔下那最高的枞树,
深深地把它浸入
爱特纳炽热的喷火口,
然后,用蘸着烈火的巨笔
我写在黑暗的天上……
其实这段译诗,在1956年2月写的《谈海涅》中也曾经重点介绍过:“《波罗的海》里边有一篇《宣言》,抒情的力量非常强烈。为了表示对安妮斯永恒的爱情,诗人诉说,要用强有力的手臂,从挪威的树林里,拔下最高的枞树,把它插入欧洲最大的火山,西西里岛的爱特纳火山口,用这样被烈火浸透的枞树写在黑暗的天上:‘安妮斯,我爱你!那气魄是惊人的。”
而这首吴伯箫转译自英译本的《宣告》,最早以《宣言——〈波罗的海〉一部之六》(海涅作)的样子刊载于1941年12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的第四版上。
由此见出吴伯箫对海涅“喜爱”之真实、强烈、持久。
尽管吴伯箫大学专业是英文系,可真正从事翻译还是从延安时期开始,延安的報刊上不时会有署名“吴伯箫”或“山屋”的译文,所译多为俄国或苏联的文艺作品及论文,且由英文转译,真正译自英语的可能只有惠特曼的几首诗和白求恩的演讲稿。吴伯箫大学时也学过一点德文,而翻译海涅用的却还是艾思奇手里的英译本。
不确知吴伯箫是从何时开始接触并喜爱海涅诗作的,在找不到更早线索的情况下,不妨就把他阅读艾思奇所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和在延安看到英译本海涅诗集作为引发他自己翻译海涅的一个契机。不过,这只是契机,若说心理动因,我总觉得与当时吴伯箫对暌违三四年的家乡亲人特别是爱人郭静君的思念有关。
吴伯箫1937年离开山东走上流亡之路,结婚才刚刚一年的妻子郭静君只能带着刚出生的长子光琦留在青岛等消息。1939年初夏,吴伯箫从晋东南前线回到延安,工作基本稳定下来,想念妻儿自是人之常情,证据之一就是他在1941年5月写的抒情散文《向海洋》,其中不但有“喔,青岛!给了我第一幢海的家的好地方啊”这样热情的感叹,更有大段大段对海的想念的告白,文章劈头就是:“我的岗位是在高原上,我底心却向着海洋。”
证据之二,也就非《波罗的海》莫属了。
盖海涅者,“文学史家说他是德国诗中第一个使人听到海洋的咆哮和它无穷的变幻和威力的。”而《波罗的海》作为海涅的游记诗,“在那里边海涅写了沙滩的贝壳,空中的海鸥,写了暴风雨里的海,风平浪静的海,写了白天和夜晚,岸上和船里,晕船、白日梦、海神和女神,关于海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写到了。幻想、传说、新鲜神奇的景象,有时情意深长,使读者都变成诗人的密友;有时幽默讽刺,诗句穿进人们的心里而在里边留下了刺;更多的是诗人的回忆、哀伤和希望。”(吴伯箫《谈海涅》)
神奇的大海,永恒的爱情,还有什么会比这些更能挑动一个客居高原者缱绻乡思的呢?
诗,其实也是吴伯箫素所喜爱的文体,甚至可以说是散文之外第二种持续喜爱的文体。北师大读书时尝试新诗,有《希望》《夏之午》《恳求》诸作,青岛济南之际又有《万年山的绿》《秋夜》,延安时期复有《炮声在呼唤》《骆驼队》,五六十年代还写过《谒列宁-斯大林墓》《钢铁的长虹》,不同阶段另有一些旧体诗。不过,更多时候,吴伯箫是将诗情融入其散文,使其更近乎散文诗的结构、章法。从他喜爱、熟悉语体诗文体形式的角度说,选择诗体的《波罗的海》和《哈尔兹山旅行记》加以译介,并非特别难以理解。延安时期的译诗,除了海涅,也还有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少量作品。
四
哈尔兹山(HarzMountains),是德国中部地区的名山和旅游胜地,18世纪就已经名扬海外,最高峰为布罗肯山,海拔1142米。当年大诗人亨利希·海涅的游览更为这座山增添了色彩,这里最有名的旅馆便是被称为“亨利希·海涅”的旅馆。
吴译《哈尔兹山旅行记》,今多译为《哈尔茨山游记》,这里以较流行的译法为准。
回到19世纪的1823年,还在读大学的海涅曾到北海之滨易北河入海口附近的库克斯港,写下八首以大海为主题的诗。翌年初秋,又徒步旅游哈尔兹山,经哈勒、耶拿,到魏玛拜访歌德,再经哥达、卡塞尔回哥廷根,1825年上半年准备毕业论文和写作《哈尔茨山游记》,同时领受基督教洗礼,7月被哥廷根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8月去北海诺德奈岛疗养,计划写作《游记》,1826、1827年《游记》第一、第二卷分别出版,接着,《短歌集》也出版了,此集是其第四部诗集,收入1827年以前的作品。
也就是说,《哈尔茨山游记》和《北海》(即《波罗的海》)都是海涅大学期间和毕业之后不久写的作品。
先说说《哈尔茨山游记》。
首先,完整的《哈尔茨山游记》是以散文为主而穿插着诗的,早在1928年就有了冯至译自德语的全本,北新书局初版,战后又经重译在报刊发表,1954年在北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故吴伯簫的译本非整本翻译,乃是其中诗歌部分的翻译,包含“序”和1、2、3、4、5、6,共7首,除了“序”诗,其他各首在原文中的确并没有标题,吴伯箫以阿拉伯数字为序。后来的译者有的加了标题,如“序”标示为“序诗”,第一首至第三首是一组,便标示为《山间田园诗》三首,第四、五、六首分别标示为《牧童》、《布罗肯山上》、《伊尔赛》,整组诗标题也改为《自〈哈尔茨山游记〉》,意谓从《哈尔茨山游记》选出的诗,倒也更准确些。(参见胡其鼎译《海涅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全本《哈尔茨山游记》作为海涅的早期作品,素以强烈的讽刺和对大自然出色的描绘为人称道,其中的这六七首诗作也有类似的特点,但更突出了爱情的主题。比如“序诗”就是先对贵族式的生活作了嘲讽,接着进入了对自己山中旅行的抒写:“我要攀登那远山了,/那里有幽静的茅屋,/那里有自由的微风在吹,/自由的胸襟可以尽意舒展。”第一首至第三首为组诗,写的是山上茅屋里一对男女青年相互的述说,氤氲着浓浓的爱情气息和神奇的神迹:“但是我们,我可爱的姑娘,/比我们所看见的一切变得更多;/黄金、锦衣和火把的光亮/都欢乐地围绕着我们闪灼。”第四首第一节为:“牧童是一个国王,/宝座是绿色的山峦,/他头上光辉的太阳/是永恒的金黄的王冠。”形象鲜明亮丽,洋溢着自然的芬芳。接下来便是对这位牧童身边绵羊、小鹿、猎狗的描绘以及这位“国王”睡梦中的缅想,有着童话般的意境。第五首是柔美的情诗,节奏明快,韵律和谐,诗境温馨浪漫。最后一首以伊尔赛公主的口吻表达她对“你”——“可怜的不幸的汉子”爱情的慰藉。伊尔赛,即是哈尔茨山北麓河流的名字,又是传说中河中水妖的名字,据说她日日清晨沐浴河中,会将遇见她的男子带入水中岩宫,故诗中有“来哟,和我一块到我的城堡,我们要幸福地生活在快乐中间”的句子。
在吴伯箫的译文之前,早有过冯至译文的初版本(1928),当时,吴还在北师大英语系读书,或许读到过此译本。不过,冯至以当时德文水平和“不能容忍的错误”而至战后重译,而吴译时间在冯译重译之前,二人是否相互借鉴不得而知。然对照二人所译,确乎能看到他们之间的近似处。举例说,第5首第一节,冯1954年重译本为:
通过太阳的微光
东方已渐渐明亮,
远远近近的山巅
在雾海里浮漾。
吴1950年初译本为:
通过太阳柔和的微光
东方是渐渐地发亮;
远远的宽阔的山顶
在雾气的海里荡漾。
1957年修订本则为:
通过太阳柔和的微光
东方已渐渐地发亮;
远远的宽阔的山顶
在雾气的海里浮漾。
除了每行诗中的音组数略有差异外,句式、词汇基本相同,特别是吴译第四行“荡漾”改为“浮漾”更与冯译保持了一致。由第6首中“伊尔赛公主”“伊尔赛石岩”译名的变化亦能看到这一点,吴译初版本为“爱尔思公主”和“爱尔赛斯坦”,修订本分别改为“伊尔赛公主”和“伊尔赛石岩”,与冯译“伊尔塞公主”“伊尔塞石岩”基本一致。不过,也不能绝对肯定吴译对冯译的全面借鉴,毕竟在另外一些章节中也有很不同的译法。而不管怎么说,单纯就吴译而言,阅读效果总体上是简洁、流畅和谐的。
冯译、吴译都先后有过对自己初译本的修改,一方面看出二人对自己要求的严格,另一方面也的确说明诗的难译。这一点,在吴译“追记”中也有过感叹,真乃甘苦寸心知。
五
凡事若不深究,往往马马虎虎就过去了,一深究,事情便复杂起来。
吴译《波罗的海》,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德国北部有两个海,一为西北侧的北海,德语为Nordsee,英语为NorthSea;一为东北侧的波罗的海,德语为Ostsee,英语为BalticSea,照说吴译《波罗的海》的原文应为Ostsee或BalticSea,可据“维基百科”查询,海涅原著却明明写作dieNordsee,且自民国时期李金发以来的译者(包括冯至),一般都直接译为《北海》或《北海集》。
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吴伯箫依据的英译本ThePoemsofHeine(E.A.Bowring1866)就是如此?
可仔细读过吴伯箫1956年撰写的《谈海涅》一文,却发现有这样一句:“海涅的第二部大著作是《旅行的图画》,一部分是诗,一部分是散文……诗的部分分三部:《归家集》《哈尔兹山旅行记》和《北海》(或《波罗的海》)。”这么说,至少在准备再版《波罗的海》的时候,已将《波罗的海》与《北海》之间划了等号。
可既然划了等号,又为何不趁着修订、再版的机会径将书名改为《北海》呢?而仅仅用一个“或”字表示两个名字等同呢?况且,海涅疗养的诺德奈岛和原诗的标题所指都是北海而不是波罗的海呢!
一时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只好作为一个问题暂且搁置于此。
一般的传记介绍到这部诗集,必会言及海涅年轻时期两度北海之游的事。一次在1823年以身体虚弱拿到伯父给的十个金路易,便去北海之滨易北河入海口附近库克斯港疗养,这次写了八首大海主题的诗;第二次是1825年7月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后又得到伯父五十个金路易的奖励,海涅于是再次到北海,在诺德奈岛疗养。此后的两三年内,包括《北海集》在内的两部《游记》先后出版,更为丰富的一个集子《短歌集》也问世了。
文学史上提及海涅这组诗,通常有“开创了德国诗人描写大海的先例”、“不押尾韵的自由韵律体”、“机智、幻想、幽默是这两组诗的要素,但这里也不乏严肃的话题”这样的评述,且将海涅视为法国革命遗嘱的执行人,封建桎梏的摧毁者,德意志各邦封建君主的对立面。
1956年海涅逝世100周年之际,在当时的东德举办了关于海涅的学术会议,吴伯箫代表中国出席,在为大会撰写的介绍海涅的论文中,吴伯箫对这组诗有所评析:“《波罗的海》是游记诗。在那里边海涅写了沙滩的贝壳,空中的海鸥,写了暴风雨里的海,风平浪静的海,写了白天和夜晚,岸上和船里,晕船、白日梦、海神和女神,关于海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写到了。幻想、传说、新鲜神奇的景象,有时情意深长,使读者都变成了诗人的密友;有时幽默讽刺,诗句穿进人们的心里而在里边留下了刺;更多的是诗人自己的回忆、哀伤和希望。文学史家说他是德国诗中第一个使人听到海洋的咆哮和它无穷的变幻和威力的。诗人曾在诗里呼喊着:‘我祝贺你,永恒的海呀!”
除此之外,吴伯箫还通过这组诗中《宣言》《海里的幻影》《在海港里》诸作,分析和称赞了海涅诗中的抒情力量以及“浪漫主义跟现实主义两种要素的融合。”
《北海》或吴译《波罗的海》,是海涅两度疗休北海陆续写下的,一共有两组,每组各12首抒情诗。自民国以来,陆续有人译介过其中的部分篇什,而将其完整译出并且以之作书名出版的,吴伯箫却还是第一人,尽管他是自英译本转译的。
从这个角度说,吴译《波罗的海》在海涅譯介史上的贡献值得铭记。
六
吴译《波罗的海》虽以海涅一组诗命名,可并非专集,而是海涅的汉译诗选集。除了《哈尔茨山游记》和《北海》两组较大规模的诗作外,也还含有海涅不同阶段创作的另外一些诗作。它们是:《奴隶船》《西里西亚织工》《路易皇帝赞歌》《两个掷弹兵》《消息》和《夜思》。
《奴隶船》,选自海涅的《1853年与1854年诗抄》(1854),此诗是海涅1853年读了美国作家斯陀夫人的名作《汤姆叔叔的小屋》后写的,显然,它是一首社会批判性的叙事诗,刻画了黑奴贩子贪婪虚伪的嘴脸。吴伯箫认为:“题为《最后的诗》里有一篇《奴隶船》,那是呼吁保障人权反对贩卖黑人的最富人道主义精神的有力作品。”
《西里西亚织工》,出自海涅《集外诗》(1828-1844)中的“时事诗”部分,1844年6月作。原题《可怜的纺织工人》,刊载于当年7月10日《前进报》。本年6月普鲁士西里西亚的朗瑞比劳和彼特斯瓦尔道两地发生纺织工人饥饿暴动,遭军队镇压,死伤数十人。吴伯箫在《谈海涅》中谈到该诗,认为“《西里西亚织工》是德意志专制制度的丧歌,里边表现出诗人对无产阶级最后解放的信心。”
吴伯箫称《路易皇帝赞歌》是“讽刺巴伐利亚国王的”,且在《谈海涅》中谈到海涅诗“尖锐的讽刺”时特别提及此诗。这首诗也出自《集外诗》(1828-1844)的“时事诗”部分,或译为《路德维希国王赞》,作于1843年12月,系阿诺尔德·卢格约稿,原载《德法年鉴》,该刊1844年3月7日出版,27日在普鲁士遭禁。吴伯箫译诗中“巴威的国王”译法不同,或译为“巴伐利亚的国王”,或译为“巴燕国王”。历史上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1786-1868),1825年即位,在政治、经济、教育上实行开明措施,崇尚文艺,借助天主教会力量实行其统治。1827年11月,海涅移居慕尼黑,曾希望在慕尼黑大学谋职,为此请出版商科塔向这位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呈献他的《短歌集》和两卷《游记》,不过他的谋职并未成功。
以上三首都属于海涅后期作品,《波罗的海》中的最后一首《夜思》也是后期作品。《夜思》写于1843年夏,此年10月,海涅流亡巴黎十二年后首次回汉堡省亲,故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流年逝去的多快哟!自从我离开我亲爱的母亲,12年已经过去了;我等得愈长,我的怀念就变得愈强。”吴伯箫选译此诗,显然也有寄托个人亲情之意。海涅此诗亦出自《新诗集》中的“时事诗”(1841-1844)。
《近卫兵》是海涅早期名诗,不少译者都译介过,吴伯箫将诗题译为《两个掷弹兵》。该诗写于1815年,最早收入海涅1822年第一部诗集《哈里·海涅的诗》,后收入《短歌集》之“青春苦恼”,以罗曼采诗体写成。诗的内容写1812年拿破仑(1769-1821)率大军征俄败北,两名近卫兵被俘,遣返后始知法国已一败涂地:“在那里他们第一次听到那不幸的消息:说是法兰西已经完全灭亡,雄伟的军队遭到了复没,人家俘虏了他们仁慈的国王。”接下来便写这两个士兵的话语,先是担忧妻儿,此后则转到‘更沉重的责任,表达了他们对祖国和国王伟大的忠诚。这首诗受到高度赞誉,有人甚至认为贝朗瑞《人民的怀念》也显得逊色,舒曼、瓦格纳也都为这首诗谱曲传唱。另外,该诗所用的“罗曼采罗”,是罗曼语诗体中西班牙诗体的一种,这种诗体采用口头(民间)语言的叙事短歌,节数和每节行数都不限,每行八音节(四音步),常用扬抑格,叙述一则故事,突出一个母题。
短诗《消息》,或译《探听消息》,与《近卫兵》同出《短歌集》之“青春苦恼”罗曼采。是一首写得俏皮、幽默的爱情诗。表达如果自己爱的金发姑娘出嫁了,干脆让听差给自己买根绳子就是了……吴伯箫《谈海涅》说:“有时诗人也讽刺自己,像一首小诗《消息》所写的那样。”指的便是这种俏皮、幽默的写法。
总之,两组长诗,七首较短的诗,构成了《波罗的海》这部海涅的诗选集,从规模和出版时间上,它不但是“解放的中国”出版的海涅的第一部译诗,也是第一部较大规模的汉译海涅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