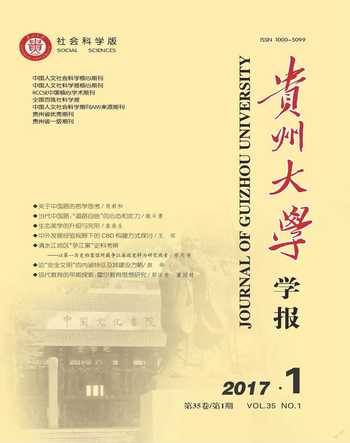礼与德的转换
谌祥勇
摘 要:因“疏不破注”之说,《中庸》郑注与孔疏被认为完全一致,然分析孔颖达之疏解可发现,其解释倾向与郑注颇为不同,尤其体现在中庸、诚身、圣人三个方面。孔疏将“中庸”理解为圣人之性情,却剥离了郑注“以礼释中”之意,他等修身于诚身,并以之为“中和之为用”的实现形式。在孔氏看来,《中庸》之圣人应从德性上加以理解,因而,有德无位的孔子与传统圣王主要在德性上具有一致性。由此,郑玄“制作礼法”的圣人观念被孔疏予以转换。
关键词:中庸;郑玄;孔疏;圣人;礼法;德性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7)01-0146-05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7.01.24
孔颖达的“中庸学”颇显尴尬。因其疏解附于郑玄之注,笃信“疏不破注”之学者往往认为孔疏与郑注大体一致。因此,孔氏之“中庸学”常被忘却。然《中庸》孔疏中颇有值得注意之处。《礼记正义》疏文“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1]2皇氏即皇侃,熊氏即熊安生。《礼记正义》孔疏本于皇疏,孔疏中,如未明言出处即为皇疏。皇氏为南梁经学家,他恰生活于梁武帝时,据《隋书·经籍志》,皇侃撰《礼记讲疏》九十九卷,《礼记义疏》四十八卷,而梁武帝亦撰《礼记大义》十卷。[2]922据《志》载,刘宋之戴顒作《礼记中庸传》两卷,梁武帝作《中庸讲疏》一卷。[2]923今皆散佚。这一时期,《中庸》单独成书。何以《中庸》受此礼遇?戴顒之行迹不可考,但梁武帝则是著名的佛教帝王,《中庸》之受重视或与此有关。皇书虽佚,但大体保留在孔疏中。欲窥南北朝之“中庸学”概况,舍此何适?①下面将从三个方面来看孔氏之“中庸学”。
一、性情与中和
《中庸》首章言“性、道、教”与“中和”。孔疏认为此节“明中庸之德,必修道而行。谓子思欲明中庸,先本于道”。[1]1988这既是说,中庸的关键在于“道”。道的含义由“性”规定,所谓“率性之谓道”,“率”即“循”,依从人性行事就是道。在此意义上,注、疏皆谓“道者,通物之名”。[1]1988万物有性,各沿其性而行,即道。于人而言,性为何物?郑玄以为“性者,生之质”,又以五行言五性,五行之神为仁、义、礼、智、信。道就是实现人性,而变为五德。郑注中,修道的主体并不明确,从而难以断定这是普遍人性论还是有所特指。尽管从“修道之谓教”一句来看,其主体定为上位者,但前文主体似又有转换。孔疏将此阐释得更为清晰。
“天命之谓性”意味着性即是天然如此,郑注表明人所感之自然实则相同,人有相同的人性结构。然而,读者很自然地就会想到,既然人皆具五行而生,也就潜在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德性,那人的差别从何而来?郑玄未曾着意于此,但孔疏对此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分解。所谓“天命”即是天命生人,这并不意味着天有意志,这在郑注中并不明显,但孔疏点出:所谓天命不过自然而已,“天本无体,亦无言语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贤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老子云:‘道本无名,强为之名曰道”[1]1988。命的问题在郑注中似未涉及,郑玄其实“通解性命为一”,“天命”不过是“强为之名”,其实质乃“人感自然”。正是在自然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才体现了出来。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是自然的,仁义礼智信虽然是五性之全体,但人自然而生时则未必能得五性之极致,否则人与人之间也就无所谓差别了。因此,孔疏称“人感自然而生,有刚柔好恶,或仁,或义,或礼,或知,或信。”[1]1988人性生而自然,其差异亦复如是。孔疏以为人性并非抽象普遍同质,人虽然具有共同结构,即“五行-五性”,但却有贤愚、刚柔好恶之差异。
人性的差异既然是天生,这种差异由何而起呢?孔疏遵从了郑玄“五行—人性”论,这是一种以气论为基础的人性论。孔疏引贺玚之言曰:“但感五行,在人为五常,得其清气,备者则为圣人,得其浊气,简者则为愚人。降圣以下,愚人以上,所禀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为九等。”[1]1988人虽为五行之秀气,具有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但每个人并不一样,还有清浊之分,由此可分出九等人。当然,这有“九品中正制”的时代背景,但也大体反映了汉以来的人性论共识,即认为圣与愚皆天生,所谓“上智与下愚”,可遇而不可求。惟中人乃可言“性相近,習相远”。否则夫子“上智与下愚不移”之说不能成立。
“性道教”似乎并不涉及“情”的问题,但在疏解郑注时,孔氏专门讨论了“性情关系”。这显得颇为奇怪,在孔疏的理解中,性与情实际上不可分割。孔疏全引贺玚之论,即《乐记》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他从“动静关系”来理解“性情关系”,所谓“性静情动”。他用波与水的关系来比喻,“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则是情。”[1]1988性情关系的生成论结构也来自气论,世间万物都皆为五行之气,人是“五行之秀气”。这与郑玄注释“性”的基础是一致的。但从五行推论到五常,并且从此处推论到六情,则是对郑注的发展。孔疏将性情问题看成是“性道教”的核心。性情问题就是道论,或者说《中庸》“道论”的基础就是情性论。孔疏对“率性之谓道”的理解是“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违越,是之曰道。”[1]1988所谓“性之所感”就是情。从孔疏的表述来看,性并不直接地起作用,必感而为情,“感仁行仁,感义行义”[1]1988。道正是沿性之所感而行这一过程,“感—情”是由寂然不动之性转换成为具体行为的关键。
孔疏之所以看重性情关系,有着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所谓“率性之谓道”即是“性静情动”的体现;其次,中、和关系的实质也是性情关系。性情关系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性与行的关系,“道”是循性而行,其中必有 “性之所感”的环节。但不管怎样,性发而为情,最终要落实为“行”。因此,孔疏认为“喜怒哀乐”之情皆是“缘事而生”,[1]1989其未发之所以谓之中,乃因“澹然虚静,心无所虑,而当于理”[1]1989。谓之和者,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限” [1]1989。郑玄认为“中”能出礼乐政教,故为大本。但孔疏并不作此看,他认为中是“人性初本,故曰天下之大本”[1]1990。而“和”则“犹如盐梅相得,性行和谐”[1]1989,那么,中与和的关系就是性与行的关系,“喜怒哀乐”之发与未发则是其中间环节。可见,中和问题就是“道”的问题,或者说,中和是“道”之极致。可见,孔疏认为中庸有超验特性。
如只言中和,则性与道足矣,因为中和即是行道之极致。但郑以中庸为“中和之为用”[1]1987,中和何以为用呢?这就要从“性道教”谈起,“性道教”是一个整体,由率性而为道即可自足于身,然教必发于外。郑玄以“修”为“治”,即“治而广之,人仿效之”,主体要将自身所体之道推广之,使人皆能率性。如行教则必须居于高位,所以孔疏谓:“人君在上,修行此道,以教于下”[1]1988。此则标示出修道、行教之主体乃居高位者,且在“率性”上趋向极致,这样的人就是圣人。因此,孔疏在“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处说:“此谓圣人修行仁、义、礼、知、信以为教化”[1]1999。中庸即“中和之为用”,此“用”乃圣人之行。唯圣人能禀五常之清,而具五德之全体,故可修习以为教化。中和之为用就是循“仁义礼智信”而行,并以此为教化。因此,孔疏言“此节明中庸之德,必修道而行”[1]1988。中和本就是修道之极致,而将中和推至极致则可使天地得正,万物得育,这种状态是中和之为用的极致效验。以正天地、育万物为标的,中庸必然是中和之推扩,从而作为一种教化泽被天下,这一主体只能是圣人。不过,在郑注与孔疏的理解中,从“中和”到“中庸”实现途径并不一致,二者在工夫论上有巨大差异。
二、修身与诚身
《中庸》篇颇为独特一点就是前篇谈中庸,而后篇谈诚,当代一些学者也据此认为《中庸》本为两篇文字组合而成。[3]266这些观点的主要根据在于《中庸》篇前后主题的差异。“哀公问政”章前,论述围绕着“中庸之道”或者君子之道展开,而“哀公问政”章之后,主题变为了“诚”。前后文似不相关,更像是两篇文字偶合而成。然而,这些观点忽略了一个问题,从汉代开始,《中庸》篇就保持现状,历代儒者大都认为“中庸”与“诚”存在内在关联。此关联不仅影响了“中庸学”,更影响了儒学的整体面貌。因此,重要的是发现《中庸》篇前后的关系。
“鬼神”章言:“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与“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具有對应性。此章虽论“鬼神之德”,实则言“中庸之德”,孔疏认为“此节明鬼神之道,无形而能显著诚信。中庸之道与鬼神之道相似,亦从微至著,不言而诚也。”[1]2004鬼神之情状就是人不可见,又能显著诚信。孔疏将“诚”理解为“信”,如何理解此“诚信”呢?孔疏看来,诚信意味着天地虽无体而不言,亦能生物、终物。中庸之道与之相似,亦是不言自诚而已。此则可见《中庸》前后之关联:诚是中庸之道的特质。合于中庸者只能是圣人,孔疏以为圣人是天生的禀气清者,贤人行中庸之道亦过之而不中。能具有中庸之德,就能“富有天下,受天之命也。” [1]2006因此,中庸非常人可学而至。但中庸所具有的诚却具有普遍意义。这一问题也正是孔疏与郑注之最大分歧所在。
诚之所以具有普遍意义,是因为无论圣人还是贤人都能具有至诚之道,这是《中庸》篇给予所有读者的保证。郑玄虽同意尽性之诚(圣)与学而至诚(贤)的功用相同,但又认为这不过是孔子勉人勤学而已。归根结底,圣与贤之间是不可逾越的,圣人与贤人是制作礼乐与遵从礼乐的关系。但无论如何,诚都是贤人接近圣人的真正着眼点。郑玄认为中庸具有礼法性质,他说“惟礼能为之中”,并且他默认了经文“以礼修身”的涵义。但孔疏这里,“以礼修身”的涵义不见了。代替修身的具体内涵的就是“诚”。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答哀公问的核心乃是修身,居上位者治政之要在于得贤人,而得贤人的前提就在于能够自修其身。广而言之,修身乃是以仁义为归。仁、义的本质乃亲亲、尊尊。然而亲亲、尊尊正是礼的价值归属,因此,郑玄将礼看作修身的根本方式。他注“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言:“修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知贤不肖,知贤不肖乃知天” [1]2013。郑玄以为修身是其他问题的基础,而修身又以“智仁勇”三者为基础[1]2016。修身是联结德性与礼制的关键。孔疏却将之进行了颠倒,修身的前提是事亲,知人,知天。[1]2014何谓“知天”?孔疏言:“欲思择人,必先知天时所佑助也。谓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当舍恶修善也。” [1]2014这即是说,欲修身当知善恶。此正与后文“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相对应。如此,孔疏实则将“诚身”与“修身”完全等同。故而,孔疏言:“修身在于至诚”[1]2016。
孔疏将修身等同于诚身,这与他的中庸理解有关,他认为中庸的重心不在发见于外之事,而在人心之内,在微小之处。其疏“戒慎其所不睹”曰:“君子行道,先虑其微,若微能先虑,则必合于道。”[1]1989孔疏对中庸的理解整体偏向于内。郑玄以礼作为中庸内在含义与实现方式,这在孔疏当中都隐而不见。经文明言“斋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郑玄未置一词,但从“唯礼能为之中”的表述来看,郑玄将之看作修身的具体内容。然孔疏却有意回避。因为,他将修身同等于诚身,以礼修身则与诚身的细微工夫并不相对应。他说:“盛服,谓正其衣冠。是修身之体也,此等非礼不动,是所以劝修身也。”[1]2018他将“斋明盛服”与“非礼不动”都看作“修身”的外务,所谓“修身之体”并不是“修身之本”,那么,何谓修身之本呢?如果对比《大学》来看,孔疏的意思就颇为明白了,《大学》中,经文认为修身在于正心、诚意,尤其是诚意,“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心在诚意”是也。所以修身就是诚意,也就是“诚身”。孔疏对中庸修身的理解显然与《大学》中的“诚身”相通,或者说孔疏根本就以《大学》的修身来理解《中庸》。除了诚意,其他皆是外事。因此,“非礼不动”不过是“劝修身”而已,非为修身的真正内容。修身与诚身的对等是孔疏联结《中庸》前后文的一条线索。能否诚身关乎能否合于中庸之道,这也透露出在孔疏的理解中,中庸是通过贤人诚身来实现“中和之为用”。
诚身的最终效验就是至诚,经文给出了至诚之意。从根本看,至诚是天地生物的一种性状,故其言“诚者,天之道也”。人并非不能达到“天之道”,圣人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天生而诚,不待学,不待教,始终合于中道,圣人之道与天地同。而圣人以下,并不能生而至诚,只能通过学。贤人仍然有通过“择善而固执”最终达到至诚的可能性。当然,不管是郑玄还是孔疏,他们都有一个明确的底线,那就是贤人不是圣人,贤人也并非通过学诚而成为圣人。只是在诚这一问题上,贤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可能达到圣人天生的至诚状态。因此,孔疏说:“诚则能明,明则能诚,优劣虽异,二者皆通有至诚也。” [1]2023孔疏明确的告知,有至诚并不意味着贤人成圣。
贤人能否为圣人?郑、孔都小心翼翼地予以否认。郑玄认为“天下至诚”能够“尽己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这是指圣人“受命在王位,致太平”[1]2024。贤人“择善固执”,通过学习,在小小之事上也能有诚。贤人经过“形、动、名、著”最终至于“化”,这一“化”并不是化育万物,而是“化而性善”。[1]2024贤人最终不过使自己之性全然为善。而孔疏虽比郑玄更进一步,但仍然严格地区分贤人之至诚与圣人之至诚。他说:“唯天下学致至诚之人,为能化恶为善,改移旧俗”,[1]2025学诚之人化性成善,也同样能得上行政,移风易俗,使民趋善。不过,这种改移风俗之举“不如前经天生至诚‘能尽其性,与天地参” 。[1]2025圣人尽己之性,如天地般化民育物,贤人远远达不到。贤人自有一番工夫让自己化性为善,具有至诚,即“择善固执”,具体而言,“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及“曲能有诚”等皆是学诚之人的工夫。《中庸》虽认为圣人与贤人皆能至诚,但至诚之道的最高效验显然专指圣人。孔疏将圣人之至诚与贤人之至诚严格区分开来,圣人之诚成己,成人,成物,而贤人则成己从而移风易俗而已。
三、圣人与孔子
孔疏将“修身”看作“诚身”,“诚身”正是“成己”之意。由“诚身”而至“至诚”则是“成己”的完成。郑玄和孔疏对此的理解已有很大分歧。这种分歧是从他们各自前提出发的必然结果。郑玄认为修身首先是“斋明盛服,非礼不动”,即“以礼修身”,这与孔疏的“诚身论”可以说是两个方向。沿此推进必然发展为两种不同的圣人观念。贤人修身的真正标准都是圣人,圣人既是历史中的圣王也是抽象的整全人格。郑玄一以贯之的思路是“礼能为之中”——“以礼修身”,故而,中庸就是圣人以其至诚为天下出礼法政教,“圣”体现在礼法上。孔疏认为中庸乃是圣人中和之性的推扩,且首先是德性的推扩,从“中和之性”到“中庸之德”,恰是圣人天生至诚的体现。贤人学圣人就是学圣人之德。因此,整个解释路向由郑注“学圣人之礼法”转向了孔疏“学圣人之德性”。
孔疏將圣人的意义集中表达为圣人之德,相比郑注,孔疏的理解发生了翻转。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他自身具有完满的德性,然在郑玄看来,这并不是圣人的充分条件,圣人自身的完满德性(中和)如何显见与发用(中庸)更为重要。此途径首先是礼乐政教,认识与模仿圣人的方式同样也是践行礼乐政教。如此,天地才能得位,万物方能得育。内在德性与万物得育并不能直接达成,它需要礼乐政教的参与,这是圣人最重大的贡献。他能制作礼乐政教是因其有完满德性。郑玄以为德性与最终的效验之间必然有复杂的中间环节。孔疏则不然,他将德性与效验之间直接打通。他说:“人君所能,至极中和,使阴阳不错,则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万物得其养育焉。”[1]1990人君自身能达中和之极,就可使阴阳不错,生成得理,从而天地位,万物育。这与郑注有根本差别,孔疏强调中和首先是一种德性,人君致极之,万物得位的效验就必然出现。
在孔疏处,礼作为中间载体的作用被降低了,他更强调“德”的直接作用。在论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时,孔疏只表述了“为政在人”,而“政由礼也”的意味则被隐去。他说:“三百、三千之礼,必待贤人,然后施行其事。” [1]2032这三百、三千之礼只是为政的部分内容,圣人之道更需贤人来施行。圣人之道的内容主要是道德。为政待贤人而后能行,贤人行道的依据也是其对道德的把握。故孔疏将“尊德性而道问学”理解为君子贤人通过勤学而“尊敬此圣人道德之性”从而达到至诚。[1]2037德性被理解为“圣人道德之性”;但郑玄却认为德性乃“性至诚者”,两者的指涉发生偏转,郑玄以为君子尊贤指向尊圣,“德性”和“问学”都是具体的人。而孔疏将品质和行为从这两种人中抽离出来,成为道德之性与勤学之行,从而变成了一种求学、修身之道。郑玄显然承接上节“大哉圣人之道”而来,也就是要复说“为政在人,政由礼也“之意。他将”尊德性“四句看作居上为政之则,而孔疏则以之为君子贤人为学之道。这种分歧在于他们对圣人有不同理解,集中体现在对孔子的理解上。
孔子有德无位,故孔子自认不敢制礼作乐,唯有居天子位的有德之人方可“议礼、制度、考文”。孔子本人也是申明夏礼、殷礼皆不足徵,故从周。然此段夫子之语中,颇有可讨论之处。首先,孔子虽言“从周”,但在他处,夫子遵其他礼制的情况也显然存在。孔疏引《郑志》赵商与郑玄之论,赵商发现孔子虽然称自己从周,但《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两楹之奠殡,哭师之处,皆有所法于殷礼,未必由周。”孔子本人所遵礼制中确有殷礼,这与所谓“从周”之论颇有矛盾。如何理解此矛盾关系重大。郑玄将这一矛盾作了具体区分,所谓“从周”是诸侯之礼,个人则可杂用殷礼。郑玄将礼分为政治礼法与个人礼法,这就透露出礼法的真正特质,那就是礼法具有政治性,同时,它又注重个体性。因此,孔子的从周之论是政治性的,当时诸侯皆行周礼,但并不对个人作具体要求。然而,郑玄在《论语注》中进一步认为孔子从周是因周礼比夏殷礼更齐备,且“自周之后,制度犹可知。以为变易损益之极,极于三代,亦不是过。” [4]14 “三代”之变代表了礼制损益变化的极致,而周礼又最为完备。因此,在郑玄看来,周礼最具现实意义。但在孔疏看来,三代的礼法损益并不具有重大意义,它们分别代表了“王天下”的三种之重,它们的意义在于后王可于其中取法、考校。[1]2040孔疏的重大转变在于,三王之礼从政治现实的根本原则褪变为后世治政的历史资源。
这一重大转变使孔子或者圣人的意义也发生了转变。郑玄一再表明,圣人的主要标志在于他将为天下制礼作乐。孔子虽未得位,不能制作专属之礼,但孔子将文王开启的周礼融于《春秋》与《孝经》,为后世取法。概而言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即孔子兼包尧、舜、文、武之德而作《春秋》;但具体而言,孔子则是继尧舜之道,而守文王之法。这是郑玄解决孔子“从周论”与“有德无位”论的巧妙途径。在孔疏中,祖述、宪章分别对应的是尧、舜之道与文、武之德;孔疏解释“宪章文武”为“夫子法明文武之德” [1]2046,尧、舜之道的“道”也是道德之意。[1]2046不管是尧舜还是文武,他们对于后世的根本意义不在礼法,而在道德上。这些先圣明王的历史所具有的深刻内涵不再体现于具体的礼制上,他们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他们一以贯之的道德本性。孔子也同样继承了这一贯的道德本性,孔子以及他所制作的《春秋》体现的都是这一道德。通过强调“德”在圣人问题中的根本性,孔子虽“有德无位”亦为圣人的叙述得到了重新诠释。
孔疏强调的“道德”并非现代“利他主义”。在其语境中,道德实为中和之德。因此,道德必然发用,所谓“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有德之人总要起而为用,将自身的道德作为化育万民的依据。所以孔疏认为“孔子之德与天地日月相似,与天子、诸侯德化相似。” [1]2047此即“以德化民”之意。然而,德在化民的过程中是如何发用的呢?经文言“君子内省不疚”,又引诗“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此表明孔子修德不已。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所谓“以德化民”集中表现为圣人对君子的德性感发与范本引导。故而,孔疏言“君子敬惧如是,故不动而民敬之,不言而民信之。”[1]2050其要在于圣人的敬与惧,圣人化民之务“本诸身”,以自身的行为与德行来为民作表率。德在化民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恰恰体现在前文所言的“诚身”之上,贤人因圣人之德而自觉的“诚其身”。如此圣人方可“不大声与色”而“使民自化”。
四、结语
在郑玄与孔疏之间,或有更多思想史线索可待发掘,然就《中庸》而论,魏晋南北朝的“中庸学”专作皆散佚,只剩孔疏中遗留的部分。就郑注与孔疏而言,虽有“疏不破注”之说,但二者在对篇旨的理解显有分歧。在中和、中庸的理解上,郑注与孔疏总体上保持一致,都将中和看作了圣人之性,中庸正是圣人之性的发用。然郑注认为实现中庸需借重礼乐政教,而孔疏却刻意淡化礼法的重要性,转而强调中和之德与“己身”的关系,将“中和之为用”的“用”的意蕴加诸己身,认为“能行之于己,即是中庸”[1]2000。由此,孔疏减小了中和与中庸之间的张力,中和之德与中庸之德渐渐趋近。这一观点也延续到关于“诚”的讨论当中,在孔疏看来,君子贤人的修身就是诚身,他将经文“以礼修身”的意义重新加以解释,从而为诚身留出空间。诚身实为贤人对圣人中和之德的模仿。孔疏认为中庸的实现需要圣人对贤人的感发,这种感发主要体现在个体德性上。就中庸与诚身而言,郑、孔的区别在于以礼法还是德性来看待圣人。郑玄以为圣人不仅具有德性还要以之为天下制定礼法,通过礼法政教教化天下。为此,他不得不用一套繁复精巧的方式来论证孔子与传统圣人完全一致。孔疏并不如此,转而强调孔子在德性上与传统圣人的一致,从而回避孔子制作礼法的问题。孔子所继承的道正是传统的圣人所具有的道德,这一传统才是确认孔子圣人位格的关键。这种道德自然而然让贤人君子向慕而自诚己身,那么,中和与中庸实无区隔。圣人以德化民也不过是使民自化而已。就孔疏而论,《中庸》之篇旨更能落在子思绍述圣德上。实际上,孔疏在疏解经文和郑注的过程中已经将理解的重心悄悄转换。礼法与中庸的紧密关系被解除,而代之以中庸之德本身。郑注与孔疏的解释差异渐构成两种解释倾向。其切要之处在于,儒学从侧重政治秩序的构建转为侧重心灵秩序的构建。
参考文献:
[1]〔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M]北京:中國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