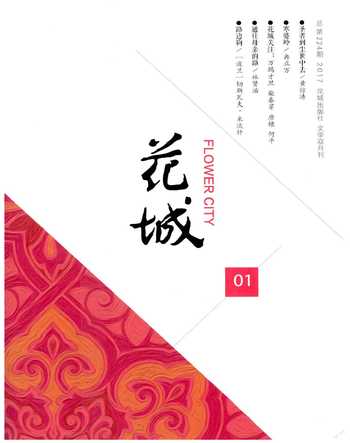路边狗(节选)
切斯瓦夫?米沃什
切斯瓦夫·米沃什,一九一一年生于立陶宛,二战时参加了华沙的抵抗纳粹的运动,战后作为波兰文化专员在纽约、华盛顿和巴黎工作。一九五一年出走巴黎,一九六〇年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是美国人文艺术学院会员之一。一九八〇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二〇〇四年去世。米沃什的著作注重内容和感受,广阔而深邃地映射了二十世纪东欧、西欧和美国的动荡历史和命运。其主要著作有《第二空间》《乌尔罗地》《路边狗》《被禁锢的头脑》《米沃什词典》等,被视为二十世纪东欧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路边狗
我曾经乘着运牛粮的马车走遍家乡的土地,挂在车后的铁皮桶互相碰撞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桶里是为马儿准备的水。当年这儿还是一片荒野——山丘,松林,零星坐落着的农舍——这种屋舍没有烟囱,所以屋顶总是烟雾缭绕,仿佛着了火一般。我一时悠闲地在农田和湖泊之间游荡,一时又信马由缰,向远处驰骋,直到能看见松林背后的村庄或庭院。这时,总会有一条尽忠职守的小狗冲出来对我叫。想来那还是世纪初的事了,百年不过一瞬而已。我不仅常常忆起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也总想起陪伴他们的那一代又一代的狗,人们日复一日地劳碌,而它們始终陪伴左右。有一天在清晨的梦里,我没来由地想到了这个有点好笑,却令我动容的名字:“路边狗”。
寻 找
我总以为,人类在二十世纪所认识到的种种残酷一定能用语言概括出来。于是我翻遍各种回忆录、报告文学、小说、诗歌,抱着能找到这些文字的希望,却每每失望:“这不是我要找的。”于是一个不敢肯定的想法在心中萌生了:人类命运的真相并不是他们教给我们的那样。但我们害怕给真相命名。
与造物主换位思考
假如给你权利重新创造世界,我想就算你绞尽脑汁,也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根本无法造出一个比现在更好的世界。你不妨去咖啡馆坐坐,看看来往不绝的男男女女。诚然,他们可以被赋予不食人间烟火之身,不再受衰老、病痛和死亡侵扰。可是,这世间层出不穷的复杂和变化多端正是源于世间万物中所蕴含的种种冲突。如果没有屠宰场、医院、墓地和色情影片这些东西作为思想的载体,那么思想的魅力也将不复存在。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精神和思想居高临下的嘲笑,人类便会受本能欲求驱使,展现出动物性的愚笨。看起来,人们已经学会质疑造物主的道德动机了——祂创造世界的原则就是:让所有事情变得更有趣和好玩。
为何而羞耻?
诗是一种令人羞耻的东西,因为它萌生于某种私密的行为。
诗与肉体的意识紧密相连。诗凌驾于肉体之上,它是精神的,但同时也脱离不了肉体。然而,它假装自己完全属于精神领域,与肉体毫不沾边,便有了令人羞耻的理由。
我为我是一个诗人而感到羞耻,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扒光衣服在公众面前展示身体缺陷的人。我嫉妒那些从不写诗的人,他们因此被我视作正常人——然而我又错了,因为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能称得上正常。
用心感受
写作时我会进行一种特殊的转化,那就是把意识的数据——我的内心感受——转化为其他与我有相同感受的人的形象。因此我不仅能写自己,还能写别人。
崇 高
崇高:清醒地用手无寸铁的肉身来面对人们嘲讽的利刀。
创造日
其实根本没这么难。
上帝创造世界。谁说是在很久以前?
不久。就在今晨。也许是一小时前。
因为那快要枯萎的花,重新绽开了笑颜。
奔 跑
他们疲于奔命,却忘了最重要的事。
他们奔跑着,好像相信自己会永生。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珍贵。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不可能
可怕的刑具变成了得救的象征,
这就是十字架的秘密。
教堂里随处可见的东西,怎么会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就让惩罚的火焰烧毁这个世界的根基吧。
缺 憾
诗与一切艺术都是缺憾,它提醒着人类社会,我们是不健康的,虽然要承认这一点很难。
幼 稚
诗人是成人世界里的孩子。他深谙自己的幼稚,所以必须假装融入成人的活动与习俗。
他心里住着一个孩子——被成人所嘲笑的天真而情绪化的孩子。
抗 拒
我不愿谈论诗的表达方式和美学理论,因为这些东西会把我们局限在一个单一的角色里。我为此感到难为情,或者说我不愿坦然接受被定义为诗人这一事实。
我很嫉妒尤里安·普舍波希①:他为何能习惯披着诗人的外衣?难道他内心没缺点,也没有黑暗的纠结和无助的恐惧?难道他觉得这些永远不会显现出来吗?
艺术崇拜
人们对艺术的崇拜日益增加,正如独立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是一群不愿封闭在社会习惯与宗教规则中的人。这群人常去博物馆,例如卢浮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也乐于参观那些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时期的真正的教堂。
每一个独立的人都想要体会所有别人体会过的东西,包括在电视屏幕和杂志画报上展现的那些:有关性、服饰、汽车和旅行。这种人喜欢聚集在一起活动,并为彼此拍照作为记录。他们并非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渴望的更高級的东西,转化成了令人惊叹的艺术。
亚历山大里亚
小时候我不知道从哪儿接受了这样一种说法: “亚历山大里亚”代表着创新热情的减退和解读旧经典的潮流。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在今天是否还正确,但在我经历过的时代,词语并不单纯代表它的本义。举个例子来说,“树”是指代“关于树的文章”;“关于树的文章”又是指代“以关于树的文章开头的文章”,等等。而“亚历山大里亚”则指代“衰落”。很久以后,人们必将忘记这种游戏,然而在什么都忘不掉的年代会怎样?
博物馆,相片,复制品和电影胶片——在这些丰富的信息之中,独立的人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被无处不在的记忆包围了,并且正在攻击他们本就不够强大的意识。
过 去
过去是不准确的。那些活得很长的人知道,亲眼所见的事总是会被流言蜚语、神话故事、各种被放大或被压制的消息包裹起来。“根本不是这样的!”他想大叫,可是却没有,因为人们只看得到他张大的嘴巴,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不阳刚的
写诗这件事被认为是不阳刚的。但从事音乐和美术的人却没有这样的困扰。好像一切艺术都具有的女人气全算在诗人身上了。
当一个族群忙于战争和猎食这种重要的事务,族里的诗人便会承担起巫医或萨满的身份,他们可以利用法术保护、治疗或伤害一个人。
诗的性别
如果诗有性别,那一定是女性。缪斯不就是女性吗?诗敞开胸怀,等待着人、灵魂或恶魔。
珍妮①说她没见过任何一个比我更像乐器的人,她说我像乐器一样被动地屈从于声音,这也许是有道理的。我感到羞耻,像是一个孩子站在成人中间,一个病人站在健康的人中间,一个爱穿女人裙子的易装癖者。他们说我性别不明,不像个男人。直到有一天,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所谓男性化而且很健康的特点,他们一直质疑我缺少这个特点,那就是神经绷得太紧,以至于被逼疯了。
语言的力量
“一切没有被说出来的,注定要消失”②:纵观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会惊讶地发现,每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都值得被寫成史诗、悲剧或抒情诗。可他们都消逝了,只留下淡淡的痕迹。可以说,即使是最有魄力、最热血、最果决的人,与仅仅是描述初升之月的几句精雕细琢的话相比,也只能勉强被称作影子罢了。
艺术与生活
该如何解释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比如有这样一位小说家,他在描述人物心理时很爱参考自己的想法。作家笔下的人物与作家本人相似,人物的劣行也许能够警示作者,促使他改正自己的品行。为什么有时作家笔下的人物就是自己的化身,他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内心展示了出来?又是为什么,有时作家所呈现出的东西与自己毫无关系,甚至像断线的气球一样,脱离了其创作者的控制?
不愿承认自己是酒鬼的人却懂得怎样描述醉酒;自诩大方的吝啬鬼却写出了抠门的实质;写下贪婪鬼的丑态的人却没意识到那就是他自己。相反,肮脏不堪的人写出了纯洁忠贞的爱,胆小软弱的人写出了英雄主义,自私自利的人写出了伟大的同情。
五光十色的世界
人类在生活的残酷之上建立了五光十色、蓬勃盛大的思想世界。然而一切艺术、神话和哲学都不会只待在属于自己的高处。因为正如我们所知,这个星球最初诞生于思想的梦,可如今它已被数学等式所改变,并将一直被改变下去。
警 告
儿童画册中的小动物们——会说话的小兔子、小狗、小松鼠,或者瓢虫、蜜蜂、蟋蟀。它们与现实中的小动物或者昆虫的相似程度,反映了我们对世界的想象与真实世界的相似程度。想想看,真令人毛骨悚然。
将来会怎样
仿佛艺术家的直觉——他灵光一闪,在一瞬间看到了自己的作品两三百年后的模样。
两三百年后他的作品是否还存在,取决于这种语言本身是否还存在。也就是说,取决于这种语言的使用者——多数人是愚昧的,他们会把语言往下拽;少数人是智慧的,他们会把语言往上提。这两种人各有多少?
我无法原谅我不曾相识的先人们,他们不好好整理波兰语的读音,把prze、przy、sci这样难读的音节留给我来头疼。
我们这个圈子
艺术家之间的嫉妒尽管引人发笑,却并不好看。好像每个人一抓到机会,就会把另一个人的头按进水里。看多了这种事,便不由自主产生了阴暗的想法。因为这恰恰就是我们人类的处境,唯一不同的只是被争夺的东西——在生活的战场上,人类追逐金钱、爱情、安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诗人和画家则追求着最抽象的荣誉,可人终有一死,追逐这种荣誉看起来似乎是完全没必要的。然而,他们在追求这种荣誉时并没有考虑到未来,只是为了当下的自我评价,仅此而已。正面的评价像一面能美化人的镜子,负面的评价则会令镜中的形象变得扭曲,再天生无害的品性也会显现出恶魔般的模样。
在男女的亲密关系中也是一样:追求、满足、欢笑哭泣——亘古不变,人们费尽心力想要得到的,最终还是对自我的肯定。换句话说,他们所求的只不过是对自己美丽的容貌、强大的吸引力或陽刚的男性魅力的证明。
迷 宫
在我生活的时代,人们非常崇拜自己头脑的迷宫。这是诗人与艺术家们日益旺盛的活力的证明。人们用遣词造句和涂抹画布代替了向天地、海洋、星云的提问——他们再也不在乎那些答案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本该感到开心的。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异议是从何而来。
“可是,正如我说过的,我生在农村。那儿的人们在木头教堂里向耶稣祷告,而由椴木雕刻的太阳和月亮是祂的随从。为了严格遵守旧式的传统,我虔诚地创作圣歌和颂歌,忘掉思想的尊荣,只是像使用纸和笔一样运用它。”
梦的疆域
梦的疆域也有自己的地形。多少次我来到那里,认出了同样的路牌,同样的山路,我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才能到达想去的地方。这些地形不完全一样,总在变化,就像是脑中对空间的记忆加密后,复又重现出来。虽然我知道梦里的地形是取材于记忆,却无法辨认出是记忆中的哪一处景色。这些地方是真实世界里不同地点的投影吗?还是它们都在模仿同一处风景呢?
超 然
年老的诗人像一位道家的智者,一边努力保持着自己内心的超脱,一边观察着年轻人盲目地奔波。这让他回忆起从前的自己,那时的他已经意识到了些什么,却没有足够的渴望。
经 验
人的生命变得更长了。这是医学知识的功劳。他自己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每天严格遵照医嘱服药,身体早被这个病给拖垮了。所以他与那些讥笑进步观念的人是持不同意见的。
同 时
我坐在火车上通过一座桥,同时我也走过一座桥。A同时又不是A。这岂非梦里的逻辑。可是,上帝是唯一的,同时又是三个人。面包和葡萄酒同时也是耶稣的身体。
怀 疑
我曾经像一个腹部受了伤的人,边跑边用手托着自己的肠子。而且据我所知,还有人和我一样。一个被迫总在担心自己伤口的人,他说的话会是理智的吗?
论 据
诗人被逐出“理想国”是必然的。①问题是怎么驱逐他们?诗人说出了所有人的脆弱敏感。他们的人数以百万计。然而,也许突然有这么一天,国家为了保护水和空气的洁净,要对某些污染世界的人实施“清扫”。
诗人被逐出“理想国”的事总是以讽刺的形式被写出来。为什么?国家成立了特殊机构,专门抓捕那些写诗上瘾的人。在这部“科幻小说”中,应当删除一切讽刺的语调,还应当体谅特殊机构工作人员的难处。正如在某些警察国家中发生的那样,诗人可以自己花钱去印刷那些难懂的诗,并且单凭可观的人数就可以让国家不得不与他们讲和。然而这部“科幻小说”的戏剧性在于,大多数人竟然都一致地把自己对诗的需求隐藏起来,并且出现了许多假意投敌的人,就像当年在西班牙的马拉诺一样。所有人都不敢在家里藏匿诗集。同时,特殊机构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在与自身的脆弱作斗争,他们假装不记得自己在家偷偷填完的诗。
好莱坞
让我们想象一下,当好莱坞的那帮人——投资人、导演、演员落到诗人手里,会是怎样的下场。这帮人每天挥金如土,侵犯数百万人的思想,他们从来不是为了任何理想,而是为了充实自己的腰包。诗人会判给他们怎样的刑罚呢?他在犹豫,不知是该切开他们的肚皮挖出肠子;还是用铁丝网把他们都监禁起来,断绝食物,逼他们自相残杀,让那些最有权势的大亨们率先成为别人的盘中餐;还是把他们都扔到一个大火炉里,或者把他们捆在一起扔进坑里活埋了?然而,当诗人审讯他们时,见到一个个卑微的、颤抖的、讨好的、毕恭毕敬的嘴脸,便又忘记了他们的傲慢,打了退堂鼓。这些人的罪恶正如集权制国家公务员的罪恶一样难以界定。最公正的裁决就是立即判他们所有人死刑。毫不在意地耸耸肩,让他们解脱。
宽 容
他早就丢掉了自己的固执,但随宽容一同增长的还有对一切的怀疑。他坐在黑暗里,看着戏台上的提线木偶竞争、祈祷、骄傲、忏悔,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愚蠢。
不 同
看起来一样的东西,往往是不同的。有些毒蘑菇看起来和可食用的蘑菇一样。有些哲学根本不是哲学。有些音乐只称得上是尖叫和噪音。
以下是一位可怜而纯粹的诗人对音乐的区分:
提到音乐,我就想到曾经看到的一则新闻,说的是美国有一位名叫桃乐丝·瑞塔莱克的女士,她花了几年时间完成了一个有关植物听音乐的实验。这个实验的结果发表在一本名为《音乐与植物》的书上。她曾在一些盆栽植物旁边播放激烈的摇滚乐,每天持续几个小时,两三个星期之后这些植物就都死了。叶子变黄脱落,茎背对音乐生长,整个植物的形态变得很奇怪。同时,瑞塔莱克女士在另一些植物旁边播放巴赫、爵士乐和印度西塔琴所演奏的宗教音乐,那些植物则变得生机勃勃。一些匍匐植物——例如菜豆,向着音乐的方向生长,有的枝蔓爬上了音箱,甚至有要钻进音箱的趋势。
——爱德华·斯塔胡拉《一切都是诗》(1975年)。
音 乐
写到音乐,值得揣摩的不仅有声音,还有做音乐这件事。交响乐团或是四重奏乐团的演奏着实令人惊叹。单单是因为几个来自这座城市不同的角落、不同的家庭,住在不同的房间,窗户面对着不同的街景的人相聚到一处,根据乐谱把写在纸上的音乐表现出来,就足以让人赞叹不已了。乐手本身也各有特点——他是光头,他留着大胡子,他是瘦子,而身穿一条绿色连衣裙的她,在一群燕尾服中格外亮眼。他们在演奏,或者说是在服务于一种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存在。那是在他们生前便出现,死后也不会消失的东西。我们作为听众和观众,参与了感性的人在另一个世界的一日游,那是一个精确均衡的、不屈从于任何逻辑的、纯粹的理想世界。乐手们在这个世界的边界上拉动琴弦,敲击琴键,吹响笛子和狩猎号。而我们,想到人间竟然如此美妙、丰富和多样,心中便升腾起巨大的喜悦。
猫的秘密
猫已经和人类共居了几千年,它们的行为表现已经没什么神秘的了。这是当然的,它们已经为人类忠诚工作了几千年。农业文明意味着粮食,而哪里有粮食,哪里就有老鼠。但不管环境和条件如何变化,猫却一直都在。
然而猫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特点。你有没有注意到男同胞们只要一谈到猫,他们的脸上就会露出一种俏皮而诙谐的神情?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谈到性的话题时。如果是谈论狗的话,就不会激起这种半明半暗、有些私密感的反应,而是达成一种众所周知共识。我断言,人类和猫是因为一种肉体上的协议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貓的面前并不作为人的角色,而是成为了一种屈从于视觉与触觉的物种,而这些感觉上的诱惑使我们被它吸引,正如我们被某些树木、花鸟、动物、山水吸引,被某些形状和颜色吸引一样。猫特有的外表让人想要抚摸,抚摸是一种爱的语言。我们给予猫无数的哄逗,还有小猫、猫咪之类的甜蜜称呼。另外,我们对猫的看法非常趋同,无论我们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而对猫的喜爱、对猫的虐待,似乎都是出于这一种吸引,只是分了两面。
这种普遍性值得深思。虽然存在个体差异,但我们属于同一个物种,同样有头、手、腿,解剖图上还展示了我们体内有什么东西。并且,我们的身体构造决定了我们会像向日葵面向太阳一样,将目光投向我们认为美好的事物。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我们对于猫在色情上的(对你没看错!)偏爱,就可以开始问自己一些关于我们的天性的问题了。
猫无疑也有它的天性,所以我们和猫之间的契约又標志着它的天性与我们的天性的交汇。可是意识、语言、历史不可能同意!它们或许会惊呼,我们怎么还远远不如那个低劣的动物!我们别再骄傲地抬高自己,也别再把我们的精神高地和低级感官区分开来。我们倒不如享受那位正在沙发上伸懒腰的家中成员所带来的好处,忘掉那些说人类天性不存在的哲学观点。如果说要在不断变化的人类天性中证明它的存在性有些困难,那至少在这个伸出红润的舌头打哈欠的生灵面前,我的天性正使我怜爱地看着它,而这说明我本人的人类天性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并且我要强调,人类天性的存在性不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存在,我们才能确定我们的法律和制度中哪些是对它有利,而哪些是与它的基本需求背道而驰的。
这样一来,我们从猫谈到了一个重大哲学问题。虽然猫听不懂,但我们姑且将此归功于它们吧。
[《路边狗》(切斯瓦夫·米沃什著 赵玮婷译)2016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杜小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