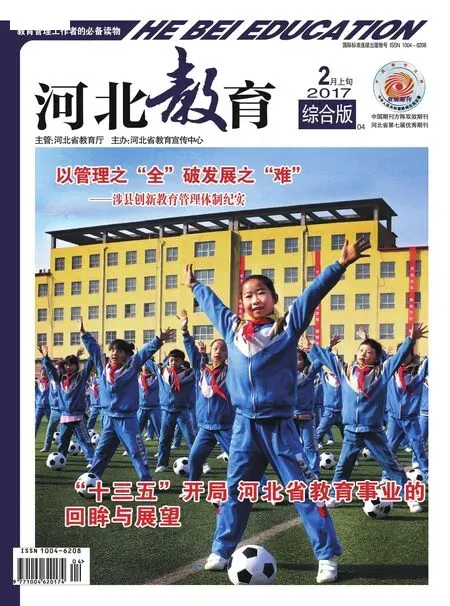光阴里的连环画
■郭建涛
光阴里的连环画
■郭建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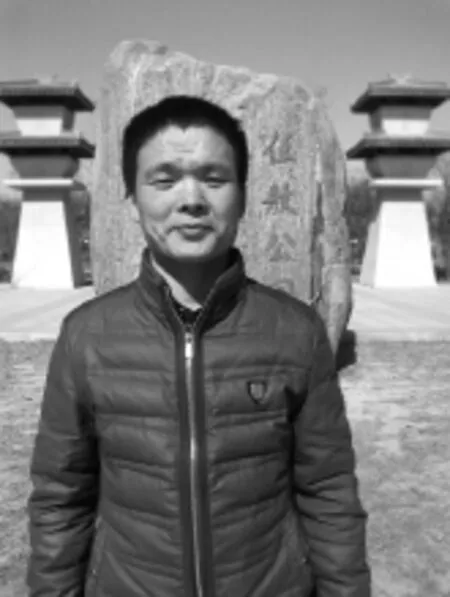
一个男人,奔四十的年纪,碌碌奔波在尘世之间,挥洒粉笔屑于讲台之上,锅碗瓢盆的碰撞里,很难有时间去怀念什么。但既是跟书本、跟文字打上了交道,在某个星稀月明的夜晚,在某个银露初绽的黎明,总有些不经意的过往穿破时空,撞向现在,在心房洒一片温润——就像,那光阴里的连环画。
我能记得的最早的“书”,是贴在老家墙上的连环画。
像当时很多人家一样,我们也是一大家子住在一起。正房四间,西边两间奶奶住,东边两间大伯一家住。我们一家住西屋两间。
老家的房子是蓝砖加泥坯的混合结构。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来的人,对这种房子应该还有比较清晰的记忆。地基由蓝砖砌起,上面铺一层秫秸,据说是为了防潮。地基往上,用麦秸泥脱成的坯垒起来,为了保护泥坯免遭日晒雨淋,也为了装裱门面,遮蔽寒陋,外侧用蓝砖裱起。房子里面用麦秸泥抹墙,再用白灰浆粉刷。因为底子差,白灰抹上去也显不出多白,而是斑驳阴沉,让人平添一股寒意。
给这房子增加色彩的,便是这过年时贴在墙上的连环画。一张有桌面大小,分作巴掌大(当然得是父亲的手,不是我的小小的手)的几十个格子(怕是得几十个吧,总觉得数都数不来呢),每个格子里都画着彩画。这幅画太阳还在树梢,那幅画已经升到了头顶;这幅画小和尚在河边担水,那幅画就已经挑到了山上;这幅画上的好汉,弓着步,亮着掌,那幅画上他已经腾空跃起,把一个大胖家伙(也或许是个贼眉鼠眼的瘦家伙)打翻在地。还有亭台,还有楼阁,有悠悠远远的山,有疏疏落落的树……每幅画下面都写着字,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
我家墙上贴过《东方旭》(似乎是这个名字)。我还不大认字儿,就看画儿。父亲得闲,也偶尔讲解几句。大意说,东方旭打败了俄国大力士,很了不起。啊,俄国——大——力士,都打得过,那当然很了不起啦。至于“俄国大力士”是什么,其实心里并不大清楚。
奶奶屋里,贴过《嫦娥奔月》。
弟弟妹妹出生后,一家五口住一盘小小的土炕就显得有些挤,于是我就去奶奶屋住。
爷爷去世多年。我跟奶奶祖孙俩住一盘炕,那是很宽敞的。炕北边放着座柜,柜上摞着被子;南边是窗户,窗户边有棵笨枣树;东墙贴些年画,我记得最准的,就是这《嫦娥奔月》,刚认字儿,不知道“嫦娥”怎么念,就自作主张想当然的拆开,念成“女常女我”。
啊,这个仙女儿,能飞!看她长袖飘逸,看她裙摆若流云,多美。至于广寒宫有多“广”,多“寒”,倒是从没想过。
踩着被窝卷,面壁“读”两眼“书”,打个滚翻下来,趴窗户边瞅外面的树,要不,就听奶奶讲故事:
“有仨媳妇,都是半语儿(吐字不清),在月亮地下边凉快。
‘好停(晴)天哦!’大媳妇说。
‘好天停(晴)哦!’二媳妇说。
三媳妇笑话她俩口白不清,就说:‘克天(注:方言,满天)一个大卧(月)亮!’”
哈哈哈,克天一个大卧亮!哎呀呀,这月亮,多大,多明!那嫦娥飞上去,都能照镜子了。
光阴似水流,匆匆三十年下来,当年润泽了我小小童心的这些优美、正气、神奇而又飘逸的画作,早已消失在时光的河流里,了无痕迹。可它们似乎又并未走远,伴着依稀旧梦,伴着白发红颜,从光阴深处走来,走向我蓦然回望的眉梢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