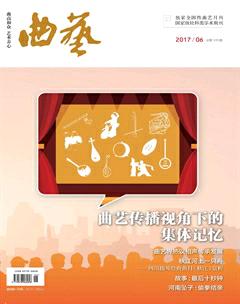曲艺作品“复原”集体记忆的“三重套合”
秦珂华
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这一社会心理学的概念,目的是为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方法。而曲艺人论及这个理论,则是试图通过对其理解、吸收、转化、借鉴,在一定层面上探讨对曲艺创作的理论指导意义,为曲艺创作的方法论研究积累素材,进行实践性的尝试,使得曲艺创作能够在理论的支撑下更加有章可循。
“集体记忆”理论具有较强的边缘性和交叉性,而且正在发展完善之中。我们以集体记忆理论讨论曲艺创作是基于其广义的定义,即“集体记忆是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这种群体可以是一个宗教集团、一个地域文化共同体,也可以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这种记忆可是分散的、零碎的、口头的,也可以是集中的、官方的、文字的,可以是对最近一个事件的回忆,也可以是对远古祖先事迹的追溯。”(搜狗百科)曲艺创作用来复原的集体记忆素材必当符合这个定义,人们脑海中共同存在的模糊的或者清晰的历史人物、传奇人物、经典故事、经典作品、艺术形象、典型事件、风土人情等等,都可以作为素材用以创作。
无论是功能主义范式的还是构建主义范式的,集体记忆研究和实现的基础都是“集体认同”,由此看来,用复原集体记忆的方法创作曲艺作品,铺垫(无论叙事铺垫,还是情绪铺垫)的过程已经由意识或潜意识深处的情感和形象构建完成。其最核心的好处是在一定范围内更容易引起共鸣,这无疑为曲艺创作省了很多力气。那么,引进集体记忆素材进行曲艺创作之后,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才能使这剂奇药发挥它应有的功效?笔者认为,要做到“三重套合”。
第一重 集体记忆素材要与技巧框架套合
技巧框架,一方面是就曲艺的本质特征而言,另一方面是就曲艺的独有风格而言。
首先,曲艺是说唱艺术,就本质而言,是言语的艺术,口语是第一要素。以曲艺形式复原集体记忆素材,就要突出和注重口语表达及诉诸观众听觉的艺术特征。
小说《林海雪原》自1956年诞生以来,京剧、话剧、电影、评书、电视剧等艺术形式分别援引这个经典故事进行再创造,均取得良好效果。杨子荣的形象和智取威虎山的故事家喻户晓,广为传颂。我们以著名的“打虎上山”一段举例,比较分析曲艺和电影本质技巧的不同。
听评书,观众是看不到具体形象的,只能靠演员的描述在脑海里勾勒出形象,唤起艺术美感,所谓“三分靠人听,七分叫人想”。因此,袁阔成先生用了三番铺垫:杨子荣骑着铁叶青(马),临近威虎山了,在一片小树林外休息,这时,“从西北角卷过来一阵风”,这风与往常的不同,格外地凄厉(这是第一番);接着通过对马的嘶鸣及其异常情况的交代,烘托紧张气氛(这是第二番);继而用杨子荣的心理活动进一步渲染情绪(这是第三番)。在将近7分钟的三番铺垫之后,老虎终于出场。
……好大的一只虎。头如麦斗眼似灯,七尺的身子八尺的尾,身上的花纹一道挨一道。嘴张开了跟小火盆似的,鲜红鲜红的,舌头往下一耷拉,露出四个门牙,牙这么一呲,呵!这个凶!老虎头上有三道纵(横)纹,一道利剑,真像个“王”字似的,两耳往后这么一撇,这老虎就过来啦……(依据袁阔成《林海雪原》第三十回演播的音频整理)
至老虎“开脸”完毕,千钧一发的紧张氛围到达顶点,观众在紧张氛围的严密包裹中急于往下听结果,那么,杨子荣和老虎搏斗的一举一动——即便是“轻拿轻放”——也都会是扣人心弦的!这是曲艺的技巧:在演员肢体语言的有限辅助之下,依靠赋赞似的语言铺排描绘,制造紧张气氛,构成艺术冲击。
再看2014年上映、徐克执导的电影《智取威虎山》是怎样处理“打虎上山”的。镜头一:杨子荣靠树休息;镜头二:马嘶;镜头三:杨子荣面部特写(转睛搜寻并思考);镜头四:老虎从远处走来。短短两秒钟,老虎的出场便完成了。紧接着,通过杨子荣与老虎的搏斗、老虎扑咬铁叶青、杨子荣枪击老虎等一系列动作,构成视觉冲击,达到艺术效果。
电影的第一要素是动作并非语言,有些语言铺垫是“动作”所不能完成的,比如,杨子荣“龙行有雨、虎行带风”“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老虎”等这样的心理活动,是无法用动作来表现的。再如老虎的外貌,也只能靠观众去看,身体多大、尾巴多长等特征也无法用动作表达出来。即便能够完成反复的铺垫,也会显得非常累赘,反而达不到理想效果。如果评书像电影那样,缺少必要的叙述交代,那么演员说不明白,观众也听不过瘾,艺术效果更是无从谈起。
对于思维深处的集体记忆,有些更适合用动作还原,有些更适合用言语还原,有些更适合用形象、线条还原。不同的艺术形式有不同的还原方式,不同的曲种也会有不同的还原手法,要根据素材的不同、艺术种类的不同来取舍、剪裁。
其次,曲艺是市井艺术,就风格而言,有着独特的市井意味。
小说《红岩》问世以来,足智多谋、枪法精准的双枪老太婆形象,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被众多艺术形式引用,改编再创造。我们看歌剧《江姐》中老太婆的一段唱词:
热血染红满天云,
革命人,永青春,
身虽死,志长存,
老彭好比苍松翠柏在山林,
你万古长青!
松涛澎湃震大地,
壮怀千秋撼人心,
铁流滚滚流不尽!
旗帜红,主义真,
蓝天高,大海深,
干革命后继自有人,
干革命后继自有人。
再看快板书《劫刑车》中老太婆的一段话:
想不到敌人真狡猾,
果然玩出鬼花活!
放心吧同志们,
我早派人把嘉陵江面全封鎖,
刘队长带领神枪射手二百多,
漫说他是一只船,
既便是条兵舰也走不脱!
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
金戈同志押俘虏,
华为开汽车,
回山去,准备听消息,
行动迅速别耽搁。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在意志坚定、刚毅果决这一性格的基础上,歌剧塑造的“老太婆”形象更加高大、伟岸;而快板书塑造的“老太婆”则更加亲和、平易,话语更加生活化。艺术形式决定了艺术风格,艺术风格决定了艺术表达,艺术表达带给观众不同的艺术感受。
用曲艺复原集体记忆,立足本质特征和独有风格选择适合的素材,则可扬长避短,腾出更多的精力直接去挖掘思想立意和锤炼技巧表达;如果素材不得当,就需要先花力气去进行素材的转化了。还应注意,如今的曲艺,主流故事载体的地位已被影视剧所取代(《曲艺》杂志2014年6月号《由快板串烧〈年味儿〉想到的》已有论述),因此,当下曲艺创作不一定追求故事的完整,场面的宏大,效果的冲击性,但必须恪守曲艺的本真,有曲艺特有的情思与意蕴,亲切与细腻才可能发挥曲艺的优长。
第二重集体记忆素材要与时间框架套合
时间框架即时代感。曲艺作品不能缺少时代感。事实上,人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总是把记忆赋予了当下的心情去体味。因此,我们选取集体记忆素材创作出来的作品不能也不可能与时代割裂。
扬州评话《皮五辣子》(原名《清风闸》)传承至今已有300余年。自乾隆年间浦琳始,经晚清龚午亭(浦琳第四代传人),至如今的杨明坤(浦琳第九代传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思想倾向、观众有不同的欣赏需求,演员(作者)有不同的心灵感悟。反应到作品中来,人物有不同的性格特征,故事有不同的思想内涵,结构有不同的表现技巧。就性格特征而言,浦琳的皮五是“无赖皮五”,龚午亭的是“侠义皮五”,杨明坤的是“凡人皮五”(季培均《时间艺术生命》),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同的皮五。就思想性和内容而言,浦琳将皮五的经历纳入“清风闸”公案之中,展开底层生活、描绘市井风情,具有一定的自传色彩;龚午亭将作品改造成纯粹的市井小说,皮五成为绝对的中心人物,着重展现皮五的喜剧色彩、无赖气以及他的凶悍和锋芒;至杨版《皮五辣子》再次拓展,将作者自己的生活和体悟融入书情,还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善恶有报”等中华传统文化观念深植在情节之中。三代皮五性格的蜕变,三次作品结构的调整和思想内容的扩充,正反映了历代创作者经历和感受的不同,这“经历”和“感受”便是时代的烙印、时代的风尚、时代的要求。
浦琳演说“皮五”或为原创,而龚午亭及杨明坤的创作可看作是发展继承,也可看作是采用集体记忆素材的再创造。自乾隆年间皮五诞生,300多年来早已深印在扬州人的脑海,家喻户晓,成为扬州人的集体记忆。由此论之,采用集体记忆素材进行创作,必然也必须套合时间框架。要选择符合当下意识形态的记忆素材,亦或赋予素材当下的思想意识,来讴歌时代精神、传递正能量,这样曲艺作品才能站得住、叫得响。
另外,直接承袭传统曲(书)目,即复排经典作品,也应属于采用集体记忆素材进行再创造的范畴,这同样涉及与时间框架套合的问题。例如相声《报菜名》《地理图》《八扇屏》《卖布头》等,自作品诞生上演以来,菜还是那些菜、地名还是那些地名、“莽撞人”还是“莽撞人”,“吆喝着卖”还是“吆喝着卖”,熟悉这些节目的观众不难发现,尽管节目核心部分大体不变,但一代又一代的演员使用的“垫话”“瓢把儿”乃至“底”不尽相同,随着调整,以利于观众接受。
第三重集体记忆素材要与空间框架套合
空间框架是指地域性特征。“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华大地,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和集体记忆。同时,同一地域的不同群体特征,也应涵盖在空间套合之下一并考虑。
首先,区域性生存环境在时间因素中传承变化的基本线索,留下了地域性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是只有该地域才有的记忆。
在地域性的集体记忆中,蕴含了无数宝藏可供挖掘。孟新的数来宝作品《数唱北京城》脍炙人口。尽管北京是我国首都,是历史文化名城,以北京城作为素材创作的作品已经有了很高的受众“兼容性”,但“北京人”和“外地人”欣赏这个作品得到的审美体验却是不同的。外地人欣赏这个作品可能会侧重欣赏作品本身的精彩以及表演的技艺等方面,而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获得技巧层面的美的享受的同时,对由集体记忆积淀而来的故都情怀的体验则更为深切,“心灵的补偿”与“回味的叹息”也更为明显。
2003年笔者创作了群口快板《锦州礼赞》,作品主要表现锦州的风景名胜和美食特产等。作品在锦州本市的首演效果较好,尤其唱到“沟帮子烧鸡”和“北镇鸭梨”等处,观众共鸣强烈,引来掌声笑声不断,而在沈阳的一次演出则效果平平。后来笔者渐渐领悟到,沈阳人虽然也品尝过沟帮子烧鸡、北镇鸭梨,但沈阳观众对锦州特产的理解一定与锦州观众的理解不同。
一两次的感受和体验留下的印象,远不如地域性集体记忆所留下的烙印幽深、绵长、强烈。这烙印经由曲艺作品形象或情感的触碰便成爆发态势,便会形成强烈的共鸣和舞台效果。因此,为特定区域创作表演,必须套合本地区的集体记忆,才能获得艺术技巧和情感共鸣所带来的双重效果。
其次,地域特征对集体记忆造成限制,即全国、全民族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共同的集体记忆在不同地域会有不同的理解。
扬州评话艺术家王少堂先生和山东快书艺术家高元钧先生——表现同样情节中的武松却不尽相同。我们以“武松斗杀西门庆”这一节作比较,王少堂先生的评话这样讲:
……这一刻武松离(狮子楼)店门三四家门面了。他不敢进去,就掩在人家店面墙拐角边。为何不敢进店?……
不是武松害怕西门庆,而是担心有人给西门庆通风报信,如果西门庆跑掉,再抓他就难了。因此要隐蔽一點,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狮子楼找西门庆算账,这样才稳妥。
高元钧先生的山东快书则这样唱:
……武松近前要上楼,跑堂的过来忙拦挡:“这不是打虎好汉武二爷吗?”“是我!”……
他口中的武松没有考虑隐蔽的问题,言明身份直接上楼,而且还把手中提的潘金莲人头给伙计看,并说这是给西门庆“添菜助兴下酒浆”用的,还承诺楼上的瓷器打“坏了多少我赔上”。
不难看出,具有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等“基本性格”的武松,在江南地区,勇猛之外更加精細、缜密,在中原一带,凸显出了豪爽、粗犷。后来,田连元先生《水浒传》中的武松多少有了一些东北幽默。
无论集体记忆、个体记忆,都不是客观的,是加进了不同理解的主观存在。人们脑海中的武松也不是客观存在、一成不变的武松。就个体而言,是融进了个体的理解、情感和判断的;就地域而言,则是融进了地域文化、地域风俗、地域性格的。“一百个人读《红楼梦》就有一百个贾宝玉”,同理,一个地域就有一个地域的武松。因此,集体记忆提供的广阔题材要与地域特征进行套合,选取重叠的情感因素、文化特征、审美趣味进行创作,才能满足特定地域观众的特定审美需求。
第三,同一地域不同群体的差异性。
同一地域群体一般会对具有本地域特征的集体记忆或者更大范围的集体记忆具有共同的理解,但同一地域不同阶层的群体又会有不同认识。正如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引述前例,同为锦州人眼中的“沟帮子烧鸡”,老年人想的是过年才能吃上一次;中年人想的是,生活条件好了,想吃就吃;青年人想的或许是禽流感来了,暂时先别吃;至于少年儿童,烧鸡可能早已被西式炸鸡替代了。
用不同群体的不同特征套合集体记忆素材来进行创作,在前人已有的曲艺表演理论中已有总结,即“把点开活”,说法不同,道理相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绝不是舍本逐末,曲艺固有的意识、理念、技法,决不能丢弃,民族文化应有的自觉、自信决不能丧失。事实上,在以往的创作实践中,优秀的曲艺作家已经有意或无意地应用了“集体记忆”理论,也注意到了“套合”的要求,只是没有明确提出来,没有纳入曲艺创作的理论体系。同时,本文只论述了“三重”套合,亦或还有第“四重”第“五重”。总之,汲取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理论,是为了使我们的曲艺理论更加丰富更加完善,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百花园中焕发更耀眼的光芒,作出更大的贡献。期待着“集体记忆”理论能为曲艺创作带来一丝新的活力、提供一缕新的灵感,也期待更多有益的“他山之石”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