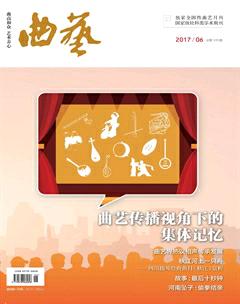“集体记忆”与中国曲艺中的典型形象
王赫
历史叙事与曲艺叙事
当代的人们对“历史”和“文学”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与对所谓“客观历史事实”的追求相异,人们开始重视“历史叙事”的意义和重构历史的可能性。如海登·怀特所说,历史学家的叙述不过是“对他认为是真实故事的一种再现”。
回溯中国传统,我们便发现“历史”和“文学(叙事)”的源头本就不是泾渭分明。如《史记》中生动无比的荆轲之歌、霸王之叹,这些叙述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文学创作?它们本就是对历史的一种重构,司马迁对悲剧英雄的评价与个人情感寓于字里行间,此所谓“成一家之言”。而中国叙事文学逐渐从史学范畴独立出来之后,也始终以历史故事为核心主题之一。小说和戏曲对历史的“戏说”或“演义”手法为人们所熟知,它们作为文人的游戏文字,也往往有寄托在焉。
而长久以来在中国土地上,尤其是中下层广大民众中传播最广、受众最多、感染力最大的艺术形式曲艺(即说唱艺术),作为一种“口头叙事文学”,其对历史的文学性与戏剧性重构,更起到了一种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所谓建构“集体记忆”的作用。同样的一段历史,如三国鼎立,如宋江起义,在千百年来说书人的传承、演绎、重构中,典型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早已脱离了客观的那段“过去的时间”,而成为千百年来广大“听书人”所共有的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而曲艺中的典型形象,正是其核心体现之一。清官就是清官,豪杰就是豪杰,奸臣就是奸臣,……每一个典型之后,都有中国中下层广大民众的价值取向与情感寄托。下面即举例分析几种当今依然活跃在中国曲艺中有代表性的 “典型”形象。
忠臣与豪杰:“忠”与“义”的紧张
在传统伦理背景下的整个中国通俗文学传统中,“忠臣”一直是典型形象之一。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曲艺中的“忠臣崇拜”并非仅仅出于对专制时代“忠君”伦理的肯定和接受,而是有与民族主义结合的传统。因此中国曲艺中最著名的的两大忠臣群像——杨家将和岳家将,均为“忠臣”兼“名将”。
以杨家将故事为例:历史上真实的“杨家将”包括杨业、杨延昭、杨文广三代。祖孙三代名将在生时已有盛名,而据考证,早在第三代杨文广尚未立战功之时,两代杨家将征辽的故事已传播开来,“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而北宋杨家将故事的流行,正与当时因强敌契丹而抬头的民族主义关系极为密切;而此后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的经历,无疑都助成了杨家将故事的丰富。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杨家将系谱的不断延续,而最长的杨家将系谱就出现在生命力最强的曲艺中。经清代《倒马金枪》等书目的扩充,今日北方评(鼓)书中已经构建出贯穿整个北宋历史的“九代杨家将”系谱。“杨家将”群体生命的延续,体现的是长期以来广大民众不变的渴望国家安定、民族独立的愿望。
在民众的期待中,面临外敌而担负民族兴亡重任的“名将”型“忠臣”应该舍命不渝地绝对“忠君”,即使或有潘仁美等“奸臣”从中作梗;然而当华夷之别、民族大义不被强调之时,常与“忠”并称的另一个概念就出现了。通俗文学传统中有为数不少的“江湖”(即“绿林”或“草莽”)豪杰。不同于杨门、岳门之“忠”,绿林弟兄的立身之本是“义”。“义”被理解为江湖之“仗义”,无论是“交友似孟尝”的秦琼,还是“及时雨”宋江,都是典型的义士形象。
如京韵大鼓《闹江州》中的李逵,作为短段,京韵大鼓节目与长篇大书不同,善于利用有限的表演时空和手段塑造人物形象。《闹江州》中连续利用侧面描写——二位解差敬重宋江,戴宗善待宋江,李逵崇拜宋江,宋江一语为张顺李逵讲和——充分衬托出宋江“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义士豪杰形象。对这种豪杰及对“江湖义气”的崇拜,无疑体现出历史上在中下层社会乃至地下社会的文化传统中真实存在而又常被理想化的社会习俗。
而通俗文学传统中,朝廷“忠臣”和江湖“豪杰”形象之间并非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如在上述故事中,杨氏父子不因宋帝不辨忠奸而改其忠心,而其股肱孟良、焦赞及后续故事中其后人杨怀玉却可因此抛弃朝廷,为王为寇;宋江本是官吏出身,落草并非其本愿;秦琼也恰恰是因为与不同出身、不同立场的各色弟兄的广泛交游造成了“忠”与“义”在他身上产生的根本矛盾,使他面临艰难的选择。对中下层民众影响最大的曲艺传统中,“庙堂之高”层面的“忠”和“江湖之远”层面的“义”两种伦理规范之间的融合、交流及其可能产生的紧张,正是中下层社会文化传统中真实存在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的复杂性的体现,而说书人的“历史”叙述中“忠”与“义”的典型形象,也就成为“小传统”中“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
智者与福将:“智”与“质”的对比
被后世主流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礼记·大学》中,“致知”是“修齐治平”的基础和前提;中国文化传统中,对“知(智)”的重视与追求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相應地,智者也成为曲艺中典型形象之一。
智者经常以谋士身份出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鲁迅所谓“多智而近妖”的诸葛亮。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形象已经塑造至极,然而在曲艺的短段节目中,孔明形象的塑造依然有独特之处。仍然以擅长讲述三国故事的京韵大鼓为例,不同的曲目在描绘孔明形象方面可谓各显其能,如《草船借箭》,在直接描写中加入孔明狡黠幽默的性格,使形象更加丰满;《博望坡》丰富了徐庶向曹操称赞孔明的言辞,强化了对孔明形象的侧面塑造。这些描述都是原著小说中不曾有的。虽然在长久以来的通俗文学传统中诸葛亮已经成为了近似于“先知先觉”的典型形象,我们依然能在不同的曲艺作品中看到各具特点的诸葛亮形象。
除了中国智者的代表诸葛亮以及包公、刘墉等智者形象,“神童”也是中国通俗文学传统中的典型形象的一种。我国最早的志人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即专门有描述“神童”的《夙慧》篇,在今天,相声《八扇屏》中的“小孩子”一段贯口脍炙人口。此类“神童”往往心智早熟,远在一般成人之上。如评书《杨家将》中的“双王”呼延丕显便是一个完全由说书人虚构出来的人物,其十二岁即点兵北行,智擒潘仁美的事迹固然嫌于夸张,然而正是这种单纯与夸张体现了此神童形象的典型特征。因为“神童”的机智往往容易与风趣和幽默相联系,所以相声中也不乏多种故事类型中的神童形象。相声《解学士》即来自于明代以来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才子解缙故事,其塑造神童形象是利用答对巧辩。
与老少智者形象相反,中国通俗文艺传统中恰恰有一类形象,其以与“智”相对的“质”,即质朴的生命力、直率的性格为特色。“福将”系列形象是一种典型:无论是著名的福将形象程咬金,还是孟良、牛皋、李逵、胡大海等,均以喜剧角色面貌出现,学者罗书华称之为“传奇喜剧英雄”。他们质朴,真实,直率,充满着生命活力。不同于诸葛亮、吴用等谋士形象,他们无甚远谋,甚至头脑简单而近乎天真,在成长时期,凭借“三板斧”或“三招半”的简单套路往往能产生很大的威慑力。当然,随着人物的成长和故事情节的推行,对“福将”的定位和描写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情感,程咬金在《薛家将》中的足智多谋已非在隋唐故事中既有的形象可以诠释的。
河南坠子《李逵夺鱼》便是塑造李逵直率与浑朴性格的典型。主人公李逵一出场便横冲直撞搅闹酒店;得知楼上有山东客人时,“顾不得吃酒就往楼上蹿”;知道来人就是其崇拜的宋江时,即“噗通通”跪倒在地;在张顺的渔船上不仅串鱼还要放鱼,与张顺厮打时一气之下就要行凶害命。这一切毫无顾忌,不需掩饰,其性格之“直”与“野”自然凸现;而被张顺拖入水中生命垂危后,不仅不表态屈服,而且依然在嘴上不服软,大夸海口的描写,更是在幽默中突出了其“视死如归”的倔犟与顽强性格。这细节为《水浒传》小说所无。正是因为对李逵形象塑造的典型而丰富,《李逵夺鱼》才广泛流传,成为诸多曲种的代表性节目。
对“智”与“质”的欣赏,其实体现了中国文化所追求的两个方面。中国人文思想的主流始终关注现实世界,在对“修齐治平”的追求中,自然欣赏“经天纬地”“先知先觉”的智慧。但这并非唯一的面向:《老子》在“见素抱朴”“絕圣弃智”“大巧若拙”的格言中体现了与“人为”相对的天生的、自然的生命潜力的价值;再加上对真诚的人性、浑朴的生命活力的欣赏,便使一种毫无伪装、掩饰,“野性”得可爱、单纯得可敬,充满生命力的人物“典型”也在曲艺观众心中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
曲艺叙事与集体记忆
从社会思想和社会记忆的角度来说,“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群体立足于现在中心观对过去的一种重构:“组成社会的各类群体每时每刻都能重构其过去。……在重构过去的行动中,这些群体往往同时也将过去歪曲了。”其“集体记忆”的理论与思维方法,对分析中国曲艺也有借鉴意义。
中国曲艺作为在最广大中下层民众中传播广、流行度高的艺术形式,始终对其受众群体有极大影响力。从唐代“俗讲”传统开始,以叙事为中心的曲艺表演有了较多的社会仪式意义。优秀的曲艺表演往往可以使观众或听众沉浸其中,对缺乏基础历史教育的民众来说,历史题材的曲艺叙事起到的就是构建民族历史记忆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题材的叙事类曲艺起到的作用就相当于中国的“民族史诗”。如果套用哈布瓦赫在《记忆的重构》一章中的用语,中国曲艺叙事就是构建一个有别于 “现在的社会”,而能令观众或听众“浸没于其中的社会”的最好工具。曲艺在其历史叙事中构建的这个社会,被赋予了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而这种魅力,就体现了在中国广大民众中长时间延续的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
十余年前,当代思想史家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中就指出,“流传的小说话本唱词”完全可以用来“讨论思想史的一些重大问题”。葛氏关注了一些问题,比如杨家将故事为什么会在积弱的宋代形成,三国故事中正统的确定与刘、关、诸葛形象的定型与政权合法性的概念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与我们所讨论的“脸谱化”形象都不无关系。容易料想:长久以来的中国中下层民众并没有与精英阶层分享严肃的“知识”。他们可能从未翻开过“正史”,但他们从“说书讲史”中获得了本民族的历史记忆;他们可能从未读过孔孟讨论仁义道德的语录,但他们从关羽、秦琼、诸葛亮、李逵等形象中接受了“忠”、“义”、“智”、“勇”等作为理想中的人格品质。他们可能不晓得“华夷之辨”,但他们从杨家将、岳家将等故事中接受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曲艺作为中国通俗文化传统中的重要角色,在重构历史、塑造典型形象中,构建了对受众群体影响深远的“集体记忆”,奠定而又体现了广大受众群体的思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