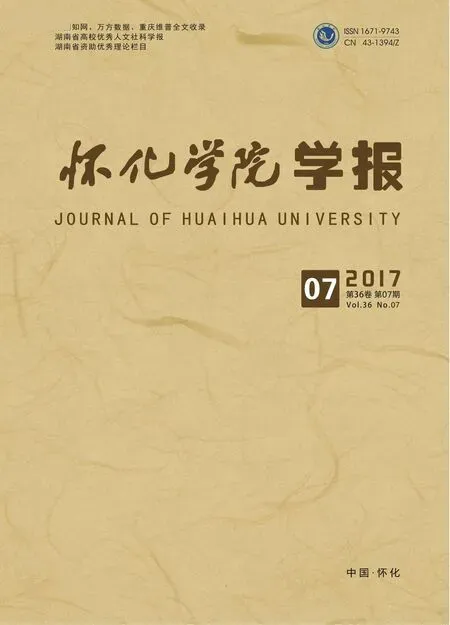唐代女性视角下的“才子佳人”婚恋模式
刘兰
唐代女性视角下的“才子佳人”婚恋模式
刘兰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00)
古往今来,两性婚配皆为世人所重,配偶的选择是缔结婚姻的必经之路。中国古代女子的择偶标准大多遵循门当户对,历史演进至唐,除南北朝就已根植社会的门第标准外,“才子佳人”婚恋模式逐渐为时人所尚。其一,唐女子生活在门荫与科举彼此消长、开放风气与传统观念羁绊的社会实践中,引发激烈思维冲击;其二,女性受开放唐风影响,接受更广泛的受教育机会,文学素养的提高促使其更乐于选择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我悦子容艳,子倾我文章”,琴瑟和鸣;其三,唐女子财产继承的法律认同及与本家的情理联系提升其婚姻生活地位。
唐代;女性;择偶观;婚恋;才子佳人
古往今来,唐女子“前所未有”“后所不容”的鲜明个性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多集中于男性视角论述择偶观,例如:贾淑荣《试析唐宋官宦阶层的择偶观》侧重分析唐宋之际男性官宦阶层择偶标准演变,指出“重门第”“重才德”“重财富”与社会各因素间的互相映衬;李志生《唐代百姓通婚取向探析》认为百姓阶层娶妇重财德,择婿重才能。同时不乏学者对唐代两性婚恋观作较为系统的论述:牛志平《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论证唐代两性婚恋自主思想的萌芽;毕宝魁《隋唐生活掠影》在择偶方式上提出“行媒”“自主”两种方式;李树桐《唐代妇女的婚姻》与牛志平《唐代婚姻的天命观》都阐述唐人婚姻中的“天命观”;妹尾达彦《“才子”与“佳人”——九世纪中国新的男女认识的形成》、孙世荣《论唐代社会变革期的婚姻观念》对“才子佳人”婚恋模式都有所涉及,前者突出科举制下“才子”与“佳人”婚恋模式的形成;后者以男权主义为着力点展开对“才子佳人”原因分析。
然而探讨女性视角下“才子佳人”婚恋模式及原因相对较少。一方面,由于唐科举风靡,才子大多科举及第,脱颖而出,社会与政治声望的获得为唐女子婚姻生活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女性自身思维革新、文学素养提升及与本家经济关系的表现上又与才子相配,“才子佳人”婚恋模式应运而生。
“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2]择偶是婚姻的立交桥,婚姻是社会的纽带。政治上,选官制度变迁扩大唐代官员来源,给拥有真才实学的庶族子弟步入仕途的机遇;经济上,社会财富迅速集聚于多元地主手中;文化上,民族杂居,风俗圈杂糅,唐社会逐渐弥漫着一股开放潮流,女性在思维、文学素养及本家对自身的经济支持方面表现出别具一格的变革,“才子佳人”婚恋模式应运而生。以唐人笔记小说为中心,从女性视角对才学婚姻及形成原因进行探讨,以证吾论。
一、笔记小说中的“才子佳人”
“最后始以恋爱居先,生殖次之,经济再次之”[3],有唐一代,关于两性婚恋故事散见于各类唐人笔记小说当中。开放社会风气之下,唐女子开始有主动追求爱情的勇气和向往琴瑟和鸣夫妻关系的思想萌芽。笔者对唐人笔记小说中的几个实例进行简要统计分析,旨在说明女子择夫“重才”“重功名”的社会普遍心理。
以“博学多才”为特征的才子与以“才艺精湛”为标榜的佳人来形容两性的记载前代并未少见,而将两性“才子佳人”婚配模式则“实始自唐代”[5]。
由表1可得出一些简要特征:
其一,唐女子对异性“才情”要求较前代尤为突出。如:丹阳公主气愤薛万彻乃一介莽夫,太宗皇帝巧妙化解尴尬,让夫妻和好如初;步非烟不喜武公业之粗俗鄙陋,与赵象以诗传情。
其二,女性自身才学技艺毫不逊色。李虔州妻虽无绝色容貌却德才兼备,夫妻二人相敬如宾;窈娘身为婢女,被乔知之如此看重,其自身才学修养不言而喻,这与文化教育从士族子弟特权到全社会普及息息相关。

表1 笔记小说中“才子佳人”表
其三,男性多为科举出身。女性重才并非以“琴瑟和鸣”为唯一目的,更多是对未来婚姻生活的保障。唐律疏议“妇人有官品邑号”条明确提出“妇人品命既因夫、子而授”,白居易于长庆元年升至中书舍人,妻子杨氏即因夫而授。唐女子自我意识开始萌芽,选择有政治前途的男性配偶,情投意合的同时保证其生活无忧,实质上“择举子为夫”即间接选择功名与人生保障。
其四,不论是出身高贵的皇帝之女,又或是官宦之女乃至平民女子多以诗文对答传达情感。“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6]崔护郊外游览,与绛娘以诗结缘,互生情愫,不久返程投入备考中去,来年故地重游才知绛娘苦等数日竟郁郁而终,崔护以泪感化绛娘,成就良缘。文化下移表明唐代以诗赋文章为主要考查内容的科举制之盛行,女性视角下“才子佳人”婚恋模式正是其自身思维模式、文学素养及本家给予支持的产物。
二、女性视角下——思维模式特征
思维模式形成于时代所赋予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高级生理技能之一;反之,实际行为效果给予其丰富的经验累积,激发人类思维模式的方向性演变。唐代女性生活在门荫与科举彼此消长、开放风气与传统观念相互羁绊的社会实践中、沉浸于经贸多元、民族交融的盛世之中,引发激烈的思想冲击。
(一)概括性
思维模式的形成依赖于对所处社会境遇及自身相对客观的评价,从而作出符合社会实际行为的价值判断。就女性视角而言,科举之风引起全社会对诗赋文章的追崇,“门阀士族不再独占文化上的优势”[7],文化教育随之普及,“打破性别与等级”[8],成为全社会行为规范与权力,女性对社会境遇的分析及文化水平的提高,更益于对配偶进行概括性分析,“才子佳人”婚恋模式的兴起正是唐女子思维概括性的体现。
(二)间接性
不言而喻,是一种需要外界媒介去感观实体世界从而做出相对准确的价值判断。有唐一代,寒门男性通过功利考试获取功名,门阀贵族为重获政治实权也加入科举行列,士族逐渐失去对文化的把控。唐文化普及与传播具有社会属性,“由男性到女性”[8]是其表现形式之一,教育内容更强调社会经验的实际运用即女性日常生活知识的教授。受教育权的有效保障与科举制的践行,女性自然倾心才子,为婚姻幸福做最合理的选择。
(三)逻辑性与灵活性
思维模式的形成是人脑对社会诸要素比对分析及整理后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并非杂乱无章,具有严密逻辑性与开放灵活性。“才子佳人”婚恋模式便是唐社会所赋予唐人的印记。开放风气的弥漫,女性与本家关系的培养与经营,“有助于他们在夫家的地位”[9];程楚宾资助吕甄进京赶考,成就“才子佳人”,可见,唐代女性获得本家对自身的维护和对其配偶赶考的资金支持,进而通过自身对知识把控、社会认知及优势的系统分析做出灵活判断,促使才学婚姻得以在唐人观念中稳定存在。
(四)批判性
批判性思维来源于对事物的多维度考虑。进士卢储献文李翱,李翱之女偶见卢储文笔,认为“此人必为状头”,李翱“深异其语,选以为婿”[10];卢储果然在科举考试中博得头筹,娶得美娇娘,作《催妆诗》向妻表达感激之情。唐代女性择偶标准由重“门阀”到重“才学”,看中的不仅是学子的文化内涵,更为重要的是及第后所带来的荣耀与显贵,她们对美满婚姻的向往根源于对科举考生发展潜力的考量与本家对自身的经济支持。
总的来说,就女性思维模式而言,唐女子迈出社会所赋予她们的固化印象,开始学会批判性衡量自身优势及对方未来发展现实,充满自我观念的思想萌芽,是自发的变革与自我的发展;“才子佳人”思维模式的不断深化正是女性心灵、精神获得一定程度解放的体现。
三、“才子佳人”婚恋模式形成原因
(一)女性视角下——教育的光芒
一个朝代经济实力与统治者对政治局势的控制力影响其文化包容程度。唐代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转型期,经历了从士族集团依靠门荫与社会声望垄断政权到寒门庶族凭借科举进入朝堂的官制转型、从以人口为重的均田法到以土地多寡为标准的两税法的税制转型、从士族家学礼法到平民文学崛起的文化转型、从男性到女性的教育转型。正如严耕望在《唐代社会约论》中阐述:“唐代社会文化的普及可以分为社会性与地理性。”[8]笔者从女性视角出发,就文化社会性表现进行论述。
随科举大兴,唐政府为庶族子弟提供改变命运的机遇,兴起读书考取功名之风,即使带有功利性,也使教育权不再为贵族集团所特有。当贵族集团失去对文化控制力时,就意味着一直以“家学礼法”为标榜的士族文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同时给全社会提出教育普及的需求,女性教育就显得格外突出了。
首先,唐诗延绵数千年,时间之久、佳作之广,经久不衰。词章绮丽的王勃诗;文若悬河、取之不竭的杨炯诗;浪漫瑰丽的李太白文;俊拔宏丽的孙逖篇,风华绝代之唐世,最耀眼的已不仅是这些浪漫风雅的男性诗人了,“自恨罗衣,空羡榜中名”[11]的女冠诗人鱼玄机;形气既雄,诗风纤丽不失爽性的李季兰;刘媛、南楚材之妻、鲍君徽、杜羔之妻赵氏等皆才情卓然,女性智慧成为唐一代最具代表的标签。
其次,“唐代的乡里村学存在于全国各地,带有一定的普遍性”[12]。就一般官宦家庭而言,既不似皇族公主受政治因素牵涉甚多,也不如后宫妇女被身份压抑,凭借本家雄厚资金及对女教的重视,官宦女性有更宽松的受教育环境;科举之兴,私学之盛,平民女子必然受到文学风气的影响,即便在街边也或多或少听到街道传唱的文化知识。儒教不再专行,儒佛道逐渐合流,谈经布道之时难免有浅薄的文化传播,易于理解,渗入人心。女性对教育的渴求性愈演愈烈,形成“三尺小童,耻不知书”的社会风气。女性教育观演变成为“才子佳人”婚恋模式生存的文化土壤。
最后,女教内容不再以教授妇德为主。《女论语》简单明了,浅显易懂,是唐代女性普及知识与行为规范的经典读本,不再像儒教说教般对女性思维进行固化,侧重生活常识的教授,“妇女亦要读书解文字,知古今情状”[13],李华的《与外孙崔氏二孩书》则是唐女子教育解放最明了的证据。
综上所述,唐代文化系统经历“经典文本——士家礼教——平民文化”[7],成为一种传播性较强、受众颇为广泛的大众媒介,文人墨客及具有功利性的科举考试唤醒树之楼阁的思想因子,使其逐渐活跃于民间,女性读物在唐时以至“十七家,二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14],牛应贞“试令开卷,则以精熟矣,著文章百余首”[10]、张生妻“幼学诗书,甚能吟咏”[10]、表1中两性也多以诗文传情,女性自身文学素养与受教育水平大大提升,“才子佳人”婚恋模式才得以在有唐一代稳定持续地发展下去。
(二)女性视角下——本家的支持
唐女子步入婚姻生活后,并未淡化与本家的情感交流,相反,本家给予其较大经济支持,同时律法也提供一定保障。女性特权扩大化是其择偶要求提升的催化剂,促使女子对男性提出更高的社会性要求,适应唐代社会演变与发展,选择最有利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理想对象,同样作为“才子佳人”婚恋模式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人对于妇女与本家的关系还有一个看法,就是,如果妇女在婚后维持与娘家的联系,会助于他们在夫家的地位。”[10]牛肃《纪闻》中所载,张长史得知女儿在夫家受委屈,卸任归家途中责骂女婿,为女儿撑腰;《广异记》中《三卫》所载夫婿对少妇不善,新妇书信与本家求助,果求得帮助,本家成为女性强有力的支撑。与本家保持情感交流,彼此提供帮助,女性自然多一道保护自身周全及保证婚姻稳定不可或缺的屏障。
“富家女易嫁,嫁早轻其夫。贫家女难嫁,嫁晚孝于姑。”[15]窦玉应举,丈人以资相助,“衣食之给,不求予人”[16];程楚宾嫁女于吕甄,给予资财进京应举,皆科举及第,赢得政治声望与社会名望,女子得到婚姻保障的同时,协助其树立自身家庭地位。也就是说,本家对女子的财富支持直接影响着其在夫家的地位;男性入仕受到女方家族支持是出于对自家女儿的爱护,为她未来生活质量作铺垫,充满女子与本家深厚的情理联系。
“诸身丧户绝者,将营藏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17]在法律层面承认女性财产继承权,虽限户绝情况,已经很大程度承认女性对本家财产的占有份额;另外,唐律承认女方婚娶时所附嫁妆的相对独立权,且明确指出不列为男方分产范畴之内,即使夫妻同体,女方亦获得相当可观的财产保障,唐律以其特有的包容赋予女性一定实践空间与活动场所。由此可见,本家与女性间的情感交流及经济支持及法律所赋予的一定保障是“才子佳人”婚恋模式得以形成的经济基础。
总之,古往今来,两性婚配皆为世人所重,配偶的选择是缔结婚姻的必经之路。其一,唐女子生活在门荫与科举彼此消长、开放风气与传统观念羁绊的社会实践中,引发激烈思维冲击;其二,女性受开放唐风影响,接受更广泛的受教育机会,文学素养的提高促使其更乐于选择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我悦子容艳,子倾我文章”[1],志趣相投;其三,唐女子财产继承的法律认同及与本家情理联系提升其婚姻生活地位,体现在择偶观念上,自然带有理智客观意味,唐代女性不再被束缚于宗教礼法桎梏中,开始寻找自我价值的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应时代演变,成为敢于冲破思想牢笼的时代女性。笔者认为女性视角下“才子佳人”婚恋模式得以在唐生根发芽,与其自身思维革新、文学素养提升及与本家经济和情理联系息息相关,夫妻琴瑟和鸣,“才子佳人”婚恋模式应运而生。
[1][清]曹寅,彭定求,等编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0:1881.
[2]郭彧译注.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06:391-392.
[3]陈顾远.中国婚姻史稿.上海:上海书店,1984:6.
[4]丁如明,李宗为,李学颖,等点校.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蒋防.太平广记:卷三四四《鬼》[M].北京:中华书局,1961:2726.
[6]孟棨.本事诗情感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4:69.
[7]张国刚.论“唐宋变革”的时代特征[J].江汉论坛,2006(3):89-93.
[8]严耕望.唐代文化约论[A].唐代研究论集(第一辑)[C].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21.
[9]陈弱水.隐蔽的光景——唐代的腐女文化与家庭生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5.
[10]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1346,2135,2250.
[11][元]辛文房著.舒宝璋校注.唐才子传[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346.
[12]万军杰.试论唐代的乡里村学[J].史学月刊,2003(5):35.
[13][清]董浩编.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192.
[14][宋]欧阳修,李祁撰[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86.
[15][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笺校(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81.
[16]王定保.唐摭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721-2729.
[17]仁井田陞原著.王占通,郭延德,等编译.唐令拾遗[M].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770.
Marriage Patterns of Caizi Jiaren(Gifted Scholars and Fair Ladi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ng Women
LIU La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Liaoning 116000)
Marriage has been considered of immense importance since time immemorial,with spousal selection being a necessary avenue.In most cases,women in ancient China chose mates in line with their own socio-economic status.From early history up until the Tang dynasty,the marriage patterns of caizi jiaren(gifted scholars and fair ladies) gradually grew in popularity,with the exception of aristocratic matching during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First,women of the Tang lived during a time in which nepotism among the scholar gentry,and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we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flux,resulting in intense ideological conflicts.Second,women,influenced as they were by the liberal atmosphere of the Tang period,enjoyed wider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and their improved state of literary attainment meant they were all the more willing to choose life partners with whom they shared common values.The gentleman's appreciation of the lady's beauty,along with the lady's admiration of the gentleman's literary talent,came to represent ideals of marital harmony.Third,legal recognition of the property inheritance of Tang dynasty women,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clan,boosted their position as regards marriage and family life.
Tang dynasty;women;views on spousal selection;love and marriage;gifted scholars and fair ladies
K242;K203
A
1671-9743(2017)07-0101-04
2017-05-18
刘 兰,1993年生,女,山西长治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代社会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