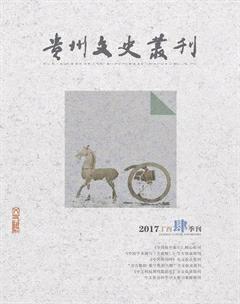何以“外民国”
张妍
摘 要:《清史稿》是民初官方主持纂修的史书,刊印不久后却因“内清室而外民国”的反动立场而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究其原因,首先,清史馆在归属问题上的含糊不清使修史宗旨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在史书纂修过程中,北洋政府对史馆成员的政治立场缺少足够的干预和控制;第三,史书纂修者在书稿中表露出了或深或浅的遗民心态。最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与北洋政府在政治理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清史稿》表现出的“表扬清室”的态度和“遗民”口吻都被视为“触犯民国”的罪证。《清史稿》从成书到被禁的历程,显示了政府与修史机构、修史者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民初复杂的政治生态。
关键词:《清史稿》 清史馆 民国 清室 遗民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4-64-71
1929年12月,历时十四载1成书的《清史稿》被南京国民政府下令禁止发售。在负责审查史稿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的十九项错误2中,前七项“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都涉及政治立场问题,也即《清史稿》被禁的最主要原因,“内清室而外民国”3。书稿被禁后,虽然有学者从史料价值等角度为其辩护,但《清史稿》因违反史例、曲笔维护前朝而饱受诟病却是不争的史实。一直以来,人们往往将《清史稿》持反动立场的原因归结于清史馆中修史诸人,认为这些前清旧人借修史以回报故主,“睠睠故君之情,时流露于字里行间”4;甚至有激烈者批判其“用民国名义,耗民国金钱,而处处表现反对民国之精神”5。然而,仅仅从修史者的角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这样的矛盾:为何最初由民国政府设立的官方修史机构,却修出了一部诋毁革命、触犯民国的史书?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进一步从清史馆的性质、北洋政府与清史馆的关系、修史者的心态、民初的政局变化甚至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寻找原因。6
一、民国与清室之间
易代修史是我国的一项优良传统,后继的王朝都要为前一任政权纂修历史。官方修史的制度保障使得我国的史学绵长而深厚。至于重视修史的目的,一般有以下几种:一是借鉴前朝经验,二是证明新王朝的合法地位,三是笼络士人、点缀升平,四是垄断修史、控制褒贬大权1。无论出于以上何种目的,官方修史总归是为新朝(政权)服务的。然而,清史馆设置的初衷却颇有让人意外之处。
民國三年,北京政府国务院呈请大总统开设清史馆,部分呈文如下:
大清开国以来,文物粲然,治具咸饬。远则金川请吏,青海敛兵,拓土开疆,历史之光荣犹在;近则重译通商,诏书变政,鼎新革故,贞元之继续攸开。洎乎末叶,孝定景皇后,尤能洞观世势,俯察舆情,宣布共和,与民更始。用能成德美文明之治,洵足追唐虞揖让之风。我中华民国,追维让德,于大清皇室,特颁优待条文,崇德报功,无微不至。惟是先朝记载,尚付阙如,后世追思,无从观感。及兹典籍具在,文献未湮,尤宜广招耆儒,宏开史馆,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2
由此可见,北京政府设置清史馆的初衷是为报效大清皇室“让德”之功,修史书以供“后世追思”。尽管在名义上,民国政府由满清皇室“禅让”而来,但为表扬前朝而开馆修史,的确是千古未有之例。现有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呈文上的各种名目和说辞,只不过是袁世凯网罗前清旧人、文饰政治的手段罢了。开设清史馆与同时期的礼制馆、国学馆等名誉机构一样,都是为了实现袁世凯的帝制野心。但这种表述无论是真心实意还是表面文章,都为日后清史馆的营运和清史的纂修埋下矛盾。清史馆究竟是民国的史馆,还是清室的史馆?清史为民国而修,还是为清廷而修?
对于这个问题,不仅后来者纠结不已,北洋政府自身也没有分辨清楚。民初历届的执政者似乎都没有认真地将清史馆当作民国的文化机构来经营。他们往往根据自身与逊清皇室的关系以及清室在民国的地位来对待清史馆。袁世凯当政时期,逊清皇室享有较高的优待,清史馆的地位也比较尊崇。虽然政府的财政预算缩减,但“清史馆经费”一项并无减少。“清史初开馆,经费尚充,故自三年至五年春,纂稿尚多。”3袁世凯死后,虽然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但政府权力主要掌握在段祺瑞手中。段祺瑞对清室并无好感,清史馆经费在其任期内减去一半,由原先的每月两万多元减到一万多元。张勋复辟事件后,清史馆经费更是减之又减,以至修史事业几乎陷于停顿。1924年北京政变,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宫并修改了《清室优待条件》,清室与民国政府的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清史馆存在的合法性也遭到极大的质疑。1927年,在与清室关系密切的北京政府大元帅张作霖的支持下,清史馆所纂清史才得以基本完稿并最终付印。
清史馆在不同时局和当政者下所受的不同待遇,反映了清史馆在从属关系上的含糊不清。民国政府开设清史馆并提供经费,但又默认它与清室的密切关系。更何况逊清皇室对于纂修清史,也表现出了认同和肯定的态度。
1914年6月初,为取得清室对修史事业的支持,赵尔巽以前朝旧臣的身份进紫禁城拜见溥仪。天津《大公报》对此事有所记载:“清史馆总裁赵次珊君,昨日曾协同世伯轩太保入隆宗门觐见清帝,当蒙清帝与瑾皇太妃召见,由赵君将此次修订清史宗旨奏明,极蒙瑾皇太妃温谕嘉奖。赵君并请派陆润庠、袁励准等襄赞一切。”4清室的态度,无疑是对赵尔巽的肯定和鼓励。清室不仅在用人问题上大力支持,还将位于东华门的原清代史馆的房屋借出,用作清史馆的新馆舍;在利用档案资料方面,也尽可能提供方便。对此,赵尔巽虔诚地表示:“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51928年,《清史稿》刊印完成,此时已避居天津的溥仪还不忘嘉奖负责此事的袁金铠,赏赐其匾额一方。6
纂修史书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史书所持的观点和立场自然受到官方态度的影响。然而,北洋政府与逊清皇室之间的暧昧关系却使清史馆的归属游离在二者之间,甚至更向清室靠拢。如此一来,史馆修史的宗旨和立场就具有不确定性和选择性:究竟是以清朝为本位,还是以民国为本位?当撰述内容不涉及二者交集时大可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公平持论”、“事事纪实”,即便对清代的文治武功大加颂扬也不会招来太大的非议;然而,一旦二者发生冲突(事实上也确实存在冲突),叙述者的立场必定要以一方为内,以另一方为外。选择站在清朝的立场看问题,也便站在了民国的对立面。对于这个严肃的问题,官方没有明确的态度,史馆内部也不曾进行统一的讨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关乎国家意识形态的官修清史的政治立场问题,最终却取决于清史编纂者的个人抉择。这个问题不仅在清史馆开馆时没有受到注意,在此后清史纂修的十四年中,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endprint
二、官修正史向私人撰述转化
《清史稿》被禁时,时人批判《清史稿》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是“以民国的名义修史,却处处表现反对民国之精神”。姑且不论此种论断是否过于夸张,它至少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时人心中,《清史稿》是一部官修正史。正因为把《清史稿》当作官方纂修的史书,才会对它的政治立场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倘若只是一部无关紧要的私家著述,恐怕也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官修正史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官方控制史馆并掌握史书的褒贬大权。比如《明史》的作者中虽然有诸多明朝遗臣,但未见其修出的成果处处表现反对清朝之精神。其中,控制史馆人员的政治立场是关键。《清史稿》刊印后因政治立场问题引发争议并饱受诟病,说明史书在编纂过程中没有得到官方应有的重视和恰当的干预。那么,这种状况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呢?
(一)无关大局的清史馆
回顾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特别是史馆修史在唐代成为定制之后,统治者对前朝史书的编纂往往非常重视。为保证史书的完成,他们不惜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比如清代纂修《明史》时,清代前中期诸位皇帝都曾累下诏令,表示关切。统治者之所以如此重视,主要是想通过史书的褒贬来宣扬新朝的合法性,确立本朝的正统地位。这与中国古代王朝的更迭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后起的王朝取代旧朝,往往经历了频繁的战争与残酷的杀戮。如若不能为其行为赋予合法的意义,名不正而言不顺的统治将难以为继。因此,官修正史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中华民国取代清朝的方式却与以往有所不同。从具体史实来看,清王朝垮台很大程度上是由革命党人领导的武昌起义引发的连锁反应造成的。但从法理程序来看,由于经历了南北和谈以及清帝颁布逊位诏书,中华民国又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的。与此同时,逊清皇室不仅免除了被灭族的命运,还被允许继续居住在紫禁城,享受民国优待。在这种历史情形下,为新朝(政权)正名的需要并不如以往那般强烈,更何况掌握新政权的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他们曾经隶属于清王朝,在和平承接政权的过程中,与先朝并没有产生激烈的冲突与对立。《清帝逊位诏书》中“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一语,就足以为袁氏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因此,民初开设清史馆,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来讲,无关大局。既然没有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也就无需过多的关注与重视。这就注定了清史馆在袁世凯死后被政府冷落的命运。
前面已经提到,开设清史馆很大程度上是袁世凯为了网罗前清旧人、实现帝制的一己之意。清史馆开馆时人员混杂,虽不乏真正有学问的宏学硕儒,确实也吸引了一批前清遗老在此聚集。袁世凯死后,宝熙、郭曾炘、顾瑗、袁励准、商衍瀛等与清室关系密切的遗老纷纷离馆。由于不再承担“招贤养士”的功能,清史馆转变为单纯的修史机构,民国政府新的领导者对其重视程度也大大降低,甚至传出了裁撤清史馆、将清史馆与国史馆合并以及赵尔巽辞去馆长职务的消息。虽然凭借赵尔巽与黎元洪的僚属旧情,清史馆得以勉强保留,但此后政府对清史馆的支持大不如前,不论是在经费拨划方面还是在资料搜集方面。
“项城殁后,馆中经费骤减十万,其后遽减月至三四千。此三四千者,犹不时至。或参以国库券、公债票之类,损折难计,拮据日形。1”在经费异常拮据、馆务几至停顿的情况下,在1923年新上任的财政部长王克敏仍然决定取消盐余项下拨给清史馆的经费。他给出的理由是,“(清史馆)普通机关非军、警、刑可比,不應分润盐余。”1此话一语道破问题的关键。因为不重要,所以不重视。更何况民初政局一片混乱,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接连不断。政府忙于各项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外交事务,自顾尚不暇,根本没有精力关注一个小小的修史机构的命运。至于清史馆究竟聘请哪些人进馆修史,馆员的政治立场是“表扬清室”,还是“反对民国”,都不为政府所关心。在史馆运营的十四年中,政府对史书的编纂几乎没有任何干涉。清史馆一直处于“消息阒寂、无人闻问”的状态,思想、立场、史例等都可以自行决定。民国著名报人陈训慈曾呼吁时人对清史之纂修多加注意,“此事实甚重大,学者要不当任若干遗老闭门为此而不加论列”。2
直到1927年《清史稿》基本完稿,在赵尔巽的请求下,政府才委托代馆长柯劭忞和“东三省才子”袁金铠负责刊印事宜。但袁金铠由于还忙于其他政治事务,不能常到史馆,便请来朋友金梁帮忙。然而,由于柯劭忞与袁金铠意见不合,不阅史稿,《清史稿》在无人总览、无人涉目的情况便交予金梁付印,“金几执全权,随校随勘”。3此外,令修史诸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靠朋友介绍在史馆中谋得校对职位的遗老金梁,却按己意削删史稿,并私自加入康有为、张勋的传记,使《清史稿》在日后招致更多的批判和责骂。对此,北洋政府恐怕要负失于监察之责。
(二)苦心孤诣的赵尔巽
除清史馆地位的演变以及民初政局变化的影响外,清史馆机构设置的独立性也是造成官方冷落纂修清史事业的重要因素。查阅相关史料可发现,时人对清史馆的认知有许多种,包括“特别机关”、“临时机构”、“闲散机构”等;研究者们也使用“半官方”、“官助私修”等词汇为清史馆定性。这些表述都反映了一个事实,清史馆虽然最初由政府开设,但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官方机构,它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在清史馆筹备时期,国务院就清史馆官制问题拟定了一份官制草案。官制草案对于清史馆与政府机构的关系是如此规定的:“总裁一人掌全馆事务,直隶于大总统”4。按照此官制的规定,总裁(后改为馆长)直隶于大总统,因此清史馆是处于政府的职官体系之中的。但是,除大总统外,清史馆与民国其他行政机关没有任何联系。如果总统不加干预,清史馆将成为由馆长掌管全馆事务的独立机构。赵尔巽在出山时对清史馆官制的修订,则将这种可能性大大提高。
赵尔巽首先将总统手中的人事权收归己有。“赵氏就职后,即要求政府对于清史馆之用人及编纂问题均不得干涉,大总统亦一一允其所请。”5人事聘用是政府控制史馆的重要手段。史书由修史者编纂,掌握修史者的任用也就能干预史书在政治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政府既然不能干涉清史馆的用人问题,也就极大地失去了对史书编纂的掌控。史馆修史人才的聘用最初有三种方式:政府举荐、馆长延聘和设名誉职,但赵尔巽任馆长之后,馆中编纂人员的聘用由举荐而变为多由馆长负责。6这也就意味着,清史馆逐渐脱离政府控制,向以赵尔巽为首的独立修史机构转化。纂修清史则似乎演变为赵尔巽和一批修史者的个人事业。endprint
当大多数人在史馆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星散而去时,少数“赞成清史必成之人”选择留在馆中,继续编纂工作,使馆务没有废止。“同人黾勉从事,获共谅苦衷,各尽义务,竭蹶之余,大致就绪。”7在没有经费支持的情况下,有人仍然选择义务修史,可见纂修清史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一份从政府获取薪俸的工作,而且是一项值得付出心血的个人事业。馆长赵尔巽则更是为了清史馆事务“百计张罗”,“竭力呼号”。在“经费万难、干戈扰攘之际”,他向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地方军阀募集捐款,还自行垫付二万余元以接续清史修纂。当史稿付印经费无从着落时,赵尔巽再次书函张作霖,以个人情谊恳请政府资助。“现定筹印史稿,正在积极进行,不日可望出书,仍乞俯怜遗业垂完,于每月部拨馆中额支,万难再减。及史稿印费,尚缺一万一千元外,再行赐予筹助一二万元,俾七级高塔,得告合尖之功,出自任施,九叩以请。”1对于已然垂暮病笃的赵尔巽而言,编纂清史的确是他后半生苦心经营的事业,是他始终无法摆脱的牵挂。1927年,《清史稿》尚未全部完成便仓促付印,时局动荡固然是迫切的原因,赵尔巽渴望在生前完成遗愿也是重要的因素。
对于清史馆究竟是民国官方机构还是普通修史机构的判定,直接关系着对《清史稿》政治立场的评价。如果清史馆并非官方机构,那么,《清史稿》反映的就只是一部分人的思想立场,并不应受到过多的批判和指责。如对查禁史稿非常不满的金梁正是此种态度:“清史馆后期因经费支绌,都由东三省张作霖和吴佩孚、张宗昌等支拨,是属个人的垫支,绝没有向国库支取分毫。因之一切工作人员的思想立场,都和中华民国没有什么关系。”2金梁的态度固然偏激,但却明确地指出了史馆的独立性。正是由于这种独立性的存在,馆中修史人员的思想立场不受政府控制,以致名义上的官方修史机构修出了一部具有“反对民国”嫌疑的史书。那么,在清史馆中纂修清史的究竟是哪些人,他们的思想立场又如何呢?
三、遗民心态的显露
关于清史馆中修史人员的选拔标准,袁世凯在《设置清史馆令》中使用“通儒”一词,以录取“优于词章”、“熟悉掌故”者。3然而,由于符合标准且进入史馆的人多为前清官员或文人学者,清史馆往往被视为“遗老”聚集之地,《清史稿》也被看作修史诸人“忠清”思想的产物。时人对此多有注意并已有警觉,“是时遗老,有主张修史者,有以为不当修者,卒至应聘者多。”4掌权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对此更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如傅斯年在中央研究所关于处置清史稿的书面意见中指责史稿编纂之人“既食民国之禄,又以遗民自居之丑态,普布于世”。5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则以更加激烈的口吻抨击馆中诸人特别是馆长赵尔巽,“承袁世凯及北洋军阀之余荫,修史者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已开修史之特例,且以遗老中最为不学无术之赵尔巽为之馆长。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6
然而,在近来的研究中,学界对“遗老”这一称谓多有争论。许多学者认为,“遗老”这一概念含有特定的政治含义,并不适合用来笼统地描述清史馆中修史群体。如李思清在《清史馆文人群体研究》7中使用“光宣文人”的提法,以涵括“遗老”、“遗少”以外的更多传统文人;伏传伟则在《进入民国:清史馆的机构与人事》中提倡使用“前清旧人”的说法,并将清史馆中诸人按照与前朝关系亲疏程度划分为四类:一是忠于清室者,進行复辟活动或紧随逊清皇室,基本不参与民国事务,此类可称为遗老;二是与清室和民国均保持一定的关系者,即在二者之间求生存,此类介于遗老与非遗老之间;三是在民国政府为官,对清室仍有感情者,此类不可称为遗老;四是与清室并无往来或牵连,具有传统思想,不在民国为官者,此类以文人为主,也有部分前清官员,可称文化遗民。8清史馆人事变动频繁,参与三个阶段的清史编纂并最终结束《清史稿》成书的只有十四人。他们分别是总纂:柯劭忞、王树枏、吴廷燮、夏孙桐;纂修:金兆蕃、章钰、金兆丰;协修:俞陛云、吴怀清、张书云、李哲明、戴锡章、奭良、朱师辙。根据上述定义,这十四人中基本没有可以称为“遗老”的人。
笔者并不否认,对概念的精确辨析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甚至是影响结论判定的关键因素。然而,我们在对一个群体进行精确划分的同时,也容易忽略掉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一些共性。综观民国时期与清史馆或《清史稿》相关的史料,其中“遗老”的范围似乎并没有局限于“改朝换代后仍然效忠前朝的老人或旧臣”。“遗老”、“遗民”、“清季遗臣”、“清代旧望”等都曾用来指代清史馆中修史群体,泛指对清室仍然怀有故主之情的前清官员或文人,并不强调是否在民国为官。而且,按照政治行为划分的标准不一定适合描述他们的心理特征。清史编纂人员或有参与民国文化事务甚或出任民国官员者1,但现实的行动不一定与他们的政治认同和思想立场完全一致。更何况鉴于民国政府和清室之间的特殊关系,“出仕民国”与“报效清室”似乎也没有很大的矛盾,入馆修史本来就是调和二者的行为。强调清史编纂者并非“遗老”容易忽视其从清代走向民国的普遍心理特征。
如被排除出“遗老”行列的赵尔巽,在活跃于民国政界与文化界的同时,对清室依然惓惓情深。他不仅自诩为报答先朝而出山,在动荡的时局中也尽己所能保护皇室周全。当溥仪蛰居天津时,他还以事君之礼亲自拜见,故君之情可见一斑。2此外,台湾学者林志宏对于“清遗民”特别是清史馆诸人的研究,也验证了此种心理的普遍性。“对那些支持修史的遗民来说,无疑正是报效清室的绝佳机会,不管如何都应义无反顾,恪守遗臣之责。柯劭忞便说,身为儒臣,国亡后无所自尽,‘修故史即以恩故国,其职也。”3鉴于在今日的学术研究中,“遗老”一词往往习惯性地带有特定的政治含义,笔者认为,在描述清史馆同人的心态时,使用“遗民”一词似乎更加客观中立。
当然,即便史馆同人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遗民情怀,这种感情也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依个人情况有浓有薄,或深或浅。上文提到,袁世凯死后,遗民心态最重的一批人如宝熙、顾瑗等已经离开史馆;修史三阶段中人事变动频繁,坚持到最后的只剩下柯劭忞、王树枏、夏孙桐等十余人。因此,能够真正参与撰写《清史稿》并影响其政治立场的主要是馆中的一少部分人。《清史稿》中争议最大的篇章是《宣统本纪》以及光、宣两朝的列传。撰写这些部分书稿的作者是怎样的心态呢?endprint
以《宣统本纪》为例,该部分的初稿由瑞洵和奭良主笔,复辑由金梁完成,最后由柯劭忞统稿、删正。在《宣统本纪》初稿中涉及辛亥革命的部分,作者即表现出了一定的敌视情绪。他们将革命党人的政治活动指为“谋乱”,并使用了“伏诛”、“叛”、“贼”等字样。虽然稿本中的很多诸如此类的字样在正式刊本中已被删除或改动,如稿本中先后出现16次的“叛”字都被改作“变”字4,但还是有所遗漏和不彻底的地方。这些呈现在最终版本中的“谬误”字样,就被视作《清史稿》敌视民国的证据。除了对辛亥革命的记载有欠妥之处外,后期加入的金梁未经馆内讨论、自作主张添加张勋、康有为等的传记,也是使《清史稿》招致骂名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瑞洵、奭良、金梁是何许人也,他们为何如此维护清室呢?比较三人的经历可以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满洲人。他们的故国之情远远超过了清史馆中的其他成员。奭良曾建议《清史稿》之史论用“史臣曰”,因为在他看来,《清史稿》是大清之臣为大清所修之史。也就是说,奭良的政治立場是以清朝为本位,而不是以民国为本位的。他的这种立场直接表现在了他所参与撰写的书稿之中。相比而言,金梁是更为典型的遗老,他参与宣统复辟的行为5加深了人们对于清史馆是“清遗老”聚集地的印象。除此满洲三君外,其他史馆成员的遗民情怀在书稿中也偶有表露。
因此,将《清史稿》“反动立场”的原因归结于清遗民“眷恋前朝”和“回护故主”是有一定道理的。即便是反对查禁《清史稿》的著名学者,也不否认这种因素的存在。孟森在《清史馆应否禁锢之商榷》一文中指出,“在馆秉笔诸人,当时采清代旧望,来者多以元遗山自况,用修史以报故君,故疑其内清而外民国,此诚有之。”容庚在《清史稿解禁议》中也表达了与孟森类似的观点,“修史者多属胜朝遗老,不忘故主,间或谓之表扬,是诚有之。”他们与南京国民政府争论的焦点不在于修史者是否“表扬清室”,而是在于“表扬清室”与“触犯民国”是否必然一致。这一点,是判定《清史稿》是否反动的关键所在。
四、“内清室”与“外民国”
孟森认为,“意主表扬清室,与敢于触犯民国,并非一事”,是否查禁书稿,“当据书中内容而言,不当以揣测之故,湮没甚富之史料”。容庚也认为,《清史稿》确有“失实”之处,但并没有达到政府所谓的“反革命”、“藐视先烈”的程度,不应过于“苛察”。容庚还建议政府如果对清史稿中若干字句或篇章不能容忍,可以抽毁、涂改,但不要查禁全书。学者伏传伟也赞同这种观点。他举出了更多的证据,“清史馆中纂修诸人在进行清史的编纂时,对于民国政府及其掌权者是取趋炎附势态度的,不当作传者亦作传,原因即是其后代子孙为民国高官。”1据此,他认为,当初南京国民政府查禁《清史稿》,认为其“内清室而外民国”于情理不通,与事实不合。相比较而言,孟森与容庚的着眼点在《清史稿》,更侧重从学术上进行辩护;伏传伟则从人事出发,用纂修者的态度来反驳“外民国”的指责。
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如,何烈认为,民国与清处于互不相容的敌对地位,偏袒清朝,必定触犯民国。“民国与满清,非仅当日处于政治、军事之敌对地位,即在思想、制度与立国精神方面,亦互不相容。执笔为两敌对团体修史,回护一方,则必贬损另一方,迨属难以避免。即今《清史稿》既曲袒满清,其触犯民国及属极为自然之事。”2
对于“内清室”与“外民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会出现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根源在于他们对清室与民国关系的认识存在差异。清室与民国的关系十分复杂,就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事实而言,二者是对立冲突的关系;就清室委托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的“禅让”名义而言,二者又是和平继承的关系。事实上,民国初期的政局,可以分为南北两派。北派属于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以至张作霖相继主持政权的北洋集团;南派属于继承了孙中山革命传统的国民党。二者虽然都称中华民国,但在意识形态方面,北派强调清室的逊让之德,南派则对清政权深恶痛绝。
“内清室”不一定“外民国”的观点正是看到了北派修史者对清室与民国的双重认同。清史编纂者在“表扬清室”的同时,也试图“讨好民国”,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如《清史稿·宣统本纪》对革命党人使用“谋乱”、“伏诛”等字样,但在武昌起义后改称“革命军”或“民军”3;《清史稿》不仅为民国高官的先人立传,还特意为革命者们编写传记。当然,某些冲突的史实是无法调和的,如刺杀恩铭、武昌起义等。站在清室的立场,必然也就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这一点,正是被南派官员和学者猛烈攻击的地方。在他们的立场上,民国与清朝根本对立,“内清室”必然“外民国”,不仅触犯民国的地方不能容忍,所有表扬清室的内容也是与民国为敌,必须加以批判。在南派诸人的相关文章中,这种批判和斥责随处可见,甚至只要是与北方政权有关的,都加以攻击。如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委员吴敬恒在致胡汉民、古应芬的函件中提到,“当时袁氏强欲使赵尔巽等承乏尸禄,果修成谬史”,“赵尔巽时代,因回护其故君,至不恤使材料不具,未敢动清宫毫末。盖因谨敬尊藏之圣绩,未敢令嗣皇帝擅发之故。此等一味尽其遗老天分,真视修史为儿戏”4。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在呈交行政院的文书中,更是明确指出《清史稿》“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等十九条罪状,请求将其查禁。可以说,对《清史稿》的学术评价,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对其政治评价的影响。
有研究指出,故宫博物院当初强烈要求查禁《清史稿》的直接原因是为完成《清代通鉴长编》争取时间。但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同意查禁书稿并以正式的文件下令执行,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的控制应该是最主要的因素。“清朝”本位与“民国”本位的争论,关系到话语权的控制与历史记忆的争夺。因此,在刚刚执政时期,无论社会舆论如何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无动于衷;但当政权稳固之后,政府却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将《清史稿》解禁。1有学者感叹,“藉令修史者,与此等处不用‘谋叛、‘伏诛等字样,而易以民国为内之辞,则此书亦不致重遭查禁,而大流行于南北各省矣。”2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清史稿》被查禁,是“南北互纽、内外相倾”3的结果。endprint
五、结论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清史稿》最初的纂修,也意在接续前二十四史,为官修正史的传统画上一个句号。然而,清史馆在设馆时过度浓厚的政治目的使它在修史宗旨上出现困惑。究竟是“内清室而外民国”还是“内民国而外清室”?按照史例,官修正史以本朝为内,以前朝为外。但鉴于逊清皇室与民国政府的特殊关系,以及受到纷乱政局的影响,袁世凯之后的北洋政府并没有给予清史馆过多的关注。这就使史稿编纂者在选择政治立场时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在馆长赵尔巽以及一批具有“遗民”情怀的史馆同人的苦心经营下,《清史稿》最终得以刊印。然而,继承了革命传统且刚刚掌握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却不能容忍《清史稿》“表扬清室”、“触犯民国”的态度,以“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等罪名将其查禁。
站在学术的立场,我们或许能够理解《清史稿》成书的特殊历史环境,但既然以官修正史的形式开始,它就始终无法撇开国家意识形态的束缚。《清史稿》被禁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国家对于史馆的控制,过紧或过松都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究竟如何处理国家与修史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在史学独立和意识形态之间求得最佳平衡。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对于正在进行的国家清史工程或许有一定的助益。
Why Draft History of Qing is Hostile to the Guo Ming Dangs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Yan
Abstract:Draft History of Qing was compiled by the official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Guoming Dangs Republic of China. However, this book was banned by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soon after published because of its hostile attitude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were four reasons for this result. First, The attribution of the Qing Historiographers Office misleads the purpose of compiling history. Second, in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history, the Northern Government did not intervene and control over the political stance of members of the office. Third, some historians in the office showed mentality of the survivors in the manuscripts to a different degree. Finally, some words and statements that praised Qing Dynasty were regarded as evidences of attacking the Guo Ming Dangs Republic of China, due to the huge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concept between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Northern government. The fate of Draft History of Qing, indicate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historians and history institutions, it also showed the complexity of political ecology.
Key words:Draft History of Qing;Qing Historiographers Office;The Republic of China;Qing Royalty;Survivors
責任编辑:林建曾
1清史馆于1914年开馆,《清史稿》于1927年大体完成。
2 《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行政院文》,许师慎编:《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第229页。
3 孟森:《<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年第3卷第4期。
4 金毓黻:《读<清史稿>札记》,《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下册),第672页。
5 哀灵:《读<清史稿>回忆录补录书后》,《逸经》1936年9月第13期。
6 目前,学界在《清史稿》、清史馆、清史馆文人群体的研究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这三方面的研究各有侧重,如《清史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例版本、内容考证、缺点不足等方面;清史馆的研究则突出机构的沿革与人事的变迁;清史馆文人群体的研究更关注人物的处境与心态。对于《清史稿》的政治立场问题,此前的研究或有涉及,但不够全面与立体。
1 王记录:《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书评》,《殷都学刊》2007年第2期。
2 《国务院为设请清史馆事致大总统袁世凯呈文》,王国彬辑:《1914年设立清史馆的几件史料》,《历史档案》2003年第4期。
3 朱师辙:《清史述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57页。endprint
4《赵次珊入觐清帝》,(天津)《大公报》,1914年6月26日。
5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0页。
6 袁金铠:《佣庐日记语存》卷五,1941年6月铅印本,第6页。
1 奭良:《清史馆馆长赵公行状》,《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下册),第1372-1373页。
1 《赵尔巽为清史馆挣盐余》,《盛京时报》,1923年12月9日。
2 陈训慈:《清史感言》,《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下册),第516页。
3 《王钟翰记张尔田讲<清史稿>纂修之经过》,《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192页。
4《清史馆官制》,《申报》,1914年2月9日。
5 《清史馆消息三则》,《时报》,1914年7月8日。
6 伏传伟:《进入民国——清史馆的机构与人事》,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36页。
7 赵尔巽:《<清史稿>发刊缀言》,《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185页。
1 《赵尔巽致张作霖书》,《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187页。
2 陆丹林:《<清史稿>的謬误》,《永安月刊》,1947年第92期。
3《大总统袁世凯设置清史馆令》,王国彬辑:《1914年设立清史馆的几件史料》。
4 《王钟翰记张尔田讲<清史稿>纂修之经过》,《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191页。
5 《教育部呈行政院:转陈中央研究所书面意见》,《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47页。
6 《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行政院文》,《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28页。
7 李思清:《清史馆文人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8 伏传伟:《进入民国:清史馆的机构与人事》,第54页。
1 如吴廷燮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十余载;王树枏做过国史编纂处编纂、参政院参政;罗惇屡任总统府、国务院秘书;王式通历任司法次长、代理总长、政事堂机要局长、国务院秘书长、全国水利局副总裁等多项要职;金兆蕃担任财政部佥事、会计司司长。
2 奭良:《清史馆馆长赵公行状》,《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下册),第1373页。
3 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24-125页。
4 李思清:《清史馆文人群体研究》,第83页。
5 1925年7月31日,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养心殿时,发现民国十三年春夏间清室密谋复辟文件,内有内务府大臣金梁以及康有为等的奏折多件。
1 伏传伟:《进入民国——清史馆的机构与人事》,第1页。
2 何烈:《六十年来<清史稿>与清史》,《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下册),第914页。
3 金毓黻:《读<清史稿>札记》,《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下册),第672页。
4《中央委员吴敬恒致胡汉民古应芬函》,《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34-235页。
1 “在该史稿未修正以前,原稿似亦不妨仍准国内书店印行,惟须责令附印吴氏之检校述略或检正表,以资纠正。或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纂述序言一篇,责令印行清史稿书商,将序言刊诸卷首,俾读者对于该史稿撰著人之政治僻见及莠言,预先明瞭,免滋淆惑。”摘自《教育部呈行政院:转陈中央研究所书面意见》,《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第246页。
2 金毓黻:《读<清史稿>札记》,《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下册),第672页。
3 尹炎武:《尹跋》,朱师辙:《清史述闻》,第1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