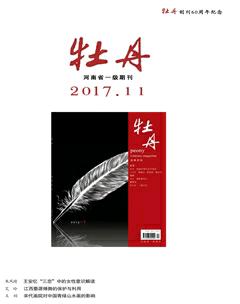多变的主题,不变的诗心
夏欢
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也是一位优秀的抒情诗人。她的诗歌成就被《剑桥文学史》评价为“站在了伟大的边缘”,而马修·阿诺德更大加赞赏,称其为拜伦之后无人可与之媲美的诗人。本文采用细读的方法,分析艾米莉诗歌荒原、自由、爱情等主题,探索艾米莉诗歌的独特之处及其心路历程。
十九世纪的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因一部荡气回肠的小说《呼啸山庄》饮誉文坛,而她的才华远不止于此,终其一生,她还创作了近两百首诗。在诗的领域,艾米莉可谓将想象和激情挥洒到淋漓尽致:受湖畔诗人的影响,她从大自然中获取创作灵感,抒发内心的复杂情感;哥特传统赋予其浪漫情怀,使她在虚构的王国里尽情表达对生活、人生的体验和感悟。艾米莉的诗歌主题丰富多样,既有对荒原的热爱,也有对自由的追寻;既有对爱情的忧思,也有生命的思考。多变的主题始终包裹着一颗不变的诗心,那就是对世间万物无法抑制的热情和冲动。生活带给艾米莉的多是苦难和孤寂,这反倒磨砺出她坚韧、倔强的品质,当她用诗人的眼光去观察这个世界时,“最幽暗的石楠丛会开放出比玫瑰还要娇艳的花;铅灰色的山坡上一处黑沉沉的溪谷,也会变成人间乐园。”
一、荒原
艾米莉从小生活在英国北部远离尘嚣的哈沃斯草原,一望无垠的荒原沼泽、连绵起伏的旷野山峦既是伴她成长的乐园,也是她笔下讴歌赞美的对象。她擅长用速写的方式,寥寥几笔便勾勒出自然的美景:
“清冷湛蓝的黎明
高高伸展出苍穹;
清冷湛蓝的沃纳湖水
映出冬日的碧空。
月亮已落,启明星闪烁
一颗恬静银白的星。”
这首诗中,诗人选取清新平淡的色调描绘出冬夜应有的清冷平静,启明星点亮了整首诗的意境,它倒映在水中让湖水与天空交融,尽管诗人也只是客观地再现身边常见的景物,却显得格外素朴,充满美感。草原的气候阴晴不定,诗人笔下的暴风雨“时而呼啸如雷,时而乐音轻婉/乌云层层叠叠奔涌翻卷,闪电耀亮划破深沉的黑暗/来去迅捷得只在一瞬”。诗句中没有繁复的修饰大加渲染,也不精雕细琢,而是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用简练的语言,两三笔就勾勒出暴风雨来临时的情景。艾米莉这种写景的技巧不事雕琢、语出自然,她善于捕捉富有诗意的画面,“那微波不兴的恬静的深湖/镶嵌在一望无际的荒原/月光轻柔又庄重肃穆/安睡在它长满石楠的湖岸/鹿群已聚在它们的宿处/受惊的羊群寻找着归路”何必苦苦寻觅诗意,诗意就在草原的牛羊间。
在艾米莉眼中,荒原不仅是一道说不尽的风景,也是心灵的慰藉之所。正如小说《呼啸山庄》里,每当希斯克里夫与凯瑟琳遭遇委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总会奔向荒野,向大自然倾诉内心的愤懑和不满,在自然的怀抱中,所有的阴郁、仇恨、愤怒会荡然无存。对艾米莉来说也是一样,她唯有在旷野中才能舒展身心、彻底放松,此时,岩石砂砾、溪水草丛、四时节令、朝云暮雨、阴晴圆缺,一切自然之景都带上了特有的情绪色彩,并在诗人泛神论的思想下与其自身的情感融为一体:“假如天色转暗,假如天有阴云/……/她的日子会像场悲剧,充满泪水、痛苦和忧虑/假如风儿清新又自由……她的日子会带着荣光,穿越世间沉郁的广漠”。诗中主人公的情感与天气的阴晴紧密联系在一起,空气沉闷、阴雨绵绵的天气无疑加剧了主人公的悲伤,而云淡风气的日子仿佛为主人公增添了一份精神力量,将昔日的忧愁一扫而光。在《高处的石楠在狂风中飘摇》这首诗里,自然万物和人类开展了一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聚会:
“夜半的溶溶月色闪闪群星下,
黑暗和光明欢聚在一道,
若九天下坠而大地崛起云霄,
将人的灵魂释放出阴郁的地牢,
碎了重重镣铐,折了层层铁栅。”
显然这首诗中荒原上的景物已经不再是审美对象,而是作为一个个鲜活的、有生命的形象,与人类同欢乐共悲伤。艾米莉如此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视为给予人类精神力量之源,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以及整个大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所以,当她描写荒野上乌云密布、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场景时,读者不会觉得阴森可怖,反而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狂野的一面,“狂风给山下的野林注入生命/激起阵阵林涛震天动地/汹涌的河水将堤岸冲决荡平,/不羁的激流在山涧河谷奔腾”点燃人们对生命的冲动和激情;而当她描写午后或傍晚的草原,一缕微风、一湖清水、一弯新月、几点星辰便能充分展示出大自然宁静祥和的一面,让人身和心在自然的怀抱中得到彻底的放松。
二、自由
荒原孕育了艾米莉的靈气,赋予了她超凡脱俗的气质,也塑造了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个性,而在外出求学以及做家庭教师的时间里,由于饱受被人役使、压迫和偏见的痛苦和折磨,她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心灵自由已经受到严重的束缚,乃至整个秩序化的社会都像是精神的牢狱和枷锁。于是在她的诗句中,天空变得阴暗;阳光也不再温暖;黄昏是惨淡的;夜晚更是黑暗的,没有月光,也没了星辰。但是,倔强的艾米莉没有感到丝毫难过和畏惧,反而表现出极大的斗争精神;她没有在诗中控诉抑或流泪,而是勇敢地正视命运的本来面目,“严酷的世界,隐藏起来到明天/人们的心,你不能全部都征服/如果你迟疑,它们一定还会反抗!”虽然恶劣的生存环境与不幸的生活造成了艾米莉的孤僻和苦闷,但同时也锻炼了她刚毅叛逆的性格,在自己一手构建的贡达尔王国,她试图将这痛苦的锁链砸个粉碎,好让她的子民重新获得自由与解放。
虽然能够为贡达尔史诗提供背景的散文没有留存下来,对整个叙事的连贯性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是艾米莉那满载激情与理想的诗句完全可以弥补这点遗憾。史诗中的人物,无论国王、平民、护卫还是囚徒,都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他们崇尚酷爱自由,英勇顽强地抵御侵略,反抗专制暴政,即使身陷囹圄,仍坚强不屈:
“我坚强地挺立,笑看
人类如何与我交战。
双方势均力敌,但我蔑视
人的那些卑鄙架势;
我的心灵完全自由
一声召唤,我就紧随它的左右。”
内心坦荡自然高尚,即便被剥夺的身体与行动的自由,也没有谁能夺走一个人精神和心灵的自由,一旦人们听从内心的召唤,那么强大的精神力量就会为他们建筑一道永远摧毁不了的堡垒。在另一首小诗中,诗人宣告道:“我若祈祷,那惟一/启动我双唇的祷文只有:/请别扰乱我的心/给我自由。”显而易见,自由之于艾米莉乃是一个坚定的人生信仰,这一信仰足以支撑她越过现实的黑暗,朝着理想的阳光迈步。
她注重从内在层面将自由与罪性、激情、死亡以及对上帝的信奉联系在一起,她的诗中有许多以“信仰”“上帝”“天堂”“梦幻”“死亡”“期待”为题,可以说她所追逐的自由是关乎心灵的、具有内在的、灵性上的意义。圣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把人生的痛苦看作是灵与肉的交战,认为自由就意味着依靠基督从各种捆绑和束缚的毁灭性势力中释放出来,因而自由也就包含了解放的意味。无论现实如何冷酷艰辛,艾米莉始终相信灵魂总会拥有最大的自由,“当我的灵魂逸出本体/游离得越远,便越欢喜/在一清风明月之夜/目光驰骋在银白世界”。
三、爱情
华兹华斯曾经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而艾米莉创作情感迸发的源头,无疑是孤寂二字。不仅仅是外在的形单影只,更主要的是她精神的孤寂、内心的孤寂。在《知更鸟儿》这首短诗中,诗人揭示了孤寂的原因“但人生久长的寂寞索居/熄灭的希望也压抑思绪”,其中“寂寞索居”一词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艾米莉生活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英国社会,父亲是牧师,几个姐妹都做过家庭教师,他们既不属于上层阶级,又不属于下层阶级,从社会地位來看是游离的,此外他们又住在哈沃斯这样一个广漠的旷野,就会显得更加离群索居,正是这样的离群索居激发了艾米莉内心深处的孤独之感,“十八岁如出生之时/无一挚友而孤独忧郁”。在成长的岁月中,在人海茫茫的大千世界,她尝遍世间的冷漠无情,她多渴望能够有一个人可以想她所想,填补她内心的寂寞,可是这个人从未曾出现过。这给艾米莉留下了更多的想象和思考爱情的空间,尽管不曾经历过爱情,但她对爱情的理解是极为深刻的。《呼啸山庄》同时期的那些小说,恐怕没有几部能像艾米莉那样把一个看似平常的爱情描写得如此刻骨铭心、惊心动魄,她在脑海中构筑的爱情比任何世俗的爱更为热烈、更为精彩。
艾米莉的爱情诗很少描写短暂的甜蜜,她表现更多的是情人间的生离与死别。这并不是说艾米莉借用诗歌来发泄心中的孤苦和怨愤,恰恰相反,她对爱情的态度非常真挚、炽烈且深沉,她所追求的是超越生死的永恒的爱:
“你在冰冷的底下,而十五个腊月寒冬,
已在那褐色的山冈上融成了阳春——
经过这么多年头的变迁和哀痛,
那长相忆的灵魂已够得上忠贞!
……
于是我戒绝青春灵魂对你的渴望,
强忍住无谓的激情催发的泪滴,
竭力克制去你墓前凭吊的如火的向往,
那个墓啊,比我自己的更属于自己!”
这一首是艾米莉曾公开发表过的诗,题目为《忆》,人们可以看到诗中男主人公早已是长眠地底的一具冰骨,而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的感情一如当年初见般炙热、浓烈,尽管添了一份凄婉伤感,但依然可以感受男女间真挚的情感中所隐藏的那一股强烈的“精神不灭”的力量。“那个墓啊,比我自己的更属于自己!”这般响彻心扉的感叹,与昔日凯瑟琳在疯癫的状态下大声喊出的那句“我就是希斯克利夫!”联系起来,人们才会发现原来诗人心目中最理想的爱情,绝非巴山夜雨、朝朝暮暮,她渴望和追求的是那种彼此精神相同,身、心、灵都完完全全融为一体的至情境界。这一信念早已化成诗人心中的北斗七星,所以她宁愿穷极一生朝那颗璀璨的明星一步一步追寻,也不愿半途而废或者迷失方向。她深信,无论多漫长、不管有多远,“有朝一日爱者与被爱者,/会在山头相聚重逢。”
四、生命
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写道:“情不知其所起,一往而深。”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艾米莉·勃朗特。尽管她的日常生活看似单调贫乏,但是她的内心情感极为丰富,仿佛天生一双慧眼,总能发现一个独特的视角去观察世间万事万物。她选取的意象往往呈现两极对立的特征,构成一股强劲的艺术张力,从而打破常规的审美情趣,融入新的感情色彩。“风琴鸣奏,军号响彻/胜利的灯光辉煌/在这千百人中没有一个/将捐躯长眠着怀想。”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人们,极少有人会想到去关心那些为战争而牺牲的人,因为捐躯者大多都是平凡人,可正是这些平凡人做了最不平凡的事,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和平与稳定,是不该被忘记的。诗句里一边是笙歌夜宴,另一边则是寂寞冰冷,诗人用欢笑去表现哀情,更加凸显出世人冷漠的本性。在《盛夏的一天》中,诗人起初赞叹“尘世的孩子啊,馨香的花”,转念又变得伤感,“稚嫩的蓓蕾必将萎落其花”,将孩子比作娇嫩的花朵,然而夏天过去冬季来临,花朵总会因严寒而凋零,暗喻孩子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终究会被社会改变模样。有谁会在花朵最初绽放的时期便想到它凋谢的时刻,诗人将花的生命过程的两端并置,展示了生命脆弱的样子。不过,既然生命原本脆弱,所以更需要坚强的意志。风暴是艾米莉钟爱的意象之一,常出现在她的诗句里,“让风暴更疯狂猛烈地刮起/把山间的积雪高高飞扬——”,这里风暴是难以抵御的可以摧毁一切的强大力量,而与之对应的石楠花、风铃草只在狂风席卷肆虐之际紧紧地把根扎进土壤。动态的风与静止的草,动静之间表现出平静的力量,好似心若止水、雁过无痕;强势的风与弱小的草,一强一弱呈现的是弱者的柔韧、坚强,恰如四两拨千斤之力。
遍观艾诗,人们可以发现诗人很少只单纯的描绘小鸟、碧草、泉水等清新明快的意象,相反,这些意象总是配合暗夜、土牢还有坟墓等阴森冰冷的场景一起出现,这不是巧合,而是刻意为之。希腊文中“象征”一词原义破碎的陶片,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破碎的陶片重新构建起最初完整的形象。于是,象征的意义就包含了至少一次分裂,原本统一的世界断裂成两个,从一个世界看到另外一个也许不复存在的世界。据此可以说,艾米莉如此执着于塑造冷暖色调强烈对比的两个世界,实际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味,其中不乏她对世界、对人生透彻的感悟。诗人极力营造出沉郁压抑的气氛,“我看见四周灰色的墓碑/延伸出的阴影望不到尾”,一位尘世的孩子,披着“阴云丧服”在狂风大作的冬夜,在黯淡的灯光下:“那双小手徒劳地推出/想把虚幻的恶魔驱逐/他眉额间铭刻着恐怖/内心充满了极度痛苦”。幼小的孩童没有在温馨的环境中成长,反倒在凄惨冰冷的墓地孤苦流浪,这并非艾米莉搜肠刮肚制造出骇人听闻的场面,而是底层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
五、结语
如果说艾米莉对荒原的热爱,从自然中寻觅诗情与浪漫主义诗人的做法似有共通之处,他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浪漫主义诗人借助诗歌“离开日常可怜、严酷、真实的世界,逃到一个浪漫、美好给人以享受的世界中去,而这个浪漫的世界比照了那个现实世界,并由于其本身的可爱,而对现实世界进行了无言的谴责”,所以这些诗歌中暖色的世界是较为明确的。艾米莉则虚构了一个诗的王国,影射自己所处时代的动乱不安:“周围的夜色越来越深沉/狂风冰冷呼啸不已/头顶是层层叠叠的乌云/脚下是无边的荒地。”环境背景的压抑阴森与思绪情感的悲郁激烈碰撞,形成艾诗独特的粗狂刚强的风格。由于内心深处的孤寂和对万事万物的浓烈爱意,这时候,艾米莉已然化身为荒原的神女,默默凝视着她的贡达尔王国以及荒原的一切。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