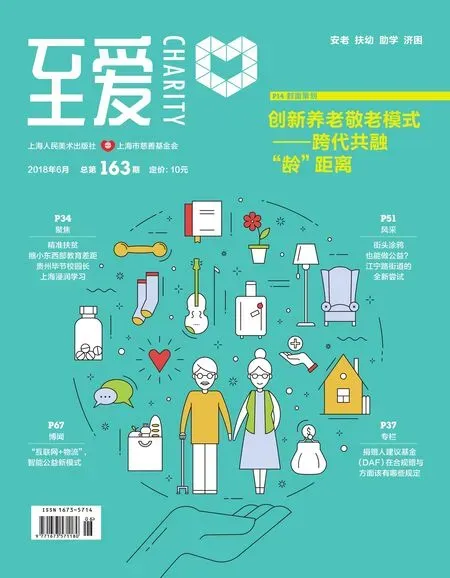“驿站大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外延式发展的新模式
文|闫磊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东四街道办事处
截至2016年底,北京市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329.2万,占户籍人口总量的24.1%,老龄人口总量和老龄化速度均位居全国前列。为此,北京市大力推进“市、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区级层面,2017年已初步建成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街乡对应成立养老服务管理中心),作为区级养老服务体系运行枢纽和指挥平台,发挥统筹、协调、组织、指导作用;在街道(乡镇)层面,通过2014—2016年3年行动计划集中建设完成252个养老照料中心,同时具备机构全托养老和辐射开展社区托老、居家助老能力;在社区层面,启动2016—2020年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作为机构养老功能的延伸和下沉,打造老年人家门口的“服务管家”,在日间照料、呼叫服务、助餐服务、健康指导、文化娱乐、心理慰藉等6类服务的基础上,拓展提供助洁、助浴、助医、助行等服务,截至2017年底已建成驿站380个。
主要问题
作为四级服务体系最关键一环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自酝酿之初就已广受关注,既有对未来前景的希冀,也有对过去类似平台建设经验的汲取。驿站运营以来,政府、运营方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扎根社区、深入家庭,开展了大量精细务实的为老服务,赢得了广泛认可。但随着周期拉长,一些问题也引起多方关 注。
“政府无偿提供设施、运行商低偿运营”“不离家”“就近养老”“老人身边的服务管家”等定位最大限度回应了当前社会各方的期待:从群众的角度,最大限度增进老年人福祉、提升服务可及性;从政府的角度,最大限度织密老年人社会福利网络、提升社会服务水平;从市场的角度,最大限度挖掘消费潜能、激活银龄产业。但这种定位就决定了现有驿站的社会公益性、福利性和微利性。在目前公开报道中,已运营驿站赢利的不足两成,严重亏损的高达五成以上;在实际运营中,一些驿站为寻求盈利点,开始在政策空隙中开展健康保健品销售、医药诊疗等;一些驿站为降低成本裁减人员、减少服务或服务外包,驿站“活力不够”,专业性缺失。
探究原因
一是较密的驿站布局,在方便老年人获得服务的同时也稀释了市场资源,一定距离范围内的驿站之间存在“争夺”老人和市场的竞争压力,运营方获利难度较大。这一问题也促使街乡照料中心收缩社区托老和居家助老服务,成为区域性小微托老机构。
二是驿站自身及其辐射范围面积较小、空间有限,既定的6大基础功能带有较多的公益和微利性质,6大功能的开展不仅占据了驿站绝大部分的空间和资源,也限制了运营方不断循环放大资源投入,在微利或亏损状态下的资源投入存在相应萎缩趋势。
三是在政府宏观政策红利刺激下,一些养老企业“走马圈地”,集中较多“驿站”作为市场资本开展市场运作,“驿站”成为市场要素,淡化了为老服务平台原有功能定位。
四是一些小微企业在政策红利刺激下纷纷投身驿站运营,以“驿站”为媒介将自身发展与宏观政策捆绑,寄希望于政府兜底和政府买单。
五是政府对驿站服务的限价政策和对其社会公益性质的强化,一定范围上限制了市场要素的创新活力,驿站之间的服务项目出现同质化趋势,这一趋势造成毗邻驿站间的同步衰弱,一些政策空隙间的灵活运作又偏离了驿站福利性质的原有定 位。
六是“驿站”嵌入“社区”不足,多数驿站以福利主体或市场主体形式出现,着重对接街道、乡镇层面,下沉和融入社区不够,还无法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提供服务,这与政策定位初衷不符。
七是驿站服务嵌入居民生活不当,要么嵌入过度,驿站成为老年人休闲娱乐活动室或各类问题“全能保姆”;要么嵌入不足,驿站成为“类商店化”业态,游离于居民日常生活之外。
“驿站大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外延式发展的新模式
驿站作为四级养老服务体系扎根社区、贴近群众的最关键和最基础一环,“规范”“专业”“务实”“有效”在政策设计伊始就被反复强调。从内涵与外延式发展两个角度来看,驿站的内涵式发展主要包括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和品质服务等方面,监管和评价体系是约束驿站内涵式发展的主要外部手段;外延式发展主要是指在政策规范以外,驿站拓展的功能、服务、形象和运作模式,基于市场利润、社会荣誉、群众需求等现实因素,运营方和行政指导方都有着强烈的外延式发展诉求,但这又存在造成驿站政策混乱、定位模糊和服务泛化等风险。
应该说,外延式发展是实现驿站内涵进步的内在张力和关键动力。外延式发展的关键是允许资本要素在市场机制下实现扩张,并在与政策的契合中得到合法性激励;基础是在稳定的场域空间内实现基于契约(或公约)的对等“交易”;最终目标是在这一场域空间构建起基于“交易”的文化共同体—融入并成为社区和群众生活的一部分。当前驿站建设、运营的监管和评价体系已逐步完善,存在的许多问题虽然可以归结为“内涵式”发展不足,但根本在于外延式发展缺失。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街道南门仓“驿站大集”是一种外延式发展的探索模式。
南门仓“驿站大集”借鉴了传统“集市”模式,以“打造覆盖东四地区的居家养老服务平台,整合资源、汇聚服务”为目标,固定每月底在南门仓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举行,当期预告下期时间和主要摊位。参加各方不仅有企业、社会组织,也有居民个人和各类兴趣小组。老年人及其家属既可以到集市上去买“服务”,也可以报名参加各类兴趣组织、志愿服务团队,还可以申请摊位展示组织、个人的为老服务成果和个人创意、才艺,吸引“志趣相投”的同 伴。
南门仓“驿站大集”首场活动广受居民关注,活动持续一天,10余家企业、社会组织、志愿团队提供了50余项服务菜单,26人现场报名驿站兴趣小组和互助团队,40人预约了15天内的驿站居家养老服务项目,10 人预约老年公寓入住,21人预约了老年餐,13人报名了老年旅游,2位老年书法家展示并为居民书写了书法作品,150余人进行了家政、按摩、修脚、金融知识、慢病管理、护理技能、养老助残卡办理等现场咨询,实现了驿站、居民、第三方产品(服务)供给方的良性互动。
第一,发挥了驿站作为为老服务平台的“链接”作用,真正实现小平台大服务的目的。通过大集整合资源,在实现驿站既定功能的同时,拓展和丰富了服务种类,便利了居民,也改善了驿站自身的资源投入结构,能够摆脱“全能保姆”的困境,集中资源聚焦特色和品牌服务项目。
第二,驿站发挥“连接”作用,改善“福利供给”模式,在市场化运作中实现“社会公益”。在大集中,以驿站为平台,居民直接面向各类服务进行选择,减少了驿站负担,从中介位置转变为信息提供者和“市场准入”把关人,以市场机制优化了服务项目供给。对参与其中的企业和社会组织而言,参加大集并非以驿站为经营场所、以交易为谋生目的,更加侧重于市场认可和消费者体验,起到了引导“自律”的效果,客观上利于为老服务企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第三,驿站发挥“联结”作用,依托“驿站大集”构建地域和文化共同体,使驿站融入社区、驿站服务融入居民生活。在驿站,人们相互交流并满足各自需求,驿站成为一种公共空间,大集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交易”和展示活动引导驿站、企业、居民各方之间构建起邻里关系、消费者关系等关系网络,互动中产生的相互影响也有利于激发价值观念等的趋同,如老年消费观、消费习惯、企业社会责任感等,形成文化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的形塑中,驿站本身既实现了政策预期,又成为社区建设更广泛意义上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在政策合法性和社会认可的激励下,有利于引导市场及社会资本力量更广泛深入地投入以社区为单元、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的社区建设发展。
“驿站大集”的走向
从目前的驿站建设来看,单体建设、连锁运营是主流,“PPP(公共私营合作制)模式”“联盟模式”极少。随着数量庞大的驿站建成,运营方特色化运营的愿望十分强烈,如“老残一体”模式、“医养结合”模式等等。这些模式都或多或少有着“便民服务综合体”的趋势。“驿站大集”作为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实践活动的一种探索性尝试,其意义也在于指向了这样的一种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造成政策混乱、定位模糊、服务泛化等问题,以相对更加开放的姿态,鼓励各方投身并共同建设尚不成熟的区域为老服务体系和为老服务市场。这一趋势的特点在于:第一,契合居民日常生活的复杂性;第二,契合基层政府和基层社会的现实条件;第三,契合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 要。
因此,“便民服务综合体”这一趋势的本质在于构建基于社区团结和公共利益的社区共同体,“驿站大集”这一具体活动形式的本质也在于成为一种以老年人为基础的,走进家庭、联结周边、扎根社区、依托社区的地域和文化共同体,并以此参与到社区整体的共同体建设之中—在这一目标下,任何形式都是值得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