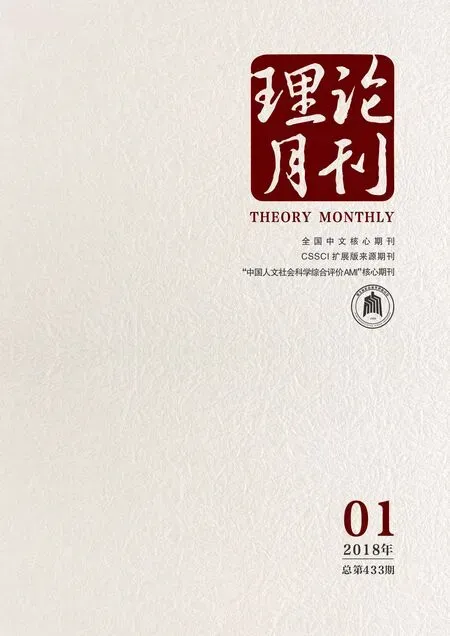从数字式脱贫到发展式脱贫:一个省级贫困乡的贫困治理逻辑分析
□卢艳齐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引言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贫困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阻碍。2014年初中央制定了精准扶贫战略,具体是指“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1]152,这为当下中国的扶贫开发指明了新的道路。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明确提出“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2]的脱贫战略目标,将精准扶贫战略转变为精准脱贫战略。
精准扶贫实施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挪用扶贫资金,截留扶贫资源,或者“扶农”不“扶贫”等问题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一些偏远的地区,“越扶越贫”的乱象也时有发生。针对不同的扶贫乱象,学界开展了相关研究。葛志军(2015)等人关注了地方扶贫实践中出现的贫困户参与不足,帮扶政策缺乏差异性和灵活性等问题[3](p157),唐丽霞(2015)指出扶贫政策本身存在制度缺陷[4](p151),邢成举(2016)指出精准扶贫中财政扶贫目标偏离的情况以及农村贫困转型对精准扶贫的挑战等问题[5](p109),刘司可(2016)则研究了精准扶贫工作中贫困退出机制不健全的问题[6](p45),李群峰(2016)分析了村干部权力寻租等瞄准偏离的现象[7](p73),李博(2016)则进一步探讨了项目制在扶贫开发中出现的功能式微问题[8](p106)。2017年,学界关于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文章呈现爆发式增长,据中国知网(CNKI)的数据分析,2017年相关文章数量400余篇,涵盖的问题更加广泛且细致。如雷望红(2017)指出,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着明显的不精准执行现象,表现为识别不精准、帮扶不精准、管理不精准和考核不精准等问题[9](p1);朱天义等(2017)认为精准扶贫中乡镇政权采取了选择性的治理行动[10](p212)。不仅如此,由于对精准扶贫的研究呈现多学科交叉分布的特点,不同学科对精准扶贫中出现的问题关注也有不同,例如经济学关注产业扶贫、金融扶贫(刘建生,2017;谢玉梅,2016)[11](p127)[12](p79),政治学关注贫困户的政治权益(李洪波,2017)[13](p145),社会学关注精准扶贫中的社会组织力量(黄建,2017)[14](p179)。这些研究对进一步深化学界对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多元化的认知角度,取得丰硕了成果。但是在精准扶贫主体的探讨层面,这些研究大多将精准扶贫中出现的问题对准中央国家、县市一级或者是村庄,却忽视了乡镇一级政府作为精准扶贫主体的重要地位,缺乏对贫困地区乡镇政府的扶贫和脱贫能力及其政策执行行为的研究。此外,也很少有学者关注到乡镇政府当中的“数字式脱贫”现象。事实上,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一级政府处于国家权力末梢,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落实者,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贫困中的实质性主体和主导,也是整个精准扶贫体系的“最后一公里”。笔者对A乡的精准扶贫工作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认为贫困地区乡镇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隐瞒和虚报的“数字式脱贫”现象,但同时为了切实减少和消除贫困,乡镇政府又在大力实施“发展式脱贫”政策。此类“貌合神离”的行为所带来的问题即是为什么乡镇政府会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出现隐瞒和虚报的情况?乡镇政府又是如何采取改进措施的?其效果如何?本文试图通过透视当下我国乡镇政府精准扶贫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困境,探索具体治理情境下优化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改进思路。
二、田野呈现:湖北省A乡的精准扶贫对策
A乡位于湖北省C市西南,距市区54公里,属省级贫困乡。全乡总面积56.3平方公里,主要地势以丘陵为主。A乡下辖13个村(居)委,92个自然村,123个村民小组,总户数4822户,总人口2.13万人,是一个典型的小乡镇。A乡地理位置偏僻,属传统粗放型纯农业生产乡镇,工业基础薄弱,外出务工人员高达61.5%,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
2015年,全乡进行了对建档立卡的户数和人数进行了摸底排查,最终按照农户申请、组级评议、组级公示、村级审核、村级公示、乡镇复核、村级公告精准识别“七步法”流程和精准扶贫对象识别“十不评”有关要求,确定全乡精准识别的对象,共有347户737人被列为精准扶贫对象。根据上级政府精准扶贫工作的总体部署,全乡计划5年内每年帮助229人实现脱贫,并力争到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对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的基础上,A乡制定了周密的精准帮扶实施方案。为了督促帮扶单位和帮扶干部,A乡执行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将扶贫工作的目标任务完成、投入、驻村帮扶情况列入考核目标,实行一季度一督查,一季度一评比,考核结果列入年度科学发展综合考评,奖优罚劣,并将其作为评优评先、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从A乡的精准扶贫工作部署来看,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考核等都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唯独缺少精准管理这一项。事实上,精准管理机制的不健全和信息的不透明恰恰给乡镇政府数字脱贫留下了可供操作的空间。在A乡,针对“脱贫任务能否完成?”这个问题,扶贫干部的普遍回答是“肯定能,这个东西就是你说脱贫他就脱贫了”①正文中楷体字部分均为笔者2017年7月至8月底在A乡进行调研时获得资料,撰写的观察笔记以及访谈记录,所有人名和地名均做了相关技术处理。。扶贫干部的回答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乡镇政府掌握了脱贫的主动权和控制权;第二,精准扶贫对象并不清楚自己的脱贫状态。精准扶贫主体和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乡镇政府在精准管理上的自由裁量权出现了扩张,使得乡镇政府可以在精准扶贫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一些扶贫对象列为已脱贫状态,自动消除这些扶贫对象的贫困档案和信息资料,按照这样一种方式,不论是提早两年还是三年,都能够顺利实现上级政府的目标和任务。如此一来,便出现了一种欺瞒上级和下级,运用精准管理上的漏洞和缺陷完成脱贫指标任务的“数字式脱贫”现象。
数字式脱贫是贫困地区乡镇政府在目标管理责任体制下回应上级政府的一种策略选择。但是,乡镇政府并不能完全依靠数字式脱贫来治理贫困,解决当地的贫困问题,也很难完成最后的验收工作。因此,乡镇政府仍然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来治理贫困,帮助贫困对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A乡目前的扶贫方式主要是产业扶贫,主要有东塘村的平菇种植基地、800亩高产油茶种植基地、富民花生油生产合作社;河平村1200亩中药枳壳子种植园;石竹村的薯粉加工项目和黑美人西瓜苗项目。各村委主动将扶贫对象吸纳到产业扶贫项目当中,通过年终分红的方式帮助部分村民实现脱贫。不仅如此,在2016年6月,换届选举之后新任领导干部通过多方渠道又为A乡拉来了高达3千万的扶贫项目,分别是3600亩的坡耕地改造项目、扶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立体生态旅游项目,与现行的短、平、快扶贫项目相比,这些新项目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创收,需要通过较长时间的成本投入才能顺利回本增收。时间长、创收慢,A乡的扶贫方式不能帮助当地政府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因而并非针对上级政府下达的政治任务,A乡的扶贫选择是通过振兴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来带动全乡农民增收,实现整体性的脱贫,也即是一种发展式脱贫。
三、数字式脱贫:乡镇政府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从粗放扶贫到精准扶贫,由“大水漫灌”转为“滴灌”,“输血”转为“造血”,国家的扶贫战略不断优化和改善,这一政策过程的价值取向是促使改革成果在更广范围共享,而其目标则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脱贫。放眼全国,一场场脱贫攻坚战正在打响,举国上下为了实现脱贫目标而奋力作为。在此形势下,中央与贫困情况严重的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签订了扶贫攻坚“军令状”,试图以“军令状”的方式来推动扶贫攻坚工作。周黎安(2014)在将行政发包制与“政治锦标赛”结合进行分析时指出,“行政发包和晋升竞争在多层级同时进行意味着纵向层级间会产生一些有趣的博弈互动”[15](p39),其导致的结果便是经济指标从中央、省、市至县的“层层加码”现象,而在脱贫任务的具体情境中,这一结果则表现为脱贫时间的不断提前。湖北省设定的全省脱贫时间是2020年,大部分县市的脱贫时间和省里保持一致,也有少部分县市在此基础上将脱贫的时间又提早了2年,定为2018年。“层层加码”之下的横向竞争无疑加重了地方政府的扶贫任务,在压力型体制下,这个扶贫重担又通过权力加压和任务传导的方式交给了乡镇一级政府,而实际上,乡镇一级政府却处于贫困治理的重重困境之中。
(一)乡镇政府的精准扶贫之困
1.目标之困:艰巨的脱贫任务
2016年3月A乡出台了精准帮扶的实施方案,文件指出,“紧紧围绕2020年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按照市委、市政府精准扶贫工作的总体部署,动员和组织全乡力量与贫困户结对帮扶,力争通过2—3年的努力,全乡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以村组为单元的区域性贫困现象彻底消除。”根据部署,全乡确定了帮扶时间安排,2016年3月15日至2016年3月20日为宣传动员阶段,2016年3月21日至2016年3月31日为联系结对阶段,2016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为开展帮扶工作阶段。同时,全乡制定了详细的结对帮扶安排表,通过“帮扶单位—帮扶企业—帮扶工作队长—帮扶乡干部—帮扶村干部”五级联动的方式,将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工作岗位上,细化到每一个乡干部身上。2014年4月A乡又相继下发了精准扶贫结对帮扶工作职责的通知,以及帮扶工作考核指标体系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乡干部与所挂点村(居)委年终考核结果实行同奖同罚的考核奖惩机制。
韦伯(1997)在阐述科层制的特征时指出,为了实现组织目标,组织常常“把为实现组织的目标所必须的日常工作,作为正式的职责分配到每个工作岗位”[16](p213),而科层制的发展与再发展恰恰是当下中国政府所实行的目标管理责任制。作为政治组织形式的各级政府,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预定目标与任务,各级政府之间、各政府组织内部及其单位与个人之间,制定了相应的目标及达到目标的计划、奖励乃至处罚措施,在贫困治理的工作中,实际上采用的管理方式仍是目标管理责任制。关于目标管理责任制,王汉生(2009)等人肯定地认为,“作为一种实践性的制度体系,目标责任制在上下级政府权威关系的基础上,引入了一种更具平等意涵的‘责任—利益连带’关系,从而在实际上创造出一种少见的政府间全面竞争的机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与维持社会秩序两个基本目标以及推动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模式先行”[17](p89),海外学者高杰(2015)等人则认为“目标责任制的独特设计,即自上而下分解下达的结果导向型的指标与高激励机制的结合,为恶性博弈的产生提供了温床”[18](p635)。事实上,目标管理责任制运行中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指标体系,二是考核方式,而两个核心要素最终都落实为“数字化管理”,以便于进行简单管理和高效监控。在贫困治理中,当数字化的管理方式遇到以结果导向型的指标体系,二者的结合催生的便是数字式脱贫的乱象。
A乡5年扶贫工作中都是一个量化的任务指标,那就是每年帮助229人实现脱贫。但是实际上,就目前A乡扶贫项目的数量和质量来看,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A乡最大的扶贫项目高产油茶种植基地为例,800亩的高产油茶,以1000元每亩的价格计算,每年盈利80万,能够帮助东塘村委9户精准扶贫对象脱贫,而东塘村委的贫困户数是51户,这就意味着需要6年时间才能实现全面脱贫。由此,在目标管理责任制下,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形势,乡镇政府在贫困治理的明线上采取了“数字式脱贫”的方式,以应对上级政府的考核和任务审查。
2.能力之困:弱化的贫困治理能力
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消除或减轻贫困的过程是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减轻贫困双重目标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治理的过程。治理理论中的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并非只有政府一个主体,还包括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公民个人等多元决策中心[19](p47)。然而,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治理贫困的经验则表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贫困治理体制。林闽钢(2008)指出,“政府主导型”的贫困治理形成了以政府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动员结构和机制,这一结构和机制在多年的扶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扶贫效率问题、贫困人口的“等、靠、要”被动扶贫现象[20](p51)。同时,在压力型体制的作用下,直接肩负脱贫重担的实质性主体是以乡镇为中心的基层政府。由于级别和权力层次的限制,除非上级政府主动要求,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很难参与到上级政府的政策过程中去,由此一来,乡镇政府有执行决策的义务却没有参与政策制定的权利。同样的,在贫困治理中乡镇政府必须毫无偏差的执行扶贫政策,完成脱贫任务。
近些年来,国家正在逐步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构建多元化的贫困治理主体,通过充分动员发达地区各级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私营企业和志愿者个人共同参与来解决贫困问题。A乡在精准帮扶方式中也提到要实行乡村干部结对帮扶全覆盖,乡属及驻乡单位结对帮扶全覆盖,企业员工、农村能人(大户)、社会组织及社会爱心人士结对帮扶贫困户全覆盖的帮扶措施,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来推动全乡脱贫目标的实现。然而在实际中,这种多元贫困治理主体的构建却出现了目标偏离的现象。在同一份文件中,A乡又明确指出乡党委、政府,村党支部、村委是精准扶贫攻坚的责任主体。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社会力量往往“出工不出力”。主管扶贫工作的乡干部指出,“市委市政府给乡里安排了相关帮扶单位,却很少看到这些单位下来协助我们的扶贫工作;还给省级贫困村东塘村配置了扶贫第一书记,但他来了之后给了1万元就没再管这件事。”还有平菇种植基地的帮扶单位C市某职业技术学院,在将相关技术和资料转交给乡里之后也没有再来过。显然,A乡的遭遇使得乡政府只能通过自身力量来治理贫困,而A乡又是一个省级贫困乡,治理资源和能力方面都处于严重匮乏状态。
周飞舟(2006)通过对税费改革过程中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考察,发现过去一直依靠从农村收取税费维持运转的基层政府正在变为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基层政权从过去的汲取型变为与农民关系更为松散的“悬浮型”[21](p1)。贺雪峰(2008)则进一步指出,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加剧了基层政权的财政困境,削弱了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基层政权在无法做坏事的同时,也丧失了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22](p168)。学界的共识是,治理能力是反贫困过程中的关键因素,而一个悬浮型政权一方面来面对上级政府的脱贫任务,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底层民众的脱贫诉求,其自身贫困治理能力不足的现状迫使乡镇政府做出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选择,这便是通过脱贫数字上的变动暂时性的摆脱困境。
3.对象之困:“精英俘获”下的乡村
2006年国家税费改革之后,国家的资金大部分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到达基层,向上要钱成为乡镇政府获取运转资金的主要来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分税制改革的完成,国家的各项财政资金逐步通过“专项”和“项目”的方式向下分配,并慢慢成为一种主要的财政支出方式。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项目制是指政府运作的一种特定形式,即在财政体制的常规分配渠道和规模之外,按照中央政府的意图,自上而下以专项化资金方式进行资源配套的制度安排[23](p82)。项目制形成后,便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下沉最终进入了乡村社会,这便有了项目下乡一说,而税费改革与项目制下乡的合成,使得当前基层政府的贫困治理需要通过依靠项目的争取和运作实现脱贫。
在乡镇政府陷入财政困境的情况下,项目制下乡为贫困治理提供了一条主要的“财路”。然而在实际中,项目制的运作导致国家的扶贫资源出现被村庄精英截留的现象,不仅被精英村庄俘获也被精英人物俘获。首先是被精英村庄俘获。A乡的12个村(居)委有两个是省级贫困村,根据省里的财政安排,两个省级贫困村每年各能获得20万元的资金扶持,但这笔资金用来发展产业扶贫却远远不够。为了向上争取更多的资金扶持,东塘村和河平村主动通过各自的权力关系网络,不断到市里和省里争取项目,在乡政府的努力和配合下,东塘村和河平村分别争取到了3个竞争性扶贫项目,共获得扶贫资金300多万。而在其他村委,由于缺少关系没有门路,只能等着上面的一些非竞争性项目,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这种缘起于村庄整体能力而导致的项目配置不均衡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村庄之间的差距,导致一些边缘化的村庄长期不具备脱贫能力。其次是被精英人物俘获。项目争取下来后,根据2015年1月实施的村财乡代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村里的项目资金统一交由乡财政所代管,但项目的运作权却委托给了村委,具体则是由村支书等村庄能人来打理。这些担任村干部的精英人物本身就有着衔接扶贫项目的明显优势,而且由于他们在跑项目的过程中立下了功劳赢得了乡政府的信任和尊重,因而精英人物掌握了扶贫资源的配置权和实施权,这也为精英人物截留扶贫资源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加深,农村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精英阶层通过与乡镇政府的利益连接进入村委,实际掌控了村庄两委,加之城镇化从农村带走了数量可观的劳动力,留守农村的“386199”部队难以对村庄能人形成有力的监督和约束,乡村治理内卷化[24](p86)趋势加强。不论是精英村庄俘获还是精英人物俘获,扶贫资源在“赢利型经纪人”的把持和操控之下,通过精准扶贫的第一道关卡——精准识别就有计划的流入到了少数人手中,而一些真正的贫困对象则被排斥在外。因而,项目制下乡过程中出现的精英俘获现象这事实上加大了乡镇政府脱贫的难度和准确度,为乡镇政府实现全面脱贫目标埋下了隐患。
(二)数字式脱贫的生成条件和隐患
1.数字式脱贫的生成条件
乡镇政府一方面陷入贫困治理的重重困境之中,另一方面又要完成超越实际贫困治理能力的脱贫任务,2020年前帮助全乡347户737人实现脱贫所面临的挑战不可谓不艰巨。为了按期完成这项硬性的指标任务,A乡采取了数字式脱贫的治理对策,即利用精准管理上的漏洞通过数字上的变更来实现脱贫目标。但是这项对策的实施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通过上级政府的检查;二是消除扶贫对象的疑虑。第一个条件不难满足,这可以通过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得到解释,但贫困治理中“共谋现象”的发生,正如周雪光(2008)所说“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政府官员或执行人员的素质或能力。共谋行为的产生和重复再生是政府组织结构和制度环境的产物,是现行组织制度中决策过程与执行过程分离所导致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近年来政府制度设计、特别是集权决策过程和激励机制强化所导致的非预期结果”[25](p1)。重要的是如何消除扶贫对象的疑虑。笔者曾随扶贫干部到新楼村完成脱贫对象的图像采集工作,贫困户对自己低保资格被取消一事进行了利益诉求,乡干部的解释是“我们也没办法,这是上面的政策,实在困难的乡里会想办法帮你们申请其他补贴”。上面的政策是什么样的,贫困户并不知情,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化解扶贫对象的疑虑,可以说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无奈之举,但也暴露了乡镇政府刻意逃避责任的缺陷。
2.数字式脱贫的隐患
不论其初衷如何,以数字式脱贫来应对上级政府的目标和任务最终将会产生巨大的负面效果。从国家层面来看,数字式脱贫通过隐瞒和虚报的行径将会对我国贫困治理的整体进程产生阻碍作用,由于中央政府难以把握地方精准扶贫的准确信息,在政策制定中必然出现偏差,导致全面性的不良影响。从基层政府层面来看,数字式脱贫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帮助地方顺利通过上级验收,完成目标和任务,但是从长远来看它无法实质性解决贫困问题,将对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产生消解作用。如果扶贫没有扶到根上,贫困问题就将继续困扰国家和地方政府。从精准扶贫对象层面来看,数字式脱贫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贫困户在脱贫之后迅速返贫,降低农民对政府的政治信任,从而进一步激化基层的矛盾纠纷,由此引发基层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2015年中央将精准扶贫战略上升到精准脱贫战略,再一次重申和明确了脱贫的目标和任务,虽然有学者认为“精准脱贫意在通过一系列的脱贫机制使贫困者具有自主脱贫的能力”[26](p7),但是在当前的治理情境下,不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格局,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仍是精准脱贫的实质性主体,提升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首先还是要提升基层政府的脱贫能力。
四、发展式脱贫:精准扶贫工作改进思路初探
数字式脱贫展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中国式情境下基层政府的策略思维,但是这种方式无法为基层官员赢得实质性的晋升筹码,也无法解决贫困的本质问题。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最终还是要回到精准扶贫的根本目标——精准脱贫上来。为了实质性解决贫困问题,A乡紧锣密鼓的探索了相关改进思路,确定了以精准扶贫之名行经济发展之事的发展式脱贫道路,这既是一种贫困治理思维的转变也是一种精准扶贫的差异化选择。作为一种有别于标准化脱贫道路的差异化选择,发展式脱贫在当前严峻和紧迫的脱贫形势下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不乏一些不足和缺陷。
(一)发展式脱贫的生成机制
1.精准扶贫与经济发展的“互嵌”
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前,乡镇政府的主要任务一是发展二是维稳,自从精准扶贫这项民生工程正式下达到基层以后,乡镇政府的工作重点向扶贫转移,地方经济发展退居次要地位,A乡同样如此。然而,A乡面临的实际情况却是:贫困治理能力不足、经济发展上不去、地方维稳工作有条不紊。负责综治工作的党委委员总结当地的维稳工作时说,“近20年来,我乡综治情况保持良好,没有出现进京上访事件,没有出现重特大刑事案件,没有发生民转刑事件,没有出现宗族械斗事件,没有发生需要专门力量参与的涉访涉稳事件,没有出现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的案件。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纠纷不上高(法院),涉稳问题不越级上访。”在实际调查中笔者也发现,当地民风淳朴,无论多大的矛盾纠纷群众首先想到的是乡政府,政治威信的树立消解了A乡的维稳难题,因此维稳问题并不在乡政府的重点工作当中。作为一个经济排名垫底的边远乡镇,A乡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发展。2015年正式实施精准扶贫之后,A乡在精准扶贫道路上做了一个调整,这便是将精准扶贫与经济发展进行“互嵌”,通过发展经济这第一要务实现全面脱贫目标。
2.“由点到面”的扶贫方式转变
A乡的扶贫措施较为单一,主要依靠产业扶贫。在扶贫的初期,A乡的发展定位是:精准扶贫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突出发展现代农业。A乡2015年的扶贫工作汇报这样阐述自己的扶贫道路:我乡将重点依托现有资源,围绕现有产业,做到“一村一法”“一户一策”。一是依靠致富能力带领村民致富。采用“村党支部+农民合作社+农户”的运行模式,按照“三统一”原则(统一免费技术指导,统一生产资料,统一销售渠道),带领村民一起脱贫致富。二是按照“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的理念,依托我们现有的油茶、花生、荞头等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重点发展油茶、花生、荞头等当地特色产业,构建“产业基地+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为贫困户提供产销一条龙服务,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但是,在实际的扶贫工作中A乡走的是一条“以点代面”的发展道路,将大量的扶贫资源输送给两个省级贫困村,导致扶贫资源难以得到优化配置。不但如此,就产业扶贫发展的现状来看,注重前期的投入而忽视后期对于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进行扶持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也导致一些产业所投入的项目半途而废,出现“年年扶贫年年贫”的现象。为了扭转局面,A乡决定回归“由点到面”的扶贫方式,在不破坏既有成果的前提下,将着力点放在推进整村脱贫的“面”上。通过积极地争取项目和资金,3600亩的坡耕地改造项目、扶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立体生态旅游项目等陆续上马。投资大、见效慢是这些项目的共同点,这就意味着A乡需要通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来解决贫困和发展问题。
3.政府的路径依赖与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
改革开放30多年的扶贫之路表明,政府主导型的扶贫方式仍是我国贫困治理的主要经验,而政府最拿手的却不是扶贫而是发展经济。制度经济学大师诺斯(1990)对制度变迁当中路径依赖的研究表明,路径依赖的形成不仅仅是历史偶然事件或小事件引起的,而更多是由行动者的有限理性以及制度转换的较高的交易成本所引起[27](p317)。当扶贫成为乡镇政府的主要任务而经济发展退居次要位置时,政府的路径依赖由此显现,而从制度经济学的层面来说,将扶贫与经济发展相互嵌套则能够为政府减轻交易成本,并且通过资源转换,能够帮助基层政府获得更多发展经济的资源。此外,在目前的形势下,政府还需要考虑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从实际情况出发做出准确判断。长期以来,我国贫困人口基数大,受输血式扶贫方式的影响,基层民众形成了等、靠、要的依赖思想。A乡的扶贫干部反映:“给老乡送饲料,他们不主动来领,反倒插着手等乡干部给他们送上门。”这样的情况并不在少数。贫困理论家阿玛蒂亚·森(2013)提出能力贫困的概念,认为贫困是对人的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要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应当从提升可行能力的角度入手[28](p62)。但是在当下,贫困人口的依赖思想并没有得到完全转变,依靠自身脱贫的能力不容乐观,提升其可行能力的路径选择与急切的脱贫任务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二)发展式脱贫的价值与效度
鉴于数字式脱贫这种完成目标任务的捷径,无论其初衷是否符合相关法规制度以及道德伦理,都难以从事实上、根本上减少和消除贫困,为此就需要乡镇政府着实从政策执行上进行审慎考虑,切实将扶贫工作落到实处。在此情境之下,乡镇政府的选择是发展式脱贫。发展式脱贫立足于较长的脱贫时间节点,意图采取将扶贫与发展进行“互嵌”的方式,大力推进由点到面的扶贫政策,从而实现整体性脱贫。这一差异化选择体现了乡镇政府的脱贫意愿和策略选择,在由“管”到“治”的政府职能转型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我国的贫困地区,普遍面临的发展难题是交通不便、区位优势不明显、生态环境恶劣以及资源匮乏等,当经济发展尚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前提下,将主要精力放在脱贫上对乡镇政府而言是个不小的转变,需要克服重重困难。走发展式脱贫的道路,将发展与扶贫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可以实现资源在同一层级的互通和共享,能够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在“省市一盘棋”的目标体制下,受自身治理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发展式脱贫也存在一定的危机。例如,由于无法同时兼顾扶贫和发展,导致一损俱损的局面出现,反而阻碍了国家整体性脱贫目标的实现。此外,招商引资竞争激烈、农村能人缺乏、大量资源流向少数精英手中的情况客观存在也加大了发展式脱贫实施的难度。民间流行的一句说法是“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个地区生存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始终还是要以自身的实际为基础,充分结合群众的意愿和想法,才能为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共同目标做出更加有利的贡献。
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以往的粗放式扶贫,2014年开始实施的精准扶贫战略更加突出对贫困治理的精和准,将国家的扶贫资源进行精确的技术瞄准,做有针对性的扶贫。当下,我国的精准扶贫工作仍然是由政府主导,针对在其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在扶贫主体的研究层面,大多数学者停留在具体村庄或者是市县一级,忽视了乡镇一级政府。事实上,在压力型体制下,处于国家政权末梢的乡镇政府是精准扶贫的实质性主体。基于此,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精准扶贫视阈下乡镇政府治理贫困的策略选择。研究发现,乡镇政府在精准扶贫中为了实现脱贫任务,采取了隐瞒和虚报,利用精准管理中的漏洞做文章的“数字式脱贫”,为了改进这一行为的负面效果,又采取了发展式脱贫的解决措施。此类行为说明,乡镇政府在治理贫困过程中出现了目标与行为的偏离,实质上是贫困地区乡镇政府“策略主义”的体现。所谓“策略主义”,在欧阳静(2011)看来,是指基层政权组织缺乏稳定的、抽象的、普遍主义的运作规则,以及基于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以各类具体的、权宜的和随意的策略与方法作为原则,并只顾追求眼前的短暂目标[29](p116)。策略主义的实施凸显了乡镇政府治理贫困的实践困境,表明贫困治理能力较弱的乡镇政府,其在帮扶农民脱贫的过程中必然力不从心,由此出现有令不从、欺上瞒下的悖逆现象。
精准脱贫作为国家“十三五”时期的重要战略目标,面对贫困地区乡镇政府采取策略性选择的治理情境,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纠正:首先,建立健全贫困地区乡镇政府的扶贫信息反馈机制,及时掌握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摒弃脱贫目标“一刀切”的做法;其次,政策制定中要统筹兼顾,充分考虑乡镇政府的贫困治理能力,尊重不同地区的差异化选择;再次,构建多元主体联动的贫困治理体系,通过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治理,监督和催促各级机关单位履行贫困治理责任的方式,优化贫困治理格局。最后,不仅要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更要注重提升乡镇政府的可行能力,强化基层政权的贫困治理能力。
[1]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J].贵州社会科学,2015(8).
[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新华网,2015-10-29.
[3]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5).
[4]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的政策和实践困境[J].贵州社会科学,2015(5).
[5]邢成举、李小云.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9).
[6]刘司可.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贫困退出机制的实践与思考:基于湖北省广水市陈家河村152户贫困户的问卷调查[J].农村经济,2016(4).
[7]李群峰.权力结构视域下村庄层面精准扶贫瞄准偏离机制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8]李博.项目制扶贫的运作逻辑与地方性实践:以精准扶贫视角看A县竞争性扶贫项目[J].北京社会科学,2016(3).
[9]雷望红.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10]朱天义,高莉娟.选择性治理:精准扶贫中乡镇政权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1).
[11]刘建生,陈鑫,曹佳慧.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6).
[12]谢玉梅,徐玮,程恩江,梁克盛.精准扶贫与目标群小额信贷:基于协同创新视角的个案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6(9).
[13]李洪波.精准扶贫视野下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保障[J].学术交流,2017(4).
[14]黄建.论精准扶贫中的社会组织参与[J].学术界,2017(8).
[15]周黎安.行政发包制[J].社会,2014(6).
[16][德]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M].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7]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J].社会学研究,2009(2).
[18]Gao Jie:Pernicious Manipulation of Performance Measuresin China’s Cadre Evaluation System,The China Quarterly,2015(23).
[19]张文礼.多中心治理:我国城市治理的新模式[J].开发研究,2008(1).
[20]林闽钢,陶鹏.中国贫困治理三十年回顾与前瞻[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8(6).
[21]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J].社会学研究,2006(3).
[22]贺雪峰.税费改革的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23]周雪光.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J].开放时代,2015(2).
[24]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省K镇调查为例[J].开放时代,2011(2).
[25]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J].社会学研究,2008(6).
[26]虞崇胜,唐斌,余扬.能力、权利、制度:精准脱贫战略的三维实现机制[J].理论探讨,2016(2).
[27]North,D.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28][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9]欧阳静.压力型体制与乡镇的策略主义逻辑[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