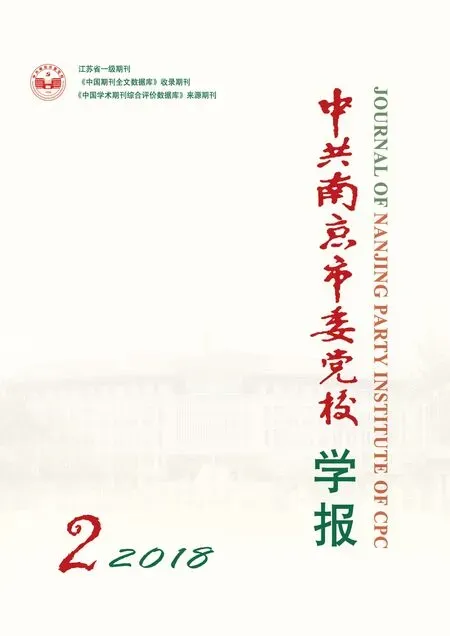深化毛泽东研究与“心理分析”的正确运用*
王 芳
(1.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校区 江苏 张家港 215600 2. 南京大学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毛泽东同志逝世已有四十年了,中国的社会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毛泽东研究的热潮已经退去,理性回归后的研究开始向纵深推进,已经不再是“神话”抑或“丑化”的意识形态狂欢,逐渐变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领域,当前学术界提出了深化毛泽东研究的任务,研究者们引入新的理论资源从微观层面丰富毛泽东的精神肖像。改革开放后,就有国内学者以毛泽东的心态和性格为研究对象,但并不运用心理学的方法。西方学者较早的运用心理学来研究毛泽东,改革开放后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心理分析的方法在毛泽东研究中的合理性得到一定的认可。我国学者开始认为,应该重视人的行为和心理,心理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并不矛盾,心理分析作为人物研究的重要方法在毛泽东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本文在一般的意义上使用“心理分析”的概念,既指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中的方法,又指通常所说的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个性特征。笔者认为,在毛泽东研究中,“心理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和工具需要研究者带着方法论自觉去厘定它的作用范围和结果效力。“心理分析”是史实和逻辑之间的粘合剂,在历史事件的理解、对毛泽东的评价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巨大的运用空间。
一、深化毛泽东研究,把“三种分析”相结合
心理分析经历了自身的理论演变,从对人物一般的心态描述,到运用心理学分析人物的“意识”层面再到挖掘“潜意识”。最初,心理分析方法通常用在对文学作品中虚构人物的分析,深化对人性的认识。从弗洛伊德起逐渐应用于对杰出人物的分析,20世纪初一些心理学家曾提出运用心理学揭示历史生活事件,形成了所谓的心理历史学派:“历史之谜——不在理智之中,而在愿望之中;不在劳动之中,而在爱情之内”。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白鲁恂(Lucian Pye)、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和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H. Soloman)为代表的“心理史学”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毛泽东的心理结构,透视毛泽东本人的“潜意识动机”。国内学者一般是研究毛泽东在决策时的心理状态和性格因素,但大多比较谨慎,认为心理分析应该和丰富的史料相结合。笔者认为,毛泽东研究不是单纯的“人物研究”,心理分析的正确运用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在准确的史实分析、严谨的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展开应用,把三种分析相结合。
(一)史实分析为基础
任何一种有价值的严肃研究都是以真实性和准确性为基础的,如果基础不坚固,理论大厦再华丽宏伟也无法摆脱倾覆的命运。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对中华民族造成了大半个世纪的直接影响了,总结毛泽东的历史遗产仍关乎中国的未来,作为不可回避的意识形态“晴雨表”,毛泽东研究需要具备识假辨伪的能力和史实考据的功力,决不能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西方国家通过污蔑、丑化毛泽东达到反共目的。例如,美国和台湾地区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作者利用曾担任过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的身份,捉刀代笔捏造事实,一些依据这本书中捏造事实的研究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除了这种故意捏造扭曲,在研究中更多的是由于史料的错误收集和使用导致的偏差。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鉴别真伪的能力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区分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注重史料的分类和事实效力层级,注重史料的丰富性及相互之间的互证或证伪。一般来说,史实分析要处理如下几种资料:1. 毛泽东的文稿书信、讲话记录、谈话记录、会议记录,读书批注等。这是直接来源于毛泽东的第一手资料,作为档案保存,是可信度最高的“铁证”。例如,一些学者说毛泽东的“两论”是抄袭苏联哲学著作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也可能是由陈伯达起草、艾思奇补充,毛泽东定稿的。中央党校的许全兴教授通过学术调查、琐细考证和逐字比对驳斥了“抄袭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首次使用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期间大量的电报和谈话记录等,还原了这个事件;陈晋教授通过毛泽东的读书批注考证了毛泽东曾在四个时间段里读过《资本论》,此类史料可信度高,价值大。2. 当事人的回忆录、日记、访谈记录等,特别是和毛泽东有直接接触的当事人提供的资料。这类资料属于间接史料,对于全面、真实还原复杂历史事件作用不可忽视。例如,李锐、黄克诚回忆1959年的“庐山会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争斗”过程等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一些和毛泽东有日常接触的当事人如警卫员、护士等提供了毛泽东的日常生活细节有助了解毛泽东。例如,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了他简朴的生活习惯、读书的浓厚兴趣和他对个人生命的豁达态度。但是,众所周知,当事人的回忆不可能绝对准确,有很多疏漏,需要通过相互印证使用。3. 各种传记、年谱、文集选集、文稿等。这类史料和第1类史料的关系像原件和复印件,是有加工和选择的二手资料,因为原始资料并没有完全开放,各类文集年谱是通过编辑者的筛选的,传记是立传者的研究结论,有时也需要辨析。4. 社会史料。例如报刊资料、社会大众的见闻等。这种史料是间接史料,提供了理解历史事件的生动“氛围”。
(二)逻辑分析为主体
当前,深化毛泽东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一部分学者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引入新的理论资源,在对原有研究进行方法论反思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毛泽东的历史资料逐渐开放,对中共其它领导人、早期代表人物等的相关史料和研究也同步推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日记等也大量面世。在海外,施拉姆、竹内实等学者从多种渠道收集编辑了相当数量的毛泽东资料集。施拉姆就曾感慨,相比过去毛泽东研究苦于资料匮乏,现在的困惑是资料太多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严肃的学者在史实分析的层面上问题不大,一些错误和谣言很容易被推翻。深度研究需要通过这些资料去寻找规律、把握本质,对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做出解释。在史实研究的基础上展开逻辑分析,这将是深化毛泽东研究道路上的主要任务。
逻辑分析有如下几种路径:其一,毛泽东文本阅读模式的方法论自觉。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爆发的几次论战把经验主义“直接阅读”模式的缺陷暴露无遗,施拉姆主张的“客观”“中立”立场遭到了尼克·奈特、保罗·哈里等学者的强烈批判。阅读过程中的“先入之见”是无法主观移除的客观存在,通过文本的表层“事实”还原作者的真实思想面貌是一种误解,停留在经验层面上的阅读是远远不够的。文本阅读模式的转换和方法论自觉是逻辑分析的前提,同时也是逻辑分析的路径。其二,把对毛泽东的人物研究和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毛泽东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人物研究,因为他的思想和实践对整个中国甚至世界都造成了不可替代的影响,研究毛泽东一定要放入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这就需要联系理论和实际、个体和集体、历史和现实等进行逻辑分析。其三,以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史为线索。毛泽东曾向斯诺回忆,1920年以前他的思想还是一个包括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大杂烩,但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思想就再没有动摇过。一些国外学者为毛泽东贴上“唯意志论”、“实用主义”“乌托邦主义”等标签,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结构性改造。
在史实分析基础上的逻辑分析主要是宏观、理性层面的研究,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非理性成分、心理因素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也正是因为毛泽东的特殊地位,他个人心理因素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又很容易被放大,在某种程度上,微观层面的心理分析起到了连接人物和事件、人物和问题、历史和逻辑之间的填充剂,是逻辑研究的延伸和补充。
(三)心理分析作补充
早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外部观察者就给予高度的关注同时表示极大困惑。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使得他在心理学层面“非同凡响”的人格和“自我”无限放大。心理历史学派开创的心理分析研究方法在毛泽东研究得到了大量的运用。例如,白鲁恂在《毛泽东的心理分析》一书中运用心理学术语“自恋”、“边际性人格综合症”等分析毛泽东的心理和行为,把政治事件还原为心理原因、把成年后的经历还原为幼年的原因。“毛泽东处理政治争议的杰出能力,不仅来自于他与父亲成功斗争的经历;而且,在一种更加深刻的心理学层次上,这种动力来自于一种有关其家庭关系的整体性的心理动力机制。”[1]利夫顿用“幸存者”(survivor)概念开创了一个独特的心理分析范式,认为经历了革命、战争、突发事变等非常规事态的“幸存者”往往表现出一种非常规的心态,“幸存者的负疚感”、“不朽象征的模式”拥有特殊的能量。他在《革命的不朽:毛泽东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中用这个心理学范式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一位领袖如果能将这些超验原则灌输给他的拥护者,那么,他就能将最严重的危险与崩溃转变为一种安稳有序的使命感,将最令人瘫软的死亡焦虑转变为傲视死亡,近乎于战无不胜的平静”。[2]台湾学者韦政通所著的《无限风光在险峰》一书在扉页上写道:本书借用人格心理学对人格特质的分类法,对毛泽东极其复杂的性格各层面,作描述和分析。国内学者在研究和毛泽东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时也开始观照毛泽东“微妙的心理变化”。另外,心理分析在对毛泽东评价中也起到相当的作用。在历史心理学家的眼中,大人物如毛泽东提供了研究人性的难得标本。
笔者认为,毛泽东研究中需要心理分析,但是,在毛泽东研究中心理分析如何正确运用急需讨论。极端“化约论”的精神分析是黑格尔所说的“巨大的结果从微小的原因出发”的“常见笑话”[3]。要明确心理分析的作用边界,它只能作为研究的辅助手段,史实分析是基础,逻辑分析为主体,心理分析是前两种分析基础上的补充,在明确心理分析的地位的前提下尝试展开运用。
二、心理分析在毛泽东研究中的运用
毛泽东研究是“问题研究”中的“人物研究”和“个人研究”中的“历史研究”,离不开“人”的因素,因此,心理分析在毛泽东研究中有巨大的应用空间。
(一)在编写毛泽东传记中的运用
大体上说,传记是记录一个人生平和思想的历史。在中国和西方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把传记看作历史学的分支,中国官方历史学的主要内容就是传记。但是从19世纪开始,人们对传记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传记逐渐被归入文学的范畴,作为文学的分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写人的历史涉及人的心理,而心理分析本质上还是一种虚构。但无论如何,由于传记对“真实性”的要求决定了传记这种文类的相对稳定性,历史的真实是所有严肃的传记家努力追求的,但是记录人的历史的真实是相对的。
古今中外大凡优秀的传记作品总是能在叙述人物生平事迹之外描绘出传主鲜明的个性和人格,20世纪以来的传记还要求对传主的行为和思想做出解释,这就决定了心理分析在传记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心理分析是体现人物个性和对人物进行解释的重要手段。随着传记文学的发展和对毛泽东认识的不断深化,毛泽东的传记就不能只罗列他做了哪些事、他是如何的伟大,而且要回答他为什么伟大?他有哪些伟大的人格?他是不是只有伟大的一面?1989年,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翻译成中文至今,再版多次,售出数百万册,成为畅销书。这本传记一个显著特点是关注毛泽东的一些生活“小事”,把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描写,从中可以看出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痕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集体编写的《毛泽东传》是侧重于历史性的“史传”,对准确性和真实性要求极高,但是我们发现这部传记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传记理论的成果,有一定的心理分析。在心理分析的运用上更侧重于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对“毛泽东是如何决策”的进行心理分析,在这部传记中细腻的描述了毛泽东去世之前的精神状态,不同的是,进行心理分析的叙述者并不是传记的编写者而是相关的历史当事人。几乎所有的毛泽东传记都运用了心理分析的手法。除了分析毛泽东在各种活动中“意识”层面的心理外,而且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深入“意识”表层探索“无意识”动因,甚至还有几部作品把毛泽东作为心理学实践的案例进行病态心理学诊断。这样的传记是以对传主的“诊断”为主体,生平记事变成了辅助,这属于西方后现代文化整体语境下的新型传记实验。笔者认为这类传记带有实验性质,对于毛泽东这样的特殊历史人物的分析可以提供一些视角,但不会成为毛泽东传记的主流方向。在毛泽东传记中运用的心理分析相当于“以文运事”,而不能变成在生平中找材料证明毛泽东人格心理的“因文生事”模式。
(二)在理解重要历史事件中的运用
把毛泽东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理解和阅读,需要心理分析,了解他的生活、个性和人格。毛泽东是一个人但又不是普通的人,他的思想、他的活动曾深刻支配和影响了中国和世界,近代中国很多起重大政治事件都跟毛泽东相关,“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期的时候,处于一种巨大的变迁的过程中,这个首领在里边起的作用往往都是很大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4]这就需要对个人进行研究,要研究他的理性的思想层面,也要研究非理性的心理层面。我们发现对毛泽进行心理分析对理解一些历史事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例如,中国共产党在1952年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设想,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一个疑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逻辑结果,直到1950年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坚持这个观点。毛泽东在1950年6月23日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说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在遥远的将来”,主张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但是,1952年毛泽东的这一观点迅速发生变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1958年在毛泽东的支持鼓励下全国掀起了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立志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在大的历史背景下社会过渡、大跃进运动都有具体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因此一些学者怀疑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主要是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或者简单概括为“急于求成”。毛泽东是个人意志十分坚定的人,他确实受到了影响,但斯大林的影响绝不是决定性的,他的急于求成如果从心理分析的视角观察更合理。毛泽东晚年经常表现出对死亡和生命的焦虑,担心“提前见马克思”,1958年12月9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到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笔者虽然不同意利夫顿用“幸存者意识”这样的概念去解释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活动,但他对生命的思考确实影响了他的心态和行动。可以说毛泽东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实现社会主义是他从青年时期就确立的理想,为了这个目标中国牺牲了上亿人民的生命,毛泽东有6位亲人为革命献出生命。1952年毛泽东虚岁60,我国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他能不急吗?社会主义建设搞了几年,中国还是那么“穷”那么“白”,毛泽东的心理是十分焦虑的,他的生命焦虑已经超出了个人的生死,而是对他毕生的理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焦虑。探索毛泽东晚年忧心忡忡的心理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近代中国一系列的历史事件。
(三)在对毛泽东进行评价中的运用
关于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已经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但是,对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和实践进行评价的历史任务远远没有结束,学术界和个人对毛泽东的评价从来没有停止过,有学者曾断言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每隔十年就会掉个头。一直有人认为对文革的否定太不彻底,反思还不深刻,特别是那些在毛泽东晚年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吃过苦头的人带着非常强烈的感情对毛泽东做出否定的极端评价。一些人把毛泽东描述成一个惯用“掺沙子”、“丢石头”、“引蛇出洞”这样的政治手段的阴谋家;一些人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来全盘否定毛泽东,把他晚年的实践都看成是从个人出发的权力斗争;更是有些人直接从心理学角度否定毛泽东,例如,王若水在《新发现的毛泽东》一书中把毛泽东晚年的心态概括为“孤独感、恐惧感和异化感”“没有私人情谊的同志关系”“逞强好胜”等。
我们首先要承认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决不能从其主观动机出发,但是对毛泽东心理准确的分析可以更全面的理解其思想和实践活动,从而帮助做出更客观、更实事求是的符合历史的评价。笔者认为,只要在客观的基础上对毛泽东进行心理分析就可以推翻那些极端丑化和歪曲毛泽东的评价。可以说毛泽东的一生,不管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他从未屈服过,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回忆说,毛泽东是有着相当深邃感情的人。他在临终的日子里健康状况已经十分恶劣了,但也很少在表情上流露出来,但是听说唐山地震百姓遭受了灾难“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5]。晚年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看到电影银幕上出现解放军到城市受到人民热烈欢迎的场面,他“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失声大哭”[6]。这时毛泽东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十分恶劣了,他意识到1976年春节可能是他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没有亲人和客人,只有几个工作人员陪着他,只吃了几口武昌鱼和米饭,他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7]宽慰陪伴他的工作人员。这样的情感多么令人动容啊!怎么能把他说成是没有私人情感的人呢?
在残酷的革命岁月、艰苦的建设时期中,毛泽东从未向任何强敌、任何困难低头。虽然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他的心里始终装着的是人民,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这一点足以否定所有那些污蔑毛泽东、丑化毛泽东的极端评价。
三、余论:深化毛泽东研究,正确运用“心理分析”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具有“超凡魅力”又充满矛盾的人物,单一视角不能完成理解复杂事物的任务,因此,中外学者都提出了“丰满毛泽东的思想肖像”、“精细化解读”、“微观化研究”、“多元视角”这样的一些概念。笔者在本文中提出通过正确运用“心理分析”的来深化毛泽东研究,并不旨在提供现成的答案,只是试图提出一种尝试和可能性,并且界划“心理分析”运用的范围和条件。
首先,“心理分析”要“具体”的运用,避免“抽象”运用。本文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心理分析的概念,既包括对人的意识层面的描述,可以感知的部分,同时包括对不能理解或不愿意承认的“非理性”的解释,作为“潜意识”的部分。心理分斗争是无比惨烈的,析要有充分的依据,例如,在毛泽东私人书信、私人谈话中就有他关于某件事的直接心理活动的表达,我们读毛泽东1966年给江青的信就体会到他当时对林彪以及发动文革的考虑和深深的忧虑,这样的心理分析就是具体的,可以被感知和理解的。需要注意的是开创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领域强调“潜意识”的深层根据,强烈的“化约论”倾向往往使得心理分析变成一种“抽象”的分析。其实,且不说精神分析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严重的批评和深刻的责难,对个人进行“潜意识”的心理分析也并不是可以任意主观臆造的,要求解释的说服力依据尽量多的资料支持。对毛泽东的心理分析一定要放入具体的情境和事件中,反对抽象的分析。例如,在《毛泽东的心理分析》这本书中把毛泽东的种种都追溯为他幼年的经历,其实伟大的人物都有类似的个性特征,在那样的历史时代中甚至是普通人都跟毛泽东有类似的经历,所以,这样的抽象分析注定意义不大。
其次,排除相互矛盾的心理分析。心理分析涉及到人的气质、人格、精神等层面,往往不为人知或不自知,却又有稳定性,这就要求在进行心理分析的时候要注意连贯性,避免和排除前后矛盾的分析。
再次,心理分析要符合事件和人物心理发展的逻辑。我们认为心理分析要具有连贯性,避免矛盾,但并不是要用机械的、一成不变的观点去分析。心理分析是一种微观研究的方法,其研究效用是受到限定的,对毛泽东的心理分析不仅要符合20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外在逻辑,而且要符合毛泽东自身思想和心理发展的内在逻辑,外逻辑和内逻辑要一致。
注释:
①转引自萧延中“在明澈冰山之下的幽暗底层——写在《心理传记学译丛即将出版的时候》”一文
②关于“抗美援朝”学术界一直有些争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的“抗美援朝”(上、下)中引用了毛泽东给彭德怀、高岗、斯大林、金日成等人的电报手稿和一些谈话记录,还原了“抗美援朝”的始末,大概弄清楚毛泽东的决策过程。
③陈晋教授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一文中认为通过毛泽东的读书批画可以证明毛泽东至少在四个时间段里读过《资本论》;东北师范大学的王占仁教授在“毛泽东读《资本论》相关史实考证”中通过大量的资料考证证明毛泽东读《资本论》的详细情况,这些考证可以驳斥那些污蔑毛泽东没有读过马克思著作的言论。
④参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汪东兴著《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⑤魏斐德在《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中把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概括为“唯意志论”;杨炳章在《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把毛泽东的成功和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胜利看成是政治实用主义的胜利;莫里斯·迈斯纳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这本书中把毛泽东的个人思想定性为“乌托邦主义”。
⑥转引自萧延中《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一文,根据萧延中的考证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全文并未公开发表,但毛泽东在《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则清楚地反映这个问题,“讲话提纲”可参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642页,
⑦参见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一书
参考文献:
[1]白鲁恂.毛泽东的心理分析[M].刘宪阁译,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122.
[2]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M]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3]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221.
[4]萧延中.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J].史林,2007,(8).
[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752、2749.
[7]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J].炎黄子孙,19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