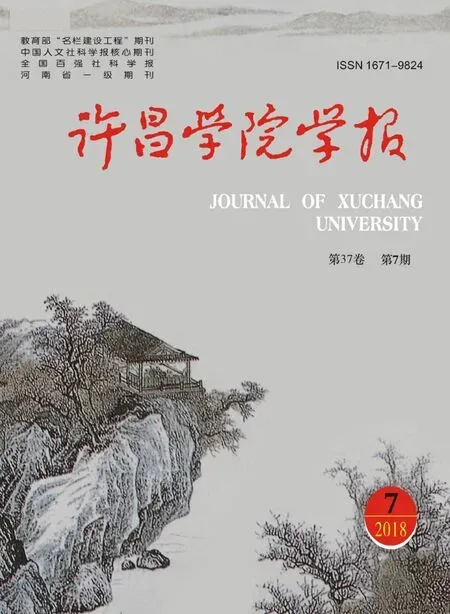司马迁出使西南的时间、路线考
马 宝 记
(许昌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司马迁在《史记》中两次提到出使西南的事情:
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1]3295
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1]1415
巴郡,治江州(今重庆市西北),亦泛指今重庆及其附近地区。蜀郡,治成都(今四川成都)。邛指邛都,粤(亦作越)巂郡治所在地,在今四川省西昌市东南。笮指笮都,沈黎郡治所在地,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北,后并入蜀郡。昆明,在今云南昆明西,后设为益州郡,郡治在今昆明市晋宁区东北。
《太史公自序》此段内容说得非常清楚,司马迁出使时职官是郎中,出使原因是“奉使”“南略”,出使地是巴蜀以南,以及邛、笮、昆明,出使之后回来立刻给武帝复命,复命时间是“天子始建汉家之封”之年,也就是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相关的事件还有,其父司马谈因病留滞周南(洛阳),且病情危重。司马迁回来后也即刻在河洛之间见到了弥留之际的父亲。《河渠书》补充了司马迁西南之行的内容:到了岷山,观察了水利工程都江堰之离碓。
但是,因司马迁没有更加具体地记载奉使出使西南的时间、过程、任务、方法、结果等等诸多细节问题,以至于人们往往忽略了司马迁的西南之行,仅仅以曾经奉使出征西南之语一笔带过,而没有真正认识到司马迁此行的重大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司马迁在鼎盛时期的武帝时代对西南地区民族融合、经济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甚至也没有理解到司马迁这次出使的现实意义,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研究的巨大缺憾。
一、司马迁出使西南的时间、行踪考辨
1.远赴西南的时间、到达的地点
元鼎五年(前112)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叛汉朝。秋,武帝派遣五路大军平定南越王叛乱:“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今云南、贵州境内北盘江及其下游流经广西、广东之红水河、黔江、浔江和西江[2]763),咸会番禺(今广东番禺)。”[3]187《汉书·西南夷传》也记载了同样内容:
及至南粤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3]3841
元鼎六年冬十月,武帝东行到山西、河南,“行东,将幸缑氏(在今河南省偃师市东南),至左邑(今山西省闻喜县)桐乡(乡名,在左邑县),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今属山西)。春,汲(今河南省卫辉市)新中乡,得吕嘉首,以为获嘉县(今属河南)”[3]188。
在平定南越的五路大军中,驰义侯遗为越人,归降汉以后被封为驰义侯。在驰义侯遗的部队中,有一支是且兰军,且兰是夜郎部落成员之一,在今贵州省福泉市等地。这支且兰部队本应跟随驰义侯开赴番禺平定南越,但是,且兰君主担心自己远行之后,旁边部落趁机虏获自己部落的老弱人口,便不再跟随驰义侯远征,而是反将汉使者和犍为太守杀掉,反叛汉朝。且兰平常就经常阻拦在滇道上,对汉朝来说,且兰早就成为通向滇地的障碍。所以,实际上,且兰反叛汉朝,所说担心部落被侵略只是借口,从内心来说,他们并不想真心归顺汉王朝。
南越平定之时,驰义侯遗所率部队尚未发兵。这时,还有一支汉朝部队在西南,这支部队由八校尉带领,本来也是前往番禺平定南越的,但是,南越很快被灭,八校尉所部便停留在西南。
且兰叛乱,武帝下令驰义侯、八校尉所部征讨。《汉书·武帝纪》载:“驰义侯遗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3]188就是在这个时候,司马迁奉命前往,到达的目的地是驰义侯以及八校尉大军驻扎地。
这里有个关键的地点,就是驰义侯及八校尉部所在位置,这个位置也是司马迁的目的地。要判断这个目的地的具体位置,可以参看以下几条史料:
①《汉书·武帝纪》:“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3]187可知驰义侯所带之兵力有“巴、蜀罪人”,还有夜郎兵,夜郎在牂柯江边。
②《汉书·西南夷传》:“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3]3841犍为郡在今四川宜宾西南,南距夜郎不远。
③《汉书·西南夷传》:“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越者八校尉击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中郎将郭昌、卫广引兵还,行诛隔滇道者且兰。”[3]3841这里是“引兵还”,即本来要去番禺,可是没走多远听到了南越被打败的消息,于是便率兵而回。回来的路上,把且兰打败了。说明他们所在的位置是在且兰部落的南面或西南面。
第①②条是同事件的不同记载,可以理解为同一支部队处在同一个位置。而巴、蜀在犍为郡(治僰道,今四川宜宾西南)之北,夜郎在犍为之南,他们要沿牂柯江东下,因此,一个比较合理的理解是,这支部队当时在牂柯江上游、夜郎附近。第③条关键词是“还”,这支部队本来是要和驰义侯的部队会合,其中“巴蜀罪人”应该还是指驰义侯所率领的那一批人。既然不再前往番禺,这支部队就要返回,返回途中顺便消灭了且兰的反叛力量,也就是说,他们当时应该在且兰之南或西南,由南向北而“还”。且兰的西南正是夜郎。所以,驰义侯和八校尉这两支部队当时会合的地点应该就在夜郎附近。这个地点也是司马迁奉旨调动部队要达到的目的地。
综上,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也就是远赴西南的时间是元鼎六年春,出发地点是汲县新中乡,到达地点是夜郎或其附近。因为司马迁是传达军令,所以行走路线应取最近距离,姑设定从河南汲县经长安、汉中,到达蜀郡、巴郡、夜郎。
2.各郡设置的时间及司马迁行踪
且兰叛乱,八校尉部中郎将郭昌、卫广在引兵回还的路上,消灭了且兰,这样,就在且兰部落占据的地区设置了牂柯郡(治且兰县,今贵州凯里西北)。之后,又相继设置了粤巂郡(治邛都)、沈黎郡(治笮都)、文山郡(治汶江县,今四川茂县北)和武都郡(治武都县,今甘肃省西和县南)。
根据《汉书·武帝纪》,武帝于元鼎六年冬十月,发兵征西羌,平之。然后:
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春,至汲新中乡,得吕嘉首,以为获嘉县。驰义侯遗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郡。秋,东越王余善反,攻杀汉将吏。[3]189
由此处时间顺序可知,武帝春天到汲县新中乡,秋天,东越王余善反。平定南越和西南夷,设置南越九郡和西南五郡都在这一时间之内,也就是在元鼎六年春天到秋天,其间,南越九郡设置在前,西南五郡设置在后。
司马迁所云“南略邛、笮、昆明”,应该就是在这些郡设置的时候作为武帝的特派使者跟随在部队中的,其任务就是奉旨设立各郡[4]。据此,认为司马迁出使西南是在设郡之后的观点是错误的,如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考《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郡。史公奉使西南,当在置郡之后。”[5]250
关于各郡的设置,《史记·西南夷列传》云:
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莋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莋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3]3842
最早设置的是牂柯郡,之后,又设越嶲郡,因越嶲郡在南部,离昆明较近,所以,司马迁应该是在设置越嶲郡的时候到达昆明,考察昆明的情况。然后,又设置了沈黎郡、汶山郡和武都郡。
各郡设置的时间也是司马迁在西南地区先后的行走路线。
3.司马迁返回时间
各郡设置之后,司马迁完成使命,开始返回。《河渠书》云“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当为司马迁返回时所为。瞻:《说文》:“临视也。”[6]72说明司马迁是到达了离碓。到离碓的具体时间无可证文献,姑置于此。
考察了离碓之后,司马迁径直返回长安,“还报命”,要给武帝汇报西南夷情况,并参加武帝次年即元封元年(前110)四月的封泰山大典。
司马迁返回的具体时间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记载推断出来。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周南代指洛阳。《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在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缑氏”,缑氏指缑氏县,在今河南偃师市东南。武帝在缑氏下了一道诏令后,“行,遂东巡海上”。然后,“夏四月癸卯,上还,登封泰山”,从正月到四月,武帝从缑氏走到海上,又从海上折回泰山,可见,武帝一直在巡行。周南在缑氏之西,也就是说,司马迁本欲返回长安面见武帝,但是,此时武帝已经向东出巡。司马迁见到武帝时,武帝已经走到周南东面的缑氏,而父亲因病留在周南。
司马迁返回周南之后,是先见父亲还是先见武帝复命,后世学者见仁见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盖史公自西南还报命当在春间,时帝已东行,故自长安赴行在。其父谈当亦护驾至缑氏、崇高(今河南省登封)间,或因病不得从,故留滞周南。适史公使反,遂遇父于河洛之间也。”[5]250祁庆富认为,按照当时礼仪,司马迁应该先面见武帝“还报命”,之后才能去面见病危的父亲:
“报命”在元封元年(前110)。这里有两件事,一是“报命”,一是“见父”,二者孰先孰后?季镇淮先生认为见父在先,报命在后。若果真如此,是违犯封建时代礼规的,因为谙熟君臣之礼的司马迁不会身负君命未报先去见父。司马谈垂危之际仍念念不忘“事君”大于“事亲”,他也不会容许其子这样做。再从自序的行文看,“报命”亦在“见父”前。最大的可能是,司马迁向武帝“报命”后,即去见父。[4]
张大可认为,司马迁“在元封元年四月赶到河洛,受父遗命后上泰山参加封禅典礼”[7]80。
司马迁返回的路线,根据他急于复命、参加四月封禅大典来看,应该是选取最近路线,如从离碓直接奔赴长安,然后到达周南、缑氏。
4.司马迁在西南的停留时间
司马迁从元鼎六年春(姑设为正月*郭宗全《司马迁出使西南任务考》(《历史教学》2009年第10期)认为,“武帝得吕嘉首级与下令征讨西南夷同时,则司马迁出发时间就为春正月”。可参。)出发,到元封元年四月之前返回洛阳。在西南停留前后共计约十六个月。其中,包含着往返路程。
据《续汉书·郡国志》载:“蜀郡,秦置,雒阳西三千一百里。”[8]302“犍为郡,武帝置,雒阳西三千二百七十里”[8]307。“牂牁郡,武帝置,雒阳西五千七百里”[8]311。“越嶲郡,武帝置,雒阳西四千八百里”[8]315。如此遥远的距离,按当时的交通情况,单程也得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另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东汉永平年间(58—75,上距司马迁约200年),益州刺史朱辅上疏称,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其中《远夷怀德歌》有“百宿到洛”[9]2856,白狼就在西南夷,从白狼到洛阳,要一百天,这还是司马迁之后二百年的事情。
即便按照这种速度,司马迁单程也要三个月左右,考虑到司马迁来往都是情况紧急,所以至少也要两个月,往返需要四个月左右,这样,他在西南停留的时间最多是十二个月,即元鼎六年三月到元封元年二月。
在这一年时间里,司马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代表武帝宣谕汉王朝威德,招降纳叛,安抚地方,设置各郡,也就是“征”“略”西南夷。
由此可见,司马迁在汉王朝对西南地区建立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司马迁出使西南的作用与意义
司马迁西南之行,一般不太引人注意,大多理解为奉使游历,而实际上,司马迁此次西南之行意义却重要得多,正如有学者所谓是“负有经略西南夷之任务”[10]。《汉书·东方朔传》云:“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3]2863正是因为这次任务,司马迁也成为和公孙弘等人一样的“奉使方外”“英俊”。
司马迁所云“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是“奉使”“征”“略”。所谓征,一般指军队出征,言以武力胁迫、夺取。在《史记》中,这种意义非常突出,用法也非常普遍。如“秦使章邯将而东征”,“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大臣征之,天诱其统,卒灭吕氏”,“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等都含有使用武力之意。当然,司马迁以朝廷使节的身份出使西南,不可能带有军队,所以,这里的“征”更多的是具有以武力恫吓、威慑、镇抚的意思,司马迁是作为大汉王朝的使节来到西南的,他的背后,是强大的国家,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宣示汉王朝的声威,让西南的少数民族臣服。所以,尽管没有军队,司马迁仍然使用“征”来表示自己出使西南的意图。
所谓略,也有以武力攻取之意,但更强调占领、统治之意。《史记》中往往“略定”连用,可见其意义所在。如“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行略定秦地”,“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略南阳郡,南阳守齮走,保城守宛”,“而遣诸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遂略定楚地”,“陈涉起而王陈,使周市略定魏地”;“乃拜彭越为魏相国,擅将其兵,略定梁地”,“汉二年,韩信略定韩十余城”等。而司马迁有时更是将“略定”与设郡、臣服放在一起:“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厓、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
由此可知,司马迁是带着武帝旨意来“征”“略”西南的,也就是说是宣旨讨伐西南夷、建立地方政权,亦即要设置西南各郡,对西南地区行使行政管辖权。据此,通过《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武帝纪》《西南夷传》等所载征略西南、设置各郡的情况,司马迁出使西南的重要意义主要有:
1.宣谕汉王朝威德,镇抚边疆地区民众,维护国家统一。
在汉武盛世,武帝一直在谋求统治全国、经略天下的盛举,除了征讨尚未宾服的少数民族之外,对于各地企图叛乱的少数民族,汉武帝毫不手软,坚决予以平定。
司马迁出使西南的这段时间,也是汉武帝奋力开疆拓土的重要时期。武帝即位之初,就以强硬手腕应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扰乱。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走,兵还”[3]158。六年(前135),“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3]160。之后,更强化战争手段,屡屡用战争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地区的安定与和平。元狩四年(前119),驱逐了匈奴;元鼎六年,平定了南越叛乱;接着就是司马迁肩负着使命出使西南夷。所以,司马迁这次西南之行,与以前一样,都是武帝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定的重要举措。
2.建立行政机构,巩固国家政权。
汉代中央集权制在行政建制方面的重要体现,就是郡县制。郡县制可以自上而下采取有效的政治统治,防止各地王侯尾大不掉,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司马迁出使西南之前,西南地区已经设立了犍为郡、益州郡,司马迁出使西南时,又设置了五郡,即牂牁郡、粤巂郡、沈黎郡、文山郡、武都郡。“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中郎将郭昌、卫广引兵还,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粤,南粤已灭,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南粤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莋侯,冉駹皆震恐,请臣置吏。以邛都为粤巂郡,莋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3]3842
西南郡县的设立,为汉武帝实施对西南地区的牢固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实施武帝经略大西南计划的重要步骤。
汉武帝十分重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一直不断地采取各种措施维护西南地区的安定,司马迁的出使就是其中的重要一步。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即位,六年,即委派唐蒙出使西南夷,“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1]2994。这是汉中央王朝首次以和平手段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实施统治,尽管仅仅是夜郎周围的“小邑”,而且他们是因为贪图财物才在名义上听从汉朝的管理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毕竟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为以后在西南地区实施统治开了先例。紧接着,汉王朝在元光五年(前130)“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1]2994。“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原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厓、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1]3046。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因为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酋长归降汉朝的目的多是为了钱财,加之距离中央王朝路途遥远,所以他们总是降了反,反了降,反复不定。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司马迁在一年时间内,不但完成了奉旨消灭反叛者且兰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设置了西南五郡,大大提高了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有效控制。
总之,司马迁出使西南,不但完成了汉武帝交付的重要政治任务,还详细考察、记录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分布区域、自然环境、丰富物产,记载了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与汉民族的交往等等,体现了司马迁大一统的民族统一思想,极大地增强了中原文化与边疆地区民族文化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