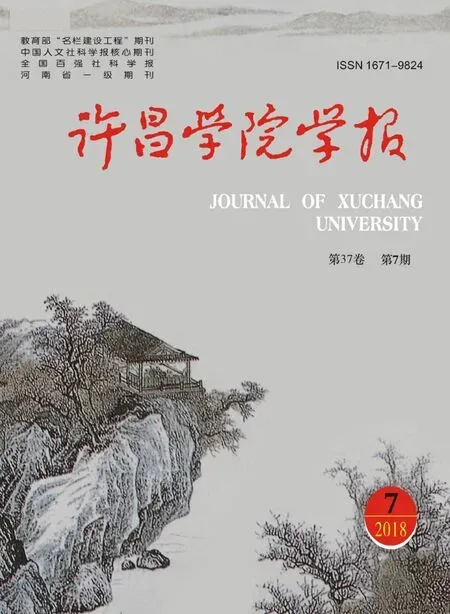仁学的实践品格:《论语》中的工夫论
邱维平, 陈振文
(福建江夏学院 设计与创意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与西方哲学着力于知识论、存有论等不同,儒学的主要旨趣是如何在真实而切近的现实世界中,通过心性的修为、德性的培壅与践履等,使人成为一个伟大的圣贤。这种成圣成贤的过程与方法即是“工夫”,工夫的依据可称作“本体”*此“本体”并非西方哲学所谓的本体,而是本根、本源的意思。,工夫达至的目标则是“境界”。此即儒学之“本体—工夫”的思想模式,其核心是践圣成仁的工夫论。牟宗三先生曾指出:“言工夫,一般人都易以为始自宋儒。其实孔子要人做仁者,要人践仁。此‘践仁’即是‘工夫’……有‘实践’处,便无不有工夫。”[1]81的确,虽然“工夫”一词不见于先秦文献,但无论是“下学上达”“克己复礼”,还是“能近取譬”等,作为儒学奠基之作的《论语》其实处处都在讲工夫,“《论语》一部自‘学而时习之’至‘尧曰’,都是做工夫处,不成只说了‘与点’便将许多都掉了”[2]2820。而这些工夫又决定了后世儒学工夫论的基本内涵与方向,因此探寻《论语》中的工夫论无论对于该著作还是对于后世儒学经典的理解都是不无意义的。
一、人性向善与成仁之目标
谈“工夫论”离不开人性论和道德目标。前者是“工夫论”得以展开的依据,回答“工夫何以可能”的问题;后者则是“工夫”欲至的理想境界,与“工夫”的路径与阶次等息息相关。
在《论语》中,孔子对人性的看法并不明确,其弟子曾感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3]77的确,纵观全书,直接涉及人性话题的只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3]164这句话,但此话至多能说明人是有着共同的人性的,至于是善是恶须结合其他两句话才能得到确切答案:其一,“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3]P86;其二,“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3]96。
第一句中的“直”字意虽然争议较多,不过笔者还是认可程颢“生理本直”的解释,意即人的生性是正直和诚的。第二句则讨论了人性与“仁”的关系。孔子是不轻易以仁许人的。“若圣与仁,则吾岂敢”[3]97?这里的“仁”意指一种终极性的为人向圣的价值准则,相当于“道”。这样的“仁者”境界孔子认为只有伯夷、叔齐等少数人方能达致,自己亦不在其列。因此,“欲仁而仁至”的自信并非说“仁”的境界是可以轻易抵达的,更不是说人人皆想成仁者就可成仁者,而是表明人的生命中本有“仁”的种子,“仁”在生性之中而非在外,这使人心中总有一趋“仁”求“仁”的祈向,故当人“欲仁”即有行仁之愿望时,“仁”便会“至矣”,即能够产生行仁的意志与行动,也就是“为仁由己”[3]125,非由外铄。总之,人人天性中皆有行仁之趋向,皆有想行仁就能行仁的可能性,但人人不必皆为“仁者”,毕竟此种境界是极难企及的。
“性相近也”意味着人有共同的“直”性、“仁”性即善性,但此性在个体生命中的存在是“几稀”还是“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3]305,这是后世顺着《论语》的人性论“接着讲”时的分歧处。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3]274,这微小的存在就是善性,其虽依稀若根芽,但正因有了此“端”,人便能向善求善,“犹水之就下也”[3]304-305。显然,孟子并不认为人性先天地就是全然为善和圆满自足的,而是认为人性中有善的天性,因此有向善的意愿。这其实是一种“人性向善论”[4]55,他将人的道德实践视作将“善”之根芽不断地“扩而充之”,最终实现“保四海”[3]221志向的过程,采取的工夫则是长期的“集义”[3]215“尽心知性知天”[3]327“求放心”[3]312等方式。与孟子之说相异的是宋明理学家的人性论。受李翱“性善情恶”等思想的影响,理学家认为人性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之别。前者是先天本性,乃纯善无恶的;后者是人出生后因秉承阴阳二气的不同而形成的,乃善恶相杂的。理学家实际上是假定人人皆有一种已经完成的、既定的和完满的人性状态,到极端处,便有“满街皆是圣人”的乐观判断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性本善论”。也因此,“复性”就成了理学家“工夫论”的中心内涵,包括“静坐”“格物致知”和“格心”等等,都是为了变换气质,复归那至善无恶的本然状态。
从结构上看,理学家的二分之性似乎最契合“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表述,但如前述,“性相近也”中之“性”并无至纯无缺之意,结合其他行文,无论是对“上知”与“下愚”[3]164的区别,还是对“生而知之者”与“学而知之者”[3]161的划分,都说明孔子不认为人性皆是完满无缺、诸德皆备的,比如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生而知之者”,因为这种人只能是圣人,而圣人则是“吾不得而见之矣”[3]95,实际上是否定了“生而知之者”的现实可能性的。事实上,他认为人性虽是向善的,但却处于远未完成的状态,用后来孟子的表述就是需要不断地“扩而充之”。他因此强调了“人的实践和成善之可贵”,“亦能面对恶的问题以及学习和教育的必要性”[4]248,“工夫”之重要性和复杂性也由此得以凸显。
“学以致其道”[3]176“朝闻道,夕死可矣”[3]70等语句彰显出孔子“工夫论”的目标便是“道”,孟子曾解释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3]259“求道”实际就是“求仁”“成仁”。“《论语》上所说的仁,皆系兼人、己而为言”[5]242。其第一义是“一个人面对自己而要求自己能真正成为一个人的自觉自反”,此即“仁者人也”[3]30,一个欲成仁的人首先要使自己的道德主体挺立起来,此即“立己、达己”。在此基础上,遂产生“不容自已的要求”[5]237,此即“仁者爱人”,此即“立人、达人”。《论语》中的工夫论主要是围绕着这“立己、立人”的成仁之学而展开的。
二、立己之工夫
立己与立人是成仁工夫中相辅相成的两部分:立人须先立己,己立则必欲立人。不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3]125?就重要性而言,成仁的关键在于能否挺立自己的主体性,因此立己是根基与前提,是第一义的。《论语》中谈论了许多关于立己的工夫,其中,“学”“克己复礼”“敬”和“执两用中”尤为重要。
(一)学的工夫
首先,“学”乃孔子成己工夫的第一要义。孔子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生而知之者”,他通向“知”的主要方式便是“学”,所谓“学而知之者”。从“十五而有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3]55-56,其成仁成德主要源自自身的“好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3]78,甚至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与“乐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3]94)。
其次,孔子之“学”在内容、目标等方面都与今人理解的“学”不同。一方面,孔子所学虽然也包括大小六艺(所谓“博学于文”[3]88),但他研习这些文献并不仅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下学而上达”[3]148,“学以致其道”,学文“归根结底在于‘学为人’,在于‘尽为人之道’”[6]15。另一方面,除了指学“文”,孔子之“学”亦指现实的道德实践行为(“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3]51),这些行为甚至是优先于“学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3]51)的。
最后,正如《礼记·学记》所言:“记问之学,不足以为师。”[7]322孔子之“学”并非今人所理解的以对象化方式把握知识,而是与所学相互呼应和遥契的生命与道德之实践活动。“学”乃由“‘效’而至于‘觉’”[6]15,即为学之人通过对范本的效仿而促成自己心灵的觉悟,进而成仁成德的过程。“孔门之学是人生觉悟之学,《论语》中的所有章句都在于启迪人生的觉悟”[6]18,“学”在孔子成己工夫中无疑处于中心地位。
(二)克己复礼的工夫
因“习相远也”的缘故,人总不免有“意、必、固、我”[3]105与“克、伐、怨、欲”[3]140等过与不善,也因“礼崩乐坏”的缘故,人常犯“非礼之视听言动”[3]125之错。因效而觉的“学”更多是通过正面范本对人之行为进行范导,面对人后天形成的私欲与过错等,还须通过“自反自觉”,祛除生理的非理性限制和私欲的羁绊,“追求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5]236,此即“克己”之工夫。“三省吾身”[3]50“内自讼”[3]81“过则勿惮改”[3]52等皆属此工夫范畴。
那么,“克己”与“复礼”又是什么关系呢?众所周知,孔子身处一“礼崩乐坏”的时代,僭礼之事不可胜数,典型的表现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3]129。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人为欲、利所蔽,遂置礼于不顾。正如徐复观指出的:“礼”在孔子已经转化而为人所固有的德性及德性的表征,故表面看是礼之崩塌,实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的丧失。所以“复礼”首先须有人本身的自反自觉,“克己”而成一个不为欲、利遮蔽的人,在此基础上方能够有契合礼乐的行为,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复礼”固然是恢复周礼,但实际上更是“恢复人所固有的德性以显露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总之,正是经由这“克己”而“成人”而“复礼”的工夫过程,人“恢复了作为人之根源的德性——仁”[5]242。这样,“礼”也就获得了其内在的根据即“仁”,从而不再流于形式,恢复其固有的活力与功用。
(三)敬的工夫
作为周人哲学中最关键的概念,“敬”意味着“精神敛抑、集中及对事的谨慎、认真”,在一种责任意识中“凸显出自己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8]15。在孔子时代,其实际是“仁”所涵盖的诸多德目之一,孔子将其独自拈出作为行孝、事上、祭祀等等行为的限定,以免于其流于形式和走向虚伪,从而实现内与外的统一。
敬的工夫被应用在各种情境下:1.行孝。其时人们多以“养”代“孝”,反映出对父母内在情感和责任意识的缺位,因此孔子强调“敬”在行孝实践中的中心地位,认为无“敬”之养无异于犬马之养。2.事上。没有对上下尊卑的真正恭敬,就可能导致犯上作乱的僭越行为,因此孔子认为只有“事上也敬”[3]78,方能维持正常的礼制秩序。3.祭祀。“吾不与祭,如不祭”[3]64,因各种原因无法亲自前往祭祀,因此让人代替,这便只有祭祀之形式,而没有对鬼神真正的敬畏。因此,孔子这句话意指祭祀的真正意义乃心中对鬼神的思念与敬畏。
(四)用中的工夫
“中”意味着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其与“庸”(即“用”)连用,即是“用中”,代表着“至”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3]88)。须注意的是,“中庸”实际上是“永远不可能全然实现在形而下的修养践履中”[6]127的,它只能是一种超越经验世界的虚灵之境,甚至可以说,“国家可均”“爵禄可辞”“白刃可蹈”,中庸亦“不可能也”[3]23。然而,现实中成圣成仁之修习,又无不以“中庸”“所指示的极致情状为祈向”[6]127,从而避免走向过与不及的两极,不偏不倚,合理有度,此即执两用中的工夫。
《论语》中虽然直接言“中庸”的语句不多,但“用中”的工夫却并不少见。概括地说,“用中”工夫大致有以下几种:1.破除执一,以防极端。如描绘孔子仪态的语句:“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3]98固执于一种德行如“温”或“威”,便会偏斜,此之谓执一。这种现象若任其发展,很可能滑向极端乃至对立面。因此,须以“厉”“不猛”来防范与补足,“温而厉”“威而不猛”方合中和之道。此外,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3]66“和而不同”[3]139等都属此种情况。2.兼顾两端,交融和谐。“用中”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二者兼容,相杂适中。“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与质,任何一方占据优势,都会造成过犹不及的后果,只有二者相辅相成,“文质彬彬”[3]86,才能成就为一名君子。3.随时变通,权变执中。正如后来孟子所言:“执中无权,犹执一也。”[3]334执中而不知随时随地权变,则会从“执两”又堕入“执一”的迷误中。“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3]102,此时之“见”、彼时之“隐”,皆为极端情境中的选择,表面上看是执于一偏,实则为最高明的“用中”。
三、立人之工夫
在“立己”“达己”处定有“立人”“达人”,这是儒学区别于老庄以及后来的佛学的最重要特征。那么,如何“立人、达人”呢?孔子曾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3]89这里的“仁之方”主要指前句中“立人达人”的方法与途径。“能近取譬”依照朱熹的解释就是:“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3]89为了论说的方便,可以将此过程分解为“以心揆心”和“推扩”两个步骤。前者是在立人行动前于内心展开的一系列思量、比类活动,后者在本文中不属于心理活动,而是具体的行为,是将己之所欲向外、向他人的推扩过程。
(一)以心揆心的工夫
孔子既云“性相近也”,说明人与人之间具有先天的相似处,但又云“习相远也”,“意必故我”等偏执之心不断添增,导致差异、隔阂逐渐显现。人因此必经“学”“克己”等工夫,弥小我、显大我,重新开启与千千万万他者相互连接的大门。换言之,正是经由立己的工夫,人才得以回到与他者的“心之同然”处,有了一种不容自已之心。于是,“己欲立”便“思随分立人”,“己欲达”则“思随分达人”[9]165,这种“立己达人”的思想便是仁。
不过,由于立人达人之内容皆由“己”所把捉、甄定,因此其所欲立者可能并非他人欲立者,这样立人者不免会犯将自己想法或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所以,在立人行为发动前,须摒弃那种唯我的单一视角,从“己—人”的角度,“自家欲立,知得人亦欲立,方去扶持他使立;自家欲达,知得人亦欲达,方去扶持他使达”[2]690。也就是将心比心,在确认己所欲立的亦是他人欲立的情况下,方能去立人。这其实就是恕之道,“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155,“恕”即“如心”,就是以己心度人心,己所不欲、己所欲而他人不欲,皆不能施于人。通过这样的重重否定,便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立人达人”工夫的客观性和自愿性。
就工夫论来说,“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皆要求人从自我中心的倾向中解脱出来,以心揆心:前者从正面阐述仁者应该做什么,后者则从反面提醒仁者不应该做什么。经由心与心的类似感通与类比,人不仅获得立人的源源动力,亦能在具体的立人实践中变得审慎与理性。
(二)推扩的工夫
经过“以心揆心”的外摄与提撕,己心与人心得以贯通,立己工夫遂以由己及人的推扩方式实现外化。从形式上看,推扩主要通过身教来完成。孔子并非以一种对象化的方式将德性规范、知识、技艺等传授于人,从而使人立或达。而是以身作则,使自己成为他人觉与效的范本,由此实现“立人达人”。比如他倡导“道之以德”[3]55,就不是单纯对他人进行道德教化,而是“躬行其实,以为民先。如必自尽其孝,而后可以教民孝;自尽其弟,而后可以教民弟”[2]547,自己做到孝与悌,他人便能学而习之,所谓“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其他如“为政以德”[3]55“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135等皆属于由身教而立人模式的表达。
从次第上看,推扩依循的是“亲亲—仁民”的路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3]51。立人达人的立足点和出发处是“己”,再按照亲疏关系向外推扩:首先将己之仁推于最切近的父母,此即为孝。接着出门居乡里则推之于兄长,此即为悌。最后再以孝、悌为基础,推之于众人,此即为泛爱。这种以自己为中心向外层层推扩的思想同样体现在“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天下”[3]149的递进式表述中。本质上,这种外推的目的在于涤荡内与外、人与己之间的障碍与阻隔,使仁德流布天下,最终实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同时,己之仁德在推己及人的过程中也获得进一步完善与提升。可以说,虽然立己为根,但若无法外推而立人,则仁德终不免要落空,“若推不去,物我隔绝,欲利于己,不利于人……似这气象,全然闭塞、隔绝了,便似天地闭、贤人隐”[2]690。因此,后世儒家大多重视“推扩”的工夫。比如孟子就认为:“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3]195他还在孔子的基础上,将仁德继续外推到万物,形成“亲亲—仁民—爱物”[3]340的仁爱差序。宋明理学大家如王阳明更是设想每一个个体都能推己及人,从而实现天下万物一体的理想世界。
四、从“志于学”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工夫阶次
上述对《论语》工夫论的探讨主要是从人己、内外的角度展开的,此乃横向、共时层面的工夫要目。若从纵向、历时的角度看,工夫论又体现为孔子一生求仁工夫的不同阶次,即孔子之成圣成贤亦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的实践与体悟中,一步步地成就的。此渐进的工夫历程在《为政》篇的“志于学”章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与充分:自“十有五而志于学”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生命之境界逐渐深化与开显,同时亦是其求仁工夫的不断提升与推进。某种意义上,这章可视为孔子晚年对自己漫长的成仁之路的夫子自道。明朝中后期的一些士人如李贽、刘宗周等甚至视其为孔子一生之年谱,亦非妄论。
在诸多“年谱说”中,顾宪成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作为东林学派的创始人,顾宪成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尤其是在修养工夫方面,他批判当时王学末流的重悟不重修的虚浮空疏倾向,主张修、悟并重。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他不仅将《论语》的“志于学”章认定为“夫子一生年谱”,而且指出其中包含着“不容躐矣”的“入道次序”:“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顺曰从心,证境也。”[10]347在他看来,正是有了十五到四十的矢志不渝之修为,孔子才有五十之“知天命”的跃然一悟,然悟道后的孔子并未止歇,而是继续躬行证道,他的生命最终臻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至境。这样的“修境—悟境—证境”说,虽然理学色彩颇浓,却也简略而精妙地概括了孔子经修而悟再证得的求仁工夫阶次,揭示出孔子学以致其道的圣人本质:“学”的真义是由“效”而“觉”。这与顾宪成在此描绘的由“修”而“悟”的过程并无二致。
当然,由于顾宪成未能详尽说明,其观点留下诸多疑问,最令人困惑的就是他因何判定孔子直到五十方悟道。其实,弄清这个历代学人未予以解决的难题的关键是要明白孔子所悟之道乃立己、立人的“仁”之道。从这个角度看,五十之前的孔子大体仍处于“修”(“效”)而非“悟”(“觉”)的阶段:“立于礼”[3]100“不知礼,无以立也”[3]181,从《论语》中的这些语句可知,“三十而立”即是立于礼。虽然三十之孔子已能在对既有“节文度数之详”又有“恭敬辞逊”之本的礼之精熟中,“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3]100,然其终究须依凭外在的因素(“礼”)而使志坚意定,从而实现身之“立”,这与立于己以及进一步使人立的“仁”之境界是不同的。至于“四十而不惑”,从“知者不惑”可看出“不惑”是对“知者”的恰切描绘。而“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3]110“知者乐水,仁者乐山”[3]87等等论断,都显示出“知者”与“仁者”的区别。盖“知者”即“智者”,指的是对外在的礼等事物的所以然之理能明了、洞察与确信之人,所谓“多闻”“多见”[3]59“博学于文”者也。显然,和“立于礼”时期一样,在此“不惑”阶段,“道德的根源是在外面的,人是由外面的客观标准(此就孔子来说,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3]38)来规律自己的生活”,即孔子仍处于对尧舜、文武的“祖述”“宪章”等“效”的过程中,而未反求诸己,“觉”到自己的道德根源“并非外来而实从内出”[5]253。
那么,为什么说孔子“知天命”就意味着悟道了呢?这需从“知天命”的双重内涵来理解:一方面,命乃数,知天命即知人之定数,即知晓人之能为与不能为的分际。“生死有命,富贵在天”[3]127,生死、富贵等皆有待于人之生存境遇,其得失并非人所能掌控,故“人应在这种地方划一界限,不为这种事情白费心力”[5]251。同时,每个人身上皆有向善之根芽,故完善自我的道德、提升自我的人格等等,是无待于外而人人皆可把握的,因此是心力应该放置的地方。所以,“知天命”即是知自身的德性、人格而非富贵、爵位等,这才是人真正的立足和发力之处。孔子也由此完成了从外在的“多闻”“多见”向内在的“立己”“修己”之学的深刻转换。另一方面,“天命”又指天之所命。“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3]95?“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3]105?这些反问表明,孔子深知人既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在努力“立己”“达己”的同时,理应承担起天地所赋予的不容回避的责任与使命。在当时,便是通过“立人”“达人”的教化活动等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综上可见,天命之知实则意味着孔子“立己达人”之仁学思想的诞生,这一思想正是其自十五“志于学”后孜孜以求几十年方才体悟之道,亦是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所在。顾宪成将“知天命”界定为孔子之“悟境”,实为至论。
必须指出的是,知悟天命不是终点,因为这仍属观念层面的活动,需“一一自家身子上打透,方肯作准”[10]348,即要进一步在身体力行中践履所悟之仁道,此正是悟道之后的证道。五十二岁时的出仕,自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期间的周游列国,以及晚年的教学、著述等,皆可视为孔子对仁道的体证。这种体证虽不再以求悟为目标,但就对精神境界的提撕而言,仍是重要的修为工夫:虽然“道之不行,已知之矣”[3]172,但“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3]69,正是在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证道过程中,孔子不知不觉抵达了“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之证境。处此境界,则己与人、内与外、人与天皆合而为一,万物一体,不存分别,故能“一切听入于耳,不复感其于我有不顺,于道有不顺”[9]28,此之谓“耳顺”;故能“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3]56,此之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之生命,“到此境界,斯其人格之崇高伟大拟于天,而其学亦无可再进矣”[9]29。
诚如顾宪成所言,此修—悟—证之工夫阶次,“亦是千古作圣妙诀”[10]347。后世学者于此当确信圣人可学而至。只是,成圣成贤亦非易事,故“当优游涵泳,不可躐等而进”,故“当日就月将,不可半途而废”[3]56。同时,亦于此当知晓,圣人一生所求,工夫所至,非为利禄功名,而只为成就那立己、达人之仁道!
ThePracticalCharacterofBenevolence:TheTheoryofGongFuintheAnalects
QIU Wei-ping, CHEN Zhen-wen
(College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onviction that human nature is good, the theory of Gong Fu in theAnalects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benevolence-seeking practice of self-realiz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other human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respecting Gong Fu, such as denying ourselves and returning to propriety, holding the two and using the middle and so on, people realize themselves. Through heart-to-heart communication and expansion, people help others to realize themselves. In the view of Confucius's own life practice, the chapter "Principles for Learning" shows the Gong Fu order of practice-comprehension-verification in his lifetime. The reason why Gu Xiancheng judged that Confucius comprehended benevolence until the age of fifty is just because he reached the state of benevolence only after he understood the mandate of heaven.
Keywords:theAnalectsofConfucius; the theory of Gong Fu; self-realization; realization of other humans; order of Gong F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