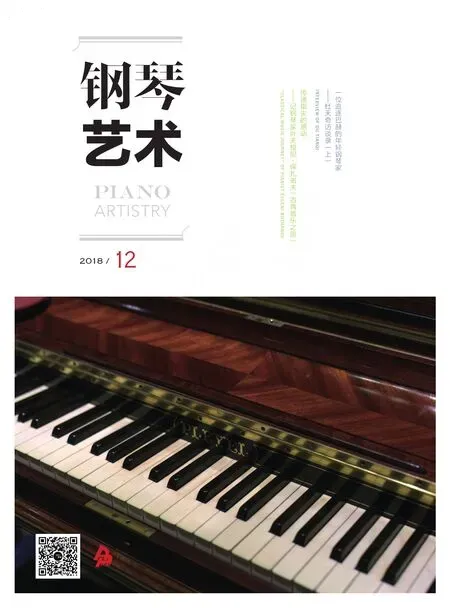一位追逐巴赫的年轻钢琴家
——杜天奇访谈录(上)
访谈者/ 但昭义

访者按:2018年6月9日晚,杜天奇继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巡演之后,如期来到了成都,在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大厅举办了巴赫《哥德堡变奏曲》专场音乐会。灯光熄灭后,舞台侧边的屏幕徐徐展开一段由天奇精心策划并自导的,如音乐会序幕一般的视频,在创造了足够情景氛围的铺垫下,一场“马拉松式”的演奏开始了。场内异常安静,所有的大人和孩子,内行和行外人士都像被磁石所吸引般聚精会神地聆听着,偶尔会传来按捺不住的轻声抽泣。天奇的《哥德堡变奏曲》琴音深深触动着音乐会现场所有的人,我的心也被激荡起层层波澜,眼前升起一片氤氲,浮想联翩。他学琴十数年经历中的不凡——无聊与逃避,挑战与享受,明朗与彷徨,坚持与挣扎,沮丧与期望,充满矛盾过程中的颓废潦倒……那一切的一切混合着我与他同时经历的欣喜、亢奋、期待、失望、疑惑不解、不知所措和动摇放弃等,一幕幕百感交集地涌上心头。
我听过的无数音乐会中,有过多少次的感动和由此带来的激动、兴奋与不眠之夜。然而,如这般噙着未能溢出的泪水听完整场音乐会,赶到后台抱着天奇百感交集地失声恸哭,却是平生唯一一次!
那晚,我给天奇写了一段感言:“感谢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音乐家、钢琴家——杜天奇,给我们带来了伟大巴赫从浩瀚宇宙空间给地球上的人类讲的话。他站在‘哲学与数学,科学与艺术都是在追寻这个世界有序运转的原力量,并试图把它描述出来’的高度,把他对伟大巴赫《哥德堡变奏曲》深刻而充满人性化的近乎完美的演绎带给了我们。”
他的音乐不断撞击心灵,让心灵震颤,回想起曾经共同走过的路(他的琴声为什么能触动并唤起这一切,我不得而知,但却始终不由自主地被音乐所打动,并哽咽着),突然一个念头闯入脑际: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人世,我会呼唤——天奇,无论你在世界的何方,你都要回来看我,为我的灵魂弹一曲令你感动的安魂曲,或那晚令我无比感动的伟大的《哥德堡变奏曲》!
在我看来,杜天奇是一个真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让我怀着巨大的崇敬代表那晚听音乐会的人向伟大的巴赫致敬!向一位没有得过任何大奖却在经历了各种坎坷后,以不懈努力正走向成熟的真正的钢琴家表示敬意!
那晚,我久久不能平静,心里一直思考着:我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让我一反常态?为了给挥之不去的疑团最终寻找到一个出口,我决定对杜天奇进行一次访谈。
坎坷的学习经历
但昭义(以下简称“但”):我们今天的访谈会有很多的内容,出国读书两年,你完全变了一个人,或许现在的你才是真实的你,甚至可以说是经历了不凡回归本真的你。在讨论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之前,我们是否可以一起来梳理一下已经过去了的这段人生,特别是你出国前那段坎坷的学习经历。
杜天奇(以下简称“杜”):好的!
但:你是怎样开始学习钢琴的,当时学琴的感觉怎样?
杜:我是在5岁时踏上了学琴之路,但之前,还有一段曲折的路。妈妈最早是送我去学画画。有一次老师要我们以大自然为主题作画,许多孩子得了100分,而我却是98分。我记得老师说我“昆虫画得比人大,减一分;人比昆虫画得小,再减一分”。那位老师刻板的教学思维令我反感,学习的兴趣顿时被浇灭了。
但:的确!许多孩子的兴趣就是在老师或家长不懂得孩子心理的情况下被消磨殆尽。那你还继续在绘画班学吗?
杜:当然没有!自那日之后我便对画画失去了兴趣。一次下课后路过楼下的电子琴班,妈妈提议说改学电子琴。之后的电子琴集体课,妈妈为了陪我练习,学得非常认真,而我却总是钻空子偷偷地睡觉。无奈,妈妈想了个法子——把电子琴老师请到家中来教我。
老师第一次上门看到家里条件不错,便提出让我改学钢琴,父母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她的建议,随即带我去找贵州师大音乐系的陈雪筠教授求教。陈老师拿起我的手一看,便摇着头说“这个小孩不仅手小,而且还软得跟面条一样!不过,看起来很有灵气”。就这样,陈老师收下了我,我正式走上了学琴之路。
学习钢琴开始对我好像很有吸引力。学琴不久后,陈老师为了进一步激发我的兴趣,便开始安排我参加一些比赛。没想到每次我都能拿奖,而且常常都是第一名,这让陈老师高兴坏了!当然,对我也是极大的鼓励,父母也特别骄傲,并对我学钢琴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但:那时候频频获奖,是否让你爱上了钢琴?
杜:事实上并没有!我属猴,生性好动,爱蹦爱跳,从幼儿园起就以好动出名,交朋友、当班长、与同学打架、带着大家恶作剧,基本上没有安静的时刻。父母送我学艺术的初衷就是让我陶冶情操,能变得文静些。而在当时,要我天天安静下来、专心练琴是一件不堪忍受的事情,我感觉简直就像一种刑罚。所以,每天一到练琴时间我就跟妈妈躲猫猫、捉迷藏,直把她追得满头大汗,招来气急败坏地一顿揍,我才老实地坐上琴凳。只要练琴,我和妈妈“躲猫猫”的“游戏”都会重复上演(笑)。因此,当时为学琴我也没少挨打!
但:既然觉得练琴如此痛苦、无趣,为什么没有选择放弃?
杜:现在想想,倒是也有十分矛盾的心理。我天生就非常享受上台的感觉,享受大家的目光和掌声,而弹钢琴让我获得了比在学校考试拿第一或打架惹事还要多得多的关注。所以,虽然淘气,也没有想过要放弃。更重要的是,妈妈对我学钢琴非常执着,如果没有她的坚持和严苛的陪练(连上厕所耽误的时间都要我必须补上),我肯定就放弃了。

但:我还听说,你认为学文化课太容易了,为了挑战自己才选择难学的钢琴来作为专业,是这样的吗?
杜:其实不是。从小,我的文化课成绩就一直很好,并且特别喜欢看书,因为那时就已经建立起良好的学习习惯,凡事都要通过理解和领悟来弄懂,而通过读书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为我的文化课学习和日后的音乐学习都带来了极大的帮助。“挑战自我”言过其实了。在我的潜意识中,所谓“挑战”更像是一种企望自己与身边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想法。
记得在贵阳一所重点中学读初一时(那时,我从深圳回来,已很长时间没学钢琴了),有一天全校学生做早操,我突然看到自己和一千多名同学穿着同样的校服,听着同样的广播操音乐,做着同样的动作……瞬间感到一种异样的悚然,“清一色”的雷同让我感到害怕——全然丧失个性的“泯然众人”。于是当天我便决定恢复练琴,哪怕因为住校,练琴时间少、条件差,酷暑严寒更艰苦。但比起淹没在“雷同”的人群中,弹钢琴让我如同抓住了一根通向更高、更远、更广阔天空的“稻草”,由此,我为自己找到了必须坚持的动力!
但:啊!那时你多少岁?
杜:十二三岁吧。
但:小小年纪,竟然有这样非同一般的想法,证明你确实是一个有思想的孩子!你这段话让我回忆起当年你刚进深圳艺校时那充满活力和灵气的样子。文化课成绩优秀,热爱音乐,弹起琴来有声有色,生动灵性,非常吸引人,在台上表演时总能博得大家的赞赏。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你刚到艺校那学期的一次音乐会,穿着一套白色燕尾服在台上演奏弗拉迪盖诺夫的《幽默曲》,受到在场师生交口称赞,大家都好奇地问,这是哪儿来的孩子,这么有灵性。当时,我真的很高兴——心想,又有了一个好苗子!你那时对进深圳艺校,举家搬到深圳有什么感觉?
杜:刚进深圳艺校的那段日子,不仅是我少年阶段最快乐的时光,更是我学琴生涯中的一个高峰。赴深之前,我已经在国内外大大小小的若干比赛中获过很多奖了,贵阳的学习环境和教学条件已无法满足我。所以初到深圳,成为您的学生,又有很好的氛围,我就像日渐长大的鱼儿换到了更大的池塘那般自由欢畅。但是,妈妈离家陪我搬到陌生的环境并不是很开心,我能体会她的心情,并从中感受到些许压力。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我初到深圳时那种在最恰当的时间来到了最恰当的地方的欢愉——自我认知的优秀与外界对我的看法相契合给我带来极大的满足感,这使我开始尝试在练琴中寻找乐趣,将看似无聊的东西变有趣,使有趣的东西更丰富,极大地激发了自身的潜能。
但:早就知道你很有思想和抱负,期望与众不同,十几岁就在网上开了博客,还就中国的教育制度写过好些文章?年纪那么小,为什么会对那么深刻的问题进行思考?
杜:我也曾有所疑问。因为看过很多书,那时我就能隐约地感到,也许哲学与文学艺术、绘画、音乐等人文学科之间并没有难以跨越的障碍。可能这只是一种直觉,并没有升成理论认知。我在思考,也许人的智商天赋只是一个因素,而通过不断学习,拓宽加深的知识结构所总结出的对智商天赋的高效运用,才是更重要的因素。这两个因素决定着一个人在学习研究的道路上能看到多大的世界,走向多远的路途。

但:的确,那时你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才气又非常阳光的孩子。当时还有一件令我感到惊讶的事,刚入学不久,我给你整理基础时布置了两首克莱门蒂的练习曲(No.1、No.2)。你回课时不仅技术上完成得不错,而且感觉弹得特别生动、有音乐性。后来才知道你为这两首练习曲写了理解和感悟的笔记,把那两首单纯的手指技巧训练,甚至可以被看作是纯粹机械性肌肉训练的练习曲,加上了富有想象力的生动艺术形象的理解(可惜那些文字没有保留下来)。还有一次,教你们班语文的王晓红老师欣喜地跑来跟我们说,你在作文里为学习格里格那首《致春天》的音乐小品写了一首诗。她表扬你那首赞美春天的诗很有意境、情怀和诗意。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能有那样积极活跃的思维和艺术想象力,让我非常意外。能谈谈那时你怎么会那么自然地把专业和文化学习紧密联系起来,还有那样的主动性把心里的意象用文字抒发出来?
杜:克莱门蒂练习曲和《致春天》的事情我也记忆犹新。正如我前面所说,那时来到新的环境,尝试着练琴时在音乐中寻找乐趣,快乐的挥发着自身的潜能,而这些都是和从小建立的知识结构和学习方法与自身潜能相结合的表现。之所以能写出有趣的练琴笔记,是因为我在那些曲子中看到了音乐的形状,也许那是第一次对音乐有了听觉之外的认知(后来我在巴赫的音乐中也看到这样的形状,而且在他的音乐中这种形状是有含义的)。或许那时我就意识到了音乐的目的性(比如练习曲技术训练意义)并不只是单一或唯一的,或许任何有目的性的作品都能从音乐本身进行解读分析与重新构建。那时肯定是没有这样的理论,但或许有着这样的直觉。可惜的是,那些刚刚开始燃烧起来的对音乐、对钢琴的热爱、憧憬和向往,瞬息间就在之后的假期里熄灭掉了。
但:那年假期回到贵阳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没有再回来?我一直没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现在你已经重新找回了自我,我想知道是什么动摇了你学习钢琴的初心,中断了那么良好的学习状态?
杜:那年放假回家,我邀请了从前的一群同学到家里玩。恰好妈妈接到您的电话,询问我回家后练琴的情况,她随后便对着楼上很凶地喊“杜天奇你琴也不练,是不是不想回深圳读书了”! 我觉得她在那么多同学面前一点儿都不顾忌我的脸面,便非常生气地顶撞道“随便啊,不回就不回啰”! 父母误将我这句话解读成了“我不想回深圳”,并直接告诉了您。当时您跟他们有怎样的沟通,我不得而知,只知道很快他们便为我安排好回贵阳读书的事情了。
但:这点儿小事就让你放弃钢琴了吗,这可不像你做事的风格,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
杜:现在客观地来看,个中确实存在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妈妈对我的气话有故意的误读,因为从内心来说,她无法忍受在深圳的生活,不想再去深圳;其次,一直以来我的文化课成绩很好,他们更希望我今后能考上名校,念“实用”的专业以继承家业;其三,以我孩童的本性,背井离乡在深圳学琴毕竟要比在家乡辛苦很多,也就懵懂地服从了他们。我无法评价这个决定的好坏,但这个结果肯定深切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当然,没有再回深圳还与半年后家里发生的不幸给我心灵上造成的深切的痛苦有关!
但:你刚刚说,回贵阳的那一年多的时间里,你遇到了很深切的痛苦,那是怎么回事?
杜:回去的那一年半里,我直面了爷爷、奶奶的相继过世。这深深地影响了我之后整整十年的生活,直至我开始投入巴赫的音乐,才使我逐渐平复、释怀、转好。
回贵阳后不久的一个中秋节,爷爷在家里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我亲眼目睹了他过世的场景——一个鲜活的生命突然变成了一具冰冷的躯体,让一个孩子第一次意识到死亡的存在!
爷爷走了,我与奶奶原本就无比深厚的情感变得更加珍贵。这时,我更加珍惜与奶奶在一起的时光,那半年里,我们一起健身、逛超市、聊天,谈论我的未来......但是,半年后,我却突然得知她罹患癌症的噩耗!我被家人隐瞒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周才知道这个事实。
奶奶离开人世的那天早上,我从学校赶到医院,家里所有的大人都看着我,他们全都在等着我。因为全家都知道我跟奶奶感情很深,他们在等待我来决定是否要取掉当时奶奶唯一赖以维系生命的呼吸机。我说不,一定要坚持!还去安慰哭泣的家人,告诉他们奶奶一定会好起来……可是,当我看到ICU病床上的奶奶全身插满管子,除了仪器上还存在的生命体征,实际上对外界的一切已全然没有任何反应,经过了一番极度矛盾的斗争,为了解除奶奶的痛苦,在我走出病房的瞬间拿定了主意,悄声而艰难地吐出沉重的三个字“拔了吧”!奶奶就这样在拔掉管子后走了!在办理丧事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没有哭,14岁的我完全想不到这会对我造成怎样深重的痛苦和影响,以至于那天没流出的眼泪,让我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每每想起还会伤心不止地泪流满面,或不可抑制地痛哭起来。整整十多年过去了,我还常常在梦里见到她,还会从梦中哭醒过来。可能大家把我当作家中的男子汉,这是责任的传承。而对于一个孩子,作为奶奶的孙子,这是不能承受也难以释怀的重负。
那之后的十年是我人生中混乱的十年。在直面“死亡”之后,我的内心犹如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为了寄托和填补,我开始读神学、哲学、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希望能找到一些理性的解释来抚平情感的创伤,但事实上我失败了。一方面想努力从阴影中走出来,另一方面却无能为力地继续在迷茫、阴郁和痛苦的黑洞中挣扎。
(一段长时间的静默)
但:在那以后,你还记得你又怎么重新回到深圳艺校吗?
杜:当然!在那个动荡不定时期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我都不会忘记。奶奶去世几个月后,您带着好几个学生来贵阳演出,那是一场为农民工子女的捐赠义演。您见到我时,亲切热情地邀请我说“天奇,你作为本地的琴童代表,也上台表演一首好吗?”那时我已经好久没上舞台表演了,内心非常感激您对我还有着很深的情感,并且我享受上舞台那种快感,所以欣然接受邀请,演奏了我非常喜爱的那首《幽默曲》。
恰恰就是那场演出重新点燃了我的钢琴情结,并且重新回到了艺校学习。但事实上,我的心境并没有从阴郁中走出来,在那灵魂的痛楚没有释怀的情况下,我根本无法集中思想专心练琴,再没有了以前那种积极进取的活力和轻松快乐开掘潜能的动力了。
我常常假想,如果当年我一直留在深圳,留在您的身边,而不是在重返贵阳的一年半里丢掉了令自己神往于音乐的时光,如果我能避开那期间所遭遇到的深切痛苦,或许之后的道路能走得更稳健、更光明,也会更充实快乐。如是那样,或许我早已成为一位钢琴家,一个以演奏钢琴为生命乐趣的音乐家?当然,这种假设是永远未知结果的“天方夜谭”!
但:我当时真不了解你潜藏心底的东西,你外表沉稳得使我们无法窥视你的内心,一切都按常态进行着。学业你依然能完成,唯独没有了往日的灵性,没有了灵性里自然绽放的火花。那时我心里也有纳闷、怀疑不解,这个孩子怎么变了?
杜:对,那时我再也没有研究音乐的心思和倾情表达的欲望。我的生活就像是一摊烂泥,步履维艰。雪上加霜的是,在经过半年高强度的训练后,您带我去日本参加“亚洲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但我竟然在台上突然忘谱,出现严重失误!让我在人生中第一次尝到失利的滋味。之前的钢琴演奏我总以为自己是光芒四射的,从未见过“低谷”的景色,失利的阴影让我更加沉沦。
但:哇!这太可怕了,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你周围的人都全然不知?那时妈妈也陪在你身边的,家里人知道吗?
杜:没有人知道!紧接着我进入了青春叛逆期,开始酗酒、旷课,浓烈地恋爱、激烈地分手,对生活中的每个人都逆反。与此同时,我又看哲学、看心理学著作,写哲学笔记和心理学案例分析,整个人成了一个矛盾体!企望在矛盾中尝试着治愈自己,再往前走。可是,印象中,我却这样纠结地度过了整个高中阶段。
但:听了你讲的这些情况,我很自责,竟没有察觉到你的内心。对你的无助,你周围的人都有责任!幸好,从整个人生旅途来看,你还没有真正偏离基本的方向和轨道,而且,最终回归了正途!
杜:我很感激但老师,是您从未放弃我,一直带领着我学习进步,带我参加一些比赛和演出,虽然成绩不尽人意,但至少在人前、在表象上让我维持着近乎正常的状态。现在看来,在那种情况下能这样挺过来,没有倒下去,已是万幸!(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