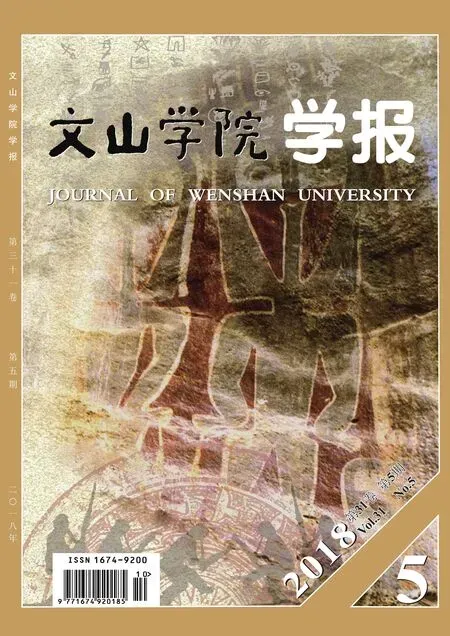鲁迅与余华的死亡叙事比较
冯阿赛
(喀什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未知生,焉知死。”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里,死亡常因其阴森、恐怖、不祥而被排斥于人生视域之外。对待死亡,中国人讳莫如深,避之不谈,企望以此避免灾难与死亡。就文学作品而言,中国文学中自然不乏对死亡的描写,但刻意隐遁的死亡观念和出于本能的心理选择使人们在创作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对“死亡”作出了冷漠的边缘化处理。死亡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抗拒、搁置并淡化,只作为一种情节辅助手段,或为渲染悲剧气氛,铺垫情感祭奠,氤氲感伤情调或为强调作品主题而出现。
一、鲁迅与余华作品中的“死亡”
余华被认为是当代与鲁迅走得最近且是鲁迅精神最有力的继承者,他们都在以反叛的姿态来审视传统文化,敢于对传统的思维定式进行大胆怀疑与颠覆。同时他们都选择以“死亡”为突破口,关注苦难的生命,体察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以寻求生命的意义及世界的本真。
鲁迅生活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堪称二十世纪中国最苦痛的灵魂,他的一生历经过太多的阴冷与黑暗,内心流淌过太多人的鲜血。如他所言,“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1]。鲁迅深刻地意识到,生命的第一要义是活着,因为这,“他才不能忘怀人们的死”[2]。淋淋的鲜血和沉重的尸体成为压在鲁迅身上终生都没摆脱掉的梦魇。日本仙台学医的客观经历和一生经历血雨腥风的双重体验,让他对死亡有着自身独特的精神感受,致使他一生的创作都从未离开过“死亡”主题。
对于同样有着从医经历,从小在医院长大,听惯哭声,看惯死亡的余华来说,与其说他选择了“死亡”,倒不如说“死亡”更倾心于这个喜欢在太平间纳凉的少年。因为对“死亡”的热衷,在当代众多先锋派代表作家当中,余华无疑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以自身对死亡独到的对传统的死亡描写模式进行有力反拨,他开始正视死亡,并以一种冷漠暴力的眼光直逼死亡本身,以精炼纯粹的话语进行死亡叙述,仿佛在为读者精心烹饪一场豪华的死亡盛宴,其在酣畅淋漓一展死亡面目的同时揭露了人性深处最隐蔽、最黑暗的劣根性。可以说,“死亡”在余华的笔下得以成就,余华则因为对“死亡”的迷恋和忠贞而成为继鲁迅之后那个真正“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之人。“叙述死亡”作为他们关怀生命、拷问灵魂的载体,那么在具体书写死亡的过程中又呈现出怎样的异同呢?
一方面,鲁迅和余华都在写“看客”。《药》里夏瑜被杀,与之伴随的是一群看客饶有兴味地咀嚼和赏玩。《复仇》中面对旷野上赤裸全身、持刀对立却“毫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的一对男女,看客们因无戏可看“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失去了生趣”[3]。“看”似乎成为了看客们活着的唯一理由,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在此几乎消失殆尽。看客在“看”的同时又“被看”,在不由自主地选择“吃人”的同时又糊里糊涂地“被吃”。鲁迅在一面批判看客愚昧麻木的同时更是向我们展示了潜藏在看客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暴力欲望以及扎根在其精神荒原里的渴血欲望。
同样,余华也在塑造“看客”。《难逃劫数》中彩蝶整容失败,看客们退场后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不约而同地静候在门外觅寻任何一丝可以玩味咀嚼的乐趣,于是内心潜在的杀戮和欲望使他们在完全“自以为是”的想象中完成了彩蝶“自杀”的过程。更有趣的是,彩蝶一个人的“死亡”似乎时刻牵动着一大群人的激情,一旦有价值的器官都被刺过,只剩下皮肉和骨骼,无法满足他们心中燃烧浮动着的欲望时,他们便会失望地离开。这里“无戏可看”已不足以构成对看客们的“报复”,余华大胆地借助想象的力量为看客搭建可以咀嚼玩味的空间和平台,在揭露人类道德之心与悲悯之情严重缺失的同时,也将“看客”灵魂的麻木空虚与心中膨胀的嗜血欲望在虚妄的想象中发挥到极致,这无疑是对鲁迅“看客”形象的超越与发展。
除此之外,鲁、余在创作中都特别强调命运的意志和力量。人乃宿命性的存在。鲁迅最先意识到几千年封建统治思想对人精神的扭曲和压迫,所以祥林嫂即便捐了门槛,任千人跨、万人踏也依旧没有摆脱受人歧视,被人唾弃,最终惨死街头的命运。而余华笔下,“那些人物总是被注定走向阴谋,走向劫难,走向死亡”[4]。《世事如烟》中的司机,即使算命先生已经告诉他“一只脚还在生处,另一只脚踩进死里了”[5],并为他指明了化解灾难的方法,但他最终还是死于非命。在此,人物对死亡的逃遁似乎已成为对死亡的追逐,潜藏在死亡背后的命运的力量与意志在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大化的膨胀与延伸。一切的死亡都显得顺理成章:这都是命!世界自身运行的规律在命运自由意志的彰显过程中隐约呈现。
同时,人物又都在绝望中倔强地反抗绝望,尽管在死亡面前生命尽显它的虚妄。《坟》意味着死亡,但它同时也是人活过的证明,人走向坟的过程无疑也是主动反抗死亡的过程。《过客》中过客在一片虚妄中倔强前进,只为来自未知的远方的一种声音。正如鲁迅自己一样不惧死亡的威胁,背着因袭的重担,肩扛住黑暗的闸门,一路向前走去。同样,余华《活着》里的福贵,尽管所有的亲人都离他而去,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人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但他依然选择活下去,哪怕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以“活着”的姿态反抗生命的虚无与死亡的荒谬。
二、突发性死亡与长期磨难致死
余华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欲望和命运的产物,是生命最基本的存在形式,自然也就大幅度地呈现出生命存在的神秘性、偶然性以及生命消逝的突发性、必然性及非自然性。据笔者统计,余华小说中的死亡人数高达百余人,其中非正常死亡占绝大多数。尤其在《世事如烟》《鲜血梅花》《第七天》等作品中的人物全军覆没于“非正常死亡”的荒原上。生命像割麦草似的一个接一个突然地倒下去,不禁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惯性心理,对“下一个谁死”在冥冥中产生了期待,似乎死才是人存在的本质与真相,死比生更有意义,更令人憧憬。而残留下来的罕见的生倒会让人平添失落之意,足见余华笔下非正常死亡人数之繁多之密集。同时太多年轻鲜活的生命突然消逝于日常视野甚至在短暂的几天之内就仓促完成其整个的生命历程,不禁让人洞见生命的脆弱无常与悲凉。
相反,在鲁迅的笔下,死亡也并非一件易事,人物在死亡前大都要用尽一生到自己所处的环境里去经历苦痛和磨难。死亡不再是任何制造悬念的工具,而是用来烛照人物真实苦难的一生和倍受折磨的悲剧性处境与命运。作者在对自我灵魂的反省与拷问的同时也引发读者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深思。基于此番考量与艺术表现需要,鲁迅诸多作品中的人物:阿Q由一开始的在未庄受辱,进城谋生到后来走投无路参加革命,再到糊里糊涂被官府捉去当作抢劫案替罪羊以及最后被杀头;祥林嫂一生两次丧夫,唯一的儿子阿毛也被狼吃掉,辗转来到鲁四老爷家做长工也受尽冷落与欺凌,最后不堪精神的重负崩溃而死;魏连殳则从一名年轻有理想的青年到后来“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经历一系列自我毁灭的过程。这些人物都责无旁贷地成为一切叙述的主心骨,他们的行为痕迹从头至尾几乎都毫无间歇,一直延续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些痕迹便自然而然地构成他们漫长悲苦的一生。所以鲁迅笔下中心人物的死亡多被安置在小说末尾,让人物在更充足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里去经历人生起伏,去体会生活百味,尽力展示真实的生命存在和生活状态,引起读者对生命的思考。
三、精神病死与肉体消逝
对于人物的死亡,鲁迅重视的是精神病死,肉体的消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的消亡与毁灭,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祥林嫂一生历尽磨难苦楚,她对死亡的恐惧来源于人死后有无灵魂的疑惑。她在孤寂冷酷的人间感受不到一丝温情,渴望在地狱中见到她的儿子。她一面寻求不到继续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和自身生命存在的意义,另一面又对死后世界恐惧之极,在残忍凉薄的现实环境中处处受排挤,遭欺辱,犹如孤魂野鬼般残喘飘摇。灵魂长期经受如此煎熬摧残,即使还活着,也早已注定了祥林嫂的死定是精神先死后肉体消亡的必然。
鲁迅曾表示“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6]26-27,较于死亡的苦痛,精神的苦似乎更能疼入骨髓。鲁迅一生都致力于通过改造人的精神,拯救人的灵魂,立人而后立国。愚弱的国民,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他通过书写精神之死寻求灵魂的疗救,探索生之道路,追问生之意义。
而余华则热衷于展示肉体消逝和血肉模糊,字里行间无不充斥着血肉的狂欢。余华以异常冷酷的审美心态对人物的死亡体验进行精描细刻式地描摹与呈现,并不遗余力地尽可能恢复暴力所能带来的一切真实场景。在余华的笔下人物只是自己书写死亡热情与意志的表达符号,是自己玩弄于股掌的小偶人,如他所言,“当我在写八十年代的作品的时候……我认为人物就是一个符号而已,我就是一个叙述者,一个作者要求它发出什么声音,它就有什么声音”[7]。《一九八六年》中随着疯子: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抖动了起来,像是在笑,那锯子锯着鼻骨时的样子,让人感到他此刻正怡然自乐地吹着口琴[8]。
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感官彼此默契地配合所呈现出的血腥画面和所产生的审美效果,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叙述者超乎常人的冷漠叙述姿态所引起的心灵碰撞。这是一股真正的叙述上的冲击力,让人领略到的是一种直觉化、感官化的现场力量。余华刻意大尺度大手笔地放大疯子沉溺于对自身肉体施刑时的感官直觉体验,加之其对死亡“情之深切”,以至于完全僭越疯子作为死亡感受主体的地位。余华还认为“人物和河流、阳光等一样,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9],人作为人的权利丧失,相反其身上的物性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成为一切暴力、血腥的化身,将人性黑暗丑恶的真相展露无遗,放大到令人绝望窒息的地步,同时也揭示了理性在非理性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与束手无策。
四、血肉模糊与大悲无声
余华对血腥暴力变态式的痴迷让他在死亡面前表现得异常冷漠,死亡被夸张式地放大,生命显其渺小甚微,荒诞至极,不再让人心生敬畏。在余华充满血腥气的死亡叙述中,人物在他暴君式的统治下行尸走肉般地活,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有自己的思想,甚至失去自己鲜活的肉体与敏锐的感知疼痛的本能。人作为人的基本特性在暴戾的压制下,被语言的利刃剔除得荡然无存,只剩下赤裸的肉体作为人最终的存在形态,只任由恐怖的骨骼和器官在生命尽头作无力挣扎,发出可怜的最后一点儿声响。
在《死亡叙述》中人物的死亡被精雕细刻,“镰刀像是砍穿一张纸一样砍穿了我的皮肤,然后就砍断了我的盲肠。接着镰刀拔了出去,镰刀拔出去时不仅又划断了我的直肠,而且还在我腹部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于是里面的肠子一涌而出……动脉里的血‘哗’的一片涌了出来……我的鲜血很像一棵百年老树隆出地面的树根。我死了”[10]。死亡过程的每一幕都是在如生铁般冰冷的叙述语境中进行,冷酷到“叙述者不是‘人’,而是‘物’,好比一块铁”[11]。冰冷到只听得见肢体破碎、骨骼碰撞的声音,甚至感受不到疼痛,只有冷酷到血液里的麻木和心碎。“我”作为一个人,一个整体被瓜分得七零八落的人,我的死亡表现为各个器官的依次死亡,同时“我”作为死亡感受主体竟可以清醒地叙述我死亡的每一步,并且将这种感受清晰地传达给了读者,这是余华在叙述上带给人的独特的感受和力量,也是他对传统死亡描写的一次超越。
余华不仅擅于书写漆黑的、感官化的死亡体验,而且还关注人“如何死”,即死亡方式的问题。因此他的小说中的人物便乐此不疲地经历各种各样的死亡,历尽种种酷刑:或命中注定走向死亡,或在血腥暴力中惨死,或历尽苦难而死,又或是以荒诞戏虐中误了卿卿性命,令人啼笑皆非,喟叹生之意义何在?
相反,鲁迅则更注重人的现世生活体验及生命过程,所以他很少去关注人物具体是怎么死的问题,而是从细微处入手,哪怕是人物的一个神情,一段独白。“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仅此一个眼神便道出了祥林嫂精神先死后肉体消亡的必然结局;孔乙己,“大约……的确死了”成为他一生的总结和归宿。有时甚至是一个简单的意象就足以对人物的死进行高度凝练地象征:或是一股秋风,一丛杂草,一片荒冢,抑或是签纸上的一个荒诞的画不圆的圆圈,一个人血馒头。将死之寂然悲凉艺术化地展现,成为他的美学。点墨不多,却掷地有声,大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悲壮。
鲁迅更看重死亡背后生命意义的深度挖掘,即使涉及到人物死因,也是出于其背后深层意蕴的考量。启蒙者夏瑜因为革命而被抓被杀;阿Q被糊里糊涂地枪毙,单四嫂的儿子宝儿因一场莫名其妙的病而死,魏连殳患肺痨而死……形形色色的死亡一方面让我们感到生之脆弱,也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的凉薄。夏瑜之死成为一心启蒙民众却反被民众耻笑的一代革命者、先觉者的悲哀。阿Q成为了当时麻木愚昧的国民的代表,其死更是权利迂腐酷虐与人性黑暗扭曲的真实反应。宝儿虽是作为次要人物出现,但他的离去却给了单四嫂心头重重的一击,意味着其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瞬间崩塌。魏连殳的死则不仅仅是对现实生活和黑暗社会的绝望反抗与报复,更是对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潦倒一生的自我嘲弄。与这些死亡所蕴含的人生意义相比,人物以哪种死亡方式终结又能与之相媲呢!
五、死为尽头与亡灵世界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对人类来说,人固有一死,死亡是生命最终的归宿。对于死亡,鲁迅认为“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12]。同时“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6]26-27。它意味着一世苦难的终结,人死了也就没有了苦痛和磨难,所以祥林嫂面对胁迫时毅然决然地选择一头撞在香案上,以一死求解脱。余华则不同,死并非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苦难始终如影随形,并不会因为人生命的结束而结束。
的确,在传统的认知里,死者本应入土为安,让亡魂抵达天堂,寻得一方净土。但在余华的笔下,人死后反而与生者继续纠缠不清,或依旧受难,被嘲弄,或还魂于世,于阴阳两界穿梭,让生者“活见鬼”,自始至终都不得安息。
《现实一种》中山岗被枪毙后尸体在一群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们的一阵谈笑风生中被零割碎剐,成为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医生们的一场盛宴,一次妙不可言的挥霍。《兄弟》中我的继父宋凡平死后因为家境贫穷买不起一具宽敞的棺材,在众人绞尽脑汁都没能将尸体装进棺材的情况下,最终只能砍断双膝,才勉强入棺。《祖先》中祖先死后被自己的子孙后代分食。《在细雨中呼喊》中年轻时威武神气的曾祖父死后,其尸体被祖父当做武器在当铺上演了一场闹剧。在这里,生命本身所具有的无尚的庄重感、崇高感被彻底消解,而人作为“物”的价值似乎已远远超越人作为人的自身生命的价值,怎不令人生悲。在死亡的烛照下,让人看到的不仅仅是肉体的死亡以及死者的被愚弄,更是生者内心的丑恶及其精神世界的虚无与荒凉,继而窥见人性的可悲。
此外,余华笔下,死亡背后是神秘恐怖、诡异奇谲的,于生者同行的亡灵世界,人物常因为对人世间一丝情感的眷恋而还魂于世。《在细雨中呼喊》里在国庆年幼时就已经去世的母亲总是在黎明前无声地走来和儿子说上几句话后又无声地离去。一次竟忘了回去的时间,在听到公鸡的啼叫后大惊失色,竟破窗而出像鸟一样飞走了。《古典爱情》里小姐惠死后还魂,竟与情郎柳生执手相看,一夜缠绵。生命就这样在本该彻底安息的时刻再次“出世”,与生者继续“缠绵”。一反传统“一劳永逸”的死亡观念,打通生死界限,使得死与生好像是一回事,甚至比生之世界更真实。死不再是生的终结,而是另外一种生命形态的再次呈现,它与人之世界比邻,甚至多了几分生机与温情。
六、结语
综上,鲁迅和余华都透过死亡深刻意识到人的丑陋和人性的异化,鲁迅以死作为关注民族命运的突破口,试图以死亡来刺痛国人麻木的神经,引领国人走向新生。而余华则更加冷血,将死亡以不加掩饰的感官化的血腥暴力画面呈现,通过死亡本身来叙述死亡,冷酷到失了分寸,只是一味地打破和消解传统,却没有新的合理的秩序建构。相比之下,鲁迅对于死亡则始终持理性思考,他在揭露旧社会“吃人”的本质,将其虚伪的面具撕得粉碎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建构,“冲破铁屋子”“复仇”“在绝望中反抗绝望”来对抗世界的虚无,寻求灵魂的救助,如此深意是余华的叙述所不能企及的,亦是鲁迅伟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