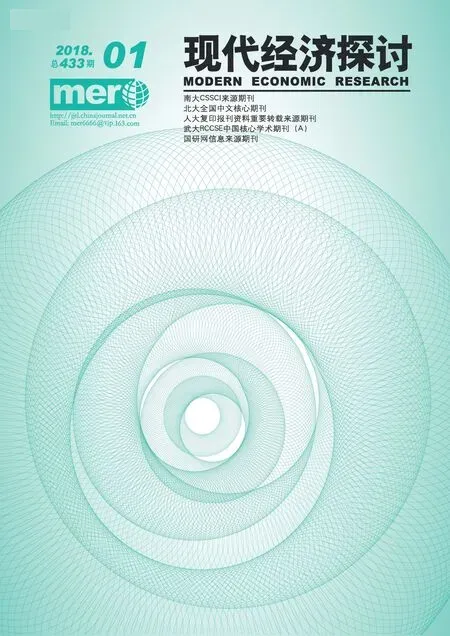中国家庭代际转移的动机作用机制研究*
周佳雯
一、 引 言
中国社会正驶入人口老龄化的快车道。根据国务院《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17.8%左右;高龄老年人将增加到2900万人左右,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老年抚养比将提高到28%左右。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社会保障造成了巨大压力,老年人如何获得养老支持,成为一个紧要的问题。自2009年以来,我国的养老保险扩大到了农村,这进一步增加了养老金支出的压力。除了筹资压力,社会保障体系的管理也面临巨大挑战。社保资金的投资运作、资产管理和风险管理都存在问题,养老体系的可持续性堪忧(Zhou,2012)。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着分配方面的问题,低收入人群所获得的公共转移和补贴相当有限。一方面,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职工之间存在着养老金的巨大差异。在很多经历了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中,下岗职工常常遇到单位拖欠退休金的问题(Cai et al.,2011)。研究发现,1990年代中期的养老金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单位职工的预期养老金财富,从而增加了他们的储蓄率,减少了他们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支出(Feng et al.,2013)。另一方面,养老金制度也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城乡居民的养老金水平差距很大。对于城镇职工而言,养老金制度采用了现收现付制和个人账户的组合。现收现付部分的数额是根据地区所有职工的平均工资来计算的。对于城镇非农和农村居民,养老金包括基本部分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目前基本部分的国家标准每月只有55元。除了保障水平的差异,农村地区的养老覆盖面也低得多。在巨大的单位差异、城乡差异的背景下,老年人成为了养老支持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的教育水平较低,收入水平较低,养老金个人账户部分的缴纳又很少。虽然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可以得到一些公共转移,但数额相当有限。在北京的“低保”计划中,2015年平均转账金额为520元,仅占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的1.66%。
此外,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也面临很大的挑战。一方面,过去若干年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已经大大提高中国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制度的实施,增加了城乡居民的保险覆盖(Wagstaff et al.,2011)。另一方面,这些保险制度主要集中在对住院费用的报销上,门诊费用往往不包括在内,或者只能报销很小一部分。一项针对79个城市的调查显示,医疗费用的平均报销率为45%,在医院实际支出的上限为3万至8万元(Lin et al.,2014)。2008年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显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平均保险率为38.52%,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为26.19%,新农合为45.80%(Zhong,2011)。虽然保险覆盖面在逐渐增加,但目标报销率只有60%,因重大疾病造成的贫困问题在农村地区仍然突出(Liu et al.,2011)。农村居民参加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比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保费率更高,但其立即报销率却较低(Zhong,2011)。大部分老人已退休,不能获得以上三种保险中报销比例比较高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因此老年人在保险方面也处于弱势。另外,由于老年人发病率高,医疗费用也较高,更有可能达到报销上限,他们受到报销政策限制的影响更大。
二、 相关文献及研究
成年子女给老年父母的代际转移可以提供养老支持。这种私人转移为老年人提供的支持,与公共转移有类似的作用。理解老年父母的收入高低对其从成年子女处获得的转移数量的影响,对设计养老保障政策而言,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文献中,这一影响被定义为“转移导数”(Transfer Derivative),用来衡量转移对收入的反应程度。
这种私人代际转移主要有两个动机,即“利他”和“交换”。在利他动机下,转移可能源自支付方对接受方的关爱。例如,Li et al. (2010)使用中国的数据发现,父母对子女的转移存在利他动机。父母通常会向收入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子女提供更多的转移。相反的,成年子女也会为低收入父母提供转移(Becker,1974)。一般来说,老年父母的收入对成年子女的转移的影响为负,也即父母收入越高,转移越少,转移导数为负值。与此同时,成年子女的收入也是老年父母收到的转移金额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例如,Cai et al. (2011)用子女的平均教育程度来衡量老年父母所能得到潜在的转移金额大小。在中国,利他动机有更复杂的含义。首先,宪法规定,父母有义务抚养子女,成年子女有义务赡养父母。如果成年子女未能为父母提供帮助,可能受到处罚。其次,在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下,对老年父母支持显得天经地义,“孝顺”意味着成年子女向年老父母提供资助和照料。因此,部分利他动机可能来自法律的要求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负向的转移导数不一定代表存在真正的利他偏好。
在交换动机下,提供转移的人可能期望在未来获得一些补偿,这包括父母在世时候的馈赠以及离世之后的遗产(McGarry,1999)。因此,有部分文献预测,转移支付金额与老年父母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Cox,2004;Cai et al.,2011)。在这种情况下,老年父母的财富对转移金额的影响可能比收入更重要。为了揭示交换动机,本文需要同时考察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 此外,还可能存在另一种交换动机,也就是“交换服务”的动机。在中国,老年父母为成年子女做家务非常普遍。当成年子女忙于工作或者外出务工时,祖父母通常会照顾孙子女。因此,从成年子女到老年父母的转移可以看作对其所提供的家庭“服务”的交换。本文预测,提供家庭服务的老年父母,收到的转移金额会更大。
传统文献主要集中于区分利他和交换动机(Barro,1974; Becker,1974; Cox,1987;Laitner,1997;McGarry et al.,1995;Ioannides et al.,2000)。在美国,由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公共安全网,私人转移显得微不足道。文献发现转移导数为正也不奇怪。*Cox and Rank (1992)和McGarry(1999)发现了正的转移导数,Cox and Jakubson (1995)和Altonji et al. (1997)发现较小的负向转移导数。对于公共转移水平较低的国家而言,Cox et al.(2004)发现在菲律宾低收入家庭中存在较大的转移导数。中国的公共转移水平位于美国和菲律宾之间,本文预计会存在一个大小适度的转移导数。具体来说,由于中国养老金金额仍然很低,对低收入家庭的公共补贴也相当有限,来自成年子女的转移在对老年人的支持中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
研究也考虑了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的同时存在(Cox et al.,2004),这使得转移大小与接受者的收入之间产生了非线性的关系。当接受者的收入较低时,转移体现出利他动机,也就是说当接受者的收入下降时,转移会增加;但当接受者收入足够高时,即使转移提供者仍然关心接受者,接受者也不再需要帮助。因此,当接受者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转移大小就不受接受者收入的影响,利他动机可能消失。如果接受者的收入足够高,转移的动机可能主要来自“交换”。因此,可能会有一个转移动机从利他变为交换的阈值。
文献中关于中国老年人所接受的代际转移支持的研究非常少。现有的研究主要都是描述性统计分析(White,1998;Shang,1999;Chow,2000;Saunders et al.,2003;Cai et al.,2011)。为更进一步深入讨论中国家庭的代际转移的动机与作用机理,本文着重讨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除了传统的交换动机,本文还考察了“交换服务”动机。第二,重点关注医疗支出在决定代际转移方面的角色。第三,本文采用一个比较新的家庭调查数据,其中包含有关代际转移的详细信息,弥补了其他数据集的许多缺点。第四,本文考察了代际转移的不同组成部分,分别考察了私人转移和公共转移,并比较了来自儿子和女儿的转移的不同。在对转移导数的估计中,本文使用了条件最小二乘法阈值模型,这一模型允许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同时存在。本文将医疗支出加入到对转移导数的分析中,用医疗支出对收入进行调整,以得到更为准确的估计。
三、 数据和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进行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该调查针对45岁及以上的居民进行。CHARLS于2012年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浙江和甘肃两省分别进行了跟踪调查。浙江省位于东海岸,甘肃省是西北地区的内陆省份。浙江省家庭平均收入是甘肃省的4倍多。在浙江,53%的样本居住在城市地区;而在甘肃,这个比例只有33%。本文将45岁以上的受访者夫妇称为“老年父母”,数据中包含了他们收到和给出的转移支付的详细记录,同时也记录了丰富的个人和家庭信息。
在调查问卷中,代际转移包括定期转移,非定期转移和非货币礼品三个部分。定期转移指货币津贴,非定期转移包括节假日、特殊事件(例如生日、婚礼和葬礼)以及紧急医疗情况下所赠送的礼物(红包)。非货币礼品是指实物礼品,礼品的价值由被访者进行估计。转移的提供者也被称为转移网络,典型的转移网络包括三组人:父母,子女和孙子女。其中成年子女是老年父母接受的代际转移的主要贡献者。除了私人转移外,问卷还提供了公共转移的相关信息。公共转移在农村和城市地区有所不同。在农村,公共转移包括农业补贴、退耕还林补贴、五保户补贴、特困户补贴、低保等。在城市地区,公共转移主要是低保、救灾援助、捐款等等。
为了估计转移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本文建立了一个在不同收入水平上有不同反应度(即转移导数)的模型。线性模型不能反映出反应度随收入的变化。对于多项式模型,如果高阶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则不能反映出反应度的变化(后面会用多项式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为此,本文使用条件最小二乘法阈值模型(Cox et al.,2004;Kazianga,2006;Cai et al.,2011)来估计转移导数。这个模型的优点在于,它允许转移导数从利他动机转换到交换动机,且转换的阈值大小可以被估计出来。本文预计,在收入低于阈值时,转移更有可能是利他动机;高于阈值,转移可能是利他和交换动机并存。实证分析的回归方程如下:
Ti=β0+β1min(Ii,K)+β2max(0,Ii-K)+Xiα+ui
(1)
在式(1)中,T是净转移支付收入,即转入和转出的差额,I是转移前人均年家庭收入。下标i表示不同的家庭。K表示阈值,如果K是已知的,则可以通过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本文预期I的系数在K以下和K以上是不同的(分别为β1和β2)。在估计中,本文将K视为未知参数,针对不同的K取值分别估计转移导数,并选择使得模型残差平方最小化的K值作为最佳拟合阈值估计值。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还会使用其他更加灵活的模型进行估计。
控制变量X包括财富、教育、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家庭大小、日常生活能力测量(ADL)、健康状况、健康保险持有情况、子女数量、子女平均受教育程度、子女平均年龄、是否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以及是否照顾孙子女等。由于成年子女的收入和老年父母的收入存在相关关系,本文控制子女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平均年龄,以减少由于遗漏变量(例如子女能力)所引起估计误差。此外,子女性别可能会对转移行为产生影响,本文在回归中控制了是否至少有一个儿子,后文还会讨论与子女共同居住以及照顾孙子女等特征的影响。
本文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老年父母样本的平均年龄为60.5岁,平均成年子女个数为2.79个。样本中47.6%的家庭来自甘肃省,57.1%的家庭居住在农村。本文还设定了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测量(ADL)指标,如果受访者在某项日常活动中遇到大问题,ADL等于2;如果受访者需要一些帮助才能进行这项活动,ADL取值为1;如果不需要帮助,取值为0。ADL数值为六种不同日常活动(即步行、穿衣、吃饭、上厕所、洗澡和大小便自理)的ADL综合平均值,为0.052。大约80%的人在日常活动中不需要任何帮助。样本中有健康保险的受访者占比为90.7%。健康保险覆盖率比较高的原因是农村大多数人都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保险。样本家庭的平均财富约为6.5万元,平均净转移880元,其中代际转移577元,公共转移303元。老年父母平均转移前收入为7750元。有3%的人没有任何收入。跨区域比较显示,浙江省样本的转移前收入比甘肃省高出很多。关键变量转移支付的标准差比较大,约10%样本的转移支付收入为负1000元以下,26%的样本超过正的1000元,5%的样本超过5000元。通过比较代际转移三个组成部分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非定期转移对转移支付额的变化贡献较大。
在文革的十年间,许多学校关闭,当时的青少年和儿童失去了教育机会。本文样本中的一部分老年人可能受此影响,教育、收入和财富都较低。1944年以前出生的人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时已经超过22岁,基本完成了教育,不受文革的影响。 相比之下,1944年以后出生的人的教育很可能受到影响(占全部样本63.1%),本文把这部分人用一个名为“失去的一代(lost generation)”的虚拟变量来代表,在主回归中控制这个虚拟变量。
高昂的医疗费用导致因病致贫问题比较突出。虽然卫生改革大大增加了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但报销水平仍然相当有限。 对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住院服务,报销率在30%-60%左右,上限在3万-5万元左右(Lin et al.,2014)。健康保险不能为医疗费用提供全额保障,特别是花费较大的疾病更是如此。如果本文考虑到那些大额医疗支出,不少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会更低,而转移导数可能会有不同。本文从转移前收入中减去医疗支出,对转移前收入进行调整。对调整后的收入水平,本文进行如下回归:

(2)

对转移导数的估计有几个可能存在的问题。首先,非退休人群的劳动供给可能受到其预期从子女或子孙处得到的转移的影响。如果成年子女非常慷慨地给父母转移,父母可能会减少劳动供给,其具体表现包括较高的保留工资或不尽全力寻找工作。换句话说,转移对收入可能存在负影响,这会使本文的估计有偏。因此,本文根据对就业和生产率的外生冲击获得预测的家户人均收入。
第二个问题是医疗支出可能是内生的,也受到所获得的转移支付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根据健康状况和过去的健康冲击(例如残疾)获得预测的医疗费用。
居住安排可能会影响转移导数。例如,与成年子女同住,可以让成年子女知道老年父母日常消费和医疗状况的更多信息,从而增加转移支付对收入的反应度。虽然本文从数据中观察到的转移是来自那些不与老年父母一起生活的成年子女,但那些与老年父母同住的兄弟姐妹可能与他们分享这些信息,从而增加他们所支付的转移支付对老年父母收入的反应度。在本文的样本中,与成年子女生活在一起的老年父母的比例约为58%。本文将在回归中控制居住安排。 本文还根据是否与成年子女同住拆分样本进行回归,以及将共同居住和转移前收入的交叉项添加到模型中,来分析居住安排的影响。
CHARLS还收集了老年人是否经常照顾孙子女的数据,这一点对了解转移支付的动机非常有帮助。在本文的样本中,照顾孙子女的百分比为29.3%。这项调查没有提供关于被照顾的孙子女的父母的信息。换句话说,本文不能将照顾孙子女的服务与这些孙子女的父母所支付的转移严格对应起来。因此,在考察转移支付对照顾孙子女的反应度时,本文使用了来自所有成年子女的代际转移的总和。与共同居住类似,本文在回归中加入转移前收入与是否照顾孙子女的交叉项。
四、 实证分析结果
本节报告的结果包括运用条件最小二乘模型估计在不同阈值下转移前收入对净转移量的影响。本文分别使用了2012年农村贫困线、转移前收入的第10和第25百分位为阈值。本文将这些结果与估计出来的最佳拟合阈值进行比较。本文还对65岁以上人口、农村、城镇等子样本分别进行了考察。此外,本文还估计了多节点和收入多项式等替代模型。
1.预测收入和医疗支出
如第2节所述,本文采用预测的转移前收入作为转移前收入的替代。这可以减少由于转移对接受者收入的反向影响所带来的偏误。为了预测转移前收入,本文需要收入的外生冲击。本文使用就业冲击(接受者是否下岗、被解雇或关闭自营业务)和生产率冲击(是否残疾、家庭成员是否发生影响日常活动的事故)作为工具变量。这些变量对收入有重要影响,但不太可能与转移支付直接相关。例如,接受更多转移不太可能会增加残疾、发生事故或被下岗的概率。此外,由于冲击主要来自宏观经济政策或者意外事件,它们也不太会和转移支付同时发生变化。
利用类似的方法,本文使用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的冲击来预测医疗支出。本文采用了两个变量,即是否残疾和家庭成员是否发生意外并接受治疗。导致残疾的因素往往是外生的,残疾人更有可能有较高的医疗费用。发生意外和接受治疗的个人也倾向于消费更多的医疗服务,而事故往往是外生的,和转移没有直接关系。本文用预测的医疗费用来调整预测的转移前收入,得到调整后的收入,并用来估计转移导数。
在第一阶段回归中,本文用这些工具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对转移前收入和医疗费用进行回归,得到预测的转移前收入,和预测的调整后的转移前收入,并代入二阶段回归。在二阶段回归中,本文使用自举法(bootstrap)来估计标准误差。表1列出了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第1列显示了对老年父母转移前收入的回归结果。残疾减少了老年父母的收入4260元,下岗、被解雇或关闭自营业务减少收入8152元。第2列显示了对医疗支出的回归结果。工具变量是受访者是否残疾以及他/她是否发生意外并接受治疗。两个变量都显著,其影响大小约为330-350元。第一阶段的F检验值为25.20和11.67,说明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表1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

续表
注:括号中是标准误差。*代表p值<0.1,**代表p值<0.05,***代表p值<0.01。其他解释变量包括省虚拟变量、健康指标、健康保险以及最高受教育程度。
2.转移前收入对净转移的影响
表2列出了使用条件最小二乘阈值模型估计的结果。A,B和C组分别显示了总转移、代际转移和公共转移的结果。转移前收入用医疗费用进行了调整。在第1列中,本文用官方的贫困线(785元)作为转移动机发生变化的阈值。在第2列和第3列中,使用了转移前收入的第10和第25百分位值(-50元和549元)作为阈值。当收入在贫困线以下时,转移导数为负,且在统计上显著。转移前收入减少1元,转移收入将增加0.71元,其中来自代际转移的部分为0.55元(B组)。如果本文选择第10百分位数的收入水平作为阈值,转移导数的估计值更大。这些结果与利他动机一致: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代际转移的反应度很高。使用不同阈值的结果比较也表明,收入水平越低,转移的反应度越大。当转移前收入高于阈值时,收入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统计上显著,其大小大约为0.03,这说明本文没有发现交换动机的证据。

表2 转移导数估计-基本模型结果
注:所有回归中的观测值是1520。括号中是标准误差。*代表p值<0.1,**代表p值<0.05,***代表p值<0.01。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在表中没有汇报。
由于老年父母的收入与成年子女的收入相关,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老年父母收入对转移支付有负影响,同时也意味着较贫穷的成年子女比那些较富裕的子女转移更多。本文对此结果有两个解释。首先,相对于成年子女的收入或财富来说,转移金额相对还是比较小的一个部分,即便对较为贫困的成年子女而言,提供这些转移也不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贫困家庭中的老年父母有可能在抚养孙子女时牺牲更多,这可能产生更强大的利他动机。因此,看到比较贫穷的老年父母从成年子女那里得到更多的转移并不奇怪。
注:括号中是标准误差。*代表p值<0.1,**代表p值<0.05,***代表p值<0.01。BF指拟合数据最佳的阈值。
第4至第6列显示了使用调整后的转移前收入的结果。从转移前收入中减去医疗费用,可以得到家庭可用于消费的实际收入水平。 转移导数的估计值变小,这表明一些转移是由于医疗服务的需求而导致的。
在所有回归中,无论是否用医疗支出进行调整,家庭财富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财富效应的不重要性可以由生育率的下降来解释,因为生育率下降使得家庭资源竞争变弱。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在只有一个子女的家庭中,这个唯一的子女不需要通过竞争就能获得父母给予的转移或者遗产。
表3列出了使用最佳拟合阈值的回归结果。本文列出了所有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标准差。转移导数的估计值大于表2中使用其他阈值得到的结果。第1栏和第2列之间的比较显示,代际转移覆盖率在低于阈值的时候高达77%(=0.760 / 0.986),公共转移仅占23%。在第3列和第4列,在用医疗支出对转移前收入进行调整后,转移导数的估计值变小,结果与表2一致。在其他解释变量中,受文革影响的人群其转移行为并没有显著不同。照顾孙子女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并且在10%水平下显著,这表明给老年父母的转移可能是对照顾孙子女服务的交换。
因为本文有多个工具变量,本文进行了过度识别检验。根据使用所有工具变量对第二阶段残差的回归,本文手动计算了Sargan统计量,即观测次数和R平方的乘积(Wooldridge,2009)。当第二阶段因变量分别为总转移和代际转移时,该统计量等于0.760和0.304,不能拒绝Sargan检验的原假设,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提供了支持。
对于65岁及以上的人群,其劳动供给的内生性并不严重,因为这些人几乎都已退休。表3第5列和第6列显示了对65岁以上人群子样本使用调整后的转移前收入作为自变量的回归结果。由于这些人的教育不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失落的一代”变量不包括在回归中。当转移前收入低于阈值时,收入的估计系数大于全样本的估计结果。收入减少1元,收到的转移将增加1元以上。老年人群的大量医疗支出可能是代际转移反应度变大的主要原因。家庭人均财富在回归中具有正的显著影响。但是,由于财富以千元计量,它的影响程度很小。为了节省空间,从现在开始,本文将讨论集中在通过医疗费用调整后的收入上。
3.农村和城市比较
由于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差异,农村和城市地区的转移导数可能会有很大差异。本文对农村和城市家庭样本分别进行估计。表4的(1)-(3)列给出了城市家庭的估计。转移前收入低于最佳拟合阈值时,收入的系数为负,与利他动机一致。父母收入减少1元,总转移增加0.89元,其中88%来自代际转移。相比而言,农村样本中转移导数要小得多。当转移前收入减少1元,总转移只增加0.25元。这个城乡差距可能是由于生活水平和成年子女收入水平的差异造成的。由于城市生活费用较高,与农村老年人相比,当城市老年人收入受到负面冲击时收到的转移也更多。照顾孙子女变量的估计系数在农村样本中更加显著,这表明在影响从成年子女到老年父母的净转移大小中,照料服务很重要。

表4 转移导数估计-农村和城市样本对比

续表
注:使用最佳拟合阈值,括号中是标准误差。*:p<0.1,**:p<0.05,***:p<0.01。
浙江和甘肃两省经济发展差距较大,本文分别对这两省进行了转移导数的估计。表5列出了估计结果。浙江省转移导数的估计值为-0.86,甘肃省为-0.64。浙江的收入和发展水平比甘肃高得多,这一结果与城乡的比较一致。此外,在浙江,代际转移与总转移的反应度一样大,而在甘肃,37%(=1-0.407/0.643)的反应来自公共转移。这些结果也比较好理解:甘肃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口较多,政府补贴相对比较重要。
4.共同居住、照料孙子女和转移导数
在中国,居住安排和照顾孙子女也是影响转移金额和转移导数的重要因素。
关于共同居住,简单的统计显示,不与任何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父母得到更多的转移,但表3和表4的回归没有发现共同居住对代际转移有显著影响。这个结果并不奇怪,因为居住安排可能与其他变量相关,比如是否居住在城市以及收入水平。接下来,本文根据是否共同居住对样本进行了拆分,并将其与收入变量进行交互。表6第1-2列显示了分样本估计的结果。对于共同居住样本,在低于阈值时,转移前收入对转移具有负的显著影响。对于不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的人,这个影响是正的。第3-5列分别列出了在全样本、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中,共同居住与收入的交叉项的回归结果。对全样本和城市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转移前收入的系数不显著,但与共同居住的交叉项为负显著。这说明共同居住增加了转移对低收入的反应度。由于这些转移来自不与老年父母一起生活的成年子女,所以反应度的提高也说明兄弟姐妹之间可能存在信息共享。总的来说,这些与共同居住有关的结果支持利他动机。

表5 转移导数估计-浙江和甘肃样本对比
注:使用最佳拟合阈值。括号中是标准误差。*代表p值<0.1,**代表p值<0.05,***代表p值<0.01。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在表中没有汇报。
关于照料孙子女,照顾孙子女对代际转移的影响较大,该影响在全样本和农村样本中都显著。例如,表3第4列显示,照料孙子女可以增加代际转移584元,这大约相当于平均转移水平。这一结果对交换服务动机提供了支持:转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老年父母照料服务的交换。在表6第6-8列中,本文加入了照顾孙子女和收入的交叉项。在低于阈值时,转移前收入的系数及其与照顾孙子女的交叉项的系数均为负显著,这意味着照顾孙子女加强了转移对低收入的反应度。这些结果证实了“交换服务”动机。

表6 居住安排、照料孙子女与转移导数
注:使用最佳拟合阈值。括号中是标准误差。*代表p值<0.1,**代表p值<0.05,***代表p值<0.01。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在表中没有汇报。
5.转移网络
子女是给老年父母转移支付的主要提供者。平均而言,女儿比儿子的转移额更少(分别为224和405元)。在中国,受父系家庭制的影响,女儿在婚后往往成为丈夫家庭的成员并且失去了财务独立(Li et al.,2011),因此这一结果是合理的。为了进一步考察转移网络,本文分别估计女儿和儿子的转移导数。表7的A组列出了结果。
第1列估计了至少有一个儿子的家庭的转移导数。转移前收入的系数不显著,这意味着儿子的转移对父母的收入没有反应。但是,在高于阈值时,转移前收入的系数为正,这与交换动机一致。相比之下,女儿的转移对低于阈值的收入非常敏感(第3列),这与利他动机一致。当样本限制在至少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年长父母时,本文得到相似的结果(第2列和第4列)。
表7的B组显示了总转移的估计结果,总转移是代际转移(净转入)和老年父母反向转移给其成年子女的数额之和。结果表明,女儿的总转移对父母的低收入也有较大的反应。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主要由儿子承担父母养老支持的责任。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和法律规定的同等义务,女儿们逐渐承担起赡养老年父母的责任(Zeng,2010)。本文的结果为这一趋势提供了初步证据。虽然儿子平均比女儿提供了更多的转移,但是女儿的转移对老年父母所受到的收入冲击更加敏感。同时,儿子的转移存在交换动机。

表7 比较来自儿子和女儿的转移
注:总转移是代际转移(净转移)和老年父母转移给成年子女转移的总和。括号中是标准误差。*代表p值<0.1,**代表p值<0.05,***代表p值<0.01。
五、 结 论
本文考察了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转移如何受到转移前收入的影响。本文将条件最小二乘阈值模型应用于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成年子女在一定程度上为父母免受低收入和高医疗费用的冲击提供了保障。在使用医疗支出对收入进行调整后,低于阈值的转移前收入的转移导数约为-0.75,这意味着父母收入每降低1元将会多收到0.75元的转移。其中,代际转移是对老年人提供支持的主要组成部分,转移前收入水平越低,反应度较高。这个结果与转移的利他动机一致。仅成年儿子存在通常意义上的交换动机,这一动机不适用于女儿。本文还发现,照顾孙子女增加了老年父母接受的转移以及转移导数,这意味着代际转移存在的“交换服务”动机。
由于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的现象很常见,转移往往通过非货币形式进行,比如向父母提供饮食和住宿。虽然CHARLS调查询问了非货币转移,但只包括实物礼品的信息,缺乏以饮食和住宿等形式提供的转移,这可能导致本文低估转移导数。
虽然本文发现成年子女的转移确实对老年父母的收入和医疗服务需求做出了反应,但有大约32%的收入降低仍然不能被代际转移所弥补。与此同时,公共转移只能弥补其中的7%,这意味着有25%的收入降低得不到补偿。这一发现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医疗卫生改革大大增加了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但因病致贫的现象仍然常见,对高医疗费用、低收入家庭提供更有力的公共支持非常有必要。
1. Cai F,Giles J,Meng X. How well do children insure parents against low retirement income? an analysis using survey data from urban China.JournalofPublicEconomics, 2006, 90(12):2229-2255.
2. Zhou Y. Social welfa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reform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CentreofAsianStudies,UniversityofHongKong. 2000.
3. Cox D. Motives for private income transfer.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 1987, 95(3):509-546.
4. Cox D,and Rank M. Inter-vivos transf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 1992, 74(2):305-314.
5. Cox D,Hansen B,Jimenez E. How responsive are private transfers to income? evidence from a laissez-faire economy.JournalofPublicEconomics, 2004, 88(9):2193-2219.
6. Feng J.,He L. and Sato H. Pension reform and household saving: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 2013, 39(4):470-485.
7. Laitner J. 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erhousehold economic links.HandbookofPopulationandFamilyEconomics. 1997, 1:189-238.
8. Li H,Rosenzweig M,Zhang J. Altruism,favoritism,and guilt in the allocation of family resources:sophie’s choice in mao’s mass send dow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10, 118(1):1-38.
9. Li L. and Wu X. Gender of Children, Bargaining Power and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China,JournalofHumanResources, 2011, 46(2):295-316.
10. Lin W,Liu G.,and Chen G. The Urban Resident Basic Medical Insurance:A Landmark Reform Towards Universal Coverage in China.HealthEconomics, 2009, 18(S2):S83-S96.
11. Liu Y. and Rao K. “Providing Health Insurance in Rural China:From Research to Policy.”JournalofHealthPolitics,PolicyandLaw,2011, 31(1):71-92.
12. McGarry K. Inter-vivos Transfers and Intended Bequests.JournalofPublicEconomics, 1999, 73(3):321-325.
13. McGarry K.,Schoeni R. Transfer Behavior in the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Measurement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within the Family.JournalofHumanResources, 1995, 30:S184-S226.
14. Wagstaff A,Yip W,Lindelow W,Hsiao W. China’s health system and its reform:a review of recent studies.HealthEconomics, 2011, 18(S2):S7-S23.
15. Zhong H. Effect of patient reimburement method on health-care utilization:evidence from China.HealthEconomics, 2011, 20:1312-1329.
16. 江克忠、裴育、夏策敏 :《中国家庭代际转移的模式和动机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证据》,《经济评论》2013年第7期。
17. 徐慧:《转型期农村贫困代际转移、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16年第5期。
18. 陈东、黄旭锋:《机会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收入不平等?——基于代际转移的视角》,《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