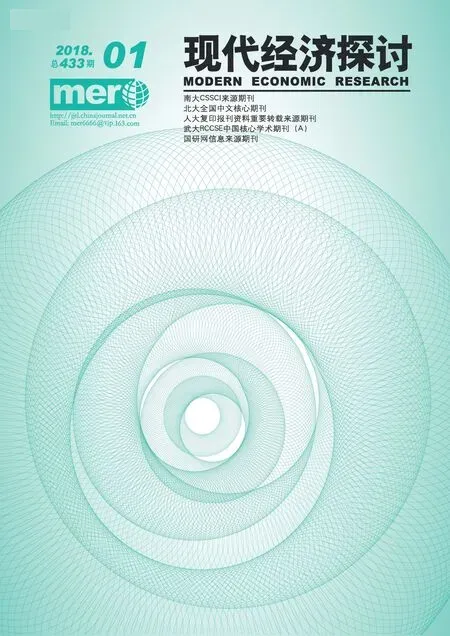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吗?*
唐保庆 韩守习 陈启斐
一、 引 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焦点是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问题(夏杰长,2008;宣烨和余泳泽,2014),服务业规模扩张基础上的结构优化不仅仅反映了服务业自身发展的技术水平和“含金量”,而且是我国实现服务业高端化发展和走向服务业强国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这甚至有助于增强我国在全球服务经济发展中的“话语权”。然而反观我国服务业发展现实却发现,我国的服务业发展呈现出“低端惨烈厮杀、高端严重短缺”的结构性失衡,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供给迟迟无法跟上。因此,我国服务业领域的结构性失衡已经充分展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服务业领域实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注重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甚至应当成为经济结构改革的重中之重。
在影响服务业结构变动的诸多因素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一个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的制度性因素,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非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两大类行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敏感度差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主要受益者会在整个服务业部门中的占比有所上升,服务业内部结构由此得以升级。当然,在注意到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也应当考察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对服务业结构升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由于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通过市场挤出效应和垄断势力效应强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在服务业市场中的既得利益,这不仅会削弱在位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也会降低在位企业的后续创新动力,这反而不利于服务业结构升级。
从上述逻辑来看,知识产权保护是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制度因素,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促使服务业实现结构转型和技术升级的关键“抓手”,更进一步地,只有通过实施“最适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才能够在更大限度上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因此,本文将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并且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整体服务业增加值的比例刻画服务业内部结构,运用“距离指数”和“铁路密度”构建的工具变量进行经验检验;此外,本文还将研究“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潜在阻碍作用,以此寻求意在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
二、 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的文献大多沿着三条路径开展研究:一是运用统计方法分析基于一定标准划分的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变动状况;二是对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进行跨国比较研究;三是运用计量方法研究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
1.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的统计分析
Wieczorek(1995)从就业维度较早研究了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提高,美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在整体服务业部门就业人数中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以年均近1%的增长率上升,这是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重要标志。Langhammer(2008)研究了俄罗斯的服务业结构变迁,发现俄罗斯2000年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的占比相比于1990年提高了7.6%。夏杰长(2008)的研究表明,总量增长缓慢与结构性缺陷两种矛盾相互交织共同制约着我国服务业的增长,重点发展生产者服务业是推动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政策着力点。马风华和李江帆(2014)运用偏离-份额法把服务业结构变动分解为服务业结构合理化和服务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并且认为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比高级化更加能够促进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且“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效应同时存在。上述部分文献较为完整地刻画了我国服务业近年来内部结构的典型化事实,指出了我国距离服务业大国之间存在的明显落差,同时运用“标准化”、“合理化”以及“高级化”等指标对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进行了更加多维的解读,把服务业内部结构的特征事实分析引向深入。
2.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的跨国比较研究
Broadberry & Gupta(2010)比较了印度与英国的服务业内部结构,认为印度在服务业领域的创新资源投入不足是印度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占比落后于英国的重要原因,进而指出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是提升服务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程大中(2008)的研究发现,中国带有较高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本含量的生产者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部门中的占比不足,表现出服务业结构低下的特征,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诚信、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制的约束所引致。李江帆和朱胜勇(2008)运用投入产出法比较了“金砖四国”的生产者服务业结构,发现我国劳动密集型生产者服务业的比重较大,知识密集型生产者服务业的比重偏小,通过提高知识密集型生产者服务业的比重来优化生产者服务业的结构是提高我国生产者服务业竞争力的关键。黄莉芳和杨向阳(2015)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比较了中美两国服务业内部结构,认为我国服务业存在投入服务化程度低和服务业内部结构低端化等严重问题,这是我国走向服务业强国路途中必须突破的关键屏障。这些运用跨国比较所开展的研究基本上都揭示了我国服务业发展内部结构的相对滞后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尽管不同国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了国家之间难以进行直接的横向比较,但是这些研究清晰地刻画了我国在服务业结构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落差,并且为我国的服务业结构优化提供了必要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3.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清晰地认识我国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的基础上,研究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则成为了一个关键点,这对于实施服务业行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裴长洪和李程骅(2010)认为,城市经济转型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系统性的互动过程,提高城市的“经济容积率”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突破性发展是一个协同并进的过程。Evangelista(2013)运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OECD国家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差异,认为制造业的生产率水平直接影响了对高端服务业的需求水平,进而形成了服务业内部结构跟随制造业生产率变动的特征。王智渊和马晶(2014)研究了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与服务业内部结构演进之间的关系,认为服务业专业化集聚能够推动生产者服务业增长快于其他类型服务业增长,由此促使生产者服务业成为服务业部门中的主导产业,有利于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倪红福和夏杰长(2015)基于中国省级投入产出表的定量研究指出,推进城镇化、拉长制造业产业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服务业开放是推动生产者服务业增长以及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突破口。上述研究从各类经济因素、城市发展因素以及服务业开放政策等多元视角研究了服务业行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力,这表明服务业行业结构的升级过程既包含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经济规律,也需要外部政策的配合与推进,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借助于积极的政策推动有利于加快服务业的结构升级。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两点:第一,从知识产权保护这一新颖的制度因素视角研究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这不仅突破了传统的经济因素视角,而且寻找到了与服务品的无形性与高知识属性高度匹配的制度视角;第二,研究“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并且检验我国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是否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理论上的“最适强度”,这对于我国审慎掌控知识产权保护的适宜强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 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框架
从理论上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会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变化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传导机制。下文将分别从线性影响和非线性影响两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
1.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线性影响理论机制
(1) 技术创新效应引致服务业结构升级。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创新者的智慧投入和知识创造,以此确保创新者能够在一定的时期中获得创新活动所产生的经济回报,并且由此塑造鼓励创新、激励创造的良好市场环境(Hodgson,2015)。从知识密集型服务品本身的特点来看,其无形性、高知识属性和低边际成本恰恰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全匹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能够极大地受益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而在整个服务业中的比重得以提高,服务业结构实现升级。首先从无形性来看,服务品的无形性特征决定了此类产品被非法竞争者进行剽窃和模仿的隐蔽性较高,这完全不同于实物商品在遭遇盗窃的过程中需要发生实物商品的空间转移,在此情形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必要性更高。其次从知识属性来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区别于非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主要特点即为知识属性,由于此类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创意、智慧和知识的投入,而这些关键要素又极易被剽窃和恶意模仿,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增长至关重要。最后从低边际成本来看,由于知识密集型服务品的边际成本较低,前期的创新投入一旦获得市场认可,产品的规模提升会不断降低平均成本(Rubalcaba et al.,2016),但是其前提是具备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发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功能。综上所述,知识密集型服务品无形性、高知识属性和低边际成本的特点决定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其快速发展,并且提升在服务业部门中的占比,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
(2) 资源跨国流入引致服务业结构升级。在开放条件下,我国服务业领域正在逐步对外开放,这是我国本土企业从国外优秀服务业企业获取技术溢出的绝佳时机。国外服务业企业的进入决策一方面与东道国开放政策有关,另一方面还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弱有关(Khoury & Peng, 2011)。当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弱时,竞争力较强的国外服务业跨国公司担心其核心技术或专利被剽窃,这会极大地挫伤服务业跨国公司进驻东道国的积极性,也就是说,松散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会导致服务业跨国公司从主观上放弃进入东道国的机遇。不仅如此,随着世界各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断加强,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已经成为全球共识(Woo et al.,2015),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几乎成为各国开展合作的“国际通行证”,一国只有在接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相关条约前提下,甚至还需要与特定国家签署额外的知识产权条约,才可能开展经济领域的合作谈判。从这一角度而言,东道国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很可能导致服务业跨国公司由于受到国家之间经济谈判方面的羁绊在客观上难以进入东道国。所以,我国只有在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够引入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新兴服务业经营模式和专利,并且促使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技术溢出,进而推动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升级。
2.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理论机制
(1) 市场挤出效应阻碍服务业结构升级。在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得到加强的过程中,创新企业不仅可以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以及技术溢出效应获得快速发展,享受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所带来的经济成果,而且还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领域的既得利益者。倘若知识产权保护措施进一步加强,那么新进入市场的服务业企业其创新产品只要与在位服务业企业的产品有些许的近似,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就有可能判定新进入企业存在剽窃或者非法模仿行为,新进入企业将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Maskus,2008)。由此可见,过于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很容易使在位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获得较强的市场势力,并且阻碍了新进入服务业企业的发展,甚至有可能把新进入企业挤出服务业市场。不仅如此,具有进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市场可能性的潜在企业也容易受到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威慑而最终放弃进入服务业市场,这对于需要多元化创新和百花齐放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市场而言极其不利,整个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市场的创新动力受阻。与此同时,由于非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不敏感,或者说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难以阻碍非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这会使得非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市场中的比重居高不下,服务业结构升级受阻。
(2) 垄断势力效应阻碍服务业结构升级。在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下,在位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不仅能够对新进入服务业企业和潜在进入的服务业企业产生挤出效应,而且自身在研发与创新活动中的决策也可能发生变化。对于任何一个企业而言,创新和研发活动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倘若创新活动的预期收益小于创新成本投入,企业通常会放弃创新。在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条件下,由于在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较小,延续现有的经营模式依然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也就是说,在位企业无需从事具有一定风险的创新活动也能够获得较好的成长,因此其进一步研发和创新的动力趋于弱化。由此,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一方面导致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市场内部的创新资源长期无法得到补给,另一方面导致市场外部的创新资源无法进入,这自然会阻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服务业部门中占比的提高,不利于服务业结构升级。
四、 经验检验模型与工具变量设计
1.计量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IPR)作为计量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主要考察该变量的回归系数。同时在模型中纳入由现有研究文献识别出的影响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其他诸多变量,以尽可能确保计量模型的一般性和核心解释变量的外生性。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Upgradingi,t=β0+β1·IPRi,t+β2·Humani,t+β3·Marketi,t+β4·Openi,t+β5·Path_depi,t+μi+λt+δi,t
(1)
其中,Upgradingi,t表示服务业结构升级,IPRi,t表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Humani,t表示人力资本水平,Marketi,t表示市场化程度,Openi,t表示开放度,Path_depi,t表示路径依赖,μ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λ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δi,t表示随机扰动项。


(2)
从理论上来说,由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能够受益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因此在位企业很可能会通过各种途径推动政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服务业结构升级之间很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这自然会导致计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我们综合运用OLS和2SLS方法进行估计,从地理因素这一外生因素构建工具变量(在下文做详细说明),同时为了做稳健性回归,我们运用了N-1变量方法,即除了某一省份以外的其他省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平均值及其平方项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而开展2SLS估计。
2.变量说明
(1) 服务业结构Upgrading。本文首先把服务业各行业按照要素密集度划分为知识密集型和非知识密集型两大类,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反映服务业的内部结构状况。本文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业。数据来源于各省(直辖市或自治区)的历年统计年鉴。
(2)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IPR。我们借鉴韩玉雄和李怀祖(2005)的方法,以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实际执行效果乘以G-P指数,其结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强度。考虑到本文所运用的省际面板数据特性,我们主要基于各省份的非服务业人均GDP*非服务业人均GDP由人均GDP减去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得到,该指标不同于韩玉雄和李怀祖(2005)的人均GDP指标。之所以我们对此有所调整,主要是考虑到非服务业人均GDP中已经扣除了服务业增加值这一成分,这就能确保计算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时不会引入内生性。、成人识字率、律师比例、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时间以及是否为WTO成员等5个计算指标作为实际执行效果的计算依据,对于前面三个指标,各省份的数据并不相同,但是对于后面两个指标,由于各省份都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其数值是相同的。*由于该指标的计算过程十分复杂,具体过程在此省略并且备索。该指标所涉及的数据来自于各省(直辖市或自治区)的历年统计年鉴、教育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律师年鉴》。
(3) 人力资本水平Human。从理论上来说,人力资本是开展创新活动的核心要素,尤其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这类以智慧和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产业而言,人力资本更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考虑到数据采集方面的问题,本文采用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法表征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具体而言,我们设定小学教育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和中专为12年,大专及以上为16年。该指标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4) 市场化程度Market。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主要通过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来促进创新资源流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领域,进而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中国市场化指数》全面刻画了我国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动态变化,我们直接从中获得市场化程度的数据。
(5) 开放度Open。一国开放度越高,国内企业越容易获得国外R&D溢出,本文用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除以GDP反映开放度。从理论上来说,对服务业发展产生影响的开放度应当用服务品进出口总额或者服务业FDI除以GDP表示,但是我们考虑到,用“服务品进出口总额(服务业FDI)/GDP”表示开放度可能会导致控制因素过度这一计量方法问题,因为前文在阐述IPR影响服务业结构升级时,其传导机制包括服务业跨国公司是否会在特定IPR强度下进驻中国,因此我们改用“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GDP”表示开放度。数据来源于各省(直辖市或自治区)的历年统计年鉴。
(6) 路径依赖Path_dep。从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实践的必要性来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通常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投资规模和领域也具有一定的惯性,以避免政策的频繁切换所引发的经济波动和就业不平稳,这使得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征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从逻辑上来看,路径依赖也会影响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演化,并且熨平其他冲击服务业结构变动的因素所带来的剧烈影响。我们在此用被解释变量服务业结构的滞后1期项反映路径依赖的效果。
3.寻找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工具变量
对于中国而言,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际上产生于改革开放时期,而且这一时期制度构建的初衷是源于1979年的中美贸易协定。此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尤其是建设经济特区和设立沿海开放城市等重大举措更是把市场经济推向了新的高潮,建设经济特区和确立沿海开放城市实质上是要在更大的自由空间里实现由市场来主导资源的配置,激励创新和鼓励个人理念、创意的自由绽放成为了时代的主题曲,这些特定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人们重新审视技术、创造和创新的内在价值,也引发了人们对技术、专利、个人财产进行保护以及建立产权制度的深入思考。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是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特殊经济区域,它们在作为经济“试验田”的同时也承担了法制“试验田”的任务,其司法质量和契约执行效率均高于其他地区(黄玖立等,2013)。因此,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对于当地以及全国后期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也为本文寻求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工具变量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启示。
本文借助于各省份分别到北京、5个经济特区以及14个沿海开放城市共计20个城市(地区)的最短空间距离(下文简称为“最短空间距离”)构造“距离指数”(Distance Index,DI)*5个经济特区分别为:深圳、海南、厦门、珠海和汕头,14个沿海开放城市分别为: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具体的构造方法详见下文。,为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工具变量奠定基础。其理由是,5个经济特区以及14个沿海开放城市是中国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最为充分的地区,是经济活动最具有创新活力的地区,也是推崇依靠个人能力创造社会财富的地区,因此这些地区的企业和个人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具有较为前沿的认知。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是各项政策与制度的发源地,在获得重要信息方面以及在贯彻国家的意志、战略方针等问题上都要领先于国内其他区域,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真正推进也比普通地区更加坚定。因此,某一个省份的最短空间距离值越小,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有可能越高,故距离指数与各省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此外,服务品一度被认为不可贸易品,即使某一省份离经济特区或者沿海开放城市的距离较短,该省份的服务业也很难得益于临近经济特区或开放城市的快速发展。因此,距离指数也满足外生性要求。
对于距离指数的计算,我们借鉴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的“海外市场接近度”的计算方法。由于本文的数据样本为包含了时间维度的省际面板数据,但是上述构建的距离指数是仅仅随横截面而变化、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选取一个随时间变化的、能够反映距离指数涵义的外生变量与之相乘。为此,我们选取第t-1年的“铁路密度”这一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与距离指数相乘得到既随横截面而变化又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作为第t年的工具变量。铁路密度是指从某一省份到离其最近的20个地区(具体包含北京、5个经济特区以及14个沿海开放城市)途中经过的所有省份的铁路密集度。由此我们得到IVi,t=DIi×railwayi,t-1这一工具变量,铁路里程数据来源于《中国交通运输统计年鉴》。
本文接下来将运用1997-2015年27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由于受到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我们删除了贵州、西藏、甘肃和新疆等4个省份的样本。。
五、 检验结果与分析
1.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总体样本检验
从表1的结果来看,知识产权保护显著促进了服务业结构升级,这一结论在表1的5个回归方案中都成立,拟合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推动我国服务业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进而实现结构升级的重要政策举措。前文的理论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以及资源跨国流入效应等渠道促进服务业的结构升级,这与Woo et al.(2015)的研究结论相似,他们认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激励创新和资源跨国流入渠道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对于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而言,创新驱动和进一步开放是推动经济战略转型的关键,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则是我国重大经济战略在服务业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实施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变革源头。
2.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分地区检验
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资源禀赋特征等因素决定了地区间的服务业内部结构存在差异,而且各地区由于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执行力度不同会深刻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强度差异。因此,本文接下来以东部地区作为基准组,通过加入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虚拟变量的方法进一步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地区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表2中的回归方案(1)显示,Central和West变量均显著为负,说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服务业结构升级方面显著落后于东部地区,从逻辑上来说,这可能是由各地区的产业传统、各类要素禀赋以及开放性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回归方案(2)-(5)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回归结果十分稳健。各回归方案还显示,IPR*Central和IPR*West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服务业结构升级方面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两个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均远远低于东部地区,通过计算发现,在样本期间内,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平均强度比东部地区低75.4%和82.8%,中西部地区过于松弛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两个地区服务业结构升级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而且拉大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我们通过进一步考察还发现,由于IPR*Central和IPR*West的回归系数均为单独相对于东部地区这一基准组而言的,对两个回归系数进行比较之后发现,在中西部地区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中,西部地区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效果比中部地区更差,其中的原因也在于西部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弱于中部地区。为了严谨地比较知识产权保护对中西部地区服务业结构升级效果的差异,我们以中部地区为基准组,设定西部地区虚拟变量进一步回归,回归结果同样证实了上述结论,即由于西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弱于中部地区,其服务业结构升级效果差于中部地区*由于受到篇幅所限,我们省略了此处的拟合结果。。

表1 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总体分析)
注:表中的OLS回归中之所以选取固定效应模型(FE)是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所确定;***、**、*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内的数值为拟合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内的数值为检验统计量的p值。
3.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检验
本文的理论研究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资源跨国流入效应等渠道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市场挤出效应和垄断势力效应阻碍服务业结构升级,因此“最适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最大限度地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平方项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并且计算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最适强度”。结果见表3。
表3的结果显示,IPR的拟合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说明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同时,IPR2的拟合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服务业结构升级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特征,即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初始阶段,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正向促进为主,进入后期阶段,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反向阻碍为主。在表3的五个回归方案中,每一个回归方案都可以计算出一个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为了降低测算误差,我们取5个回归方案中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的平均值,即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2.818时,其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达到最大。根据样本期间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2015年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强度为0.776,远远低于2.818这一“最适强度”,这表明我国目前仍然处于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阶段。当然,需要警惕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并非越高越好,超越发展阶段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反而不利于经济目标的实现。以美国和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对我国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出了诘责,并且通过相关的谈判要求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但是本文的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确定应当以该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目标作为重要参考依据,一味地满足发达国家和地区提出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反而会对自身的经济发展形成阻碍,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制定适宜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供了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

表2 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地区差异分析)
注:同表1。

表3 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非线性分析)
注:同表1。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变量(IPR)是本文最核心的解释变量,为了检验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有必要运用其他测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指标做稳健性检验。为此,我们总共选取了3个不同的IPR指标,具体为: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数据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标(记为IPRWGI)、加拿大Fraser机构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标(记为IPREFW)以及樊纲和王小鲁历年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标(记为IPRFan)*由于本文的样本期间为1997-2015年,IPRFan的最新数据只更新至2014年,所以2015年的缺失数据是基于1997-2014年的数据运用回归方法推算而得到。。由于IPRWGI和IPREFW是国家层面的数据,因此有必要转化为省级层面的数据。我们用专利侵权和其他纠纷结案量,查处冒充专利行为和假冒他人专利行为结案量两个维度的指标计算各省份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强度。回归结果表明,运用不同知识产权保护指标的回归结果与原始回归结果十分吻合,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可靠的*由于受到篇幅所限,本文未能报告具体的回归结果,此处的回归结果备索。。
六、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不足之处
本文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研究了服务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并且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开展了经验检验,得到了以下重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1) 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长显著促进了服务业结构升级。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在于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代表的汇聚智慧、创意和理念等高级要素的高端服务业的爆发式增长(杜运苏等,2016),而智慧、创意和理念这些核心要素的无形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决定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才能激发创新者的创新意愿。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起步较晚,尽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督促而被动地实施了大量完善措施,但是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提升我国服务业竞争力和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必由之路。在此过程中,不仅需要国家制定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而且地方政府也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执行力度,并且辅之以宣传和教育等措施使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深入人心,由此形成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多维度和立体式的政策体系。
(2) 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由于受制于较为松弛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两个地区的服务业结构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趋于扩大。在全球制造业产业转移浪潮中,中西部地区可以借助于服务业全球转移的有利时机缩短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包括服务业的规模扩张和结构升级。首先,中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尤其武汉、西安和兰州等地是著名高校的云集之地,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吸引高端人才在当地安家落户,甚至吸引其他地区的优秀人力资源进入(张为付和张文武,2016);其次,中西部地区可以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打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维护健康的市场秩序,由此激发当地的创新活力,同时吸引优秀人才的流入,实现人力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
(3) 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业结构升级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呈现先扬后抑的“倒U”型特征。虽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资源跨国流动效应等渠道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但是政策制定部门应当考虑到其“两面性”特征。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依然低于理论“最适强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所产生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因此相应的政策措施应当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此外从我们的企业调研情况来看,被访企业的多位高层管理者均认为我国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削弱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的创新热情。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应当成为主旋律,尤其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尤为必要。
1. Broadberry, S. , and B. Gupta.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India’s Service-led Development: A Sectoral Analysis of Anglo-Indian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1870-2000.ExplorationsinEconomicHistory, 2010, 47(3):264-278.
2. Evangelista, R., M. Lucchese, and V. Meliciani. Business Services, Innovation and Sectoral Growth.StructuralChange&EconomicDynamics, 2013, 25:119-132.
3. Hodgson, G. M. Much of th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Devalues Property and Legal Rights.JournalofInstitutionalEconomics, 2015, 11(4):683-709.
4. Khoury, T. A. and M. W. Peng. Does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ead to More Inbound FDI?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JournalofWorldBusiness, 2011, 46(3):337-345.
5. Langhammer, R. J. Sectoral Distortions and Service Protection in Russia: A Comparison with Benchmark Emerging Markets and EU Accession Candidates.EasternEuropeanEconomics, 2008, 46(6):70-83.
6. Maskus, K. E.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Innovation in Services.JournalofIndustryCompetition&Trade, 2008, 8(3):247-267.
7. Rubalcaba, L., D. Aboal, and P. Garda. Service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 2016, 52(5):607-626.
8. Wieczorek, J. Sectoral Trends in World Employment and the Shift toward Services.InternationalLabourReview, 1995, 134(2):205-226.
9. Woo, S., P. Jang, and Y. Kim. Eff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Patented Knowledge in Innovation and Industry Value Added: A Multinational Empirical Analysis of Different Industries.Technovation, 2015, s 43-44:49-63.
10. 程大中:《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结构及影响——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国际比较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
11. 杜运苏、丁静、陈鑫:《医药制造企业的融资难与所有制歧视有关吗——基于CCER、CSMAR数据的实证分析》,《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12. 韩玉雄、李怀祖:《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科学学研究》2005年第3期。
13. 黄玖立、李坤望:《出口开放、地区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14. 黄玖立、吴敏、包群:《经济特区、契约制度与比较优势》,《管理世界》2013年第11期。
15. 黄莉芳、杨向阳:《中、美现代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趋势比较——来自投入产出表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研究》2015年第3期。
16. 李江帆、朱胜勇:《“金砖四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结构与影响——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国际比较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08年第9期。
17. 马风华、李江帆:《城市服务业结构变动与生产率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上海的经验数据》,《上海经济研究》2014年第5期。
18. 倪红福、夏杰长:《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结构及其与制造业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级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山东财政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19. 裴长洪、李程骅:《论我国城市经济转型与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20. 王智渊、马晶:《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与服务业内部结构演进》,《产业经济评论》2014年第4期。
21. 夏杰长:《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经济研究参考》2008年第4期。
22. 宣烨、余泳泽:《生产性服务业层级分工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地区38城市的经验分析》,《产业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
23. 张为付、张文武:《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加、减、乘、除”策略研究——以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为例》,《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