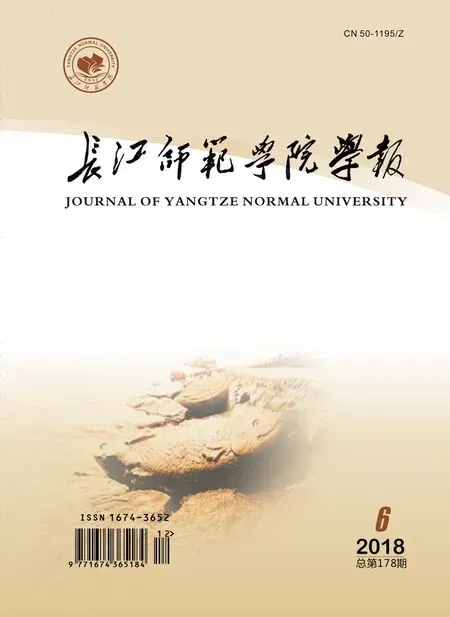民国时期来川女传教士的角色审视
——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中心
王 锐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传教士研究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和现实意义的话题,国内外学术界出现了大量相关成果。在传教士群体中,女性传教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相比较而言,关于女传教士研究仍存在着不足:首先,女传教士研究较男传教士数量少,其性别角色往往被忽视;其次,研究具有区域性意义的四川女传教士的成果更少,且大多只简单论述其事业及影响等,未仔细从性别角色角度探讨;最后,国外的研究成果大多站在西方的立场,缺乏中国的研究视角。本文聚焦于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的女传教士群体,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中心,以“女性”角色为切入点,考察女传教士在各项事业中、闲暇时的社会观察中的表现,以及她们与男性传教士、四川女性的碰撞,进而探讨她们的性别优势、限度和四川社会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认识四川女传教士,并为其他地区女传教士的研究提供借鉴。
需要说明的是,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合大学正式成立。1911年,受到四川保路运动的影响,华西协合大学的教学一度停滞,直到1913年恢复教学。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华西协合大学,1951年,人民政府从外国教会手中正式收回了教育主权,华西协合大学改名为“华西大学”。因此,以华西协合大学为研究中心的时限大致与民国时期(1912—1949)时间一致,但是受传教士个人生平的影响,本文的“民国时期”与严格史学意义上的民国时期有略微的出入①民国时期是从中华民国建国(1912)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而本文的“民国时期”大约要追溯到民国建立之前的若干年。。
一、民国时期女传教士来川传教的概况
1901年12月31日,重庆海关海恩斯(W.C.Haines Watson)在一份关于十年(1892~1901)重庆海关情况的报告里提到,来川传教的人数每年都在增长,且女性传教者居多,并统计到英、美、法、加等国有九大教会在四川境内活动,男女传教士共有315人[1]。到1910年,“外国教会增加到十三个,传教士增至五百一十五人”[2]7。到1920年,在四川地区的传教士有543人,其中女传教士339人。1910年,由加拿大英美会,英国公谊会、圣公会,美国浸礼会、美以美会五大教会团体联合主办的华西协合大学成立,成为这个时期传教的中心,“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以华西协合大学为基地,开始向四川地区开拓布道、教育、医疗事业”[3]12。传教士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献、档案等,他们不仅是四川地区教会大学的创办者与教育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四川政治风云变化的见证者、医疗与卫生事业的开拓者。
(一)女传教士来川传教的原因
1.民国政府、四川军阀的支持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就任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及不少革命党人都曾有基督教信教背景。1912年3月,孙中山在致函教友康德黎夫人时说:“我们正在谋求中国实行宗教自由,而在此制度下,基督必将繁荣昌盛。”[4]同时蒋介石与其夫人宋美龄同为基督教徒,蒋曾命四川军阀保护传教士,“1927年2月25日,蒋介石令军阀刘湘部确保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5]。鉴于此,四川军阀为了“亲近”蒋介石,纷纷保护传教士。1927年,在军阀刘文辉给华西协合大学毕启的一封信件中,他承诺将保护“外人”,特别是华西协合大学外籍教员的生命财产安全[6]。因此,较为宽松的环境使得传教士们纷纷到四川各地进行传教。
2.四川地区传教活动对女性传教士的需求
1877年,因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英国基督内地会在重庆设立了四川第一个布道点,此后许多差会来到四川,并且1899年的华西传教会议“缓解了各派教会的矛盾,协调了关系,调动了传教士的积极性……四川各地基督教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7]。这吸引着各地传教士包括女传教士来到四川。1878年,克拉克夫人成为第一位来到四川的女性传教士,加拿大女传教士饶珍芳(Muriel J.Hock⁃ey),也就是下文提到的伊莎白的母亲“先后于1912年、1913年来华传教,1915年在成都结婚”[8]377。饶珍芳属于加拿大卫理公会华西会。
基督教认为,妇女占到人口的一半,要完成基督世界,妇女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四川地区,妇女当然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且由于妇女本身的特征与家庭位置,容易受到教义的感染,并在家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家庭成员。因此,各差会非常重视对四川妇女的传教。但是由于传统封建礼仪的束缚,如“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有别”“男女不可同堂”等,男传教士不便于对四川妇女进行教义的宣扬。于是,各差会派遣大量女传教士给四川妇女进行教义宣讲。由于女传教士们能更容易接近妇女,接近她们的生活,并“消除四川妇女的忧虑和戒心”[9],从而达到传播教义的目的。
3.大部分已婚女传教士随丈夫来到四川进行传教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地区,地理位置独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正是对四川地区特殊地形的形象描述。但是这块土地拥有数千万的“异教徒”,使得源源不断的西方传教士跨过千山万水来到这里。女传教士莫尔思夫人(A.K.Morse)和其丈夫医学传教士莫尔思来到四川时,曾绘下了长江三峡的艰险图貌。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各差会大力向中国西部发展势力,一批又一批为实现‘中华归主’的传教士涌入四川”[2]5。对于一部分已婚女传教士来说,像莫尔思夫人跟随自己的丈夫一起来到四川传教也是自然而然之事。
当传教士在成都兴建华西协合大学之后,英美会的客士伦和他的夫人入住了“华西坝”(华西协合大学建成以后,“华西坝”这个名字就有了)。据载:“1902年2月,一个阴雨蒙蒙的下午,一对外国夫妇搬进了在这里的新家。”[2]15像这样跟随自己的丈夫来到四川的女传教士还有罗成锦夫妇(Robert⁃sons)、麦尔生夫妇(Carsons)、杜焕然夫妇(Stewarts)、周芝德夫妇(Johns)以及启尔德夫妇,她们都陆续居住在华西坝,并成为华西协合大学的老师。在华西坝住宿环境的不断改进之下,“公谊会的石恒励夫妇(Silcocks)也来了,还有美以美会也搬来了柯理尔小姐(Miss Clara Collier)和约斯特夫妇(yosts) ”[2]16。
(二)来川女传教士的身份、目的及指导思想
民国时期来川的女传教士,由于传教事业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对女传教士的要求也有所提高。华西协合大学的女传教士教职员工毕业于其国内著名的院校,拥有丰富的学识,“华西协合大学的教员都是由各教会选派,分别来自英、美、加三国,所代表的有剑桥、牛津、多伦多、耶鲁等西方院校”[3]12。如华西协合大学的加拿大英美会女传教士启希贤是医学博士、美国卫理公会女传教士满秀实是芝加哥大学皮肤科专业毕业的高材生。
女传教士来到四川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传播教义,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更好地传教;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她们试图证明,作为女性,一样可以像男性一样有一番作为,渴望真正的男女平等,“赴海外传教,犹如拓荒探险,虽险犹荣,能得到社会的肯定,心理的补偿”[10]。何况,当时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传教基地,能够为来川女传教士实现价值、得到社会肯定。除此之外,很多已婚的女传教士来到四川,可能更多是为了相夫教子。
“妇女工作为妇女”思想是这一时期女传教士来华传教,也是来川传教的指导思想。贝内特认为:“女性传教士通过教育,培养中国女性成为医生和护士,使中国女性能在封建传统为女性所限定的角色之外发挥自己的作用。”[11]因此,来川女传教士把自己在国内的带有“女性主义”特征的思想,即女性也可以有作为的思想带给她们,而深受传统封建思想迫害的四川妇女就成为女传教士的传教对象,使她们能够在教育、医疗、慈善事业等领域有所作为。
二、民国时期来川女传教士的“女性”角色
(一)布道、教育事业中的“女性”角色
1.布道事业中的“女性”角色
女传教士大多成为男性传教士布道的“助手”,特别是已婚的女传教士往往是其丈夫的助手。但她们发挥了“女性”角色特有的魅力,如能更好地接近女性,这是男性传教士所不能及的。华西协合大学的传教士,虽然受不同教会的派遣,但是“他们‘为主作功’的目的是相同的,不仅以自身的言行、举止,如家庭礼拜等,着力表现基督人格与生活,而且直接地对学生进行基督训练”[2]23。如当时任华西协合大学教师的启真道和费尔朴(D.L.Phelps)等就在家中组织英文查经班等,主要是吸引学生的参加,而这时候就需要发挥女传教士“女性”角色的作用。启真道等人组织查经班的同时,由“外籍师母聚集喜欢唱歌的学生,训练唱诗班,庆祝圣诞节等”[2]23。“外籍师母”亦指男性传教士的夫人,可见在布道中,女性传教士确实扮演着助手角色,以自己的“女性”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女传教士以自己“女性”的角色面向四川地区的妇女,在四川妇女参加集会、庙会时进行布道,以及通过邀请到家庭、创办妇女圣经学校等进行布道。论者指出:“成都妇女有一种特别的嗜好,好游庙者十分之七。”[12]于是女传教士利用性别优势,向她们布道,“我们在集市的这一天举行基督布道会来吸引妇女入教,同时我们也直接进入妇女的家庭来宣传基督”[13]。在《华西教会新闻》中,女传教士Miss L.M.在总结1918年绵竹地区的基督妇女工作时表达了上述做法。
女传教士除了进入妇女家庭布道,也邀请妇女来到自己的家庭中布道,向她们介绍教义内容。在进行家庭式的布道时,更能够看到女传教士作为“女性”对四川妇女的影响,从四川妇女的反应可以有所了解,“如果唯一的基督教女传教士能够在这里多待上两年时间的话,我也许就不会剃发成为一个尼姑”[14]。从创办于1934年的成都协合妇女圣经学校毕业的学生,大都从事着与教会事业相关的工作,这样一来既培养了女性基督布道员,又使得这一部分的四川妇女有了工作,并获得了一定的工资酬劳。
2.教育事业中的“女性”角色
女传教士创办了一系列的女子学校,招生的对象是一些贫困或被遗弃的女孩。成都华美女子中学在建校初期,招收的多为处于社会下层的女孩,并且“许多刚入校的学生,学校提供食物、衣服和路费等”[15]。对于这种情况,女子学校受到很多四川人的欢迎,因为这减轻了很多家庭的负担,使很多原本不能够读书的女孩有了一定的出路。1924年,华西女子教会大学成立并与华西协合大学进行合作教育,女传教士们在该校任职,教授学生医学、教育、艺术等方面的内容。1928年,任教于该校的达伍娜(Miss Downer)为艺术系的学生教授钢琴,并且“同事发现达伍娜把时间与精力都用在了女子大学的教学和华西协合大学外语系的管理上了”[16]。像达伍娜这样的女传教士有很多,她们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人才。
女传教士从事的教育类别不同于男传教士。根据“华西医科大学及其前身在校的外籍教职员表”[17]统计:女传教士刘延龄夫人(AGnew.M.C)、杨济玲夫人(Best.G.C)、启希贤、启尔德的夫人以及她的女儿启静卿在医科供职;安德胜夫人(Anderson.E.M)、白明道夫人(Mrs.Bayne.P.M)、布礼士夫人(Mrs.Brace.A.J)、客士伦夫人(Mrs.Carscallen.C.R)在文科供职;林则夫人(Lind⁃say.A.T)在图书馆供职……经统计发现华西医科大学的外籍志愿表中,其工作基本上集中在医科、文科、图书馆、英语,其中从事文科和医科的较多,而只有两位女传教士即徐维里夫人(Sewell.H.G)和丁克生夫人(Mrs.Dickinson.F)在理科供职。男传教士的工作领域除了涉及在医科、文科、图书馆、英语之外,还集中在理科、牙科、行政部门、宗教、教育,特别是学校行政部门和宗教科,这些工作几乎全部都是由男性传教士担任,如下文提到的伊莎白的父亲饶和美,于1928年“出任华西协合大学的教务长”[8]2。因此,华西协合大学一些重要的行政部门和关乎基督传教的宗教科都由男传教士主导,女传教士主要从事医科、文科和美术等学科的教学,比如1934年华西协合大学的美术系系主任为女传教士安德胜夫人。
基于华西协合大学任教的传教士对中国做出的贡献,他们经常受到政府的嘉奖,但大多数都是男性传教士。据载:“政府褒奖牙科创办人林则(A.W.Lindsay),博物馆创始人戴谦和(D.S.Dye);毕启更是因为多方面的贡献,先后受到袁世凯以及国民政府的嘉奖与褒奖。”[3]从华西协合大学传教士人事档案来看,“华西协合大学并不给予传教士的妻子以薪水,不管她是否在大学任教”[3]。因此,客观地说,在教育事业中,女传教士在很多方面都处于一种弱势或者被忽视的状态,虽然西方宣扬男女平等,但女传教士的待遇低于男传教士,“戴德生给予十余名英国女性以极低的待遇后,令她们深入内地”[18]。在女传教士群体里面,差会也给予未婚传教士以更多的支持。华西协合大学的教师大多由英、美、加各差会指派来校,加拿大英美会女传教士启希贤是启尔德的妻子,她和莫尔思等人是华西协合大学医科的创始人,“1914年,她与莫尔思等人创办大学医科,任药理学、毒理学教授”[2]75。作为医科的创始人之一,启希贤拥有卓越的医学学识和作为西方“女性”的一种敢于挑战困难的魄力,这就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女性,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
(二)医疗、慈善事业中的“女性”角色
1.医疗事业中的“女性”角色
由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妇女囿于传统意识,是极不愿意让外国男性医生医治疾病的,当时的华西协合大学的医科汇集了一批学识渊博的医学教师,并且从事着医疗、护理的工作,启尔德家族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据载:“有些家庭二三代人都在华西坝传教任职,如启尔德家族三代人都先后在华西从事医学教育和医疗、护理工作。”[2]52启尔德的妻子启希贤,是加拿大英美会的女传教士,也是医学博士,“1896年,她在成都惜字宫街创建仁济女医院,是四川最早的女医院,为妇女治病”[2]75。女医院希望将教义传达给每个来看病的妇女[19]。她专为妇女治病,为四川妇女来医院就诊提供了方便,体现着女传教士身为“女性”的优势。此外,很多传教士家族几代人都留在了四川,除了本身传教的目的,她们兼顾着孕育下一代的职责。在医疗事业方面,除了西方的女传教士的贡献之外,还有受到教义感染的中国女教徒的付出,而华西协合大学第二任校长张凌高的女儿张君儒便是一个。张君儒是虔诚的基督教公谊会徒,原来属于美国美以美会,“张君儒是一位杰出的儿科大夫,她早年在成都惜字宫女医院工作,后来创办四川医学院儿科”[2]56。
女传教士的供职单位主要是在有关妇女的科室与部门,如妇科、产科,担任护士等,这可能和她们自身性别有关,也和四川地区妇女的特殊状况有关。如美国卫理公会女传教士满秀实,她“看到四川女性生产多沿用旧习,于是她深感有推广接生新法之必要,立即返回美国学习产科专业,毕业后回到四川”[20]614,并创办了妇产科医院。由于她们从事妇科、产科,减少了四川妇女疾病的痛苦,提高了四川妇女的医疗条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幼儿的健康。由于女传教士创办的女医院是专门针对四川妇女的,因此就职医生的工作科室也多由女性负责,“英国女医生卢华棣为进一步扩大在潼川地区的医疗事业,建成新妇女医院,医院设有住院部、产科接生室和隔离室等”[21]。在医疗事业中,女传教士针对四川妇女的需要,主要从事妇产科,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很多护士学校,吸引四川妇女来学习。
2.慈善事业中的“女性”角色
女传教士的救助对象也是从“女性”角色出发,主要针对妇女与儿童,创办了慈善性质的孤儿院等。据载:“1911年,苏格兰福音会在四川开设的孤儿院里有十二名孤儿,其中一名是来自农村的女盲童。她原先是由其祖母照顾,然而在祖母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后,由于家庭的贫困,祖母把女盲童交给了教会,她相信教会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孙女。”[22]这说明四川妇女还是比较信任女传教士的。位于阆中的圣公会福音女孤院,“1904年由澳大利亚女传教士贝永光创办,收养被遗弃的女童并教她们学习文化等,1931年由美国女传教士贾美玉主持”[20]480。除了以上的例子,还有很多类似的孤儿院,确实救助了不少四川地区的孤儿。
(三)来自基督世界的女性观察者:伊莎白(Isabel Crook)与《兴隆场》
1.伊莎白在四川的情况及《兴隆场》背后的故事
1915年12月15日,伊莎白出生于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家庭”[23],一出生就与华西协合大学结缘。其父饶和美在华西协合大学文科任教,其母饶珍芳接受华西协合大学的安排,管理当时的成都私立弟维小学,并且新设了一所幼稚园。父母在四川的停留使伊莎白从小生活在四川。1933年,伊莎白返回加拿大学习心理学与人类学。1938年,伊莎白决定回到四川作人类学调查。1939年,伊莎白回到成都,得到教会的资助,“开始在四川阿坝理县附近的一个少数民族村庄进行社会调查”[23],她说:“虽然我从小受的是基督教育,但我一直关心的不是教义,而是人,特别是那些穷苦的人。”[23]
兴隆场属于璧山县,民国时期属于四川,现隶属重庆市。在兴隆场的乡建实验区进行社会调查是伊莎白的任务之一。1940年,“加拿大妇女差会批准伊莎白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工作,任务之一就是在乡建合作实验区调查研究适合乡村教会发展的道路”[8]378。伊莎白在理县进行社会调查期间,“相遇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家晏阳初、李安宅、葛维汉等人,并参与在兴隆场的乡建实验区,这是抗战时期四川乡建运动的一部分”[24]。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一位华人女传教士俞锡玑,当时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农村工作部工作人员的身份,前往四川”[8]376。最后伊莎白与俞锡玑在兴隆场的乡建实验区相遇了,开始了题为《兴隆场》的社会调查。《兴隆场》是抗战时期关于兴隆场农民生活的社会调查,也是伊、俞两人严谨观察的结果。
2.基督世界观察者“女性”角色在《兴隆场》的体现
作为一份社会调查,《兴隆场》是由伊、俞两人观察到的兴隆场世界组成的充满了“本真性与朴实感”[25]251的作品。通过这部作品,可以看到来自基督世界观察者“女性”角色的一些特殊表现。
19世纪40年代,兴隆场是处于抗战大后方背景下的封建世界,充斥着“男女有别”等封建思想,这些本来对于社会调查是极其不利的。但是,伊与俞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难题,她们在书中淡及她们进行调查的优势有:“调查者本人均为女性,且长期共处之后已为当地人所认同。”[8]6伊与俞因为性别优势不仅可以亲密无间地接触到兴隆场的女性,也能够接触到中小家庭的男性户主与年轻男人。这样的特殊优势使伊莎白与俞锡玑能够开展自己的事业,除了社会调查之外,还开展教会事业,如开办幼儿园、妇女识字班等。伊莎白在当地福音堂开设贫民千字班,免费招收当地贫困孩子并教他们识字。据伊莎白当时的学生曹洪英回忆,“在她十多岁时,有一个外国女人来到她家,叫她去学校读书,而这个人就是伊莎白。来到学校之后,班上四十多人全是女生,伊莎白在学校教授文艺课”[26]。另一个学生张敬文回忆,“伊莎白时常围一根围巾,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的,很喜欢交朋友并在长隆回龙桥认了一个名叫朱显珍的干姐姐”[26]。
角色认同使基督世界的女性观察者观察到更多关于女性的问题。伊与俞在角色认同的驱使下不自觉地关注女性并倾向将女性作为受访者。有论者指出,“童养媳问题在《兴隆场》一书中有大量记述”[25]251,并涉及到休妻卖妻、偷情乱伦等问题,关于妇女在家中的地位、婚姻状况,与婆家人、丈夫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记录得比较多,如“孙陶氏的故事”[8]41。当然也观察到重男轻女的社会现象,如将女婴溺水等。此外,由于妇女喜欢谈论家长里短、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从其口中更容易听到对于生活艰辛的诉苦与抱怨”[8]5,这就弥补了观察的不足,从而增加更多的资料。伊与俞有一位好朋友,是她们雇来帮忙的彭嫂,书中对她的描述是“年近50的彭嫂是个寡妇,认识的人多,消息灵通”[8]6。于是,她们从彭嫂那里得到更多不为人知的消息。
由于伊莎白与俞锡玑同时都是传教士,她们在兴隆场的观察中,会着重记录到有关教会的事物,如圣诞节与教堂,教会在医疗、教育事业方面的作为,教会与兴隆场基督教徒和百姓的关系,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在医疗事业方面,来自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护士朱小姐经常给兴隆场的妇女接生,兴隆场的百姓有什么病情,也愿意主动去诊所找朱小姐。在教育事业方面,卫理公会在璧山县开设了璧山淑德女中,很多想让女儿接受新式教育的家庭就将孩子送在这里。同时,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也开办了幼稚园,并有当地的女教徒在里面帮忙做事。很多时候教会也会担当起仁慈基督的角色,如帮助生产后无人照顾的产妇等。
不过,教会与百姓的关系似乎也是复杂的,很多百姓会向教会寻求帮助,如找教会帮助逃避兵役[8]304,由于教会有着特殊的政府背景,可能鉴于这种原因,很多百姓会假装是基督教徒。
3.来自基督教世界的观察者性别角色比较
女性传教士观察到的世界在很多内容上能够深入到百姓生活的内部,特别是更加容易接近妇女。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的男性传教士徐维里(W.G.Sewell)的《龙骨:一个外国人眼中的老成都》一书,主要描述的是19世纪20年代成都普通百姓的生活故事,如挑水夫、卖花女、剃头匠、农夫、农妇等。《龙骨》对四川女性的描写大多是宏观的、客观的,比如弹棉花的家庭主妇、细心养蚕的农妇们、络丝缫丝的妇女、磨黄豆的妻子等[27]。伊莎白与俞锡玑共同完成的《兴隆场》则是从“女性”角色出发,因而更多地观察到有关女性的问题,如上文论述过的“童养媳、休妻卖妻”等问题,这可能由于作者能以“女性”身份与四川女性接触,并从她们那里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但是,他们都能观察到当时四川女性大多是被封建教化毒害的群体,徐维里在书中说道,“那个时代的特征是传统社会仍在苟延,妇女丝毫不被提及,女孩在家中几乎不算数……她们只是男人延续家庭的附属品”[27]139。因此,作者在《兴隆场》一书中始终透露着对四川女性悲惨境遇的认识与同情。
(四)女传教士眼中的民国“乱世”景况
民国时期,四川地区处于抗战大后方,女传教士深入四川农村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伊莎白的《兴隆场》是一份关于抗战时期四川地区农民生活的调查,书中写道:“那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两年前国民政府刚刚被迫迁都重庆,将四川作为指挥全国抗战、向各战场输送人力物力支援的大后方。”[8]2在这样的情况下,四川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下江人”的到来也创造了巨大的商品和市场。因此,“1938年至1942年是带给他们大动荡、大艰苦、也是大希望的五年”[8]2。作为“女性”传教士的伊莎白在书中如此描述当时四川农村地区的情况,表现了她对当时的政治时局有一定的了解与关心。伊莎白还说:“我从小就经历过四川地区的军阀混战,还经常捡子弹壳玩,因此并不害怕战争。”[23]笔者认为这体现了一位女传教士面对政治动乱的一种气魄,除了抗日战争,伊莎白也经历过军阀混战,以至后来的解放战争与新中国建设。事实上,在抗日战争中,女传教士与女基督教徒也参与其中,“成都基督教女青年会与成都市妇女会等12个妇女团体,组织抗日宣传队到城镇动员妇女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28]101。
三、性别的优势与限度:来川女传教士的社会影响
(一)来川女传教士作为“女性”对四川妇女的感情
女传教士与四川妇女之间建立起了类似于“姐妹情”的关系,能够从“女性”的角度去关注同情当地妇女。在川女传教士工作的对象是广大同性姐妹,她们秉承基督平等、博爱的精神介入社会现实,比如反对缠足、纳妾、重婚等一系列恶习。
随着对四川感情的加深,很多女传教士将其视为自己的第二个故乡,冲破了传播教义这一层动机。比如伊莎白,尽管她多次回国,但大半生在中国度过。伊与她的女学生始终都有着书信之间的联系,自第一次到四川璧山县兴隆场之后,后来的几十年里她曾多次回到这里,与自己的学生见面,如上文已经提到伊莎白在兴隆场学生的回忆以及她的一个干姐姐朱显珍。
(二)性别的优势:来川女传教士的社会影响
第一,在教育实践中,女传教士利用性别优势,创办了四川地区最早的女子教育。女子教育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三常五纲”“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牢笼枷锁。女传教士无论是作为教员还是工作人员,能更好地与女性学生接触,使教育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在女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子中学、大学中,如当时著名的华西女子教会大学和成都华美女中等,诞生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四川女性。这在客观上提高了四川妇女的知识水平,冲击了封建传统社会中国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民国时期的四川妇女“就是这样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开始接受现代启蒙教育的,教育启女性之心智,去女性身上千年尘垢”[29]26。除了专门的女子教育,各差会的女传教士还利用性别优势创办了很多妇女识字班,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程度。民国时期出现的职业女性,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教会女子学校,她们毕业以后主要从事与传教、教育、医疗等相关的职业。
第二,在布道与慈善事业中,来川女传教士因是“女性”,所以更加关心与同情四川的同性姐妹,女传教士针对处于社会底层受到缠足伤害的妇女,大力宣传反对缠足,“近12个月内,在本县四乡分发天足会书多册,且张贴天足会单于城内之墙壁通衡,律众观览。本城教会不准父母缠小女之足,而父母亦乐顺从”[30]。启希贤也曾“担任成都天足会的会长,积极宣传废除缠足的恶习”[31]41。同时女传教士反对纳妾、重婚、童养媳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风气,提高了四川妇女的社会地位,使她们不至于完全处于“男权”之下。并且,一部分女子在女传教士开办的女子学校中毕业后,有了正当的职业,这证明了“女性”也可以如男性一般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
(三)性别的限度:来川女传教士的社会影响
由于基督教传教士主体仍然是男性,女传教士不可能获得与男传教士绝对平等的权利,这一时期活动于四川的女传教士也是如此。因此,受自身教义的影响,女传教士在倡导四川女性解放有其局限性,也受到其性别的限制。
第一,在教育实践上,女传教士虽然能够利用性别优势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性别的限度也导致一些弊端,限度来源于基督的教义与身为女传教士的职责。首先,基督女学教育目的有其明确的宗教性,即将在教会女校就读的女孩培养成“本地”的女传教士、合格的中国基督教妻子与母亲。其次,教会女校的课程设置,也包括其他教会大学都设置了宗教课程并从事一些宗教活动,比如华西协合大学在创办前期设置了宗教课程,直到后来四川政府接收了华大的教育权。因此,教育事业带有很强的传教目的,女传教士在任职期间是没有办法超越的。
第二,女传教士在解放妇女、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中的作用有明显的限度。女传教士受到保守福音派思想的束缚,她们“输出女性主义,而非女权主义”[32]。她们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封建传统的长久影响,并不主张四川妇女追求真正的男女平等与女权,而是更多地希望皈依基督的四川妇女成为一位贤妻良母。女传教士帮助四川妇女免受缠足、童养媳等的毒害,让她们走出家庭与深闺,拥有可以与男性同样的机会,但这大多并未涉及到女权与封建传统,女传教士也认识到传统意识的强大,且很难轻易改变。
第三,在实践中,女传教士虽有性别的优势,但四川地区的传统观念与基督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不免有其限度,“当传教士为老乡们哄抢印有《圣经》故事的传单而欢欣鼓舞时,却很快发现他们只是为了用这些纸张来糊鞋底”[2]8。很多百姓受到自身知识水平与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与制约,无论男女,还不能接受基督福音,在很多时候她们参与教会活动只是为了得到基督福音施与的一些小便宜,比如免费的食物等。所以,女传教士性别上的优势存在一定的限度。
四、结语
民国时期,来川传教士以华西协合大学为基地开始向四川地区传播基督教义,作为来川传教士的组成部分——女性传教士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作为。由于当时来川女传教士人数众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女传教士到四川大多是因为传教事业的需要,但是笔者认为她们更多的是为了实现在国内不能实现的理想。无论是在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中,还是作为观察者,女传教士都有其自身的“女性”角色,这种性别角色突出表现在与四川女性的交往中。女性传教士来到四川后,性别优势使之能够更好地接触到当地女性,开展一系列与女性有关的教育事业与解放妇女的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观念习俗,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四川女性,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当然,女传教士毕竟是传教士,因此她们无法逾越这重身份。所以,在很多实践活动中,仍有着明显的基督教烙印。总而言之,在民国时期,女传教士在四川的各项事业中扮演着一个具有多重功能的“女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