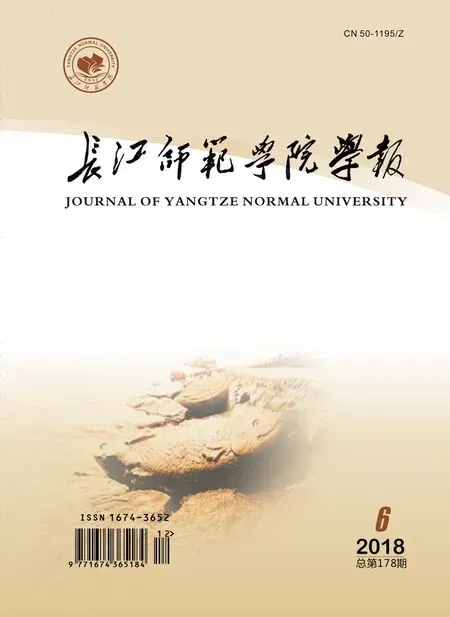知识形态、国民性话语与被压迫者的教育学
——艾芜《南行记》的“国民性”书写
熊庆元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扬州 225000)
《南行记》是艾芜创作生涯中第一部公开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其初版于20世纪30年代。围绕这部作品,至今已出现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论述也各有侧重,但关于这部小说集中涉及的知识形态及与此相关的国民性话语问题,现有的研究则所涉不多,本文拟就此加以考察。
一、知识形态冲突与国民性话语的异变
(一)知识的两种形态及其内在冲突
艾芜在《南行记》一书中描写了许多底层人物,这些人物身上的一些性格特点在五四时期都曾被视为国民劣根性而遭到批判。然而,对底层人物的上述性格特点,《南行记》的态度则似乎更为复杂。在艾芜看来,这些性格有时甚至具有某种正面的价值。比如,《山峡中》里有一段关于“学问”的对话就颇有意思:当“我”和魏大爷、鬼冬哥们坐在火堆前取暖时,魏大爷正在责怪被打伤的小黑牛“太笨”,这时,鬼冬哥看到“我”手里拿着书,就一把抓着“我”的书喊道:“看什么?书上的废话,有什么用呢?一个钱也不值,……烧起来还当不得这一根干柴。……听,老人家在讲我们的学问哪!”[1]26接着,魏大爷就说:“我们的学问,没有写在纸上,……写来给傻子读么?”[1]26鬼冬哥便顺势接着说道:“烧了吧,烧了吧,你这本傻子才肯读的书。”[1]26到最后,魏大爷又做了补充:“你高兴同我们一道走,还带那些书做什么呢?……那是没用的,小时候我也读过一两本。”[1]27通过上述引文,我们发现,艾芜已注意到魏大爷等“底层人物”的“知识”并对其加以描写。而这样一种“知识”更多是以颠覆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为其表现形态的:“书”这一被作为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的表征符号,被认为是“废话”“没用的”“一个钱也不值”,而知识分子则被这些底层人物视为“傻子”。从这一对知识分子“知识”的否定可以看出,《南行记》似乎已经暗含了将底层人物主体化的努力。这在《南行记》收录的其他小说中同样可以反映出来。
在《在茅草地》中,“我”经人介绍“到那家店里去教几个小孩子”,临行前一晚,“我”“照上流社会的客气,就趁夜里摇晃的油灯下面,写了一封给洋学堂校长的英文自荐书,字错了一圈一点,也得另行誊清,从没有用过的小心,也恭而敬之使出来了”[2]57。但是次日前去的时候,没有碰到校长,而是碰到一个穿着白衣的洋修女,于是“我”不禁感慨道:“昨夜费心誊好的信,所用的精力都等于零了”,“‘傻子,你又上当了!’暗暗骂我自己。”[2]59在这里,我们同样发现,知识分子的普遍性知识在东南亚的地方空间中遭遇了挫败。与《山峡中》里类似的情况则是,作为“知识者”(知识)对立面的“傻子”(无知)依然是被指向知识分子这一“知识”的载体,知识分子的“书本知识”再一次遭到质疑和否定。唯一不同的或许在于,《山峡中》里“傻子”这一身份的指认是由作为“他者”的魏大爷、鬼冬哥等人做出的,而此处则变成了身为“知识者”的“我”的自我解构。
如果说《在茅草地》仅仅是完成了解构“知识者”所承载的知识形态的话,那么《我们的友人》则是将底层民众的“地方知识”形态正面展现了出来。在《我们的友人》中,艾芜赋予了老江这一人物更多的层次感。老江替人偷卖鸦片烟和吗啡,生活无着,铤而走险,但却毫不畏惧,坦然自若;他会偷拿“我”的钱出去赌博,但却会事后归还,不事声张;爱说大话和吹牛,但却有底层人的勤劳;身有恶疾,却很坚毅,从不叫苦连天;……在艾芜笔下,老江身上几乎包含了一个“底层人物”一切的性格特征,以至于老江的性格无法具体归类。细读《我们的友人》,我们仍可以发现,这一小说文本中依然包含着《山峡中》里关于“知识”和“学问”的讨论。小说记叙了某一次饭后老江和“我们”的闲聊。当我们以老江腿上的疮为话柄责怪他“胡闹”时,老江解释说:“一个人总是自己捣自己的鬼哪!你们看,叫化子真不要脸么?也要呀,可是那肚皮捣鬼时,也就顾不得谁张着嘴向他笑了,人人都是一样。”[3]93而当“我们”中有人以叫化子本来就不要脸反驳时,老江的回答是那肚子饿了怎么办?而当“我们”随之应以“去作工找饭吃”时,他的回答则是“找不到工作呢?”当“我们”无言以对时,老江就开始讲述他的人生哲学:“我问你,你能忍着活活地饿死么?眼睁睁地就让手足硬了么?你不愿做叫化,是的,那使你太难过,但也不由你不去干坏事呀!”[3]93而对于干坏事会丢命的说法,老江更是不屑一顾,他说:“丢命有那容易?真丢了命,他也是个饱死鬼哪。你白白饿死,才真叫做活该!”[3]93-94我们发现,在这里,老江的话中所体现出来的完全是底层人的“知识”,这类“知识”的产生同样来自于对“饥饿”和“贫穷”的生活状态所做出的反应,因此,其首先表现为一种关于“生存”的论述:要活下去。而当“生存”出现问题时,一切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道德和价值就都遭到清算和颠覆:迫不得已,为了活着,干些坏事也无妨。而当这些溢出道德之外的事有可能再一次触及到“生命”时,它的逻辑依然还是服从“生存”至上的原则:与其活活饿死,不如在刀上过日子,还有活下去的可能。这样的一种“生存”哲学,在《山峡中》里被魏大爷形象地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不怕和扯谎。”[1]26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一退至底线的“生存”哲学,使得如老江这类的底层人物得以在获得基本的生存所需之后,将剩余的与大家一同分享:老江每次赌完,赢了钱,就买香烟并且把烟散给“我们”,和“我们”一起抽。
书本知识与“地方知识”之间的冲突,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知识分子与底层人物之间在生活和世界观上的龃龉,几乎贯穿整部《南行记》,它构成了这一作品对知识的两种不同形态及其内部张力的描述。
(二)知识形态冲突下国民性话语的异变
《南行记》对底层人物所拥有“知识”的正面书写,使底层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底层人物不再是愚昧和麻木的形象,而是富有鲜活的生命气息的人群。在《我诅咒你那么一笑》中,从小说开篇对那些傣族姑娘旺盛的生命活力的描写就可以看出,底层人物不再被视为无知的人,他们身上自由热情、富于活力的性格,得到了作者充分的肯定。那么,面对底层人物关于“生存”的这一类“知识”,“我”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在《山峡中》里,对于魏大爷、鬼冬哥们的“学问”,“我”仍是不能完全赞同的,但又不愿与他们争执:“因为就有再好的理由也说不服他这顽强的人”[1]27,在这里,“我”仍然对“我”所拥有的知识分子的“知识”极为重视,并自觉与魏大爷等人区分开来。然而,到了小说《在茅草地》中,如前文提到的那样,“我”的“知识”却遭到了质疑和否定。我们可以认为,作者此处提及的知识分子的“知识”便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启蒙现代性知识形态,它在遭遇本土性知识形态时与之发生了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然而,这虽然部分解释了《在茅草地》中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形态冲突,却不能完全为《山峡中》知识形态的冲突做出解释。《山峡中》所体现出的冲突,更多地表现为现代知识和知识分子本身被质疑和批判,而不是具体的某种知识或某类知识分子被质疑和批判。
由于《南行记》对“知识者”的“现代知识”做了上述处理,使得“我”这一“知识者”形象在“知识”这一层面似乎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我们无法在《南行记》中找到五四时期的小说文本对“国民性”所做出的激烈批判。艾芜对“国民性”的理解和书写并不像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从鲁迅的这句话可以看出,五四时期,“国民性”被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国民身上的“病苦”需要被“疗救”和“改造”。1917年初,光升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的文章,他将国民性视为“种性”“国性”和“宗教性”的集合体,并且认为中国人善于容忍,因此丧失了独立自由的精神,从而造成了极其薄弱的法制和民主观念。光升进而得出结论:误入迷津的中国国民性已经不适应现代世界的生存方式了,应加以彻底改造[5]。而鲁迅则是在阅读了亚瑟·史密斯(Arthur Smith,中文亦可译作明恩溥)的《中国人气质》一书以后,开始思考经由文学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途径。五四时期,鲁迅在言及国民性时,大多都是将它做贬义处理,并与“批判”和“改造”相联系。刘禾指出:“‘国民性’的意义向国民劣根性滑动,成为不折不扣的贬义词,主要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功劳”[6]。而从上文光升的论述逻辑来看,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建立在五四对民族国家建设的要求之上的。而鲁迅在五四时期阅读了《中国人气质》之后开始寻求改造国民性的途径,也不能不说是与这种民族国家建设的诉求有关。由此可见,“国民性”改造实际上是一个现代问题。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现代性”在介入“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时,势必会将原先具有丰富性和特殊性的“国民性”问题普遍化,由此,“国民性”被简单地处理成史密斯所说的“漠视时间”“缺乏公心”“轻视外族”等一系列极富概括性的词汇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对艾芜来说,对“国民性”的书写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对这一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普遍特征进行描摹。作为一个与底层民众“一道受过剥削和侮辱”的“知识者”,艾芜所理解的“国民性”更多地携带了那些底层人物所在的“地方”和“本土”的特殊性。“饥饿”和“贫穷”带给艾芜的是与这些底层人物休戚与共的感受,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因此,在1980年版《南行记》的《后记》中,艾芜写道:“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我写《南行记》第一篇的时候,所以标题就是《人生哲学的一课》。”[7]338艾芜所说的“上课”,是就“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而言的,前者更多是指向具体的实践,而后者则较为偏向普遍性的层面。由此也可看出,在他的“国民性”叙事中,自然也混杂着现代性与本土性的对话。
二、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底层叙事中的教育话语
艾芜的“国民性”叙事,如前所述,凝结着他与底层人物之间休戚与共的情感,并且,这一情感通过“上课”这一“教育话语”得以外化。从《南行记》整体的文本情况来看,“上课”这一“教育话语”在形成艾芜“国民性”叙事的过程中,至少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身份的确认:自我与他者
《南行记》底层叙事中教育话语的使用,首先体现在叙述者对“自我”“他者”的身份及二者关系的确认。在《南行记》小说文本中,叙述者的“自我”在前后是发生过变化的。比如,在《山峡中》里,叙述者“我”起初是自觉与魏大爷们区别开来,在经历了将小黑牛投江一事之后,这一分歧导致了冲突的爆发,但“我”在与野猫子们进行了争辩以后却又逐渐对魏大爷、野猫子们产生了一定的认可。这一认可在《我们的友人》中表现得更为深入,虽然“我”深知与老江并非同类人,却可以和他打成一片,老江变成了“我们的友人”。《南行记》中的叙述者“自我”似乎就呈现为这样一种由具有强烈排他性的“个体”自我渐渐走向较具有融合性和包容性的“群体”自我的过程。因此,在处理《南行记》中的“自我”问题时,就不能将它视为静止的。《南行记》中叙述者“自我”(一定程度上也可被视为作家的“自我”)的确立便是建立在对东南亚本土“国民性”(“他者”)的对话和认识过程之上的。在这一对话和认识过程中来读解艾芜所说的“上课”,或许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南行记》中的“国民性”会呈现出这么多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当《南行记》的叙述主体“我”试图对他的“自我”加以建构时,他首先需要将他现有的“自我”“他者化”,由此,“我”便是以“客体”而非“主体”的身份介入“国民性”想象。这在《南行记》具体的小说文本中可以得到相应的证明。
在《在茅草地》中,“我”经人介绍去一个村子教书,作者写道:“徐徐走进这山村,却给我一个有味的惊奇,差不多把来时的希冀,暂时忘掉了”[2]58,“我”被纳入到“我”眼前的风景和场面之中,使得叙述者的“自我意识”暂时性地消失了,这时的“我”更多地被整合进“他者”之中。可是,艾芜却在后文写道:“每走过一二家茅屋的门前,就有这样的女人停着工诧异地望望我。我想起来此的目的了,遇着一个男子就问学校所在的地方。”[2]58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叙述者“我”的“自我意识”被唤起,在与“他者”的对话关系中,叙述者的“自我”重新浮现出来。而在《我诅咒你那么一笑》中,“我”的自我意识则更为具体地体现为“伙计”和“教书先生”两个身份之间的对话与冲突;“老汤哥”和“先生”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冲突,似乎可以被处理成本土性与地方性冲突的某种表征。在此,“自我”与“他者”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也同时反映出了本土性与地方性的某种冲突形态。当“自我”被“他者化”以后,事实上更多的不是消泯了“自我”和“他者”的区别,而是模糊了二者的界限,由此,“他者”获得了一定的“主体”位置,并且是一个带有“群体性”特征的“主体”。《南行记》中“个体”自我走向“群体”自我的叙事过程,在这里就演变为将“群体性”的“他者”主体化的过程。因此,综观《南行记》中的小说文本,我们发现,即便在老江、魏大爷、野猫子这些人物身上,也可以看到极富个性色彩的国民性表达,但这些人物都无法被实名化,他们只能被作为“国民性”——指向“群体”叙事——表达的符号化的象征,而这一符号化的象征却是与五四时期不完全相同的。如安敏成所言:“在鲁迅、叶绍钧、茅盾的作品中,群众的形象往往是呈现于主人公孤立的视野当中的;他们构成了衡量个体内心的社会背景的一部分”[8]189,而在面对《南行记》这样的文本时,“读者必须直接与本身作为一个实体的大众相认同,正如认同于其他类型小说中的一个个体人物”[8]189。
(二)空间的政治化:对压迫的抽象批判
除了关于“自我/他者”的身份确认,《南行记》底层叙事中的教育话语,还体现在对压迫问题的书写上。艾芜的《南行记》书写的是“被压迫者的知识”,但在小说中,作者却并没有对不同的“压迫形式”做出明确的区分。在《在茅草地》中,克钦山中店家的老板对“我”的压迫,在《洋官与鸡》中,是洋官对缅甸下层人民的压迫,在《我诅咒你那么一笑》中,“英国绅士”对傣族少女的压迫,在《我的爱人》中,是统治者对沙拉瓦底战士妻子的压迫,这些几乎被统一做了等质化处理。对这些不同的压迫形式,作者只是在其同为“压迫”这一点上,表现出了强烈的愤慨。换句话说,艾芜在作品中似乎忽略了不同压迫形式之间的差别,而将不同形式的压迫抽象为“压迫”本身。比如,《洋官与鸡》中就很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点。当洋官让克钦兵砍老刘的房子时,老刘并没有骂万恶的洋人,天杀的洋鬼子,而是骂“天杀的官呀!天杀的狗官呀!”[9]69而寸师爷在提到英国人要拆缅甸人房子是因为英国人重视法律时,则是这样说:“英国人对待缅甸人,也是这样的。只顾在乡村地方修铁路汽车路,好运他们的洋货,到处行销,人民的苦楚死活,他们是不管的。管的时候也有,就是你犯了他们的法律。”[9]70在这里,英国人俨然被处理成统治者,而不是帝国主义者(从表述上说,“人民的苦楚死活”并不等同于“缅甸人民的苦楚死活”),而反抗则被处理成“官逼民反”,而不是某种殖民逻辑。艾芜后来在为《南行记》写《后记》时提到:“我热爱劳动人民,是在南行中扎下根子的。憎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地主的统治,也可以说是在南行中开始的。”[7]338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对举,似乎将一个与“国家”有关的“政治”问题转变为一个与“社会”有关的“阶级”问题。这当然与19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动有关,而这在《南行记》的文本中则是体现为具有抽象性与普遍性的“压迫”话语。艾芜在《南行记》中所反对的,是一切“压迫性”的力量,而所有“被压迫”的形式,在其“被压迫”这一普遍共性之上,都是值得同情的。这一点几乎完全独立于正面的道德和价值:《山峡中》的小黑牛被害死,无论小黑牛是否做错了事,在其被压迫这一点上,完全是需要被理解和同情的;在《我们的友人》中老江偷马、贩烟,是个“坏蛋”,但“看见这可怜的人吐出可怜的声音,我便不由得不转成另一种的心情原谅他”[3]97。由于“压迫”与“被压迫”的行为发生在东南亚特定的地理空间之中,使得这一地理空间本身也带上了“政治性”,它恰好变成“压迫”话语所构筑的斗争双方进行斗争的场域,这一斗争也内在地体现为现代性与本土性的冲突与对话。
将空间政治化处理,使得作家的“自我认同”得以在此充分展开。泰勒认为,“自我的意识就是关于我成长和生成的意识。这种事情的真正本性不可能是瞬间的”[10]74。个体不仅需要时间来获得自我的连续性(personality),而且,“只有作为成长和生成的人,通过我的成熟和退化、成功和失败的历史,我才能认识我自己。我的自我理解必然有时间的深度和体现出叙述性”[10]74。泰勒所说的这一过程被艾芜表述为“上课”,而“南行”则成为某种“教程”。对艾芜来说,这一“教程”的起点源于切身的“饥饿”体验。在《南行记》中,在将魏大爷、鬼冬哥等人视为被压迫的下层民众时,艾芜肯定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反抗力量,因为这种力量所针对的对象是“压迫”力量;反之,当他们害死小黑牛时,他们身上的这一强势力量则体现为某种“压迫”力量,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而这种压迫性的强势力量自然也就成为需要批判的对象了。因此,我们会发现,在艾芜这里,“压迫”问题似乎不自觉地被转换成了“权力”问题,与其说艾芜是要反对“阶级压迫”,毋宁说他更倾向于反对一切具有“压制性”的“权力”。
(三)观影体验与“知识化”
艾芜“国民性”书写的第三个面向,来源于其观影的体验。1933年11月,艾芜在为即将出版的《南行记》所写的《序言》中,提到他曾在仰光的某个戏院里看了一部名为Telling The World的好莱坞电影,片中极尽渲染支那民族的“卑劣”和“野蛮”,由此带给艾芜极大的震惊体验,“从此认清了文艺并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11]4。艾芜认为像Telling The World这样的电影,会使“世界上不了解中华民族的人们,得了这么一个暗示之后,对于帝国主义在支那轰炸的‘英雄举动’,……加以赞美”[11]4。然而,在观看电影的时候,艾芜说“全戏院的观众,欧洲人,缅甸人,印度人,以至中国人,竟连素来切齿帝国主义的我,也一致噼噼啪啪大拍起手来”[11]4。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批判国民性思想的由来。鲁迅批判国民性思想的产生除了受明恩溥《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影响以外,也来自于类似的观影体验。
鲁迅对他观看幻灯片事件的叙述主要体现在《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两文中。在《呐喊·自序》里,鲁迅主要是为了说明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因而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显得较为简略。他写道:“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而喝采”[12],这一表达在《藤野先生》中则变成:“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13]317《藤野先生》中的表达方式显然有别于《呐喊·自序》,在《藤野先生》里,“我”更多地是作为一个“后缀”被拖带叙述,似乎是为了自觉地与“我”的那些日本同学区分开来。在《藤野先生》后面的行文中,鲁迅这样写道:“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13]317我们发现,艾芜在观看影片时出现的“震惊”体验和他思想的前后变化与鲁迅此处的状况极为相似:由带有较为浓烈的殖民色彩的影片所带来的震惊体验,使得“民族感”被召唤出来。然而,艾芜与鲁迅的不同则在于,同为“震惊”体验,艾芜的反应是试图揭示出国民性中正面的反抗精神,“打算把我身经的,看见的,听过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给写了出来,也要像大美帝国主义那些艺术家们一样‘Telling The World’的”[11]5;鲁迅则显得较为悲观,回国以后,他“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便不禁感叹道“呜呼,无法可想!”[13]317从此,他便开始“疗救”国民性。
艾芜做出的回应,从他的表述来看,无疑是某种“知识化”的处理。在他看来,美帝国主义通过影片Telling The World试图表达的,是对中国“国民性”知识的曲解,所以,要对抗这种曲解,他所寻求的资源,也势必是“知识性”的。因此,从他将南行比作“大学”这一“教育话语”本身来看,我们就可以理解,“国民性”为什么会被作为“被压迫者的知识”这一“知识”形态被呈现出来。虽然鲁迅也接受了明恩溥关于中国国民性的知识,但是他的话语并不建立在知识层面,他不会对《中国人气质》一书中的知识话语提出挑战,而幻灯片事件也并不是在知识形态上影响着他最后的选择。如果说,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冲动依然还有知识成分在内的话,那只能被表述为:鲁迅认可“幻灯片”和《中国人气质》中对国民劣根性的指认,他并不反抗这一知识性的表述。而鲁迅所认可的在艾芜这里恰恰成为需要被质疑和批判的。不过,认识到这一点,还不足以完全解释艾芜将国民性表达为“被压迫者的知识”的全部内容。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帝国主义被认为是需要被批判和质疑的,那用以批判和质疑帝国主义的“国民性”“知识”——被压迫者的知识——本身是否可疑。罗岗认为:“知识不仅是被政治化的(politicized),知识就是政治(political)。”[14]艾芜在书写老江、魏大爷等人的“学问”和“知识”(它们不是写在书本上,因而无法被知识化和组织化)时,这种书写本身就体现为某种选择性和组织性。因此,质疑“被压迫者的知识”是否可疑并不是关键所在,关键在于“被压迫者的知识”如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