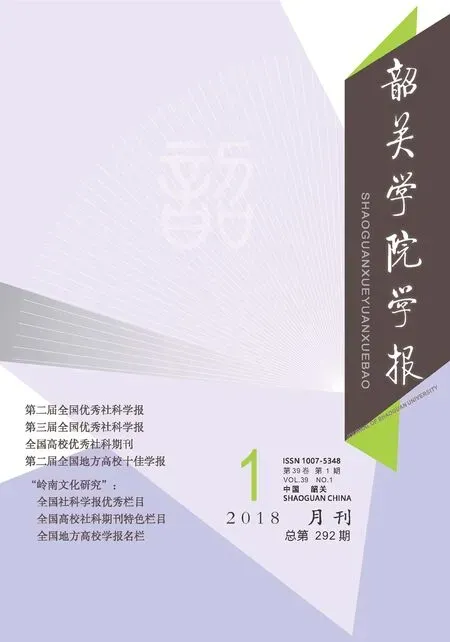佛源禅风旨要
郑 平
(韶关学院 文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佛源是中国当代的著名禅师,云门宗第十三代传人,对云门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而在禅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佛源一生所为堪称禅宗大德,其修禅风格特色鲜明,主旨要点可提炼为三个方面:纯粹的禅心、互参的禅法、空明的禅趣。佛源一生的向禅之心真诚坚定,悟禅之法注重理解与践行的相互参证,说禅之文追求空灵明澈的审美意趣。如此为禅之风是禅门信徒的可贵所在,对于当前的宗教界具有相应的启示意义。
一、纯粹的禅心
佛源(1923-2009),俗姓莫,名汝宝,号仁辉,湖南桃江人。18岁出家为僧,29岁时来到云门寺,依止禅门泰斗虚云大师,成为虚门弟子。虚老为之赐法名妙心,法号佛源。后继虚云任云门寺方丈,成为云门宗第十三代传人,住持云门数十年。佛源自出家始至入云门寺,期间十余年,曾经辗转数地,历经几番波折,但始终未有动摇迷惑之心。由其早年从教生涯,已可初见其信佛意志之专一。
自1951年入寺至2009年圆寂,佛源禅师在云门寺历经近60载。期间禅寺兴衰不定。佛源禅师长期担任云门寺方丈,禅寺沉浮与禅师荣辱密切伴随。正是其不同平凡的修禅生涯,表现出了他的纯粹的禅心。期间有三件重要事件,最能体现佛源的向佛之真、护佛之坚、弘法之诚。
建国初期的1951至1952年间,云门寺经历了一起“云门事件”。方丈虚云经难犹生,虔诚弟子不肯离弃。1952年再次波及云门寺,情势再度危急。虚云“预知此乃又一大祸临头,若北京不来人解决,全寺僧人又要遭难。乃招大家于方丈内开会,望能有人去北京求助,但众僧摄于威胁,无人敢去,老人焦急万分。”[1]2167-2168当此危急关头,佛源挺身而出,“先于二月十九燃指供佛,见此情形,毅然受命北上。”[1]2168佛源历尽艰险周折,才得中央政府干预,事件终于平息,随后,佛源一行奉命紧急护送虚云进京,使其人身安全终有保障。佛源此番之举,更见其心之纯。
1953年,佛源任云门寺住持。恢复寺院秩序,组织集体生产,实现自给自足。1958年,反右运动开始,佛源被划为右派,在南华寺接受劳动改造长达21年。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佛源历尽磨难,但道心坚毅。1966年文革兴起,南华寺遭受一场浩劫,保存于此的六祖惠能大师的真身被严重破坏,红卫兵们声称要破除封建迷信,把它用车推到市区大街游行,期间有人打破真身,将腑脏抓出,骨头丢落。佛源目睹六祖真身毁坏,非常难过,待众人散去,一人偷偷收敛灵骨,埋藏地下。文革之后,佛源不顾阻挠,在中央有关人士干预之下,取出灵骨放入六祖真身体内,六祖真身得以恢复。佛源甘冒生命危险,维护这一保存已逾千年的祖师真身,这一舍身护法的壮举最见其禅心之纯粹。
80年代国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各地宗教寺宇逐渐恢复。1983年佛源法师从北京回到韶关,重新振兴云门寺。当时的云门寺院满目疮痍,殿宇残破,危房满目,经像难寻,法器尽无。更为重要的是僧人散尽,只剩三人。面对如此不堪景象,佛源知难而进,勇担重任,重建道场,重集众心。
他日夜操劳,事必躬亲,率众出坡,不辞辛劳。在他的感召之下,经过一番艰苦努力,道场渐次修复完好,设备也日渐得以完善。如今的云门寺院,格局宏大,面貌庄严。更为重要的是,在佛源的精神感召之下,四众仰皈,住僧日增,祖庭常住三百余人,板点分明,道风整肃,呈现出一派历经磨难而法脉不息的六和禅林气象。佛源人至晚年,仍然不遗余力,为复兴道场而如此奉献,其弘法之诚心昭然可见。
在佛源的一生里,上述三件大事,最能体现其禅心之纯粹。这种坚实精诚的从禅心志,是其功德得以成就的根本所在。佛源住持云门,始终坚守传统,拒绝流俗,因此寺院一直以来戒律清净,道风纯正。在日渐汹涌的经济浪潮的冲击之下,如今的佛禅道场,尤其是一些著名丛林,难敌诱惑或压力,逐渐沦为追求收入的旅游景点。他对这类现象深感痛惜,每在重要场合便公开批评,“现在许多的地方修庙,庙子修好了,但不是和尚的庙,和尚是到那里做一个服务员,就是搞钱,作为一个商品,搞经忏也作为一个商品,反正你拿钱来我就做,你没有钱我就不给你做,作为一个商品,把佛法作为一个商品。这样搞啊,将来佛法就完了!我们和尚如果为一个职业者,现在的僧叫职业者,就变了,完全变了!”[1]361-362并以此诫勉门下弟子,其语气之深切,亦见其禅心之纯粹。
二、互参的禅法
佛源的修禅之法特色鲜明:主张学修互参,解行相证。也就是理论和实践互相参照,理解和修行彼此证悟。其具体实施方式就是兴办教育和农禅并举。
佛教对信徒的修行,提出了一套基本的法则,即信、解、行、证。具体而言,也就是树立信仰和净化心志,理解佛理和领会本质,付诸言行和渗透生活,验证奥妙和彻悟佛性。由此可见,其中的“解”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佛理的知晓是正途的保障。对此,佛源深有理解,并操持始终。
上课伊始,教者提问:“你从哪里看出武松是个什么样的人?”学生互相启发补充,从“闪、抡、劈、丢、揪、按、踢”等一连串的动作看出武松智勇双全。这是全面捕捉课文信息,培养学生思维全面性的第一步。正当所有同学把目光都集中到描写武松的语句时,我轻轻发问:“难道表现武松只有从武松身上下手?”学生一下子有了发现:“哦!还可以从老虎‘一扑、一掀、一剪、咆哮、扒坑’等词语看出老虎的凶猛,老虎越是凶猛,越能反衬出武松的智勇双全。”
一方面,佛源特别注重教理研习。他认为,通晓佛禅理论是信徒能够正确入门的基础,否则,佛子就难免会盲目修炼。佛教的终极目的是启示智慧和普度众生,三藏经典透彻地教示了智慧的内涵和普度的途径,因此,通达教理确是佛教修行者的必要条件。他多次重申自己的理念:“一个出家的法师不研究教理,不但不能够弘法,而且就自己的修行也是糊里糊涂。”“古代的祖师讲,教理行证,我们就是要通过教育来明白理论,通过行持达到证果。”[2]为此,佛源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以加强佛子对教理的研习。早在1989年,云门寺就创建了僧伽培训班,三年之后,培训班扩大升格为佛学院。发展至今,云门佛学院已有四个专业,学僧二百余人。在开学典礼讲话中,佛源明确表示寺院办学目的,就是让僧众通过经教觉悟心性。“以前那个时候,达摩祖师到中国带《楞伽经》来,《楞伽经》管我们的心性。后来到六祖是《金刚经》,没有离开教理。……如来是我们的心,法界亦是我们的心,要发扬我们心性。性是什么?不研究教理,你怎样明宗呢。心是什么?明心见性,出家人根本的目的就是明心见性。了生死,不明白你的心,不见性,怎样去了生死?”[1]94他勉励学僧道:“佛学院的同学那就要努力读,拼命读,把教理搞通,三藏十二部,南传佛教也要讲一讲,要学好四禅八定、五家宗风、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三乘、四果、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一步步了解这些道理。对如来一代遗教,如果我们知道,道理摸得清清楚楚,自己才知怎么用功。”[1]95
另一方面,佛源始终强调实践体会。禅师一直主张徒众的参悟禅道与日常生活的渗透结合。有人用上百万字来注解《坛经》,请老和尚写序,老和尚写了评语“一部坛经字已多,百余万字墨成河。如知本来无一物,月白风清唱赞歌。”[1]1792老和尚说:“修学,学要不要学?学也要学,但天天学没有修,那是没有用的。”[3]209在佛教对信徒的修行要求里面,“解”而后“行”,才能实现“证”,也就是说,思与为,二者互相参悟,才能达到最终的明了心性。佛源的主张与此完全符合。其重要表现之一,即一直力行农禅并举的传统道风。这是一种融禅于农、以农参禅的生活方式。云门寺院一直坚持“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传统。要求住寺僧人都要参加劳动,做到自食其力。不论职位高低、年龄大小。他自己身体力行,率众种植水稻、花生,栽培果树和竹林,困难时期还会上山砍柴下山去卖。寺院现有的五百余亩田地,在全体僧众的辛勤劳作下,基本能够自给自足。寺院全体僧众每人都有自己的活干,或耕田种菜,或煮饭扫地,或建筑维修,或迎宾待客,养成了农禅一体的道风。另一重要表现,是重视日常生活的修禅参悟。佛源禅师强调,对于佛理的体悟,应该渗透于僧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于禅法的修行,应该表现在僧人一生的行为细节之中。也就是说,修行参悟不仅限于农业生产,而是贯穿于所有的僧务工作或个人行事。对于云门佛学院的办学宗旨,他明确说明:“这个佛学院是丛林化,佛学院的学习是丛林化,你将来读书出来了,对丛林的东西不懂,规矩不懂,功课不熟,生产劳动都没有搞好,你连地都不扫,那像什么话?”[4]学院里的僧众,无论学习什么专业,在读书的同时,都必须随常住过丛林生活。学僧们平时除了上课学习以外,一律坚持早晚功课、过堂、出坡劳动、坐香、布萨等日常活动。学院里面的学生,毕业基本就能胜任知客、维那、僧执、班首等职,由此可见禅师对学修结合的重视。佛源对于行的重视,本质是想让参禅之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过程中都要回光返照、提持正念。对此,他有如此开示:“你要把正念放到生活中去,走路也好,穿衣也好,迎宾待客也好,都要有一个正念,都要有清净心、觉悟心,那个就是禅。”[1]596“除了穿衣吃饭,屙屎放尿,迎宾待客,有什么禅机呀!两手空空,空手而来,空手而去,就是最高的禅。”[1]184-185也就是说,禅就是消除了各种妄想的真实生活,无妄想的生活即是禅。对此,他在《七月初六广州明芳明涛居士索句》中写道:“饥来食饭困来眠,坐卧经行总是禅。十字街头无色相,一轮明月挂青天。”
总之,佛源禅师的修禅之法是以解行互参、学修并重为特色。一方面重视学理,一方面强调修行。因此,创办教育和从事劳动相辅而行,为培养优秀僧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净慧禅师这样评价佛源禅法:“以农禅为家风,将不可思议的禅法融合在日常生活中,在耕田种地、吃饭穿衣乃至嬉笑怒骂中参禅悟道,令学人在每一个当下回光返照、领受法益,成就了一片独特的禅门风光。”[3]103
三、空明的禅趣
作为一位学富思深的高僧,佛源不仅勤于教化,还长于文学,特别是其诗作,佳篇颇多。佛源留存下来的诗作、联语等文学性较强的作品,经由弟子记录整理,陆续收入相关宗教文化典籍公开出版,主要的是关于云门禅宗的三部著作,即《佛源老和尚法汇》(明向主编,四川省佛教协会2006年出版)、《佛源妙心禅师广录》(冯焕珍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出版)以及《佛源妙心禅师禅要》(冯焕珍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出版)。佛源诗作题材丰富,内容广泛,既有开示、酬赠,也有感怀、山水。他一生以参禅传戒和护法兴教为己任,僧人、俗众多有求教、乞示,前辈师长、后学衲子,僧界同参、在家居士,他随缘接引、见机开示,所以诗作多为开示、酬赠之作。又因他的晚年多驻山寺丛林,因此题咏山水、抒写感悟的作品也数量不少。
身为僧人的佛源,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无论从宗教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都可看到其中的个性特色。他的诗作、联语所表现出来的禅趣,带有他的个性气质。概括而言,佛源的禅思意趣,是以空明为特色。具体而言,这种空灵、澄明的审美理想,表现于其作品中的三个方面,即法理、境界、意象。
首先,佛源作品的论禅之理有空明之趣。
僧人以参禅弘法为任,所以僧诗当然是以阐释佛理为要。以诗寓教,多有方便,因此,以诗参禅、借诗弘法,是宗教界的一个悠久传统。对于高僧来讲,无时无地不是参禅道场,他们吟咏修行生活,往往语涉禅机,因事说理。佛源禅师也是如此,他的诗作吟咏源于弘教之心,或者表达佛法禅理、禅修心得,或者开示学人、劝人起信。而在论禅之理时,诗作特别突出空明之趣,形象启示佛禅空明见心的本质。以下几首诗,就是典型的例证。“饥来食饭困来眠,坐卧行经总是禅。十字街头无色相,一轮明月挂青天。”(《广州明芳明涛居士索句》其三)“一部坛经字已多,百余万字墨成河。如知本来无一物,月白风清唱赞歌。”(《题某居士坛经注》)“学佛原来是歇心,慈悲手眼即观音。若能一念灵光耀,遍地风光春满林。”(《赠谢力贤赵力通居士》)这些诗句警醒世人以修持心得与参悟智慧,印证禅宗“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参悟要义。形象指点众生佛法就在当下生活,禅并非遥远神秘,其实就是人生的自然状态。而修禅之道在于清净本心,消除累赘,做到思理空明,找到自性。类似的诗作还有“梦幻空花如水月,拂开尘垢识心灵。”(《云门丈寺写怀》)“风花雪月一时休,哪管春秋运与筹。只要无心于万物,乾坤任转自然稠。”(《和僧诗》)“佛我众生同一心,只因迷悟有升沉。圆明清净今古合,听取如来妙发音。”(《赠黄志伟》)这些诗句说明人生的虚幻、贪嗔的恶果,指引众生早日觉悟,了脱生死。这些论禅之语,虽然韵味较淡,但还是力求以直白方式指引空明思维。
其次,佛源作品的悟禅之境有空明之趣。
禅宗强调自视本心,自寻本性,以参究之法,达到心性本源。佛源作诗注重心与境合,体现个体生命与天地万物的彼此同一。将外界眼中的山水风月,内化为禅者心中的主观境界。而这种境界,玲珑剔透,虚空清明,也是以空明为特征。以下几首诗作可为例证。“北粤云门千嶂奇,桂花坛影印禅机。相逢一笑群山舞,翠竹青松满目晖。”(《颂云门山大觉禅寺》)“午宴龙山系画舟,行云流水意何悠。回光返照来时路,似鸟飞空迹不留。”(《参加中日韩三国佛教文化交流会日本会议》)“芒鞋破袖随云水,淡饭香茶聊业痕。满目青山无一事,松风明月伴法轮。”(《德真法师忆述辛卯年我离开益阳后家中亲人卜问吉凶关帝示机语云真心即佛空幻为天当时我法名真空有感于此试为二韵》其二)“寻幽访隐上凌云,古涧泉声入耳闻。山似观音天际耸,寺朝西面翠微芬。”(《探圣一老法师》)“共笑人生为逝水,随波逐浪向低流。孤高一曲和声少,涧壑云天笑不休。”(《客居志莲探圣一老法师并看望宝林寺方丈见智大和尚》其一)又如“一溪云水自然界,渔夫桃花分外玄。”(《与愿炯明禅等访武陵桃花源》其一)“尘埃不到神仙地,花落花开不记春。”(《与愿炯明禅等访武陵桃花源》其二)大自然的一切都在演示着佛法空性,作者从自然出发,构建直指本心的空明境界,使得心与境同,以此来体现“禅观自然”的认知方式和“明心见性”的参悟过程。
最后,佛源作品的说禅之象有空明之趣。
佛源诗作的取象特点也是重在空明。为了启发禅思而创造禅境,而境界的特征决定了意象的选择。作者在修行生活中,选择具有空明色彩的形象,点化入诗,使得玄妙的意趣能够生动表现。在这些具有空明色彩的意象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月”。例如下列诗句:“禅家独爱曹溪月,照彻澄潭古道场。”(《和成都冯学成居士》)“三乘教法秋天炯,一片禅心月色高。”(《云门天子》)“禅风拂尽千重嶂,明月光辉无与俦。”(《怀虚公老和尚》)“人间至此生禅悦,皓月一轮照古今。”(《礼嵩山少林寺》)又如联语:“归来一路禅心寂,独抱双林明月回”、“归来直入如来地,坐看虚空明月辉”(《云门凉亭组联》)作者以澄净空间的明月清辉,表达对普照佛法和清净之心的体悟,进而以玄妙的禅境启示空寂无著的心性。佛源作品中的空明之象,除了月,还有“云”。例如下列对联:“慈悲峰顶云常绕,古亭寺中月色留”、“剪一片慈云来补衲,留当前皓月好看经”、“夜听水流松竹月,昼看云起慈悲峰”(《云门寺联》)。又如“满目风光无俗念,白云片片似袈裟”(《访庆南梁山灵鹫丛林迎度寺知因长老》)。这里的云,无挂无碍、任性随缘,空人心性,是富有禅味的形象。此外,“群山相对终无语,一水长流却有声”(《其它联》)等以“水”为意象也值得注意。水的清净无碍与明心见性的佛理内蕴相符,取水为象,参水悟心,以化禅意,以示禅心。
总而言之,佛源的诗作联语,多用明月、白云、流水之类的形象,它们都带有空明色彩,和佛禅空明审美意趣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佛源的禅风要旨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也就是,纯粹的禅心,互参的禅法,空明的禅趣。法师的真诚坚定的向禅之心,解行并举的参禅之法,虚空明澈的说禅之趣。这些个性鲜明的禅僧品格,在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释明向,冯焕珍.佛源妙心禅师广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明斌.深切缅怀佛源老和尚[J].法音,2009(12):35.
[3]释明向.佛源老和尚纪念册[M].韶关:云门山大觉禅寺,2010.
[4]冯焕珍.佛源妙心禅师禅法初探[J].佛学研究,2011(1):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