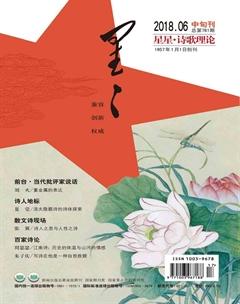写诗在他是一种自我救赎
朱子庆
新诗或曰现代诗遭遇读者信任危机,这一现象不是现在才有。问题的吊诡在于,近年来人们对新诗的质疑异常汹涌,它发生于新诗创作空前繁荣之际,而且质疑之声直指:“诗歌的标准何在?”言下之意,现在的新诗创作已完全失范,全乱套了!此时在物质商品生产的彼岸,却行行业业都在颁布标准,而且每一次的产品出问题(譬如三鹿奶粉事件),都会引发对既有标准的修正。野松邀我为他的新诗集《裸袒的灵魂》作序,这颇令我沉吟再三;我之所以再三沉吟,仍是源于诗歌标准问题的困扰。
诗歌书写固不必且应该坚决拒绝标准化——标准化乃是诗歌的敌人,但是,问题马上就随之而来,如果你谈论诗歌而心里没个“准谱”,那么,要么落个游谈无据,要么你就尊口难开。“道可道,非常道”,举凡可道的诗歌标准,总难脱人为、主观因而片面的指责,而且别指望会“天龙闻而下之”(《叶公好龙》),给出一个客观的现身和证明。这么讲无非是说,诗歌标准讨论此路不通。但面对诗坛的失范乱局,我们是否就束手无策呢?其实,“可道”者非常,而“常道”恒在,相比于对诗歌标准的热闹探讨,我们对“诗道”的关怀似乎太不够了——甚至根本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诗道”关怀之所在,显然更深刻、更本质。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任何一个诗歌标准或一种诗歌主张,其被人们承认多少、接受几何,根本原因还在这里。但毕竟“诗道”之深无远弗界,本文宕出一笔,不过意在提起关注。至于下面谈野松的诗歌,不敢坐而论道,权充一得之见吧。
诗人野松算得上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了。由于曾为其诗集《歌唱和自白》作序,对他早期的诗歌创作,我有过一种“地毯式轰炸”的阅读。观笔名而知志,野松跻身官场(“以鱼的姿态,潜入不深也不浅的水中”),却心期于自在,比德于青松。既曰“野”矣,何必青松?可见其情致趣味,是古典的、不那么现代的。却也并不落伍,不但曾在互联网上纵横捭阖,十分活跃,其手机写作也兴头甚高,时常于兰台走马、官会高蹈之余,既托物而言志,亦缘情而绮靡。那么,在怪力乱神网名充斥之地,“野松”二字表达的“坚执”和诗歌书写的“赋性”,就给定其人其诗一种独异的存在。在我看来,诗歌书写在他,与其说是一种雕镂创作,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救赎。
一向以志士仁人自期自许,这样的诗人在诗坛已近乎古董,在官场恐怕更是“骨灰”了。然而在野松的作品里,最初却正是这一点吸引我的眼球。中国的文学传统历来最重“气”,言志之作历来以“气”胜,野松早期的诗歌有这种“气”;他又性喜游历,每登临名胜古迹必赋诗,写到佳处也不无“气象”,这多少就潜接古典意趣,就颇对了我的胃口。我们知道,今日新诗个性恣纵、疏影横斜,自有诗人的 “个体”自在,全然不理睬什么“修齐治平”。而在我,于花朝月夕的阅读中,悠然心会的作品,大多还是那些“有为”之作——原因无它,人生本来荒寂、一地鸡毛,慎终追远的心性,使我们每每择善而从——诗歌大可“以美储善”也(李泽厚语)。于是,我颇肯定野松的创作;同时也发现,在他那个时期的写作中,已潜含了某些厌烦、揭露和批判的意绪。
然而,即便在前些年创作的“壮游”之作中,也存在过纵主观、情景拼贴的问题——不止是王国维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物皆着我之色彩”;趨于主观孤峭,终归有欠浑成;在书写形态上,则难脱旧式“遣怀”的窠臼。而我一向珍视的“气”,也有些馁而散了!说到“遣怀”,我们似乎陷于这样一种悖论,即一方面,现代诗由于其形式或语言的不支,在“遣怀”一路殊少承载和包容力,所以诗路(亦即题材面)过窄;而另一方面,那种类似宋词“上下片”(写景抒情)的偷懒的“遣怀”,又使其书写殊少意兴、单调无味——因为,毫无疑问,浑融于主体抒情的书写,乃是新诗的根本特征。为此,我一直期待野松:既稍敛其主观,亦放纵而超越,总之要“蜕变”,来一个抒情方式的现代“蜕变”。
这样,当我读到他的新诗集《裸袒的灵魂》,其抒情方式的“蜕变”和现实内容之 “深化”,令我感到眼前为之一亮。读着这些作品,我感到其中有按捺不住的“慨乎之言”,有不甘沉沦的内在冲动,而由于部分直击题材不无敏感,远远不是“现实主义”写照所宜,所以便借意象、象征与主体的浑融关照,使其“反虚入浑”、别臻高致,反而使他的作品获得一种熨帖而内在的抒情品质。对下列两句诗的蕴藉通脱,我就印象殊深:
不说命运,不说沧桑
燃烧的火焰在大海之上
而《世界已经苍老》,则书写了一种大悲凉,令人不免联想起当年闻一多的《死水》——这种联想令人暗自吃惊:
目光所及都是废墟。
尽管时间像绿叶依然滴水。
田园确实荒芜了。
红裙子的蝴蝶在坟墓之上翩飞。
世界因这些沉重而拥挤的头颅苍老。
“红裙子的蝴蝶在坟墓之上翩飞”,这是当今时代精神的象征?
几年前,在某作协召开的关于网络文学研讨会下,一个来自深圳的诗人告诉我,他的一位诗友,自边地一个县长的短暂任上归来,却再也写不出那种“白”诗歌,我听了不禁黯然神伤。是啊,“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句)然而,“君问归期未有期”!(李商隐句)“归来池院‘非依旧”!(改白居易句)《世界已经苍老》呈露的正是一幅时代精神荒原图。此类表现诗人对现实忧思的诗作,诸如《孤独》、《在这样的季节》《春天了,叶仍落满地》,均有深意存焉。
从不做“口语诗”的“物观”絮语,野松是偏于主观(“说”)和抒情的。而当他一旦对“说”(主观直陈)有所警觉,取径于敛藏,着意将意象、象征由修辞性运用,转而为一种整体性“境象幻构”,一切就焕然而为“表现”了:
我已倦。已怠。那修篁最终不属于诗人。
我前生面壁几十载,今生依然不清不醒。
我竟欲渡河!
伤是自己的。去吧!
天空无风无雪。空!空!空!
但生命最后的诗句还是要写的。
结束就是飞翔!
飞翔就是渡河!
——《飞翔就是渡河》
此诗如就其内容而言,似乎是前诗的逻辑延续。它从“我已倦。已怠”入手,其底子是高度主观抒情的。但仔细体会,你却感到它并不空泛,诗人虽说不事写实描摹,诗中却宛然有画意、有事境,诸如“修篁”、“渡河”、“天空无风无雪”乃至“飞翔”,这些散碎的意象、事态或曰经验碎片,通通有着可整饬于特定时空之树的整一关联性。试想一下陈子昂的名作《登幽州台歌》和许多古典作品,那种整一于客观的“意境”呈现,相形之下,此诗结体趣味之现代,我以为是显而易见的。而其可贵之处却在于:寓于主观的客在(经验)散点直观。它使我们阅读的诗思,于体认之际,有可能迁延和归宿于理念深处。
这在野松,当然是化蝶一般的“蜕变”,是其抒情方式的一个小小飞跃。
以下的发挥或许关乎“诗道”,即诗歌鉴赏的经验告诉我们:拘泥于现实整一的书写是愚笨的,而一味玄空高蹈也与诗疏离,“允厥执中”的诗歌书写,似乎始终是让诗句处在主客逆反的滑动之中,亦即当其以客观呈现时,它内在地在向主体方向滑动;而当其以主观出现时,却又内在地向客体方向滑动。这一“诗道”图式,令人想起《易经》的“阴阳鱼”图——那式微而渐巨的阴阳潜转。这种主客体的对象化潜变、“转贷”,是诗之为诗的“诗道”所寄?是诗歌形象思维的“诗艺”核心?野松近作抒情方式的“蜕变”,庶几近之。
在野松的“裸袒的灵魂”系列诗作中,无论像《潜水》、《大海深处依然是大海》的整一取景,还是《一棵雨中开花的树》、《我一直在无边的空寂中抵抗》、《生命是孤寂的》的立足抒情,都具有这种逆向潜转的特征,从而富于感性直观和象征意蕴。例如《大海的深处依然是大海》,作品中的“哦,你说”的抒情视角,既有别于“我”(第一人称)的主观抒发,也和他者眼光的“物观”不同,这是一种主客互逆的视角妙转,本质上它是将“我”化入“对象”,通过一种对象化直观,“以盐的无形”把主体“转贷”出去。它不同于古诗的客观整一(意境),而是结体于主观整一的,然而其中有象(意象、事象)——经验的散点直观的语象,那种可以联点拟境(物境、事境)的语象。正是这些语象,草蛇灰线地凝结着诗人的经验积淀,给了读者归返自身的“转贷”可能——而在经验积淀的深处,人与人“理念”潜同因而潜通。无所附丽的抒情容易沦于“说”(议论),同样,无所附丽的“物观”,容易流于泛实——空泛无寄的琐屑现实。情无孤悬,而合于“诗道”的表现,恰恰是于物表(主、客观)之下别有积淀。
《飞翔就是渡河》是一首令人读后为之感到不安的诗。该作隐然传达出作者的现实幻灭感,对诗意地栖居的可能(以“修篁”象征)的幻灭;而“生命最后的诗句还是要写的”,其执著的主体诉求,俨然把诗歌“升级”为终极目、“以美储善”的宗教——给了李泽厚主义一个实证。此所以我说野松的诗歌书写,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自我救赎。如果说《渡河》一诗在宣说寻求解脱(“飞翔”),那么《这决不是我道路的尽头》,表达的依然是渴望自由的诉求:
高过我心中那片高地的
河流,此时,也正从我的体内
奔入这茫茫的大海
这是其倾心和价值认同的直观表达,那汇入“大海,这自由的元素”(普希金诗)的,被他在心头高举的“河流”,无疑正是不羁的自由!这是一首更蕴藉、更积极,堪与前诗媲美的佳作。那么,是什么在消磨着诗人的意志,他挣扎于其中与之抗争的又是什么?循此我们即走入其现实关怀的沉重深处。《潜水》是野松对自身处境的隐喻:“缺氧的水在浸润我的同时/给我一种压迫,一种强行的压迫/……我不是一条得水的鱼儿”。价值游离产生的心理厌烦,导引诗人的诗笔向外、向下,由此揭露和批判现实之作,开始一一浮现……
限于篇幅,本文仅就抒情方式的“蜕变”及主体特征,对野松近作略陈管见。在我看来,今日中国诗坛的众声喧哗、浮尘无序,正反映了写作者精神的迷漠无据。而欲深化有关诗歌标准的讨论,首先必须对这一精神现状有所洞悉。如果脱离之,欲求一个“约略近之”也难。
野松近期詩歌的艺术“蜕变”,在我看来,恰在于内容上返还经验“积淀”,在“诗道”上趋于主客体契合,而在对现代人精神状况的呈现上,则表现出真挚而热切的价值诉求。因之可视为一种成长和进步。这种成长和进步,是否隐微例证着当代诗歌的某种成长与进步?诗事一局棋,举凡盘面存在(无数个别),都自有彼此缠络的整一关联性。据此,打量一下野松近作——解剖一个麻雀,或可于我们致力构拟诗歌共识,不无裨益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