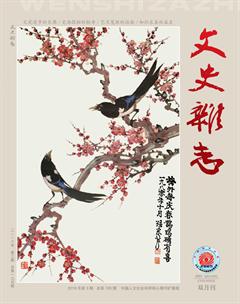古代的学与仕
王文承
学与仕的关系,是古代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敏感问题,直接牵涉到学习观、仕宦观和人生价值观,牵涉到长达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对此,古籍中有不少论述,构成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品尝研究。
一
1.学(读书学习)与仕(从政为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古人求学或送子读书,大体有两种目的:第一种,不带功利性质,旨在提高素质,完善自身,明理悟道,为善积德。古籍一再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日就月时,学有缉熙于光明”“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读书以明理,积学以富才”“欲知天下事,须读古人书”“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理自知”“书犹药也,可以医愚”“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裙”,以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为善最乐,读书便佳”“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学(读书)与仕(做官)没有多少联系。
第二种,急功近利,读书求学就是为了当官。所谓:“读书都为稻粱谋”“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出仕先入学,读书利万倍”“卖金买书难,读书买金易”“杖头钱尽,俯仰何堪,论寒苦则书不可不读;名场争重,落魄人轻,论势利则书不可不读”,等等。古代大多数文人及其家庭的理想、动机、目标,就是读书做官。在这种情况下,学与仕紧密相联,合二为一。韩愈写道:“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两家各生子,孩提巧相如……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达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符读书城南》)此诗把读书的意义提到最高度(“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并指出:子孙能读书为官者意味着飞黄腾达,为公为相为龙。反之,不肯读书学习,就不能入朝为官,只能充当“马前卒”,如同“猪”。
2.古籍提倡学以致用,经世致用。对此有两种理解:其一,学以致用,首先和主要是将所学所学用之于治国理政、从政为官,故士(读书人)必仕(从政为官)。《韩诗外传》:“君子学之,则为国用。”子路:“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韩愈说:“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上宰相书》)其二,学以致用,其用颇多,既可以将所学用之于从政为官,也可以用之于修身齐家、为人处世。能修身齐家、与人和谐就是学问,而且善莫大焉。因此,士(读书人)可以仕可以不仕。苏轼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二者各有利弊得失,应做到“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指不仕)皆有节士廉退之行”。(《灵壁张氏园亭记》)宋熙宁五年,钱塘之士贡于礼部者五人,杭州太守陈公作诗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时迁者松柏也,万世不移者山也,时飞时止者鸿雁也”。此诗以流水、高山、鸿雁、松柏為喻,讲为官做人必须遵循的动静出(出仕)处(不仕)之道。苏轼《送杭州进士诗叙》评论:“士之求仕也,志于得也,仕而不志于得者,伪也。苟志于得而不以其道,视时上下而变其道曰:吾期得而已矣。则凡可以得者无不为也,而可乎?”他反对求仕者“凡可以得者无不为也”,主张仕与不仕取决于“道”,决不能“视时上下而变其道”,还说“而况使之弃其所学,而学非其道欤!”这是相当坚定鲜明的立场和态度。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曾国藩具有真知灼见,他认为读书之目的和用处是进德修业。士子可以谋取科名仕宦,但不是读书学习的主要目的和用场。两相比较,进德修业是大者远者,科名仕宦是小者近者。能否出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意(科名前定),不应强求;自己应该力争的是道德文章,孝悌齐家。这就叫“尽人事以听天命”。他告诉几位兄弟:“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至于“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总之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科名之所以为贵者,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曾国藩家书》)
3.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当官究竟图什么?出仕之目的何在?古代有四种观点和主张:
其一,千里为官,只为吃穿。当官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有权有势,升官发财,封妻荫子,光宗耀祖。
其二,当官首先是为了谋利(取得俸禄,养家糊口,丰衣足食),与此同时也要行义(履职尽责,造福一方),把利和义、私与公结合起来,不可偏废。
其三,当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抱负,施展才华,建功立业,造福社会,报效国家(朝廷、社稷),因为朝廷中的宦位是最好的平台、阵地和机会,让读书人(士)大有作为。欧阳修写道:“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惜之所同也……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言下之意,仕宦之志有两种,一种是追求荣华富贵,另一种是追求德被生民,功施社稷,后者比前者更正确、更高尚。
其四,当官意味着策名委质,委身致命,将自己献给朝廷,任由君王驱使,甘效犬马之劳,而不再顾及自我和家庭。所谓“念念用之君民,则为吉士;念念用之套数,则为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则为贼臣”。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和主张。
4.把读书求学之目的与从政为官之目的联系贯通起来思考追问。古籍提供的标准答案是:“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朱子家训》)文天祥就义前在衣带上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言下之意,读书和做官,都应希圣希贤,成仁取义,忠君报国,忧国忧民。杜甫写道:“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满腹诗书,才华横溢,志在获取朝廷中重要职位,把皇帝变成好皇帝,让民众过太平日子。可是事与愿违:“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当作“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反映仕途艰难,命运多舛,命运捉弄人也考验人。他还写道:“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后两句说自己只要不死,总想实现平生志向,意志何其坚定。杜甫还说自己“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也就是坚持忠君爱民。在不断碰壁受挫之后,他说:“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最后两句表示自己也不肯学尧时那两位隐士的清高,不愿放弃、改变自己的初衷、志向、节操。这正是“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而不是读书志在仕宦,为官心系富贵。
与“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系君国”紧密相伴的,是“尧舜事功,孔孟学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此是孔孟学术;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此是尧舜事功。总起来是一个念头”。(明·吕坤:《呻吟语·问学篇》)这个“念头”,就是胸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此“天下”,不仅是君王之天下,更是人民之天下。因此,无论读书求学和从政为官,都要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可以认为这两句名言代表古代读书学习和从政为官的最高境界,是学与仕的最佳结合,体现正确的高尚的读书观、仕宦观和人生价值观。它超越了世俗价值,摆脱了低级趣味,完全没有私心杂念。问题在于,这两句话说起来轻松容易,做起来沉重艰难,需要人们毕生为之奋斗。古代文场官场,不少人嘴上如此,外表冠冕堂皇,道貌岸然,内心深处和实际行动却与此截然相反。他们学术、政术和心术都存在严重问题,类似于假道学、伪君子。明人吕坤写道:“心术、学术、政术,此三者不可不辨也。心术要辨个真伪,学术要变个邪正,政术要辩个王霸。总是心术诚了,别个再不差。”“能辨真假是一种大学问。视世之抵死奔走者,皆假也,万古唯有“真”之一字磨灭不了,盖藏不了……道也者,道此也;学也者,学此也。”(吕坤:《呻吟语·问学篇》)
5.读书人(文人学士)入朝为官之后,还要不要继续读书做学问呢?大体有四种答案:
其一,當官后继续坚持读书做学问,“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仕与学、事业与文章(著作)相互支持促进,双丰收。这是好传统。
其二,担负重任,公务繁忙,加之才智所限,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顾一头,于是舍学问文章而保事业和政绩。
其三,一旦出仕为官,便不再读书求学。他们对读书学习毫无兴趣,当年苦读是迫不得已而为之,那只不过是手段、梯子、敲门砖而已。韩愈写道:“古之人日已进,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为学,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业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诗》曰:……‘乐只君子,德音不已。谓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务利而遗道,其学其问,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获一位,则弃其业,而役役于持权者之门。故其事业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韩愈:《上考功崔虞部书》)
其四,撰写奏折呈文时,办理政务遇到麻烦时,偶尔也翻书,从中找资料、依据、办法;或借读书作文吟诗卖弄风雅,装点门面。
客观地说,人的精力有限,既要从政为官干事业,又要读书做学问写文章(内含艺术创作),这是两难。欧阳修写道:“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刘禹锡)、柳(柳宗元)无称于事业,而姚(姚崇)、宋(宋璟)不见于文章。彼四人者犹不能于两得,况其下者乎!”(《薛简肃公文集序》)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古代确有一批杰出的文士出身的官员,包括欧阳修本人,从小就是“读书种子”,始终热爱知识学问艺术,读书学习对他们来说,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乐生要素,虽然公务繁忙,仍然手不释卷,笔耕不辍。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既在官场政界大有作为,又在文坛艺苑大显身手,仕与学相结合两不误。一旦告别官场,摆脱公务,便把主要心思精力用之于读书做学问搞创作。他们的人生轨迹,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青少年潜心读书——中壮年亦官亦学——老年致仕勤学。”在他们的心目中,公务有年限,读书无年限;当官是一时的,问学是一生的。所谓“学不可以已”“学至于没而后已”“朝于斯,夕于斯,数十年,如一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偶有吟哦殊不倦,深知文字乐无穷”。他们真正做到了以学为生,学与仕互动兼顾,实现了五“有益”,即有益于从政为官,有益于文化繁荣,有益于自身完善,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教育培养子孙后代。
二
研究古代学与仕的关系,有必要重温孔、孟、荀的论述,其中包含经典的学习观、仕宦观和人生价值观。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讲孔子。
1.孔子很重视学习,自己以学为乐,学而不厌,提出读书人(士)应“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不患无位,患所以立”,(《里仁》)而所以立者,仁义是也。《论语》记载,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言下之意,子羔质虽美而未学,遽使为官治民适以宰之。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先进》)范祖禹注曰:“古者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为学,失先后本末之序矣。不知其过而以口给御人,故夫子恶其佞也。”孔子主张先读书学习然后从政为官,以免糊涂官害人,这是远见卓识。关于学习目的,孔子曰:“下学而上达。”(《宪问》)即下学人事,上达天理。“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为己,指欲得于己也;为人,指欲见知于人也。孔子主张学习为己,即得之于己。用现代话讲,这是提高素质,完善自身。需要说明的是,“学者为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见知于人,取悦于人,炫耀于人;另一种是帮助人,服务人,奉献人。前者是恶习,后者是善行,应该加以区别。孔子曰:“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这个意义上讲,“古之学者”即模范的学者,既为己又为人。《颜氏家训》写道:“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尤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字,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这段文章,是对孔子上述格言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再说,学者用自己的知识才能帮助人、服务人,这是利人利己的双赢,如老子所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孔子的门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子夏还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这也是孔子的观点。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孔子虽然大力倡导非功利主义的或者说伦理主义的学习观,但也有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他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礼记·儒行》记载,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儒有……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儒有……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这是肯定儒者出仕为官。孔子还说:“儒……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通“现”),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言下之意,儒者出仕为官应遵礼合义。《论语》记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路》)所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也就是出仕为官,而且是职位相当高的官。孔子主张士(儒)从政为官,是有前提和原则的。他一再重申和强调:“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问》)“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孔子还有一段话:“鄙夫可与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确切的说是“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阳货》),《四书章句集注》引胡氏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贵而已者,则亦无所不至矣。志于富贵,即孔子所谓鄙夫也。”照此说法,则“士”有三种:志于道德者为丈夫,志于功名者为凡夫,志于富贵者为鄙夫。这分明是对读书一心为做官者的鄙薄。
不可否认,孔子自己也想从政为官。他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不辞辛劳地游说诸侯,必闻其政,欲谋其位。《论语》记载,子贡问孔子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他还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吾将仕矣。”(《阳货》)《吕氏春秋》记载:“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所见八十余君。”《孔子家语》记载:“孔子适郑。或人谓子贡曰:‘东门有一人焉……累然如丧家之狗。子贡以告,孔子欣然而叹曰:‘如丧家之狗,然乎哉!”但孔子求官,不同于一般士子贪图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行其道——以仁义治天下。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在教学上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这是崇高的思想品德。苏轼写道:“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后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贾谊论》)在苏轼看来,孔子和孟子从政为官,决不是志于富贵,也不是至于功名,而是至于仁义,即务引其君于道,以仁义礼乐等治天下、济苍生。
2.孟子对读书学习讲得不如孔子多,他简略地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四书章句集注》:“学问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则在于求放心而已。盖能如是,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可以上达。不然,则昏昧放逸,虽日从事于学,而终不能有所发明矣。”读书学习旨在明义理,“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孟子讲得最多的,是仕宦(从政为官)之目的和原则。《孟子》记载,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滕文公下》)万章问:“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孟子曰:“事道也。”(《万章下》)在孟子看来,“士”或者说“君子”读书学习是为了明道,从政为官是行道,伺候君王是事道,学与仕皆统一于道。孔子对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乎!”(《论语·述而》)《四书章句集注》:“圣人……其行非贪其位,其藏非独善也。”孟子对孔子的话加以发挥:“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下》)他斩钉截铁地说:“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告子上》)“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万章上》)孟子和孔子一样,把仁义道德看得比仕宦和生命更重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3.荀子认为,在学习上有君子和小人之分,二者具有不同的目的(志向)。其中,“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一可以为法则。”“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君子之学,“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其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劝学》)言下之意,读书学习之根本目的是进德美身,成贤成圣,与仕宦无关。荀子也赞成读书人从政为官,他自己也出仕。但他认为,当官必须走正路,靠德行取位。“故曰:贵名不可以比周争也,不可以夸诞有也,不可以势重胁也;必将诚此然后就也。”“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儒效》)荀子有一句名言:“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修身》)他把官位(富贵、王公)看成身外之物,主张重道义、修志意而轻外物。对待官爵与对待学习一样,也有君子和小人之分,结论是:“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修身》)。
在学与仕的关系上,孔、孟、荀基本观点一致,他们都主张学以增其智、益其德、致其道、美其身。从总体上讲,学不为贫,但有时也为贫。学者(读书学习的人)可以仕,也可以不仕。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仕意味着“达”,不仕意味着“穷”。达则兼善天下,建功立业;穷则独善其身,安贫乐道。君子先学而后仕,学而优则仕。君子之仕也,决非贪图荣华富贵,而是以道劝君(君主),道济天下。官爵权势,君子视之为身外之物;非其道而得之,君子不处也。
三
深入研究古代学与仕的关系,不能不高度重视科举制。对此,学者们存在争议。
1.科举制始于隋、唐,发展于唐、宋、明、清,清末废除,运行了一千三百多年。苏轼指出:朝廷官员“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宋代)出于科举。”(《苏文忠公全集》第五)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繁多,最受重视的是明经、进士两科,尤其是进士科。进士考试,试诗赋、帖经、实务策五道。武则天执政时重在诗赋取士。考试成绩前三名获状元、榜眼、探花的称号。据资料,有唐一代,科举考试登进士科6646人,得人最盛。然而进士科最难考,每一百人中不过取一二名。民谚:“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五十岁考上进士,还算是年轻的。所以,考取进士比作“登龙门”。关于科考,明代规定:先经童试——无论年龄大小,取得功名之前须经童试考取秀才,始有功名。次为乡试——每年八月在省城举行一次,也叫大比。中试者称举人,第一名为解元。然后会试——乡试后第二年春在京城举行,中试者称贡士,第一名为会元。最后是殿试——此乃科举制的最高级别,分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取三人,第一、二、三名称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分别录取若干名。
2.科举制为众多士子开辟了一条从政为官的大路,备受其青睐。他们讲“人生至乐事”有三,其中之一就是“金榜题名时”。一旦科考中第,命运立即改观:“十年人谓好诗章,今日成名出举场”“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韩愈《送陆畅归江南》写道:“举举江南子,名以能诗闻。一来取高第,官佐东宫军。迎妇丞相府,夸映秀士群。鸾鸣桂树间,观者何缤纷。”如果不幸名落孙山,那就下次重来,一考再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可见其吸引力颇大。科举制首先是一种选任官员的制度,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文官考试制度。较之以前的世袭制、察选制、九品中正制等,是一大进步。它第一次撇开了血缘、门第、出身、家世等先赋性因素,而将无法世袭的文化素养或者说学问,作为官员录用的基本标准,从而更新了官员的成分结构,提高了官員的基本素质。从隋唐到明清,多数政治家都是科举中人。科举制为朝廷选拔录用了一大批人才,其中包括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王安石、包拯、欧阳修、苏轼、朱熹、辛弃疾、文天祥、海瑞、张居正、曾国藩、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科举制下应试,除了娼、优、隶、皂、罪户子弟外,一切人原则上均可公开报考。其最大优点是开放、客观、公正,在考试成绩面前人人平等,成绩优良者被录取。即使是最贫贱家庭的子弟,也能通过正常的竞争程序而被择优录取,入朝为官。在明代,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科举制还意味着“学而优则仕”“学者非必仕,而仕者必如学”,从而鼓励朝廷和民间重学。这有利于文明进步。
不可否认,科举制也有缺陷,如一考定终身。苏轼指出:“今夫制策之及等,进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间,而决取终身之富贵。此虽一时之文辞,而未知其临事之能否,则其用之也不已太遽乎?”(《应诏集策略》)加之选士主要看文章才学,士的品德在考场上难以识别,这与任人唯贤的原则存在差距。更大的问题,是考试作弊,包括考生作弊和考官作弊屡禁不绝,历来为人诟病。再说,士子在礼部考试中第后,不会立即委任官职,还需经吏部审查考核,有一段待命补缺时间,甚至有进士出身后二三十年待选的情况发生。礼部可以循私舞弊,吏部更可以循私舞弊,这种现象极大损害了科举制的声誉。
3.在学与仕的关系上,科举制最大之弊(副作用)是使读书学习之目的、意义和内容被扭曲。科举考试的内容和题目,大都依据儒家经典,如五经、四书之类。众多士子,确切地说是考生,他们读圣贤书,只是为了应考中第,结果有意无意地使儒学异化为谋取官位的工具。说得严重些:科举制使儒家仕途通而孔孟之道亡。在这种制度、机制的作用下,形象地说,在科考这根大棒的指挥下,读书人变成赶考者和求仕者,他们心目中只有科举——为科举而读书学习,按照科举的要求选择读什么样的书,根据猜测的若干考试题目花大量精力去搜集资料写文章,包括应试对策之类。从此,“读书→应举→中举→出仕为官”成为人生正途。古圣先贤谆谆教导的“古之学者为己”“君子之学也美其身”“读书志在圣贤”“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等至理名言,被忽略、遗忘、抛弃。朝廷官场和民间流传的是这样一些说教:“读书最为贵,可以登甲科”“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柳屯田劝学文》:“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司马温公劝学歌》:“勉后生,力求诲,投明师,莫自昧。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亚等呼先辈。室中若未结亲姻,自有佳人求匹配。”《王荆公劝学文》:“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书显官人才,书添官人智。”宋真宗《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还有一首广为流传的《劝学歌》:“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达而相天下,穷则善其身。白日莫闲过,青春不再来。窗前勤苦读,马上衣锦还。”明代顾炎武批评说,众多士人“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日知录》)。
4.关于科举制扭曲读书学习之目的、败坏学风政风的问题,古籍中有不少批判性论述。韩愈的《答吕毉山人书》:“方今天下入仕,惟以进士、明经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习熟时俗,工于语言,识形势,善侯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坏,恐不复振起。”苏轼写道:“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工,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拟进士对御试策》)到了明清,主要考八股文,号称“文章举业”,遭人诟病。明代绿竹阁主人《续菜根谭》写道:“读书人,最不齐,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华,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高背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算是百姓朝廷晦气。”《曾国藩家书》写道,科举考试,“此中误人终身多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小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奈何亦以考卷误终身也。”为赶考而写出的诗文,鲜有佳作。“若说考试,则需说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怀,则诗意高矣;若说必以得科名为荣,则意浅矣。”梁启超带有总结性地指出:“宋太祖开馆辑书,而曰‘天下英雄,在吾彀中。明太祖制艺取士,而曰‘天下莫予毒。本朝雍正间有上谕禁满人学八股,而曰‘此等学问,不过笼制汉人。……试观今日所以为教育之道者何如?非舍八股之外无他物乎!八股犹以为未足,而又设为割裂截搭、连上犯下之禁,使人入于其中,销磨数十年之精神,犹未能尽其伎俩,而遑及他事。”(《中国积弱溯源论》)
清人吴敬梓著《儒林外史》。鲁迅称作者“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在书中,作者借迟衡山之口说:“而今读书朋友,只不过讲学举业,若会做几句诗赋,就算雅致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借杜少卿之口说:士大夫们“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书中马纯上(马二先生)对蘧公孙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须做的……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倘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指八股文)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那‘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贤弟,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讲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是什么‘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马二先生对“举业”这番议论,是对科举制透骨的揭底,差不多被所有文学史著作所引用。可以认为,科举制上述缺陷弊端,是它后来被取消的原因。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已经积淀为一种文化传统。至今,它对读书目的、学与仕的关系和学风文风官风以及人生价值观的恶劣影响,并未因其已被废除而消失。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